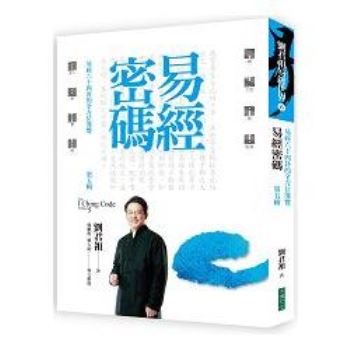黑暗之心—明夷卦第三十六
最深沉痛苦的卦
日出的晉卦之後是日落、黑暗的明夷卦,這是很自然的由盛轉衰、由光明到黑暗的輪替過程。明夷卦是六十四卦中最痛苦的卦,這種痛苦很深沉,而且近乎絕望的漫長,處在這樣的環境中,需要相當的忍耐力,不是短時間就可以紓解的。明夷卦就是這樣一個把人生種種諸如內心的痛苦或周遭的黑暗描繪得很深刻的卦。我們在晉卦一章中就講過,夷是受傷的意思,而且傷得很重。從卦象上看,光明一旦受傷,光明就無從發出,只能藏在下卦,隱藏在內心。
明夷卦明入地中的象跟晉卦的明出地上剛好是一個對照。從外卦、內卦來看,明夷卦的內心很清楚,光明被收斂起來,但是絕對不會放出來,因為外卦是坤,要忍耐、柔順對待,不會直接跟不利的黑暗環境起衝突。光明整個收斂起來,外面是順從的象,這就是明夷卦的特性;代表在亂世痛苦黑暗的時代採取自保的手段,有點像韜光養晦。在明夷卦的〈大象傳〉、〈彖傳〉還有爻辭裡面,都有「晦」的象,就是黑暗。
另外,「夷」字也代表文化程度不高,夷狄之族就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民族,在孔子寫的《春秋》中就很強調夷、夏之分。「夏」是華夏,整個中原比較先進的文化象徵,春秋時代的管仲,向齊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主張,就代表王道跟夷道是有差別的。在明夷卦中,夷是文明的墜落,光明被夷平,形勢很嚴峻。這裡的夷就有平的意思。在明末清初的時候,知識分子讀到《易經》明夷卦,就有深深的國破家亡之痛,總覺得一個過去看不起的東北蠻夷—女真人,那麼少的人口居然把這麼大的一個漢民族建立的明朝帝國給滅了,心裡就有百般痛苦,覺得華夏文明沉淪;尤其是清軍入關之後,要平定天下,剛開始也用了一些比較殘酷的手段,如「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等,給老百姓帶來深深的痛苦,造成一種時代的創傷。此時的文明沉淪了,找不到出路,如長夜漫漫。鄭成功就是在明夷的痛苦中據守臺灣一隅,試圖反清復明,恢復大明江山。以當代或者後代的眼光來看,反清復明到最後純屬虛妄,再到後來清朝也結束了,統治時間也沒有超過明朝。恢復明朝的旗幟雖然在清初此起彼伏,但清朝初年的君王勵精圖治,都很英明,漸漸地也挽回了民心。不像明朝從明成祖、明宣宗之後就沒有一個好皇帝,大多昏庸腐朽。
從長遠歷史的合理性來看,明朝的滅亡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不管怎麼講,明夷就代表著時代的悲痛,所以那個時候有三個很有名的遺老—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也是跟《易經》的淵源很深的。王夫之著有《船山易傳》,這個湖南人堅韌不拔,在反清復明的時代過去之後,回到鄉下,不食清黍,把全部心思完全用在學術上,幾乎將所有的經典都注了一遍。而黃宗羲、顧炎武亦標榜自己是明朝的遺臣,終身抱「明夷之痛」,絕對不跟清朝合作。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就直接從明夷卦的典故而來,剛好又影射了明朝的滅亡。
箕子與文王
我們在講否卦的時候就提到過,《尚書》「洪範九疇」的作者箕子裝瘋賣傻,熬過了那個痛苦的時代,沒有遭受紂王迫害,最後把「洪範九疇」這一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思想口授給周武王。箕子的行為完全是為了保存文明,而不是站在改朝換代的觀點,所以他能夠在最痛苦的明夷時代,為了洪範大法的傳承而活下來。政權可以淪亡,但是文明不可以淪亡,他把這一大法傳給武王之後,便隱居到今天的朝鮮一帶,據說今天在朝鮮還有箕子的墓。明夷卦中也有箕子那個時代的故事,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發伐紂的故事就是明夷卦的劇本。
這一劇本具有永恒的意義。任何一個時代在沒落時期往往會出現昏君或暴君,新興勢力勢必要串聯各方面的力量起來革命。這樣的歷史在中國古代社會往往重演,所以這樣的事情可以作為明夷卦的經典素材,來探討這個時代明夷的原因,然後再讓黑暗變成光明。箕子在當時萬分痛苦的情況下堅持活下來,沒有其他道路可選,只有裝瘋賣傻。在商紂時期,他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像比干一樣剖心而死。或者他可以選擇逃亡,但是他決定留下來,要等待新的朝代到來,把自己保留下來的智慧傳承下去;然後他就出國了,不想留在這個令人傷心的昔日故國,只有乘桴浮於海,遠遁他鄉。這就是明夷卦的故事。這一故事剛好跟《易經》的作者之一周文王因緣很深。《周易》也可以說是革命的學問,一個時代的大行動可以靠《易經》的智慧推翻暴政,建立新朝。
我在坎卦一章中說過,坎卦就是文王的故事,歷盡人生的險關考驗;而箕子經歷的是明夷卦椎心泣血的痛苦。在六十四卦中,明夷卦和坎卦這兩個卦都跟《周易》的重要作者之一周文王那個時代的故事有關。這些故事如果不具有代表性,是不會放在這樣的經典中的,幾千年後這些故事依然有其永恒的教訓。
坎卦第四爻是政治犯很痛苦的象,任何一個政治犯都可以從坎卦第四爻跟第五爻的關係得到一些啟示,所以坎卦雖然跟周文王的關係很深,但它是隱名的,沒有凸顯個人。這可能也是因為經典跟史書不一樣,史書要存真,經書就不需要了,盡可能不提個人,只需把共通的原則講出來。明夷卦則不然,在君位的第五爻直接點出箕子:「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不是紂王,也不是商朝末代的君主,他怎麼能佔據這個君位呢?黃宗羲寫《明夷待訪錄》是在明朝滅亡的時候,他的感覺跟箕子作為一個殷末遺老的痛苦應該是差不多,就只差裝瘋賣傻了。他也想學箕子這個大賢「待訪」,可是沒有辦法,明朝滅亡了,他又不願意仕宦清朝,因為自己一肚子學問,心中卻又覺得應該為文化的長遠發展留下一些東西,於是就有了《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在當時來看,這部書提出反對君主專制、提倡民權是很有震撼力的,對於清末推動辛亥革命也有思想啟迪之功;只是對後來的民主社會來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調子了。而且就學術的角度來說,王夫之的作品又比他深厚多了。
在〈彖傳〉中不但點名了箕子,還點名了文王。這兩者雖屬敵對陣營,但是兩人在那個時代都是「難兄難弟」,文王是被政治迫害,就像坎卦,要吃大兒子的肉醬;箕子則被自己的至親、昏暴的君主紂王所迫害。他們分別在最痛苦、最黑暗、近乎絕望的時代中,堅持內心的信念;用各種不同的應對方法,硬是在那種情況下挺了下來,而且都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文王讓兒子武王完成了除暴安良、改朝換代的大事。箕子所隸屬的殷王朝雖然結束了,但是他為後世留下了「洪範大法」這一偉大的政治遺產,然後自己遠遁他鄉。作為一個活的文化載體,對於後世的朝鮮文化發展來說,他是一個偉大的先驅者。雖然箕子到朝鮮之後,詳細的歷史記載沒有了,但他如今在朝鮮人的心目中,地位無可比擬。
在《易經》中同時出現兩個古代先賢,這是很少見的。晉卦中的康侯雖然確有其人,可是大家對文王、紂王、箕子的熟悉度遠遠超過康侯。所以康侯只是一個象徵,甚至只是代表富強康樂的時代,其分量遠遠不能與明夷卦中直接講箕子、文王可比。經文裡面仍然沒有提到文王,只是爻辭裡面有提到箕子,說明還是很隱諱;可是〈彖傳〉把兩者都提了出來,這一點就很有意思。這樣一來,傳統的講法說伏羲畫八卦之後文王重卦變成六十四卦,完全是白癡的說法。因為夏朝的《易經》—《連山易》、商朝的《易經》—《歸藏易》就已經是六十四卦了。另外,從〈繫辭下傳〉第二章「制器尚象」的十三個文明發展的卦來說,第一卦是離卦,還可以說是八卦,有網罟之象,下面的都是六劃卦;但是有些人依然認為是文王重卦,那麼從伏羲到文王三千年中間的人都是呆子嗎?三千多年的易學史是空白的?所以文王不可能重卦,至於說文王寫卦辭,這倒是不無可能,不過文王也絕對不是第一個,不然怎麼會有夏朝的《易經》和商朝的《易經》呢?但是他可以改寫,依據自己的經驗,加上兒子周公的輔助,到最後寫就《周易》,取代夏、商兩代的《易經》卦爻辭。這一點就像倉頡造字,他只是集大成而已,而不是無中生有一下子造那麼多字出來;前面一定有漫長的過程,源遠流長至最後集大成而進行規範化的處理。
當然,《易經》的發展到最後離不開孔子的功勞,孔子贊易則是進入了所謂的〈易傳〉時代。如果說文王跟寫卦爻辭多少有一些關聯的話,那這個人真的是很謙虛;明夷卦、坎卦都是他親身經歷的,他沒把自己寫進去,只有在〈易傳〉中被孔子點名之後,我們才知道隱藏的男主角不只有箕子,還有一個文王。文王只提了敵對陣營一個可敬的角色—箕子,連紂王都沒有提。但是大家都知道第六爻就是紂王的角色,是如何地讓人失望,而在箕子的痛苦中,我們也可以找到文王的影子,雖然他完全把自己隱藏起來,直到〈彖傳〉才提出這一對受苦受難的「兄弟」。
這一點跟歷史上的文王形象是很接近的。我們常說人心不古,像周文王怎麼講都是歷史上正面的角色,諸如《詩經》、《尚書》、《中庸》、《大學》都在歌頌他,孔子也很佩服他,而且把文王當成文化的象徵。文王是在坎卦中受過歷練的人,也是在明夷卦中受過最大痛苦的人,但他絕對不是浮躁張揚,喜歡凸顯自己,完全是「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因此,千秋萬世有熬過明夷卦這種痛苦的人物,我們要從明夷卦裡面去琢磨,文王如是,箕子亦如是。
另外,明夷卦和晉卦一樣都是遊魂卦,身心非常不安定,明夷卦是坎宮的遊魂卦,用京房八宮卦來講,周文王大概就在坎宮中打轉了。坎卦是本卦,可見坎的遊魂卦—明夷卦多痛苦,無法安身立命,此生不知魂歸何處。
最深沉痛苦的卦
日出的晉卦之後是日落、黑暗的明夷卦,這是很自然的由盛轉衰、由光明到黑暗的輪替過程。明夷卦是六十四卦中最痛苦的卦,這種痛苦很深沉,而且近乎絕望的漫長,處在這樣的環境中,需要相當的忍耐力,不是短時間就可以紓解的。明夷卦就是這樣一個把人生種種諸如內心的痛苦或周遭的黑暗描繪得很深刻的卦。我們在晉卦一章中就講過,夷是受傷的意思,而且傷得很重。從卦象上看,光明一旦受傷,光明就無從發出,只能藏在下卦,隱藏在內心。
明夷卦明入地中的象跟晉卦的明出地上剛好是一個對照。從外卦、內卦來看,明夷卦的內心很清楚,光明被收斂起來,但是絕對不會放出來,因為外卦是坤,要忍耐、柔順對待,不會直接跟不利的黑暗環境起衝突。光明整個收斂起來,外面是順從的象,這就是明夷卦的特性;代表在亂世痛苦黑暗的時代採取自保的手段,有點像韜光養晦。在明夷卦的〈大象傳〉、〈彖傳〉還有爻辭裡面,都有「晦」的象,就是黑暗。
另外,「夷」字也代表文化程度不高,夷狄之族就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民族,在孔子寫的《春秋》中就很強調夷、夏之分。「夏」是華夏,整個中原比較先進的文化象徵,春秋時代的管仲,向齊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主張,就代表王道跟夷道是有差別的。在明夷卦中,夷是文明的墜落,光明被夷平,形勢很嚴峻。這裡的夷就有平的意思。在明末清初的時候,知識分子讀到《易經》明夷卦,就有深深的國破家亡之痛,總覺得一個過去看不起的東北蠻夷—女真人,那麼少的人口居然把這麼大的一個漢民族建立的明朝帝國給滅了,心裡就有百般痛苦,覺得華夏文明沉淪;尤其是清軍入關之後,要平定天下,剛開始也用了一些比較殘酷的手段,如「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等,給老百姓帶來深深的痛苦,造成一種時代的創傷。此時的文明沉淪了,找不到出路,如長夜漫漫。鄭成功就是在明夷的痛苦中據守臺灣一隅,試圖反清復明,恢復大明江山。以當代或者後代的眼光來看,反清復明到最後純屬虛妄,再到後來清朝也結束了,統治時間也沒有超過明朝。恢復明朝的旗幟雖然在清初此起彼伏,但清朝初年的君王勵精圖治,都很英明,漸漸地也挽回了民心。不像明朝從明成祖、明宣宗之後就沒有一個好皇帝,大多昏庸腐朽。
從長遠歷史的合理性來看,明朝的滅亡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不管怎麼講,明夷就代表著時代的悲痛,所以那個時候有三個很有名的遺老—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也是跟《易經》的淵源很深的。王夫之著有《船山易傳》,這個湖南人堅韌不拔,在反清復明的時代過去之後,回到鄉下,不食清黍,把全部心思完全用在學術上,幾乎將所有的經典都注了一遍。而黃宗羲、顧炎武亦標榜自己是明朝的遺臣,終身抱「明夷之痛」,絕對不跟清朝合作。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就直接從明夷卦的典故而來,剛好又影射了明朝的滅亡。
箕子與文王
我們在講否卦的時候就提到過,《尚書》「洪範九疇」的作者箕子裝瘋賣傻,熬過了那個痛苦的時代,沒有遭受紂王迫害,最後把「洪範九疇」這一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思想口授給周武王。箕子的行為完全是為了保存文明,而不是站在改朝換代的觀點,所以他能夠在最痛苦的明夷時代,為了洪範大法的傳承而活下來。政權可以淪亡,但是文明不可以淪亡,他把這一大法傳給武王之後,便隱居到今天的朝鮮一帶,據說今天在朝鮮還有箕子的墓。明夷卦中也有箕子那個時代的故事,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發伐紂的故事就是明夷卦的劇本。
這一劇本具有永恒的意義。任何一個時代在沒落時期往往會出現昏君或暴君,新興勢力勢必要串聯各方面的力量起來革命。這樣的歷史在中國古代社會往往重演,所以這樣的事情可以作為明夷卦的經典素材,來探討這個時代明夷的原因,然後再讓黑暗變成光明。箕子在當時萬分痛苦的情況下堅持活下來,沒有其他道路可選,只有裝瘋賣傻。在商紂時期,他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像比干一樣剖心而死。或者他可以選擇逃亡,但是他決定留下來,要等待新的朝代到來,把自己保留下來的智慧傳承下去;然後他就出國了,不想留在這個令人傷心的昔日故國,只有乘桴浮於海,遠遁他鄉。這就是明夷卦的故事。這一故事剛好跟《易經》的作者之一周文王因緣很深。《周易》也可以說是革命的學問,一個時代的大行動可以靠《易經》的智慧推翻暴政,建立新朝。
我在坎卦一章中說過,坎卦就是文王的故事,歷盡人生的險關考驗;而箕子經歷的是明夷卦椎心泣血的痛苦。在六十四卦中,明夷卦和坎卦這兩個卦都跟《周易》的重要作者之一周文王那個時代的故事有關。這些故事如果不具有代表性,是不會放在這樣的經典中的,幾千年後這些故事依然有其永恒的教訓。
坎卦第四爻是政治犯很痛苦的象,任何一個政治犯都可以從坎卦第四爻跟第五爻的關係得到一些啟示,所以坎卦雖然跟周文王的關係很深,但它是隱名的,沒有凸顯個人。這可能也是因為經典跟史書不一樣,史書要存真,經書就不需要了,盡可能不提個人,只需把共通的原則講出來。明夷卦則不然,在君位的第五爻直接點出箕子:「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不是紂王,也不是商朝末代的君主,他怎麼能佔據這個君位呢?黃宗羲寫《明夷待訪錄》是在明朝滅亡的時候,他的感覺跟箕子作為一個殷末遺老的痛苦應該是差不多,就只差裝瘋賣傻了。他也想學箕子這個大賢「待訪」,可是沒有辦法,明朝滅亡了,他又不願意仕宦清朝,因為自己一肚子學問,心中卻又覺得應該為文化的長遠發展留下一些東西,於是就有了《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在當時來看,這部書提出反對君主專制、提倡民權是很有震撼力的,對於清末推動辛亥革命也有思想啟迪之功;只是對後來的民主社會來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調子了。而且就學術的角度來說,王夫之的作品又比他深厚多了。
在〈彖傳〉中不但點名了箕子,還點名了文王。這兩者雖屬敵對陣營,但是兩人在那個時代都是「難兄難弟」,文王是被政治迫害,就像坎卦,要吃大兒子的肉醬;箕子則被自己的至親、昏暴的君主紂王所迫害。他們分別在最痛苦、最黑暗、近乎絕望的時代中,堅持內心的信念;用各種不同的應對方法,硬是在那種情況下挺了下來,而且都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文王讓兒子武王完成了除暴安良、改朝換代的大事。箕子所隸屬的殷王朝雖然結束了,但是他為後世留下了「洪範大法」這一偉大的政治遺產,然後自己遠遁他鄉。作為一個活的文化載體,對於後世的朝鮮文化發展來說,他是一個偉大的先驅者。雖然箕子到朝鮮之後,詳細的歷史記載沒有了,但他如今在朝鮮人的心目中,地位無可比擬。
在《易經》中同時出現兩個古代先賢,這是很少見的。晉卦中的康侯雖然確有其人,可是大家對文王、紂王、箕子的熟悉度遠遠超過康侯。所以康侯只是一個象徵,甚至只是代表富強康樂的時代,其分量遠遠不能與明夷卦中直接講箕子、文王可比。經文裡面仍然沒有提到文王,只是爻辭裡面有提到箕子,說明還是很隱諱;可是〈彖傳〉把兩者都提了出來,這一點就很有意思。這樣一來,傳統的講法說伏羲畫八卦之後文王重卦變成六十四卦,完全是白癡的說法。因為夏朝的《易經》—《連山易》、商朝的《易經》—《歸藏易》就已經是六十四卦了。另外,從〈繫辭下傳〉第二章「制器尚象」的十三個文明發展的卦來說,第一卦是離卦,還可以說是八卦,有網罟之象,下面的都是六劃卦;但是有些人依然認為是文王重卦,那麼從伏羲到文王三千年中間的人都是呆子嗎?三千多年的易學史是空白的?所以文王不可能重卦,至於說文王寫卦辭,這倒是不無可能,不過文王也絕對不是第一個,不然怎麼會有夏朝的《易經》和商朝的《易經》呢?但是他可以改寫,依據自己的經驗,加上兒子周公的輔助,到最後寫就《周易》,取代夏、商兩代的《易經》卦爻辭。這一點就像倉頡造字,他只是集大成而已,而不是無中生有一下子造那麼多字出來;前面一定有漫長的過程,源遠流長至最後集大成而進行規範化的處理。
當然,《易經》的發展到最後離不開孔子的功勞,孔子贊易則是進入了所謂的〈易傳〉時代。如果說文王跟寫卦爻辭多少有一些關聯的話,那這個人真的是很謙虛;明夷卦、坎卦都是他親身經歷的,他沒把自己寫進去,只有在〈易傳〉中被孔子點名之後,我們才知道隱藏的男主角不只有箕子,還有一個文王。文王只提了敵對陣營一個可敬的角色—箕子,連紂王都沒有提。但是大家都知道第六爻就是紂王的角色,是如何地讓人失望,而在箕子的痛苦中,我們也可以找到文王的影子,雖然他完全把自己隱藏起來,直到〈彖傳〉才提出這一對受苦受難的「兄弟」。
這一點跟歷史上的文王形象是很接近的。我們常說人心不古,像周文王怎麼講都是歷史上正面的角色,諸如《詩經》、《尚書》、《中庸》、《大學》都在歌頌他,孔子也很佩服他,而且把文王當成文化的象徵。文王是在坎卦中受過歷練的人,也是在明夷卦中受過最大痛苦的人,但他絕對不是浮躁張揚,喜歡凸顯自己,完全是「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因此,千秋萬世有熬過明夷卦這種痛苦的人物,我們要從明夷卦裡面去琢磨,文王如是,箕子亦如是。
另外,明夷卦和晉卦一樣都是遊魂卦,身心非常不安定,明夷卦是坎宮的遊魂卦,用京房八宮卦來講,周文王大概就在坎宮中打轉了。坎卦是本卦,可見坎的遊魂卦—明夷卦多痛苦,無法安身立命,此生不知魂歸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