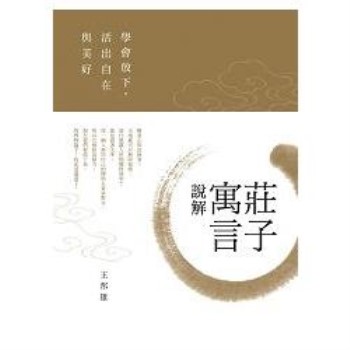存在處境的兩難困局──材與不材
材與不材之間,我們要超離社會「有用」與「無用」的相對區分之上,回到每一個人的自己,那才是我們一生要走的路。
山中木無用,保有天年
這個寓言故事,出自〈山木〉篇,說莊子帶著弟子在山中遊學,看到山頭有一棵枝葉繁茂之極為罕見且等同於神木級的大樹。伐木工人群集於此,他們到山上來物色木材,就圍繞在大樹的周邊,只是觀賞,卻沒有人動手砍伐這棵大樹。
莊子不解,問說你們不是來找好木材嗎?而今,大樹美材就在眼前,為什麼你們「止其旁,而不取呢」?伐木者回答說:「你只要看這棵樹可以長得這麼高、這麼大,你就知道它的材質是『無所可用』的。假定它有用的話,老早被砍掉了。」莊子聽了之後,就隨機指點追隨在身邊的眾弟子說:「你們看看這棵大樹,因為沒有用,才能夠『終其天年』,享有它天生的年歲。」因為不材,沒有什麼用,閩南話說就是「無路用」,沒有用途的意思,像這樣的材質,沒有什麼可以派得上用場。
主人雁不會叫,被殺
這天傍晚,他們從山上下來,到了朋友的家,主人看到好久不見的莊子來了,趕快喊來童子說,殺一隻鵝來接待嘉賓。童子就請教主人說,我們家有兩隻鵝,一隻會叫,一隻不會叫,請問要殺哪一隻?還好鵝聽不懂人的話,不然的話,生死存亡完全繫在主人一念間,而不是由自身做出存在抉擇,一定感覺很不好。
主人回答說:「殺那隻不會叫的!」這個晚上,想必賓主同歡,久別重逢,一定有很多話要說。不過,這一餐一定吃得很悶,這頓鵝肉大餐雖味美,但對於被殺掉的那隻鵝,大家可是一肚子困惑,疑問悶在心裡面,注定消化不良。
第二天清晨,一行人跟主人告辭,離開主人家。大概沒走幾步路吧,學生就迫不及待地問說:老師,問題來了,昨天山中的木,是因為沒有用,而保有它的天年;今天,主人家的鵝,卻因為不會叫而被殺。你不是教導我們,沒有用是養生之道嗎?可以存全生命嗎?怎麼這隻鵝反而因為不會叫而被殺呢?老師的教言,立即被推翻了,大家忍不住要為這隻鵝抱屈。樹無用,可以長成大樹;怎麼鵝不會叫,反而中道夭呢?當下學生就請教老師:假如是你,你要怎麼自處?莊子答道:我就處在山中木跟主人雁之間。材與不材之間的兩難
山中的那棵木,跟主人家的鵝,二者之間,你要做出怎麼樣的抉擇?莊子當然很難給出答案,只好笑著回答:我將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你要怎麼樣面對這樣的人生困局?這一存在處境,已落在兩難之中;且雖屬兩難,總得做出抉擇。所謂「材與不材之間」,「材」是有用,「不材」是無用,說是有用,就不會是無用;說是無用,就不會是有用。莊子卻說:我處在有用與無用之間,這是戲答的遊戲文字,顯現莊子的幽默感。他的意思是說,我是山中木的時候,我當然會以無用的姿態現身,因為無用,可以保有天年,長成一棵大樹;當我是主人家的鵝,那本人就得猛叫,因為不會叫,就會有被殺的危險。
為什麼我說這是一段遊戲的文字,因為你的人生教言,在現實裡面出現了難以兩全的矛盾現象。所以,莊子只好用遊戲的文字來回答。當我是山中木時,我無用;而我是主人雁時,我就大叫。這樣的話,我就可以長成,而不會被宰殺。這終究是遊戲的文字,因為你猛叫,也沒有保證。諸位試想一下,萬一那一天清晨,主人家在酣睡中,被一陣鵝聲吵醒的話,那天傍晚給出的答案,可能就大不同了。他不會說殺那隻不會叫的,反而會說殺那隻亂叫的。所以,你就是會叫,也不見得可以存全自己,這叫兩難。在叫與不叫之間,在材與不材之間,人生面對的是一個兩難的困境。
回歸天道本德,與天地同遊
所以,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不是標準答案,不是究竟解答,只是莊子一時的權宜之言,來回應學生的質疑。學生的問難,是大有道理的,你教導我們說,讓自己無用,可以保有自身,那不是百分百,那沒有必然的保證。莊子最後才說出他真正想要說的話,他說,人生只能「乘道德而浮遊」。道德是道家義的道德,「道」是天道,「德」是天真;從源頭來說,是天道,從生命來說,是天真。天道生萬物,天道內在於萬物的德,就是每一個人都天生而有的本德天真,老子的書就以「道德經」為名,乘道德而浮遊,意謂跟天地同在同行,無何有之鄉,就是道德之鄉。道家的道德跟儒家的道德,指涉的義理內涵有異,儒家的理解,自覺有心才是道德,道家的智慧,無心天真才是道德。一樣講道德,孔子講「志於道,據於德」,又說「道之以德」。你以為只有老子講道德嗎?孔子最重要的觀念,就在道德,而且還連結起來說,要以德來引導天下人民。在「志於道,據於德」之後,又講「依於仁」,他的「德」,跟他的「道」,是通過「仁心」彰顯出來的。儒家的道德,以不安、不忍的仁心、愛心作為依據。由仁心而貞定德行,再由德行而開出道路。人生的道路,是由德行來,而德行由仁心顯發而來,你沒有德行、仁心,你的德,行不出來,你的道,也開不出來。
「仁」有心負累,「不仁」無心自在
老子的《道德經》,是講「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仁」是仁心、愛心;老子講「不仁」是無心,因為你有愛心,你的心會起執著,愛會讓我們高貴,愛也會讓我們傲慢。道家一眼就看到心執著「愛」的後遺症,所以不仁、無心,就是無掉心知的執著。很多人在「愛」裡面受苦受難,就是因為給出「愛」的人,太神聖了,太偉大了;而被愛的人,就好像失去自主權一樣,相對之下,顯得卑微。大男人主義的「大」,就從這邊來的,因為小女子要靠男人的照顧與疼惜。
此所以老莊的「德」跟「道」,是通過「不仁」來講的。「不仁」是無心,解消你愛的執著,放下愛的高貴,不要那麼神聖,不要那麼偉大,這樣才會尊重我們所愛的人,給出對等的尊嚴。「乘道德而浮遊」,就是跟天地自然同在同行,不是落在人間社會的利害得失來評估。你要超離人間相對的是非,相對的美醜、善惡與成敗、得失;所謂材與不材之間,意謂超離在人間材與不材的二分之上,而跟天地自然一體並行,這時候你才真正解消了這一存在處境的兩難困局。
超離人間街頭有用無用的價值二分
不然的話,你說什麼話,都可能得罪人,我說這一邊的演講比較值得聽,那一邊的文物展不一定值得看,這不就得罪了展覽的主辦單位嗎?行走人間,都在相對中,那邊大排長龍,這邊還有空位,然而這是活的經典,不是死的文物,這是我們的幾千年,不僅是世界古文明之一。你一定有立場,你一定有角度,你一定有觀點,在人我相對之間,你的觀點就不可能是全面的觀照。所以,我們只好超離在人間的成敗榮辱,與利害得失之上,這就是乘道德而浮遊的意思。搭計程車的時候,有位司機先生一路跟我聊天,他問我:你覺得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怎麼樣?我說很好哇!只是排名沒有像台大、清華、交大那麼高而已,也是很好的大學。他說:我女兒在這邊唸研究所。我問唸什麼研究所?他說:唸土木研究所;又說:她也考上成大,我勸她唸台北這邊。我們總是要講真心話,我說:當然啦!唸這邊也有道理,因為離家近,就讀書情境來說,有家人的親情作為支柱,讀書才不會那麼寂寞,感覺孤軍奮鬥。不過,我要老實說一句話,成大可能比較好,比較開闊,比較有傳統,我還是忍不住說了這句話。顯然我的老莊不到家,還是用儒家來回應,因為面對天下父母心,這個時候我就很難用老莊說,直以儒家對應。
人間的熱門可能是我的冷門
像這樣,你到底是要唸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還是唸國立成功大學?一個在台北,一個在台南,一個可以跟家裡連線,一個校園比較有傳統,人生立刻要面對一個選擇,你不可能兩邊都唸。就我們當前來說的話,最直接面對的問題是,你是要唸人文,還是唸工商?或是唸法政?現在法律系、政治系當紅,大家的思考是什麼科系最熱門,工商是熱門,那文理相對冷門。學生或兒女在填寫志願的時候,你會說當然要填熱門。現在的青少年比較不一樣,比較有主見,他可以唸醫科,但是他不要,他要唸動物系。分數可以填到某一個醫學院醫科,但他選擇的是台大動物系,而且很多同學都是如此。看起來醫科最熱門,但他們想唸動物系,也就是生命科學系。
是要依父母親的出路思考,還是依兒女的才氣志趣?是現在正熱門,還是未來較有發展性?因為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現在的熱門,三十年後可能轉成冷門;現在的冷門,或許三十年後轉為大熱門,這沒有必然性。就像舊金山的矽谷,是我們新竹科學園區取經效法的範本,如今已經呈現沒落的蕭條景象,二十萬人離開舊金山,南下到洛杉磯,原因是公司關門或裁員,不是最尖端的嗎?一片榮景嗎?還是靠不住。所以,在熱門、冷門之間,什麼是我們要走的路?莊子告訴我們,你不要管社會的熱門或冷門,你只要回到你的天真,你的道德之鄉,「乘道德而浮遊」,回到你自己的感覺,回到你自己的喜歡。人間的冷門可能是我的熱門
你喜歡,你一生才會守在那裡,才會有成就。只要我真的喜歡,就算是社會的冷門,也會是我一生路上獨一的熱門。所以,在材與不材之間,我們要超離社會「有用」與「無用」的相對區分之上,回到每一個人的自己,你的性向,你的才情,你的遺傳基因,你一路走過來的感覺與喜歡,那才是我們一生要走的路。人人走出自己想要走的路,老子說是「常道」;人人活出自己想要的內涵,老子說是「常名」。走出自己想要走的路,活出自己想要的內涵,這才是每一個人都要做出的存在抉擇,而不是搖擺在有用、無用之間,跟著社會的流行、時髦走,而在那裡舉棋不定。社會流行什麼,自己就跟著時尚走,那就是存在的迷失與價值的失落。
決定自己一生要走的路,對自己真誠,對自己負責,千萬不要搖擺浮沉,我喜歡文史,我一生就走文史的路,不要一面對工商,就覺得自己欠缺、匱乏,好像輸掉一片大好江山。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人人頭上一片天,我們有自己的天空,這個叫「乘道德而浮遊」。我們面對存在處境的兩難困局之間,你到底要有用,還是無用?無用可以保全,還是有用可以存活?都靠不住,都是一時不定的。既然是相對,當然就沒有保證;那我們就回歸自己的性向才情,走自己理想抱負的路,通過儒家的話來講,這叫當仁不讓,或義無反顧。就道家來說,是歸根復命,歸根是回歸天道的根源,復命是回歸本德的天真,也就是「然」從自己來的「自然」。你要疼惜自己的才情氣魄,還是要看社會的流行時髦往哪邊走?如果隨波逐流,流失的可能就是自己美好的一生。
不改的人可以不殆
實則,我的喜歡,就是唯一的熱門,我要活出自己,走出自己想要走的路,活出自己想要的內涵。這樣的人,就是老子所描述之天道的存在性格,一是「獨立而不改」,二是「周行而不殆」。我走我的路,我自己立,就是獨立;我一生走我自己的路,我不改初衷,不改本色,不管人生的路走到哪裡,我永遠是我。只有獨立的人,才可以周行。也只有不改本懷初衷的人,才可能不殆。像這樣的人,就可以從存在處境的兩難困局中走出來。不是人間社會的冷門或熱門,而是我自己的門,獨一無二的門;這是莊子在〈山木〉篇所拋出的人生議題。你到底要走哪一條路?最基本的區分,就是有用跟無用,熱門跟冷門,有出路或沒有出路;莊子要我們超離在人間社會「用」的標準之上。青少年的分數主義,或大人世界的功利主義,主義是「義」要以何為「主」?也就是執定「用」的標準。學生分數考得很高,這個學生很有用;那個人獲利甚豐,所以他很有用,且大大的有用。如果表現不符合這一「用」的標準,就會被判為無用。有沒有想過,每一個人的成長背景不同,機遇也不同,此中有人物的「命」,與人間的「緣」。
無掉人間社會的小用,而活出自家生命的大用
我們來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成長環境,我們有各自不同的性向才情,你怎麼可以用同樣的標準來評估判定呢?我們要擺脫民間世俗的標準,不通過這個「用」的標準,來論定自身是有用,還是無用。莊子講「無用之用,是為大用」,就是我無掉社會「用」的標準,擺脫了社會「用」的標準對我的拘限與羈絆,就是所謂的無用。「無」掉了社會的「用」之後,就能顯現我自家的用,這才是我生命自身的大用。
「無用」,不是沒有用,只是不願意接受社會流行的價值標準,而回到我自己的美好,那是「無用」之後所顯發的「用」。那個「無」當動詞,無掉世俗流行的用,而回到人人自家的用。這樣的用,讓每一個人都有自家的用,才是大用;不然的話,少數人有用,大多數人無用,那是小用。大用就是人人走出自己的路,人人活出自身的用,而不是每個人在街頭漂流,而失落自身的用。「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無用」是鬆綁,不以「用」的標準綁死人間每一個人,而讓每一個人活出自己本身的用。「大」在人人皆有用,人人都是「然」從自己來。
常道常名的放開自得
老子講「無為」,莊子講「無用」。老子的政治智慧,是身在政治的殿堂,知識分子擔負治國平天下的重任,你要「無心而為」;莊子的人生智慧,更貼近民間世俗,對每一個人來說,要無掉社會「用」的標準,也無掉這一執著標準對我們生命的壓迫。不然的話,人間多少人,一生自責,在分數主義下,在功利主義下,總覺得自己輸掉了,那個是可道、可名的認可規定,而不是常道、常名的放開自得。常道、常名就是回到我自己,走我的路,活出我的內涵,我不接受社會的分數主義跟功利主義的宰制。你說道家思想很消極嗎?但你聽我講話的語氣,好像英雄豪傑說出的話吧!道德是天道人德,活出自己的真實美好,這不是人間最積極的嗎?跟著人家跑,流落天涯,而痛失自己,那才消極。這是在材與不材之間,做一個存在的抉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戲答背後藏有深意,看似搖擺在二者之間,實則超越在二者之上。莊子也說「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倘若一直在二者之間搖擺,在社會流行風向之間擺盪,社會風潮一直在轉變,而你老被牽引而定不住自己,成為生命最大的負累。最後,會發現失落了自己的獨特風格與品味,甚至不曉得自己到底是誰了。
材與不材之間,我們要超離社會「有用」與「無用」的相對區分之上,回到每一個人的自己,那才是我們一生要走的路。
山中木無用,保有天年
這個寓言故事,出自〈山木〉篇,說莊子帶著弟子在山中遊學,看到山頭有一棵枝葉繁茂之極為罕見且等同於神木級的大樹。伐木工人群集於此,他們到山上來物色木材,就圍繞在大樹的周邊,只是觀賞,卻沒有人動手砍伐這棵大樹。
莊子不解,問說你們不是來找好木材嗎?而今,大樹美材就在眼前,為什麼你們「止其旁,而不取呢」?伐木者回答說:「你只要看這棵樹可以長得這麼高、這麼大,你就知道它的材質是『無所可用』的。假定它有用的話,老早被砍掉了。」莊子聽了之後,就隨機指點追隨在身邊的眾弟子說:「你們看看這棵大樹,因為沒有用,才能夠『終其天年』,享有它天生的年歲。」因為不材,沒有什麼用,閩南話說就是「無路用」,沒有用途的意思,像這樣的材質,沒有什麼可以派得上用場。
主人雁不會叫,被殺
這天傍晚,他們從山上下來,到了朋友的家,主人看到好久不見的莊子來了,趕快喊來童子說,殺一隻鵝來接待嘉賓。童子就請教主人說,我們家有兩隻鵝,一隻會叫,一隻不會叫,請問要殺哪一隻?還好鵝聽不懂人的話,不然的話,生死存亡完全繫在主人一念間,而不是由自身做出存在抉擇,一定感覺很不好。
主人回答說:「殺那隻不會叫的!」這個晚上,想必賓主同歡,久別重逢,一定有很多話要說。不過,這一餐一定吃得很悶,這頓鵝肉大餐雖味美,但對於被殺掉的那隻鵝,大家可是一肚子困惑,疑問悶在心裡面,注定消化不良。
第二天清晨,一行人跟主人告辭,離開主人家。大概沒走幾步路吧,學生就迫不及待地問說:老師,問題來了,昨天山中的木,是因為沒有用,而保有它的天年;今天,主人家的鵝,卻因為不會叫而被殺。你不是教導我們,沒有用是養生之道嗎?可以存全生命嗎?怎麼這隻鵝反而因為不會叫而被殺呢?老師的教言,立即被推翻了,大家忍不住要為這隻鵝抱屈。樹無用,可以長成大樹;怎麼鵝不會叫,反而中道夭呢?當下學生就請教老師:假如是你,你要怎麼自處?莊子答道:我就處在山中木跟主人雁之間。材與不材之間的兩難
山中的那棵木,跟主人家的鵝,二者之間,你要做出怎麼樣的抉擇?莊子當然很難給出答案,只好笑著回答:我將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你要怎麼樣面對這樣的人生困局?這一存在處境,已落在兩難之中;且雖屬兩難,總得做出抉擇。所謂「材與不材之間」,「材」是有用,「不材」是無用,說是有用,就不會是無用;說是無用,就不會是有用。莊子卻說:我處在有用與無用之間,這是戲答的遊戲文字,顯現莊子的幽默感。他的意思是說,我是山中木的時候,我當然會以無用的姿態現身,因為無用,可以保有天年,長成一棵大樹;當我是主人家的鵝,那本人就得猛叫,因為不會叫,就會有被殺的危險。
為什麼我說這是一段遊戲的文字,因為你的人生教言,在現實裡面出現了難以兩全的矛盾現象。所以,莊子只好用遊戲的文字來回答。當我是山中木時,我無用;而我是主人雁時,我就大叫。這樣的話,我就可以長成,而不會被宰殺。這終究是遊戲的文字,因為你猛叫,也沒有保證。諸位試想一下,萬一那一天清晨,主人家在酣睡中,被一陣鵝聲吵醒的話,那天傍晚給出的答案,可能就大不同了。他不會說殺那隻不會叫的,反而會說殺那隻亂叫的。所以,你就是會叫,也不見得可以存全自己,這叫兩難。在叫與不叫之間,在材與不材之間,人生面對的是一個兩難的困境。
回歸天道本德,與天地同遊
所以,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不是標準答案,不是究竟解答,只是莊子一時的權宜之言,來回應學生的質疑。學生的問難,是大有道理的,你教導我們說,讓自己無用,可以保有自身,那不是百分百,那沒有必然的保證。莊子最後才說出他真正想要說的話,他說,人生只能「乘道德而浮遊」。道德是道家義的道德,「道」是天道,「德」是天真;從源頭來說,是天道,從生命來說,是天真。天道生萬物,天道內在於萬物的德,就是每一個人都天生而有的本德天真,老子的書就以「道德經」為名,乘道德而浮遊,意謂跟天地同在同行,無何有之鄉,就是道德之鄉。道家的道德跟儒家的道德,指涉的義理內涵有異,儒家的理解,自覺有心才是道德,道家的智慧,無心天真才是道德。一樣講道德,孔子講「志於道,據於德」,又說「道之以德」。你以為只有老子講道德嗎?孔子最重要的觀念,就在道德,而且還連結起來說,要以德來引導天下人民。在「志於道,據於德」之後,又講「依於仁」,他的「德」,跟他的「道」,是通過「仁心」彰顯出來的。儒家的道德,以不安、不忍的仁心、愛心作為依據。由仁心而貞定德行,再由德行而開出道路。人生的道路,是由德行來,而德行由仁心顯發而來,你沒有德行、仁心,你的德,行不出來,你的道,也開不出來。
「仁」有心負累,「不仁」無心自在
老子的《道德經》,是講「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仁」是仁心、愛心;老子講「不仁」是無心,因為你有愛心,你的心會起執著,愛會讓我們高貴,愛也會讓我們傲慢。道家一眼就看到心執著「愛」的後遺症,所以不仁、無心,就是無掉心知的執著。很多人在「愛」裡面受苦受難,就是因為給出「愛」的人,太神聖了,太偉大了;而被愛的人,就好像失去自主權一樣,相對之下,顯得卑微。大男人主義的「大」,就從這邊來的,因為小女子要靠男人的照顧與疼惜。
此所以老莊的「德」跟「道」,是通過「不仁」來講的。「不仁」是無心,解消你愛的執著,放下愛的高貴,不要那麼神聖,不要那麼偉大,這樣才會尊重我們所愛的人,給出對等的尊嚴。「乘道德而浮遊」,就是跟天地自然同在同行,不是落在人間社會的利害得失來評估。你要超離人間相對的是非,相對的美醜、善惡與成敗、得失;所謂材與不材之間,意謂超離在人間材與不材的二分之上,而跟天地自然一體並行,這時候你才真正解消了這一存在處境的兩難困局。
超離人間街頭有用無用的價值二分
不然的話,你說什麼話,都可能得罪人,我說這一邊的演講比較值得聽,那一邊的文物展不一定值得看,這不就得罪了展覽的主辦單位嗎?行走人間,都在相對中,那邊大排長龍,這邊還有空位,然而這是活的經典,不是死的文物,這是我們的幾千年,不僅是世界古文明之一。你一定有立場,你一定有角度,你一定有觀點,在人我相對之間,你的觀點就不可能是全面的觀照。所以,我們只好超離在人間的成敗榮辱,與利害得失之上,這就是乘道德而浮遊的意思。搭計程車的時候,有位司機先生一路跟我聊天,他問我:你覺得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怎麼樣?我說很好哇!只是排名沒有像台大、清華、交大那麼高而已,也是很好的大學。他說:我女兒在這邊唸研究所。我問唸什麼研究所?他說:唸土木研究所;又說:她也考上成大,我勸她唸台北這邊。我們總是要講真心話,我說:當然啦!唸這邊也有道理,因為離家近,就讀書情境來說,有家人的親情作為支柱,讀書才不會那麼寂寞,感覺孤軍奮鬥。不過,我要老實說一句話,成大可能比較好,比較開闊,比較有傳統,我還是忍不住說了這句話。顯然我的老莊不到家,還是用儒家來回應,因為面對天下父母心,這個時候我就很難用老莊說,直以儒家對應。
人間的熱門可能是我的冷門
像這樣,你到底是要唸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還是唸國立成功大學?一個在台北,一個在台南,一個可以跟家裡連線,一個校園比較有傳統,人生立刻要面對一個選擇,你不可能兩邊都唸。就我們當前來說的話,最直接面對的問題是,你是要唸人文,還是唸工商?或是唸法政?現在法律系、政治系當紅,大家的思考是什麼科系最熱門,工商是熱門,那文理相對冷門。學生或兒女在填寫志願的時候,你會說當然要填熱門。現在的青少年比較不一樣,比較有主見,他可以唸醫科,但是他不要,他要唸動物系。分數可以填到某一個醫學院醫科,但他選擇的是台大動物系,而且很多同學都是如此。看起來醫科最熱門,但他們想唸動物系,也就是生命科學系。
是要依父母親的出路思考,還是依兒女的才氣志趣?是現在正熱門,還是未來較有發展性?因為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現在的熱門,三十年後可能轉成冷門;現在的冷門,或許三十年後轉為大熱門,這沒有必然性。就像舊金山的矽谷,是我們新竹科學園區取經效法的範本,如今已經呈現沒落的蕭條景象,二十萬人離開舊金山,南下到洛杉磯,原因是公司關門或裁員,不是最尖端的嗎?一片榮景嗎?還是靠不住。所以,在熱門、冷門之間,什麼是我們要走的路?莊子告訴我們,你不要管社會的熱門或冷門,你只要回到你的天真,你的道德之鄉,「乘道德而浮遊」,回到你自己的感覺,回到你自己的喜歡。人間的冷門可能是我的熱門
你喜歡,你一生才會守在那裡,才會有成就。只要我真的喜歡,就算是社會的冷門,也會是我一生路上獨一的熱門。所以,在材與不材之間,我們要超離社會「有用」與「無用」的相對區分之上,回到每一個人的自己,你的性向,你的才情,你的遺傳基因,你一路走過來的感覺與喜歡,那才是我們一生要走的路。人人走出自己想要走的路,老子說是「常道」;人人活出自己想要的內涵,老子說是「常名」。走出自己想要走的路,活出自己想要的內涵,這才是每一個人都要做出的存在抉擇,而不是搖擺在有用、無用之間,跟著社會的流行、時髦走,而在那裡舉棋不定。社會流行什麼,自己就跟著時尚走,那就是存在的迷失與價值的失落。
決定自己一生要走的路,對自己真誠,對自己負責,千萬不要搖擺浮沉,我喜歡文史,我一生就走文史的路,不要一面對工商,就覺得自己欠缺、匱乏,好像輸掉一片大好江山。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人人頭上一片天,我們有自己的天空,這個叫「乘道德而浮遊」。我們面對存在處境的兩難困局之間,你到底要有用,還是無用?無用可以保全,還是有用可以存活?都靠不住,都是一時不定的。既然是相對,當然就沒有保證;那我們就回歸自己的性向才情,走自己理想抱負的路,通過儒家的話來講,這叫當仁不讓,或義無反顧。就道家來說,是歸根復命,歸根是回歸天道的根源,復命是回歸本德的天真,也就是「然」從自己來的「自然」。你要疼惜自己的才情氣魄,還是要看社會的流行時髦往哪邊走?如果隨波逐流,流失的可能就是自己美好的一生。
不改的人可以不殆
實則,我的喜歡,就是唯一的熱門,我要活出自己,走出自己想要走的路,活出自己想要的內涵。這樣的人,就是老子所描述之天道的存在性格,一是「獨立而不改」,二是「周行而不殆」。我走我的路,我自己立,就是獨立;我一生走我自己的路,我不改初衷,不改本色,不管人生的路走到哪裡,我永遠是我。只有獨立的人,才可以周行。也只有不改本懷初衷的人,才可能不殆。像這樣的人,就可以從存在處境的兩難困局中走出來。不是人間社會的冷門或熱門,而是我自己的門,獨一無二的門;這是莊子在〈山木〉篇所拋出的人生議題。你到底要走哪一條路?最基本的區分,就是有用跟無用,熱門跟冷門,有出路或沒有出路;莊子要我們超離在人間社會「用」的標準之上。青少年的分數主義,或大人世界的功利主義,主義是「義」要以何為「主」?也就是執定「用」的標準。學生分數考得很高,這個學生很有用;那個人獲利甚豐,所以他很有用,且大大的有用。如果表現不符合這一「用」的標準,就會被判為無用。有沒有想過,每一個人的成長背景不同,機遇也不同,此中有人物的「命」,與人間的「緣」。
無掉人間社會的小用,而活出自家生命的大用
我們來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成長環境,我們有各自不同的性向才情,你怎麼可以用同樣的標準來評估判定呢?我們要擺脫民間世俗的標準,不通過這個「用」的標準,來論定自身是有用,還是無用。莊子講「無用之用,是為大用」,就是我無掉社會「用」的標準,擺脫了社會「用」的標準對我的拘限與羈絆,就是所謂的無用。「無」掉了社會的「用」之後,就能顯現我自家的用,這才是我生命自身的大用。
「無用」,不是沒有用,只是不願意接受社會流行的價值標準,而回到我自己的美好,那是「無用」之後所顯發的「用」。那個「無」當動詞,無掉世俗流行的用,而回到人人自家的用。這樣的用,讓每一個人都有自家的用,才是大用;不然的話,少數人有用,大多數人無用,那是小用。大用就是人人走出自己的路,人人活出自身的用,而不是每個人在街頭漂流,而失落自身的用。「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無用」是鬆綁,不以「用」的標準綁死人間每一個人,而讓每一個人活出自己本身的用。「大」在人人皆有用,人人都是「然」從自己來。
常道常名的放開自得
老子講「無為」,莊子講「無用」。老子的政治智慧,是身在政治的殿堂,知識分子擔負治國平天下的重任,你要「無心而為」;莊子的人生智慧,更貼近民間世俗,對每一個人來說,要無掉社會「用」的標準,也無掉這一執著標準對我們生命的壓迫。不然的話,人間多少人,一生自責,在分數主義下,在功利主義下,總覺得自己輸掉了,那個是可道、可名的認可規定,而不是常道、常名的放開自得。常道、常名就是回到我自己,走我的路,活出我的內涵,我不接受社會的分數主義跟功利主義的宰制。你說道家思想很消極嗎?但你聽我講話的語氣,好像英雄豪傑說出的話吧!道德是天道人德,活出自己的真實美好,這不是人間最積極的嗎?跟著人家跑,流落天涯,而痛失自己,那才消極。這是在材與不材之間,做一個存在的抉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戲答背後藏有深意,看似搖擺在二者之間,實則超越在二者之上。莊子也說「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倘若一直在二者之間搖擺,在社會流行風向之間擺盪,社會風潮一直在轉變,而你老被牽引而定不住自己,成為生命最大的負累。最後,會發現失落了自己的獨特風格與品味,甚至不曉得自己到底是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