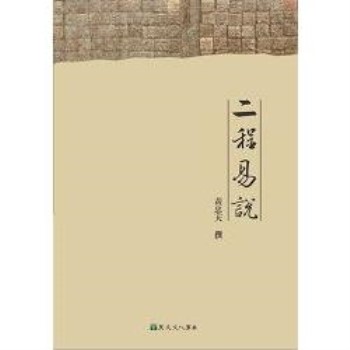一、通論
(一)論陰陽動靜升降消息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卻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腳踏處便溼,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強齊之,豈能齊也?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 「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概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
曰: 「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 「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
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天地動靜之理,天圜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 「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故曰動靜一源。
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 「試喻之。」
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
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伊川與和靖 論義命。和靖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奚以命為?」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靖曰: 「說著靜,便多一箇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靖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冬至一陽生,卻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一)論陰陽動靜升降消息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卻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腳踏處便溼,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強齊之,豈能齊也?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 「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概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
曰: 「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 「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
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天地動靜之理,天圜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 「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故曰動靜一源。
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 「試喻之。」
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
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伊川與和靖 論義命。和靖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奚以命為?」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靖曰: 「說著靜,便多一箇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靖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冬至一陽生,卻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