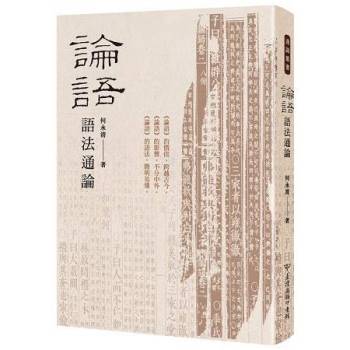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作三節,第一節敘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第二節述研究的範圍與限制,第三節言研究方法。
第二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論語》是儒學的要籍,也是一部流傳廣遠的儒家經典,宋代之後列入「十三經」,也是《四書》之一,更是現代人為人處世的道德依據。這部書不僅流行於華夏,也深深影響韓國、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儒家文化浸潤的邦域,成為生活指針。
中國文化以儒家為中心,要了解儒家思想,必須從記載孔子語錄的《論語》入手,故柳詒徵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 漆緒邦說:「孔子的言論,遠不止於《論語》所記,但是應當指出,凡所記述,大都精粹扼要,頗能反映恐子的思想、學說、精神風貌,便於誦習流傳。」 因此探討《論語》為研究孔子思想、言行和中國文化的根本。
其次,從漢語發展來看,《論語》保留了先秦的一些書面或口頭語料,栩栩如生,是古漢語語法的活化石,無論是它的構詞或造句,對於先秦與後代的散文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學術價值不言而喻。
我國當代一些名人、學者諄諄告訴我們,研讀古籍要先重視「文法」,讀書才會有大用。舉其犖犖大者,孫中山說:「欲知文章之所當然,則必自文法之學始;欲知其所以然,則必自文理之學始。文法之學為何?卽西人之『葛郎瑪』也,教人分字類詞,聯詞造句而達意志者也。」, 楊樹達說:「凡讀書有二事焉:一曰明訓詁,二曰通文法。訓詁治其實,文法求其虛。」, 胡適曾對胡頌平說:「活的語言是有文法的。我的文章寫通的原因,是從《論語》、《孟子》裡讀通的。你應該熟讀《論語》,把《論語》讀得熟透了,文章自會寫通的。」, 黃慶萱說:「文法學的學習,可以使學生知道怎樣構成通順的說辭或文章。」, 黃錦鋐說:文法與修辭,是國文教學中的兩大工具,因為中國文章的組織,很多模稜兩可的地方,很容易望文而生義,若不講求文法,則必扞格而不通。古人雖無文法,然學童入學,一年視離經辨志。離經,卽離析經書的義理,能夠離析經書的義理(見《禮解疏》),也就是能分析經書的文法,雖無文法之名,卻有文法之實,古人所謂「句讀」、「章句之學」,實卽文法的分析,知道什麼是主語,什麼是動詞,什麼是賓語。
從諸家的這些看法,可知精通文法對於研讀國學的重要性。探討《論語》的語法,除了有助於了解上古漢語的語法的一些現象之外,並能夠幫助我們深究古文的精義。林傳甲說:
《論語》章法,多一句二句成章者,周秦諸子,不如此之簡,一便也;文理平易近人,無奇字難解,二便也;今塾師已能講解,童子已能熟誦,三便也。變《論語》為初學文法書,亦隨時通變之一端也。
林傳甲所說「初學文法」,雖然言及初學古文的章法,其實與學習古漢語的句法,息息相關;許世瑛也說:「文言文的結構方式,有很多地方和現代國語的結構方式不同,如果不研究中國古代文言文的文法,又如何能理解文言文,更如何能寫通文言文。」 ,可見熟悉《論語》的語法,對探悉古代典籍的構詞、造句規律、學習古文等亦有莫大的裨益。
專書語法的描述,對於衷心於語言研究的筆者,是件責無旁貸的工作。植基於《論語》的高度價值,希冀藉語法的知識輔助閱讀《論語》,與個人多年來研究漢語語法的興趣與專業知能這些動機,筆者遂探討《論語》一書的語法,希冀能達到下列幾項研究目的:
第一、 敘述《論語》的實詞、虛詞的種類及其分類,各個詞類的語法特點。
第二、 了解《論語》單詞及各種構詞方式,並統計出它們所占的百分比例。
第三、 分析《論語》的各種句型與特殊句法(含倒置、外位、被動的表示法)的語法規律。
第四、 系統地了解《論語》的語法特點及其語法體系。
第五、 敘述《論語》的價值與影響。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論語》為範疇,採用清代阮元校勘《論語注疏》的二十卷本《論語》為研究的文本,探討其中語句語法現象。囿於篇幅限制,除了重要的關鍵點之外,同樣的語法舉其部分實例為例,以免篇幅冗贅。各章節的號碼係採用楊伯峻《論語譯注》的編號,以便利檢索,此係目前多數研究者所用,故筆者遵循它。
西方所謂的Grammar,目前或譯為「語法」、「文法」,其意義均相同,馬建忠說:「葛郎瑪者,音原希臘,訓曰字式,猶云學文之程式也。」, 王力說:「Grammar,在希臘文原意是『字學』。」, 楊樹達說:「語言文字之初起,其組織蓋亦錯互而不醇。迨積年既久,隨時改善,至於約定俗成,則形成共遵之規律而不可畔越,後人紬繹其規律而敘述之,則所謂文法是也。」 是知「語法」(文法)指根據語料所歸納出來的語言規律,包含構詞及造句的各種法則,這是科學化處理古代文獻的方式。
大抵來說,《論語》為上古書面語的一部分,它保留的口語文獻也有其限度,若認為要透過《論語》來全面了解古代語言的全貌,這也是不可能的事,這是研究上的先天限制。其次,《論語》為早期的語錄體,以對話為主,敘事為輔,在詞法的研究上比較有可觀的成果,而在單句及複句的類型上,就相對顯得薄弱,這是研究者共同面臨的另一種限制。即便是如此,筆者仍覃精竭力,運用下述七種研究方法,補足前賢零星片段研究的不足,希冀將《論語》語法的研究成果作有系統、全貌的呈現。
本章分作三節,第一節敘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第二節述研究的範圍與限制,第三節言研究方法。
第二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論語》是儒學的要籍,也是一部流傳廣遠的儒家經典,宋代之後列入「十三經」,也是《四書》之一,更是現代人為人處世的道德依據。這部書不僅流行於華夏,也深深影響韓國、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儒家文化浸潤的邦域,成為生活指針。
中國文化以儒家為中心,要了解儒家思想,必須從記載孔子語錄的《論語》入手,故柳詒徵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 漆緒邦說:「孔子的言論,遠不止於《論語》所記,但是應當指出,凡所記述,大都精粹扼要,頗能反映恐子的思想、學說、精神風貌,便於誦習流傳。」 因此探討《論語》為研究孔子思想、言行和中國文化的根本。
其次,從漢語發展來看,《論語》保留了先秦的一些書面或口頭語料,栩栩如生,是古漢語語法的活化石,無論是它的構詞或造句,對於先秦與後代的散文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學術價值不言而喻。
我國當代一些名人、學者諄諄告訴我們,研讀古籍要先重視「文法」,讀書才會有大用。舉其犖犖大者,孫中山說:「欲知文章之所當然,則必自文法之學始;欲知其所以然,則必自文理之學始。文法之學為何?卽西人之『葛郎瑪』也,教人分字類詞,聯詞造句而達意志者也。」, 楊樹達說:「凡讀書有二事焉:一曰明訓詁,二曰通文法。訓詁治其實,文法求其虛。」, 胡適曾對胡頌平說:「活的語言是有文法的。我的文章寫通的原因,是從《論語》、《孟子》裡讀通的。你應該熟讀《論語》,把《論語》讀得熟透了,文章自會寫通的。」, 黃慶萱說:「文法學的學習,可以使學生知道怎樣構成通順的說辭或文章。」, 黃錦鋐說:文法與修辭,是國文教學中的兩大工具,因為中國文章的組織,很多模稜兩可的地方,很容易望文而生義,若不講求文法,則必扞格而不通。古人雖無文法,然學童入學,一年視離經辨志。離經,卽離析經書的義理,能夠離析經書的義理(見《禮解疏》),也就是能分析經書的文法,雖無文法之名,卻有文法之實,古人所謂「句讀」、「章句之學」,實卽文法的分析,知道什麼是主語,什麼是動詞,什麼是賓語。
從諸家的這些看法,可知精通文法對於研讀國學的重要性。探討《論語》的語法,除了有助於了解上古漢語的語法的一些現象之外,並能夠幫助我們深究古文的精義。林傳甲說:
《論語》章法,多一句二句成章者,周秦諸子,不如此之簡,一便也;文理平易近人,無奇字難解,二便也;今塾師已能講解,童子已能熟誦,三便也。變《論語》為初學文法書,亦隨時通變之一端也。
林傳甲所說「初學文法」,雖然言及初學古文的章法,其實與學習古漢語的句法,息息相關;許世瑛也說:「文言文的結構方式,有很多地方和現代國語的結構方式不同,如果不研究中國古代文言文的文法,又如何能理解文言文,更如何能寫通文言文。」 ,可見熟悉《論語》的語法,對探悉古代典籍的構詞、造句規律、學習古文等亦有莫大的裨益。
專書語法的描述,對於衷心於語言研究的筆者,是件責無旁貸的工作。植基於《論語》的高度價值,希冀藉語法的知識輔助閱讀《論語》,與個人多年來研究漢語語法的興趣與專業知能這些動機,筆者遂探討《論語》一書的語法,希冀能達到下列幾項研究目的:
第一、 敘述《論語》的實詞、虛詞的種類及其分類,各個詞類的語法特點。
第二、 了解《論語》單詞及各種構詞方式,並統計出它們所占的百分比例。
第三、 分析《論語》的各種句型與特殊句法(含倒置、外位、被動的表示法)的語法規律。
第四、 系統地了解《論語》的語法特點及其語法體系。
第五、 敘述《論語》的價值與影響。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論語》為範疇,採用清代阮元校勘《論語注疏》的二十卷本《論語》為研究的文本,探討其中語句語法現象。囿於篇幅限制,除了重要的關鍵點之外,同樣的語法舉其部分實例為例,以免篇幅冗贅。各章節的號碼係採用楊伯峻《論語譯注》的編號,以便利檢索,此係目前多數研究者所用,故筆者遵循它。
西方所謂的Grammar,目前或譯為「語法」、「文法」,其意義均相同,馬建忠說:「葛郎瑪者,音原希臘,訓曰字式,猶云學文之程式也。」, 王力說:「Grammar,在希臘文原意是『字學』。」, 楊樹達說:「語言文字之初起,其組織蓋亦錯互而不醇。迨積年既久,隨時改善,至於約定俗成,則形成共遵之規律而不可畔越,後人紬繹其規律而敘述之,則所謂文法是也。」 是知「語法」(文法)指根據語料所歸納出來的語言規律,包含構詞及造句的各種法則,這是科學化處理古代文獻的方式。
大抵來說,《論語》為上古書面語的一部分,它保留的口語文獻也有其限度,若認為要透過《論語》來全面了解古代語言的全貌,這也是不可能的事,這是研究上的先天限制。其次,《論語》為早期的語錄體,以對話為主,敘事為輔,在詞法的研究上比較有可觀的成果,而在單句及複句的類型上,就相對顯得薄弱,這是研究者共同面臨的另一種限制。即便是如此,筆者仍覃精竭力,運用下述七種研究方法,補足前賢零星片段研究的不足,希冀將《論語》語法的研究成果作有系統、全貌的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