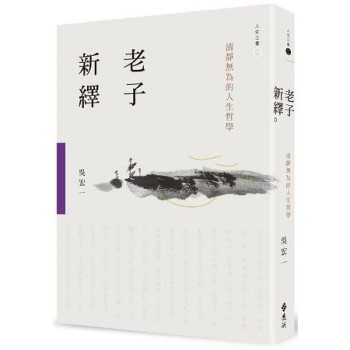《老子》一名《道德經》,是認識老子思想及道家源流的必讀書,也是想了解中華文化的人不可或缺的經典著作。歷代研讀注解的學者,不知凡幾,但對全書五千言的玄言妙論,似乎永遠尋繹不盡,無法測其底蘊。它的傳本很多,字句頗有不同,加上往往「正言若反」,所以常使讀者似懂非懂,無所適從。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由於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兩種帛書本,和湖北荊門郭店村戰國楚墓的三種楚簡本,先後出土,更引起中外學者的熱烈討論和關注。對於各種傳本文字的異同,經文章句的解釋,以及老子思想主張的探索,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紛紛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
筆者以為這些現象,對於有志研讀《老子》的初學者而言,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治絲益棼,不知道該何所抉擇。因此,筆者在《論語新繹》撰成之後,馬上撰寫《老子新繹》這本書。所謂「新繹」者,重點有三:
一、採用直譯的方式,逐字逐句,用白話來翻譯《老子》的經文。原來有押韻的字句,也盡量求其音節的和諧。這是最貼近原文,也是最容易把握原意的做法。
二、校勘各種傳本文字的異同,比較歷來各種注家的解釋,折衷眾說,可採者採之,取其長而捨其短,力求簡明,以便初學。
三、參考有關的研究資料,對每一章的章旨、結構,乃至修辭以及前後經文之間的關係等等,作一番爬梳整理的工夫。間有推陳出新處,希望對讀者有幫助。
第1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❶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❷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❸
【校注】
❶以上四句——帛書甲本作:「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帛書乙本則有脫文。恒、常二字同義。有人以為此書傳本在漢代避文帝劉恒名,故易「恒」為「常」。河上公本、傅奕本皆同王弼本。也,是語尾助詞,作字句停頓之用,猶如今日的標點符號。
❷以上八句——前四句有人斷句為:「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歷來據以解說的大有人在,觀其所論,亦言之成理,第三十二章說的:「道常無名」,更足以為據。但筆者以為上文既云「名可名,非常名」,則此不宜再以「有名」、「無名」為說,而且下文又有「常無」、「常有」之辭,故於「無」、「有」下斷句,似較可取。又,「天地之始」,帛書本作「萬物之始也」,亦可通。
後四句,帛書本作:「故恒無欲也,以觀其眇;恒有欲也,以觀其所噭。」蓋以「無欲」、「有欲」為讀。這種讀法自亦有據,河上公注:「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就是如此解讀的。查第三章:「常使民無知、無欲」,第三十七章:「夫亦將無欲」,第五十七章:「我無欲,而民自樸」等等,皆其證。但就上下文氣論,傳統讀法將「欲」字連下文作助動詞者,似乎仍較可取。例如書中第十五章:「保此道者不欲盈」,第二十九章:「將欲取天下而為之」,第三十六章:「將欲翕之」、「將欲弱之」、「將欲廢之」、「將欲奪之」等等,都是這種用法。噭、徼同音通假。徼,音叫,世德堂本云即「竅」字。說文:「竅,空也。」猶言山谷之洞穴、房室之門戶,與下文「眾妙之門」相呼應。有人以為「妙」同「眇」,有要眇幽微之意,而「徼」同「儌」、「曒」,有邊際向明之意。一暗一明,互為對應。
❸以上五句——帛書本作:「兩者同出,異名同胃。玄之有玄,眾眇之門。」「胃」字應為「謂」抄寫之誤。「眇」同「妙」,皆有幽微之意,已見上注。帛書本的「兩者同出」二句,比傳統通行本句子要簡短整齊,都是說「有」與「無」是一體的兩面,是相生相成的。推而衍之,「名」與「道」也是一體的兩面,有形相聲色可以指稱的一面,叫做名或器或物;無形相聲色可以指稱的一面,叫做道或法或德。如此說來,把「無,名天地之始」以下,斷句為「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也都可以此解之。「有」、「無」既相生相成,則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無」什麼「有」什麼,也都可以互文見義了。《紅樓夢》有云:「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或可移作「玄之又玄」的注解。
【直譯】
道理可以說明的,就不是永恆的道理。名義可以指稱的,就不是永恆的名義。
「無」,指稱天地的開端;「有」,指稱萬物的本源。因此常「無」,想藉此來觀察它的奧妙;常「有」,想藉此來觀察它的訣竅。
「無」、「有」這兩樣東西,同時出現卻有不同的名義,同樣可以稱呼它們為玄妙;玄妙啊它們真玄妙,是所有奧妙的訣竅。
【新繹】
此章是全書或者說是「道經」中的開宗明義第一章,說明「道」是天地萬物的創始者,難以指稱,卻具有永恆的本質和玄妙的變化。要了解它永恒的本質和玄妙的變化,必須先從「有」、「無」二者的概念及其作用說起。
全章可以分為三段:
「道可道」的上個「道」字,是名詞,在《老子》一書中,它指的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生命狀態。它是宇宙間天地萬物的主宰。天地的形成,萬物的誕生,都與它有關。大自然界的寒暑陰陽、因革變化,人類歷史的古往今來、興亡成敗,彷彿也因它的存在,而具有一定可以遵循的法則。它有如古人之看雞卵,雖然孕育著新生命,卻渾沌一片,令人看不清、摸不著,可是它卻又真真實實的「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存在著一種生命狀態。它可以有形狀和顏色,卻沒有固定的形狀和顏色;它可以有聲音和氣味,卻沒有固定的聲音和氣味;以此類推,總之,它恍兮惚兮,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當任何人要稱呼它時,它可以有名義,卻沒有固定的名義。就像《莊子.知北遊篇》所說的:「道不可聞」、「道不可見」、「道不可言」,「道不當名」。它是不可有固定名義的。當它化為無形時,可稱之為道氣;有跡可循時,可稱之為道路;於事稱為道理;於人稱為道士或道人。總之,它是不固定的。
就因為它不固定,所以不可言說。「道可道」下字的「道」,就是動詞的「說」。不可道,就是不可言說,不可用言語道盡,無法用語言文字來完全充分的說明形容。「名」就是言說時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就因為不可用言語道盡,無法用語言文字來完整說明形容,所以它雖然一直存在著,卻沒有固定的形相、聲氣和名義。無以名之,只好一仍舊名,稱之為「道」。第二十五章就這樣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它「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所謂「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是說它使天地萬物有一定可以遵循的法則,從不斷的變動中,找到了一個不變的規律。在無常之中,找到了一個統攝天地萬物的道理。可是它有萬千端緒,千變萬化,令人不知從何說起,又令人不知其極。《管子.心術上篇》也這樣說:「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德,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韓非子.解老篇》說得更好:「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析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
也因此,不能不令人感悟:能用語言文字來說明解析的道理,都只是「道」的一端,而不是「常道」,不是恒常不變的「道」的全部。
「道」既不可道,能道者又非「常道」,因此,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然而為了向世人說法,為了「傳道、受業、解惑」,又不能不道,因而只好藉「名」來論「道」。更何況「道」本來的另一意義,就是「說」。
「名」和「道」是對待的詞語,雖然相對待,但卻不是相對立而是相因依的。「道」常常恍兮惚兮,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名」卻是具體的存在。譬如說,人都有父母和親人,我們一談到父母和親人的名號,他們的形貌、聲音等等,就會自然具體的呈現在眼前。一談到天地,就可以馬上想到天空和土地的實體;一談到古琴和鋼琴、西裝和旗袍等等,我們也都可以馬上從它們的名義上知道它們種種的不同。總而言之,談到任何人或事物,我們都可以從其不同的名字、名分、名號或統稱為名義之中,去辨認其實體存在的意義。即使是抽象的東西,也通常可以從大家為它所取的名稱中,得到若干共識。例如天空、天然、天神的天,有其不同的意義,大家即使不能客觀分析,卻仍然可以感受。
古人說,「名」是聖人為萬物所取的名稱,用來表達萬物不同的概念。這萬物不同的概念,統攝起來,固然有一個無以名之的道,寓乎其間,但它往往是形而上的,如何孕育,如何長成,都恍兮惚兮,難以理解。可是分別來看,萬物仍然各自有其不同的名義可以指稱,而不同的名義,往往又代表了不同的固定的形狀、顏色、聲音、氣味等等特質。因而相對於形而上的「道」,這些可以指認稱呼的天地間的一切萬物,古人認為它們是形而下的東西,就稱為「器物」或「器」。
器或器物,究竟與「道」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一器物有一器物之用,因而各有其特定的名稱。每一個器物的名稱,常常因時間空間的不同、語言文字的不同、觀念的不同、種族的不同等等因素,而有所改變;不可能一成不變,也不可能永恒不改,甚至在同一時空、同一種族、同一語文、同一觀念的環境之中,都又有了不同的名義。相傳古代倉頡造文字時,「天雨粟,鬼夜哭」,可見創造文字,為宇宙天地萬物命名定義,是多麼不容易之事,足以驚鬼神而動天地。《管子.心術上篇》說:「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可見聖人即是為宇宙萬物取名得當的人。聖,本意是耳聰目明,所以能為萬物命名者,必定聰明而神聖。誰有權力可為萬物命名呢?無疑的,他必然是所謂最高的統治者或領導人。這在《老子》書中,就稱之為「聖人」。可是,不管你多麼聰明神聖,當你為某一器物命名時,它就已經具有了特定的名稱和意義;當它有了特定的名稱和意義,它已經同時又有了一定的限制,無法呈現它原來就具有的全部意義和價值。因此「道」這個字,當你解釋為「道理」時,你已經忽略了它還有其他的很多意義。對於那不可道的常道,更不知如何界定名義了。
例如「天」、「地」等等,幾乎每一個字,當你解釋它的名義時,你會發現無論怎麼詳細解釋都不可能周全,而且用不同的語言文字來翻譯解說時,你更會發現它還有許多有待詮釋的意義。可見任何器物的名義,不管你如何界定,永遠界定不完。這就是所謂「名可名,非常名」。
以上說的是前四句第一段,以下八句第二段主要是說明「無」與「有」二者的概念及其相生相成的作用。
上述的「道」,先天地萬物而長存,雖實有而看似虛無;上述的「名」,依天地萬物而指稱,雖看似實有而實虛無。第四十章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這是說天地間的一切萬物,都有其「名」,是有形相聲色等等可以指稱的實體,可是它們是如何誕生的,如何形成的,推究起來,它們其實都來自那先天地萬物而長存的「道」,依一定永恒的法則運行而成。依照《列子.天瑞篇》和《淮南子.天文訓》等等的說法,道原是先宇宙而生的一道元氣,當它運行時,先是清輕者上升為天,濁重者下降為地,而後發生陰陽四時的變化,而後產生日月星辰風雨雷電等等萬物。這道元氣即是「道」的本身,也叫做「一」。《淮南子.原道訓》說得很清楚:「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既然「名實同居」,也就表示我們可以由「名」以識「道」,而名之「有」、「無」,也就關係到天地萬物的要妙所在了。
「有」與「無」,實存與虛無,是相對的詞語,可是它們不是相對立而是相因依的。這也就是下文第二章所要說的:「有無相生」。這裡的「無」,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零有」,而只是還沒有顯現出它的形相聲色而已,有如風之無形,水之無色。也因此,「無」可以用來稱呼「天地之始」,也可以用來稱呼「萬物之母」。相同的道理,「有」也可以兼攝「天地之始」與「萬物之母」。這四句顯然是互文見義,同樣是合用「無」、「有」二者,來說明天地萬物的開端和生命的起源。《莊子.大宗師篇》有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說的就是道合「有」、「無」二者的道理。
《老子》第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郭店楚簡本《老子》作:「天下之物生於有,生於無。」這是單從「有」的方面來說的,拿來和第四十二章所說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理正相契合。一物衍生一物,終至衍為萬物,這是從實存的「有」來說的,它只是沒有把「有」背後的「無」同時說出來而已。因為假使「道可道」,那就是「非常道」了。
就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要常從上述「無」與「有」的概念中,去體察「道」與「名」之間的關係,去體察天地萬物的奧祕和生命的出路。道之用,生天地萬物,而後萬物有其名,而後聰明之人由名以說道。「觀其妙」,是靜觀其內在的幽微要妙;「觀其徼」是瞻望其外在的歸趨出路。一幽一明之間,就是所謂灰色地帶,也就是下文所說的介乎黑白之間的「玄」。至於「玄」是什麼,下文自有分解。
名,也就是字,是說為某人或事物取個稱呼,以便指認辨別。古人名字有別,我們今天卻名字連用,事實上,指的都是一個特定的人或事物。有人從甲骨文去探究「名」的本義,以為「名」原指古代一種盛肉用的禮品,雖然證據不夠充分,但古代確實是常將名與器並稱的。例如《左傳.成公二年》孔子說:「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這裡的器指禮器,名即指名義、名分。名器應該相符,才有意義,但名與器卻常常不相符,例如《論語.雍也篇》中孔子說的「觚不觚」,觚原是飲酒用的禮器,可是孔子所看到的觚,形制用途都已經不是原來的觚了。這可以說是有其名而無其實,所以孔子才會感嘆觚不像觚。這就是名器不符、名不符實的例子。這個例子說的,是具體有形的器物;下面還可舉一個無狀可言的概念,來說明名與實不相符的情況。
我們都知道儒家講禮,講正名。《論語.顏淵篇》中,孔子回答齊景公的問題,就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說君要像君,臣要像臣,不論是什麼名義,都要符合自己的身分。又在同篇章中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這些話中的君臣父子,都有兩個字,上面的君臣父子,指的都是正式名義,下面的君臣父子,指的都是名不符實的對象,說不像君臣父子該有的樣子。易言之,名義和實際已不相符合了。
這裡再以君臣為例來作進一步的說明。君字的本義,原是指嘴巴說出的話就要用雙手來執行的人,所以稱為君上;臣,指俯首屈身屈伏在地的人,所以稱為臣下。在古代封建社會裡,君上對臣下可以發號施令,予取予求,而臣下對君上則必須畢恭畢敬,絕對服從。《韓詩外傳》卷五就記載了下面一段故事:孔子有一次侍坐在魯國執政大臣季孫身邊,季孫的家臣來報告說魯君派人來「假馬」(即借馬。假,即借),不知道借不借給他。孔子馬上說:「君取於臣曰取,不曰假。」意思是該家臣只能說魯君來「取」馬,而不應說是來「借」馬。季孫同意孔子的說法。就因為要正名義,魯君來向臣下借馬一用,只能說是「取」而不能說是「借」,所以孔子才說:「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這也是說君是君,臣是臣,假使君不像君,臣不像臣,那麼名義和實際就混亂了。
可見儒家非常重視「名」,重視名實或名器是否相符,而老子所說的「名」,則超越這個層次,藉之與「道」並稱。天地萬物創始之初,「道」渾沌一片,無形相可言,既非器物,所以無以名之,只能概稱為「道」或「大」(見下文第二十五章),後人因而稱之為「大道」;等到天地創始、萬物衍生之後,萬物各有其形制,此有彼無,彼有此無,所以也就各有其不同的名義。這從「無」到「有」的過程中,可以說都是由於「有」、「無」二者相生相成的作用。
此章的最後五句,是第三段,說明「有」、「無」二者同出於「道」,而且是同時產生,同時發揮作用。它們雖然名稱不同,但它們必須合在一起,「道」才能發揮其玄妙的功能。下面各章所說的道理,幾乎都由此衍化而出,所以說是「眾妙之門」。
【論老子絕句】之一
名道開篇各擅場,可名可道即非常。有無分合妙何在,我欲談玄不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