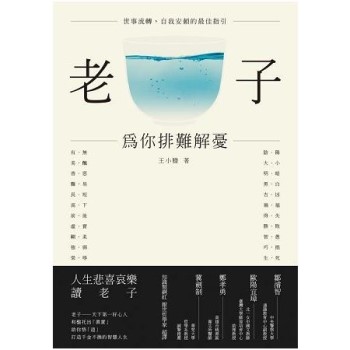前言
一、老子其人其書
漢代司馬遷(約公元前一四五—八六年)所著《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向來是學術界藉以了解老子生平的主要依據文獻,本書亦以之為基準,在此綜合整理如後: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東周的春秋時期(公元前七二二—四八一年),楚國苦縣(今河南省鹿邑縣東)厲鄉曲仁里人。由於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曾向老子問禮,故可推知老子應較孔子年長,但是無從確知其生卒年,有學者推測約為公元前五八O—五OO年。
老子在當時定都雒邑(今河南省洛陽市)的周天子朝廷中,擔任「守藏室之史」,此一職位相當現今國家圖書館館長。任職甚久,眼見周王朝日益衰微,因而離去。將出關(學者通常認為是函谷關)時,守關的官員要求他著書,他因此寫下一書,分為上下篇,約五千多字。著作完成,老子便離去。此後,再也無人知曉他的行蹤。
《老子》又稱《道德經》,這是因為老子著作的上下篇,上篇始於「道可道,非常道」,下篇則始於「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因此人們取上篇的「道」字,稱上篇為〈道經〉;另取下篇的「德」字,稱下篇為〈德經〉,並且合稱為《道德經》。古本《老子》是否分章,無法確知,現今通行的魏‧王弼(公元二二六—二四九年)注本暨河上公(無從確知其時代,學者通常認為其人的年代較王弼晚)注本,都分為八十一章。
一九七三年,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的「漢墓」出土許多帛書,其中包括《老子》的帛書甲本與乙本。這兩種版本互有異同,也都各有殘損,都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而且也都沒有分章。另外,甲本無避諱,乙本避「邦」字諱,說明兩本抄寫時代不同。甲本抄寫在劉邦稱帝(公元前二O六年)之前,乙本抄寫在劉邦稱帝之後。
一九九三年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戰國楚墓」出土許多竹簡,其中有三種《老子》的摘抄本,分為甲、乙、丙三組。摘抄本的字數只有通行本的三分之一,其中丙組的文句與帛書本、通行本較為接近。另外,專家認為甲組較為接近《老子》祖本,它的抄寫時代距離老子逝世「可能」只有一百多年。
雖然現今有上述之新出土資料,但是研讀老子全書仍以通行本為宜。由於學術界一致公認通行的王弼注本優於河上公注本,因此本書即依王弼注本進行說明。
二、本書簡介
本書介紹老子,首先是以「前言」,介紹「老子其人其書」以及本書的大概內容。
接著是依序介紹老子八十一章正文。每章介紹的方式,都是先在章名之下,嘗試提出老子之所以書寫此章的緣由,也就是老子察見了什麼問題,或欲解決什麼問題;其次,列出此章原文中的第一段敘述;其次,針對這段敘述,若有字義須加以解釋,則解說之;其次,說明這段敘述的文字字面之意;其次,詮釋這段敘述涵藏的義理。爾後,再列出此章原文中的第二段敘述,再依序說明字義、這段敘述的字面之意、義理。依此類推。
關於《老子》書中的思想,有學者認為其中包括「宇宙論、人生哲學、政治思想」等範疇。不過,或許也可了解為:書中論及萬物之生成、人生之修養、政治理想的敘述,都是老子藉之以說明「道」的記載。換言之,「道」是全書的主旨,由於「道」不遠人,它無所不在,處處皆在,是人們生命的真實,也是人們存活之環境的真實,所以老子藉由生活中的任一面向,隨時舉例,以向讀者揭示「真實」,也就是揭示「道」。
本書詮釋老子義理,並不僅只停留在文字之字面,因此與學者們通常依從文字之字意所進行的解釋,不盡相同。然而本書並未標新立異,而是跟隨「道」不執著的流動本質以及渾全不割裂的整體性質,說明老子埋藏在字裡行間的洞見與智慧。試想老子開宗明義,書首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揭示語言文字僅僅指向「意」,並不等於「意」。亦即「言」與「意」不能劃上等號,也就是《莊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因此,本書不僅只停留在文字字面,而是跟隨「道」的性質進行說明,是否悖離抑或相應於老子,即留予讀者思考。
本書以淺白文字進行說明,深信有助於讀者突破常識的片面知見,了解老子記錄的「真實」,進而明瞭老子不是一般大眾所誤會的消極遁世、權謀陰險、苛薄殘忍、反知識、反文明,而是時時和盤托出,指出「真實」。
一章
觀諸天地四時,是否能追尋出「常道」?人類畢其心智,化萬物於言語,然而「言」與「意」可否劃上等號?如何以「言」說明「道」之「意」?
道可道,非常道。
「可道」的「道」,是以語言文字進行說明。「常」:恆常不變。
可以使用語言文字敘述說明的「道」,不是恆常不變的「常道」。
其中至少有兩項內涵:(一)語言文字不等於「真實」,例如我們發出「火」的讀音,或在紙張寫下「火」的文字符號,但是並沒有「真實」的「火」,由我們的口中或由紙張中冒了出來。故知語言文字不等於「真實」,語言文字僅僅指向「真實」。但是,人類雖然創設語言文字以指向「真實」,然而「真實」從未停止改變,至於語言文字卻只是一項固定、而且並不隨著「真實」同步改變的媒介而已。例如「粉紅玫瑰」的敘述,雖使人們了解這朵玫瑰花的色澤,但是「真實」的粉紅玫瑰,並非永遠停駐在此色澤,它必將變化為凋萎枯敗,不再具有此一色澤。故知從未停止改變的「真實」,與語言文字並不密合;也就是語言文字不等於「真實」。所以讀者一旦見聞語言文字,必須自行由語言文字跳躍至「真實」。因此如果只是停留在語言文字的「道」,那麼將無法了解老子所揭示之「真實」的「道」,讀者必須由語言文字之「道」,跳躍至「真實」的「道」。
(二) 「常」是不變。天地之中,一切皆不斷地改變,然而「變」卻是不曾改變的恆常法則。所以老子揭示的「道」,即是因為始終不斷地改變,因此是恆常不變的「常道」。也就因為「常道」不斷地改變,無從以語言文字進行表述。故言「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可名」的「名」,是以語言文字進行指稱。「常」:恆常不變。
可以使用語言文字指稱的「名稱」,不是恆常不變的「常名」。
此之內涵與前二句「道可道,非常道」相近:(一)老子將所欲表述之「真實」,以語言文字取了「道」的名稱,但是此一「名稱」,不等於「真實」,讀者必須由語言文字的「名稱」跳躍至「真實」。(二) 恆常不變的「常道」,不斷地改變,所以它的「名」也就隨著它的不斷改變而改變。舉例來說,露珠聚積在地面,我們稱之為「水」;相同的物質一旦進入大氣的循環,我們稱之為「雲」;當它們凍結凝聚,我們又稱之為「冰」。由此可見,即使是相同的物質,在不同的狀態下便擁有相異的名稱。亦即它恆常不變的「常名」,乃不斷地改變,因此無從以日常的語言文字來概述。故言「名可名,非常名。」
雖然語言文字不等於「真實」,僅僅指向「真實」,有其侷限性,但是老子仍然使用語言文字做為媒介表述「道」。以下即是舉「有」、「無」為例,以說明「道」。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以「無」稱呼天地的開始,以「有」稱呼萬物的母親。
在此不宜因為由語言文字觀之,「始」與「母」的名稱不同,便誤以為「始」與「母」有所不同,只須參看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便知「始」即是「母」,「始」與「母」是「一」而不是「二」。「始」與「母」均為根源之意。
再看萬物都存在於天地中,也都不可能離開天地,存在於天地之外;亦即「萬物」存於「天地」,「天地」中有「萬物」。雖然由常理觀之,萬物被涵蓋於天地之中以仰賴天地而生,因此「天地」與「萬物」之間似乎存有階級、次序性的關係。然而,由自然觀之,哪一處的地形地貌不因萬物之活動而有所更易?哪一處的天地不因萬物之存在而隨時空演替不已?疾風撼動蒼茫的沙洲,溪澗切穿深邃的溪谷,森林更隨著四季將天地換成不同的色彩;故知「天地」與「萬物」誠然為無從切割的整體。換言之,「天地」兼涵「萬物」,「萬物」蓄養「天地」;不可因語言文字不同,便誤以為二者可以切割、各自獨立。由此則可明瞭:不宜因為表述「天地之始」與「萬物之母」的語言文字不同,便誤以為二者的意涵不同, 實則「天地之始」即是「萬物之母」,兩者同存相依。
另外,常識認為「有」、「無」不並存,但是老子提出與常識不同的觀察,十一章「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車輪的三十根木條(車輻),共同聚集於車輪的軸心(車轂),正因為車轂中央的空「無」,與車輻木條的「有」,相互配合,所以車輪可以平穩滾動,提供給我們車輛的作用。揉和陶土做成器皿,器皿中央的空「無」,與器皿的陶土部分的「有」,相互配合,所以使我們的器皿具有盛物的功能。開鑿門窗建造成房屋,由於室內的空「無」,與房屋牆壁的「有」,相互配合,所以造就我們的房屋居住的功用。由以上三項生活中的例證,可知「有」之所以給予我們便利,乃因「有」與「無」相互配合,方才可能完美發揮作用;而且由車輛、器皿、房屋三項例證,可明瞭「有無」是無從切割的整體,也就是「有無」混融為「一」而不是「二」,其作用方才完整無所缺欠。
「有無」混融為「一」的情況,隨處可見,不僅僅只是以上三項例證而已,例如人類的血肉之軀是「實有」,然而我們張開嘴,口腔內部卻是「空無」,正因為口腔是「空無」,所以食物可由此進入體內,供給人體存活所需之營養與能量。此例再次說明「有無」不可分離的必然性,「有無」並非楚河漢界之不相往來。「有無」是無從切割的整體,並不因為語言文字給予不同之「名」便可切割為「二」。它們互通有無,是混融之「一」而不是「二」。
以此則可進一步了解:「無」既是「天地之始」,也是「萬物之母」;「有」既是「萬物之母」,也是「天地之始」。綜合言之,「有無」混融,即為「天地萬物」之根源,「天地萬物」出自「有無」混融之整體。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恆常立於「無」,希望觀察萬有之「妙」;「妙」指開端、初始、本體、本質。也恆常立於「有」,希望觀察萬有之「徼」;「徼」指終點、最遠的邊際、作用、現象。
總是觀察「無」,但也改變觀察基點,總是觀察「有」。然而,由於「有無」互通,它們是混融之「一」;所以由「無」觀之,即是以「有」觀之;以「有」觀之,即是以「無」觀之。
至於「徼」──「終點、最遠的邊際、作用、現象」,必可追溯至「開端、初始、本體、本質」,也就是由「徼」必可追溯至「妙」;至於「妙」──「開端、初始、本體、本質」,必然同時存在於「終點、最遠的邊際、作用、現象」之中,也就是「妙」必然表現於「徼」之中,正如信手劃一條直線,不論直線有多長,有開端則必然出現終端,兩者自然而然地相應而生。所以「開端與終點」、「初始與最遠的邊際」、「本體與作用」、「本質與現象」,也是無從切割的整體。因此而明瞭「妙與徼」是無從切割的整體,並不因為語言文字給予不同之「名」便可切割為「二」;它們是混融之「一」而不是「二」。「妙」中有「徼」,「徼」中有「妙」。所以「常無」不僅可觀「妙」,也可觀「徼」;「常有」不僅可觀「徼」,也可觀「妙」。綜言之,立於「有無」混融之整體,則可「妙」與「徼」併觀。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此兩者」指「有」與「無」。
本句可由兩個面向來了解:(一)通常學者均認為「有」與「無」同出,也就是一同出自「有無」混融的整體,不過它們各自呈顯不同的樣貌,因此人們給予不同的命「名」,所以是「此兩者同出,而異名。」(二)「此兩者同,出而異名。」也就是「有」與「無」相同,因為「有無」是無從切割的混融整體,所以「有」同於「無」;不過它們雖然是「同」,但由混融的整體出來之後,因為各自顯現不同的樣貌,因此人們給予不同的「名」,所以是「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
「玄」:深遠。
本句也可由兩個面向來了解:(一)「有」與「無」都可稱為「玄」。因此不僅「無」是「玄」,「有」也是「玄」,也就是「有無」混融的整體可稱為「玄」。(二)「有」與「無」彼此「相同」的這個狀態,可稱為「玄」。也就是「有無」混融的整體可稱為「玄」。以此不僅「無」是「玄」,「有」也是「玄」。
有鑑於人類的視覺對深遠之處,無從進行辨識,故知老子以「玄」表述道,揭示我們無從藉由感官對「道」進行認知。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妙」指奧妙精微、起始、萬有。
就在這「有與無」混融的「玄」的狀態,「有無」相互激盪,一切的奧妙精微、起始、萬有,都由此產生,都由此門中走出。
在此,讀者或許應該思考:藉著老子所舉「有」、「無」之例,是否了解流動不已,變化無常,無從以語言文字賦予固定名稱的「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