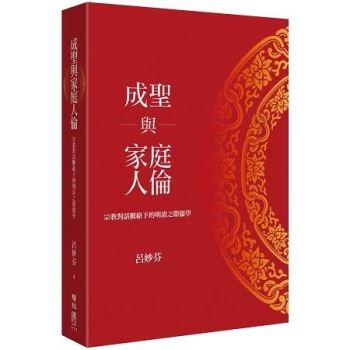第一章 生死觀的新發展
本章主要欲探討明清之際的儒學是否出現近似個體靈魂(individual soul)的概念?是否更具像地描述死後的情狀?中國傳統雖有關於魂魄和死後情狀的描述,但並未明確提出個體靈魂的概念,而儒學發展到宋明理學階段,早期典籍中人格神的色彩大幅消減,形上義理成分加重。理學家基本上以氣之變化來解釋生死現象,雖然他們沒有否認鬼神的存在,但對於生死議題主要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晚明社會動盪、戰亂頻仍、宗教氛圍濃厚,學者對於生死議題格外關切,晚明許多理學家都追求悟道,強調儒學的終極目標在於了究生死。本章主要研究清初儒者的生死觀,及其對死後理想歸宿的想像,將就此議題說明儒學在明清之際延續性的發展。
一、道德修養決定死後情狀
宋明理學從氣化的觀點講鬼神、不認為有永久不散的個體性神魂。舉例而言,張載(1022-1077)以氣之聚散講生死,氣聚生成人物,人物死後,氣散歸回太虛。鬼神乃陰陽二氣之往來屈伸,是氣之良能妙用。張載認為,人死後個體性的靈明便隨之消散,他也以此批判佛教的輪迴觀。二程對於張載氣化思想雖有批評,但同樣認為人死氣散的看法。朱熹(1130-1200)對於鬼神、魂魄的討論,包括「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死後「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鬼神乃陰陽二氣之靈」等,均可見其大體承繼二程與張載的看法。目前學界對於朱熹鬼神觀的討論較多,學者指出他在不同語境下使用「鬼神」二字,有意指氣之往來屈伸、陰陽二氣之靈、人身之精氣、造化之神妙等不同意涵。吳展良則指出朱熹的鬼神觀既非無神論,又非人格神論,而是具有統合神靈、精神、物質與人生界之特性。儘管學者對於朱熹鬼神觀的詮釋重點不盡相同,然仍有相當的共識,其中與本章論旨相關的是:朱熹沒有個體靈魂不朽的概念,也反對具位格的鬼神觀,此又與其反對佛教輪迴有關。朱熹認為人死後,氣會回歸天地間公共之氣,只有在子孫誠敬祭祀時,祖先神魂才可能被暫時性地感格而會聚,即使聖賢亦然。他說:
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也。
這段話一方面解釋祭拜山川神祇與祭祀祖先的原理差異,一方面解釋古書中記載人死魂氣不散,回到人世報仇的事例。朱熹承認確實有人死後氣不散的現象,但主要是因為凶死為厲作怪,或者如僧道是通過修養使氣不散,但朱熹認為此均非正道,亦非仁人君子所應嚮往追求的。生順歿寧、與道消息,才是儒者了然生死變化、大公無私的正確態度。
簡言之,張載、程朱等宋儒對氣之聚散的看法,基本上適用於所有人,即無論智愚賢不肖,生死聚散的原理並無差別,都是氣聚而生,死後氣散;人死後,個體性亦隨之消亡。生死的變化,並不是氣從有到無的變化(亦即氣仍存在),而是曾經聚集成個體生命的氣,隨著生命的死亡而散化,個體性亦隨之消失。朱熹明白說道:「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即使聖賢,死後氣亦散歸天地公共之氣,不再具有可區辨的個體性。這樣的看法構成理學論述的主流,影響後代學者甚鉅。宋儒中雖也有胡宏(1105-1161)、程顥(1032-1085)曾說心體不死,不過這樣的看法受到程朱的批評,在宋代較不顯。明代心學思想高漲,晚明以降許多儒者都強調儒學的終極意義在了究生死,有關心體或性體不死的論述也更多。例如,王陽明(1472-1529):「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其臨終遺言「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強力表達了對自己心體與道合一的信心。唐樞(1497-1574):「人之所以為人,其始也不始於生,而始於所以生;其終也不終於死,而猶有所未嘗死者。」文翔鳳(1642卒):「百年為有盡之身,萬古有不滅之性。」李顒(1627-1705):「形骸有少有壯,有老有死,而此一點靈原,無少無壯,無老無死,塞天地、貫古今,無須臾之或息。」楊甲仁(約1639-1718):「以形骸論,一生一死,百年遞嬗,乃氣之變遷也。至於此性,無有變遷,不見起滅,有甚生死。」其他如「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吾生有盡,吾生生之心無盡」這類相信心體或性體不朽的說法,在明中葉以降的理學文本中經常可見。儘管如此,此尚不足以說明這些儒者已具有明確個體性靈魂的概念,除非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個體性身分辨識(individual identity)始終存在的表述,才能作如此推論。
明清之際也開始出現許多質疑程朱鬼神觀與生死觀的聲音,我們從以下這段記載可以看到明代學者已有不同想法:
人有問劉獅泉(劉邦采):「為學人,死了,何歸?」獅曰:「歸太虛。」又問:「不學人,死了,何歸?」獅曰:「歸太虛。」詢諸渠(鄧豁渠),渠曰:「學人不敢妄為,死歸太虛;不學人無所不為,死亦歸太虛。何不效他無所不為?同歸太虛,豈不便宜!」
劉邦采(1528舉人)的看法接近朱熹,人死後氣散回歸太虛,是天道的自然變化,人不應該過分追求個體不死,因為那是違反天道的自私行為。但是鄧豁渠(1498-約1569)的疑問代表了另一種聲音,也是關於個體生命終極意義的思索:如果儒家所重視的道德修養,最終並不能在修練者個人生命中鑄成永恆性的變化,其價值何在?就生命終極存在的境界而言,若果真不分賢愚都同樣散回太虛公共之氣,同樣無知,那麼是非善惡的價值與最終的公義何在?此似乎不符天道善惡之理。
對於這個問題的思索,鄧豁渠並不孤單,許多後來的儒者都持類似的看法,反對程朱等「死後氣散無知」之說。下文將一一列舉明清儒者如何反對賢愚善惡同歸於盡,強調個人道德修養具有決定死後神魂歸趨的作用,甚至出現近似個體靈魂觀的論述。這些學者並不隸屬於特定學派或地域,但都生活於晚明清初時期;他們的思想也存有許多差異,顯示此時期思想創作的活力與複雜性。儘管如此,他們試圖賦予個人道德成就超越死亡、具有不朽價值的眼光,則又頗一致。以下讓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羅汝芳(1515-1588)認為人具有精氣凝成之形骸與神遊變化之靈魂,即魄與魂的二元組合。靈魂心智是修身入聖之關鍵,人死之後,形骸氣魄消散,至於靈魂之歸趨,則不相同。他說:
人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淡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接應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為徒焉已矣。若人以己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于力為,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沒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為徒焉已矣。
人死後能否還歸太虛與造化者為徒,端賴生時之道德修養而決定。人若能妙用心知、感通得諸當下,生可望以入聖,歿可望以還虛;相反,若心思受限於軀殼,不僅生時難以成聖,死後也無法還歸太虛,終將與凡塵為徒。
王時槐(1522-1605)說聖門論生死,不以形氣言,身體形氣隨死亡而消散,人心卻死而不亡。他也反對人死神散、舜跖同歸必朽的看法:
夫學以全生全歸為準的,既云全歸,安得謂與形而俱朽乎?全歸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之所以悠久而無疆也,孰謂舜跖之同朽乎?
高攀龍(1562-1626)和王時槐看法類似,同樣強調生死僅就形而言,性無生死,也認為賢愚善惡不可能同歸於盡。高攀龍說:
伊川先生說遊魂為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遊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即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
高攀龍雖知程朱是因為闢佛的立場而強調人死氣散,不欲落入輪迴之說,但他不同意程朱的看法,他認為聖人不可以存亡言、忠臣義士何曾亡減?高攀龍的弟子陳龍正(1585-1645)也看出老師的說法與程朱不同,他自己則在細體二說之後,認為老師高攀龍之說較長。陳龍正說聖人無生死,其心充滿古今天地,死後精神周遍,故「不可作散觀,亦無處說得聚,總與生前一般」。他又分辨聖人與忠臣義士,認為聖人死後之神靈,與忠臣義士之靈不同,一般鬼神(包括忠臣義士之靈)或靈於一方,或盛於一世,只有聖人之靈「無所專在,無所不在」。陳龍正的想法,可以說已具有永恆個體性存在的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