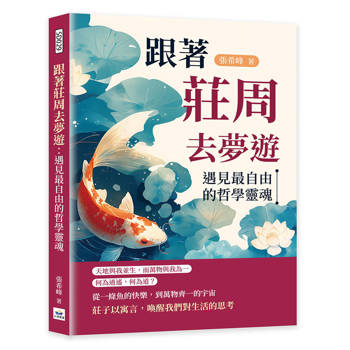第一章 從人生如戲到自在從容
從西元前475年到西元前221年嬴政統一中國,是中國歷史上變革最為劇烈的時期,史稱「戰國」。「戰國」的命名,大概是因為戰爭在這一歷史時期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戰國時期的254年內,戰亂頻仍,烽火連天,戰爭成為諸侯兼併爭霸最主要的手段。另一方面,各國諸侯為增強爭霸實力,大都積極進行政治、軍事、經濟制度的改革,迫切需要多方面的、大量的人才。於是,傳統的宗族出身和政治經濟地位限制被突破,傳統的思想文化觀念禁錮被打開,一大批有才能、有文化的士走上政治舞臺。他們有的高居相位,如李悝、衛鞅、吳起、申不害等,充當改革先鋒;有的成為名將,南征北戰,如樂毅、白起、王翦;有的成為遊說之士,如張儀、蘇秦,憑其三寸不爛之舌謀求富貴,合縱連橫;有的成為高士,如段干木、顏斶、魯仲連,高潔尚義;有的成為俠士,如聶政、田光,荊軻,視死如歸。除此之外,在思想文化領域湧現出一大批學士,他們著書立說,廣聚徒眾,成家立派,爭相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共同開創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百家爭鳴」的活躍局面。
「百家爭鳴」不僅促進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空前繁榮,還造就了一大批天才思想家,如墨翟、孟軻、惠施、公孫龍、荀卿等,一時群星璀璨。而莊子,當然是這璀璨群星中極為耀眼的一顆!
一、貧賤不能移
莊子名周,宋國蒙(今河南商丘市東北)人,其家世不可考,史籍無傳。莊子生活在西元前369年至西元前286年,與有名的戰爭狂人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嘗為蒙漆園吏,即管理漆園的小官,因這與其志趣不合,不久莊子便辭職而去。此後,莊子從未出仕,大約終身為自由職業者。
因為沒有固定職業,其祖輩大概也沒有留給他豐厚的家產,所以莊子的生活狀況一直很慘。在莊子所處的時代,士這個階層的人出路還是較多的。如上所述,士可以去遊說諸侯,鼓吹治國興邦之術,一旦得到賞識,可以入朝為將相,例如蘇秦曾掛六國相印。次之是投靠權貴,做個門客,例如馮諼寄食孟嘗君門下,吃飯有魚,出門有車,所得還可供養家人。但這些莊子皆不願為。另外,當時齊國東門外有個稷下學宮,招羅天下著名學者,列第為大夫,不治而議論。孟軻、荀況曾先後去講學。莊子「善屬書離辭」、「其學無所不窺」,有蓋世之才。按理說,他不願出仕與暴君、貪官同流合汙,去稷下學宮講講學混碗飯吃總可以吧!但莊子認為,稷下學宮那班學者整日搖唇鼓舌、喋喋不休地爭論一些諸如「卵有毛,雞三足」之類的事情,實在無聊得很,所以也沒有去。
莊子究竟窮困潦倒到什麼地步,史書沒有記載,不過從莊子的著作裡可以看到一點蛛絲馬跡。他曾垂釣於濮水,可能是為了轆轆飢腸;他也曾同弟子行於山中,可能是砍樵換米。儘管莊子如此辛苦,挨餓的時候也是有的。據《莊子.外物》記載: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雖然莊子窮到了告貸無門的地步,但是仍然對監河侯的無理予以辛辣的諷刺。
莊子告貸,監河侯非但不予救濟,反而以其將得封邑百姓之租稅傲人,並以「將貸子三百金」戲弄莊子。由此可見當時統治者對不跟他們同流合汙的士人的敵視和仇恨。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要保持清白而不喪失品格,又是多麼艱難!
莊子「忿然作色」回擊監河侯。他說,昨天於車轍中見一鮒魚,為「東海之波臣也」,欲求斗升之水活命;而他稱要南遊吳越之王,然後激西江之水迎鮒魚回東海。這實際是見死不救,因此遭到鮒魚「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的痛斥。莊子用這則寓言,揭露了統治者對正直清白不為其所用之士趕盡殺絕的狼子野心。
在窮困潦倒的生活中,莊子清楚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原因。《莊子.山木》中記載說: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繫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
「非遭時也」,一語道破真機!
身上穿著打了補丁的粗布衣衫,腳上是一雙麻繩綁著的草鞋,而莊子這衣履不完的樣子,魏王認為其是「憊」,莊子則自稱是「貧」。莊子透過對「憊」和「貧」的辨析,表現了其「貧賤不能移」的高貴品格。他清醒地知道,他的貧困是他所處的那個黑暗社會的「昏上亂相」造成的。
從西元前475年到西元前221年嬴政統一中國,是中國歷史上變革最為劇烈的時期,史稱「戰國」。「戰國」的命名,大概是因為戰爭在這一歷史時期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戰國時期的254年內,戰亂頻仍,烽火連天,戰爭成為諸侯兼併爭霸最主要的手段。另一方面,各國諸侯為增強爭霸實力,大都積極進行政治、軍事、經濟制度的改革,迫切需要多方面的、大量的人才。於是,傳統的宗族出身和政治經濟地位限制被突破,傳統的思想文化觀念禁錮被打開,一大批有才能、有文化的士走上政治舞臺。他們有的高居相位,如李悝、衛鞅、吳起、申不害等,充當改革先鋒;有的成為名將,南征北戰,如樂毅、白起、王翦;有的成為遊說之士,如張儀、蘇秦,憑其三寸不爛之舌謀求富貴,合縱連橫;有的成為高士,如段干木、顏斶、魯仲連,高潔尚義;有的成為俠士,如聶政、田光,荊軻,視死如歸。除此之外,在思想文化領域湧現出一大批學士,他們著書立說,廣聚徒眾,成家立派,爭相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共同開創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百家爭鳴」的活躍局面。
「百家爭鳴」不僅促進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空前繁榮,還造就了一大批天才思想家,如墨翟、孟軻、惠施、公孫龍、荀卿等,一時群星璀璨。而莊子,當然是這璀璨群星中極為耀眼的一顆!
一、貧賤不能移
莊子名周,宋國蒙(今河南商丘市東北)人,其家世不可考,史籍無傳。莊子生活在西元前369年至西元前286年,與有名的戰爭狂人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嘗為蒙漆園吏,即管理漆園的小官,因這與其志趣不合,不久莊子便辭職而去。此後,莊子從未出仕,大約終身為自由職業者。
因為沒有固定職業,其祖輩大概也沒有留給他豐厚的家產,所以莊子的生活狀況一直很慘。在莊子所處的時代,士這個階層的人出路還是較多的。如上所述,士可以去遊說諸侯,鼓吹治國興邦之術,一旦得到賞識,可以入朝為將相,例如蘇秦曾掛六國相印。次之是投靠權貴,做個門客,例如馮諼寄食孟嘗君門下,吃飯有魚,出門有車,所得還可供養家人。但這些莊子皆不願為。另外,當時齊國東門外有個稷下學宮,招羅天下著名學者,列第為大夫,不治而議論。孟軻、荀況曾先後去講學。莊子「善屬書離辭」、「其學無所不窺」,有蓋世之才。按理說,他不願出仕與暴君、貪官同流合汙,去稷下學宮講講學混碗飯吃總可以吧!但莊子認為,稷下學宮那班學者整日搖唇鼓舌、喋喋不休地爭論一些諸如「卵有毛,雞三足」之類的事情,實在無聊得很,所以也沒有去。
莊子究竟窮困潦倒到什麼地步,史書沒有記載,不過從莊子的著作裡可以看到一點蛛絲馬跡。他曾垂釣於濮水,可能是為了轆轆飢腸;他也曾同弟子行於山中,可能是砍樵換米。儘管莊子如此辛苦,挨餓的時候也是有的。據《莊子.外物》記載: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雖然莊子窮到了告貸無門的地步,但是仍然對監河侯的無理予以辛辣的諷刺。
莊子告貸,監河侯非但不予救濟,反而以其將得封邑百姓之租稅傲人,並以「將貸子三百金」戲弄莊子。由此可見當時統治者對不跟他們同流合汙的士人的敵視和仇恨。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要保持清白而不喪失品格,又是多麼艱難!
莊子「忿然作色」回擊監河侯。他說,昨天於車轍中見一鮒魚,為「東海之波臣也」,欲求斗升之水活命;而他稱要南遊吳越之王,然後激西江之水迎鮒魚回東海。這實際是見死不救,因此遭到鮒魚「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的痛斥。莊子用這則寓言,揭露了統治者對正直清白不為其所用之士趕盡殺絕的狼子野心。
在窮困潦倒的生活中,莊子清楚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原因。《莊子.山木》中記載說: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繫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
「非遭時也」,一語道破真機!
身上穿著打了補丁的粗布衣衫,腳上是一雙麻繩綁著的草鞋,而莊子這衣履不完的樣子,魏王認為其是「憊」,莊子則自稱是「貧」。莊子透過對「憊」和「貧」的辨析,表現了其「貧賤不能移」的高貴品格。他清醒地知道,他的貧困是他所處的那個黑暗社會的「昏上亂相」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