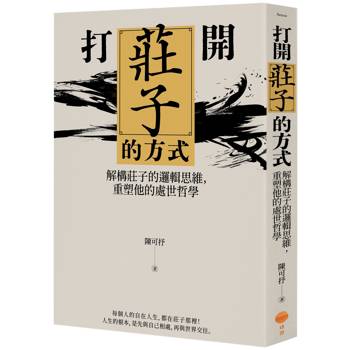第一篇、逍遙遊——一切逍遙的本質都指向一個命題:如何做自己(節錄)
世人多認為莊子承襲老子衣鉢,「清靜無為」,然而,在〈逍遙遊〉的開篇,莊子便展示了他宏大的志願——魚子化為巨鯤,鯤化為鵬,鵬怒而飛,身在北冥,卻又追逐南冥,不遺餘力——試問,這哪裡是「無為」呢?
其實,莊子之人生宏願便是探尋天道,並為此孜孜不倦,其精神積極而進取,其情懷浪漫而奇崛,其處世圓融而智慧,所謂「清靜無為」,不過是探尋天道的一個法門,不過是身處亂世一個小小的智慧罷了,哪裡是莊子的全部呢?
讀莊子,要先瞭解莊子的積極進取之智慧,再談清靜無為等法門,故此,《莊子》的開篇便是〈逍遙遊〉,先樹立境界,然後才是其他各篇的詳細辨析。
在〈逍遙遊〉一篇裡,莊子煌煌數言,侃侃而談,羅列神奇,講述了鯤鵬之大與蜩鳩之小,講述了宋榮子笑看世事與列子御風而行,講述了不龜手之藥與大瓠之用,凡此種種,多篇對比的故事,其實都指向一個命題:逍遙遊的本質——「知道」。
如何能夠「逍遙遊」?莊子的答案是:要認清大小的本質,要明瞭自己的位置,要知曉自己的不足,要開拓思路、追求更高遠的境界。這便是所謂「知道」:探知己之道,明知己之道不如天之道,求知天之道。
郭象對此有一段非常精要的評述: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這即是說:
其一,明確差距。要承認小和大是有區別和差距的。莊子常常有「大即是小,小即是大」的闡述,但那只是看問題的方法,它只是辨明事物的相對論,並不是否定小和大的本來面貌。
其二,不爭勝負。小與大的區別不重要,不必爭出勝負。小和大只是生命中不同的階段,若是執著於其中的高下,又何以「逍遙」?
其三,自得其分。要「自得」,要「各當其分」。小有小的追求,大有大的目標,應當各自為此而努力,「物任其性,事稱其能」。
由此,我們便大略可以看出,其實莊子的學說充滿了進取的精神,而且,很有手段,很有方法,不用蠻力,尊崇智慧。至於「清靜無為」等號召,不過是揚棄與進取的法門而已,並非是真正的目標所在。
總之,富有大智慧的進取心,逍遙於本我,才是莊子學說的真諦,而如何獲得逍遙之遊,便是進入莊學的門徑。故此,整本《莊子》,開宗明義,第一篇便是〈逍遙遊〉。
不龜手之藥有用還是無用?
【逍遙遊寓言之三:若有大知,便成大用】
惠子故意用一個問題來難為莊子:有一個特別大的葫蘆,能夠怎麼用呢?在此,他還特意加上了兩個限定條件:其一,葫蘆不夠結實,若是裝水就會被壓裂;其二,若是剖成瓢則太大了,沒有容納的地方。
從這兩個條件可以看出,這是惠子特意設置的難題之局。葫蘆的通常用途無非就是兩個,裝水或者剖瓢,而惠子特意把這兩個選項全部封死,既不能裝水,又不能做瓢,還有什麼用途呢?難道莊子竟會硬生生變出來一個嗎?
面對惠子這兩個奇怪的限定,莊子一眼看破,並且用一句話便占據了上風:「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其實就是在批評惠子說:小知不及大知,你沒有我這樣的大知,何敢前來挑戰!
其實此時莊子心中已有答案,但若是直截了當地給出,則不過一兩句話而已,氣勢上顯得不夠充足,於是他便先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宋人有不龜手之藥,卻沒有「大知」,只能用於漂洗絲絮;某位客人卻很識貨,將之獻給吳王,用於保衛國家的戰爭,以此獲得封地。這位客人顯然比宋人要高明多了,而且,宋人世世代代聚族而謀,其價值才值數金,連客人隨手甩來的百金都遠遠難比。如此,小知與大知,宋人與客人,惠子與莊子,究竟誰更高明,還用說嗎?
做足氣勢之後,莊子也給出了他的答案:何不繫於腰身,借助於它的浮力而遍遊江湖呢?如此一來,這便不再是個通常的葫蘆,只能用於盛水、盛物,而是成了世所罕見的寶物了!
這真是一個具有大智慧的回答!老子也曾經說過:「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既然不許用這個葫蘆盛水、盛物,那麼乾脆發揮其更「無」之用。看問題換一個角度,提升一個層次,果然就能變廢為寶。
至此,莊子大獲全勝,便趁勢給出最後一擊,直接面斥惠子,稱他的心被茅草堵塞了。其實,堵塞惠子之心的哪裡是蓬草呢?明明是缺乏敬畏與故步自封使然。
這一段,莊子先是進行「固拙於用大」的嘲笑,再是「聚族而謀」而不成的諷刺,又是「有蓬之心」的直斥,對惠子酣暢淋漓的三連擊,正向我們展示了「小知不及大知」的道理,他就像飛在九萬里高空的逍遙的大鵬,充分地展示了「大知」的愉悅和暢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涂,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樑,不避高下;中於機闢,死於罔罟。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徬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無何有之鄉即是我心
【逍遙遊寓言之四:若知天道,便是逍遙】
惠子在第一個問題上完敗,很不服氣,計上心來,又有了第二個問題:大而無用的樹,其意義在哪裡呢?
和上一個問題很相似,惠子也是一上來就進行了各種限定,勾畫出一棵既不中繩墨又不中規矩的樹。大概是惠子認為在上一個題目中還是給莊子鑽了空子,故而在這個題目中,特意地堵上所有的可能,直接定義這棵樹「大而無用」,以至「眾所同去」,無人認為它有用。
即便如此,莊子也依然對答如流,而且也先講了一個小故事:小獸善於捕鼠,卻也容易因此而死;犛牛不會捕鼠,卻不屑於此。
這個故事暗諷了惠子思維的侷限:某些具體的技能,比如捕鼠,必然有其侷限所在,怎能成為評價一切的標準呢?
如此一來,惠子佈下的困局便又被莊子破解了:工匠們所謂「無用」的評價,就如同捕鼠的技能一樣,怎能成為評價一切的標準呢?工匠們的「無用」,也正是生命的「有用」,且讓它自由地成長,不必擔心斧頭的加害,該有多麼好呢!
雖然惠子兩次出的題目很類似,但這一次莊子的回答卻完全不同:莊子從全新的角度闡述了小大之辯的方法論,所謂「用」也可以辯證地轉化。
如果說,在第一個問題上,惠子是為了較量智慧,那麼,在第二個問題上,惠子便純粹是為了駁倒莊子而辯論了。對此,莊子則給出了十分漂亮的回應:糾結於爭辯是毫無意義的,不如追逐智慧的增長,瞭解並順應天道,才是真諦。
在這一節,莊子一改之前咄咄逼人的口吻,而是乾脆俐落地進行解答。——既然棒喝也無法使對方醒悟,又何必再糾纏呢?不如將大智慧直接展示出來吧!然後便抽身而去,不必在此多做停留。
本篇名為〈逍遙遊〉,前半段在展示不同的角度看待逍遙的視角,以此立言,後半段共有四個寓言,前兩個寓言用來打破執念,後兩個寓言展示逍遙之境。怎樣才能展示逍遙呢?最妙的當然是立言者莊子親力親為——只有大鵬飛到了南冥,才會得到《齊諧》的認可,人間之事不都是如此嗎?
故此,莊子在上一個故事中展示了智慧的表象,在這個故事中又展示了智慧的境界。大知便是逍遙,大知便是天道。若是能像莊子這棵大樹一樣,將自己樹立在「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人世間的種種糾纏又怎能使其困苦呢?何愁不逍遙呢?
所謂「無何有之鄉」,並非處所,而是心境。世間既有至人,也有神人和聖人,只要「定乎內外之分」,便可以「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便可以不斷地達到更高的境界。同在一個俗世之中,惠子視莊子為辯論的敵手,木匠們看他是無用的大樹,其實他是無何有之鄉的無限逍遙。
世人多認為莊子承襲老子衣鉢,「清靜無為」,然而,在〈逍遙遊〉的開篇,莊子便展示了他宏大的志願——魚子化為巨鯤,鯤化為鵬,鵬怒而飛,身在北冥,卻又追逐南冥,不遺餘力——試問,這哪裡是「無為」呢?
其實,莊子之人生宏願便是探尋天道,並為此孜孜不倦,其精神積極而進取,其情懷浪漫而奇崛,其處世圓融而智慧,所謂「清靜無為」,不過是探尋天道的一個法門,不過是身處亂世一個小小的智慧罷了,哪裡是莊子的全部呢?
讀莊子,要先瞭解莊子的積極進取之智慧,再談清靜無為等法門,故此,《莊子》的開篇便是〈逍遙遊〉,先樹立境界,然後才是其他各篇的詳細辨析。
在〈逍遙遊〉一篇裡,莊子煌煌數言,侃侃而談,羅列神奇,講述了鯤鵬之大與蜩鳩之小,講述了宋榮子笑看世事與列子御風而行,講述了不龜手之藥與大瓠之用,凡此種種,多篇對比的故事,其實都指向一個命題:逍遙遊的本質——「知道」。
如何能夠「逍遙遊」?莊子的答案是:要認清大小的本質,要明瞭自己的位置,要知曉自己的不足,要開拓思路、追求更高遠的境界。這便是所謂「知道」:探知己之道,明知己之道不如天之道,求知天之道。
郭象對此有一段非常精要的評述: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這即是說:
其一,明確差距。要承認小和大是有區別和差距的。莊子常常有「大即是小,小即是大」的闡述,但那只是看問題的方法,它只是辨明事物的相對論,並不是否定小和大的本來面貌。
其二,不爭勝負。小與大的區別不重要,不必爭出勝負。小和大只是生命中不同的階段,若是執著於其中的高下,又何以「逍遙」?
其三,自得其分。要「自得」,要「各當其分」。小有小的追求,大有大的目標,應當各自為此而努力,「物任其性,事稱其能」。
由此,我們便大略可以看出,其實莊子的學說充滿了進取的精神,而且,很有手段,很有方法,不用蠻力,尊崇智慧。至於「清靜無為」等號召,不過是揚棄與進取的法門而已,並非是真正的目標所在。
總之,富有大智慧的進取心,逍遙於本我,才是莊子學說的真諦,而如何獲得逍遙之遊,便是進入莊學的門徑。故此,整本《莊子》,開宗明義,第一篇便是〈逍遙遊〉。
不龜手之藥有用還是無用?
【逍遙遊寓言之三:若有大知,便成大用】
惠子故意用一個問題來難為莊子:有一個特別大的葫蘆,能夠怎麼用呢?在此,他還特意加上了兩個限定條件:其一,葫蘆不夠結實,若是裝水就會被壓裂;其二,若是剖成瓢則太大了,沒有容納的地方。
從這兩個條件可以看出,這是惠子特意設置的難題之局。葫蘆的通常用途無非就是兩個,裝水或者剖瓢,而惠子特意把這兩個選項全部封死,既不能裝水,又不能做瓢,還有什麼用途呢?難道莊子竟會硬生生變出來一個嗎?
面對惠子這兩個奇怪的限定,莊子一眼看破,並且用一句話便占據了上風:「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其實就是在批評惠子說:小知不及大知,你沒有我這樣的大知,何敢前來挑戰!
其實此時莊子心中已有答案,但若是直截了當地給出,則不過一兩句話而已,氣勢上顯得不夠充足,於是他便先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宋人有不龜手之藥,卻沒有「大知」,只能用於漂洗絲絮;某位客人卻很識貨,將之獻給吳王,用於保衛國家的戰爭,以此獲得封地。這位客人顯然比宋人要高明多了,而且,宋人世世代代聚族而謀,其價值才值數金,連客人隨手甩來的百金都遠遠難比。如此,小知與大知,宋人與客人,惠子與莊子,究竟誰更高明,還用說嗎?
做足氣勢之後,莊子也給出了他的答案:何不繫於腰身,借助於它的浮力而遍遊江湖呢?如此一來,這便不再是個通常的葫蘆,只能用於盛水、盛物,而是成了世所罕見的寶物了!
這真是一個具有大智慧的回答!老子也曾經說過:「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既然不許用這個葫蘆盛水、盛物,那麼乾脆發揮其更「無」之用。看問題換一個角度,提升一個層次,果然就能變廢為寶。
至此,莊子大獲全勝,便趁勢給出最後一擊,直接面斥惠子,稱他的心被茅草堵塞了。其實,堵塞惠子之心的哪裡是蓬草呢?明明是缺乏敬畏與故步自封使然。
這一段,莊子先是進行「固拙於用大」的嘲笑,再是「聚族而謀」而不成的諷刺,又是「有蓬之心」的直斥,對惠子酣暢淋漓的三連擊,正向我們展示了「小知不及大知」的道理,他就像飛在九萬里高空的逍遙的大鵬,充分地展示了「大知」的愉悅和暢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涂,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樑,不避高下;中於機闢,死於罔罟。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徬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無何有之鄉即是我心
【逍遙遊寓言之四:若知天道,便是逍遙】
惠子在第一個問題上完敗,很不服氣,計上心來,又有了第二個問題:大而無用的樹,其意義在哪裡呢?
和上一個問題很相似,惠子也是一上來就進行了各種限定,勾畫出一棵既不中繩墨又不中規矩的樹。大概是惠子認為在上一個題目中還是給莊子鑽了空子,故而在這個題目中,特意地堵上所有的可能,直接定義這棵樹「大而無用」,以至「眾所同去」,無人認為它有用。
即便如此,莊子也依然對答如流,而且也先講了一個小故事:小獸善於捕鼠,卻也容易因此而死;犛牛不會捕鼠,卻不屑於此。
這個故事暗諷了惠子思維的侷限:某些具體的技能,比如捕鼠,必然有其侷限所在,怎能成為評價一切的標準呢?
如此一來,惠子佈下的困局便又被莊子破解了:工匠們所謂「無用」的評價,就如同捕鼠的技能一樣,怎能成為評價一切的標準呢?工匠們的「無用」,也正是生命的「有用」,且讓它自由地成長,不必擔心斧頭的加害,該有多麼好呢!
雖然惠子兩次出的題目很類似,但這一次莊子的回答卻完全不同:莊子從全新的角度闡述了小大之辯的方法論,所謂「用」也可以辯證地轉化。
如果說,在第一個問題上,惠子是為了較量智慧,那麼,在第二個問題上,惠子便純粹是為了駁倒莊子而辯論了。對此,莊子則給出了十分漂亮的回應:糾結於爭辯是毫無意義的,不如追逐智慧的增長,瞭解並順應天道,才是真諦。
在這一節,莊子一改之前咄咄逼人的口吻,而是乾脆俐落地進行解答。——既然棒喝也無法使對方醒悟,又何必再糾纏呢?不如將大智慧直接展示出來吧!然後便抽身而去,不必在此多做停留。
本篇名為〈逍遙遊〉,前半段在展示不同的角度看待逍遙的視角,以此立言,後半段共有四個寓言,前兩個寓言用來打破執念,後兩個寓言展示逍遙之境。怎樣才能展示逍遙呢?最妙的當然是立言者莊子親力親為——只有大鵬飛到了南冥,才會得到《齊諧》的認可,人間之事不都是如此嗎?
故此,莊子在上一個故事中展示了智慧的表象,在這個故事中又展示了智慧的境界。大知便是逍遙,大知便是天道。若是能像莊子這棵大樹一樣,將自己樹立在「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人世間的種種糾纏又怎能使其困苦呢?何愁不逍遙呢?
所謂「無何有之鄉」,並非處所,而是心境。世間既有至人,也有神人和聖人,只要「定乎內外之分」,便可以「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便可以不斷地達到更高的境界。同在一個俗世之中,惠子視莊子為辯論的敵手,木匠們看他是無用的大樹,其實他是無何有之鄉的無限逍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