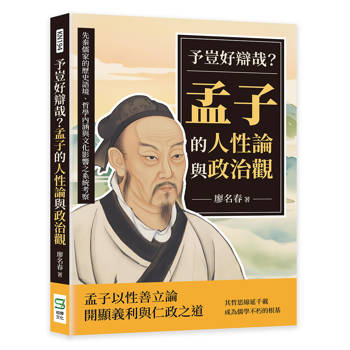第五章 民貴君輕
第一節 民本與民主
民本與民主,現在人們一般都認為這是兩個本質上不同的概念,這是很有道理的。所謂民本,即民為君本,民為邦本。這裡的「民」,指的是與「君」相對的所有人,既包括了平民、奴隸,也包括了貴族,但一般是指平民百姓,指以農民為主體的被統治者。 「本」,《說文》云:「木下曰本。」本即樹根,引申為指事物在空間上的基礎或時間上的起點,可以衍生和維繫他物,是他物之存在不可缺少的條件。「民本」就是說民是君王的資本、憑藉。由於「朕即國家」,君主是國家、社稷的代表,所以「民本」又含有民是國家、社稷的基礎的意義。先秦時期出現的「重民」、「保民」、「愛民」、「仁民」、「恤民」、「息民」、「得民」、「裕民」、「利民」等概念,都屬於民本論的範疇。它們的核心都是重民。為什麼要重民呢?因為民為君本,民為邦本,民是君王的資本,是國家社稷的基礎。君主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就必須要將君民矛盾調節在一定範圍內,以保證「水」不覆「舟」。所以,民本論是以維護君權為目的的一種重民思想,是建立在君、民不平等基礎上的,主張君主要愛惜百姓、重視自己的統治資本。
「民主」一詞,源於希臘文,由「人民」和「權力」兩個詞合成,意為「人民的權力」或「主權在民」。從狹義上說,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一種國家形態」。作為一種政體,「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 ,意味著少數服從多數,意味著排除個人的專斷。從廣義上說,凡是遵循或展現平等原則,主張少數服從多數,反抗專制的政策、法令、制度、思想及各種行事,都可以冠以「民主」之稱,所以,民主的實質就是「民為主」。
由此可知,儘管「民本」與「民主」這兩個概念都有重民的內涵,但其出發點有著本質的不同。民本是以君為本位,視民為君王事業的資本,故要重視民眾。實質上,在民與君的關係上,君是第一位的,民是第二位的;君是出發點,而民只是達到目的的工具。而民主卻不然,它不但重民,而且以民為本位,在民與君的關係上,民是第一位的,君是其次的;民是君的出發點,而君只是民的工具。
正因為民主是對君主專制的否定,而民本論卻是對君主專制的維護,所以歷史上的專制君主們可以容忍民本思想,採納民本學說,而對於民主思想,他們往往會加以排斥,因為這觸動了他們的根本利益。
釐清了「民本」和「民主」概念的內涵,再來看人們對歷史上特別是先秦時期民本思想的認識,就會發現有很多的分歧。
曾有學者提出,先秦不存在「民本」論,只有「重民」論。因為「民本」一詞,出自《尚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一語。而〈五子之歌〉係後人偽作,「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一語經閻若璩考定係竊自《淮南子.泰族訓》。因此,於先秦最好稱「重民」而不應稱「民本」,「民本」一詞非先秦所有。
此說有待商榷。姑且不論《淮南子》一書材料多出自先秦,且就現在公認的先秦文獻而言,「民本」的提法也並不罕見。如《管子.霸形》云:「管仲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這是說齊國百姓為齊桓公圖霸王之業的資本和憑藉,是所謂民為君本說。又如《管子.霸言》云:「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這裡的「人」和「理」,可能為唐寫本避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諱所致:「以人為本」即「以民為本」,「本理則國固」即「本治則國固」。《嬰子春秋》(曾有學者疑其非先秦之書 ,不過現銀雀山漢簡中就有《晏子》 ,可見其屬先秦作品無疑)也兩次提到「民本」,《內篇.問上》說:「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內篇.問下》則說:「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孟子》中也有一段話可與此相互證明:「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上〉)這裡的「家」,不是「大夫曰家」的家,而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家庭。身,指個人,實指一般意義上的民。諸侯的國是天下的基礎,家庭是國的基礎,而個人又是家的基礎。換言之,就是說人是天下國家之本。人,絕大部分都是民,所以孟子之意也是說民是國之本。因此,認為先秦時期沒有「民本」的提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近代以前的中國,沒有「民為主」意義上的「民主」概念。先秦文獻如《尚書》、《左傳》等,雖屢屢提及「民主」,如「簡代夏作民主」、「天惟時求民主」、「其語偷,不似民主」等,但其含義皆非「民為主」,而是「民之主」。因此,現在很多人都認為,古代,特別是先秦時期,中國只有民本思想而無民主思想。這種認知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特別是不符合孟子思想的實際。因為它沒有分清什麼是民本思想,什麼是民主思想,結果把前人的民主思想也誤認為民本思想。我們分析孟子思想,尤其要注意區分這兩種既有連繫又有本質區別的思想。
第一節 民本與民主
民本與民主,現在人們一般都認為這是兩個本質上不同的概念,這是很有道理的。所謂民本,即民為君本,民為邦本。這裡的「民」,指的是與「君」相對的所有人,既包括了平民、奴隸,也包括了貴族,但一般是指平民百姓,指以農民為主體的被統治者。 「本」,《說文》云:「木下曰本。」本即樹根,引申為指事物在空間上的基礎或時間上的起點,可以衍生和維繫他物,是他物之存在不可缺少的條件。「民本」就是說民是君王的資本、憑藉。由於「朕即國家」,君主是國家、社稷的代表,所以「民本」又含有民是國家、社稷的基礎的意義。先秦時期出現的「重民」、「保民」、「愛民」、「仁民」、「恤民」、「息民」、「得民」、「裕民」、「利民」等概念,都屬於民本論的範疇。它們的核心都是重民。為什麼要重民呢?因為民為君本,民為邦本,民是君王的資本,是國家社稷的基礎。君主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就必須要將君民矛盾調節在一定範圍內,以保證「水」不覆「舟」。所以,民本論是以維護君權為目的的一種重民思想,是建立在君、民不平等基礎上的,主張君主要愛惜百姓、重視自己的統治資本。
「民主」一詞,源於希臘文,由「人民」和「權力」兩個詞合成,意為「人民的權力」或「主權在民」。從狹義上說,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一種國家形態」。作為一種政體,「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 ,意味著少數服從多數,意味著排除個人的專斷。從廣義上說,凡是遵循或展現平等原則,主張少數服從多數,反抗專制的政策、法令、制度、思想及各種行事,都可以冠以「民主」之稱,所以,民主的實質就是「民為主」。
由此可知,儘管「民本」與「民主」這兩個概念都有重民的內涵,但其出發點有著本質的不同。民本是以君為本位,視民為君王事業的資本,故要重視民眾。實質上,在民與君的關係上,君是第一位的,民是第二位的;君是出發點,而民只是達到目的的工具。而民主卻不然,它不但重民,而且以民為本位,在民與君的關係上,民是第一位的,君是其次的;民是君的出發點,而君只是民的工具。
正因為民主是對君主專制的否定,而民本論卻是對君主專制的維護,所以歷史上的專制君主們可以容忍民本思想,採納民本學說,而對於民主思想,他們往往會加以排斥,因為這觸動了他們的根本利益。
釐清了「民本」和「民主」概念的內涵,再來看人們對歷史上特別是先秦時期民本思想的認識,就會發現有很多的分歧。
曾有學者提出,先秦不存在「民本」論,只有「重民」論。因為「民本」一詞,出自《尚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一語。而〈五子之歌〉係後人偽作,「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一語經閻若璩考定係竊自《淮南子.泰族訓》。因此,於先秦最好稱「重民」而不應稱「民本」,「民本」一詞非先秦所有。
此說有待商榷。姑且不論《淮南子》一書材料多出自先秦,且就現在公認的先秦文獻而言,「民本」的提法也並不罕見。如《管子.霸形》云:「管仲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這是說齊國百姓為齊桓公圖霸王之業的資本和憑藉,是所謂民為君本說。又如《管子.霸言》云:「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這裡的「人」和「理」,可能為唐寫本避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諱所致:「以人為本」即「以民為本」,「本理則國固」即「本治則國固」。《嬰子春秋》(曾有學者疑其非先秦之書 ,不過現銀雀山漢簡中就有《晏子》 ,可見其屬先秦作品無疑)也兩次提到「民本」,《內篇.問上》說:「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內篇.問下》則說:「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孟子》中也有一段話可與此相互證明:「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上〉)這裡的「家」,不是「大夫曰家」的家,而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家庭。身,指個人,實指一般意義上的民。諸侯的國是天下的基礎,家庭是國的基礎,而個人又是家的基礎。換言之,就是說人是天下國家之本。人,絕大部分都是民,所以孟子之意也是說民是國之本。因此,認為先秦時期沒有「民本」的提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近代以前的中國,沒有「民為主」意義上的「民主」概念。先秦文獻如《尚書》、《左傳》等,雖屢屢提及「民主」,如「簡代夏作民主」、「天惟時求民主」、「其語偷,不似民主」等,但其含義皆非「民為主」,而是「民之主」。因此,現在很多人都認為,古代,特別是先秦時期,中國只有民本思想而無民主思想。這種認知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特別是不符合孟子思想的實際。因為它沒有分清什麼是民本思想,什麼是民主思想,結果把前人的民主思想也誤認為民本思想。我們分析孟子思想,尤其要注意區分這兩種既有連繫又有本質區別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