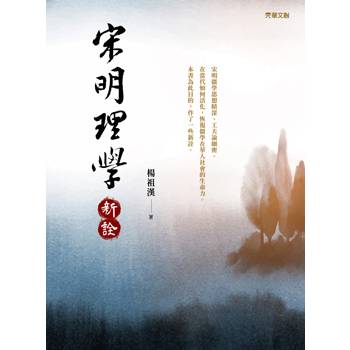緒論:如何活化宋明理學的智慧
一、引論:藉陳寅恪先生之言論宋明義理如何活化
清儒在異族入主,文字獄的威脅下,又兼以宋儒的思想學術的爭論,如朱陸異同問題之不能解決,希望從探究經典的原意,來定學術上的是非,於是重視訓詁考據,不能承繼宋明理學的講學傳統,也喪失了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1919-2017)在《中國的自由傳統》書上所說的,通過論學而表現精神的高度自由的境界。當代新儒家認為,民國以來的思想界所以不上軌道,是由於清代專制政治與文字獄的壓迫,使學者埋首於考據、聲韻訓詁的研究,理學的研究雖然維持官學的地位,但也喪失了士以天下為己任,擔當世運的精神,成為為清廷的統治者而服務的御用學者,完全喪失了宋明理學家的講學精神與氣概,這一傳統的衰弱也等於是哲學的思辨、概念性的思維能力的衰退,造成面對清中葉以來的西方軍事、學術、宗教等衝擊而不能作出合理回應的悲劇。這應該是近世中華民族或中華文化整體性的衰敗的重要原因。固然不能因此便認為恢復宋明的講學精神,讀書人的氣概,就可以成功地回應西方文化的衝擊,但恢復這一精神傳統是振興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所必要的,此意唐君毅(1909-1978)先生有詳細的論述。
牟宗三(1909-1995)先生曾表示,要讀懂宋明理學家的書,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強烈的道德意識;二是深入的哲學性的思考。儒學當然是要顯發人生命中的道德意識,如果沒有這方面的體會,是很難讀進去的,而宋明儒對於心性本體與工夫論的討論非常詳細,沒有思辨的訓練及興趣,也很難深入其中的義理。照牟先生這個說法,宋明儒學應該是很難普及的,並非為一般人所樂於閱讀的。但在當代的華文學界,對於宋明儒的研究,不能說不興盛,一些宋明理學普及性的著作,如《近思錄》、《傳習錄》等,不斷有新的註解本出版,讀者也不少,何以會是如此呢?最近重看陳寅恪(1890-1969)先生評馮友蘭(1895-1990)《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覺得有些意思非常精到,表現了史學家的疏通致遠,指出了宋明儒所以成為重要的學術成就及未來中國學術思想發展該走的途徑。陳先生此文所表達的意思,很受學界注意,也頗引起討論,由於他文中之意很能引發我對於宋明理學的智慧如何活化的思考,後面還是引用他的原文來展開論述。他說:
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此書於朱子之學多所發明。昔閻百詩在清初以辨偽觀念,陳蘭甫在清季以考據觀念,而治朱子之學,皆有所創獲。今此書作者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而多新鮮。
陳先生引用佛教《法華經》「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之說,來形容宋明理學的興起在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認為從秦以後到現在兩千年來的學術思想的發展,是為了達成「產生宋明理學」這個目的,這是作為大史學家的陳先生對中國學術思想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判斷,應該是表示了宋明理學雖然是承接先秦儒學的思想,但也必須通過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及南北朝佛教與道教的長期發展、衝擊,而醞釀成功,使中國的民族文化的精神重新回到儒學,而此時的儒學,卻又有非常豐富而不同於先秦儒學的內容與面目。這樣說固然表達了宋明理學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但好像給出一個宋明理學是儒與道、佛融合的思想理論。如果是這樣了解,當然是不必合於深入宋明儒的著作,對理學的思想內容,作仔細研究的學者的看法。如牟宗三先生認為,一般學者常認為宋儒的義理是陽儒陰釋或陽儒陰道,這是對宋明理學的不了解,宋明儒的義理純粹是儒學本質的表現,不能說混雜佛老的成分。當然牟先生也認為如果沒有道家與佛教的刺激,宋儒不會對先秦儒學的義理作進一步的發展,但所謂「刺激」是承認其外部的作用,而「影響」則是說內部義理有轉變,牟先生對此二語的意義作嚴格的區分,認為宋明儒是先秦儒學的進一步發展,二者的不同如同一個人生命不同階段的成長,雖有不同,但還是同一個人。說受佛老刺激可以,但不能說受影響。上引文陳寅恪則似從史學的角度看三教的相互的影響,並非內在地從宋明儒的思想本身上作衡量,觀點或重點與牟先生不同,應該不至於有衝突。從歷史發展的外部現象上來看,宋明儒當然是通過了玄學、佛教,或再加上道教的階段而重新反省先秦儒學的義理,對此歷史現象作一整體的掌握,就有陳先生的判斷。陳寅恪此處又表達了研究朱子(1130-1200)需要不斷引入新觀念,如閻若璩(1636-1704)用辨偽、陳澧(1810-1882)用考據來治朱子學,而都有發明,而現在馮友蘭在其哲學史書中所論述的朱子思想,是引入了西方哲學來對朱子學作詮釋,陳先生認為很有發明,而且有新鮮感,這就表示了陳先生認為馮著的詮釋,能夠活化宋明儒的義理。
馮友蘭先生此書中對於朱子學的詮釋,其實並不能為此領域的專家認同,如他認為朱子所說的理是共相之理,而理先氣後,是邏輯上在先之意,這些解釋是引入了新實在論的觀點來解釋理學。他另有《新理學》一書,更詳細表達了這種詮釋,而自詡為「接著講」,而並非「照著講」。但朱子哲學思想中的理,當然是道德之理,道德之理是人性中之理,也是天地萬物所以能存在之理,因此朱子所謂的「理在先」,是所謂形而上學的,作為存在物的根據之先,這是當代新儒家關於朱子學的研究的重要主張,應該是合理的,因此馮先生的「接著講」可能接得不妥當,而這一引入西方哲學的詮釋,影響了他對宋明理學的理解的合理性。雖然如此,陳寅恪先生的觀點仍然可以成立,就是宋明理學是秦以後各階段學術思想發展而成的重要目的,可以說是「正果」。而今後的中國學術,也會是順著宋明理學繼續發展,而所以能夠讓理學繼續發展,引進當代的其他學術思想,如西方哲學,來詮釋理學,是恰當的做法。他又說:
然新儒家之產生,關於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學說,其所受影響甚深且遠。自來述之者皆無愜意之作。〔……〕而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數百年間,道教變遷傳衍之始末,及其與儒佛二家互相關繫之事實,尚有待於研究。〔……〕釋迦之教義,無父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衝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易則決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長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盪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沈歇絕。近雖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終不能復振,其故匪他,以性質與環境互相方圓鑿枘,勢不得不然也。六朝以後之道教,包羅至廣,演變至繁。不以[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會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貫吸收。凡新儒家之學說,似無不有道教或與道教有關之佛教為之先導。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義最富之一宗也。(其創造者慧思所作〈誓願文〉,最足表現其思想。〔……〕)其宗徒梁敬之與李習之之關係,實啟新儒家開創之動機。
陳先生認為朱子思想中含有道教的成分,這個判斷或許需要商榷,但如果從作為宋儒開山的周濂溪(1017-1073)的思想與文獻上來看,至少從文字的表面意義,是用了道家的觀念來表達道的形上性格,如用「無極」來說明「太極」;用「無為」來形容「誠」;用「無思而無不通」來說明聖人境界。固然儒學經典本來就可含上述的概念(也可以說上面種種意義),但沒有道家或道教的刺激,周濂溪應該不會運用這些概念來說明他所體會到的道體的意義。說宋儒是從釋、道的思想衝擊,而回到先秦儒家,於是對儒家的義理,不期然地採用了異教而卻又是相應的概念來說明,這一做法使儒學深化而又有新鮮的面貌,這也是陳寅恪所說佛道思想的長期發展,是以產生宋明理學為目的,為大事因緣的看法之由來。從陳先生這一根據歷史發展而給出來的判斷,可以看到宋明理學的重要地位。陳先生認為道教對於理學的成立有大的影響,對此他作了強調,而且就道教的吸收外來思想宗教的態度,給出了重要的觀察,即他認為道教既努力吸收外來文化,又沒有忘掉本身的民族立場。他認為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之重要,與影響之大,是由於成為政治制度或立法的依據,但在思想深度上,並不如釋道二教。他言下之意,是宋明儒的思想由於佛老的影響而得以深化,而不同先秦儒學。而道教在思想義理上,與政治的牽連不深,於是在思想上就容易融貫吸收。這應該表示了他認為佛教傳入中國,需要以道家思想為中介,而道教融合了佛教及其他宗教的思想,對於促成宋明理學的成立有重要的貢獻,這一看法大體上合乎歷史的事實。他又認為中國大乘佛學中的天台宗,是道教思想成分最多的佛教宗派,陳先生應是從慧思(515-577)的〈誓願文〉中有道教求長生的思想來說的;但天台宗教義的真正確立者智顗(538-597),其思想恐怕與道教的思想並無密切關係,因此陳先生此說可能有問題,或有需要進一步說明的地方,但此看法很有啟發性。天台宗是屬於實相學,對於般若空宗的義理有特別的體會,而般若智證空與道家思想相近,但不能據此就說天台宗思想含有道教的成分,陳先生是以天台初祖慧思的思想為據。但天台宗真正的奠基者智顗之判教論對於東來種種佛法,判攝罄無不盡,其圓教理論不能只從般若實相一脈來說明,如牟宗三先生所說,天台圓教除了有「般若作用的圓」的空宗的說法外,還有「存有論的圓」,即一念三千、三道即三德,佛即九法界而為佛的理論,來對一切法的根源作說明,而比大乘起信論的說法更為完備。即是說存有論的圓與般若作用的圓,兩種說法合起來,才是天台圓教內容的全部,這當然不能用含有道教成分來概括。當然,道教的思想內容是否與天台宗的理論有關,是否如陳先生所舉的例證,可以再作研究。對於中國佛教的理論內容的理解是後學轉精,不能要求在陳先生那個時代的學人就有正確而深入的了解。在上引文,陳先生給出的看法有很值得參考的地方,即認為外來的學術思想,如果一成不變地在中土發展,是不能夠流傳久遠的。他舉唐玄奘(602-664)的法相唯識宗作為例證,此派二三傳而絕,民國初年雖然有歐陽漸(字竟無,1871-1943)等人提倡唯識學,而且認為此是佛學正宗,極力排斥《大乘起信論》所代表的真常唯心系的思想,陳先生認為也不可能使唯識學死灰復燃。於是他認為外來的思想哲學或宗教,如果要在中土長遠發展,一定要與中國文化的特性相融,即必須在傳播的過程中為中國的學者或信徒不斷地轉化,以融通固有的文化觀念。而中國固有的學術思想,也必須吸收外來的思想,這樣才能有創新而昌盛的發展。陳先生此論籠罩了或指出了未來的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方向,即一方面不能不吸收外來的思想學術,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失掉了本來民族的地位與立場,他說:
北宋之智圓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號中庸子,并自為傳以述其義。(孤山《閑居編》)其年代猶在司馬君實作《中庸廣義》之前。(孤山卒於宋真宗乾興元年,年四十七。)似亦於宋代新儒家為先覺。二者之間其關係如何,且不詳論。然舉此一例,已足見新儒家產生之問題,猶有未發之覆在也。至道教對輸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無不盡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說以後,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之教義。此種思想上之態度,自六朝時亦已如此。雖似相反,而實足以相成。從來新儒家即繼承此種遺業而能大成者。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詔示者也。
陳先生重視道教思想的兼收並蓄的特色,並以這種特色來說明宋代新儒家能夠開創儒學的新體系與新面目之故,其中宋儒與道教,及與天台山外派的孤山智圓(976-1022),是否有思想上的關係,這確有學者申述,但還不能有定論,而陳先生此意則非常有啟發性。天台宗雖未必與道教思想有密切的關聯,但天台圓教肯定九法界的存在,認為佛必須即於九法界而為佛,在天台宗與華嚴宗人對何謂真圓教的爭論中,強調了地獄餓鬼畜生以至於聲聞緣覺等九法界,都不能因成佛而斷絕,而批評華嚴宗是「緣理斷九」。於是人生一切可能的遭遇、狀況,都可以成為佛法身的示現,於是人只要通過實踐而有佛智或佛的知見,就可以不離開人生任何種種遭遇而為佛,這種成佛而不斷九法界,一切世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違的思想,如同牟宗三先生所說,是繞了一個大圈而肯定人生一切的存在。佛教雖然以緣起性空為宗旨,但並不否定世間任何一法的存在,九法界中的種種差別,也就是種種具體的人生情況,都因為可以是佛界呈現的場所,於是九法界都可以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這種思想很容易就轉成為宋儒肯定人間、肯定世界的看法。陳先生雖然不一定對天台宗的義理有上述的理解,但他看出了天台宗與宋儒的思想或許有其關聯性,實在非常有識見。他指出了唐末五代的佛教思想有往儒學的肯定世間的理論型態接近的趨勢,強調了天台宗孤山智圓肯定儒學,甚至自號中庸子的緣由,明白地說孤山智圓是宋儒學問的先覺。這裡等於點出了宋代理學所以能夠成為一個興發人心的學理,也就是活化了先秦儒學的緣故,宋儒義理如果只是先秦兩漢儒學的重複,不會對當時的社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陳先生此處認為道教思想與天台宗有關,藉道教的不排斥外來思想,但一面又堅守自己民族的立場,這一做法說明了宋代新儒家的策略,即與外來思想融為一體後,則堅持夷夏之論,這一說法十分深刻,可謂是表達了宋明理學的時代感受。或許可以補充一個例子,上述天台宗的圓教義理,其中為了要肯定一切法存在的必然性,有無明與法性同體之說,即表示在同一存在的事物(法)上,可以是無明煩惱的表現,也可以是清淨的法性之所在,這一思想在南宋胡宏(號五峰,1105-1161)有很清楚的表示,如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 ,很難說五峰對於佛教天台宗的說法沒有吸收,但五峰藉此圓說表達了儒家的義理,而且對佛教作出嚴格的批評,這好像也可以如同陳寅恪所說,融成一家之說後,則堅持夷夏之辨。陳先生此說確提示了今後儒學的理論如何能繼續發展並有其強大的生命力所需要有的做法,這裡表達了大史學家的宏觀識見。
一、引論:藉陳寅恪先生之言論宋明義理如何活化
清儒在異族入主,文字獄的威脅下,又兼以宋儒的思想學術的爭論,如朱陸異同問題之不能解決,希望從探究經典的原意,來定學術上的是非,於是重視訓詁考據,不能承繼宋明理學的講學傳統,也喪失了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1919-2017)在《中國的自由傳統》書上所說的,通過論學而表現精神的高度自由的境界。當代新儒家認為,民國以來的思想界所以不上軌道,是由於清代專制政治與文字獄的壓迫,使學者埋首於考據、聲韻訓詁的研究,理學的研究雖然維持官學的地位,但也喪失了士以天下為己任,擔當世運的精神,成為為清廷的統治者而服務的御用學者,完全喪失了宋明理學家的講學精神與氣概,這一傳統的衰弱也等於是哲學的思辨、概念性的思維能力的衰退,造成面對清中葉以來的西方軍事、學術、宗教等衝擊而不能作出合理回應的悲劇。這應該是近世中華民族或中華文化整體性的衰敗的重要原因。固然不能因此便認為恢復宋明的講學精神,讀書人的氣概,就可以成功地回應西方文化的衝擊,但恢復這一精神傳統是振興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所必要的,此意唐君毅(1909-1978)先生有詳細的論述。
牟宗三(1909-1995)先生曾表示,要讀懂宋明理學家的書,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強烈的道德意識;二是深入的哲學性的思考。儒學當然是要顯發人生命中的道德意識,如果沒有這方面的體會,是很難讀進去的,而宋明儒對於心性本體與工夫論的討論非常詳細,沒有思辨的訓練及興趣,也很難深入其中的義理。照牟先生這個說法,宋明儒學應該是很難普及的,並非為一般人所樂於閱讀的。但在當代的華文學界,對於宋明儒的研究,不能說不興盛,一些宋明理學普及性的著作,如《近思錄》、《傳習錄》等,不斷有新的註解本出版,讀者也不少,何以會是如此呢?最近重看陳寅恪(1890-1969)先生評馮友蘭(1895-1990)《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覺得有些意思非常精到,表現了史學家的疏通致遠,指出了宋明儒所以成為重要的學術成就及未來中國學術思想發展該走的途徑。陳先生此文所表達的意思,很受學界注意,也頗引起討論,由於他文中之意很能引發我對於宋明理學的智慧如何活化的思考,後面還是引用他的原文來展開論述。他說:
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此書於朱子之學多所發明。昔閻百詩在清初以辨偽觀念,陳蘭甫在清季以考據觀念,而治朱子之學,皆有所創獲。今此書作者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而多新鮮。
陳先生引用佛教《法華經》「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之說,來形容宋明理學的興起在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認為從秦以後到現在兩千年來的學術思想的發展,是為了達成「產生宋明理學」這個目的,這是作為大史學家的陳先生對中國學術思想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判斷,應該是表示了宋明理學雖然是承接先秦儒學的思想,但也必須通過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及南北朝佛教與道教的長期發展、衝擊,而醞釀成功,使中國的民族文化的精神重新回到儒學,而此時的儒學,卻又有非常豐富而不同於先秦儒學的內容與面目。這樣說固然表達了宋明理學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但好像給出一個宋明理學是儒與道、佛融合的思想理論。如果是這樣了解,當然是不必合於深入宋明儒的著作,對理學的思想內容,作仔細研究的學者的看法。如牟宗三先生認為,一般學者常認為宋儒的義理是陽儒陰釋或陽儒陰道,這是對宋明理學的不了解,宋明儒的義理純粹是儒學本質的表現,不能說混雜佛老的成分。當然牟先生也認為如果沒有道家與佛教的刺激,宋儒不會對先秦儒學的義理作進一步的發展,但所謂「刺激」是承認其外部的作用,而「影響」則是說內部義理有轉變,牟先生對此二語的意義作嚴格的區分,認為宋明儒是先秦儒學的進一步發展,二者的不同如同一個人生命不同階段的成長,雖有不同,但還是同一個人。說受佛老刺激可以,但不能說受影響。上引文陳寅恪則似從史學的角度看三教的相互的影響,並非內在地從宋明儒的思想本身上作衡量,觀點或重點與牟先生不同,應該不至於有衝突。從歷史發展的外部現象上來看,宋明儒當然是通過了玄學、佛教,或再加上道教的階段而重新反省先秦儒學的義理,對此歷史現象作一整體的掌握,就有陳先生的判斷。陳寅恪此處又表達了研究朱子(1130-1200)需要不斷引入新觀念,如閻若璩(1636-1704)用辨偽、陳澧(1810-1882)用考據來治朱子學,而都有發明,而現在馮友蘭在其哲學史書中所論述的朱子思想,是引入了西方哲學來對朱子學作詮釋,陳先生認為很有發明,而且有新鮮感,這就表示了陳先生認為馮著的詮釋,能夠活化宋明儒的義理。
馮友蘭先生此書中對於朱子學的詮釋,其實並不能為此領域的專家認同,如他認為朱子所說的理是共相之理,而理先氣後,是邏輯上在先之意,這些解釋是引入了新實在論的觀點來解釋理學。他另有《新理學》一書,更詳細表達了這種詮釋,而自詡為「接著講」,而並非「照著講」。但朱子哲學思想中的理,當然是道德之理,道德之理是人性中之理,也是天地萬物所以能存在之理,因此朱子所謂的「理在先」,是所謂形而上學的,作為存在物的根據之先,這是當代新儒家關於朱子學的研究的重要主張,應該是合理的,因此馮先生的「接著講」可能接得不妥當,而這一引入西方哲學的詮釋,影響了他對宋明理學的理解的合理性。雖然如此,陳寅恪先生的觀點仍然可以成立,就是宋明理學是秦以後各階段學術思想發展而成的重要目的,可以說是「正果」。而今後的中國學術,也會是順著宋明理學繼續發展,而所以能夠讓理學繼續發展,引進當代的其他學術思想,如西方哲學,來詮釋理學,是恰當的做法。他又說:
然新儒家之產生,關於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學說,其所受影響甚深且遠。自來述之者皆無愜意之作。〔……〕而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數百年間,道教變遷傳衍之始末,及其與儒佛二家互相關繫之事實,尚有待於研究。〔……〕釋迦之教義,無父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之制度無一不相衝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易則決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長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盪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沈歇絕。近雖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終不能復振,其故匪他,以性質與環境互相方圓鑿枘,勢不得不然也。六朝以後之道教,包羅至廣,演變至繁。不以[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會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貫吸收。凡新儒家之學說,似無不有道教或與道教有關之佛教為之先導。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義最富之一宗也。(其創造者慧思所作〈誓願文〉,最足表現其思想。〔……〕)其宗徒梁敬之與李習之之關係,實啟新儒家開創之動機。
陳先生認為朱子思想中含有道教的成分,這個判斷或許需要商榷,但如果從作為宋儒開山的周濂溪(1017-1073)的思想與文獻上來看,至少從文字的表面意義,是用了道家的觀念來表達道的形上性格,如用「無極」來說明「太極」;用「無為」來形容「誠」;用「無思而無不通」來說明聖人境界。固然儒學經典本來就可含上述的概念(也可以說上面種種意義),但沒有道家或道教的刺激,周濂溪應該不會運用這些概念來說明他所體會到的道體的意義。說宋儒是從釋、道的思想衝擊,而回到先秦儒家,於是對儒家的義理,不期然地採用了異教而卻又是相應的概念來說明,這一做法使儒學深化而又有新鮮的面貌,這也是陳寅恪所說佛道思想的長期發展,是以產生宋明理學為目的,為大事因緣的看法之由來。從陳先生這一根據歷史發展而給出來的判斷,可以看到宋明理學的重要地位。陳先生認為道教對於理學的成立有大的影響,對此他作了強調,而且就道教的吸收外來思想宗教的態度,給出了重要的觀察,即他認為道教既努力吸收外來文化,又沒有忘掉本身的民族立場。他認為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之重要,與影響之大,是由於成為政治制度或立法的依據,但在思想深度上,並不如釋道二教。他言下之意,是宋明儒的思想由於佛老的影響而得以深化,而不同先秦儒學。而道教在思想義理上,與政治的牽連不深,於是在思想上就容易融貫吸收。這應該表示了他認為佛教傳入中國,需要以道家思想為中介,而道教融合了佛教及其他宗教的思想,對於促成宋明理學的成立有重要的貢獻,這一看法大體上合乎歷史的事實。他又認為中國大乘佛學中的天台宗,是道教思想成分最多的佛教宗派,陳先生應是從慧思(515-577)的〈誓願文〉中有道教求長生的思想來說的;但天台宗教義的真正確立者智顗(538-597),其思想恐怕與道教的思想並無密切關係,因此陳先生此說可能有問題,或有需要進一步說明的地方,但此看法很有啟發性。天台宗是屬於實相學,對於般若空宗的義理有特別的體會,而般若智證空與道家思想相近,但不能據此就說天台宗思想含有道教的成分,陳先生是以天台初祖慧思的思想為據。但天台宗真正的奠基者智顗之判教論對於東來種種佛法,判攝罄無不盡,其圓教理論不能只從般若實相一脈來說明,如牟宗三先生所說,天台圓教除了有「般若作用的圓」的空宗的說法外,還有「存有論的圓」,即一念三千、三道即三德,佛即九法界而為佛的理論,來對一切法的根源作說明,而比大乘起信論的說法更為完備。即是說存有論的圓與般若作用的圓,兩種說法合起來,才是天台圓教內容的全部,這當然不能用含有道教成分來概括。當然,道教的思想內容是否與天台宗的理論有關,是否如陳先生所舉的例證,可以再作研究。對於中國佛教的理論內容的理解是後學轉精,不能要求在陳先生那個時代的學人就有正確而深入的了解。在上引文,陳先生給出的看法有很值得參考的地方,即認為外來的學術思想,如果一成不變地在中土發展,是不能夠流傳久遠的。他舉唐玄奘(602-664)的法相唯識宗作為例證,此派二三傳而絕,民國初年雖然有歐陽漸(字竟無,1871-1943)等人提倡唯識學,而且認為此是佛學正宗,極力排斥《大乘起信論》所代表的真常唯心系的思想,陳先生認為也不可能使唯識學死灰復燃。於是他認為外來的思想哲學或宗教,如果要在中土長遠發展,一定要與中國文化的特性相融,即必須在傳播的過程中為中國的學者或信徒不斷地轉化,以融通固有的文化觀念。而中國固有的學術思想,也必須吸收外來的思想,這樣才能有創新而昌盛的發展。陳先生此論籠罩了或指出了未來的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方向,即一方面不能不吸收外來的思想學術,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失掉了本來民族的地位與立場,他說:
北宋之智圓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號中庸子,并自為傳以述其義。(孤山《閑居編》)其年代猶在司馬君實作《中庸廣義》之前。(孤山卒於宋真宗乾興元年,年四十七。)似亦於宋代新儒家為先覺。二者之間其關係如何,且不詳論。然舉此一例,已足見新儒家產生之問題,猶有未發之覆在也。至道教對輸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無不盡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說以後,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之教義。此種思想上之態度,自六朝時亦已如此。雖似相反,而實足以相成。從來新儒家即繼承此種遺業而能大成者。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詔示者也。
陳先生重視道教思想的兼收並蓄的特色,並以這種特色來說明宋代新儒家能夠開創儒學的新體系與新面目之故,其中宋儒與道教,及與天台山外派的孤山智圓(976-1022),是否有思想上的關係,這確有學者申述,但還不能有定論,而陳先生此意則非常有啟發性。天台宗雖未必與道教思想有密切的關聯,但天台圓教肯定九法界的存在,認為佛必須即於九法界而為佛,在天台宗與華嚴宗人對何謂真圓教的爭論中,強調了地獄餓鬼畜生以至於聲聞緣覺等九法界,都不能因成佛而斷絕,而批評華嚴宗是「緣理斷九」。於是人生一切可能的遭遇、狀況,都可以成為佛法身的示現,於是人只要通過實踐而有佛智或佛的知見,就可以不離開人生任何種種遭遇而為佛,這種成佛而不斷九法界,一切世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違的思想,如同牟宗三先生所說,是繞了一個大圈而肯定人生一切的存在。佛教雖然以緣起性空為宗旨,但並不否定世間任何一法的存在,九法界中的種種差別,也就是種種具體的人生情況,都因為可以是佛界呈現的場所,於是九法界都可以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這種思想很容易就轉成為宋儒肯定人間、肯定世界的看法。陳先生雖然不一定對天台宗的義理有上述的理解,但他看出了天台宗與宋儒的思想或許有其關聯性,實在非常有識見。他指出了唐末五代的佛教思想有往儒學的肯定世間的理論型態接近的趨勢,強調了天台宗孤山智圓肯定儒學,甚至自號中庸子的緣由,明白地說孤山智圓是宋儒學問的先覺。這裡等於點出了宋代理學所以能夠成為一個興發人心的學理,也就是活化了先秦儒學的緣故,宋儒義理如果只是先秦兩漢儒學的重複,不會對當時的社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陳先生此處認為道教思想與天台宗有關,藉道教的不排斥外來思想,但一面又堅守自己民族的立場,這一做法說明了宋代新儒家的策略,即與外來思想融為一體後,則堅持夷夏之論,這一說法十分深刻,可謂是表達了宋明理學的時代感受。或許可以補充一個例子,上述天台宗的圓教義理,其中為了要肯定一切法存在的必然性,有無明與法性同體之說,即表示在同一存在的事物(法)上,可以是無明煩惱的表現,也可以是清淨的法性之所在,這一思想在南宋胡宏(號五峰,1105-1161)有很清楚的表示,如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 ,很難說五峰對於佛教天台宗的說法沒有吸收,但五峰藉此圓說表達了儒家的義理,而且對佛教作出嚴格的批評,這好像也可以如同陳寅恪所說,融成一家之說後,則堅持夷夏之辨。陳先生此說確提示了今後儒學的理論如何能繼續發展並有其強大的生命力所需要有的做法,這裡表達了大史學家的宏觀識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