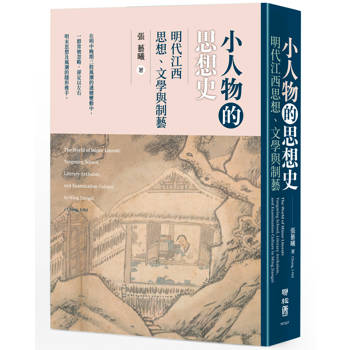第一章 從古籍復興到儒經詮釋:明中晚期三股風潮的變動
前言
明中期有陽明心學運動與文學復古運動,文學復古運動最初主要是一場文學運動,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以復古為創新,希望走出新路。由於復古的需求,於是帶動對先秦兩漢以來的典籍蒐獵的熱潮,配合當時印刷術與出版業的發達,於是許多過去少見、不易得,或者是版面錯亂的,都一一被重新校訂編排而出版,於是典籍大量增加,並更廣泛流通於一般人手中。隨著古籍的越來越多,也有進一步統整這些古籍的工作。
文學復古運動所取法及所蒐獵的主要以史、子、集等三類書籍為主。由於很少連結到尊經或復興經書等口號,所以能夠疏離於「文以載道」的要求,而歸向於文學本位。但在蒐獵古籍的風氣下而大量刊行的諸子書,影響所及,則已逸出文學本位之外。
陽明心學的致良知說,所對抗的是僵化以後的程朱理學,而有意在程朱理學所壟斷的儒學詮釋以外開闢新途。良知雖不假知識聞見,但「六經註我」的立場讓人在詮釋典籍上較為自由,人們可以不必進入典籍的考證、章句的講究,而可以用一套原則來貫通諸多典籍。這其實在面對日益增多的典籍時,是相對簡捷便當的一種作法及立場,而這些古籍等於提供了陽明心學詮釋儒經的思想資源。
另一方面,陽明心學與儒經詮釋最初是若即若離的,王守仁雖以儒經的內容來印證所悟,最初所側重的在致良知說而不在儒經的詮釋,但陽明心學不可能跟儒經詮釋完全無關,如心學大儒對《大學》改本各類詮釋及見解,就是很好的例子。這讓陽明心學很容易被制藝寫作所用,至少在萬曆朝便已見到科舉用書中引用陽明心學來詮釋儒經。明末江西制藝風潮中,古籍的復興與陽明心學作為儒經詮釋,是兩項凸出的特點。
制藝也有變,從單純的應試之文,到漸漸受到正面肯定。萬曆朝制藝宗匠湯賓尹先是高度肯定制藝詮釋儒經的價值,已開了明末制藝風潮的風氣之先。明末江西派對湯賓尹的某些見解雖有批評,但對於以制藝詮釋儒經則又更往前推了一步,而形成以制藝作為新文體,以古學為內容的主張,而古學的主軸即諸子百家之學。
第五章將談到,由於不少人把諸子書定位為羽翼六經,相當於把諸子書納入到六經的詮釋中,待明末制藝風潮起,由於制藝被定位為經義之學,是詮釋儒經的新文體,於是這些重刊的諸子書,便被入制藝寫作中,如江西派便擅長援引諸子書入制藝寫作中,以諸子書來詮釋儒經。
一、文學復古運動與古籍的蒐獵整理
1. 從文學復古到古籍的校訂刊刻
復古派主張文學創作必須以古人為典型,詩作倣效以杜甫(712-770)為首的盛唐詩,或益之以漢魏古體,排斥宋詩。古文辭則祖述以《史記》為主的秦漢文。原則上,對詩的重視甚於對古文辭。在創作方法上,嚴守古人成法,不但用語措辭上形似,也須在內容感情上神似,標榜「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要求人們在寫作詩及古文辭,模擬盛唐詩及秦漢文。但復古派並不是簡單為復古而復古而已,而是有寓創新於復古之意。如吉川幸次郎(1904-1980)指出:「他們認為從事文學的不二法門,無他,只要精研這些有限的古代典型之作,字模句擬,依樣葫蘆,如能求其近似或一致,便可進入文學的堂奧,上比古人,自成名家」,「這樣的方法就更直截了當,可謂簡易率直之至」。這種簡率、樸質,甚至帶點生硬的文體,讓人們更容易入手寫作詩文。以摹倣為入手法,人們為了參考先秦兩漢的典籍及漢魏盛唐的詩作,而有更多閱讀古籍的需要,於是帶動蒐獵古籍的風潮。
前言
明中期有陽明心學運動與文學復古運動,文學復古運動最初主要是一場文學運動,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以復古為創新,希望走出新路。由於復古的需求,於是帶動對先秦兩漢以來的典籍蒐獵的熱潮,配合當時印刷術與出版業的發達,於是許多過去少見、不易得,或者是版面錯亂的,都一一被重新校訂編排而出版,於是典籍大量增加,並更廣泛流通於一般人手中。隨著古籍的越來越多,也有進一步統整這些古籍的工作。
文學復古運動所取法及所蒐獵的主要以史、子、集等三類書籍為主。由於很少連結到尊經或復興經書等口號,所以能夠疏離於「文以載道」的要求,而歸向於文學本位。但在蒐獵古籍的風氣下而大量刊行的諸子書,影響所及,則已逸出文學本位之外。
陽明心學的致良知說,所對抗的是僵化以後的程朱理學,而有意在程朱理學所壟斷的儒學詮釋以外開闢新途。良知雖不假知識聞見,但「六經註我」的立場讓人在詮釋典籍上較為自由,人們可以不必進入典籍的考證、章句的講究,而可以用一套原則來貫通諸多典籍。這其實在面對日益增多的典籍時,是相對簡捷便當的一種作法及立場,而這些古籍等於提供了陽明心學詮釋儒經的思想資源。
另一方面,陽明心學與儒經詮釋最初是若即若離的,王守仁雖以儒經的內容來印證所悟,最初所側重的在致良知說而不在儒經的詮釋,但陽明心學不可能跟儒經詮釋完全無關,如心學大儒對《大學》改本各類詮釋及見解,就是很好的例子。這讓陽明心學很容易被制藝寫作所用,至少在萬曆朝便已見到科舉用書中引用陽明心學來詮釋儒經。明末江西制藝風潮中,古籍的復興與陽明心學作為儒經詮釋,是兩項凸出的特點。
制藝也有變,從單純的應試之文,到漸漸受到正面肯定。萬曆朝制藝宗匠湯賓尹先是高度肯定制藝詮釋儒經的價值,已開了明末制藝風潮的風氣之先。明末江西派對湯賓尹的某些見解雖有批評,但對於以制藝詮釋儒經則又更往前推了一步,而形成以制藝作為新文體,以古學為內容的主張,而古學的主軸即諸子百家之學。
第五章將談到,由於不少人把諸子書定位為羽翼六經,相當於把諸子書納入到六經的詮釋中,待明末制藝風潮起,由於制藝被定位為經義之學,是詮釋儒經的新文體,於是這些重刊的諸子書,便被入制藝寫作中,如江西派便擅長援引諸子書入制藝寫作中,以諸子書來詮釋儒經。
一、文學復古運動與古籍的蒐獵整理
1. 從文學復古到古籍的校訂刊刻
復古派主張文學創作必須以古人為典型,詩作倣效以杜甫(712-770)為首的盛唐詩,或益之以漢魏古體,排斥宋詩。古文辭則祖述以《史記》為主的秦漢文。原則上,對詩的重視甚於對古文辭。在創作方法上,嚴守古人成法,不但用語措辭上形似,也須在內容感情上神似,標榜「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要求人們在寫作詩及古文辭,模擬盛唐詩及秦漢文。但復古派並不是簡單為復古而復古而已,而是有寓創新於復古之意。如吉川幸次郎(1904-1980)指出:「他們認為從事文學的不二法門,無他,只要精研這些有限的古代典型之作,字模句擬,依樣葫蘆,如能求其近似或一致,便可進入文學的堂奧,上比古人,自成名家」,「這樣的方法就更直截了當,可謂簡易率直之至」。這種簡率、樸質,甚至帶點生硬的文體,讓人們更容易入手寫作詩文。以摹倣為入手法,人們為了參考先秦兩漢的典籍及漢魏盛唐的詩作,而有更多閱讀古籍的需要,於是帶動蒐獵古籍的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