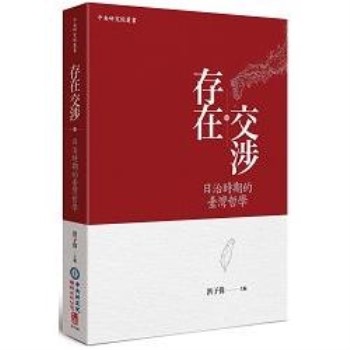第一章 日治時期臺灣哲學系譜與分期
臺灣現代哲學的發展始於何時?早期哲學又是何種面貌?本文的目的在替早期本土哲學概況勾勒出大致輪廓。為此,本文首先簡述其誕生的時代背景,並定義何謂「臺灣哲學家」,以釐清研究的對象與範圍。其次,本文提出早期哲學發展的「前啟蒙」、「啟蒙發展」與「成熟期」三階段觀點,並探討第一代與第二代哲學家的角色。同時也刻畫出當時哲學家重視基本存有與運動實踐的兩大特徵。其三,根據早期臺灣哲學家的理論師承與哲學系譜,將早期哲學區分為「歐陸─日本哲學」、「美國實用主義」、「基督宗教哲學」與「漢學」等四大學派,並簡述其發展特色與時代精神。最後,本文簡述研究早期哲學有何思想史之外的哲學重要性。
一、臺灣哲學的誕生與困挫
「哲學」一詞不論就其漢字詞源,或是其作為現代化學科傳入東亞的歷史來看,都是十足的舶來品。而臺灣具有現代意義的哲學發展,也始於19世紀末日本統治下的西化浪潮。
1853年美國黑船來航,震驚日本,打破江戶幕府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在維新志士推動下,明治天皇開啟了「文明開化」的現代化革新。從政府體制、服裝髮型到語言文字,都有「脫亞入歐」論辯。這種西化運動,與其說是典章制度的移植,毋寧說是文化上的皈依。短短二十幾年,日本不但「散髮脫刀」,更有系統地引進了英國效益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等思潮。如中村敬太郎翻譯彌爾的《自由之理》(1871)、服部德翻譯盧梭的《民約論》(1877)、西周翻譯評註彌爾的《利學》(即《效益主義》)(1877)等。而「哲學」一詞,也是由日本學者西周所譯定(當時清國學者尚稱「Philosophy」為「智學」)。1868年,明治天皇開辦開成學校作為研究與教授西學的官方機構。1877年4月東京大學成立,文學部的第一科中包含了史學、哲學與政治學,這是哲學第一次以現代專門學科出現於日本。相較之下,清帝國同治皇帝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則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維出發。1903年光緒皇帝在模仿西方學制頒訂「奏定學堂章程」以建立現代化教育機構時,依舊將哲學排除在高等教育外。
1895年,兩帝國黃金交叉,臺灣島變成日本新疆。
清國割臺後,現代哲學思想便透過赴日本內地念書的臺灣學子,傳回本島逐漸發展。和幕末的維新志士一樣,臺灣青年積極接受歐美思潮,也有其救亡圖存的使命。廖仁義說得好:「臺灣哲學一開始就不是一種囿於學院藩籬的觀念推演,而是源自於民間尋找反支配思想的需求。」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哲學發展有兩個背景條件,造就其豐富多元、具生命力的特性。一方面,此時本土哲學家面臨日本總督府殖民同化所引發一連串在文化、語言、政治、社會上的生存危機。這些哲學家出於存在焦慮而展開本能求生,提出各種具開創實驗性質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自1910年代末期起,除了整個臺灣文化界受到中國五四運動、日本大正民主、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美國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主張與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的衝擊之外,臺灣哲學家更汲取諸如基督教神學、德國觀念論、辯證唯物論、美國實用主義與繼起的海德格哲學等歐美思潮的養分,對於上述生存危機展開各種大膽的論述與運動。
在這股浪潮下,早期哲學發展出兩個重要特徵:一是對於存有問題的關注、一是對運動實踐的重視。首先,這個時代的臺灣哲學家所共同關心的問題是,如果臺灣在語言文化上不同於日本,政治上又不歸屬中國,那它到底是什麼?面臨同化又該如何自處?他們透過現實世界(殖民臺灣)與抽象概念(哲學理論)之間的反覆辯證,來重新界定自己的存在現狀。除了先驗的哲學概念,他們更關注現實中倫理學意義下的存在問題。其次,臺灣自1920年代起經歷了政治民族運動與1930年代的文化民族運動,這群哲學家也在各種政治光譜的改革場域無役不與。從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革命青年團,到放棄東京大學學業潛渡中國參軍抗日者盡皆有之。正如馬克思所言:「哲學家至今只以各種方式來解釋世界,但更重要的是去改變它。」在那個年代,臺灣哲學就是一種行動、一種實踐!
然而,哲學始於懷疑,常體現於對既有價值體系的反叛。故而早期哲學發展所遭遇的困挫,也多來自當權者的壓迫。
例如洪耀勳〈風土文化觀〉(1936)曾以主客辯證來證成臺灣在文化上既不從屬於日本,也不歸屬中國。但這種論證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建立在對日本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否定,這在帝國皇民化運動與戰時體制下可說是困難重重。即便日本戰敗,在兩蔣政權漫長的戒嚴時期,其本土哲學論述也很容易被貼上「文化臺獨」標籤。因此,本土哲學的發展自1940年代起產生思想史上的斷裂,戰後哲學家更被迫在再殖民的獨裁體制下集體噤聲失語。廖仁義認為,這段時期「中國哲學以一種外來思潮暫時扮演臺灣本土哲學的整體」。
解嚴後,只有廖仁義在1988年曾分析臺灣哲學的歷史構造。即便臺灣史在1993年成為顯學後,哲學界也僅有李明輝在1995年探討本土思想家李春生的論述,整個學界對臺灣早期哲學研究雖有零星論述卻並不熱中。究其諸多原因中,固然有文化認同與學術市場的考量,但或許其中一個難處在於「何謂哲學」此看法上的分歧,以至於如何去界定研究對象主體仍未有定論。例如,「傳統中國是否有哲學」一直是個爭議,連帶影響臺灣清代經學者如鄭用錫、洪棄生的定位問題。重之以臺灣研究日益熱門,也有學者指出原住民文化中已具有原始哲學的特徵。這些諸多因素都在決定臺灣哲學的研究對象與範圍時產生阻礙。
為減少可能的爭議,本文所稱的「哲學」明確定義為現代化過程中,所引進西方的系統性思辨工具。舉凡笛卡兒的演繹法、培根的歸納法、黑格爾或馬克思的辯證法、胡賽爾的現象學、羅素的邏輯分析與巴特的辯證神學等皆屬之。在此意義下,清代文人鄭用錫的《周禮解疑》並不算是本文定義之哲學,但林茂生1916年在東京大學以現代方法書寫,並比較唯心論與陽明學的〈王陽明の良知說〉則是。
依此,則本文對臺灣哲學家的定義可分別從「臺灣」與「哲學家」加以說明:一方面,臺灣「哲學家」是指以(上述定義之)哲學為工具從事相關論述與改革運動者。另一方面,對「臺灣」哲學家是採取屬人而非屬地認定。故並非所有居住在「臺灣」的「哲學家」都是臺灣哲學家,而是將臺灣總督府戶籍五大族別中的日本人排除在臺籍之外。
是故,長年在臺北帝國大學哲學科任教,戰後更一度留任臺灣大學的淡野安太郎不符此範疇,但大半輩子在外漂泊,終致客死異鄉的廖文奎卻屬之。
依此交集定義,則臺灣哲學家的「內涵」(intension)是指以哲學為工具從事相關論述與改革運動的臺灣人,其「外延」(extension)則至少包括了李春生、林茂生、周在賜、郭馬西、蘇薌雨、洪耀勳、林秋梧、張深切、廖文奎、陳紹馨、郭明昆、楊杏庭、曾天從、吳振坤、黃彰輝、黃金穗、鄭發育、張冬芳、蔡愛智、林素琴等人。若以發展特色分期,有前啟蒙期(1896-1916)、啟蒙發展期(1916-1930)、成熟期(1930-1945)三個階段。若進一步依據思想系譜區分,則大略有歐陸—日本哲學、美國實用主義、基督宗教哲學與漢學等四大學派。二、發展分期與時代精神
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受到兩股力量交互影響。一方面,它承襲了日本內地哲學的主流理論,甚至「屬於廣義的日本哲學發展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卻又與當時臺灣社會的政治與文化抗日運動密切結合。在這兩股力量拉扯下形塑出臺灣哲學的獨有特徵。依其發展分期,可約略分為「前啟蒙期」(1896-1916)、「啟蒙發展期」(1916-1930)與「成熟期」(1930-1945)。
1. 前啟蒙期(1896-1916)
前啟蒙期始於李春生1896年在日本橫濱出版《主津新集》後的一系列宗教哲學作品,而終於林茂生在1916年所出版的第一篇現代意義的學術論文。這個階段之所以稱為前啟蒙,乃是因為當時的臺灣文人多未接受現代教育與系統性的思想訓練,只有少數透過教會而接觸西方思潮,且多具鮮明的宣教立場。由於臺灣在1915年噍吧哖事件以前仍處於武裝抗日的階段,發展政治或文化的主體論述並非此時的重點。再加上第一批接受現代化教育的新興知識分子當時仍處中、小學階段(如洪耀勳和張深切)。因此,李春生、林茂生與周再賜這三位生於19世紀清帝國的第一代哲學家,便成為前啟蒙期的代表人物。此時他們的作品多以西方宗教或傳統儒學為主題,較無涉於臺灣主體之自覺。
舉例來說,李春生透過西洋傳教士與對洋貿易而自學通達東西思想,也是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奠基者。
他的作品眾多,自1896年李春生訪日回臺完成《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之後,他不再過問時政而潛心基督神學研究。他的宗教哲學著作包括《主津後集》(1896)、《天演論書後》(1907)、《東西哲衡》(1908)、《宗教五德備考》(1910)、《哲衡續編》(1911)、《聖經闡要講義》(1914)等等。在哲學上,詮釋學(Hermeneutics)原指對聖經文本的解釋方法,後擴展到對於其他文本的解釋上。目前雖無證據顯示李春生有意識地利用詮釋學方法來解經,然而,李春生在闡述基督教義與其他學說的不相容性(如演化論、效益主義、共產主義)或相容性(論語、孟子)時,除承襲蘇格蘭長老宗批判羅馬天主教的詮釋傳統,在調和諸如先秦儒家的「天」與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時,也發展出極具個人特色的詮釋方法與策略。廖仁義認為,雖然李春生的論證時顯粗糙,又不乏宗教成見,但卻顯示其在面對近代思潮的反省時的洞察。黃俊傑則認為他是臺灣第一位思想家。
此外,同屬基督教長老會的林茂生受教會補助赴京都求學,自1908-1913年,也在《臺南教會報》發表7篇有關京都見聞的作品。然而,林茂生真正具有哲學重要性的代表作,是他在1916年東京帝大哲學科畢業時連載於《東亞研究》第6卷第11-12號上的〈王陽明の良知說〉。這篇論文率先以康德思想詮釋儒家,黃崇修認為,當時林茂生這種方法相當前衛,不但早於1921年後參酌西方理論的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等人,更早於戰後來臺以康德詮釋儒家道德哲學的牟宗三。林茂生的〈王陽明の良知說〉不但是臺灣哲學史上第一篇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重要文獻,也標示著臺灣哲學正式從前啟蒙期邁向啟蒙發展階段。2. 啟蒙發展期(1916-1930)
這個時期始於1916年林茂生發表〈王陽明の良知說〉,到他1930年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為止。這個階段之所以稱為啟蒙發展期,乃緣於兩個因素:一是1910年代後,日本哲學開始步上專業學院化之發展,此時東大、京大紛紛將哲學獨立單獨設科,著名的京都學派也開始萌芽茁壯。另則是臺灣本土新興知識分子逐漸崛起,在歐美思潮與世界局勢的衝擊下,開始各種大膽而具實驗性質的論述與衝撞。
這個階段,除有林茂生從前期到後期思想的轉變外,臺灣第二代哲學家也依序登上歷史舞臺。所謂的第二代哲學家是指出生於日本領臺後的二十世紀初,以臺、日語為母語的雙語世代。他們也是第一批接受完整現代化教育的新興知識分子,在臺灣哲學的啟蒙發展期和成熟期中扮演關鍵角色。
啟蒙發展期開始出現不少文獻,且多與各種風起雲湧的社會改革運動有關。例如在杜威應胡適與蔣夢麟之邀訪問中國期間(1919-1921),林茂生也在《臺灣日報》連載〈社會之進化及學校教育〉(1924)八篇,探討現代教育的理念,展現了他投入杜威門下之前的教育哲學觀點,以及對於日本殖民教育的看法。林秋梧1927年起開始在《南瀛佛教》、《中道》發表宗教改革的文章。1929年更在《臺灣民報》連載〈唯物論者所指謫的歷史上的宗教所演的主角〉十篇,將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應用到反思臺灣佛教之現狀。此外,廖文奎在芝加哥大學的碩士論文《唯心論及其批判》(Modern Idealism as Challenged by Its Rivals)(1929),則討論了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實在論(Realsim)對觀念論的挑戰,算是臺灣少數純粹西方哲學論著之先驅。
然而此時的臺灣哲學家不止於著書立說,更熱中於各種政治改革與運動實踐。這多少受到19世紀以來德國哲學典範轉移的影響。原本,黑格爾認為哲學的任務是在歷史事件發生後的消極省察與反思,正如同「米納瓦的夜梟只有在夜幕低垂時才會展翅高飛」。但是馬克思卻主張,歷史演變來自人類的自覺與努力,而哲學應扮演改變世界的積極力量。這種對於黑格爾觀念論傳統的批判,也影響了早期日本哲學的發展。1920年代後,日本政府雖然開始打壓左翼思想與共產黨,但這種精神卻以另一種形式在日本延續,並以宮島肇1940年在《理想》雜誌上發表〈哲學即實踐〉達到最高峰。
這股反傳統的實踐風潮,同樣席捲臺灣。例如,林秋梧與楊杏庭在學生時代就分別參與了1922年北師學潮與1928年第二次中師學潮。其中林秋梧遭日警逮捕拘禁,後遭退學,1924年轉往廈門大學哲學系就讀。他批判佛教團體與資本財閥的靠攏,並以馬克思「階級鬥爭」重返大乘佛學中不二與無分別的思想。
他的詩作「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體現出家人的入世情懷。此外,張深切在留學中國期間推動反日本殖民革命,曾與許乃昌在上海創立「上海臺灣青年會」、與謝雪紅成立「臺灣自治協會」、與李友邦在廣東成立「臺灣革命青年團」。1927年回臺籌款時遭日警逮捕。受監兩年不忘鑽研馬克思與孔學,1930年出獄後更組織演劇活動推廣理念。他所主張的「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則是代表了反奴役的時代精神。
除了與當權者對抗,不少哲學家也走入群眾直接對話,以喚醒自覺。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後,林秋梧擔任辯士並參與演講活動、林茂生出任文協評議員並巡講哲學。林茂生的學生陳紹馨受其影響,後來也在文化協會主持1926年夏季學校「星宿講話」講座,使新思維漸成風氣。1931年,臺灣知識分子的政治改革運動隨著「臺灣民眾黨」遭解散而造成困頓,但是這種淑世理想,卻以更細膩的形式表現在「成熟期」文化主體性的哲學建構上。3. 成熟期(1930-1945)
此階段始於臺灣第一位留美博士林茂生畢業返臺任教,結束於日本戰敗。這個階段之所以稱為成熟期,乃因1937年中日戰爭前,有關於本土文化的論述在質、量方面均達到巔峰。1937年後因皇民化運動轉而對形上學與知識論等純理論哲學研究,其學術性亦盛況空前。
1930年代,隨著臺灣從政治民族運動轉變為文化民族運動,文化主體性就成為許多臺灣知識分子的共同焦點。然而哲學家基於本身的訓練,對本土文化的後設問題或基本的存在設定更為敏銳,他們除了從描述層次(descriptive)來界定現狀,也在規範層次(normative)提出理想的解決之道。舉例來說,洪耀勳的〈風土文化觀〉(1936)不只指出在現實上臺灣「文運」的理論基礎闕如,更透過和辻哲郎的風土論與黑格爾的主客辯證,來論證臺灣文化有不可化約到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並以此建構本土哲學之本體論(第一哲學)。林茂生的博士論文《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不僅分析自1895年以來的殖民教育實況,更引用實用主義教育哲學建議當局應以「尊重相互的文化」與「教育機會平等」政策,來取代在朝鮮與臺灣強行推動的同化教育。
同樣的,陳紹馨在1936年也探討黑格爾在近代國家形成之背景下的公民社會理論,並藉此研究理想中的社會典型。曾天從則是在1937年探索真理原理以作為其「哲學體系重建論」之第一步。
此外,語言作為一種文化識別,也是當時知識分子的討論核心之一。在日本殖民同化政策下,不少臺灣人在成長過程中對於講母語而遭壓制都有深刻體認。例如張深切在草鞋墩公學校五年級時因為講臺語而遭毆打退學,而黃彰輝在大學畢業回臺灣的船上巧遇多年不見的胞弟,卻因與之臺語交談使其弟遭受教師(官)嚴斥。然而,臺語的弱勢固然有殖民政策因素,但其缺少普遍通行的書寫系統也影響觀念的傳達。故對於臺人「應以何語文作為思想的媒介」此問題上,許多知識分子也提出不同看法。在1920年代已有蘇薌雨發表〈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略述〉並鼓吹中國白話文。1930年代後,有洪耀勳發表〈創造臺人言語也算是一大使命〉、林茂生連載十五期的〈新臺灣話陳列館〉、郭明昆發表〈北京話〉、〈福佬話〉等。其中,郭明昆反對以中國白話文作為書寫系統。他主張應以臺灣通用的福佬話為基礎,發展出適當的書寫系統方為正途。他說:「嘴講是福佬話,耳孔聽也是福佬話,不拘,手無寫福佬話文。這是不正經的。」至於洪耀勳則提出更激進的主張,他認為不只是書寫系統,連口語系統也需要創造。他說:「我臺人為著受了變態的畸形的教育、言語尚未確立、日常所想的、意欲的、未得十分自由來表現。」這是因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即便當時流通的福佬話中也充斥著許多外來新語。口語用法的不一致往往使溝通難以順暢。為此,林茂生還特別在〈新臺灣話陳列館〉向大眾介紹諸如「元氣」、「美術」、「不動產」、「動員」、「團結」、「獨立」、「陳情」等新用語。正因為如此,洪耀勳才呼籲應以創造適用於臺灣人的專屬語言為使命。此外,同屬南神教會系統的吳振坤、黃彰輝則是受到巴克禮(Thomas Barclay,1849-1935)以羅馬拼音標示漳廈臺音的影響。黃彰輝更在戰後大力推廣羅馬白話字,對教會內臺語書寫系統的一致化(又稱「欽定化」)有所貢獻。
1937年是本土文化運動的分水嶺,是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由於皇民化與戰時體制使得文化民族運動宣告瓦解。許多第二代哲學家投入高等教育體制內,轉而成為純學術研究。這時除了已有林茂生在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書、郭明昆在早稻田大學擔任講師外,洪耀勳在1937年從臺北帝大轉往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任教。楊杏庭1940年自東京文理科大學哲學科肄業後赴南京中央大學任教。黃金穗1939年自京都大學哲學科畢業後進入田邊元(Tanabe Hajime,1885-1962)研究室。同年,鄭發育自京都大學哲學科畢業,留在京都大學研究心理學並擔任助教。曾天從1944年則前往滿洲國遼寧農業大學任教。此外,蘇薌雨1937年就讀東京大學期間,因盧溝橋事件投筆從戎,西渡中國加入陸軍第三十一師抗日,參與1938年的臺兒莊戰役與武漢會戰。到了1939年,蘇薌雨也轉往廣西大學任教。至於黃彰輝雖然1941年在倫敦以「敵對國」日本公民身分遭英國政府限制自由,但1943年開始也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東方語言(日語、福建語)。
戰爭期間,許多學術著作出版。例如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1937)、《真理觀之諸問題》(1941)、《純粹現象學之構想》(1941)、《批判的辯證法與實在論的範疇論》(1943)。洪耀勳也在《哲學科研究年報》與《師大學刊》等學術期刊發表〈存在與真理〉(1938)、〈實存之有限性與形而上學之問題〉(1942)、〈存在論之新動向〉(1943)等文章。他將在北京師大上課講義以線裝書方式出版的《認識論》,則是最早由臺灣人撰寫的知識論教科書。
雖然臺灣哲學家的淑世熱情因大戰而暫時沉寂,卻在戰後一度復甦。初期有林茂生創辦《民報》、黃金穗創辦《新新》、廖文奎成立《前鋒》、洪耀勳與張深切等人在北京創辦《新臺灣》。二二八事件後,在海外有楊杏庭參與日本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文奎在香港向聯合國遊說支持臺灣獨立。黃彰輝也在1965年流亡異鄉,並於1972年在華府與離散歐美的同胞發起「臺灣人民自覺運動」。至於島內,則有吳振坤透過臺南神學院系統維繫本土意識,而洪耀勳更是在戒嚴下默默捍衛二十多年的學術自由,直到1972年「臺大哲學系事件」前為止。
臺灣現代哲學的發展始於何時?早期哲學又是何種面貌?本文的目的在替早期本土哲學概況勾勒出大致輪廓。為此,本文首先簡述其誕生的時代背景,並定義何謂「臺灣哲學家」,以釐清研究的對象與範圍。其次,本文提出早期哲學發展的「前啟蒙」、「啟蒙發展」與「成熟期」三階段觀點,並探討第一代與第二代哲學家的角色。同時也刻畫出當時哲學家重視基本存有與運動實踐的兩大特徵。其三,根據早期臺灣哲學家的理論師承與哲學系譜,將早期哲學區分為「歐陸─日本哲學」、「美國實用主義」、「基督宗教哲學」與「漢學」等四大學派,並簡述其發展特色與時代精神。最後,本文簡述研究早期哲學有何思想史之外的哲學重要性。
一、臺灣哲學的誕生與困挫
「哲學」一詞不論就其漢字詞源,或是其作為現代化學科傳入東亞的歷史來看,都是十足的舶來品。而臺灣具有現代意義的哲學發展,也始於19世紀末日本統治下的西化浪潮。
1853年美國黑船來航,震驚日本,打破江戶幕府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在維新志士推動下,明治天皇開啟了「文明開化」的現代化革新。從政府體制、服裝髮型到語言文字,都有「脫亞入歐」論辯。這種西化運動,與其說是典章制度的移植,毋寧說是文化上的皈依。短短二十幾年,日本不但「散髮脫刀」,更有系統地引進了英國效益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等思潮。如中村敬太郎翻譯彌爾的《自由之理》(1871)、服部德翻譯盧梭的《民約論》(1877)、西周翻譯評註彌爾的《利學》(即《效益主義》)(1877)等。而「哲學」一詞,也是由日本學者西周所譯定(當時清國學者尚稱「Philosophy」為「智學」)。1868年,明治天皇開辦開成學校作為研究與教授西學的官方機構。1877年4月東京大學成立,文學部的第一科中包含了史學、哲學與政治學,這是哲學第一次以現代專門學科出現於日本。相較之下,清帝國同治皇帝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則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維出發。1903年光緒皇帝在模仿西方學制頒訂「奏定學堂章程」以建立現代化教育機構時,依舊將哲學排除在高等教育外。
1895年,兩帝國黃金交叉,臺灣島變成日本新疆。
清國割臺後,現代哲學思想便透過赴日本內地念書的臺灣學子,傳回本島逐漸發展。和幕末的維新志士一樣,臺灣青年積極接受歐美思潮,也有其救亡圖存的使命。廖仁義說得好:「臺灣哲學一開始就不是一種囿於學院藩籬的觀念推演,而是源自於民間尋找反支配思想的需求。」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哲學發展有兩個背景條件,造就其豐富多元、具生命力的特性。一方面,此時本土哲學家面臨日本總督府殖民同化所引發一連串在文化、語言、政治、社會上的生存危機。這些哲學家出於存在焦慮而展開本能求生,提出各種具開創實驗性質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自1910年代末期起,除了整個臺灣文化界受到中國五四運動、日本大正民主、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美國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主張與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的衝擊之外,臺灣哲學家更汲取諸如基督教神學、德國觀念論、辯證唯物論、美國實用主義與繼起的海德格哲學等歐美思潮的養分,對於上述生存危機展開各種大膽的論述與運動。
在這股浪潮下,早期哲學發展出兩個重要特徵:一是對於存有問題的關注、一是對運動實踐的重視。首先,這個時代的臺灣哲學家所共同關心的問題是,如果臺灣在語言文化上不同於日本,政治上又不歸屬中國,那它到底是什麼?面臨同化又該如何自處?他們透過現實世界(殖民臺灣)與抽象概念(哲學理論)之間的反覆辯證,來重新界定自己的存在現狀。除了先驗的哲學概念,他們更關注現實中倫理學意義下的存在問題。其次,臺灣自1920年代起經歷了政治民族運動與1930年代的文化民族運動,這群哲學家也在各種政治光譜的改革場域無役不與。從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革命青年團,到放棄東京大學學業潛渡中國參軍抗日者盡皆有之。正如馬克思所言:「哲學家至今只以各種方式來解釋世界,但更重要的是去改變它。」在那個年代,臺灣哲學就是一種行動、一種實踐!
然而,哲學始於懷疑,常體現於對既有價值體系的反叛。故而早期哲學發展所遭遇的困挫,也多來自當權者的壓迫。
例如洪耀勳〈風土文化觀〉(1936)曾以主客辯證來證成臺灣在文化上既不從屬於日本,也不歸屬中國。但這種論證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建立在對日本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否定,這在帝國皇民化運動與戰時體制下可說是困難重重。即便日本戰敗,在兩蔣政權漫長的戒嚴時期,其本土哲學論述也很容易被貼上「文化臺獨」標籤。因此,本土哲學的發展自1940年代起產生思想史上的斷裂,戰後哲學家更被迫在再殖民的獨裁體制下集體噤聲失語。廖仁義認為,這段時期「中國哲學以一種外來思潮暫時扮演臺灣本土哲學的整體」。
解嚴後,只有廖仁義在1988年曾分析臺灣哲學的歷史構造。即便臺灣史在1993年成為顯學後,哲學界也僅有李明輝在1995年探討本土思想家李春生的論述,整個學界對臺灣早期哲學研究雖有零星論述卻並不熱中。究其諸多原因中,固然有文化認同與學術市場的考量,但或許其中一個難處在於「何謂哲學」此看法上的分歧,以至於如何去界定研究對象主體仍未有定論。例如,「傳統中國是否有哲學」一直是個爭議,連帶影響臺灣清代經學者如鄭用錫、洪棄生的定位問題。重之以臺灣研究日益熱門,也有學者指出原住民文化中已具有原始哲學的特徵。這些諸多因素都在決定臺灣哲學的研究對象與範圍時產生阻礙。
為減少可能的爭議,本文所稱的「哲學」明確定義為現代化過程中,所引進西方的系統性思辨工具。舉凡笛卡兒的演繹法、培根的歸納法、黑格爾或馬克思的辯證法、胡賽爾的現象學、羅素的邏輯分析與巴特的辯證神學等皆屬之。在此意義下,清代文人鄭用錫的《周禮解疑》並不算是本文定義之哲學,但林茂生1916年在東京大學以現代方法書寫,並比較唯心論與陽明學的〈王陽明の良知說〉則是。
依此,則本文對臺灣哲學家的定義可分別從「臺灣」與「哲學家」加以說明:一方面,臺灣「哲學家」是指以(上述定義之)哲學為工具從事相關論述與改革運動者。另一方面,對「臺灣」哲學家是採取屬人而非屬地認定。故並非所有居住在「臺灣」的「哲學家」都是臺灣哲學家,而是將臺灣總督府戶籍五大族別中的日本人排除在臺籍之外。
是故,長年在臺北帝國大學哲學科任教,戰後更一度留任臺灣大學的淡野安太郎不符此範疇,但大半輩子在外漂泊,終致客死異鄉的廖文奎卻屬之。
依此交集定義,則臺灣哲學家的「內涵」(intension)是指以哲學為工具從事相關論述與改革運動的臺灣人,其「外延」(extension)則至少包括了李春生、林茂生、周在賜、郭馬西、蘇薌雨、洪耀勳、林秋梧、張深切、廖文奎、陳紹馨、郭明昆、楊杏庭、曾天從、吳振坤、黃彰輝、黃金穗、鄭發育、張冬芳、蔡愛智、林素琴等人。若以發展特色分期,有前啟蒙期(1896-1916)、啟蒙發展期(1916-1930)、成熟期(1930-1945)三個階段。若進一步依據思想系譜區分,則大略有歐陸—日本哲學、美國實用主義、基督宗教哲學與漢學等四大學派。二、發展分期與時代精神
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受到兩股力量交互影響。一方面,它承襲了日本內地哲學的主流理論,甚至「屬於廣義的日本哲學發展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卻又與當時臺灣社會的政治與文化抗日運動密切結合。在這兩股力量拉扯下形塑出臺灣哲學的獨有特徵。依其發展分期,可約略分為「前啟蒙期」(1896-1916)、「啟蒙發展期」(1916-1930)與「成熟期」(1930-1945)。
1. 前啟蒙期(1896-1916)
前啟蒙期始於李春生1896年在日本橫濱出版《主津新集》後的一系列宗教哲學作品,而終於林茂生在1916年所出版的第一篇現代意義的學術論文。這個階段之所以稱為前啟蒙,乃是因為當時的臺灣文人多未接受現代教育與系統性的思想訓練,只有少數透過教會而接觸西方思潮,且多具鮮明的宣教立場。由於臺灣在1915年噍吧哖事件以前仍處於武裝抗日的階段,發展政治或文化的主體論述並非此時的重點。再加上第一批接受現代化教育的新興知識分子當時仍處中、小學階段(如洪耀勳和張深切)。因此,李春生、林茂生與周再賜這三位生於19世紀清帝國的第一代哲學家,便成為前啟蒙期的代表人物。此時他們的作品多以西方宗教或傳統儒學為主題,較無涉於臺灣主體之自覺。
舉例來說,李春生透過西洋傳教士與對洋貿易而自學通達東西思想,也是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奠基者。
他的作品眾多,自1896年李春生訪日回臺完成《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之後,他不再過問時政而潛心基督神學研究。他的宗教哲學著作包括《主津後集》(1896)、《天演論書後》(1907)、《東西哲衡》(1908)、《宗教五德備考》(1910)、《哲衡續編》(1911)、《聖經闡要講義》(1914)等等。在哲學上,詮釋學(Hermeneutics)原指對聖經文本的解釋方法,後擴展到對於其他文本的解釋上。目前雖無證據顯示李春生有意識地利用詮釋學方法來解經,然而,李春生在闡述基督教義與其他學說的不相容性(如演化論、效益主義、共產主義)或相容性(論語、孟子)時,除承襲蘇格蘭長老宗批判羅馬天主教的詮釋傳統,在調和諸如先秦儒家的「天」與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時,也發展出極具個人特色的詮釋方法與策略。廖仁義認為,雖然李春生的論證時顯粗糙,又不乏宗教成見,但卻顯示其在面對近代思潮的反省時的洞察。黃俊傑則認為他是臺灣第一位思想家。
此外,同屬基督教長老會的林茂生受教會補助赴京都求學,自1908-1913年,也在《臺南教會報》發表7篇有關京都見聞的作品。然而,林茂生真正具有哲學重要性的代表作,是他在1916年東京帝大哲學科畢業時連載於《東亞研究》第6卷第11-12號上的〈王陽明の良知說〉。這篇論文率先以康德思想詮釋儒家,黃崇修認為,當時林茂生這種方法相當前衛,不但早於1921年後參酌西方理論的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等人,更早於戰後來臺以康德詮釋儒家道德哲學的牟宗三。林茂生的〈王陽明の良知說〉不但是臺灣哲學史上第一篇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重要文獻,也標示著臺灣哲學正式從前啟蒙期邁向啟蒙發展階段。2. 啟蒙發展期(1916-1930)
這個時期始於1916年林茂生發表〈王陽明の良知說〉,到他1930年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為止。這個階段之所以稱為啟蒙發展期,乃緣於兩個因素:一是1910年代後,日本哲學開始步上專業學院化之發展,此時東大、京大紛紛將哲學獨立單獨設科,著名的京都學派也開始萌芽茁壯。另則是臺灣本土新興知識分子逐漸崛起,在歐美思潮與世界局勢的衝擊下,開始各種大膽而具實驗性質的論述與衝撞。
這個階段,除有林茂生從前期到後期思想的轉變外,臺灣第二代哲學家也依序登上歷史舞臺。所謂的第二代哲學家是指出生於日本領臺後的二十世紀初,以臺、日語為母語的雙語世代。他們也是第一批接受完整現代化教育的新興知識分子,在臺灣哲學的啟蒙發展期和成熟期中扮演關鍵角色。
啟蒙發展期開始出現不少文獻,且多與各種風起雲湧的社會改革運動有關。例如在杜威應胡適與蔣夢麟之邀訪問中國期間(1919-1921),林茂生也在《臺灣日報》連載〈社會之進化及學校教育〉(1924)八篇,探討現代教育的理念,展現了他投入杜威門下之前的教育哲學觀點,以及對於日本殖民教育的看法。林秋梧1927年起開始在《南瀛佛教》、《中道》發表宗教改革的文章。1929年更在《臺灣民報》連載〈唯物論者所指謫的歷史上的宗教所演的主角〉十篇,將馬克思對宗教的批判應用到反思臺灣佛教之現狀。此外,廖文奎在芝加哥大學的碩士論文《唯心論及其批判》(Modern Idealism as Challenged by Its Rivals)(1929),則討論了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實在論(Realsim)對觀念論的挑戰,算是臺灣少數純粹西方哲學論著之先驅。
然而此時的臺灣哲學家不止於著書立說,更熱中於各種政治改革與運動實踐。這多少受到19世紀以來德國哲學典範轉移的影響。原本,黑格爾認為哲學的任務是在歷史事件發生後的消極省察與反思,正如同「米納瓦的夜梟只有在夜幕低垂時才會展翅高飛」。但是馬克思卻主張,歷史演變來自人類的自覺與努力,而哲學應扮演改變世界的積極力量。這種對於黑格爾觀念論傳統的批判,也影響了早期日本哲學的發展。1920年代後,日本政府雖然開始打壓左翼思想與共產黨,但這種精神卻以另一種形式在日本延續,並以宮島肇1940年在《理想》雜誌上發表〈哲學即實踐〉達到最高峰。
這股反傳統的實踐風潮,同樣席捲臺灣。例如,林秋梧與楊杏庭在學生時代就分別參與了1922年北師學潮與1928年第二次中師學潮。其中林秋梧遭日警逮捕拘禁,後遭退學,1924年轉往廈門大學哲學系就讀。他批判佛教團體與資本財閥的靠攏,並以馬克思「階級鬥爭」重返大乘佛學中不二與無分別的思想。
他的詩作「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體現出家人的入世情懷。此外,張深切在留學中國期間推動反日本殖民革命,曾與許乃昌在上海創立「上海臺灣青年會」、與謝雪紅成立「臺灣自治協會」、與李友邦在廣東成立「臺灣革命青年團」。1927年回臺籌款時遭日警逮捕。受監兩年不忘鑽研馬克思與孔學,1930年出獄後更組織演劇活動推廣理念。他所主張的「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則是代表了反奴役的時代精神。
除了與當權者對抗,不少哲學家也走入群眾直接對話,以喚醒自覺。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後,林秋梧擔任辯士並參與演講活動、林茂生出任文協評議員並巡講哲學。林茂生的學生陳紹馨受其影響,後來也在文化協會主持1926年夏季學校「星宿講話」講座,使新思維漸成風氣。1931年,臺灣知識分子的政治改革運動隨著「臺灣民眾黨」遭解散而造成困頓,但是這種淑世理想,卻以更細膩的形式表現在「成熟期」文化主體性的哲學建構上。3. 成熟期(1930-1945)
此階段始於臺灣第一位留美博士林茂生畢業返臺任教,結束於日本戰敗。這個階段之所以稱為成熟期,乃因1937年中日戰爭前,有關於本土文化的論述在質、量方面均達到巔峰。1937年後因皇民化運動轉而對形上學與知識論等純理論哲學研究,其學術性亦盛況空前。
1930年代,隨著臺灣從政治民族運動轉變為文化民族運動,文化主體性就成為許多臺灣知識分子的共同焦點。然而哲學家基於本身的訓練,對本土文化的後設問題或基本的存在設定更為敏銳,他們除了從描述層次(descriptive)來界定現狀,也在規範層次(normative)提出理想的解決之道。舉例來說,洪耀勳的〈風土文化觀〉(1936)不只指出在現實上臺灣「文運」的理論基礎闕如,更透過和辻哲郎的風土論與黑格爾的主客辯證,來論證臺灣文化有不可化約到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並以此建構本土哲學之本體論(第一哲學)。林茂生的博士論文《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不僅分析自1895年以來的殖民教育實況,更引用實用主義教育哲學建議當局應以「尊重相互的文化」與「教育機會平等」政策,來取代在朝鮮與臺灣強行推動的同化教育。
同樣的,陳紹馨在1936年也探討黑格爾在近代國家形成之背景下的公民社會理論,並藉此研究理想中的社會典型。曾天從則是在1937年探索真理原理以作為其「哲學體系重建論」之第一步。
此外,語言作為一種文化識別,也是當時知識分子的討論核心之一。在日本殖民同化政策下,不少臺灣人在成長過程中對於講母語而遭壓制都有深刻體認。例如張深切在草鞋墩公學校五年級時因為講臺語而遭毆打退學,而黃彰輝在大學畢業回臺灣的船上巧遇多年不見的胞弟,卻因與之臺語交談使其弟遭受教師(官)嚴斥。然而,臺語的弱勢固然有殖民政策因素,但其缺少普遍通行的書寫系統也影響觀念的傳達。故對於臺人「應以何語文作為思想的媒介」此問題上,許多知識分子也提出不同看法。在1920年代已有蘇薌雨發表〈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略述〉並鼓吹中國白話文。1930年代後,有洪耀勳發表〈創造臺人言語也算是一大使命〉、林茂生連載十五期的〈新臺灣話陳列館〉、郭明昆發表〈北京話〉、〈福佬話〉等。其中,郭明昆反對以中國白話文作為書寫系統。他主張應以臺灣通用的福佬話為基礎,發展出適當的書寫系統方為正途。他說:「嘴講是福佬話,耳孔聽也是福佬話,不拘,手無寫福佬話文。這是不正經的。」至於洪耀勳則提出更激進的主張,他認為不只是書寫系統,連口語系統也需要創造。他說:「我臺人為著受了變態的畸形的教育、言語尚未確立、日常所想的、意欲的、未得十分自由來表現。」這是因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即便當時流通的福佬話中也充斥著許多外來新語。口語用法的不一致往往使溝通難以順暢。為此,林茂生還特別在〈新臺灣話陳列館〉向大眾介紹諸如「元氣」、「美術」、「不動產」、「動員」、「團結」、「獨立」、「陳情」等新用語。正因為如此,洪耀勳才呼籲應以創造適用於臺灣人的專屬語言為使命。此外,同屬南神教會系統的吳振坤、黃彰輝則是受到巴克禮(Thomas Barclay,1849-1935)以羅馬拼音標示漳廈臺音的影響。黃彰輝更在戰後大力推廣羅馬白話字,對教會內臺語書寫系統的一致化(又稱「欽定化」)有所貢獻。
1937年是本土文化運動的分水嶺,是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由於皇民化與戰時體制使得文化民族運動宣告瓦解。許多第二代哲學家投入高等教育體制內,轉而成為純學術研究。這時除了已有林茂生在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書、郭明昆在早稻田大學擔任講師外,洪耀勳在1937年從臺北帝大轉往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任教。楊杏庭1940年自東京文理科大學哲學科肄業後赴南京中央大學任教。黃金穗1939年自京都大學哲學科畢業後進入田邊元(Tanabe Hajime,1885-1962)研究室。同年,鄭發育自京都大學哲學科畢業,留在京都大學研究心理學並擔任助教。曾天從1944年則前往滿洲國遼寧農業大學任教。此外,蘇薌雨1937年就讀東京大學期間,因盧溝橋事件投筆從戎,西渡中國加入陸軍第三十一師抗日,參與1938年的臺兒莊戰役與武漢會戰。到了1939年,蘇薌雨也轉往廣西大學任教。至於黃彰輝雖然1941年在倫敦以「敵對國」日本公民身分遭英國政府限制自由,但1943年開始也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東方語言(日語、福建語)。
戰爭期間,許多學術著作出版。例如曾天從的《真理原理論》(1937)、《真理觀之諸問題》(1941)、《純粹現象學之構想》(1941)、《批判的辯證法與實在論的範疇論》(1943)。洪耀勳也在《哲學科研究年報》與《師大學刊》等學術期刊發表〈存在與真理〉(1938)、〈實存之有限性與形而上學之問題〉(1942)、〈存在論之新動向〉(1943)等文章。他將在北京師大上課講義以線裝書方式出版的《認識論》,則是最早由臺灣人撰寫的知識論教科書。
雖然臺灣哲學家的淑世熱情因大戰而暫時沉寂,卻在戰後一度復甦。初期有林茂生創辦《民報》、黃金穗創辦《新新》、廖文奎成立《前鋒》、洪耀勳與張深切等人在北京創辦《新臺灣》。二二八事件後,在海外有楊杏庭參與日本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文奎在香港向聯合國遊說支持臺灣獨立。黃彰輝也在1965年流亡異鄉,並於1972年在華府與離散歐美的同胞發起「臺灣人民自覺運動」。至於島內,則有吳振坤透過臺南神學院系統維繫本土意識,而洪耀勳更是在戒嚴下默默捍衛二十多年的學術自由,直到1972年「臺大哲學系事件」前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