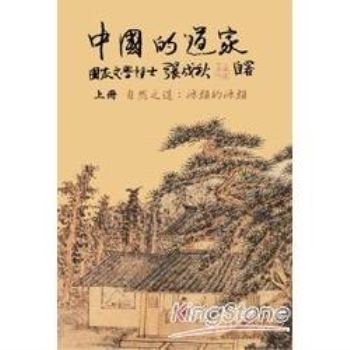第二章 先秦道家思想之資料問題
吾人研究古代學術,當先確定其可供研究之資料,然後始能著手進行。研究先秦道家思想,自亦不能例外。然則如何確定研究之資料耶?曰,根據目錄。由目錄上查得有某書某書可供研究,再按圖索驥,循序以求,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於此所當注意者,資料有真偽,不辨其偽,則易:(1)失去各家學說之真象;(2)亂了學說先後之次序;(3)亂了學派相承之系統。(胡適說)
然偽書亦有其應用之價值,不可全然棄置。其價值何在?
山可以窺知作者當時之思想:例如黃帝之書,必非黃帝之所作,其理甚明;然而吾人知其作偽者之時代當在戰國,則可以由此窺知戰國時托為黃帝思想之一斑。管子雖非管仲之所作,亦可以由此研究戰國時法家思想之大概。
偽書中保有前代資料,可以藉此闡發先代學說之意旨:梁啟超曰:『偽書非辨別不可,那是當然的。但辨別以後,並不一定要把偽書燒完。固然也有些偽書可以燒的……但自唐以前的偽書?很可寶貴……其故因為偽書斷不能憑空造出,必須參考無數書籍;假貨中常有真寶貝,我們可以把它當作類書看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故偽書資料,倘運用得當,亦未始不可補真書史料之不足。惟當特別謹慎,不可受其迷惑而已。
先秦道家思想,最可靠之書目,當推漢書藝文志。(漢志則本諸劉氏父子之七略。)今且就漢志所載各書一一討論之。
一、伊尹五十一篇
漢書藝文志注:「湯相。」又:本志小說家伊尹說廿七篇。注曰:「其語淺薄,似依托也。」隋書經籍志無著錄。
王應麟曰:「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民也。……』伊尹所謂道,豈老氏所謂道乎?志於兵權謀者,伊尹太公而入道家,蓋戰國權謀之士,著書而托之伊尹也。」(漢書藝文志考證)
梁啟超曰:「伊尹時已有著作傳後,且篇數多至五十餘,此可斷其必誣。然孟子已徵引伊尹言論多條,則孟子時已有所謂伊尹者可知。逸周書有伊尹獻令,其起源當亦頗古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成秋按:本書已佚,世界書局印有清馬國翰輯佚本,共計十篇,其中有篇目可考者五篇,餘俱收入雜篇。其言與戰國術士語近,蓋出依托。王說是也。
二、太公二百冊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漢書藝文志注:「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師古曰:父讀曰甫也。」
成秋按:此書今佚,梁啟超謂今本陰符經當在太公謀中,不知然否?又六韜,三略均托為太公兵法,亦非此書。
三、辛甲二十九篇
注云:「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成秋按:本書之佚已久,隋、唐志皆不著錄。世界書局印有清馬國翰輯佚本,其虞箴似太公金匱陰謀,故入道家。
四、鬻子二十二篇
注云:「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師古曰:鬻,昔戈六反。」又小說家有鴦子說十九篇,注曰:「俊世所加。」隋志及兩唐志,宋志,俱載鬻子一卷。
葉夢得曰:「世傳鬻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書藝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鬻熊文王師,不知何以名道冢?而小說家亦別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逢行珪所獻。其文大略,古人著書不應爾。廖仲容子抄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行珪先後差不倫。恐行珪書或有附益。」(文?通考引)
李壽曰:「藝文志二十二篇,今十四篇。崇文總目以為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某謂劉向父子及班固所著錄者,或有他本,此蓋後世所托也。熊既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何耶?又文多殘闕,卷第?篇目皆錯亂,甚者幾不可曉,而注尤謬誤,然不敢以意刪定,姑存之以俟考。」(同上)
黃震曰:「逢行珪序其書云:『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熊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遂師之。』故其書首之以文王問,此必戰國處士假托之辭。蓋自漢藝文志已有其篇目,其語亦多可採。如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為大忌』,如曰『自謂賢者為不肖』,如曰『察吏於民』,皆足以警世。其餘載五帝、禹、湯之政,皆主得人。文亦不煩,異乎諸子之寓言虛誕者矣。然每篇多以『政曰』起語,而以『昔者』追述文王之問。既託文王,而下又曰魯周公。且亦未知自稱『政曰』者為誰。逢行珪既不能明言,而反釋以為政術之問,則非辭矣。」(黃氏日鈔)
楊慣認為今所存鬻子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又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文選注亦引有一條,皆今本所無,是以知其為偽書矣。(丹鉛雜錄)
胡應麟曰:「今子書傳於世而最先者,惟鬻子。其書概舉修身治國之術,實雜家言也,與柱下漆園宗旨?異,而漢志列於道家,諸史藝文及諸家目錄靡不因之。雖或以為疑,而迄莫能定。余謂理氏義例,咸規訣、向,不應謬誤若斯。載讀漢志小說家有鬻子一十九篇,乃釋然悟曰:此今所傅鬻子乎?蓋鬻子道家言者漢末已亡,而小說家尚傳於後,後人不能精覈,遂以道家所列當之。故歷世紛紛,名實咸爽,漢志故灼然明也。」(九流緒論)
姚際恒曰:「鬻子今一卷,止十四篇,唐逢行珪所上。案史記楚世家:『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非矣。又書載三監、曲阜事,壽亦不應如是永也。是其人之事已謬悠莫考,而況其書乎?論之者葉正則、宋景濂,皆以兩見漢志為疑,莫知此書誰屬。胡元瑞則以屬小說家,亦臆測也。高似孫以為漢儒綴緝,李仁父以為後世依托,王弇州疑其『七大夫』之名,楊用修歷引賈誼書及文選註所引鬻子,今皆無之。此足以見其大略矣。」(古今偽書考)
四庫提要曰:「劉勰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咨詢,遺文餘事,錄為鬻子。』則裒輯成編,不出能手,流傳附益,或構虛詞,故漢志別入小說家歟?獨是偽四八目一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來帝王輔佐有數可紀者,靡不具載;而此書所列禹七大夫:皋陶、杜子業、既子施、子黯、季子?、然子堪、輕子玉;湯七大夫:慶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西門疵、北門側,皆具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六朝之末尚無此本。或唐以來好事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撰為膺本,亦末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為佚脫錯亂之狀,而誼書所引,則無一條之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生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古無此體,又每篇寥寥數言,詞旨膚淺,決非三代舊文。」
譚獻曰:「鬻子遺文殘缺,非盡偽造。以逢注本較賈生所引,不至有武夫魚目之歎。」(復堂日記》
成秋按:鬻子之言,賈誼新書、文選註、列子、呂氏春秋均有摘引,故先秦道家必有鬻子之書,可以斷言;然今本鬻子,已大悖於柱下漆園之旨,甚無可取。其後人之偽托乎?抑係原屬漢志所列小說家之鬻子乎?資料殘缺,無從論斷。姑取其可與道家思想相參者三條,並合以各書佚語,作一?述,以窺其一斑而已。
五、筅子八十六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師古曰:筅讀與管同。」司馬遷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史記管晏列傳贊)
博玄曰:「管子之書過半便是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鄙俗。」(劉恕通鑑外紀引)
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法家均有管子十八卷,管夷吾撰。宋代有管子二十四卷,齊管夷吾撰。
末廉曰:「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說是矣。」(諸子辨)
四車提要曰:「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其他姑無論,即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中其孰為手撰,孰為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為記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為推其義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必由後人混而一之,致疑竇耳。」
梁啟超以管子批評兼愛非攻息兵,明係戰國初年墨家興起後方成為問題。若認管子為管仲作,則春秋初年即有人講兼愛非攻等問題,時代豈非紊亂?(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又以其中一部份當為春秋末年傳說,其大部份則戰國至漢初遞為增益,一種無系統之類書而已。(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羅根澤以牧民、形勢、五輔問,戰國政治思想家作;霸形、霸言,戰國中世後政冶思想家作;立政、乘馬、君臣上、君臣下、七臣、七主,戰國末政治思想家作;七法,戰國末為孫、吳、申、韓之學者所作;法禁,法法,戰國法家作;任法、明法,戰國中世後法家作:樞言,戰國末法家緣道家為之;宙合、侈靡、四時、五行,戰國末陰陽家作;勢,戰國末兵陰陽家作;心術上、心術下、白心,戰國中世以後道家作;制分,疑戰國兵家作;小稱,戰國儒家作;內業,戰國中世以後,混合儒道者作;戒,戰國末調和儒道者作,正戰國末雜家作;管子解五篇,戰國末秦未統一前雜家作;禁藏,戰國末至漢初雜家作;大匡,戰國人作;地圖,最早作於戰國中世,版法似亦戰國時人作;中匡、四稱,疑亦戰國人作;王言(亡)疑亦戰國中世以後人作;入國、九守、桓公問,疑戰國末年人作;九變疑戰國以後人作;權修,秦漢間兵家作;幼官,秦漢間兵陰陽家作;水地,漢初醫家作;封禪司馬遷作;輕重十九篇,漢武、昭時理財家作;八觀、正世、治國西漢文、景後政治思想家作;小匡、度地,漢初人作;地員,疑亦漢初人作;參患,漢文、景以後人作;弟子職疑漢儒家作;幼官圖,漢以後人作;小問,輯戰國關於管子之傳說而成;謀失、正言、言昭、修身、問霸並亡,無考。(管子探源)
成秋按:莞與管同,筦子今作管子。管子書所包甚廣,必非夷吾之自箸,梁任公以類書稱之,近是。然其中多言富國強兵之道,實近於刑名法術之間,故後世多列為法家。今惟取其書中可與道家思想相參者,作一?述而已。
六、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七、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述老子學。」
八、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子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九、劉向說老子四篇
成秋按:以上四書,皆解釋老子或發揮老學者;可見班氏之前,老子書早已流行,而漢志獨不備載,甚感奇怪。今四書均已不傳,惟老子巋然獨存,因補列其書於俊,且附考證焉。
[補]老子道德經上下篇計八十一章
司馬遷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謐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七略曰:「劉向?校中老子書二篇,太史書一篇,臣向書二篇,凡中外書五篇,一百四十二章,除複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八十一章。上經第一,三十七章;下經第二,四十四章。」(道藏宋謝首?混元聖紀引)
班固曰:「昔老聃著虛無之書兩篇。」(漢書揚雄傳贊)
闞澤對孫權曰:「漢景帝以?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令朝野悉諷誦之。」
(法苑珠林引吳書)
隋書經籍志道家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舊唐書經籍志儒家有老子二卷,老子撰。又二卷,河上公注。唐書藝文志道家有老子道德經二卷,李耳撰。又三卷,河上公注二卷。三志均有他家注若干卷。
晁讒之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尚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道德經跋——景迂生集)
宋濂曰:「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于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臣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抵歛守退藏,不為物失,而壹反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弇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主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聃亦豪傑士哉!傷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聃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是之慘也。」
成秋按:老子書為道家學說之總綱:道家流派雖殊,罔不以此書為根源。書成以來,歷數千載,其章句雖不免小有異同;而其內容,至今仍能保持其本來之面目,甚為難得。洵為研究道家思想之重要資料。(另有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討論,見本論第一章)
十、文子九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托者。」
隋書經籍志道家有文子十二卷,注曰:「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柳宗元曰:「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汙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增益之歟?或者眾家為聚斂以成其書歛?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閔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柳柳州文集)
洪邁曰:「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馬總只載其?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問,計然答』,列於農陳,其是矣,而今不存。」(榮齊髓筆)黃震曰:「文子者,周平王時辛妍之字,郎范蠡之師計然。嘗師老子,而作此書。其為之註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偽書爾。孔子後於周平王幾百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者,先能師老子耶?范蠡戰國人,又安得尚師平王時之文子耶?此偽一也。老子所談者清虛,而計然之所事者財利,此偽二也。其書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後世轉聲為霸耳,平王時未有霸之名,此偽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而書以老子之言,此偽四也。偽為之者,殆郎所謂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歟?其序盛稱唐明皇垂衣之化,則其崇尚虛無,上行下效,皆失其本心。為可知明皇之不克終,於是乎兆矣!豈獨深宮女子能召漁陽?鼓之變哉?書之每章必托老子為之辭。然用老子之說者,文衍意重,淡於嚼蠟;否則又散漫無統,自相反覆。謂默希子果有得於老子,吾亦未之信。」(黃?日抄)
姚際恒以文子列入「真書雜以偽者一類。」並云:「河東(柳宗元)之辨文子,可謂當矣。其書雖偽,然不全偽也,謂之『駁書』良然。其李邏為之歟?高似孫謂子厚所刊之書,今不可見。」(古今偽書考)
孫星衍曰:「黃帝之言述於老聃,老聃之學存於陳子。西漢用以冶世,當時諸臣,皆能稱道其說,故其書最顯。唐天寶能尊老氏,而不用其言,又號之真經,儒者始束而不觀。然諸子散佚,獨此有完本存道藏中,其傳不絕,亦其力也。今文子十二卷,實七錄舊本,班固藝文志稱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義、上禮三篇為一篇,以配下德耳。「藝文志注言『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托。』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為問答,非謂其書由後人偽託。宋人誤會其言,遂疑此書出於後世也。案書稱平王,並無周字,又班固誤讀此書,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書有云:『老子見常縱,見舌而知柔。』又云:『齒堅於舌而先弊。』考孔叢子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子不見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老聃疑即老萊子。史記所云:『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文子師老子,亦或遊於楚,平王同時,無足怪者。杜道堅亦以為楚平王不聽其言,遂有鞭屍之禍也。書又云:『秦、楚、燕、魏之歌』,則其人至六國時猶在矣。」(文子序)陶方琦曰:「文子非古書,現今屬於雜家之文子,與漢志屬道家之文子不同。文子雖冠以『老子曰」,中間有『故曰』,實引淮南作為老子之語。又准南作為戰國時人問答者,文子亦作為老子之語。詳細考之,文子首章之道原,即淮南之原道,精誠即精神,上德即說林,上義即兵略,實相一致,而割裂矛盾之跡顯然。」(漢孳室文鈔)
梁啟超曰:「此書自班氏已疑其依托,今本蓋並非班舊,實偽中出偽也。其大半勦自淮南子。」(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黃雲眉曰:「星衍既謂班固誤讀楚平王為周平王,則固之疑為依托,當由誤讀而來,不應又謂班固依托之托,乃托為問答之托,非後人假托之托。且問答之托,為古書所常有,班固既誤讀此平王為周平王,則文子與平王問答,不妨直言依托,何必曰『似依托』?似之云者,蓋懷疑及其書之本身,末敢為斬然之?,則似之云爾!星衍又據史記『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之說,謂老聃疑即老萊子,則史記又云:『或曰儋即老子』,將謂老聃即太史儋耶?此等惝恍之辭,本不足憑,星衍乃以偽孔叢,強事比附,惑矣。且此平王即定為楚平王,而楚平王之卒,距三家分晉之時,已百四十年,星衍謂其人至六國時猶在,亦不應老壽至此。綜星衍所辨,無以勝黃震,則定是書為偽書,實無不可。」(百今偽書考補證)
成秋按:此書世界書局之諸子集成,及古今文化出版社之百子全書,均不收錄,惟在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見之,題曰璧字通玄真經,歌希子注。(藝文印書館出版)吳全節通玄真經纜義序:「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文子法老子而立言。」其文皆稱老子曰,然不盡老子言也。文句多抄錄淮南子,而思想則本乎老子,間亦雜有莊子及法家、儒家、陰陽家言,末見深意。
十一、蜎子十三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音一元反。」
成秋按:娟子書久已亡佚,亦無輯本。近人或以為娟淵即環淵。引史記孟荀列傳云:「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旨意,著上下篇。」並謂上下篇即道德經,乃蝎子錄其師老子之說;至蜎子十三篇,則為其個人之思想。(見古史辨第四冊)
十二、關尹子九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名喜,為開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葛洪序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望見有紫氣浮關,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喜既得老子書,亦自著九篇,名關尹子。」
宋濂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為名,蓋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冶淮南王事,得之。」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擬即定之所為也。
「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為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人哉!」(諸子辨)
胡應麟曰:「闕尹子九篇,似即老聃弟子,而莊周稱之者。案七略道家有其目,自隋志絕不載,則是書之亡久矣。今所傳,云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者。陳振孫疑定所受不知何人,宋景濂以即定撰,皆有理。余則以藏定二子,尚非如阮逸,宋成輩實有其人,或俱子虛鳥有,末可知也。篇首劉向序,稱:『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等語,蓋晚唐人學昌黎聲口,亡論西京,即東漢至開元無有也。至篇中字句體法,全倣釋典成文,如『若人有超生死心,厭生死心』等語,亡論莊列,即鶡冠至亢倉亡有也。且隋志既不載,新、舊唐志亦敻無聞,而特顯於宋,又頗與齊丘化書有相似處,故吾嘗疑五代間方外士掇拾柱下之餘文,傅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書。雖中有絕到之談,似非淺近所辦。第以關尹,則萬無斯理。彼藏耶,定耶,真耶,膺耶?吾何暇辯之也哉!「關尹子談理,閒入莊列長生,其文則全倣釋氏。九篇之中,亡弗然者,世反以釋氏掇之。夫莊列,釋氏掇之者也,讀其文,於釋氏毫髮類乎?今篇掇其一,餘可類推……(下略)」(四部正?)梁啟超曰:「關尹子所講,全是佛教思想,即名詞亦全取自佛經,如受想行識,眼耳鼻舌心意,都不是中國固有的話。文章則四字一句,同楞嚴經一樣。史記稱關尹子名喜,守函谷,是老子後輩,老子出關,他請老子作書。莊子天下篇亦把老聃,關尹並列,說他們是古之博大真人。這樣看來,關尹這個人生得很早,但是關尹子這部書則出得很晚,看其文章,純是唐人翻譯佛經的筆墨,至少當在唐代以後。」(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成秋按:本書隋、唐志均不載,足見其亡佚已久,至宋復出,其文體內容又絕不類,梁啟超認其至少當在唐代以後,信然。又據張心激之考證,作偽者係五代時蜀人杜光庭。原名文始先生說道經,宋徽宗求書時得之,入道藏,鄭樵亦著錄於通志。而外間一本,經改題關尹子,故?庭堅張邦基得見之。西元一一七三年(癸巳),張仲才南遊攜歸金國,故世稱此書出於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其說甚為有理,似可採信。然關尹之學,莊子天下篇論之已詳,而苦無其他參考資料。姑以天下篇之言為本,而以書中不涉佛教道教之文參之,作一推斷而已。
十三、莊子五十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名周,宋人。」
司馬遷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隋書經籍志道家有莊子二十卷,注曰:「梁漆園吏莊周撰。晉散?常待向秀注。本二十卷,今闕。梁有莊子十卷,東晉議郎崔讚注,亡。」又十六卷,注曰:「司馬彪注,本二十一卷,今闕。」又三十卷,目一卷,注曰:「晉太傅主簿郭象注。梁七錄三十三卷。」又集注莊子六卷,注曰:「梁有莊子三十卷,晉承相參軍李頤注;莊子十八卷,孟氏注,錄一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俱有莊子十卷,郭象注;二十卷,向秀注,及其他各家注解若干卷。宋代有郭象注莊子十卷,成玄英莊子疏十卷,文如海莊子正義十卷,又莊子邈一卷,呂惠卿莊子解十卷,張昭補注莊子十卷,張炬莊子通真論三卷,李士表莊子十論一卷(宋史藝文志)
末濂曰:「?跖、漁父、讓王、說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剿入。」(諸子辨)
焦竑曰:「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莊子身當其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而胠?曰:『陳成子弒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俊盂前,莊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恒為田常,其為假託尤明。」(焦氏筆乘)
林景伊先生曰:「莊子……今所存者三十三篇,共分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蓋郭象之所訂也。內篇者,莊子學說之綱領,外篇充其不足之意,雜篇其雜記也。然內篇雖為莊子宗旨所寄,猶有後人加入之語,至外篇,雜篇之為莊子所作,或其弟子所記,尤難言矣。」(中國學術思想大綱)
成秋按:莊子與老子並為道家思想之兩大支柱。莊書以內篇為綱領,外、雜之作者雖不可必,又有後人加入之資料,然大旨在於發揮內篇之學說。故吾人取內篇為骨幹,而以外、雜篇之合於莊學綱領者為輔翼,則綱舉目張,莊學之大旨,可得而窺知也。
十四、列子八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劉向上列子序曰:「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在新書有棧,校?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洽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惟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傅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立傳。」
張湛列子序曰:「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並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問。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
高似孫曰:「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遊,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異,固以為誕。然觀太史公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獨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墨翟、秦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御寇獨不在其列。豈御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萃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猶疑之。夫『天毒之國,紀於山海,竺乾之師,聞於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為?,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子略)
宋濂曰:「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糯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之十年;向因魯穆公而誤為鄭耳。』其說要為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書本黃老言,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粹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端黃帝二篇,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遊』,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楊朱,力命,則『為我』之意多;疑即古楊朱書,其未亡者勦附於此。御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
「間嘗孰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凝形?,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行說』乎?『?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非『修習教觀說』乎?『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學幻』,非『幻化生滅說』乎?『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天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輪同不息說』乎?『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為樂說』乎?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為至論也。」(諸子辨)
四庫提要曰:「柳宗元以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云云。今考第五卷湯問篇中,併有鄒衍吹律事,不止魏牟孔穿,其不出禦寇之手更無疑義。然考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宏郭宏溥介純夏憮?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云云,是當時實有列子,非莊周之寓名。又穆天子傳出於晉太康中,為漢魏人之所未睹,而此書第三卷所?。鴛八駿,造父為御,至巨蒐,登崑崙,見西王母於瑤池事,一一與傳相合,此非劉向之時所能偽造,可確信為秦以前書。考公羊傳隱公十一年:『子沈子曰』,何休註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著其為師也。』然凡稱子某子者,乃弟子之稱師,非所自稱。此書皆稱子列子,則決為傳其學者所追記,非禦寇自著。其雜記列子後事,正如莊子記莊子死,管子稱吳王西施,商子稱秦孝公耳,不足為怪。張湛作是書註,於天端篇首昕稱子列,知為追記師言,而他篇復以載及後事為疑,未免不充其類矣。」
章炳麟曰:「列子書漢人無引者。王、何、稽、阮,下及樂廣,清談玄義,散在篇籍,亦無有引列子者。觀張湛序,殆其所自造。湛謂與佛經相似,實則有取於佛經耳。」(菿漢昌言)馬?倫有列子偽書考,認列子書及劉向序,均屬偽造,共列二十條證據,見天馬山房叢書,又見古史辨第四冊。後有日人武內義雄作列子?詞,逐條駁之,認列子八篇,非禦寇之筆,且經後人刪改,然大體上尚存向校定時面目,非王弼之徒所偽作。至於以鄭繆公之誤,斷為序非向作,因一字之誤,而疑序之全體,頗不合理。況由後人之偽寫,抑由向自誤,尚未可知。(武內義雄之文,見於先秦經籍考)
呂思勉曰:「此書前列張湛序,述得書源流,殊不可信。而云:『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同歸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指歸,多稱其言』,則不啻自寫供招。佛經初入中國時,原有以其言與老莊相參者,一以為同,一以為異,兩派頗有爭論。湛蓋亦以佛與老莊之道為可通,乃偽造此書,以通兩者之郵也。其云莊子慎到等多稱其言,蓋郎湛造此書時所取材。」(經子解題)
?秋按:本書非列子自著,中間又經劉向、張湛兩番整編,益非原來之面目矣。世之疑此書者,一因魏牟、孔穿、鄒衍,為列子所不能見,二因張湛所述得書經過事涉離奇,三因中有佛理。關於第一點因係列子後人所記,不成問題,四車提要言之已詳。至於書之來歷不明,及含有佛理,本人亦有一點不成熟之意見。吾以為設若張湛存心作偽,以常理言,自當設法使之天?無縫,何至於故意將得書經過曲述離奇,又自言其可與佛理相參,以啟後人之疑竇?且以本書與劉向所言之書相校,又頗為接近,不能謂毫無根源矣。故謂本書為張湛之所偽作,證據似尚欠充分。以吾之見,本書雖經張湛整理,並可能加入部份其他資料,但其內容,仍有大部承自劉氏之所傳;尤其楊朱、力命、天端、黃帝四篇,更有絕對可能為先秦道家思想之史料,末可全然舍棄。至於謂列子中含有佛理,此一問題,亦值得討論。夫道家思想,本近於佛,而於莊子為尤甚。列子書本近於莊,又數經整理,可能滲入其他資料,則其中間或夾入一二佛學名詞,自亦難免。然若遽以推定其書為佛經初入中國時所為造,似又未免過於孟浪。總而言之,吾以謂此書固然不無些許可疑之成分,但就整體而論,仍不失為先秦道家思想之重要史料也。
十五、老戌子十八篇
十六、長盧子九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楚人。」
十七、王狄子一篇
戍秋按:以上三書,均已亡佚,又無輯本,不可考證。
十八、公子牟四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成秋按:書已亡佚,其學蓋近於楊朱之縱欲派,世界書局印有清馬國翰緝佚本,可供參考。
十九、田子二十五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名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音步田反。」
成秋按:書已亡佚,其學蓋由道入法,所謂「老莊之後,流為申韓」者也。清馬國翰有輯佚本,世界書局印行。
二十、老萊子十六篇
漢書藝文志注:「楚人。」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二十一、黔婁子四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齊隱士,守道不訑,威王下之。師古曰:黔,音其炎反,下,音胡稼反。」
成秋按:二書已亡,世界書局印有輯本,載其言行。
二十二、宮孫子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師古曰;宮孫,姓也,不知名。」
成秋按:此書已亡,亦無輯本遺事可考。
二十三、鶡冠子一篇
漢書藝文志注:「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師古曰:以鶡鳥羽為冠。」
隋書經籍志道家有鶡冠子三卷,注曰:「楚之隱人。」
唐代,宋代,均有鶡冠子三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
崇文總目曰:「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氏嘗辯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鶡冠子者。」
晁公武曰:「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鵬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鶡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昕稱兩篇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俊雨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辭雜黃老刑名,意皆鄙淺,宗元之評蓋不誣。」(郡齊讀書志)
王應轔曰:「鶡冠子博選篇用國策郭隗之言,王鐵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鵬賦而已。柳子之辨,其知言哉!」(困學記聞)
胡應麟曰:「鶡冠子之偽與亢倉不同,蓋賈誼鵬賦所云,初非出鶡冠子;後世偽鶡冠者剽誼賦中語以文飾其陋。唐人不能辨,以鶡冠在誼前,遂指誼為所引,河東之說極得之。」(四部正?)姚際恒曰:「鶡冠子漢志止一篇,韓文公所讀有十九篇,四庫書目有三十六篇,逐代增多,何也?意者原本無多,餘悉後人燴入歟?」(古今偽書考)
梁啟超曰:「今書時含名理,且多古訓,似非出魏、晉以後人手。惟晁氏曰:『按四庫書目鶡冠子三十六篇,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然則此書經後人竄亂附益者多矣。今所存者,即中三卷,雖未必為漢人之舊,然猶為近古,非偽關尹、偽鬼谷之比也。」(漠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成秋按:今所見之鶡冠子,收入百子全書者,已去其前後各卷,僅餘十九篇,蓋復韓愈所見之舊也;然其所述,多雜黃老刑名之說,實言道家之用者。
二十四、周訓子十四篇
漢書藝文志注:「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人間小書,其言俗薄。」
成秋按:書已亡佚,不可考矣。
二十五、黃帝四經四篇
二十六、?帝銘六篇
二十七、?帝君臣十篇
漠書藝文志注曰:「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二十八、雜黃帝五十八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六國時賢者所作。」
成秋按:以上四書,均題為黃帝,而書又已亡佚,無法考證。然衡諸常理,三代之前,當不可能有此等書行世,其為偽託也明矣。至於作偽之時代,據漢書藝文志注,黃帝君臣、雜黃帝均在六國,則黃帝銘、?帝四經想亦在此前後。今由荀子、呂氏春秋,摘其一、二遺文,雖非真正之黃帝思想,然亦可以代表戰國時托為?帝思想之一斑矣。
二十九、力牧廿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成秋按:此書已亡,其為偽書甚明。
三十、孫子十六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六國時。」
成秋按:漢書藝文志別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師古注曰:「孫武也,臣於闔廬。」故此處所列必非孫武之作。其書已佚,不可詳考。
三十一、捷子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齊人,武帝時說。」
成秋按:此書今已亡佚,繞穆有接子考,謂即捷子,史記孟荀傳稱其「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其殆主命定之論者乎?(見古史辨第四冊)
三十二、曹羽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三十三、郎中嬰齊十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武帝時。師古曰,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遊觀名,能為文。」
三十四、臣君子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楚人。」
成秋按:以上三書均已亡佚,無考。
三十五、鄭長者
漢書藝文志注曰:「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人,不知姓名。」
成秋按:此書今亡,馬國翰據韓子所引一條,稱其主虛無,無見★採道旨,不且隱合禪宗乎?
三十六、楚子三篇
三十七、道家言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近世,不知作者。」
成秋按:以上二者亦已亡佚,無考。
先秦道家思想之原始資料,除此而外,尚有藝文志未著錄之書三種:陰符經、亢倉子、子華子,法家、雜家有關之書五種,即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尸子、晏子春秋是。約略討論如下:(管于漢志列道家,實亦法家,書已論之於前矣。)
(1)陰符經:題為?帝撰,唐李筌註。但隋書經籍志兵家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周書陰符九卷,是以多有疑之者。李筌自謂得此書於嵩山虎口巖石室,又謂驪山老母傳授微旨。以事涉離奇,難以取信。故一般人多以書即筌所偽造,亦有疑為寇謙之者。獨梁啟超曰:「其文簡潔,不似唐人文字……特未必太公或寇謙之所作。置之戰國末,與繫辭、老子同時可耳。蓋其思想與二書相近也。」(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說甚有理,從之。
(2)子華子:題曰周程本撰。按今本子華子鳩集眾語,非主一家,道家思想之成分甚少,且漢志不綠,甚為可疑,論者多辨其偽。然子華子之言,呂氏春秋已有引錄,則在漠以前,實有一子華子,可無疑也。至呂氏春秋之所本者,是否與今本相同,則不可必。姑取其書之可與道家相參者,作一?述而已。
(3)亢倉子:題為周庚桑楚撰。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然亢倉子代無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載。唐開元末,襄陽王士源獻上此書,當時即被指為士源之偽造。且史記明言亢桑子乃莊子虛造之人物,空言無實,則其偽益明矣。
(4)韓非子:題為周韓非撰。韓非為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後入秦,為李斯所害。其書有非所自作者,有黃老或道家言混入者,有縱?或遊說家言混入者,有後人有關非之記載因而混入者,攙雜不清,難以一一析辨。然非自著之部份,仍佔不少。主張法術並重,勢利兼顧,執一以靜,集法家之大成。
(5)呂氏春秋:題曰秦呂不韋撰,實其賓客之集體創作。本書上觀上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凡二十六卷。綜合各家之言論,以為一代之典範,故漢志列為雜家。
(6)淮南子:題為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注,二十一卷。此書雖屬雜家,然其大較,歸之於道,因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
(7)尸子:漢志雜家有尸子二十篇,注曰:名佼,魯人,秦相商鞅師之。其書今亡,世界書局有清汪繼培輯本。大指言道家之用,近乎刑名儒術之間。雖闕佚已甚,然單詞碎義,足以取證經子者,實屬指不勝屈。
(8)晏子春秋:張純一晏子春秋注?曰:「周季百家之書,有自著者,有非自著者。晏子書非晏子自作也,蓋晏子歿後,傳其學者綴晏子之言行而為之也……其學蓋原於墨儒,兼通名法農道,尼父兄事之,史遷願為之執鞭,有以夫!」成秋按:此書實以儒墨思想為主,但亦有合於道家思想者,不可不論。
以上所論資料之範圍,漢志道家著錄者計三十七種,漢志未著錄者三種,法家雜家之與道家有關者五種,合計四十五種。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再詳為條理,予以?述討論。以下各篇之論述,即本乎此。
吾人研究古代學術,當先確定其可供研究之資料,然後始能著手進行。研究先秦道家思想,自亦不能例外。然則如何確定研究之資料耶?曰,根據目錄。由目錄上查得有某書某書可供研究,再按圖索驥,循序以求,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於此所當注意者,資料有真偽,不辨其偽,則易:(1)失去各家學說之真象;(2)亂了學說先後之次序;(3)亂了學派相承之系統。(胡適說)
然偽書亦有其應用之價值,不可全然棄置。其價值何在?
山可以窺知作者當時之思想:例如黃帝之書,必非黃帝之所作,其理甚明;然而吾人知其作偽者之時代當在戰國,則可以由此窺知戰國時托為黃帝思想之一斑。管子雖非管仲之所作,亦可以由此研究戰國時法家思想之大概。
偽書中保有前代資料,可以藉此闡發先代學說之意旨:梁啟超曰:『偽書非辨別不可,那是當然的。但辨別以後,並不一定要把偽書燒完。固然也有些偽書可以燒的……但自唐以前的偽書?很可寶貴……其故因為偽書斷不能憑空造出,必須參考無數書籍;假貨中常有真寶貝,我們可以把它當作類書看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故偽書資料,倘運用得當,亦未始不可補真書史料之不足。惟當特別謹慎,不可受其迷惑而已。
先秦道家思想,最可靠之書目,當推漢書藝文志。(漢志則本諸劉氏父子之七略。)今且就漢志所載各書一一討論之。
一、伊尹五十一篇
漢書藝文志注:「湯相。」又:本志小說家伊尹說廿七篇。注曰:「其語淺薄,似依托也。」隋書經籍志無著錄。
王應麟曰:「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民也。……』伊尹所謂道,豈老氏所謂道乎?志於兵權謀者,伊尹太公而入道家,蓋戰國權謀之士,著書而托之伊尹也。」(漢書藝文志考證)
梁啟超曰:「伊尹時已有著作傳後,且篇數多至五十餘,此可斷其必誣。然孟子已徵引伊尹言論多條,則孟子時已有所謂伊尹者可知。逸周書有伊尹獻令,其起源當亦頗古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成秋按:本書已佚,世界書局印有清馬國翰輯佚本,共計十篇,其中有篇目可考者五篇,餘俱收入雜篇。其言與戰國術士語近,蓋出依托。王說是也。
二、太公二百冊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漢書藝文志注:「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師古曰:父讀曰甫也。」
成秋按:此書今佚,梁啟超謂今本陰符經當在太公謀中,不知然否?又六韜,三略均托為太公兵法,亦非此書。
三、辛甲二十九篇
注云:「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成秋按:本書之佚已久,隋、唐志皆不著錄。世界書局印有清馬國翰輯佚本,其虞箴似太公金匱陰謀,故入道家。
四、鬻子二十二篇
注云:「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師古曰:鬻,昔戈六反。」又小說家有鴦子說十九篇,注曰:「俊世所加。」隋志及兩唐志,宋志,俱載鬻子一卷。
葉夢得曰:「世傳鬻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書藝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鬻熊文王師,不知何以名道冢?而小說家亦別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逢行珪所獻。其文大略,古人著書不應爾。廖仲容子抄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行珪先後差不倫。恐行珪書或有附益。」(文?通考引)
李壽曰:「藝文志二十二篇,今十四篇。崇文總目以為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某謂劉向父子及班固所著錄者,或有他本,此蓋後世所托也。熊既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何耶?又文多殘闕,卷第?篇目皆錯亂,甚者幾不可曉,而注尤謬誤,然不敢以意刪定,姑存之以俟考。」(同上)
黃震曰:「逢行珪序其書云:『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熊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遂師之。』故其書首之以文王問,此必戰國處士假托之辭。蓋自漢藝文志已有其篇目,其語亦多可採。如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為大忌』,如曰『自謂賢者為不肖』,如曰『察吏於民』,皆足以警世。其餘載五帝、禹、湯之政,皆主得人。文亦不煩,異乎諸子之寓言虛誕者矣。然每篇多以『政曰』起語,而以『昔者』追述文王之問。既託文王,而下又曰魯周公。且亦未知自稱『政曰』者為誰。逢行珪既不能明言,而反釋以為政術之問,則非辭矣。」(黃氏日鈔)
楊慣認為今所存鬻子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又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文選注亦引有一條,皆今本所無,是以知其為偽書矣。(丹鉛雜錄)
胡應麟曰:「今子書傳於世而最先者,惟鬻子。其書概舉修身治國之術,實雜家言也,與柱下漆園宗旨?異,而漢志列於道家,諸史藝文及諸家目錄靡不因之。雖或以為疑,而迄莫能定。余謂理氏義例,咸規訣、向,不應謬誤若斯。載讀漢志小說家有鬻子一十九篇,乃釋然悟曰:此今所傅鬻子乎?蓋鬻子道家言者漢末已亡,而小說家尚傳於後,後人不能精覈,遂以道家所列當之。故歷世紛紛,名實咸爽,漢志故灼然明也。」(九流緒論)
姚際恒曰:「鬻子今一卷,止十四篇,唐逢行珪所上。案史記楚世家:『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非矣。又書載三監、曲阜事,壽亦不應如是永也。是其人之事已謬悠莫考,而況其書乎?論之者葉正則、宋景濂,皆以兩見漢志為疑,莫知此書誰屬。胡元瑞則以屬小說家,亦臆測也。高似孫以為漢儒綴緝,李仁父以為後世依托,王弇州疑其『七大夫』之名,楊用修歷引賈誼書及文選註所引鬻子,今皆無之。此足以見其大略矣。」(古今偽書考)
四庫提要曰:「劉勰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咨詢,遺文餘事,錄為鬻子。』則裒輯成編,不出能手,流傳附益,或構虛詞,故漢志別入小說家歟?獨是偽四八目一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來帝王輔佐有數可紀者,靡不具載;而此書所列禹七大夫:皋陶、杜子業、既子施、子黯、季子?、然子堪、輕子玉;湯七大夫:慶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西門疵、北門側,皆具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六朝之末尚無此本。或唐以來好事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撰為膺本,亦末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為佚脫錯亂之狀,而誼書所引,則無一條之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生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古無此體,又每篇寥寥數言,詞旨膚淺,決非三代舊文。」
譚獻曰:「鬻子遺文殘缺,非盡偽造。以逢注本較賈生所引,不至有武夫魚目之歎。」(復堂日記》
成秋按:鬻子之言,賈誼新書、文選註、列子、呂氏春秋均有摘引,故先秦道家必有鬻子之書,可以斷言;然今本鬻子,已大悖於柱下漆園之旨,甚無可取。其後人之偽托乎?抑係原屬漢志所列小說家之鬻子乎?資料殘缺,無從論斷。姑取其可與道家思想相參者三條,並合以各書佚語,作一?述,以窺其一斑而已。
五、筅子八十六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師古曰:筅讀與管同。」司馬遷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史記管晏列傳贊)
博玄曰:「管子之書過半便是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鄙俗。」(劉恕通鑑外紀引)
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法家均有管子十八卷,管夷吾撰。宋代有管子二十四卷,齊管夷吾撰。
末廉曰:「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說是矣。」(諸子辨)
四車提要曰:「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其他姑無論,即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中其孰為手撰,孰為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為記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為推其義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必由後人混而一之,致疑竇耳。」
梁啟超以管子批評兼愛非攻息兵,明係戰國初年墨家興起後方成為問題。若認管子為管仲作,則春秋初年即有人講兼愛非攻等問題,時代豈非紊亂?(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又以其中一部份當為春秋末年傳說,其大部份則戰國至漢初遞為增益,一種無系統之類書而已。(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羅根澤以牧民、形勢、五輔問,戰國政治思想家作;霸形、霸言,戰國中世後政冶思想家作;立政、乘馬、君臣上、君臣下、七臣、七主,戰國末政治思想家作;七法,戰國末為孫、吳、申、韓之學者所作;法禁,法法,戰國法家作;任法、明法,戰國中世後法家作:樞言,戰國末法家緣道家為之;宙合、侈靡、四時、五行,戰國末陰陽家作;勢,戰國末兵陰陽家作;心術上、心術下、白心,戰國中世以後道家作;制分,疑戰國兵家作;小稱,戰國儒家作;內業,戰國中世以後,混合儒道者作;戒,戰國末調和儒道者作,正戰國末雜家作;管子解五篇,戰國末秦未統一前雜家作;禁藏,戰國末至漢初雜家作;大匡,戰國人作;地圖,最早作於戰國中世,版法似亦戰國時人作;中匡、四稱,疑亦戰國人作;王言(亡)疑亦戰國中世以後人作;入國、九守、桓公問,疑戰國末年人作;九變疑戰國以後人作;權修,秦漢間兵家作;幼官,秦漢間兵陰陽家作;水地,漢初醫家作;封禪司馬遷作;輕重十九篇,漢武、昭時理財家作;八觀、正世、治國西漢文、景後政治思想家作;小匡、度地,漢初人作;地員,疑亦漢初人作;參患,漢文、景以後人作;弟子職疑漢儒家作;幼官圖,漢以後人作;小問,輯戰國關於管子之傳說而成;謀失、正言、言昭、修身、問霸並亡,無考。(管子探源)
成秋按:莞與管同,筦子今作管子。管子書所包甚廣,必非夷吾之自箸,梁任公以類書稱之,近是。然其中多言富國強兵之道,實近於刑名法術之間,故後世多列為法家。今惟取其書中可與道家思想相參者,作一?述而已。
六、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七、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述老子學。」
八、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子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九、劉向說老子四篇
成秋按:以上四書,皆解釋老子或發揮老學者;可見班氏之前,老子書早已流行,而漢志獨不備載,甚感奇怪。今四書均已不傳,惟老子巋然獨存,因補列其書於俊,且附考證焉。
[補]老子道德經上下篇計八十一章
司馬遷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謐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七略曰:「劉向?校中老子書二篇,太史書一篇,臣向書二篇,凡中外書五篇,一百四十二章,除複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八十一章。上經第一,三十七章;下經第二,四十四章。」(道藏宋謝首?混元聖紀引)
班固曰:「昔老聃著虛無之書兩篇。」(漢書揚雄傳贊)
闞澤對孫權曰:「漢景帝以?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令朝野悉諷誦之。」
(法苑珠林引吳書)
隋書經籍志道家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舊唐書經籍志儒家有老子二卷,老子撰。又二卷,河上公注。唐書藝文志道家有老子道德經二卷,李耳撰。又三卷,河上公注二卷。三志均有他家注若干卷。
晁讒之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尚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道德經跋——景迂生集)
宋濂曰:「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于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臣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抵歛守退藏,不為物失,而壹反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弇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主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聃亦豪傑士哉!傷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聃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是之慘也。」
成秋按:老子書為道家學說之總綱:道家流派雖殊,罔不以此書為根源。書成以來,歷數千載,其章句雖不免小有異同;而其內容,至今仍能保持其本來之面目,甚為難得。洵為研究道家思想之重要資料。(另有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討論,見本論第一章)
十、文子九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托者。」
隋書經籍志道家有文子十二卷,注曰:「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柳宗元曰:「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汙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增益之歟?或者眾家為聚斂以成其書歛?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閔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柳柳州文集)
洪邁曰:「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馬總只載其?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問,計然答』,列於農陳,其是矣,而今不存。」(榮齊髓筆)黃震曰:「文子者,周平王時辛妍之字,郎范蠡之師計然。嘗師老子,而作此書。其為之註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偽書爾。孔子後於周平王幾百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者,先能師老子耶?范蠡戰國人,又安得尚師平王時之文子耶?此偽一也。老子所談者清虛,而計然之所事者財利,此偽二也。其書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後世轉聲為霸耳,平王時未有霸之名,此偽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而書以老子之言,此偽四也。偽為之者,殆郎所謂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歟?其序盛稱唐明皇垂衣之化,則其崇尚虛無,上行下效,皆失其本心。為可知明皇之不克終,於是乎兆矣!豈獨深宮女子能召漁陽?鼓之變哉?書之每章必托老子為之辭。然用老子之說者,文衍意重,淡於嚼蠟;否則又散漫無統,自相反覆。謂默希子果有得於老子,吾亦未之信。」(黃?日抄)
姚際恒以文子列入「真書雜以偽者一類。」並云:「河東(柳宗元)之辨文子,可謂當矣。其書雖偽,然不全偽也,謂之『駁書』良然。其李邏為之歟?高似孫謂子厚所刊之書,今不可見。」(古今偽書考)
孫星衍曰:「黃帝之言述於老聃,老聃之學存於陳子。西漢用以冶世,當時諸臣,皆能稱道其說,故其書最顯。唐天寶能尊老氏,而不用其言,又號之真經,儒者始束而不觀。然諸子散佚,獨此有完本存道藏中,其傳不絕,亦其力也。今文子十二卷,實七錄舊本,班固藝文志稱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義、上禮三篇為一篇,以配下德耳。「藝文志注言『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托。』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為問答,非謂其書由後人偽託。宋人誤會其言,遂疑此書出於後世也。案書稱平王,並無周字,又班固誤讀此書,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書有云:『老子見常縱,見舌而知柔。』又云:『齒堅於舌而先弊。』考孔叢子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子不見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老聃疑即老萊子。史記所云:『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文子師老子,亦或遊於楚,平王同時,無足怪者。杜道堅亦以為楚平王不聽其言,遂有鞭屍之禍也。書又云:『秦、楚、燕、魏之歌』,則其人至六國時猶在矣。」(文子序)陶方琦曰:「文子非古書,現今屬於雜家之文子,與漢志屬道家之文子不同。文子雖冠以『老子曰」,中間有『故曰』,實引淮南作為老子之語。又准南作為戰國時人問答者,文子亦作為老子之語。詳細考之,文子首章之道原,即淮南之原道,精誠即精神,上德即說林,上義即兵略,實相一致,而割裂矛盾之跡顯然。」(漢孳室文鈔)
梁啟超曰:「此書自班氏已疑其依托,今本蓋並非班舊,實偽中出偽也。其大半勦自淮南子。」(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黃雲眉曰:「星衍既謂班固誤讀楚平王為周平王,則固之疑為依托,當由誤讀而來,不應又謂班固依托之托,乃托為問答之托,非後人假托之托。且問答之托,為古書所常有,班固既誤讀此平王為周平王,則文子與平王問答,不妨直言依托,何必曰『似依托』?似之云者,蓋懷疑及其書之本身,末敢為斬然之?,則似之云爾!星衍又據史記『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之說,謂老聃疑即老萊子,則史記又云:『或曰儋即老子』,將謂老聃即太史儋耶?此等惝恍之辭,本不足憑,星衍乃以偽孔叢,強事比附,惑矣。且此平王即定為楚平王,而楚平王之卒,距三家分晉之時,已百四十年,星衍謂其人至六國時猶在,亦不應老壽至此。綜星衍所辨,無以勝黃震,則定是書為偽書,實無不可。」(百今偽書考補證)
成秋按:此書世界書局之諸子集成,及古今文化出版社之百子全書,均不收錄,惟在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見之,題曰璧字通玄真經,歌希子注。(藝文印書館出版)吳全節通玄真經纜義序:「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文子法老子而立言。」其文皆稱老子曰,然不盡老子言也。文句多抄錄淮南子,而思想則本乎老子,間亦雜有莊子及法家、儒家、陰陽家言,末見深意。
十一、蜎子十三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音一元反。」
成秋按:娟子書久已亡佚,亦無輯本。近人或以為娟淵即環淵。引史記孟荀列傳云:「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旨意,著上下篇。」並謂上下篇即道德經,乃蝎子錄其師老子之說;至蜎子十三篇,則為其個人之思想。(見古史辨第四冊)
十二、關尹子九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名喜,為開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葛洪序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望見有紫氣浮關,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喜既得老子書,亦自著九篇,名關尹子。」
宋濂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為名,蓋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冶淮南王事,得之。」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擬即定之所為也。
「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為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人哉!」(諸子辨)
胡應麟曰:「闕尹子九篇,似即老聃弟子,而莊周稱之者。案七略道家有其目,自隋志絕不載,則是書之亡久矣。今所傳,云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者。陳振孫疑定所受不知何人,宋景濂以即定撰,皆有理。余則以藏定二子,尚非如阮逸,宋成輩實有其人,或俱子虛鳥有,末可知也。篇首劉向序,稱:『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等語,蓋晚唐人學昌黎聲口,亡論西京,即東漢至開元無有也。至篇中字句體法,全倣釋典成文,如『若人有超生死心,厭生死心』等語,亡論莊列,即鶡冠至亢倉亡有也。且隋志既不載,新、舊唐志亦敻無聞,而特顯於宋,又頗與齊丘化書有相似處,故吾嘗疑五代間方外士掇拾柱下之餘文,傅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書。雖中有絕到之談,似非淺近所辦。第以關尹,則萬無斯理。彼藏耶,定耶,真耶,膺耶?吾何暇辯之也哉!「關尹子談理,閒入莊列長生,其文則全倣釋氏。九篇之中,亡弗然者,世反以釋氏掇之。夫莊列,釋氏掇之者也,讀其文,於釋氏毫髮類乎?今篇掇其一,餘可類推……(下略)」(四部正?)梁啟超曰:「關尹子所講,全是佛教思想,即名詞亦全取自佛經,如受想行識,眼耳鼻舌心意,都不是中國固有的話。文章則四字一句,同楞嚴經一樣。史記稱關尹子名喜,守函谷,是老子後輩,老子出關,他請老子作書。莊子天下篇亦把老聃,關尹並列,說他們是古之博大真人。這樣看來,關尹這個人生得很早,但是關尹子這部書則出得很晚,看其文章,純是唐人翻譯佛經的筆墨,至少當在唐代以後。」(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成秋按:本書隋、唐志均不載,足見其亡佚已久,至宋復出,其文體內容又絕不類,梁啟超認其至少當在唐代以後,信然。又據張心激之考證,作偽者係五代時蜀人杜光庭。原名文始先生說道經,宋徽宗求書時得之,入道藏,鄭樵亦著錄於通志。而外間一本,經改題關尹子,故?庭堅張邦基得見之。西元一一七三年(癸巳),張仲才南遊攜歸金國,故世稱此書出於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其說甚為有理,似可採信。然關尹之學,莊子天下篇論之已詳,而苦無其他參考資料。姑以天下篇之言為本,而以書中不涉佛教道教之文參之,作一推斷而已。
十三、莊子五十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名周,宋人。」
司馬遷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隋書經籍志道家有莊子二十卷,注曰:「梁漆園吏莊周撰。晉散?常待向秀注。本二十卷,今闕。梁有莊子十卷,東晉議郎崔讚注,亡。」又十六卷,注曰:「司馬彪注,本二十一卷,今闕。」又三十卷,目一卷,注曰:「晉太傅主簿郭象注。梁七錄三十三卷。」又集注莊子六卷,注曰:「梁有莊子三十卷,晉承相參軍李頤注;莊子十八卷,孟氏注,錄一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俱有莊子十卷,郭象注;二十卷,向秀注,及其他各家注解若干卷。宋代有郭象注莊子十卷,成玄英莊子疏十卷,文如海莊子正義十卷,又莊子邈一卷,呂惠卿莊子解十卷,張昭補注莊子十卷,張炬莊子通真論三卷,李士表莊子十論一卷(宋史藝文志)
末濂曰:「?跖、漁父、讓王、說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剿入。」(諸子辨)
焦竑曰:「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莊子身當其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而胠?曰:『陳成子弒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俊盂前,莊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恒為田常,其為假託尤明。」(焦氏筆乘)
林景伊先生曰:「莊子……今所存者三十三篇,共分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蓋郭象之所訂也。內篇者,莊子學說之綱領,外篇充其不足之意,雜篇其雜記也。然內篇雖為莊子宗旨所寄,猶有後人加入之語,至外篇,雜篇之為莊子所作,或其弟子所記,尤難言矣。」(中國學術思想大綱)
成秋按:莊子與老子並為道家思想之兩大支柱。莊書以內篇為綱領,外、雜之作者雖不可必,又有後人加入之資料,然大旨在於發揮內篇之學說。故吾人取內篇為骨幹,而以外、雜篇之合於莊學綱領者為輔翼,則綱舉目張,莊學之大旨,可得而窺知也。
十四、列子八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劉向上列子序曰:「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在新書有棧,校?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洽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惟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傅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立傳。」
張湛列子序曰:「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並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問。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
高似孫曰:「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遊,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異,固以為誕。然觀太史公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獨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墨翟、秦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御寇獨不在其列。豈御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萃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猶疑之。夫『天毒之國,紀於山海,竺乾之師,聞於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為?,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子略)
宋濂曰:「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糯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之十年;向因魯穆公而誤為鄭耳。』其說要為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書本黃老言,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粹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端黃帝二篇,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遊』,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楊朱,力命,則『為我』之意多;疑即古楊朱書,其未亡者勦附於此。御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
「間嘗孰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凝形?,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行說』乎?『?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非『修習教觀說』乎?『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學幻』,非『幻化生滅說』乎?『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天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輪同不息說』乎?『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為樂說』乎?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為至論也。」(諸子辨)
四庫提要曰:「柳宗元以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云云。今考第五卷湯問篇中,併有鄒衍吹律事,不止魏牟孔穿,其不出禦寇之手更無疑義。然考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宏郭宏溥介純夏憮?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云云,是當時實有列子,非莊周之寓名。又穆天子傳出於晉太康中,為漢魏人之所未睹,而此書第三卷所?。鴛八駿,造父為御,至巨蒐,登崑崙,見西王母於瑤池事,一一與傳相合,此非劉向之時所能偽造,可確信為秦以前書。考公羊傳隱公十一年:『子沈子曰』,何休註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著其為師也。』然凡稱子某子者,乃弟子之稱師,非所自稱。此書皆稱子列子,則決為傳其學者所追記,非禦寇自著。其雜記列子後事,正如莊子記莊子死,管子稱吳王西施,商子稱秦孝公耳,不足為怪。張湛作是書註,於天端篇首昕稱子列,知為追記師言,而他篇復以載及後事為疑,未免不充其類矣。」
章炳麟曰:「列子書漢人無引者。王、何、稽、阮,下及樂廣,清談玄義,散在篇籍,亦無有引列子者。觀張湛序,殆其所自造。湛謂與佛經相似,實則有取於佛經耳。」(菿漢昌言)馬?倫有列子偽書考,認列子書及劉向序,均屬偽造,共列二十條證據,見天馬山房叢書,又見古史辨第四冊。後有日人武內義雄作列子?詞,逐條駁之,認列子八篇,非禦寇之筆,且經後人刪改,然大體上尚存向校定時面目,非王弼之徒所偽作。至於以鄭繆公之誤,斷為序非向作,因一字之誤,而疑序之全體,頗不合理。況由後人之偽寫,抑由向自誤,尚未可知。(武內義雄之文,見於先秦經籍考)
呂思勉曰:「此書前列張湛序,述得書源流,殊不可信。而云:『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同歸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指歸,多稱其言』,則不啻自寫供招。佛經初入中國時,原有以其言與老莊相參者,一以為同,一以為異,兩派頗有爭論。湛蓋亦以佛與老莊之道為可通,乃偽造此書,以通兩者之郵也。其云莊子慎到等多稱其言,蓋郎湛造此書時所取材。」(經子解題)
?秋按:本書非列子自著,中間又經劉向、張湛兩番整編,益非原來之面目矣。世之疑此書者,一因魏牟、孔穿、鄒衍,為列子所不能見,二因張湛所述得書經過事涉離奇,三因中有佛理。關於第一點因係列子後人所記,不成問題,四車提要言之已詳。至於書之來歷不明,及含有佛理,本人亦有一點不成熟之意見。吾以為設若張湛存心作偽,以常理言,自當設法使之天?無縫,何至於故意將得書經過曲述離奇,又自言其可與佛理相參,以啟後人之疑竇?且以本書與劉向所言之書相校,又頗為接近,不能謂毫無根源矣。故謂本書為張湛之所偽作,證據似尚欠充分。以吾之見,本書雖經張湛整理,並可能加入部份其他資料,但其內容,仍有大部承自劉氏之所傳;尤其楊朱、力命、天端、黃帝四篇,更有絕對可能為先秦道家思想之史料,末可全然舍棄。至於謂列子中含有佛理,此一問題,亦值得討論。夫道家思想,本近於佛,而於莊子為尤甚。列子書本近於莊,又數經整理,可能滲入其他資料,則其中間或夾入一二佛學名詞,自亦難免。然若遽以推定其書為佛經初入中國時所為造,似又未免過於孟浪。總而言之,吾以謂此書固然不無些許可疑之成分,但就整體而論,仍不失為先秦道家思想之重要史料也。
十五、老戌子十八篇
十六、長盧子九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楚人。」
十七、王狄子一篇
戍秋按:以上三書,均已亡佚,又無輯本,不可考證。
十八、公子牟四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成秋按:書已亡佚,其學蓋近於楊朱之縱欲派,世界書局印有清馬國翰緝佚本,可供參考。
十九、田子二十五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名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音步田反。」
成秋按:書已亡佚,其學蓋由道入法,所謂「老莊之後,流為申韓」者也。清馬國翰有輯佚本,世界書局印行。
二十、老萊子十六篇
漢書藝文志注:「楚人。」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二十一、黔婁子四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齊隱士,守道不訑,威王下之。師古曰:黔,音其炎反,下,音胡稼反。」
成秋按:二書已亡,世界書局印有輯本,載其言行。
二十二、宮孫子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師古曰;宮孫,姓也,不知名。」
成秋按:此書已亡,亦無輯本遺事可考。
二十三、鶡冠子一篇
漢書藝文志注:「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師古曰:以鶡鳥羽為冠。」
隋書經籍志道家有鶡冠子三卷,注曰:「楚之隱人。」
唐代,宋代,均有鶡冠子三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
崇文總目曰:「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氏嘗辯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鶡冠子者。」
晁公武曰:「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鵬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鶡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昕稱兩篇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俊雨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辭雜黃老刑名,意皆鄙淺,宗元之評蓋不誣。」(郡齊讀書志)
王應轔曰:「鶡冠子博選篇用國策郭隗之言,王鐵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鵬賦而已。柳子之辨,其知言哉!」(困學記聞)
胡應麟曰:「鶡冠子之偽與亢倉不同,蓋賈誼鵬賦所云,初非出鶡冠子;後世偽鶡冠者剽誼賦中語以文飾其陋。唐人不能辨,以鶡冠在誼前,遂指誼為所引,河東之說極得之。」(四部正?)姚際恒曰:「鶡冠子漢志止一篇,韓文公所讀有十九篇,四庫書目有三十六篇,逐代增多,何也?意者原本無多,餘悉後人燴入歟?」(古今偽書考)
梁啟超曰:「今書時含名理,且多古訓,似非出魏、晉以後人手。惟晁氏曰:『按四庫書目鶡冠子三十六篇,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然則此書經後人竄亂附益者多矣。今所存者,即中三卷,雖未必為漢人之舊,然猶為近古,非偽關尹、偽鬼谷之比也。」(漠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成秋按:今所見之鶡冠子,收入百子全書者,已去其前後各卷,僅餘十九篇,蓋復韓愈所見之舊也;然其所述,多雜黃老刑名之說,實言道家之用者。
二十四、周訓子十四篇
漢書藝文志注:「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人間小書,其言俗薄。」
成秋按:書已亡佚,不可考矣。
二十五、黃帝四經四篇
二十六、?帝銘六篇
二十七、?帝君臣十篇
漠書藝文志注曰:「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二十八、雜黃帝五十八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六國時賢者所作。」
成秋按:以上四書,均題為黃帝,而書又已亡佚,無法考證。然衡諸常理,三代之前,當不可能有此等書行世,其為偽託也明矣。至於作偽之時代,據漢書藝文志注,黃帝君臣、雜黃帝均在六國,則黃帝銘、?帝四經想亦在此前後。今由荀子、呂氏春秋,摘其一、二遺文,雖非真正之黃帝思想,然亦可以代表戰國時托為?帝思想之一斑矣。
二十九、力牧廿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成秋按:此書已亡,其為偽書甚明。
三十、孫子十六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六國時。」
成秋按:漢書藝文志別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師古注曰:「孫武也,臣於闔廬。」故此處所列必非孫武之作。其書已佚,不可詳考。
三十一、捷子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齊人,武帝時說。」
成秋按:此書今已亡佚,繞穆有接子考,謂即捷子,史記孟荀傳稱其「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其殆主命定之論者乎?(見古史辨第四冊)
三十二、曹羽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三十三、郎中嬰齊十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曰:「武帝時。師古曰,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遊觀名,能為文。」
三十四、臣君子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楚人。」
成秋按:以上三書均已亡佚,無考。
三十五、鄭長者
漢書藝文志注曰:「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人,不知姓名。」
成秋按:此書今亡,馬國翰據韓子所引一條,稱其主虛無,無見★採道旨,不且隱合禪宗乎?
三十六、楚子三篇
三十七、道家言二篇
漢書藝文志注云:「近世,不知作者。」
成秋按:以上二者亦已亡佚,無考。
先秦道家思想之原始資料,除此而外,尚有藝文志未著錄之書三種:陰符經、亢倉子、子華子,法家、雜家有關之書五種,即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尸子、晏子春秋是。約略討論如下:(管于漢志列道家,實亦法家,書已論之於前矣。)
(1)陰符經:題為?帝撰,唐李筌註。但隋書經籍志兵家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周書陰符九卷,是以多有疑之者。李筌自謂得此書於嵩山虎口巖石室,又謂驪山老母傳授微旨。以事涉離奇,難以取信。故一般人多以書即筌所偽造,亦有疑為寇謙之者。獨梁啟超曰:「其文簡潔,不似唐人文字……特未必太公或寇謙之所作。置之戰國末,與繫辭、老子同時可耳。蓋其思想與二書相近也。」(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說甚有理,從之。
(2)子華子:題曰周程本撰。按今本子華子鳩集眾語,非主一家,道家思想之成分甚少,且漢志不綠,甚為可疑,論者多辨其偽。然子華子之言,呂氏春秋已有引錄,則在漠以前,實有一子華子,可無疑也。至呂氏春秋之所本者,是否與今本相同,則不可必。姑取其書之可與道家相參者,作一?述而已。
(3)亢倉子:題為周庚桑楚撰。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然亢倉子代無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載。唐開元末,襄陽王士源獻上此書,當時即被指為士源之偽造。且史記明言亢桑子乃莊子虛造之人物,空言無實,則其偽益明矣。
(4)韓非子:題為周韓非撰。韓非為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後入秦,為李斯所害。其書有非所自作者,有黃老或道家言混入者,有縱?或遊說家言混入者,有後人有關非之記載因而混入者,攙雜不清,難以一一析辨。然非自著之部份,仍佔不少。主張法術並重,勢利兼顧,執一以靜,集法家之大成。
(5)呂氏春秋:題曰秦呂不韋撰,實其賓客之集體創作。本書上觀上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凡二十六卷。綜合各家之言論,以為一代之典範,故漢志列為雜家。
(6)淮南子:題為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注,二十一卷。此書雖屬雜家,然其大較,歸之於道,因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
(7)尸子:漢志雜家有尸子二十篇,注曰:名佼,魯人,秦相商鞅師之。其書今亡,世界書局有清汪繼培輯本。大指言道家之用,近乎刑名儒術之間。雖闕佚已甚,然單詞碎義,足以取證經子者,實屬指不勝屈。
(8)晏子春秋:張純一晏子春秋注?曰:「周季百家之書,有自著者,有非自著者。晏子書非晏子自作也,蓋晏子歿後,傳其學者綴晏子之言行而為之也……其學蓋原於墨儒,兼通名法農道,尼父兄事之,史遷願為之執鞭,有以夫!」成秋按:此書實以儒墨思想為主,但亦有合於道家思想者,不可不論。
以上所論資料之範圍,漢志道家著錄者計三十七種,漢志未著錄者三種,法家雜家之與道家有關者五種,合計四十五種。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再詳為條理,予以?述討論。以下各篇之論述,即本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