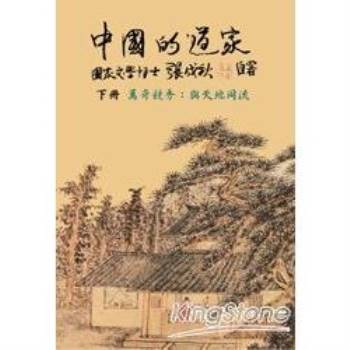第一章 老子書之作者——老聃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於知欲瞭解一篇作品,不可不知其作者;欲探究一家之思想,不可不略知其為人之生平。茲編之作,命之曰「老子王弼畢」,則老子與王弼生平之大略,首應討論。在此,先論老子書之作者——老聃。
老聃生平之最可靠記載,見於史記之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裡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蔽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皆已朽矣,獨箕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默,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送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史記卷六十三)
由上之記載,可知老子書——今亦分上下篇,五千言,言道德之意——之作者,即為老子,名曰李耳,亦即老聃。高亨老子正詁云:「老李乃一聲之轉,老子原姓老,後以晉同,變為李,非有二也。」
但老子為隱君子(見下引),不求闐達,且當時姓老而又思想相近,亦號稱老子者不一人,太史公為忠於歷史之學者,故又捃拾有關之資料,附記於老聃傳後,並列其世系焉。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借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幹。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復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邛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史記卷六十三,老莊申韓列傳)
近世學者,誤以史記老子傳中之數人為一人,再考其年代,諸多疑竇,因而對此傳大表懷疑(詳見古史辨第四冊第六冊)。既以正史為不可信,因而馳其聰明,大倡奇說,或曰老子生於黃河流域,或曰老子為印度之移住者,或曰老子在母胎中敷十年,生時已有白髮故名曰老子。或謂老子名耳,料屬緬甸地方大耳國之人種,遠徙中土。或曰老子姓李,係因其家有李樹。或曰老子人與老子書非同一時代,老子人早於孔子,老子書晚至戰國秦漢。又或曰不然,老子書當早於論語之前。或以為老子即一隱居之老先生,不必辯其為何人……驟訟紛紜,莫衷一是。
餘以為不必庸人自擾。老聃(李耳)著老子,且孔子向其問禮等事,載於正史,黑白分明,且莊子、禮記、呂氏春秋,均有甚多之佐證,皆絕對可信。老子世為史官,又典守周世之藏書,博學通禮,故孔子問焉。然老子雖學禮、守禮,至其晚年,則思想大有改變。夫禮為周公所制定,至老子時已敷百年。封建解體,禮壤樂崩。一般人非傲慢無禮,即貌恭而心不敬。老子既身受禮制之束縛,又痛時人之虛偽不誠,深感與其維護有名無實之禮制,何若放棄虛偽之形式而反璞歸真。故老子並非橫蠻無法之人,乃欲更進一步,達到禮制所不能達到之境界。(見拙著先秦道家思想研究中編第一章,中華書局。)
要之,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精於禮學,明於歷史故實,故孔子問焉。其基本主張,為聳道貴德,欲人得時則駕,不得時則退藏於野。並應謙虛守愚,柔弱居下,自隱無名,清淨自正,無為自化,為可信耳。
又,群書之中,記老子逸聞佚事者甚多,今擇其尤要者三條,錄之於下,以補史記老子傳之不足: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可以語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邪?」「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敬其老邪?」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已矣。」「子知之乎?」老子曰:「豈非柔存而剛亡邪?」常樅曰:「噫,天下之事盡於此矣!吾何以復語子哉?」(高士傳作商容,世說註云:商容,老子師。)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雲。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呂氏春秋曰: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附錄
漢代於吾邦產生一中華固有之宗教——道教,即以老子為其崇敬之博大真人,又以老子道德經之書為其主要經典,後先比附,老子遂成為神仙般之人物。太平廣記卷一引葛洪神仙傳,其中有對老子之記載,多取前史,而加入不少神奇之事,於可見道教對老子傳說之一斑,又有若干可補正史之不足。固不得全信,亦可資參研。愛錄於後,以供賞玩: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裡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振,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曰:「其母無夫,老於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於,帝譽時為祿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雲守藏史。」或云:「在越為範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皆見於群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
葛稚川云:「洪以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上,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明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於蓋得道之尤精者也,非異類也。」
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事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為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非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頰,則非可學也。
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間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一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敷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為主。井老仙經88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
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鬥,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為守蔽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為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遠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濟,眾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轂,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
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為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
孔子嘗往問禮,先使子貫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邱,相從三年而後可敬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女曷為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虻噆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擊蚊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
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莫不獻之其君;使進而可進入,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於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邱治詩、書、疆、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跡,以幹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陳者,皆因陳跡也。跡者履之出,而跡豈異哉?」
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為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未嘗不街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為鉤緡而投之,未嘗不釣而制之也。至於籠,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
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猱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已;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
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裡,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
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惟計甲所應得之值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駭,乃見老子。
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乙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值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
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于復乙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遺之而去。並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而得仙。
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琉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顛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為宗也。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於知欲瞭解一篇作品,不可不知其作者;欲探究一家之思想,不可不略知其為人之生平。茲編之作,命之曰「老子王弼畢」,則老子與王弼生平之大略,首應討論。在此,先論老子書之作者——老聃。
老聃生平之最可靠記載,見於史記之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裡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蔽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皆已朽矣,獨箕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默,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送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史記卷六十三)
由上之記載,可知老子書——今亦分上下篇,五千言,言道德之意——之作者,即為老子,名曰李耳,亦即老聃。高亨老子正詁云:「老李乃一聲之轉,老子原姓老,後以晉同,變為李,非有二也。」
但老子為隱君子(見下引),不求闐達,且當時姓老而又思想相近,亦號稱老子者不一人,太史公為忠於歷史之學者,故又捃拾有關之資料,附記於老聃傳後,並列其世系焉。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借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幹。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復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邛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史記卷六十三,老莊申韓列傳)
近世學者,誤以史記老子傳中之數人為一人,再考其年代,諸多疑竇,因而對此傳大表懷疑(詳見古史辨第四冊第六冊)。既以正史為不可信,因而馳其聰明,大倡奇說,或曰老子生於黃河流域,或曰老子為印度之移住者,或曰老子在母胎中敷十年,生時已有白髮故名曰老子。或謂老子名耳,料屬緬甸地方大耳國之人種,遠徙中土。或曰老子姓李,係因其家有李樹。或曰老子人與老子書非同一時代,老子人早於孔子,老子書晚至戰國秦漢。又或曰不然,老子書當早於論語之前。或以為老子即一隱居之老先生,不必辯其為何人……驟訟紛紜,莫衷一是。
餘以為不必庸人自擾。老聃(李耳)著老子,且孔子向其問禮等事,載於正史,黑白分明,且莊子、禮記、呂氏春秋,均有甚多之佐證,皆絕對可信。老子世為史官,又典守周世之藏書,博學通禮,故孔子問焉。然老子雖學禮、守禮,至其晚年,則思想大有改變。夫禮為周公所制定,至老子時已敷百年。封建解體,禮壤樂崩。一般人非傲慢無禮,即貌恭而心不敬。老子既身受禮制之束縛,又痛時人之虛偽不誠,深感與其維護有名無實之禮制,何若放棄虛偽之形式而反璞歸真。故老子並非橫蠻無法之人,乃欲更進一步,達到禮制所不能達到之境界。(見拙著先秦道家思想研究中編第一章,中華書局。)
要之,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精於禮學,明於歷史故實,故孔子問焉。其基本主張,為聳道貴德,欲人得時則駕,不得時則退藏於野。並應謙虛守愚,柔弱居下,自隱無名,清淨自正,無為自化,為可信耳。
又,群書之中,記老子逸聞佚事者甚多,今擇其尤要者三條,錄之於下,以補史記老子傳之不足: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可以語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邪?」「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敬其老邪?」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已矣。」「子知之乎?」老子曰:「豈非柔存而剛亡邪?」常樅曰:「噫,天下之事盡於此矣!吾何以復語子哉?」(高士傳作商容,世說註云:商容,老子師。)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雲。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呂氏春秋曰: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附錄
漢代於吾邦產生一中華固有之宗教——道教,即以老子為其崇敬之博大真人,又以老子道德經之書為其主要經典,後先比附,老子遂成為神仙般之人物。太平廣記卷一引葛洪神仙傳,其中有對老子之記載,多取前史,而加入不少神奇之事,於可見道教對老子傳說之一斑,又有若干可補正史之不足。固不得全信,亦可資參研。愛錄於後,以供賞玩: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裡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振,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曰:「其母無夫,老於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於,帝譽時為祿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雲守藏史。」或云:「在越為範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皆見於群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
葛稚川云:「洪以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上,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明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於蓋得道之尤精者也,非異類也。」
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事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為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非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頰,則非可學也。
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間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一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敷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為主。井老仙經88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
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鬥,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為守蔽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為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遠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濟,眾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轂,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
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為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
孔子嘗往問禮,先使子貫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邱,相從三年而後可敬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女曷為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虻噆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擊蚊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
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莫不獻之其君;使進而可進入,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於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邱治詩、書、疆、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跡,以幹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陳者,皆因陳跡也。跡者履之出,而跡豈異哉?」
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為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未嘗不街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為鉤緡而投之,未嘗不釣而制之也。至於籠,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
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猱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已;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
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裡,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
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惟計甲所應得之值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駭,乃見老子。
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乙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值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
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于復乙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遺之而去。並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而得仙。
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琉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顛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為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