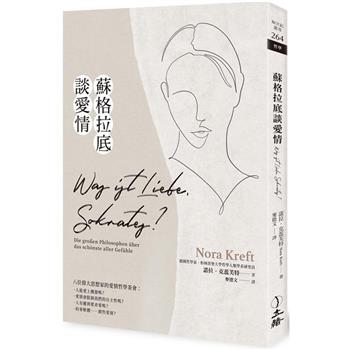第二章
愛情和智慧有什麼關係?
蘇格拉底說明愛欲、美與追求智慧之間的關聯
蘇格拉底輕輕來回扭動,搖臀擺頭。他的披巾從肩膀滑落。「愛是個開明的女乞丐,」他這般開場:「她慧黠,飄忽不定……」他沉思地靜默。然後他搖搖頭,解釋說:「我像個愛情專家站在你們面前,根本難以置信,不是嗎?我可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對吧?!」他抬起視線,輕笑著:「相當棘手的情況,而我難辭其咎。我知道,我知道,但就是發生了。我曾多次吹噓知道愛的本質,結果現在我必須發言和回答問題。」他按摩著手心,先是一手,然後換手。他的聽眾似乎有些不安,但是耐著性子,安靜坐在位子上。
「我希望,要是迪奧蒂瑪(Diotima)在這裡就好了……」他終於繼續說下去,從地上收拾起他的披巾。「或者我就忘了演講什麼的,直接向你們述說,我和她對愛的討論究竟談了些什麼,當我還年輕而你們還是學生的時候。」
「這個好!」發自艾瑞絲,但西格蒙德攪著咖啡,就像順口而出地說:「為什麼是迪奧蒂瑪?她根本不存在,她只是你虛構出來的!」
*
女祭司迪奧蒂瑪是柏拉圖〈會飲篇〉裡的一個角色。柏拉圖是蘇格拉底最知名的學生,在他的老師去世之後撰寫了哲學對話錄,蘇格拉底是其中的主角。在〈會飲篇〉中,蘇格拉底介紹迪奧蒂瑪是他的哲學老師,描述兩人對愛與欲的討論。柏拉圖對話錄當中的大部分角色都以歷史人物為雛形,但迪奧蒂瑪是真實存在或是完全虛構,一直都受到正反雙方的討論。
*
蘇格拉底又讓披巾滑落,似乎忿忿不平,「虛構?她絕對真實存在!沒有迪奧蒂瑪我絕不會開始哲學思辯——後來的你們也不會,坦白說。」他拍了下手,瞬間清醒過來:「一切都從她問我愛情是什麼開始。我結巴地說什麼心動和無眠的夜晚,但是說沒幾句她就打斷我的話,要求我整理思緒。我應該徹底思考而非天馬行空。幾回失敗的嘗試之後,她協助我跨出一大步。她認為,這麼看吧:愛上些什麼的人畢竟有所欲求,愛卻無所求——沒有這樣的愛,不是嗎?我們甚至可以說,愛就是一種欲求吧?這啟迪了我,直到今日依然啟迪著我。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奧古斯丁、西蒙和西格蒙德點點頭,但是其他人卻滿臉疑惑。馬克斯剛吸了口氣要說些什麼,伊曼紐卻搶在他前頭:「我認為這個說法至少非常容易理解。我們就暫時這麼認定,蘇格拉底,我們接受這個說法,那麼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我也這麼問迪奧蒂瑪,她立刻反問我:我們和我們欲求的對象處在何種關係之中?我嘆息著說,你的問題依舊這麼抽象。哎呀,她生氣地喊著,自己回答了問題:我們只會對我們認為自己還未擁有的東西產生欲求。要是你已經和贊西佩結婚,你也確實意識到這段婚姻,那麼你就不會再想著要和贊西佩結婚。要是……」蘇格拉底環顧室內,尋找其他例子,「要是索倫知道他已經擁有某一本書,他就不再欲求這本書。當然他可以想要這本書的新版本,或者他希望永遠不會失去這本書,但是他的欲求不會只是這本書現在應該屬於他。」
索倫睜大雙眼。
「因此迪奧蒂瑪的論點是:為了欲求些什麼,我們有所欠缺雖是必要條件,但這還不足以當作解釋。」蘇格拉底彎起一條腿。「因為有許多東西,我們不擁有卻也不想要它們。好比說,我沒有任何紅鞋子,但是對我而言無關緊要,我感受不到對這樣一雙鞋的欲求。欲求的對象是我們眼下尚未擁有,而且這種欠缺讓我們感到不滿,少了它就覺得有所不足、不完整。那麼,什麼會讓我們滿足和完整?我們還能更進一步討論嗎?」他輕鬆地敞開雙臂,自行回答:「我們可以,但是我必須再多回顧一段。迪奧蒂瑪其實曾經和詩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爭執過一個問題。我們坐在一起,詩人剛對我們說完他所寫的故事後半段,你們知道,就是我們人類原本長得像顆圓球,宙斯為了懲罰人類的高傲,將人分成兩個半球,然後撒到世界各地的那個故事。
*
阿里斯托芬是西元前五世紀到四世紀初的知名希臘喜劇詩人,他同樣出現在柏拉圖的〈會飲篇〉當中,他在其中談論愛,說起被分開的球體這個神話,他們正尋找自己的另一半。但是這個神話並不能算在歷史上的阿里斯托芬頭上,而是出自柏拉圖筆下:他把這個故事塞進阿里斯托芬嘴裡,好讓他被迪奧蒂瑪反駁。
*
根據阿里斯托芬的說法,我們帶著身上的傷,變得脆弱而不安,只渴望一件事:和迷失的另一半重新合而為一。要是我們有幸和另一半重逢,這樣的喜悅難以估量。雖然我們再也不能以從前的方式合而為一,但我們擁抱對方,再也不想放開對方,宙斯最終想出一個緊急解決方式。當時祂感到一陣憐憫,於是讓我們殘缺的身體至少能有片刻連結,這短暫的交錯帶來稍微的緩解,一瞬間我們自覺完整,被治癒。阿里斯托芬認為愛就像對另一半的欲求,表現成追求重新合而為一。」
「就直說是性交嘛。」西格蒙德建議。
「好吧,性慾。所以,在阿里斯托芬看來,愛是理解人類的核心要素:對另一半的欲求主宰我們一切作為與無所作為。當然嘍,因為我們除了和另一半結合,沒有其他方式能讓我們完整,能治癒我們。所有欲求都是渴求失去的另一半。
說得通俗一點,他認為當我們奪回我們確實曾經擁有後來卻失去的東西,才會滿足和完整。他的故事說的是我們的另一半,但因為這只是個故事,他的意思當然並非全然是字面上的。我們期望些什麼就像渴求我們的另一半——能重建原始一體狀態的一些什麼,不管確切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這就是了!」西格蒙德喊著。「和母親合而為一……原始經歷。」
「嗯,我可不確定。」蘇格拉底猶豫,「迪奧蒂瑪反正有不同看法,她首先仔細傾聽阿里斯托芬的故事,她一直都這樣,然後反駁對方的說法:如果另一半沒有價值,甚至對你有害,你還會企求你失去的另一半回歸嗎?難道你不會反倒因擺脫對方而高興?阿里斯托芬躊躇地點頭,迪奧蒂瑪繼續滔滔不絕:同樣道理豈不適用於我們任何部分?——只有當它們既不是毫無價值也不是無害,而是對我們有益的時候,我們才想要得回或保有那些部分。請想像一下,你的手嚴重發炎,只有截肢才能防止你敗血症。你可能同意接受手術,雖然在手術之後,你很想再有一隻手,卻不想要原先發炎的那一隻,而是一隻新的、你可以使用的一隻手,因而對你有益的手。對上述的另一半也是同樣道理。我們樂得完整無缺,但是只在完好無缺帶給我們益處的時候。或者換句話說:如果不能引我們趨向好處,就不是真正的完整無缺,否則我們依舊覺得缺少什麼,欲求將不會被止息。
我完全信服迪奧蒂瑪的論點:當我們相信對我們有益,才會想要得回失去的部分。若非如此,我們會渴求新的、好的東西。因此我們是否曾經擁有某個東西,和欲求畢竟毫不相關,是否對我們有益才是重點。當然必須適合我們——但所謂適合是我們應該擁有它,理想上我們該擁有它。總結而言,欲求的客體是我們以為我們尚未擁有,此外我們認定為好的東西,對我們有益的東西。」
「那什麼對我們有益?」艾瑞絲問道。
「女士先生們:智慧,這就是答案。但是未經研究的答案不具多少意義,也沒有人在意。你們為何應該相信我?可惜研究需要經年累月。」蘇格拉底回答道。
「我們有時間!」伊曼紐表示,每個人都點頭。
艾瑞絲眨眨眼:「我們向你學的,蘇格拉底,把你的話當回事。看看我們,時間是我們的朋友。」
蘇格拉底轉身,「呼,迪奧蒂瑪這會兒真該親自現身。」他說這話像自言自語。然後他收拾心緒,他的表情變得專心一致:「讓我們先認定這是個重要的問題,因為我們認為好的一切並非就是好的,更別提只因我們認定是好的。我們可能自我欺騙,甚至是在對我們有益這方面。現在——何謂智慧?知的狀態,但不是隨意的某種『知』。智慧意味著對世界的究極原則了然於心,知道何以如是,如何至此,才可說理解。要是循著一連串的『為何』問題直到終點,末了就能掌握最終的因,所有一切都能回歸到這個因。我也稱這最後的因或說究極原則為「理型」(Idee/Idea),理型永恆且維持不變。如理型不是永恆且維持不變,就不會是究極原則。我的……迪奧蒂瑪的論點是,唯有我們的心靈理解理型,才對心靈有益。」
「我們的心靈?你指的是什麼?」西蒙詢問。
「我指的是我們想法、感受、欲求及精神活動所在。我們自身,也可以這麼說。理型令心靈真正成為心靈,只要心靈理解理型。然後心靈得以進行心靈要做的事情:思考,用『內在眼睛』觀看,但是也引導自身,獨立自主等等。」
「心靈沒有理型不也能這麼做?」西蒙繼續深究:「沒有理型或許不能正確思考,看得不正確,不能將自身引導往好的方向。但是錯誤思考和觀察依然是思考和觀察,可悲的自決依舊是自決。」
「確實,我應該更精準表達我的看法,我的意思是:所有思考、感受、觀察、自決的人,都想要正確思考、感受、觀察和自決。沒有人想犯錯,沒有人自願犯錯,不是嗎?」
奧古斯丁舉手,但蘇格拉底匆促地繼續說:「每個人都致力追求真相,畢竟都想做得好。如果只有運用理型才行得通,那麼如果心靈沒有理型,不管怎麼努力只會一直挫敗,心靈只是自身的悲傷陰影,無法開花綻放。」
「心靈無法展翅高飛——你曾經在另一個場合這樣表達,我一直都覺得這是個適當的描繪。」艾瑞絲加以補充。
「對,這個描述更貼切。如果我們想像心靈擁有翅膀,沒有理型,心靈就像雙翅再也無法鼓動的鳥兒。再也無法飛翔的鳥雖然還是隻鳥,但牠缺乏基本核心以發揮牠的根本要素,不能擁有幸福的飛鳥生活。一旦遠離理型,無法理解理型,心靈亦將如是;但是藉助理型,心靈能展開雙翼,自主走上心靈的道路。心靈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和理型相似:心靈安住自身之中,在核心之中維持不變。因此智慧是我們心靈所需一切。因為我們和心靈同一,我們的身體依附著我們,就像塊木頭綁在腿上,智慧是我們所需的一切。」
西格蒙德大聲清了清嗓子,在記事本裡寫了些什麼。
蘇格拉底串起他的論點:「回到主題。這對我們現在分析欲求的意義何在?我再重複一次:我們的欲求乃是針對我們自認欠缺,但是對我們有益的東西。然後我們又說,唯有智慧才真正對我們有益。現在我們可做出結論,至少每個正確的欲求都是智慧有所欠缺的表現,而且都是為了追求智慧。」
「也有錯誤的欲求嗎?」馬克斯皺起眉頭提問。
「當然,因為人會自欺,以為自己擁有什麼,或誤以為什麼對自己有益。雖然,當人弄錯自己擁有什麼——好比堅信沒有一雙紅鞋,就因為忘記自己把這樣一雙鞋塞在櫃子最下方的抽屜裡——那麼就某個意義層面而言的確少了一雙紅鞋,因為這樣就無法使用這雙鞋,不管怎麼穿或者何時想穿。沒有紅鞋的印象可說自證為真。即使如此,涉及善惡時如果弄錯,就會欲求智慧以外的東西,好比權力、名聲或金錢或是這一類的。就算擁有這些錯誤的東西,人當然依舊不滿足,依然遠離智慧。這些東西對我們並非真的有益,無法令我們滿足,欲求繼續飢餓地咕嚕叫,將我們推向任何可能的方向,直到終於朝向智慧為止。或者你怎麼看?你有不同的想法?」
「這不斷的反覆詰問實在煩人……」馬克斯喃喃地說,「而且說到底,這一切和愛有什麼關係?」他困惑地搖搖頭。
*
蘇格拉底特有的提問技巧相當有名,藉著這個技巧,他讓談話對象批判地檢視自己的信念,懷疑地放下這些信念,最後有所認知。這個技巧被稱為 Mäeutik,也就是助產術,蘇格拉底自視為談話對象精神子嗣的助產士。這個技術和他對愛的理論也相關,我們在下文還會讀到。
*
「馬上,我現在就回到愛這個主題!」蘇格拉底急忙說:「你們還記得:我們剛才說愛是種欲求。就和所有的欲求一樣,愛同樣朝向智慧。等等,等等!」他伸出雙手,房間裡正響起一片懷疑的低語。
「你們現在當然想著:戀愛的人欲求許多東西,但可不包括智慧!我們畢竟對另一個人感覺到愛——而且是我們非得不停想著對方,非要在對方身邊,關照對方,我們想為對方做任何事情的時候。乍看之下這一切跟追求智慧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得說你們沒錯,迪奧蒂瑪第一次對我闡述她對愛與智慧的看法時,我就和你們現在一樣驚訝。
但是她讓我冷靜下來:確實——她解釋——愛是特別執著另一個人,我們覺得對方很美,愛感覺起來灼熱又甜美,正如我們眾人周知。但是這種感覺背後藏著對智慧的欲求。對方的美讓我們趨向智慧的時候,可說我們就愛上某人。是的,我們愛上美,而且因為美啟發我們。美讓我們變得有創意,不僅身體上,而是特別在精神上。某種程度而言,美就像助產士,協助我們產下內在的精神子嗣。美就這樣協助我們踏上通往智慧的道路,現在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索,然後我們也就了解為何愛是上天的贈禮。你們準備好進行下一步了嗎?」蘇格拉底這時激動地問,他的聽眾們充滿期待地點頭。
愛情和智慧有什麼關係?
蘇格拉底說明愛欲、美與追求智慧之間的關聯
蘇格拉底輕輕來回扭動,搖臀擺頭。他的披巾從肩膀滑落。「愛是個開明的女乞丐,」他這般開場:「她慧黠,飄忽不定……」他沉思地靜默。然後他搖搖頭,解釋說:「我像個愛情專家站在你們面前,根本難以置信,不是嗎?我可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對吧?!」他抬起視線,輕笑著:「相當棘手的情況,而我難辭其咎。我知道,我知道,但就是發生了。我曾多次吹噓知道愛的本質,結果現在我必須發言和回答問題。」他按摩著手心,先是一手,然後換手。他的聽眾似乎有些不安,但是耐著性子,安靜坐在位子上。
「我希望,要是迪奧蒂瑪(Diotima)在這裡就好了……」他終於繼續說下去,從地上收拾起他的披巾。「或者我就忘了演講什麼的,直接向你們述說,我和她對愛的討論究竟談了些什麼,當我還年輕而你們還是學生的時候。」
「這個好!」發自艾瑞絲,但西格蒙德攪著咖啡,就像順口而出地說:「為什麼是迪奧蒂瑪?她根本不存在,她只是你虛構出來的!」
*
女祭司迪奧蒂瑪是柏拉圖〈會飲篇〉裡的一個角色。柏拉圖是蘇格拉底最知名的學生,在他的老師去世之後撰寫了哲學對話錄,蘇格拉底是其中的主角。在〈會飲篇〉中,蘇格拉底介紹迪奧蒂瑪是他的哲學老師,描述兩人對愛與欲的討論。柏拉圖對話錄當中的大部分角色都以歷史人物為雛形,但迪奧蒂瑪是真實存在或是完全虛構,一直都受到正反雙方的討論。
*
蘇格拉底又讓披巾滑落,似乎忿忿不平,「虛構?她絕對真實存在!沒有迪奧蒂瑪我絕不會開始哲學思辯——後來的你們也不會,坦白說。」他拍了下手,瞬間清醒過來:「一切都從她問我愛情是什麼開始。我結巴地說什麼心動和無眠的夜晚,但是說沒幾句她就打斷我的話,要求我整理思緒。我應該徹底思考而非天馬行空。幾回失敗的嘗試之後,她協助我跨出一大步。她認為,這麼看吧:愛上些什麼的人畢竟有所欲求,愛卻無所求——沒有這樣的愛,不是嗎?我們甚至可以說,愛就是一種欲求吧?這啟迪了我,直到今日依然啟迪著我。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奧古斯丁、西蒙和西格蒙德點點頭,但是其他人卻滿臉疑惑。馬克斯剛吸了口氣要說些什麼,伊曼紐卻搶在他前頭:「我認為這個說法至少非常容易理解。我們就暫時這麼認定,蘇格拉底,我們接受這個說法,那麼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我也這麼問迪奧蒂瑪,她立刻反問我:我們和我們欲求的對象處在何種關係之中?我嘆息著說,你的問題依舊這麼抽象。哎呀,她生氣地喊著,自己回答了問題:我們只會對我們認為自己還未擁有的東西產生欲求。要是你已經和贊西佩結婚,你也確實意識到這段婚姻,那麼你就不會再想著要和贊西佩結婚。要是……」蘇格拉底環顧室內,尋找其他例子,「要是索倫知道他已經擁有某一本書,他就不再欲求這本書。當然他可以想要這本書的新版本,或者他希望永遠不會失去這本書,但是他的欲求不會只是這本書現在應該屬於他。」
索倫睜大雙眼。
「因此迪奧蒂瑪的論點是:為了欲求些什麼,我們有所欠缺雖是必要條件,但這還不足以當作解釋。」蘇格拉底彎起一條腿。「因為有許多東西,我們不擁有卻也不想要它們。好比說,我沒有任何紅鞋子,但是對我而言無關緊要,我感受不到對這樣一雙鞋的欲求。欲求的對象是我們眼下尚未擁有,而且這種欠缺讓我們感到不滿,少了它就覺得有所不足、不完整。那麼,什麼會讓我們滿足和完整?我們還能更進一步討論嗎?」他輕鬆地敞開雙臂,自行回答:「我們可以,但是我必須再多回顧一段。迪奧蒂瑪其實曾經和詩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爭執過一個問題。我們坐在一起,詩人剛對我們說完他所寫的故事後半段,你們知道,就是我們人類原本長得像顆圓球,宙斯為了懲罰人類的高傲,將人分成兩個半球,然後撒到世界各地的那個故事。
*
阿里斯托芬是西元前五世紀到四世紀初的知名希臘喜劇詩人,他同樣出現在柏拉圖的〈會飲篇〉當中,他在其中談論愛,說起被分開的球體這個神話,他們正尋找自己的另一半。但是這個神話並不能算在歷史上的阿里斯托芬頭上,而是出自柏拉圖筆下:他把這個故事塞進阿里斯托芬嘴裡,好讓他被迪奧蒂瑪反駁。
*
根據阿里斯托芬的說法,我們帶著身上的傷,變得脆弱而不安,只渴望一件事:和迷失的另一半重新合而為一。要是我們有幸和另一半重逢,這樣的喜悅難以估量。雖然我們再也不能以從前的方式合而為一,但我們擁抱對方,再也不想放開對方,宙斯最終想出一個緊急解決方式。當時祂感到一陣憐憫,於是讓我們殘缺的身體至少能有片刻連結,這短暫的交錯帶來稍微的緩解,一瞬間我們自覺完整,被治癒。阿里斯托芬認為愛就像對另一半的欲求,表現成追求重新合而為一。」
「就直說是性交嘛。」西格蒙德建議。
「好吧,性慾。所以,在阿里斯托芬看來,愛是理解人類的核心要素:對另一半的欲求主宰我們一切作為與無所作為。當然嘍,因為我們除了和另一半結合,沒有其他方式能讓我們完整,能治癒我們。所有欲求都是渴求失去的另一半。
說得通俗一點,他認為當我們奪回我們確實曾經擁有後來卻失去的東西,才會滿足和完整。他的故事說的是我們的另一半,但因為這只是個故事,他的意思當然並非全然是字面上的。我們期望些什麼就像渴求我們的另一半——能重建原始一體狀態的一些什麼,不管確切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這就是了!」西格蒙德喊著。「和母親合而為一……原始經歷。」
「嗯,我可不確定。」蘇格拉底猶豫,「迪奧蒂瑪反正有不同看法,她首先仔細傾聽阿里斯托芬的故事,她一直都這樣,然後反駁對方的說法:如果另一半沒有價值,甚至對你有害,你還會企求你失去的另一半回歸嗎?難道你不會反倒因擺脫對方而高興?阿里斯托芬躊躇地點頭,迪奧蒂瑪繼續滔滔不絕:同樣道理豈不適用於我們任何部分?——只有當它們既不是毫無價值也不是無害,而是對我們有益的時候,我們才想要得回或保有那些部分。請想像一下,你的手嚴重發炎,只有截肢才能防止你敗血症。你可能同意接受手術,雖然在手術之後,你很想再有一隻手,卻不想要原先發炎的那一隻,而是一隻新的、你可以使用的一隻手,因而對你有益的手。對上述的另一半也是同樣道理。我們樂得完整無缺,但是只在完好無缺帶給我們益處的時候。或者換句話說:如果不能引我們趨向好處,就不是真正的完整無缺,否則我們依舊覺得缺少什麼,欲求將不會被止息。
我完全信服迪奧蒂瑪的論點:當我們相信對我們有益,才會想要得回失去的部分。若非如此,我們會渴求新的、好的東西。因此我們是否曾經擁有某個東西,和欲求畢竟毫不相關,是否對我們有益才是重點。當然必須適合我們——但所謂適合是我們應該擁有它,理想上我們該擁有它。總結而言,欲求的客體是我們以為我們尚未擁有,此外我們認定為好的東西,對我們有益的東西。」
「那什麼對我們有益?」艾瑞絲問道。
「女士先生們:智慧,這就是答案。但是未經研究的答案不具多少意義,也沒有人在意。你們為何應該相信我?可惜研究需要經年累月。」蘇格拉底回答道。
「我們有時間!」伊曼紐表示,每個人都點頭。
艾瑞絲眨眨眼:「我們向你學的,蘇格拉底,把你的話當回事。看看我們,時間是我們的朋友。」
蘇格拉底轉身,「呼,迪奧蒂瑪這會兒真該親自現身。」他說這話像自言自語。然後他收拾心緒,他的表情變得專心一致:「讓我們先認定這是個重要的問題,因為我們認為好的一切並非就是好的,更別提只因我們認定是好的。我們可能自我欺騙,甚至是在對我們有益這方面。現在——何謂智慧?知的狀態,但不是隨意的某種『知』。智慧意味著對世界的究極原則了然於心,知道何以如是,如何至此,才可說理解。要是循著一連串的『為何』問題直到終點,末了就能掌握最終的因,所有一切都能回歸到這個因。我也稱這最後的因或說究極原則為「理型」(Idee/Idea),理型永恆且維持不變。如理型不是永恆且維持不變,就不會是究極原則。我的……迪奧蒂瑪的論點是,唯有我們的心靈理解理型,才對心靈有益。」
「我們的心靈?你指的是什麼?」西蒙詢問。
「我指的是我們想法、感受、欲求及精神活動所在。我們自身,也可以這麼說。理型令心靈真正成為心靈,只要心靈理解理型。然後心靈得以進行心靈要做的事情:思考,用『內在眼睛』觀看,但是也引導自身,獨立自主等等。」
「心靈沒有理型不也能這麼做?」西蒙繼續深究:「沒有理型或許不能正確思考,看得不正確,不能將自身引導往好的方向。但是錯誤思考和觀察依然是思考和觀察,可悲的自決依舊是自決。」
「確實,我應該更精準表達我的看法,我的意思是:所有思考、感受、觀察、自決的人,都想要正確思考、感受、觀察和自決。沒有人想犯錯,沒有人自願犯錯,不是嗎?」
奧古斯丁舉手,但蘇格拉底匆促地繼續說:「每個人都致力追求真相,畢竟都想做得好。如果只有運用理型才行得通,那麼如果心靈沒有理型,不管怎麼努力只會一直挫敗,心靈只是自身的悲傷陰影,無法開花綻放。」
「心靈無法展翅高飛——你曾經在另一個場合這樣表達,我一直都覺得這是個適當的描繪。」艾瑞絲加以補充。
「對,這個描述更貼切。如果我們想像心靈擁有翅膀,沒有理型,心靈就像雙翅再也無法鼓動的鳥兒。再也無法飛翔的鳥雖然還是隻鳥,但牠缺乏基本核心以發揮牠的根本要素,不能擁有幸福的飛鳥生活。一旦遠離理型,無法理解理型,心靈亦將如是;但是藉助理型,心靈能展開雙翼,自主走上心靈的道路。心靈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和理型相似:心靈安住自身之中,在核心之中維持不變。因此智慧是我們心靈所需一切。因為我們和心靈同一,我們的身體依附著我們,就像塊木頭綁在腿上,智慧是我們所需的一切。」
西格蒙德大聲清了清嗓子,在記事本裡寫了些什麼。
蘇格拉底串起他的論點:「回到主題。這對我們現在分析欲求的意義何在?我再重複一次:我們的欲求乃是針對我們自認欠缺,但是對我們有益的東西。然後我們又說,唯有智慧才真正對我們有益。現在我們可做出結論,至少每個正確的欲求都是智慧有所欠缺的表現,而且都是為了追求智慧。」
「也有錯誤的欲求嗎?」馬克斯皺起眉頭提問。
「當然,因為人會自欺,以為自己擁有什麼,或誤以為什麼對自己有益。雖然,當人弄錯自己擁有什麼——好比堅信沒有一雙紅鞋,就因為忘記自己把這樣一雙鞋塞在櫃子最下方的抽屜裡——那麼就某個意義層面而言的確少了一雙紅鞋,因為這樣就無法使用這雙鞋,不管怎麼穿或者何時想穿。沒有紅鞋的印象可說自證為真。即使如此,涉及善惡時如果弄錯,就會欲求智慧以外的東西,好比權力、名聲或金錢或是這一類的。就算擁有這些錯誤的東西,人當然依舊不滿足,依然遠離智慧。這些東西對我們並非真的有益,無法令我們滿足,欲求繼續飢餓地咕嚕叫,將我們推向任何可能的方向,直到終於朝向智慧為止。或者你怎麼看?你有不同的想法?」
「這不斷的反覆詰問實在煩人……」馬克斯喃喃地說,「而且說到底,這一切和愛有什麼關係?」他困惑地搖搖頭。
*
蘇格拉底特有的提問技巧相當有名,藉著這個技巧,他讓談話對象批判地檢視自己的信念,懷疑地放下這些信念,最後有所認知。這個技巧被稱為 Mäeutik,也就是助產術,蘇格拉底自視為談話對象精神子嗣的助產士。這個技術和他對愛的理論也相關,我們在下文還會讀到。
*
「馬上,我現在就回到愛這個主題!」蘇格拉底急忙說:「你們還記得:我們剛才說愛是種欲求。就和所有的欲求一樣,愛同樣朝向智慧。等等,等等!」他伸出雙手,房間裡正響起一片懷疑的低語。
「你們現在當然想著:戀愛的人欲求許多東西,但可不包括智慧!我們畢竟對另一個人感覺到愛——而且是我們非得不停想著對方,非要在對方身邊,關照對方,我們想為對方做任何事情的時候。乍看之下這一切跟追求智慧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得說你們沒錯,迪奧蒂瑪第一次對我闡述她對愛與智慧的看法時,我就和你們現在一樣驚訝。
但是她讓我冷靜下來:確實——她解釋——愛是特別執著另一個人,我們覺得對方很美,愛感覺起來灼熱又甜美,正如我們眾人周知。但是這種感覺背後藏著對智慧的欲求。對方的美讓我們趨向智慧的時候,可說我們就愛上某人。是的,我們愛上美,而且因為美啟發我們。美讓我們變得有創意,不僅身體上,而是特別在精神上。某種程度而言,美就像助產士,協助我們產下內在的精神子嗣。美就這樣協助我們踏上通往智慧的道路,現在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索,然後我們也就了解為何愛是上天的贈禮。你們準備好進行下一步了嗎?」蘇格拉底這時激動地問,他的聽眾們充滿期待地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