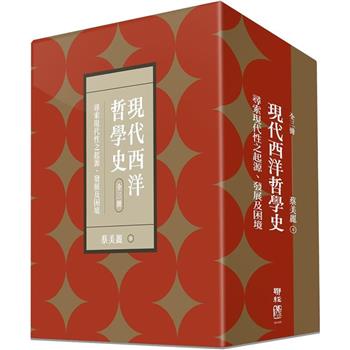導論──現代性及其困境
本書是一部現代西洋哲學史,始於文藝復興(西洋現代思想初萌新機),終於19世紀上半葉(黑格爾綜合前代頡頏對立、洶湧澎湃的哲思,架構出學養豐博、靈思玄妙的哲學系統)。1450年至1850年,悠悠四百年歲月,西方歷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主義、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等歷史轉捩點與文化轉型期。這部作品將繁簡不一,審視探索四百年中二、三十位大小哲學家、科學家如何面對時代危機和文化困境;又如何創發對宇宙、人類、歷史乃至文化全新解讀,構思前所未有的概念。
為什麼要撰寫這樣一部耗時長久,工作量極繁重又艱苦的作品呢?除卻遠古的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ërtius,3世紀)的《哲學史》(History of Philosophy),自從黑格爾於19世紀開端在柏林大學講授哲學史,百餘年來西方於哲學史的講授、寫作,從未間斷,巨冊與小本的著述汗牛充棟。其中威廉.溫德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的《哲學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霍夫丁(Harald Hø_ding, 1843-1931)的《現代西洋哲學史》(A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柯普斯登(Frederick Copleston, 1907- 1994)的《哲學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等作品,均被學界公認作名著。筆者生長在西方文化傳承之外的中國文化之中,窮畢生精力,理解一家一派言論已非易事,何苦自找麻煩撰寫這種博而不專的論著?更何況,西方人早已寫出被評為經典的作品。
筆者撰寫這部《現代西洋哲學史》的唯一理由是,意圖在西方四百年的哲學思想發展中,搜尋塑造西方現代文化的基本概念,審視這些概念的轉化、發展過程,並且探索潛存在這些概念之中,西方現代文化危殆的根源。綜觀其他哲學史家,似乎未曾有人做過這類嘗試。至於筆者又為什麼對西方文化現代性議題產生如此大的興趣?這問題也許必須從兩個層面加以回答。其一是筆者託身其中的特殊時空交匯點,其二是20世紀末期西方哲學世界爆發的一場熱烈的辯爭。
身為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人,目睹一個古舊文明,曾經華美如此,卻不由自主又無可奈何地轉化為西方現代文化。尾隨百年來的中國學人,筆者忍禁不住要懷疑,什麼是西方現代文化的本質?中國文化是否已然確切地現代化?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攫獲了什麼,又損失了什麼?1960、1970年代於西方,法國冒現了一批被歸類作「後現代」的哲學家,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 2004)、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等,承襲了19世紀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20世紀中期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對西方現代文化的批判,提出一些被標示作「後現代」的哲學理念。1980年代以還,西方哲學世界之中,觸動了一場「現代」對「後現代」的論戰。不論倡議後現代文化的學者如李歐塔、羅逖(Richard Rorty, 1931-2007)、瓦帝莫(Gianni Vattimo, 1936-),維護現代文化的哲人如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查理士.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皮平(Robert B. Pippin, 1948-),抑或是意圖在前現代文化中擷取靈思,補充現代文化之不足的學人如麥金泰(Alasdair Maclntyre, 1929-)、貝爾(Daniel Bell, 1919-2011)。不論批判文化現代性,維護文化現代性,西方文化現代性,終歸是他們思索、分析的議題。他們的作品,實際上增進了筆者研探文化現代性的興趣。筆者總覺得,對西方文化現代性築基其上的哲學理念產生比較詳盡、全方位性了解,則一方面可以更精準地評估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成、敗、得、失之所在,另方面,亦可以在對西方現代文化而言,極為異質的中國文化之中,淘挖補足現代西方文化欠缺的源泉。
下面概約綜談一下西方現代文化的特質及其衍生之困境。也許,先行擁具一個簡要的全觀,瀏覽下面各章各節時,比較容易浮現一個檢索的圖譜。
本書是一部現代西洋哲學史,始於文藝復興(西洋現代思想初萌新機),終於19世紀上半葉(黑格爾綜合前代頡頏對立、洶湧澎湃的哲思,架構出學養豐博、靈思玄妙的哲學系統)。1450年至1850年,悠悠四百年歲月,西方歷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主義、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等歷史轉捩點與文化轉型期。這部作品將繁簡不一,審視探索四百年中二、三十位大小哲學家、科學家如何面對時代危機和文化困境;又如何創發對宇宙、人類、歷史乃至文化全新解讀,構思前所未有的概念。
為什麼要撰寫這樣一部耗時長久,工作量極繁重又艱苦的作品呢?除卻遠古的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ërtius,3世紀)的《哲學史》(History of Philosophy),自從黑格爾於19世紀開端在柏林大學講授哲學史,百餘年來西方於哲學史的講授、寫作,從未間斷,巨冊與小本的著述汗牛充棟。其中威廉.溫德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的《哲學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霍夫丁(Harald Hø_ding, 1843-1931)的《現代西洋哲學史》(A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柯普斯登(Frederick Copleston, 1907- 1994)的《哲學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等作品,均被學界公認作名著。筆者生長在西方文化傳承之外的中國文化之中,窮畢生精力,理解一家一派言論已非易事,何苦自找麻煩撰寫這種博而不專的論著?更何況,西方人早已寫出被評為經典的作品。
筆者撰寫這部《現代西洋哲學史》的唯一理由是,意圖在西方四百年的哲學思想發展中,搜尋塑造西方現代文化的基本概念,審視這些概念的轉化、發展過程,並且探索潛存在這些概念之中,西方現代文化危殆的根源。綜觀其他哲學史家,似乎未曾有人做過這類嘗試。至於筆者又為什麼對西方文化現代性議題產生如此大的興趣?這問題也許必須從兩個層面加以回答。其一是筆者託身其中的特殊時空交匯點,其二是20世紀末期西方哲學世界爆發的一場熱烈的辯爭。
身為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人,目睹一個古舊文明,曾經華美如此,卻不由自主又無可奈何地轉化為西方現代文化。尾隨百年來的中國學人,筆者忍禁不住要懷疑,什麼是西方現代文化的本質?中國文化是否已然確切地現代化?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攫獲了什麼,又損失了什麼?1960、1970年代於西方,法國冒現了一批被歸類作「後現代」的哲學家,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 2004)、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等,承襲了19世紀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20世紀中期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對西方現代文化的批判,提出一些被標示作「後現代」的哲學理念。1980年代以還,西方哲學世界之中,觸動了一場「現代」對「後現代」的論戰。不論倡議後現代文化的學者如李歐塔、羅逖(Richard Rorty, 1931-2007)、瓦帝莫(Gianni Vattimo, 1936-),維護現代文化的哲人如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查理士.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皮平(Robert B. Pippin, 1948-),抑或是意圖在前現代文化中擷取靈思,補充現代文化之不足的學人如麥金泰(Alasdair Maclntyre, 1929-)、貝爾(Daniel Bell, 1919-2011)。不論批判文化現代性,維護文化現代性,西方文化現代性,終歸是他們思索、分析的議題。他們的作品,實際上增進了筆者研探文化現代性的興趣。筆者總覺得,對西方文化現代性築基其上的哲學理念產生比較詳盡、全方位性了解,則一方面可以更精準地評估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成、敗、得、失之所在,另方面,亦可以在對西方現代文化而言,極為異質的中國文化之中,淘挖補足現代西方文化欠缺的源泉。
下面概約綜談一下西方現代文化的特質及其衍生之困境。也許,先行擁具一個簡要的全觀,瀏覽下面各章各節時,比較容易浮現一個檢索的圖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