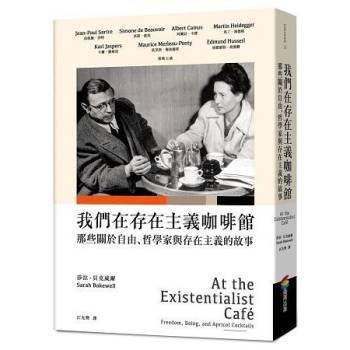第一幕 先生,糟透了,存在主義!
三人正啜飲著杏子雞尾酒,許多人徹夜談論自由,更多人一生從此改變……這就是存在主義嗎?
有人說,與其說存在主義是哲學,倒不如說它是一種心境。追根究柢,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苦悶的小說家,更遠可追溯到被無聲無息的無盡空間嚇得要死的巴斯卡(Blaise Pascal),更遠嗎?還有埋首省思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聖經.舊約》中大嘆「虛空」的〈傳道書〉(訓道篇)作者,甚至是敢於質疑上帝在他身上搗鬼但最終臣服於上帝威嚴的約伯;總之,可追溯到對所有事滿懷怨憤、心存叛逆或備感疏離的任何人。
但我們也可以換一個方向,把現代存在主義的誕生定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之交的一個時刻。當時,三個年輕哲學家坐在巴黎蒙帕納斯路(rue du Montparnasse)的煤氣燈(Bec de Gaz)酒吧,聊著最新的軼聞,喝著酒吧特製的杏子雞尾酒。
三人中後來最詳細講述這個故事的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她當時年約二十五歲,沉溺於用她那雙優雅而深邃的眼睛察看世界。陪伴在側的是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她這位二十七歲的男朋友肩膀渾圓,嘴唇像石斑魚般下斂,膚色斑駁,有一對招風耳。還有,他雙眼外瞥,因為右眼近乎失明,目光總是散漫地向外掃射,結果就是嚴重的外斜視,視線無法協調。不明就裡的人總覺得,他跟你說話時像無法集中精神;可是如果你盡量專注於他的左眼,就一定會發現那眼神正帶著溫厚的睿智凝視著你—眼睛的主人對你告訴他的所有事物都興味盎然。
沙特和波娃這刻肯定興致勃勃,因為同桌的第三個人給他們捎來了新消息。他是沙特溫文爾雅的老同學雷蒙.阿宏(Raymond Aron),他和沙特都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跟同桌的另外兩人一樣,阿宏是來巴黎過寒假的。不過沙特和波娃都在法國國內教書—沙特在勒阿弗爾(Le Havre),波娃在盧昂(Rouen),阿宏卻在德國柏林念書。他告訴兩位朋友,在彼邦發現了一種哲學,名字婀娜多姿,叫「現象學」(phenomenology)。好一個長長的詞語,可是不論法文還是英文,都優雅地勻稱,像詩歌音步組成的抑揚三步格。
阿宏大概這樣說:傳統哲學家往往從抽象的原則或理論起步,德國現象學家卻一步跨出去面對每一刻所經驗的人生。他們不再理會大部分自柏拉圖(Plato)以來讓哲學忙個不停的謎題:譬如世間事物是否真實,或如何能對所有事都獲得肯定無疑的認知。取而代之,他們指出,一旦哲學家從這種謎題提出疑問,就已經墜入一個充滿著事物的世界;起碼可說,充滿著事物的「形相」,或稱為「現象」(phenomena,來自希臘文,意謂「呈現形相之物」)。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聚焦於與現象的接觸,而對其他置之不理?那些舊式謎題也不是就此遭拋諸腦後,而是不妨說「把它們放進括弧」,那麼哲學家就可以處理更腳踏實地的事了。
現象學主要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振臂高呼:「回歸事物本身!」這表示:不要浪費時間在事物堆積起來的詮譯,尤其不要花時間質疑事物是否真實。就看呈現在你眼前的「這東西」,不管它是不是實在的,只管盡可能確切描述它。另一位現象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又添加了不一樣的解讀。他說,世世代代以來,哲學家把時間浪費在次要問題上,而忘記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存在(Being)的問題。我們說某事物「存在」,說自己「存在」,是什麼意思?他認為,除非你懂得問這個問題,否則將始終不得要領。同樣,他建議採用現象學方法:拋開智性糾葛,把注意力集中在事物本身,讓它們自行顯現在你眼前。
「你瞧,我的小伙伴(mon petit camarade,這是他們念書時阿宏對沙特的暱稱),」阿宏說:」如果你是個現象學家,就可以從這杯雞尾酒大談哲學!」
在波娃筆下,沙特聽了突然一臉慘白。更戲劇化的是,她字裡行間暗示自己和沙特從沒聽說過現象學。事實上,兩人曾試著讀一點兒海德格。沙特早年一篇文章一九三一年在《比弗》(Bifur)雜誌發表時,雜誌同時刊登了海德格〈何謂形上學〉(What Is Metaphysics?)的譯文。但波娃談到這篇演講稿時說:」我們讀來一竅不通,看不到什麼感興趣的。「可是在這一刻他們看到了:它是一種哲學方法,把哲學跟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繫起來。
他們對這個新的開始期待已久。在中學和大學念書時,沙特、波娃和阿宏都啃過法國學生要應付的艱澀哲學課程,重頭戲要不是認識論的問題,就是對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沒完沒了的詮釋再詮釋。認識論的問題一個引向另一個,像萬花筒的影像反來覆去,總是回到原來的起點:我相信我認知某事,但我怎麼能夠認知,我認知所認知的事?對這三位學生來說,這是吃力而徒勞的苦差事,儘管他們考試都考得很好,卻始終不能滿足,沙特尤其如此。他畢業後曾暗示,正孕育一種「破舊立新」的哲學,但究竟那是什麼模樣,卻總說不清,因為他根本拿不出什麼主意來。他想來想去,還是停留在徒具叛逆精神的階段。如今似乎有人捷足先登。如果沙特對阿宏捎來的現象學新知一臉茫然,也許就是興奮莫名的同時,也在大感氣惱。
不管怎樣,沙特永遠忘不了那一刻,四十年後他在一次訪問說:「我可以告訴你,我被一舉擊倒了。」真正的哲學終於出現了。據波娃所說,沙特衝到最近的書店,大聲嚷著說:「把這裡每一本有關現象學的書拿給我,快!」他們拿得出來的,就是胡塞爾的學生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寫薄薄一冊的《胡塞爾現象學的直觀論》(La 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那是一本尚未裁開來的毛邊書,沙特來不及找裁紙刀,就徒手把書頁撕開,一邊往街上走一邊讀了起來。他就像初次與喬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翻成英文的《荷馬史詩》邂逅的濟慈一樣:
然後我恍如觀星者,
目睹新星潛入視野;
又似勇者柯特茲(Cortez)銳眼掃射 ,
瞥見了太平洋。啊!君不見—
一行人面面相覷,相視無言,
呆立達連(Darien)山巔。
沙特是大而化之的人,也不甘於沈默,但現在的他肯定滿腹疑團。阿宏看他一腔熱情,便建議他這個秋季到柏林去,在法國文化中心研習,就像阿宏一樣。沙特可以學習德語,讀現象學家的原文,就近吸收他們的哲學能量。
當時納粹勢力竄起,一九三三年不是前去德國的理想時機。但那是沙特改變人生方向的好時機。他對教學感到厭倦,對大學裡所學的感到厭倦,對於自兒時以來一直期望自己成為天才作家而迄無成果感到厭倦。他知道,要寫他想寫的—不管是小說、散文,還是其他什麼,他首先要踏上冒險之旅。他屢有奇想: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跟碼頭工人一起幹活,到希臘阿索斯山(Mount Athos)跟修士一起冥想,去印度跟賤民一起過躲躲藏藏的生活,又或去紐芬蘭(Newfoundland)海岸跟漁夫與風暴搏鬥。可是如今,光是不用在勒阿弗爾教導學童就夠冒險了。
他安排好暑假過後去柏林研習。當他年底回國,將帶回來揉合多種元素的新哲學:德國現象學方法,摻雜了早些時候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等人的概念,再在起點上以他自己的文藝觸覺加入獨特的法式風味。他以更令人興奮、更個人化的方式把現象學應用到一般生活上,是現象學創始人從沒想像過的,他因此創造了一種新的哲學—現代存在主義,風靡國際,卻始終帶著巴黎風情。
沙特這項發明的精采之處,在於他真的把現象學變成了杏子雞尾酒的哲學,也是侍酒服務生的哲學,又是塵世浮生種種形相與種種感覺的哲學:不管那是期待、倦怠、憂慮、興奮,還是山坡上的漫步、情人間的激情、怨偶間的怨懟、巴黎的花園、勒阿弗爾寒冷秋日的海岸,甚至沙發襯墊太厚太軟、美人春睡雙乳盪漾、拳擊比賽刺激緊張,又或一部電影、一首爵士歌曲、一眼瞥見陌路人相逢街燈下。他的哲學可以來自一刻的眩暈、一瞬的偷窺,還有羞恥感、虐待狂、革命、音樂和性愛—很多很多的性愛。
沙特之前,哲學家動筆寫的是小心翼翼的命題和論辯,沙特動筆寫起來卻像個小說家。毫不意外,他就是個小說家。在他的長篇或短篇小說、戲劇和哲學論文中,他描寫世間的感官知覺,以及人生的結構和意境。尤其重要的是,他筆下有一個重大課題:自由是怎麼一回事?
對他來說,自由是所有人類經驗的核心,把人類跟其他萬物區別開來。其他物體只是呆著不動,靜待外力推動或拉動。他又相信,即使人類以外的動物,大部分也只是順著本能或所屬物種的行為特性而動起來。人類卻完全沒有預定的天性,每個人透過選擇做些什麼,而塑造自己的本性。當然個人可能受到生理,或是文化和個人背景等因素影響,但所有這些元素湊合起來也不會成為塑造個人的完整藍圖。我總是比自我先走一步,邊走邊把自我塑造出來。
沙特用一個只包含三個詞語的口號,把這項原則概括起來,在他看來足以界定存在主義:「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這道方程式以簡潔見稱,卻失諸難以理解。但粗略而言它所指的是,當我發覺自己墜入塵世,我便隨之把自己的定義(或說本性、本質)創造出來,這在其他物體或非人類生命個體身上,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你也許認為你已經用一些標籤把我界定了,但你弄錯了,我總是創作中的未完成作品。我不斷透過行動創造自我,在沙特看來,這對於人生在世的境況具有根本意義,簡直就是「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從最初有知覺的一刻,到死亡把知覺抹掉的一刻。我,就等於自身自由的體現:兩者完全相等。
這是個令人著迷的概念,待沙特賦予它完整定義之後,就馬上成為哲學界的明星,當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一年。他成為眾人所歡迎而追隨求教的導師,他接受訪問,在鏡頭下亮相,受委託撰寫論文和序文,獲邀加入委員會,在電台廣播。他經常受邀談及非他專精的課題,他也從來總不會拙於應對。波娃也撰寫小說、廣播稿、日記、散文和哲學論文,都包含統一的哲學觀點,跟沙特的觀點相近,不過那主要是她自行發展出來的哲學,重點也有所不同。兩人一起學術演講,一起推介新書,有時在討論會中置身高高在上的坐位,儼如登上王座,與他們的存在主義天王天后身分匹配。
沙特首次察覺到他成為了名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天他在巴黎的中央會堂(Salle des Centraux)為時代俱樂部(Club Maintenant)舉行公開演講會。他和主辦機構都低估了他的演講能吸引多少人慕名到場。售票處陷入暴亂;很多人無法走近購票,乾脆無票硬闖進場。在擠擠撞撞中椅子給撞毀了,有幾個聽眾因為場內異常酷熱而昏倒了。《時代雜誌》(Time)一幀照片配上了這樣的圖說:「哲學家沙特。女士們如痴如醉。」
這次演講十分成功。身高才五呎左右的沙特,在人群中肯定幾乎被淹沒,但他精采萬分地闡述了他的哲學概念,後來把演講內容改寫成書—《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不論演講還是這本書,高潮都在一起軼事,對當時的聽眾來說那是耳熟能詳的事,因為納粹的占領及其後的解放記憶猶新。這個故事也足以概括沙特哲學發聾振聵的價值和吸引力。
沙特說,法國被納粹占領期間, 某天一位昔日的學生前來求教。這個年輕人的兄弟在一九四○年法國投降前的一次戰役中喪生,他的父親拋妻棄子變成通敵者,母親只能仰賴身邊僅存的這個兒子陪伴支持。但這個年輕人卻渴望從邊境偷渡到西班牙再前往英國,加入流亡自由法國的軍隊對抗納粹,展開血戰,為兄弟復仇,否定父親的所作所為,為光復國家出力。問題是,母親會獨自處身險境,能否找到食物果腹也是個問題,德國占領者也可能給她找麻煩。因此,這個年輕人的正確作法是陪在母親身邊嗎—這樣顯然有人可以受惠,但只限母親一人,抑或他應該豁出去搏一搏,為眾人的福祉參軍?
今天的哲學家依然為瞭解答這類倫理難題而糾纏不休。沙特這個謎題,跟有名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異曲同工。在這個思想實驗中,假想你看到一列失控的火車或電車沿著軌道猛衝,而前面不遠處,有五個人被縛在軌道上。如果你什麼也不做,那五個人就會喪命,但你發現可以撥動一根控制桿使列車轉到鐵路側線。可是如果這樣做,一個人勢必喪生:他被縛在另一條軌道的位置,如果不是因為你的行動,或可逃過一劫。那麼你打算讓這個人犧牲,還是撒手不管讓五個人死亡?(有另一個版本稱為「胖子難題」:你可以從附近一座橋上把一個大胖子拋到軌道上令火車出軌。這個難題更直逼內心,更難抉擇,因為你要直接出手造成那人喪生。)沙特那位學生的抉擇可看作「電車難題」,但更為複雜,因為他不確定前往英國實際上能否幫到誰,也不確定離開母親是否會令她遭受嚴重打擊。
沙特不打算採取哲學家的傳統作法,透過倫理算計尋求出路,更遑論當個所謂「電車難題專家」。他引導聽眾更個人化地思考問題。面對這個抉擇是怎麼一回事?一個心亂如麻的年輕人實際上該怎麼處理這個何去何從的抉擇?誰幫得上忙,怎樣幫忙?對於最後一個問題,沙特的解答,是從誰無法幫得上忙著手。
那位學生來找沙特之前,曾想過向傳統道德權威求助。他曾考慮找神職人員—可是這類人有時本身就是通敵者,而且不用說也可知道,基督教的倫理只能告訴他愛他的鄰人,善待他人,卻不具體指明他人是誰:他的母親還是他的國家。另外,他考慮去找念書時念過的那些哲學家—他們被奉為智慧的泉源。但哲學家太抽象,對自己這個處境恐怕沒有什麼好說的。然後,他嘗試傾聽自己心裡的聲音,看看能不能從內心深處找到答案。然而卻行不通,他只聽到喧鬧的聲音各有主張(比如說:我一定要留下,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做勇敢的事,我一定要做個好兒子,我要付諸行動,但我心裡害怕,我不想送死,我要出走。我要做一個比父親好的人!我真的愛國嗎?還是假裝愛國而已?)。面對這一堆雜音,他甚至不能信賴自己。最後,這位年輕人只能求助於昔日的老師沙特,知道他起碼不會給自己一個老生常談的答案。
三人正啜飲著杏子雞尾酒,許多人徹夜談論自由,更多人一生從此改變……這就是存在主義嗎?
有人說,與其說存在主義是哲學,倒不如說它是一種心境。追根究柢,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苦悶的小說家,更遠可追溯到被無聲無息的無盡空間嚇得要死的巴斯卡(Blaise Pascal),更遠嗎?還有埋首省思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聖經.舊約》中大嘆「虛空」的〈傳道書〉(訓道篇)作者,甚至是敢於質疑上帝在他身上搗鬼但最終臣服於上帝威嚴的約伯;總之,可追溯到對所有事滿懷怨憤、心存叛逆或備感疏離的任何人。
但我們也可以換一個方向,把現代存在主義的誕生定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之交的一個時刻。當時,三個年輕哲學家坐在巴黎蒙帕納斯路(rue du Montparnasse)的煤氣燈(Bec de Gaz)酒吧,聊著最新的軼聞,喝著酒吧特製的杏子雞尾酒。
三人中後來最詳細講述這個故事的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她當時年約二十五歲,沉溺於用她那雙優雅而深邃的眼睛察看世界。陪伴在側的是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她這位二十七歲的男朋友肩膀渾圓,嘴唇像石斑魚般下斂,膚色斑駁,有一對招風耳。還有,他雙眼外瞥,因為右眼近乎失明,目光總是散漫地向外掃射,結果就是嚴重的外斜視,視線無法協調。不明就裡的人總覺得,他跟你說話時像無法集中精神;可是如果你盡量專注於他的左眼,就一定會發現那眼神正帶著溫厚的睿智凝視著你—眼睛的主人對你告訴他的所有事物都興味盎然。
沙特和波娃這刻肯定興致勃勃,因為同桌的第三個人給他們捎來了新消息。他是沙特溫文爾雅的老同學雷蒙.阿宏(Raymond Aron),他和沙特都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跟同桌的另外兩人一樣,阿宏是來巴黎過寒假的。不過沙特和波娃都在法國國內教書—沙特在勒阿弗爾(Le Havre),波娃在盧昂(Rouen),阿宏卻在德國柏林念書。他告訴兩位朋友,在彼邦發現了一種哲學,名字婀娜多姿,叫「現象學」(phenomenology)。好一個長長的詞語,可是不論法文還是英文,都優雅地勻稱,像詩歌音步組成的抑揚三步格。
阿宏大概這樣說:傳統哲學家往往從抽象的原則或理論起步,德國現象學家卻一步跨出去面對每一刻所經驗的人生。他們不再理會大部分自柏拉圖(Plato)以來讓哲學忙個不停的謎題:譬如世間事物是否真實,或如何能對所有事都獲得肯定無疑的認知。取而代之,他們指出,一旦哲學家從這種謎題提出疑問,就已經墜入一個充滿著事物的世界;起碼可說,充滿著事物的「形相」,或稱為「現象」(phenomena,來自希臘文,意謂「呈現形相之物」)。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聚焦於與現象的接觸,而對其他置之不理?那些舊式謎題也不是就此遭拋諸腦後,而是不妨說「把它們放進括弧」,那麼哲學家就可以處理更腳踏實地的事了。
現象學主要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振臂高呼:「回歸事物本身!」這表示:不要浪費時間在事物堆積起來的詮譯,尤其不要花時間質疑事物是否真實。就看呈現在你眼前的「這東西」,不管它是不是實在的,只管盡可能確切描述它。另一位現象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又添加了不一樣的解讀。他說,世世代代以來,哲學家把時間浪費在次要問題上,而忘記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存在(Being)的問題。我們說某事物「存在」,說自己「存在」,是什麼意思?他認為,除非你懂得問這個問題,否則將始終不得要領。同樣,他建議採用現象學方法:拋開智性糾葛,把注意力集中在事物本身,讓它們自行顯現在你眼前。
「你瞧,我的小伙伴(mon petit camarade,這是他們念書時阿宏對沙特的暱稱),」阿宏說:」如果你是個現象學家,就可以從這杯雞尾酒大談哲學!」
在波娃筆下,沙特聽了突然一臉慘白。更戲劇化的是,她字裡行間暗示自己和沙特從沒聽說過現象學。事實上,兩人曾試著讀一點兒海德格。沙特早年一篇文章一九三一年在《比弗》(Bifur)雜誌發表時,雜誌同時刊登了海德格〈何謂形上學〉(What Is Metaphysics?)的譯文。但波娃談到這篇演講稿時說:」我們讀來一竅不通,看不到什麼感興趣的。「可是在這一刻他們看到了:它是一種哲學方法,把哲學跟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繫起來。
他們對這個新的開始期待已久。在中學和大學念書時,沙特、波娃和阿宏都啃過法國學生要應付的艱澀哲學課程,重頭戲要不是認識論的問題,就是對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沒完沒了的詮釋再詮釋。認識論的問題一個引向另一個,像萬花筒的影像反來覆去,總是回到原來的起點:我相信我認知某事,但我怎麼能夠認知,我認知所認知的事?對這三位學生來說,這是吃力而徒勞的苦差事,儘管他們考試都考得很好,卻始終不能滿足,沙特尤其如此。他畢業後曾暗示,正孕育一種「破舊立新」的哲學,但究竟那是什麼模樣,卻總說不清,因為他根本拿不出什麼主意來。他想來想去,還是停留在徒具叛逆精神的階段。如今似乎有人捷足先登。如果沙特對阿宏捎來的現象學新知一臉茫然,也許就是興奮莫名的同時,也在大感氣惱。
不管怎樣,沙特永遠忘不了那一刻,四十年後他在一次訪問說:「我可以告訴你,我被一舉擊倒了。」真正的哲學終於出現了。據波娃所說,沙特衝到最近的書店,大聲嚷著說:「把這裡每一本有關現象學的書拿給我,快!」他們拿得出來的,就是胡塞爾的學生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寫薄薄一冊的《胡塞爾現象學的直觀論》(La 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那是一本尚未裁開來的毛邊書,沙特來不及找裁紙刀,就徒手把書頁撕開,一邊往街上走一邊讀了起來。他就像初次與喬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翻成英文的《荷馬史詩》邂逅的濟慈一樣:
然後我恍如觀星者,
目睹新星潛入視野;
又似勇者柯特茲(Cortez)銳眼掃射 ,
瞥見了太平洋。啊!君不見—
一行人面面相覷,相視無言,
呆立達連(Darien)山巔。
沙特是大而化之的人,也不甘於沈默,但現在的他肯定滿腹疑團。阿宏看他一腔熱情,便建議他這個秋季到柏林去,在法國文化中心研習,就像阿宏一樣。沙特可以學習德語,讀現象學家的原文,就近吸收他們的哲學能量。
當時納粹勢力竄起,一九三三年不是前去德國的理想時機。但那是沙特改變人生方向的好時機。他對教學感到厭倦,對大學裡所學的感到厭倦,對於自兒時以來一直期望自己成為天才作家而迄無成果感到厭倦。他知道,要寫他想寫的—不管是小說、散文,還是其他什麼,他首先要踏上冒險之旅。他屢有奇想: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跟碼頭工人一起幹活,到希臘阿索斯山(Mount Athos)跟修士一起冥想,去印度跟賤民一起過躲躲藏藏的生活,又或去紐芬蘭(Newfoundland)海岸跟漁夫與風暴搏鬥。可是如今,光是不用在勒阿弗爾教導學童就夠冒險了。
他安排好暑假過後去柏林研習。當他年底回國,將帶回來揉合多種元素的新哲學:德國現象學方法,摻雜了早些時候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等人的概念,再在起點上以他自己的文藝觸覺加入獨特的法式風味。他以更令人興奮、更個人化的方式把現象學應用到一般生活上,是現象學創始人從沒想像過的,他因此創造了一種新的哲學—現代存在主義,風靡國際,卻始終帶著巴黎風情。
沙特這項發明的精采之處,在於他真的把現象學變成了杏子雞尾酒的哲學,也是侍酒服務生的哲學,又是塵世浮生種種形相與種種感覺的哲學:不管那是期待、倦怠、憂慮、興奮,還是山坡上的漫步、情人間的激情、怨偶間的怨懟、巴黎的花園、勒阿弗爾寒冷秋日的海岸,甚至沙發襯墊太厚太軟、美人春睡雙乳盪漾、拳擊比賽刺激緊張,又或一部電影、一首爵士歌曲、一眼瞥見陌路人相逢街燈下。他的哲學可以來自一刻的眩暈、一瞬的偷窺,還有羞恥感、虐待狂、革命、音樂和性愛—很多很多的性愛。
沙特之前,哲學家動筆寫的是小心翼翼的命題和論辯,沙特動筆寫起來卻像個小說家。毫不意外,他就是個小說家。在他的長篇或短篇小說、戲劇和哲學論文中,他描寫世間的感官知覺,以及人生的結構和意境。尤其重要的是,他筆下有一個重大課題:自由是怎麼一回事?
對他來說,自由是所有人類經驗的核心,把人類跟其他萬物區別開來。其他物體只是呆著不動,靜待外力推動或拉動。他又相信,即使人類以外的動物,大部分也只是順著本能或所屬物種的行為特性而動起來。人類卻完全沒有預定的天性,每個人透過選擇做些什麼,而塑造自己的本性。當然個人可能受到生理,或是文化和個人背景等因素影響,但所有這些元素湊合起來也不會成為塑造個人的完整藍圖。我總是比自我先走一步,邊走邊把自我塑造出來。
沙特用一個只包含三個詞語的口號,把這項原則概括起來,在他看來足以界定存在主義:「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這道方程式以簡潔見稱,卻失諸難以理解。但粗略而言它所指的是,當我發覺自己墜入塵世,我便隨之把自己的定義(或說本性、本質)創造出來,這在其他物體或非人類生命個體身上,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你也許認為你已經用一些標籤把我界定了,但你弄錯了,我總是創作中的未完成作品。我不斷透過行動創造自我,在沙特看來,這對於人生在世的境況具有根本意義,簡直就是「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從最初有知覺的一刻,到死亡把知覺抹掉的一刻。我,就等於自身自由的體現:兩者完全相等。
這是個令人著迷的概念,待沙特賦予它完整定義之後,就馬上成為哲學界的明星,當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一年。他成為眾人所歡迎而追隨求教的導師,他接受訪問,在鏡頭下亮相,受委託撰寫論文和序文,獲邀加入委員會,在電台廣播。他經常受邀談及非他專精的課題,他也從來總不會拙於應對。波娃也撰寫小說、廣播稿、日記、散文和哲學論文,都包含統一的哲學觀點,跟沙特的觀點相近,不過那主要是她自行發展出來的哲學,重點也有所不同。兩人一起學術演講,一起推介新書,有時在討論會中置身高高在上的坐位,儼如登上王座,與他們的存在主義天王天后身分匹配。
沙特首次察覺到他成為了名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天他在巴黎的中央會堂(Salle des Centraux)為時代俱樂部(Club Maintenant)舉行公開演講會。他和主辦機構都低估了他的演講能吸引多少人慕名到場。售票處陷入暴亂;很多人無法走近購票,乾脆無票硬闖進場。在擠擠撞撞中椅子給撞毀了,有幾個聽眾因為場內異常酷熱而昏倒了。《時代雜誌》(Time)一幀照片配上了這樣的圖說:「哲學家沙特。女士們如痴如醉。」
這次演講十分成功。身高才五呎左右的沙特,在人群中肯定幾乎被淹沒,但他精采萬分地闡述了他的哲學概念,後來把演講內容改寫成書—《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不論演講還是這本書,高潮都在一起軼事,對當時的聽眾來說那是耳熟能詳的事,因為納粹的占領及其後的解放記憶猶新。這個故事也足以概括沙特哲學發聾振聵的價值和吸引力。
沙特說,法國被納粹占領期間, 某天一位昔日的學生前來求教。這個年輕人的兄弟在一九四○年法國投降前的一次戰役中喪生,他的父親拋妻棄子變成通敵者,母親只能仰賴身邊僅存的這個兒子陪伴支持。但這個年輕人卻渴望從邊境偷渡到西班牙再前往英國,加入流亡自由法國的軍隊對抗納粹,展開血戰,為兄弟復仇,否定父親的所作所為,為光復國家出力。問題是,母親會獨自處身險境,能否找到食物果腹也是個問題,德國占領者也可能給她找麻煩。因此,這個年輕人的正確作法是陪在母親身邊嗎—這樣顯然有人可以受惠,但只限母親一人,抑或他應該豁出去搏一搏,為眾人的福祉參軍?
今天的哲學家依然為瞭解答這類倫理難題而糾纏不休。沙特這個謎題,跟有名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異曲同工。在這個思想實驗中,假想你看到一列失控的火車或電車沿著軌道猛衝,而前面不遠處,有五個人被縛在軌道上。如果你什麼也不做,那五個人就會喪命,但你發現可以撥動一根控制桿使列車轉到鐵路側線。可是如果這樣做,一個人勢必喪生:他被縛在另一條軌道的位置,如果不是因為你的行動,或可逃過一劫。那麼你打算讓這個人犧牲,還是撒手不管讓五個人死亡?(有另一個版本稱為「胖子難題」:你可以從附近一座橋上把一個大胖子拋到軌道上令火車出軌。這個難題更直逼內心,更難抉擇,因為你要直接出手造成那人喪生。)沙特那位學生的抉擇可看作「電車難題」,但更為複雜,因為他不確定前往英國實際上能否幫到誰,也不確定離開母親是否會令她遭受嚴重打擊。
沙特不打算採取哲學家的傳統作法,透過倫理算計尋求出路,更遑論當個所謂「電車難題專家」。他引導聽眾更個人化地思考問題。面對這個抉擇是怎麼一回事?一個心亂如麻的年輕人實際上該怎麼處理這個何去何從的抉擇?誰幫得上忙,怎樣幫忙?對於最後一個問題,沙特的解答,是從誰無法幫得上忙著手。
那位學生來找沙特之前,曾想過向傳統道德權威求助。他曾考慮找神職人員—可是這類人有時本身就是通敵者,而且不用說也可知道,基督教的倫理只能告訴他愛他的鄰人,善待他人,卻不具體指明他人是誰:他的母親還是他的國家。另外,他考慮去找念書時念過的那些哲學家—他們被奉為智慧的泉源。但哲學家太抽象,對自己這個處境恐怕沒有什麼好說的。然後,他嘗試傾聽自己心裡的聲音,看看能不能從內心深處找到答案。然而卻行不通,他只聽到喧鬧的聲音各有主張(比如說:我一定要留下,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做勇敢的事,我一定要做個好兒子,我要付諸行動,但我心裡害怕,我不想送死,我要出走。我要做一個比父親好的人!我真的愛國嗎?還是假裝愛國而已?)。面對這一堆雜音,他甚至不能信賴自己。最後,這位年輕人只能求助於昔日的老師沙特,知道他起碼不會給自己一個老生常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