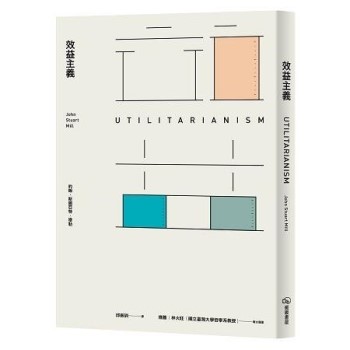第一章 緒論
在人類知識現況的各種情形中,沒有什麼會比爭論對錯判準的決定,在進展上如此些微而更不符預期了,或者說,至今關乎各類重要議題的思辨中,沒有什麼會比這一項還更明顯停留在倒退狀態。打自哲學初萌之時起,關於至善(summum bonum),或者說關於道德的基礎(這兩者其實是同一回事),就一直是思辨中最主要的問題,總是佔據在最天才洋溢的知識份子心頭,將他們分成了不同的宗派學門,彼此奮力攻訐不休。兩千多年過去,同樣的論辯卻仍未止息,哲學家仍舊簇擁著各家學說,而無論是思想家或是普羅大眾,對這主題難有共識的程度,也絲毫不亞於年輕的蘇格拉底在聽到老邁的普羅塔哥拉斯(Protagoras)學說時,提出效益主義來反對在辯士(sophist)間流行的道德主張的情況(如果柏拉圖的對話錄是根據真實對話寫成的話)。
在考慮各門學問的第一原則時,其實都有著同樣的困惑與不確定,某些學科中也同樣有所不和,就連被認為是所有學科中最確定的數學也不能例外;但是這些學問的結論並不會受到太大影響,而且一般說來其實根本毫無影響。這實在太過奇特,而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因為一門學問的細節內容通常並不是從所謂的第一原理演繹而來,也不是以第一原理作為支持的證據。若非如此,就沒有比代數更岌岌可危、更不足以推定結論的學科了。代數的確定性並不是從平常教導學生時所稱的基礎原理而來,因為這些由睿智先師所制定下來的原理,其實就像英國法律一樣充斥著幻想,像神學一樣充滿了奧祕。在一門學科中最終被認定為第一原理的真理,其實是對那門學科中的基礎概念進行形上學分析後所得到的最終結果;這些第一原理對該學科來說,並不像是大廈的地基,反而更像是樹木的根,雖然同樣能夠發揮支持的功能,卻從未遭人深掘,不曾見光。可是儘管在科學領域中,個別事實先於一般性理論出現,但在道德或立法等實踐問題上,情況或許恰恰相反。所有的行動都有某種目的,而我們很自然就會假定,行動所依據的這些規則,其整體樣貌也必定源自行動之目的。在進行某種活動時,我們一開始就看似需要對該活動有個清楚而精確的想法,而不是到了最後才來探求這想法。我們會認為,分辨對錯的測試是用來斷定對錯的方式,而不是在確定了對錯之後才出現的成果。
這種困難並不會因為訴諸人們經常採取的理論(亦即我們可以依靠自然官能、感覺或直覺來分辨對錯)而得以避免。因為除了道德直覺究竟是否存在這個仍待商榷的問題之外,那些自稱相信道德直覺的哲學家也都放棄了我們能用這些官能在個別案例中分辨對錯的想法,正如我們用其他感官分辨影像或聲音的情形中所做的一樣。依據支持那些假思想家的人所說,我們的道德官能只會提供道德判斷的許多一般性原則;道德官能是理性的分枝之一,而不屬於感覺官能;道德官能是在尋找道德的抽象教訓時的依據,而不是在實際案例中觀察發現。倫理學中的直覺學派對一般性法則之必要性的堅持,絲毫不亞於所謂的歸納學派。這兩個學派都同意,某個個別行動是否道德,並不是可以直接察知的問題,而是法則在個例上的適用問題。他們大抵也都認定同樣一套道德法則,但是對於這些法則的例證,以及衍生這些法則的權威有何根源,則有不同見解。根據直覺學派的意見,道德原則顯然是先驗的(à priori),除了瞭解那些字詞的意義之外,毋需訴諸其他事物肯定;依據歸納學派的看法,對或錯,就和真或假一樣,都是仰仗觀察與經驗來解決的問題。這兩者都同樣認為道德必須從原則演繹而來。直覺學派也和歸納學派同樣堅決主張,的確有所謂道德的科學;不過,他們甚少試著將充當這門科學前提的那些先驗原則表列出來,更罕於致力將這些不同的原則化約為某一條第一原則,或是說化約到義務的共同根基上。他們會假定一般的道德規誡就是先驗權威,或是會制定出某種共同基礎,卻往往不比那些準則本身更明顯具有權威,而他們所制定出的這種基礎也從來無法廣獲認同。不過,若要能支持他們的主張,所有道德的根本就應該要有一條基礎的原則或法則;或者,就算有好幾條原則或法則,其中也應該要有確定次序;而這條基礎原則,或是解決不同原則間衝突的那條規則,應該要是自明的(self-evident)。
要探究這個缺陷的惡劣情況到底改善了多少,或是要了解人類的道德信念會因為毫無一絲對終極標準的明白體認,而淪落到何等敗壞不定的程度,就意味著要對古往今來道德學說加以完整考察與批判。不過,我們倒是很容易就能指出,這些道德信念之所以能如此穩定與一致,主要是因為它們隱隱受到一個尚未肯認的標準所影響。儘管倫理學因為缺乏廣受認知的第一原則而不被奉為人們真正情感的指引,不過,人們的情感(無論是偏好或嫌惡),卻都同樣大大受到自己認為各類事物會對自己的幸福產生何種影響的想法所左右。而效益原則(the principle of utility),或者邊沁(Bentham)後來所謂的最大幸福原則(the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在各式道德學說的形成過程中,就算其他學說再怎麼輕蔑地拒斥其權威,仍然在各學說中都佔據了極大份量。而且,就算再怎麼不願承認效益原則就是道德的根本原則以及道德義務的根源,也沒有任何思想學派會否認行為對幸福的影響在許多道德細節上會是重要的因素,甚至是最主要的考量。我可以更進一步向那些自認非反對不可的先驗道德家說,使用效益主義的論證是避無可避的。我這裡的用意並不是要批評這些思想家;但是為了說明起見,我不得不指稱在他們之中最具象徵性的一部系統性論述,也就是康德(Kant)所著的《道德的形上學》(Metaphysics of Morals)。這位非凡大家的思想體系,在哲學思辨史上絕對能繼續作為重要的里程碑。他在這本著作中倡立了一條作為道德義務之根源與基礎的第一普遍原則,也就是:「依照你能讓所有理性存有者都奉為法則的那種原則而行動。」但是荒唐的是,當他開始從這條規定來推演實際的道德義務時,他卻無法證明,如果所有理性存有者都採取最邪惡、不道德的行為規則,在邏輯上會有任何的矛盾與不可能(更甭提在物理上的不可能了)。他所證明的,就只是沒有人會選擇承擔普遍採納那種規則的後果罷了。
這裡我就不再繼續討論其他理論了。我要試圖提出一些能夠有助於理解與接納效益主義或幸福理論的說法,並且證明這套理論,而這顯然不會是常見或通行意義下的證明。任何能夠被證明為善的事物,必定是因為該事物能被指認為某種手段,可以達致另一個公認毋需證明的善。醫療技術會被證明為善,因為這樣的技術能夠帶來健康;但是哪有可能證明健康是善的呢?音樂技藝是善,因為即使不管其他原因,音樂能使人快樂;但是又有什麼能夠證明快樂是善呢?那麼,如果說有個全面性的程序,能適用所有本身是善的事物以及其他不是作為目的、只當作手段的善,儘管這樣的程序可以為人所接受或拒斥,但它本身卻不是一般理解中的證明。然而,我們並不是說要接受或拒斥這程序一定是出於盲目的衝動或任意的選擇。證明這個詞還有個更廣的意義,但這說法就和哲學中其他問題一樣飽受爭議。這是理性官能的認知問題;但理性要理解的方式也並非只依賴直覺。能夠決定在知性上是否要同意某個學說的思慮,也就相當於是證明。
我們現在就是要檢視這些思慮的性質為何;看看它們是以何種方式得以應用,然後又有何理性根據,能夠據以接受或拒斥效益主義程序。不過,在理性上要接受或拒斥的先決條件,是要正確理解效益主義程序。我相信,一般對於效益主義程序那種非常不足的概念,就是阻撓人們接受它的主要障礙;而只要能夠對之加以澄清,即使只是排除了粗鄙低俗的那些誤解,也能大大簡化問題,更能除去大部份的困難。因此,在我進入能夠為接受效益主義標準的哲學論據之前,我要先對這門學說提供一些描繪,以期能夠更清楚地指出它是什麼,有別於它所不是的那些事物,還要駁斥那些源自(或攸關)對這學說的錯誤詮釋而引發的反駁。在備妥這些基礎之後,我會盡我所能地將這學說當作哲學理論般細細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