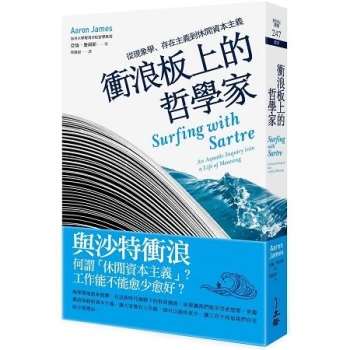對每個人最好的事就是盡可能過得輕鬆。——亞當.斯密《國富論》
麥可.里菲佛(Mike Lefevre)是一名住在芝加哥外圍的鋼鐵工人。他忿忿地指著一名工人,訴說著心裡的不滿:「我們做工的人不是笨好嗎?他只是累了,就這樣而已。」里菲佛也提出了一套解決這問題的辦法:
要是我一個星期只要工作二十小時,我就可以跟我的孩子、跟我老婆混熟一點。有個小鬼找我去社區大學看看,跟我說要約在夏天的某個週六。開玩笑!要是得在帶老婆小孩去野餐跟去大學之間選擇的話,當然是去野餐啊!可是如果每個星期只要工作二十小時,我就可以兩個都選了。
對大多數勞工而言,美好人生總是在遙不可及的地平線彼端。一般的衝浪客對此肯定深有體會。畢竟,大多數衝浪客也都過著每週工作五天的傳統日子。澳洲人會把漫長的工作日集中,拿著積了幾星期的假飛去印尼衝浪,但他們也得和其他人一樣努力工作。只有少數衝浪客衝浪是有薪水可領的。不過,雖然頂尖的職業好手現在可以領到驚人的高薪,但是說實話,大部分職業選手能拿來當作衝浪品牌行銷的選手生涯還是非常短暫,之後他們就會轉入衝浪業界的其他工作,甚至徹底轉行了。一心追夢的年輕衝浪客很快就會發現人生最重要的決定就是要做哪一行、要不要生孩子,還有要怎麼找到知心的另一半。要是隨便哪一個選錯了,這輩子就別指望能經常去衝浪了,因為你根本就抽不出時間來啊!
所以一般的衝浪客絕對會贊同里菲佛的主張,要在從事有意義的休閒活動和工作賺錢之間做選擇時,多想要能夠有充裕一點的時間安排啊!所以說,我們得向週末衝浪的衝浪客致敬,他們可從來沒錯過哪個週六的浪頭。但是衝浪這回事就和其他的才能一樣,需要耐心、專注投入、充分的時間、對時機的把握,對於想要衝到好浪、讓自己能駕馭各種浪頭的衝浪客來說更是如此。我們尊敬在工作中所得到的愉悅,但是除了幫我們付清賬單之外,每週四十小時工時的安排還是奪走了每個人最珍貴的事物——我們真正活著的每一分、每一秒。工作與休閒的墮落沉淪
在這個科技時代裡,工作是不是已經喪失了原本的意義?照馬修.柯勞佛(Matthew Crawford)的說法,十八世紀的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裡,工資是按件計酬。這馬上就遇到了問題:提高薪資並不會刺激勞工增加產量。勞工只會愈做愈少,做到滿足需求的限度就好。這在衝浪客耳裡聽起來再有道理不過了。絕對要保有自由的時間啊!但是在生產效率掛帥的趨勢底下,取代了過去富蘭克林(Ben Franklin)那種清教徒的道德勸說——「能省則省」——結果就產生了「刺激消費」的風氣,把「想要」當成了「需要」。由於廣告和消費債務的不斷轟炸,讓你真的愈來愈想要獲得那些新鮮酷炫的玩意兒,你現在就可以馬上享受,晚點再借用你未來的時間來付錢就好。一旦有了消費債務,勞工就緊緊套牢在愈來愈專門的工作上,而且這日趨精密的分工會使得我們原本從寬鬆知識中懂得的技巧以及對應的人生意義逐漸消失。
工作愈來愈無趣,時間愈來愈遭到壓縮,「休閒活動」就成了你為了這活動本身而做,而且做了也拿不到錢的事。照柯勞佛的說法,在此同時,好的工作就變成了——
能夠增加讓人追求〔休閒〕活動,好讓人生得到意義的工作。抵押貸款經紀人努力工作一整年,然後才可以去爬聖母峰。他這暑假中瘋狂填補的精神食糧,支持著他繼續撐過接下來的秋天、冬天和春天。
現在,我們就可以感受到柯勞佛所謂在工作生活與休閒生活中的「斷裂」了。這兩種生活「是兩種潛在自我之間的交易,而不是在一個完整生活中彼此合理連結的不同部分。」
柯勞佛建議我們在工作與休閒之間要有「更緊密的連結」。在一個能夠肯認工作本身內在價值的社群中,工作就像休假一樣,是「全心投入的活動」,能夠做到最好,讓人體驗到內在於工作本身的價值。換句話說,工作會變得比較像是在摩托車修理店中的生活。他以自身經歷為例,修理機械功夫這門傑出技藝只有同路人才懂得欣賞,才看得出摩托車機械運作的門道,懂得「打鐵跟打仗一樣精采」。我說我們當然可以肯定各行各業,甚至除了讀大學以外,也可以鼓勵孩子從事這些事業,就像柯勞佛所說的一樣。但光是這樣其實無法表達現代勞工的不滿心聲,因為他們不滿的並非任何一種工作或是沒有什麼工作。問題根本就不在於一般的勞動分工。柯勞佛也會同意,精細的角色分工可以增加個人的工作意義。你可以動手寫一本書,但不用去管書的版面或印刷,或者也可以修理摩托車但不用自己親手打造零件或鋪設路面。就算是無比專業的工作也可以充滿意義;你可以專注在確保建築藍圖的某個單位或電腦運算法是正確的。在經濟學中,大規模的分工最後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富裕,藉此省下許多時間去衝浪或玩摩托車。
柯勞佛也不反對休閒活動這件事本身。各個職業的人都需要發懶的自由時間,也要在有靈感的時候努力工作,就跟其他人一樣。登山和衝浪都需要某種置身其中的具體知識,柯勞佛對這種知識也盛讚不已。所以真正的問題有一部分在於能去衝浪或玩摩托車這種活動的時間太少了——畢竟這些活動都是「貴族運動」。但是這樣一來,休閒和工作間要有更緊密的連結只不過是表示我們需要更多的自由時間,才能夠讓我們自由參與各種不同重要的活動。
衝浪客會告訴你,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勞工的時間控制上。即使是「做你所愛」這句老生常談,如今這話的意思也已經變成了「沒收錢不做」,因為你若不把這件事當工作做,就根本抽不出時間來做。我們大部分人都能從工作中找到意義,甚至只是藉以餬口的工作也行,而且理想上我們都會找一份能全心投入的工作來做。但是呢,就因為每週四十小時的工時制度,這個社會最看重的是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時間賺夠多的錢,還要陪家人,還要玩遊戲、做運動、做社區服務、完成生活中林林總總的瑣事(例如洗衣服、理財、烹飪等)。更別說失傳已久的無所事事了。你為了養家活口工作賺錢,結果就是沒有充足的時間能讓你好好靜下心來,去細細感應品味的其他值得投入的事物。還好,行事曆「塞滿」倒不是無法避免的事。我們可以讓所有人都去工作,但是大家都做得很少,每週只要工作二十小時就好。我們所有人都能夠有更多的自由,能夠擁有更多自己的自由時間。
為了存在的文化?
對沙特來說,我們一直在自身的自由中努力掙扎,永遠都在建構自己的身分。雖然這句話從一個成天泡在花神咖啡館聊天的標準法國人口中說出來有點奇怪,不過我們打從嚮往我們自由的本性中接受這番話,就像接受基督新教的工作倫理一樣。在基督新教工作倫理中,你至少會因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收穫。你透過對自我的否定和勤奮工作,不斷努力成就美好德行、提升自我,就能逐步成聖成賢,買得起各種如蒙上帝祝福象徵的奢侈品了。就算這高估了個人成就和財富的意義,但至少不是無的放矢。沙特那套焦躁的自我創造理論讓我們身上除了責任之外還是責任。在這一切不斷的創造與再創造之中,除了我們選擇的目標之外就沒有更重大的價值了,甚至連這份自由也算不上是給你的酬賞,因為你本來就已經在使你必須不斷為了存在而勞動的人類境況中擁有了這一點點自由。
探究至此,我們有了一個主要結論。沙特似乎搞錯了人性的模樣,把自由看得比流動更重要。衝浪客則認為流動才是第一優先。流動就是感應超越自身之外的其他對象,透過感應,我們就能找到真正的自由、平靜、自足。焦慮不是我們的天生狀態,是社會透過像基督新教工作倫理這種文化要求所造成的結果。對沙特來說,現下的焦慮文化完全反映了我們焦慮的自我。我們需要讓人看見、受人喜愛、被人肯定、有人在 Instagram 上幫我們按「讚」;我們不斷專注在展現自我上,透過社群媒體發文、跟風、炫耀自己的財富、外貌、聰明才智或品味——這些都是我們「為他者存在」的袒露,無時無刻都佔據著我們的腦子。每個人都希望透過他人對自己的注視獲得肯定,結果卻總是使自己內心陷入更嚴重的衝突,不斷否定彼此,拒絕平靜。不過,對衝浪客來說,我們的天性與社會動態並不是那麼牢不可破。我們對他人或周遭自然環境的感應可能受到混亂的文化所蒙蔽,但也可以透過彼此合作來撥雲見日。不斷驅使著我們接受「時間就是金錢」的工作文化說穿了真蠢,我們其實可以藉由縮短工時來減輕工作的負擔,進而減少不必要的焦慮。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擁抱衝浪客對生活的這份輕鬆態度。
亞當.斯密在他一七七六年所證成的工業化資本主義經典《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說,人性天生懶散,主要追求的就是「輕鬆」。人類的天性不是持續工作,更不是要持續建構自己的獨特身分。而這就是為什麼要用金錢的誘惑或是挨餓的威脅來哄騙懶惰的勞工去工作。勞工的不滿是資本主義文化的產物,卻也是社會獲得經濟成長之必需。
亞當.斯密在大讚製針廠這資本主義產業模範時清楚地說道,有效率的組裝線能將工人盲目飄移的心思轉向更有意思的事情上。用一堆瑣事麻痺心靈就是生產更多零件的辦法:工人不需要浪費時間將注意力從這項作業轉移到另一項。這就叫「有效率」,因為時間不會「浪費」在各種變化、刺激或複雜細節上,更不用耗在勞工的心智健康上。(反正要是工人發瘋了,只要換一個就好。)不過就在一九七○年代初期,福特汽車公司一名負責在生產線焊接的員工就說過:「根本就沒得休息。生產線一直跑個不停……這不像是叫你把這個東西搬到另一頭去放好,之後再走回來繼續——你走回來的時候還能喘上口氣呢!福特公司有更好的辦法在八小時內用工作把你給榨乾。」
如果說沙特認為焦慮來自我們的天性是搞錯了方向,那亞當.斯密則是另一種搞錯方向,認為人天生就懶散怠惰。這帶出了另一個重要結論:就算是衝浪客,也不是天生就懶散。要活得像個人主要是靠你做些什麼,靠你如何在知覺與行動中做出調節反應。但活著也不僅僅是不斷努力做事而已。因為自己的主動參與才讓人覺得輕鬆。在衝浪中如此,在生活中也一樣。在流暢而熟練的行動中,藉由主動領會世界的自然變化,領會在合作中的其他人,就能帶來一種和諧、超脫、寧靜的感受。
亞當.斯密說:「任何東西真正的價格……就在於獲得那事物的折磨與麻煩。」在工業革命開始之前,絕大部分必要的勞動的確都是些折磨與麻煩,所以大家做了當然要收錢。可是資本主義的成功已經讓這些差事沒那麼痛苦了。事到如今,最爛的工作——雖然有一大堆例外——通常都是靠科技或是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勞工幫我們處理了。現在大部分先進國家裡的工作其實可以很有意思,那我們又為什麼非得做那些吃力不討好的麻煩活兒?而如果大家都會逃避折磨與麻煩,就很難推論出人類天生懶惰,只想過著輕鬆的生活。麥可.里菲佛說得好,大家就只是累了而已。如果在除了睡覺和休息之外還有多一些休閒時間,大家就會興起追求創意與琢磨技巧的熱情,或是懂得藉著愛來生活,就像衝浪客會憑著對海浪的熱愛,在海裡划行好幾個小時一樣。人都會因為沉迷在有意義的活動中而「努力不懈」,但是卻無法在不斷痛苦、煎熬和無謂的折磨與麻煩中生出任何成就。這也許不是因為天生懶散,而是為了一份自尊,看重自己短短一生中有限時間的真正價值。
當波特萊爾(Baudelaire)說「工作比休閒不那麼無聊」時,他一定還沒體驗過組裝線作業或是辦公室瑣事之枯燥煩悶。工作和休閒可以同樣有趣,也同樣無聊。我們可能蹉跎掉休閒時光。大家常會看一大堆無腦的電視節目,但是他們其實可以拿這段時間去衝浪、看書或是散步。這問題的解方不必非得在勞動市場做更多工作。他們真正欠缺的是更深層、更專注的閒散,他們可以輕鬆躺著休息,或是仔細聆聽美妙的音樂、散散步,當然,也可以直接去海邊衝個浪。
有些人很愛吹噓自己「努力工作、盡情玩樂」,而且會拚命投入能獲得短暫愉悅的所謂休閒活動(例如拚命參加派對、重口味性愛、極限運動等)。「休閒」對這些人來說若僅是指狂熱的健身或熱瑜伽,而且還非要在社群媒體上大吹大擂,那他們的生活就只會變得更無趣,畢竟我們其他人所認為的「休閒」還只是想著不知道能不能去海邊而已。無所事事或消極的「擺爛」是應該「無聊」沒錯;因為這種事的意義就是要封閉主動官能,才能好好休息復原。相反地,休閒時間去衝浪則是會徹底攝人心魄。衝浪會使人在流動中、在需要高超技巧的移動中連結到崇高的外在事物,這種連結在衝浪的喜悅中佔了大半。這就是為什麼值得一輩子投入衝浪運動,但一輩子休息或無所事事卻大概划不來的道理。
工作其實也同樣可以很有趣。發揮才能也許就有其意義。說不定是要應付某個真正的挑戰,或是為了某個共同目標,抑或是滿足個人心裡最深處那份追求專精、地位的深刻驅力。不過,如果工作是在這些方面有價值,那就是說我們每週長時間從事有給職的工作不對了。因為在勞動市場外沒有薪水的工作也同樣有這些價值。想想看,養育孩子、社區服務或藝術創作這些活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再不然,花時間去衝浪,去鑽研衝浪技巧中所包含的努力、紀律和效率這些基督新教工作倫理美德也可以。
既然工作和休閒可以同樣有趣或無聊,那麼真正的問題就在於我們缺乏時間去發掘什麼有趣、什麼無聊,而其間的適當比例又該如何。麻煩的是,要怎麼生出自由時間來好好感應?
我們的工作場所是為了「努力工作」來規劃,或者至少為了看起來像是給努力工作的人使用的,所以會要求所有同事都待在同一幢建築物裡,這樣才能夠監督他們。但是在「看起來很認真」和「用心創作」之間,或是在「強迫自己做事」和「製作重要事物」之間並沒有密切的連結。懶懶散散往往還做得比較好。說不定我在某個下午不想從沙發上爬起來讀一篇重要的文章;我得要勉強自己打開電腦才能讀。所以我乾脆躺在那裡,拿出手機,點開文章,躺在沙發上邊看邊思考。搞不好這樣反而會靈光一閃,生出這整個星期最棒的點子來(而且同事之後還會誇讚我的「努力用功」呢)。資本主義能順利運作靠的是創新,而面對面的合作則公認是讓群體內產生流動的關鍵。可是真正的創意交流在整個星期的工作中往往只佔了極小部分。近來,即使是大企業也體認到,想要培養創造力,休閒與發呆和工作同樣重要。真正會關注整個市場的大局,而不是在細節上攪和的CEO就會過得比較像是衝浪客或藝術家。同樣地,人文藝術方面——在點子、文本、文化、工藝品、表演、社會意義、法律、歷史等領域——的專門人員也會積極重構老問題,設法找尋新解方,才能在競爭中不斷推陳出新。在進行所有的創意活動時,如果有時間讓心靈嘗試放手一搏和犯錯重來,能練習嚴格約束和放肆想像,能體會專心致志和不著邊際,能經歷共同討論和獨自思索等種種高低潮,就最能產出美妙的成果。
現在的工作場所已經變得更有趣、更有彈性、更吸引人了,數位時代的來臨也使得工作多少可以不用再束縛在辦公室裡。不過這種開明的管理通常也有龐大的代價,我們得要為此付出以前所謂的自由時間。我們愈來愈少時間可以不受工作騷擾,電子郵件頻頻急催,總是有人覺得你要是沒有馬上處理他交代的事,那你到底是跑去做了什麼別的事?(還好,至少現在衝浪時還沒辦法帶手機下海。)這種緊迫盯人的催促讓人更難關掉手機,沒辦法跑出去閒晃兩個小時,不用急著確認手機裡傳來了些什麼訊息。更不幸的是,在數位時代裡,基督新教的新工作倫理甚至把休閒也當成了一種資源。創意只不過是工作的一部分,只是另一種「生產力」罷了。
可是一談到所有工作的尊嚴,衝浪客就會告訴你自由絕不只是一種產生其他事物的手段而已。人應該擁有自己的思想自由,隨心靈自由飄移,例如在大城市裡信步閒晃時做做輕鬆的白日夢或是發揮創意。沙特會說,人類在流動的反思中是自由的。所以無論是否在工作中,讓人能夠自由想像這件事本身就有其尊嚴。
休閒之所以會沉淪,主因是來自於急促繁雜的工作節奏充斥整個生活。對斯多噶學派來說,會因這種情形而產生的焦慮都只能算是個人責任。我要把注意力放在什麼上,應該完全取決於自己。無論周遭文化有任何暗示,要是我因為新興科技的難擋魅力而分心,無法靜心專注下來,那都是我的問題;我應該要更努力克制注意力。我在先前的章節裡反駁過這麼苛刻的主張。我們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周遭環境確實可能影響我們領會多少的難易與否。我們都是社會性動物,就連內心思考也受到他人的影響,文化會形塑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哪裡、領會些什麼事物,也會影響這樣做的難易程度。將每週工時縮至二十小時,建立重視休閒的資本主義肯定對此能有長足進步。時間與心靈都可以更自由自在。
麥可.里菲佛(Mike Lefevre)是一名住在芝加哥外圍的鋼鐵工人。他忿忿地指著一名工人,訴說著心裡的不滿:「我們做工的人不是笨好嗎?他只是累了,就這樣而已。」里菲佛也提出了一套解決這問題的辦法:
要是我一個星期只要工作二十小時,我就可以跟我的孩子、跟我老婆混熟一點。有個小鬼找我去社區大學看看,跟我說要約在夏天的某個週六。開玩笑!要是得在帶老婆小孩去野餐跟去大學之間選擇的話,當然是去野餐啊!可是如果每個星期只要工作二十小時,我就可以兩個都選了。
對大多數勞工而言,美好人生總是在遙不可及的地平線彼端。一般的衝浪客對此肯定深有體會。畢竟,大多數衝浪客也都過著每週工作五天的傳統日子。澳洲人會把漫長的工作日集中,拿著積了幾星期的假飛去印尼衝浪,但他們也得和其他人一樣努力工作。只有少數衝浪客衝浪是有薪水可領的。不過,雖然頂尖的職業好手現在可以領到驚人的高薪,但是說實話,大部分職業選手能拿來當作衝浪品牌行銷的選手生涯還是非常短暫,之後他們就會轉入衝浪業界的其他工作,甚至徹底轉行了。一心追夢的年輕衝浪客很快就會發現人生最重要的決定就是要做哪一行、要不要生孩子,還有要怎麼找到知心的另一半。要是隨便哪一個選錯了,這輩子就別指望能經常去衝浪了,因為你根本就抽不出時間來啊!
所以一般的衝浪客絕對會贊同里菲佛的主張,要在從事有意義的休閒活動和工作賺錢之間做選擇時,多想要能夠有充裕一點的時間安排啊!所以說,我們得向週末衝浪的衝浪客致敬,他們可從來沒錯過哪個週六的浪頭。但是衝浪這回事就和其他的才能一樣,需要耐心、專注投入、充分的時間、對時機的把握,對於想要衝到好浪、讓自己能駕馭各種浪頭的衝浪客來說更是如此。我們尊敬在工作中所得到的愉悅,但是除了幫我們付清賬單之外,每週四十小時工時的安排還是奪走了每個人最珍貴的事物——我們真正活著的每一分、每一秒。工作與休閒的墮落沉淪
在這個科技時代裡,工作是不是已經喪失了原本的意義?照馬修.柯勞佛(Matthew Crawford)的說法,十八世紀的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裡,工資是按件計酬。這馬上就遇到了問題:提高薪資並不會刺激勞工增加產量。勞工只會愈做愈少,做到滿足需求的限度就好。這在衝浪客耳裡聽起來再有道理不過了。絕對要保有自由的時間啊!但是在生產效率掛帥的趨勢底下,取代了過去富蘭克林(Ben Franklin)那種清教徒的道德勸說——「能省則省」——結果就產生了「刺激消費」的風氣,把「想要」當成了「需要」。由於廣告和消費債務的不斷轟炸,讓你真的愈來愈想要獲得那些新鮮酷炫的玩意兒,你現在就可以馬上享受,晚點再借用你未來的時間來付錢就好。一旦有了消費債務,勞工就緊緊套牢在愈來愈專門的工作上,而且這日趨精密的分工會使得我們原本從寬鬆知識中懂得的技巧以及對應的人生意義逐漸消失。
工作愈來愈無趣,時間愈來愈遭到壓縮,「休閒活動」就成了你為了這活動本身而做,而且做了也拿不到錢的事。照柯勞佛的說法,在此同時,好的工作就變成了——
能夠增加讓人追求〔休閒〕活動,好讓人生得到意義的工作。抵押貸款經紀人努力工作一整年,然後才可以去爬聖母峰。他這暑假中瘋狂填補的精神食糧,支持著他繼續撐過接下來的秋天、冬天和春天。
現在,我們就可以感受到柯勞佛所謂在工作生活與休閒生活中的「斷裂」了。這兩種生活「是兩種潛在自我之間的交易,而不是在一個完整生活中彼此合理連結的不同部分。」
柯勞佛建議我們在工作與休閒之間要有「更緊密的連結」。在一個能夠肯認工作本身內在價值的社群中,工作就像休假一樣,是「全心投入的活動」,能夠做到最好,讓人體驗到內在於工作本身的價值。換句話說,工作會變得比較像是在摩托車修理店中的生活。他以自身經歷為例,修理機械功夫這門傑出技藝只有同路人才懂得欣賞,才看得出摩托車機械運作的門道,懂得「打鐵跟打仗一樣精采」。我說我們當然可以肯定各行各業,甚至除了讀大學以外,也可以鼓勵孩子從事這些事業,就像柯勞佛所說的一樣。但光是這樣其實無法表達現代勞工的不滿心聲,因為他們不滿的並非任何一種工作或是沒有什麼工作。問題根本就不在於一般的勞動分工。柯勞佛也會同意,精細的角色分工可以增加個人的工作意義。你可以動手寫一本書,但不用去管書的版面或印刷,或者也可以修理摩托車但不用自己親手打造零件或鋪設路面。就算是無比專業的工作也可以充滿意義;你可以專注在確保建築藍圖的某個單位或電腦運算法是正確的。在經濟學中,大規模的分工最後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富裕,藉此省下許多時間去衝浪或玩摩托車。
柯勞佛也不反對休閒活動這件事本身。各個職業的人都需要發懶的自由時間,也要在有靈感的時候努力工作,就跟其他人一樣。登山和衝浪都需要某種置身其中的具體知識,柯勞佛對這種知識也盛讚不已。所以真正的問題有一部分在於能去衝浪或玩摩托車這種活動的時間太少了——畢竟這些活動都是「貴族運動」。但是這樣一來,休閒和工作間要有更緊密的連結只不過是表示我們需要更多的自由時間,才能夠讓我們自由參與各種不同重要的活動。
衝浪客會告訴你,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勞工的時間控制上。即使是「做你所愛」這句老生常談,如今這話的意思也已經變成了「沒收錢不做」,因為你若不把這件事當工作做,就根本抽不出時間來做。我們大部分人都能從工作中找到意義,甚至只是藉以餬口的工作也行,而且理想上我們都會找一份能全心投入的工作來做。但是呢,就因為每週四十小時的工時制度,這個社會最看重的是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時間賺夠多的錢,還要陪家人,還要玩遊戲、做運動、做社區服務、完成生活中林林總總的瑣事(例如洗衣服、理財、烹飪等)。更別說失傳已久的無所事事了。你為了養家活口工作賺錢,結果就是沒有充足的時間能讓你好好靜下心來,去細細感應品味的其他值得投入的事物。還好,行事曆「塞滿」倒不是無法避免的事。我們可以讓所有人都去工作,但是大家都做得很少,每週只要工作二十小時就好。我們所有人都能夠有更多的自由,能夠擁有更多自己的自由時間。
為了存在的文化?
對沙特來說,我們一直在自身的自由中努力掙扎,永遠都在建構自己的身分。雖然這句話從一個成天泡在花神咖啡館聊天的標準法國人口中說出來有點奇怪,不過我們打從嚮往我們自由的本性中接受這番話,就像接受基督新教的工作倫理一樣。在基督新教工作倫理中,你至少會因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收穫。你透過對自我的否定和勤奮工作,不斷努力成就美好德行、提升自我,就能逐步成聖成賢,買得起各種如蒙上帝祝福象徵的奢侈品了。就算這高估了個人成就和財富的意義,但至少不是無的放矢。沙特那套焦躁的自我創造理論讓我們身上除了責任之外還是責任。在這一切不斷的創造與再創造之中,除了我們選擇的目標之外就沒有更重大的價值了,甚至連這份自由也算不上是給你的酬賞,因為你本來就已經在使你必須不斷為了存在而勞動的人類境況中擁有了這一點點自由。
探究至此,我們有了一個主要結論。沙特似乎搞錯了人性的模樣,把自由看得比流動更重要。衝浪客則認為流動才是第一優先。流動就是感應超越自身之外的其他對象,透過感應,我們就能找到真正的自由、平靜、自足。焦慮不是我們的天生狀態,是社會透過像基督新教工作倫理這種文化要求所造成的結果。對沙特來說,現下的焦慮文化完全反映了我們焦慮的自我。我們需要讓人看見、受人喜愛、被人肯定、有人在 Instagram 上幫我們按「讚」;我們不斷專注在展現自我上,透過社群媒體發文、跟風、炫耀自己的財富、外貌、聰明才智或品味——這些都是我們「為他者存在」的袒露,無時無刻都佔據著我們的腦子。每個人都希望透過他人對自己的注視獲得肯定,結果卻總是使自己內心陷入更嚴重的衝突,不斷否定彼此,拒絕平靜。不過,對衝浪客來說,我們的天性與社會動態並不是那麼牢不可破。我們對他人或周遭自然環境的感應可能受到混亂的文化所蒙蔽,但也可以透過彼此合作來撥雲見日。不斷驅使著我們接受「時間就是金錢」的工作文化說穿了真蠢,我們其實可以藉由縮短工時來減輕工作的負擔,進而減少不必要的焦慮。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擁抱衝浪客對生活的這份輕鬆態度。
亞當.斯密在他一七七六年所證成的工業化資本主義經典《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說,人性天生懶散,主要追求的就是「輕鬆」。人類的天性不是持續工作,更不是要持續建構自己的獨特身分。而這就是為什麼要用金錢的誘惑或是挨餓的威脅來哄騙懶惰的勞工去工作。勞工的不滿是資本主義文化的產物,卻也是社會獲得經濟成長之必需。
亞當.斯密在大讚製針廠這資本主義產業模範時清楚地說道,有效率的組裝線能將工人盲目飄移的心思轉向更有意思的事情上。用一堆瑣事麻痺心靈就是生產更多零件的辦法:工人不需要浪費時間將注意力從這項作業轉移到另一項。這就叫「有效率」,因為時間不會「浪費」在各種變化、刺激或複雜細節上,更不用耗在勞工的心智健康上。(反正要是工人發瘋了,只要換一個就好。)不過就在一九七○年代初期,福特汽車公司一名負責在生產線焊接的員工就說過:「根本就沒得休息。生產線一直跑個不停……這不像是叫你把這個東西搬到另一頭去放好,之後再走回來繼續——你走回來的時候還能喘上口氣呢!福特公司有更好的辦法在八小時內用工作把你給榨乾。」
如果說沙特認為焦慮來自我們的天性是搞錯了方向,那亞當.斯密則是另一種搞錯方向,認為人天生就懶散怠惰。這帶出了另一個重要結論:就算是衝浪客,也不是天生就懶散。要活得像個人主要是靠你做些什麼,靠你如何在知覺與行動中做出調節反應。但活著也不僅僅是不斷努力做事而已。因為自己的主動參與才讓人覺得輕鬆。在衝浪中如此,在生活中也一樣。在流暢而熟練的行動中,藉由主動領會世界的自然變化,領會在合作中的其他人,就能帶來一種和諧、超脫、寧靜的感受。
亞當.斯密說:「任何東西真正的價格……就在於獲得那事物的折磨與麻煩。」在工業革命開始之前,絕大部分必要的勞動的確都是些折磨與麻煩,所以大家做了當然要收錢。可是資本主義的成功已經讓這些差事沒那麼痛苦了。事到如今,最爛的工作——雖然有一大堆例外——通常都是靠科技或是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勞工幫我們處理了。現在大部分先進國家裡的工作其實可以很有意思,那我們又為什麼非得做那些吃力不討好的麻煩活兒?而如果大家都會逃避折磨與麻煩,就很難推論出人類天生懶惰,只想過著輕鬆的生活。麥可.里菲佛說得好,大家就只是累了而已。如果在除了睡覺和休息之外還有多一些休閒時間,大家就會興起追求創意與琢磨技巧的熱情,或是懂得藉著愛來生活,就像衝浪客會憑著對海浪的熱愛,在海裡划行好幾個小時一樣。人都會因為沉迷在有意義的活動中而「努力不懈」,但是卻無法在不斷痛苦、煎熬和無謂的折磨與麻煩中生出任何成就。這也許不是因為天生懶散,而是為了一份自尊,看重自己短短一生中有限時間的真正價值。
當波特萊爾(Baudelaire)說「工作比休閒不那麼無聊」時,他一定還沒體驗過組裝線作業或是辦公室瑣事之枯燥煩悶。工作和休閒可以同樣有趣,也同樣無聊。我們可能蹉跎掉休閒時光。大家常會看一大堆無腦的電視節目,但是他們其實可以拿這段時間去衝浪、看書或是散步。這問題的解方不必非得在勞動市場做更多工作。他們真正欠缺的是更深層、更專注的閒散,他們可以輕鬆躺著休息,或是仔細聆聽美妙的音樂、散散步,當然,也可以直接去海邊衝個浪。
有些人很愛吹噓自己「努力工作、盡情玩樂」,而且會拚命投入能獲得短暫愉悅的所謂休閒活動(例如拚命參加派對、重口味性愛、極限運動等)。「休閒」對這些人來說若僅是指狂熱的健身或熱瑜伽,而且還非要在社群媒體上大吹大擂,那他們的生活就只會變得更無趣,畢竟我們其他人所認為的「休閒」還只是想著不知道能不能去海邊而已。無所事事或消極的「擺爛」是應該「無聊」沒錯;因為這種事的意義就是要封閉主動官能,才能好好休息復原。相反地,休閒時間去衝浪則是會徹底攝人心魄。衝浪會使人在流動中、在需要高超技巧的移動中連結到崇高的外在事物,這種連結在衝浪的喜悅中佔了大半。這就是為什麼值得一輩子投入衝浪運動,但一輩子休息或無所事事卻大概划不來的道理。
工作其實也同樣可以很有趣。發揮才能也許就有其意義。說不定是要應付某個真正的挑戰,或是為了某個共同目標,抑或是滿足個人心裡最深處那份追求專精、地位的深刻驅力。不過,如果工作是在這些方面有價值,那就是說我們每週長時間從事有給職的工作不對了。因為在勞動市場外沒有薪水的工作也同樣有這些價值。想想看,養育孩子、社區服務或藝術創作這些活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再不然,花時間去衝浪,去鑽研衝浪技巧中所包含的努力、紀律和效率這些基督新教工作倫理美德也可以。
既然工作和休閒可以同樣有趣或無聊,那麼真正的問題就在於我們缺乏時間去發掘什麼有趣、什麼無聊,而其間的適當比例又該如何。麻煩的是,要怎麼生出自由時間來好好感應?
我們的工作場所是為了「努力工作」來規劃,或者至少為了看起來像是給努力工作的人使用的,所以會要求所有同事都待在同一幢建築物裡,這樣才能夠監督他們。但是在「看起來很認真」和「用心創作」之間,或是在「強迫自己做事」和「製作重要事物」之間並沒有密切的連結。懶懶散散往往還做得比較好。說不定我在某個下午不想從沙發上爬起來讀一篇重要的文章;我得要勉強自己打開電腦才能讀。所以我乾脆躺在那裡,拿出手機,點開文章,躺在沙發上邊看邊思考。搞不好這樣反而會靈光一閃,生出這整個星期最棒的點子來(而且同事之後還會誇讚我的「努力用功」呢)。資本主義能順利運作靠的是創新,而面對面的合作則公認是讓群體內產生流動的關鍵。可是真正的創意交流在整個星期的工作中往往只佔了極小部分。近來,即使是大企業也體認到,想要培養創造力,休閒與發呆和工作同樣重要。真正會關注整個市場的大局,而不是在細節上攪和的CEO就會過得比較像是衝浪客或藝術家。同樣地,人文藝術方面——在點子、文本、文化、工藝品、表演、社會意義、法律、歷史等領域——的專門人員也會積極重構老問題,設法找尋新解方,才能在競爭中不斷推陳出新。在進行所有的創意活動時,如果有時間讓心靈嘗試放手一搏和犯錯重來,能練習嚴格約束和放肆想像,能體會專心致志和不著邊際,能經歷共同討論和獨自思索等種種高低潮,就最能產出美妙的成果。
現在的工作場所已經變得更有趣、更有彈性、更吸引人了,數位時代的來臨也使得工作多少可以不用再束縛在辦公室裡。不過這種開明的管理通常也有龐大的代價,我們得要為此付出以前所謂的自由時間。我們愈來愈少時間可以不受工作騷擾,電子郵件頻頻急催,總是有人覺得你要是沒有馬上處理他交代的事,那你到底是跑去做了什麼別的事?(還好,至少現在衝浪時還沒辦法帶手機下海。)這種緊迫盯人的催促讓人更難關掉手機,沒辦法跑出去閒晃兩個小時,不用急著確認手機裡傳來了些什麼訊息。更不幸的是,在數位時代裡,基督新教的新工作倫理甚至把休閒也當成了一種資源。創意只不過是工作的一部分,只是另一種「生產力」罷了。
可是一談到所有工作的尊嚴,衝浪客就會告訴你自由絕不只是一種產生其他事物的手段而已。人應該擁有自己的思想自由,隨心靈自由飄移,例如在大城市裡信步閒晃時做做輕鬆的白日夢或是發揮創意。沙特會說,人類在流動的反思中是自由的。所以無論是否在工作中,讓人能夠自由想像這件事本身就有其尊嚴。
休閒之所以會沉淪,主因是來自於急促繁雜的工作節奏充斥整個生活。對斯多噶學派來說,會因這種情形而產生的焦慮都只能算是個人責任。我要把注意力放在什麼上,應該完全取決於自己。無論周遭文化有任何暗示,要是我因為新興科技的難擋魅力而分心,無法靜心專注下來,那都是我的問題;我應該要更努力克制注意力。我在先前的章節裡反駁過這麼苛刻的主張。我們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周遭環境確實可能影響我們領會多少的難易與否。我們都是社會性動物,就連內心思考也受到他人的影響,文化會形塑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哪裡、領會些什麼事物,也會影響這樣做的難易程度。將每週工時縮至二十小時,建立重視休閒的資本主義肯定對此能有長足進步。時間與心靈都可以更自由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