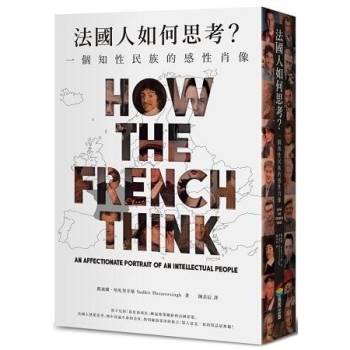第十章 法國思維的封閉
二〇一三年夏季,一股消極浪潮襲捲法蘭西民族。民意調查顯示,法國成為「歐洲悲觀主義的冠軍」(注1),大眾對於未來想望的黯淡程度遠遠超過鄰國。調查也一致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法國人認為國家正在衰敗。(注2)對於這股沮喪情緒,保守路線的《費加洛日報》在社論中稱法國已經「觸礁」,社會氣氛低迷不振,無論是在相對和絕對數字來看,經濟都落後其餘歐洲競爭對手。值此同時,政府與許多反對團體之間進行「冷內戰」,爭議涵蓋反對同性婚姻到布列塔尼的財經政策。(注3)《迴聲報》一篇社論指出負面氛圍也是懷舊,盼望如同戰後黃金時代一樣的飛快成長,以及戴高樂般的絕對權威:「現在我們只剩下衰退。」(注4)
縱觀之前十年,法國的萎靡不振已經成為知識和文化精英的討論焦點。有人嘗試將此現象解釋為高盧人的矛盾性格之一,比方說曾有個人發展專家認為法國人的不快樂或許源於「想太多」。(注5)生命的苦痛(mal de vivre),一個其實無法精準翻譯的概念,也得到史學家的直白詮釋:它是現代性的基本要素之一,因為「思想的進步與絕望感無法切割」。(注6)然而,從薩科吉執政晚期到歐蘭德這段期間,高盧人的末日心態有個明確的特徴是,認為在可見的範圍內,沒有獲得救贖的機會。衰落主義成為政治精英最重要的課題,前總理費雍宣稱法國「失去實質」;這說法更加令人擔憂,因為背後真正的含義並不明確。(注7)社會主義陣營以典型的方式因應危機:舉辦研討會。(注8)但許多進步人士承認出現社會的「道德恐慌」現象,「法國集體想像正在右傾」。(注9)各領域、各地區都陷入這種蕭條景況,《世界報》社論警告法國正經歷「持續的工業衰退」,產業雜誌《新工廠》(L’Usine nouvelle)感嘆「法國汽車製造業回不去了」,曾經得到蕭邦讚賞的鋼琴大廠普萊耶爾表示,要在二〇一三年底結束營運。(注10)
經濟衰退也會影響到地理問題,許多省城如康城大量流失人口,(注11)北部和東部面臨慢性去工業化的問題。(注12)鄉村的處境並不比較好,根據一個常被引用的研究,普羅旺斯某村莊已經不如彼得‧梅爾(Peter Mayle)筆下的溫暖友善,社區團結的傳統凋零,當地居民彼此疏離,也與時代脫節。一個當地人說:「我們的世界正在死去,卻不知道要用什麼取代。」(注13)這層空虛感成為米歇爾‧維勒貝克的反烏托邦小說《地圖與領土》(La Carte et le territoire)的靈感源頭,其中法國鄉村成為全球旅遊天堂,「除了迷人的酒店、香水和肉罐頭之外,沒有東西可以賣。」(注14)
即使在節慶紀念這種應該輕鬆的時刻,也彷彿是葬禮。二〇一三年,一次世界大戰紀念日前夕的社會氛圍,被皮埃爾‧諾拉形容是喚起「法國在二十世紀走下坡的集體意識」(到了二〇一五年滑鐵盧戰役兩百週年時,情況也沒有好轉)。(注15)卡繆誕生一百週年時同樣帶有這樣的病態感受,這位小說家的作品主題正是解析自我懷疑和疏離。一位文學史家表示,悲觀主義原本專屬於文化精英,卻已經蔓延到社會各階層:「現在連白痴都快樂不起來。」(注16)毫不奇怪,唯一還能振作的政治運動屬於國民陣線。《觀點》主編弗朗茲‧奧利維耶‧吉斯貝爾(Franz-Olivier Giesbert)從「法國思想馬琳化」加以分析,認為悲觀的民族情緒有一部分反映出該政黨在馬琳‧雷朋的領導下重新壯大,能夠操作所有議題,如移民、安全、失業、貪汙,乃至於工業農業的失敗。然而,他也補充:國民陣線只不過是喚起集體的深層焦慮,「在衰退的感受中,確實有一種形而上的東西正在吞沒整個舊世界,在法國尤其嚴重」。(注17)
目前法國的經歷其實是歐洲整體病況的一部分,儘管法國人的體驗似乎特別深刻。其中一部分原因在前面章節已經提過,也就是法國精英自從大革命之後就常常對未來感到焦慮,「反現代主義」是法國思想的基本要素。(注18)進步主義者的絕望感也有悠久歷史,主要由於敗給保守勢力是一再出現的經驗。一八六三年拿破崙三世治理達到巔峰時,普魯東寫下:「我相信我們完全墮落了,而我越是透過縱容來欺瞞自己,就越對這個國家的生命力失去信心。對於未來,對於法國人的人道主義使命,我無法保持信念。我們越早退場,對於文明、對於人類將越有益。」(注19)上回如此慘淡的氣氛出現在一九三〇年代,文明的危機感瀰漫各地(包括英國)。(注20)
由此觀之,吉斯貝爾的說法呼應了羅伯特‧阿隆(Robert Aron)和阿爾諾‧丹第歐(Arnaud Dandieu)的《法蘭西民族的頹廢》(Décadence de la nation française),該書主張法國的萎靡源於「形上的和精神上的苦痛」。(注21)二〇一三年,許多媒體比較兩個時代後下了多彩多姿的標題,如「救命,三〇年代回來了!」(注22)最後注意力自然而然轉向扮演國家先知的傳統角色,也就是知識分子,藉由檢討他們的過失,以求找出能夠逃離絕望感且有意義的新路線。共產主義的《人道報》感慨法國知識分子已經被「哲學頹廢」滲透,民粹主義週刊《瑪麗安娜》也惋惜「沒有一套國際視野可以填補目前法國思維的絕對真空」。(注23)於是哲學家加斯帕爾‧科寧格(Gaspard Koening)提出建言:既然理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都死了,也許終於到了法國擁抱自由主義的時刻?(注24)
國家的病
對於國家的現況與未來越來越悲觀,這種症狀被歷史學家米歇爾‧維諾克(Michel Winock)稱之為「法國國家病」(French national disease),(注25)我們從這種現象可以看到什麼?知名歷史學者的親自診斷已經透露了許多線索,反映出法國知識精英傾向從心理層面看待這件事,認為這是主觀問題,無法藉由客觀事實或數據進行分析。的確,雖然法國衰退主義者的著作點出了特定的趨勢、時間、轉捩點事件,如二〇〇一年總統選舉、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但這類著作的矛盾之一在於無法提出確鑿的證據。為了符合法國思維喜愛整體性的特徴,現象本身通常被視為既定事實,然後才試圖找出更普遍的大框架來套入──可能是人性、歷史、經濟、文化,以至於種族。
其他方面也一樣,這是經典的法式討論,強調失落、異化和死亡,這些概念根基於國家文化。同時,一些論述走向抒發個人情緒,對於常見的哲學觀感到嚴重的挫折失望:無論保守派、自由派或進步派,他們的共同點在於對之前抱持的信念徹底幻滅。這類文獻也喜歡講大方向,反復使用修辭上的二分法,如善良與邪惡、文明與野蠻、進步和頹廢等等。換言之,最為誇張、最覺得國家末日已至的言論(像是移民無法融入,或者法國人缺乏集體自我認同),多半來自於居住在法國核心區域且很少出去外面看看的那群人。他們對於一般人的生活瞭解甚少。此外,還有陰謀論(這個群體喜愛的主題之一)將矛頭指向精英階層,又或者其他更棘手、更難定義的對象(「新自由主義」或「伊斯蘭」)。
這些討論也具備法式特徴,大半時候生不出具體的解決方案或行動計畫,聲稱最重要的改革要從心靈或態度著手。看在長期關注法國知識圈的人眼中,當前這些意見中瀰漫的平行世界氛圍非常熟悉,尤其他們偏愛糾結在消極的情緒,疾聲大呼模糊或難以實現的理想,例如主張將法國轉變為種族完全相同的國家;提案和分析時的邏輯思考,也總是走到最遙遠的極端。
悲觀哲學最全面的版本出自生於羅馬尼亞的散文家蕭沆(Emil Cioran),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在拉丁區定居,因《解體概要》(Précis de décomposition, 1949)一書而成品。書中充滿格言警句,被譽為存在主義的傑作,原因不僅是斷然拒絕生命可能有意義:「光芒是例外,衰亡才是規則。生命無時無刻不崩解,只是不斷地失去光,平淡無味地消融,沒有權杖,沒有榮耀,沒有光環。」(注26)他的作品的主題主要是孤獨、無聊,當然還有死亡這個「偉大的肯定」,(注27)看似直接回歸了神祕主義傳統,卻又完全剝除了潛藏的樂觀思考。蕭沆將從負面執著推演出的邏輯結論寫進《誕生之不便》(De l’inconvénient d’être né, 1973),認為(徒勞的)創造是個悲劇,存在只是對悲劇引發的反應:「我們不急著衝向死亡,卻急著逃離誕生這場災禍。我們蠕動掙扎,像是倖存者想要忘記恐怖。我們害怕死亡,但那只是病態的投射,追溯到我們最初的一瞬間。」(注28)
世紀更迭的時刻,法國思想墜進黑暗深淵,蕭沆的中歐陰鬱重獲新生。伽利瑪出版社於他過世十五年後,也就是二〇一一年時,將其作品全集收入知名的七星文庫(Pléiade)系列。他對法國衰退的集體反思最顯著的貢獻,在〈來自法國〉(De la France)這篇文章,實際上完成於一九四一年德軍占領時期,直到二〇〇九他死後才得以發表。文中預測了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法國社會氛圍,指出在他看來法國精神基本上是鄉土與享樂主義,以及(受到笛卡兒影響)傾向「狹隘的完美主義」──偏愛風格優雅、形式清晰,卻不具哲學深度。(注29)其智識上的偉大來自構築了「理性主義神話」,並且霸占了現代歐洲人的思維。蕭沆認為法國人將無法繼續沉迷在那些理念中:「心靈的井乾涸了,他們在沙漠中醒來,環抱身體,恐懼未來。」(注30)蕭沆的信徒之一是哲學家弗雷德里克‧史福特(Frédéric Schiffter),自稱「小資產階級虛無主義者」,其著作抨擊現代性枯燥、倫理無益,還有傅柯無用(他不讀傅柯作品,因為傅柯「穿套頭圓領毛衣」)。(注31)
與蕭沆的哲學、美學感性相反,阿蘭‧佩雷菲特表達悲觀情緒的管道是歷史框架;不過整體結論一樣陰霾密布。首次出版於一九七六的《法國惡》是一本複合作品,一部分以戴高樂時期前部長幻滅後的自傳探索法國的「制度失靈」;另一部分則試圖解釋法國現代政治文化有何缺陷。佩雷菲特的中心論點在於法國與其他工業發達社會有所不同,受到異化的公民、政府的入侵雙面夾攻所「詛咒」。(注32)他延續托克維爾的論點,認為高度中央集權是絕對君主專制政體的殘留,大革命與後來幾次共和政府還將之強化了。隨時間推移,法國人因此成「叛逆的保守派」,患上名為「抽搐麻痺」的特俗疾病。(注33)病徵表現是偶像崇拜的傳統(「古人和現代人爭吵時,多半都是古人占上風」);(注34)仰慕絕對權力又喜愛週期性的危機(「戀痙攣」〔spasmophilia〕);(注35)執著於普世平等卻又拒絕差異性;(注36)偏好不真實之物(「在法國,邏輯精神會被魔法精靈取代」);(注37)以及將每件事情簡單地二元劃分如「自由」與「權威」、「秩序」與「運動」之類。(注38)
佩雷菲特的結論很簡潔:「我們不是能與自己共處的民族。」(注39)雖然他自稱相信法國人能完成「精神革命」來改變自己,其言行的沉重、準人類學的特質卻似乎是反證。一九九六年新版的序言裡,他明確陳述了內心的消極,表示儘管一九八〇年代社會黨做了很多去除中央集權的改革措施,法國仍停留在柯爾貝爾的傳統下,國家牢牢箝制一切。(注40)結論更是消沉,佩雷菲特指出,其實這種負面氛圍的暗流從戴高樂時期就出現,只是被唯意志論和外表的光鮮亮麗給掩蓋。
另一種更萎靡的消極潮流於一九八〇年代在國族主義右派內重現,核心命題就是法國的「衰敗」,而且主張衰敗是一種本質,無法逆轉,表現的形式就是既有秩序會全面崩潰。(注41)這種慘淡思想靈感來自於反大革命、反現代主義的著作,主要作者為弗約、德魯蒙、巴雷斯和拉荷歇爾,(注42)他們認為當今社會被困在道德和精神的腐敗,理性主義與個人主義已經凌駕任何形式的集體歸屬感,(注43)人類與自身的真實(宗教)疏離之後,躲進「粗俗的唯物主義,一種結合怠惰思考、貪求安逸之後的可怕產物」。(注44)
悲觀敘事之中,另一個鮮明的命題是法國國族的衰亡,也就是移民造成的威脅。「伊斯蘭主義」(一個模糊的概念,毫無來由地認為所有伊斯蘭教徒都有極端思想)會奪走國家,是自一九八〇年代起國民陣線主打的論點。除此之外,他們譴責的還有各種社會寬容的表現:性工作、毒品、暴力、家庭破裂、校園違紀;全部濃縮起來之後,就成為對國家滅亡的憂慮。一九四四年九月演講時,尚‧馬利‧勒龐說:「法國繼續倒退,走上西方和北方那種道路,現在重大危機不只出現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連文化和道德也受害了。法國的國體、法國人民的整體性,已經來到生死存亡的關頭。」(注45)
衰退的體現
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裡,衰敗論調已經深植人心。這一派人還提供了擴大和深化負面感受需要的材料。進入下一階段,主題轉為「高級」文化的隕落,原本不斷重複這議題的只有保守派民族主義者,或者稱之為「傾頹主義者」(decadentist),不過近期巴黎文化精英也起了興趣。這個新文類的早期經典是阿蘭‧芬基爾克羅的《思想潰敗》(La Défaite de la pensée, 1987),筆調憂鬱,警告啟蒙時代留下的遺產可能遭到第三世界主義者、道德相對主義者及大眾藝人這些烏合之眾給毀掉。芬基爾克羅發明的一些概念使其漸漸成為法國最重要的新共和辯論家,同時也代表世俗主義對抗多元文化主義帶來的威脅。(注46)他表示自己特別在意的是,提倡「文化差異」的同時,也就會否定解放了現代人類的智識特質,例如懷疑論、反諷、理性個人主義。根據這個前提,他推斷文明正遭受野蠻新時代的威脅:「生命和思想慢慢屈服於狂熱分子和殭屍挑起的,可怕又輕慢的衝突。」(注47)芬基爾克羅直覺判斷法國文化領域有某種根本的元素被打破了,這想法獲得其他人支持,最主要是反現代的作家及評論家菲利普‧穆瑞,還有讓‧弗朗索瓦‧馬太的《內在的野蠻》(La Barbarie intérieure, 1999)一書,從哲學層面痛陳大眾文化敗壞了文明。(注48)
隨著衰敗這個主題進入文化領域,法國文學不可避免地成為受到檢視的對象。一九九五年《精神》的前編輯尚‧瑪利‧多梅納(Jean-Marie Domenach)以駭人聽聞的說法形容當代法國文學,他批評真正的文學評論傳統已經消失,就像英國、美國一樣,由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紐約書評之類把持;他也抨擊多數法國小說走入「邪門歪道」,欠缺有效的人物塑造,脫離社會現實,喜愛異常的格式與省略。(注49)《快訊》週刊也刊出標題為「小說之死」的長文呼應多梅納的慘淡觀點,透過沮喪論調指出新流行的寫作形式看似內斂、表達主觀,實則「歇斯底里、急躁、悲慘、自大狂,極端清教徒卻又極端情色」。(注50)十多年後,小說家派崔克‧貝森(Patrick Besson)對法國當代文學概況的看法一樣消極,標題挑釁地定為「法國文學死了嗎?」(注51)而英語世界也有類似觀察,覺得當代法國文學已經迷失方向,變得過於內向也過於痴迷在抽象概念上,不再繼承過去優秀的說故事能力。
然而,在這個層面上法國人又出現矛盾:他們有兩千多個關於書籍的獎項,包括久負盛名的龔古爾、勒諾多、費米娜和美第奇,每年的文學季(rentrée littéraire)也越來越盛大,怎麼看都覺得法國文學活力十分充沛。事實上,這個問題必須從國際舞臺來分析,雖然福樓拜、大仲馬、普魯斯特和卡繆已然是全球文學遺產的一部分,繼承他們路線的暢銷(或獲獎)作家如凱特琳‧彭歌(Katherine Pancol)、紀優‧穆索(Guillaume Musso)、安娜‧戈華達(Anna Gavalda)、艾曼紐‧卡黑爾(Emmanuel Carrère)、阿梅麗‧諾冬(Amélie Nothomb)、瑪麗‧達里厄斯克(Marie Darrieussecq)、克里斯多夫‧歐諾迪比奧(Christophe Ono-dit-Biot),很難在英語世界吸引到足夠讀者。即便諾貝爾獎得主勒克萊齊奧和派崔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也一樣,在英語世界中幾乎沒有知名度。雖然翻譯法國小說並出版以美國為最多,但數量相對而言依舊少(二〇一二年有六十二部,二〇一三年有七十七部),(注52)且多半是小量發行,也只有極少數能夠進入美國的暢銷排行榜。
觀察能夠打進美國市場的作品,會發現內容符合對於法國人的刻板印象:過分發達的腦力,代表人物是妙莉葉‧芭貝里(Muriel Barbery)《刺蝟的優雅》(The Elegance of Hedgehog)裡極有教養的女門房荷妮;縱使在最可怕的情境中依舊性格輕浮輕率,洛朗‧比奈(Laurent Binet)的《HHhH》是作者想像力融入納粹安全部長海德里希被暗殺的故事;經久不衰的反猶太思想,像是依蕾娜‧內米洛夫斯基(Irène Némirovsky)的《法蘭西組曲》(Suite français)在她死後才發表,內容是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作者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內;當然還有性變態,好比米歇爾‧維勒貝克的所有作品。
二十一世紀初法國經濟每況愈下,成為衰敗論者的新戰場,主要論述來自尼可拉‧巴斐雷(Nicolas Baverez)《失速下墜的法國》(La France qui tombe, 2003),這本小冊發揮很大影響力,用意是更加聚焦於佩雷菲特的診斷,基底則是雷蒙‧阿隆的保守自由主義。巴斐雷的主要論點是法國之所以倒退,原因在於社會精英從十九世紀後期刻意推行相關政策,「法國模式」產生了巨大的公部門,政府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尤其是醫療和福利方面),也更傾向內部社會和諧而排斥劇烈變革;呼應史丹利‧奧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經典說法:「社會僵局。」(注53)據巴斐雷分析,法國面對後冷戰的世界變遷只有固定套路:其他國家進行的經濟現代化是減少公部門規模、促進創新和競爭力,但歷屆法國政府不分左右只會重申傳統的「法國模式」,從而使國家債務攀升,外來投資卻急劇下跌。因此,法國國內生產總值三分之一以上用於福利和公部門人事,只有百分之二點五進入投資。(注54)他估計這種「政治自閉症」(又是病理學詞彙)是「政治、經濟和社會,以至於智力和道德層次的癱瘓」。他斷言後果必然是「法國失速下墜」。(注55)
還有更細緻的版本出現在已故的雅克‧馬賽(Jacques Marseille)的《內戰在法國的妙用》(Du bon usage de 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這本書在二〇〇五年歐盟公投後問世,借鑑一系列歷史案例試圖說明法國衰敗並非必然,政治危機有可能化為變革動力,戴高樂一九五八年回歸就是鐵證。二十一世紀初很難有這麼樂觀的想法,法國社會產生了新的隔閡──就業者與失業者、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獲得政府保護的領域和曝露在全球化風險下的領域。他的結論是,法國精英最可能採取的行動路線就是「脆弱地躲回殼裡」。(注56)
經濟停滯的預言在二〇一二年的總統選舉中得到克里斯逖安‧聖德田(Christian Saint-Etienne)的《語無倫次的法文》(L’Incohérence française)一書呼應。書中將持續不斷的經濟困境歸咎於法國精英的「智力怯懦」。(注57)菲利普‧馬尼爾(Philippe Manière)的《生活最苦的國家》(Le Pays où la vie est plus dure)也是同一主題的演繹。但比起西蒙娜‧瓦普勒(Simone Wapler)的《為何法國會破產》(Pourquoi la France va faire faillite),(注58)已經少了很多末日氛圍的災難性終結。巴斐雷在二〇一二發行的另一本小冊中,簡直像是在傷口上撒鹽,哀怨表示就連具有相同意識形態的人也沒聽見自己的訴求:儘管薩科吉承諾改革法國制度,卻進一步擴大公共支出和國家借貸,從而加劇國家衰落的速度。他認為除非統治者願意放棄中央經濟統制論和反自由經濟的偏見,否則狀況不會好轉。(注59)
將衰敗等同於政府失靈的這個主題催生了大量文獻,許多人盡力分析各部門遭遇的危機,並提供(偶爾算是)睿智的建言。(注60)問題是用於診斷問題的語言往往過度膨脹,針對教育體系的討論尤其如是。校長馬克‧勒布利斯(Marc Le Bris)認為法國公眾(公立)學校可謂「文化浩劫」,基本的識字、算術、一般紀律都不行,教師失去權威,經典文化被摒棄。(注61)他示警說,原本共和派理念之一就是傳承國家文化,如今看來並沒有達成。(注62)另一本小冊的態度同樣激烈,教師尚‧保羅‧布里格利(Jean-Paul Brighelli)譴責「製造白癡」的教程,主張根本問題出在在一九六八以後的教育哲學從傳統模式轉向於學生無益的「能力」,以及個別自律。(注63)這種新平均主義表面光鮮亮麗,不稱學生為學生(élèves),套上了「學習者」的頭銜(apprenants)。(注64)布里格利指出這種系統的一大惡果,是資產階級的社會精英和遭受「去思考化」的底層(注65)之間的文化差距越來越大。一九八〇年代早期開始實行另項一計畫,試圖為「偏鄉」設置「優先教育區」(ZEPS),結果也徹底失敗。(注66)就教育而言,共和派的最終理念應當是促進機會平等,但這樣的雙軌制根本背道而馳。(注67)
二〇一三年夏季,一股消極浪潮襲捲法蘭西民族。民意調查顯示,法國成為「歐洲悲觀主義的冠軍」(注1),大眾對於未來想望的黯淡程度遠遠超過鄰國。調查也一致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法國人認為國家正在衰敗。(注2)對於這股沮喪情緒,保守路線的《費加洛日報》在社論中稱法國已經「觸礁」,社會氣氛低迷不振,無論是在相對和絕對數字來看,經濟都落後其餘歐洲競爭對手。值此同時,政府與許多反對團體之間進行「冷內戰」,爭議涵蓋反對同性婚姻到布列塔尼的財經政策。(注3)《迴聲報》一篇社論指出負面氛圍也是懷舊,盼望如同戰後黃金時代一樣的飛快成長,以及戴高樂般的絕對權威:「現在我們只剩下衰退。」(注4)
縱觀之前十年,法國的萎靡不振已經成為知識和文化精英的討論焦點。有人嘗試將此現象解釋為高盧人的矛盾性格之一,比方說曾有個人發展專家認為法國人的不快樂或許源於「想太多」。(注5)生命的苦痛(mal de vivre),一個其實無法精準翻譯的概念,也得到史學家的直白詮釋:它是現代性的基本要素之一,因為「思想的進步與絕望感無法切割」。(注6)然而,從薩科吉執政晚期到歐蘭德這段期間,高盧人的末日心態有個明確的特徴是,認為在可見的範圍內,沒有獲得救贖的機會。衰落主義成為政治精英最重要的課題,前總理費雍宣稱法國「失去實質」;這說法更加令人擔憂,因為背後真正的含義並不明確。(注7)社會主義陣營以典型的方式因應危機:舉辦研討會。(注8)但許多進步人士承認出現社會的「道德恐慌」現象,「法國集體想像正在右傾」。(注9)各領域、各地區都陷入這種蕭條景況,《世界報》社論警告法國正經歷「持續的工業衰退」,產業雜誌《新工廠》(L’Usine nouvelle)感嘆「法國汽車製造業回不去了」,曾經得到蕭邦讚賞的鋼琴大廠普萊耶爾表示,要在二〇一三年底結束營運。(注10)
經濟衰退也會影響到地理問題,許多省城如康城大量流失人口,(注11)北部和東部面臨慢性去工業化的問題。(注12)鄉村的處境並不比較好,根據一個常被引用的研究,普羅旺斯某村莊已經不如彼得‧梅爾(Peter Mayle)筆下的溫暖友善,社區團結的傳統凋零,當地居民彼此疏離,也與時代脫節。一個當地人說:「我們的世界正在死去,卻不知道要用什麼取代。」(注13)這層空虛感成為米歇爾‧維勒貝克的反烏托邦小說《地圖與領土》(La Carte et le territoire)的靈感源頭,其中法國鄉村成為全球旅遊天堂,「除了迷人的酒店、香水和肉罐頭之外,沒有東西可以賣。」(注14)
即使在節慶紀念這種應該輕鬆的時刻,也彷彿是葬禮。二〇一三年,一次世界大戰紀念日前夕的社會氛圍,被皮埃爾‧諾拉形容是喚起「法國在二十世紀走下坡的集體意識」(到了二〇一五年滑鐵盧戰役兩百週年時,情況也沒有好轉)。(注15)卡繆誕生一百週年時同樣帶有這樣的病態感受,這位小說家的作品主題正是解析自我懷疑和疏離。一位文學史家表示,悲觀主義原本專屬於文化精英,卻已經蔓延到社會各階層:「現在連白痴都快樂不起來。」(注16)毫不奇怪,唯一還能振作的政治運動屬於國民陣線。《觀點》主編弗朗茲‧奧利維耶‧吉斯貝爾(Franz-Olivier Giesbert)從「法國思想馬琳化」加以分析,認為悲觀的民族情緒有一部分反映出該政黨在馬琳‧雷朋的領導下重新壯大,能夠操作所有議題,如移民、安全、失業、貪汙,乃至於工業農業的失敗。然而,他也補充:國民陣線只不過是喚起集體的深層焦慮,「在衰退的感受中,確實有一種形而上的東西正在吞沒整個舊世界,在法國尤其嚴重」。(注17)
目前法國的經歷其實是歐洲整體病況的一部分,儘管法國人的體驗似乎特別深刻。其中一部分原因在前面章節已經提過,也就是法國精英自從大革命之後就常常對未來感到焦慮,「反現代主義」是法國思想的基本要素。(注18)進步主義者的絕望感也有悠久歷史,主要由於敗給保守勢力是一再出現的經驗。一八六三年拿破崙三世治理達到巔峰時,普魯東寫下:「我相信我們完全墮落了,而我越是透過縱容來欺瞞自己,就越對這個國家的生命力失去信心。對於未來,對於法國人的人道主義使命,我無法保持信念。我們越早退場,對於文明、對於人類將越有益。」(注19)上回如此慘淡的氣氛出現在一九三〇年代,文明的危機感瀰漫各地(包括英國)。(注20)
由此觀之,吉斯貝爾的說法呼應了羅伯特‧阿隆(Robert Aron)和阿爾諾‧丹第歐(Arnaud Dandieu)的《法蘭西民族的頹廢》(Décadence de la nation française),該書主張法國的萎靡源於「形上的和精神上的苦痛」。(注21)二〇一三年,許多媒體比較兩個時代後下了多彩多姿的標題,如「救命,三〇年代回來了!」(注22)最後注意力自然而然轉向扮演國家先知的傳統角色,也就是知識分子,藉由檢討他們的過失,以求找出能夠逃離絕望感且有意義的新路線。共產主義的《人道報》感慨法國知識分子已經被「哲學頹廢」滲透,民粹主義週刊《瑪麗安娜》也惋惜「沒有一套國際視野可以填補目前法國思維的絕對真空」。(注23)於是哲學家加斯帕爾‧科寧格(Gaspard Koening)提出建言:既然理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都死了,也許終於到了法國擁抱自由主義的時刻?(注24)
國家的病
對於國家的現況與未來越來越悲觀,這種症狀被歷史學家米歇爾‧維諾克(Michel Winock)稱之為「法國國家病」(French national disease),(注25)我們從這種現象可以看到什麼?知名歷史學者的親自診斷已經透露了許多線索,反映出法國知識精英傾向從心理層面看待這件事,認為這是主觀問題,無法藉由客觀事實或數據進行分析。的確,雖然法國衰退主義者的著作點出了特定的趨勢、時間、轉捩點事件,如二〇〇一年總統選舉、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但這類著作的矛盾之一在於無法提出確鑿的證據。為了符合法國思維喜愛整體性的特徴,現象本身通常被視為既定事實,然後才試圖找出更普遍的大框架來套入──可能是人性、歷史、經濟、文化,以至於種族。
其他方面也一樣,這是經典的法式討論,強調失落、異化和死亡,這些概念根基於國家文化。同時,一些論述走向抒發個人情緒,對於常見的哲學觀感到嚴重的挫折失望:無論保守派、自由派或進步派,他們的共同點在於對之前抱持的信念徹底幻滅。這類文獻也喜歡講大方向,反復使用修辭上的二分法,如善良與邪惡、文明與野蠻、進步和頹廢等等。換言之,最為誇張、最覺得國家末日已至的言論(像是移民無法融入,或者法國人缺乏集體自我認同),多半來自於居住在法國核心區域且很少出去外面看看的那群人。他們對於一般人的生活瞭解甚少。此外,還有陰謀論(這個群體喜愛的主題之一)將矛頭指向精英階層,又或者其他更棘手、更難定義的對象(「新自由主義」或「伊斯蘭」)。
這些討論也具備法式特徴,大半時候生不出具體的解決方案或行動計畫,聲稱最重要的改革要從心靈或態度著手。看在長期關注法國知識圈的人眼中,當前這些意見中瀰漫的平行世界氛圍非常熟悉,尤其他們偏愛糾結在消極的情緒,疾聲大呼模糊或難以實現的理想,例如主張將法國轉變為種族完全相同的國家;提案和分析時的邏輯思考,也總是走到最遙遠的極端。
悲觀哲學最全面的版本出自生於羅馬尼亞的散文家蕭沆(Emil Cioran),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在拉丁區定居,因《解體概要》(Précis de décomposition, 1949)一書而成品。書中充滿格言警句,被譽為存在主義的傑作,原因不僅是斷然拒絕生命可能有意義:「光芒是例外,衰亡才是規則。生命無時無刻不崩解,只是不斷地失去光,平淡無味地消融,沒有權杖,沒有榮耀,沒有光環。」(注26)他的作品的主題主要是孤獨、無聊,當然還有死亡這個「偉大的肯定」,(注27)看似直接回歸了神祕主義傳統,卻又完全剝除了潛藏的樂觀思考。蕭沆將從負面執著推演出的邏輯結論寫進《誕生之不便》(De l’inconvénient d’être né, 1973),認為(徒勞的)創造是個悲劇,存在只是對悲劇引發的反應:「我們不急著衝向死亡,卻急著逃離誕生這場災禍。我們蠕動掙扎,像是倖存者想要忘記恐怖。我們害怕死亡,但那只是病態的投射,追溯到我們最初的一瞬間。」(注28)
世紀更迭的時刻,法國思想墜進黑暗深淵,蕭沆的中歐陰鬱重獲新生。伽利瑪出版社於他過世十五年後,也就是二〇一一年時,將其作品全集收入知名的七星文庫(Pléiade)系列。他對法國衰退的集體反思最顯著的貢獻,在〈來自法國〉(De la France)這篇文章,實際上完成於一九四一年德軍占領時期,直到二〇〇九他死後才得以發表。文中預測了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法國社會氛圍,指出在他看來法國精神基本上是鄉土與享樂主義,以及(受到笛卡兒影響)傾向「狹隘的完美主義」──偏愛風格優雅、形式清晰,卻不具哲學深度。(注29)其智識上的偉大來自構築了「理性主義神話」,並且霸占了現代歐洲人的思維。蕭沆認為法國人將無法繼續沉迷在那些理念中:「心靈的井乾涸了,他們在沙漠中醒來,環抱身體,恐懼未來。」(注30)蕭沆的信徒之一是哲學家弗雷德里克‧史福特(Frédéric Schiffter),自稱「小資產階級虛無主義者」,其著作抨擊現代性枯燥、倫理無益,還有傅柯無用(他不讀傅柯作品,因為傅柯「穿套頭圓領毛衣」)。(注31)
與蕭沆的哲學、美學感性相反,阿蘭‧佩雷菲特表達悲觀情緒的管道是歷史框架;不過整體結論一樣陰霾密布。首次出版於一九七六的《法國惡》是一本複合作品,一部分以戴高樂時期前部長幻滅後的自傳探索法國的「制度失靈」;另一部分則試圖解釋法國現代政治文化有何缺陷。佩雷菲特的中心論點在於法國與其他工業發達社會有所不同,受到異化的公民、政府的入侵雙面夾攻所「詛咒」。(注32)他延續托克維爾的論點,認為高度中央集權是絕對君主專制政體的殘留,大革命與後來幾次共和政府還將之強化了。隨時間推移,法國人因此成「叛逆的保守派」,患上名為「抽搐麻痺」的特俗疾病。(注33)病徵表現是偶像崇拜的傳統(「古人和現代人爭吵時,多半都是古人占上風」);(注34)仰慕絕對權力又喜愛週期性的危機(「戀痙攣」〔spasmophilia〕);(注35)執著於普世平等卻又拒絕差異性;(注36)偏好不真實之物(「在法國,邏輯精神會被魔法精靈取代」);(注37)以及將每件事情簡單地二元劃分如「自由」與「權威」、「秩序」與「運動」之類。(注38)
佩雷菲特的結論很簡潔:「我們不是能與自己共處的民族。」(注39)雖然他自稱相信法國人能完成「精神革命」來改變自己,其言行的沉重、準人類學的特質卻似乎是反證。一九九六年新版的序言裡,他明確陳述了內心的消極,表示儘管一九八〇年代社會黨做了很多去除中央集權的改革措施,法國仍停留在柯爾貝爾的傳統下,國家牢牢箝制一切。(注40)結論更是消沉,佩雷菲特指出,其實這種負面氛圍的暗流從戴高樂時期就出現,只是被唯意志論和外表的光鮮亮麗給掩蓋。
另一種更萎靡的消極潮流於一九八〇年代在國族主義右派內重現,核心命題就是法國的「衰敗」,而且主張衰敗是一種本質,無法逆轉,表現的形式就是既有秩序會全面崩潰。(注41)這種慘淡思想靈感來自於反大革命、反現代主義的著作,主要作者為弗約、德魯蒙、巴雷斯和拉荷歇爾,(注42)他們認為當今社會被困在道德和精神的腐敗,理性主義與個人主義已經凌駕任何形式的集體歸屬感,(注43)人類與自身的真實(宗教)疏離之後,躲進「粗俗的唯物主義,一種結合怠惰思考、貪求安逸之後的可怕產物」。(注44)
悲觀敘事之中,另一個鮮明的命題是法國國族的衰亡,也就是移民造成的威脅。「伊斯蘭主義」(一個模糊的概念,毫無來由地認為所有伊斯蘭教徒都有極端思想)會奪走國家,是自一九八〇年代起國民陣線主打的論點。除此之外,他們譴責的還有各種社會寬容的表現:性工作、毒品、暴力、家庭破裂、校園違紀;全部濃縮起來之後,就成為對國家滅亡的憂慮。一九四四年九月演講時,尚‧馬利‧勒龐說:「法國繼續倒退,走上西方和北方那種道路,現在重大危機不只出現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連文化和道德也受害了。法國的國體、法國人民的整體性,已經來到生死存亡的關頭。」(注45)
衰退的體現
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裡,衰敗論調已經深植人心。這一派人還提供了擴大和深化負面感受需要的材料。進入下一階段,主題轉為「高級」文化的隕落,原本不斷重複這議題的只有保守派民族主義者,或者稱之為「傾頹主義者」(decadentist),不過近期巴黎文化精英也起了興趣。這個新文類的早期經典是阿蘭‧芬基爾克羅的《思想潰敗》(La Défaite de la pensée, 1987),筆調憂鬱,警告啟蒙時代留下的遺產可能遭到第三世界主義者、道德相對主義者及大眾藝人這些烏合之眾給毀掉。芬基爾克羅發明的一些概念使其漸漸成為法國最重要的新共和辯論家,同時也代表世俗主義對抗多元文化主義帶來的威脅。(注46)他表示自己特別在意的是,提倡「文化差異」的同時,也就會否定解放了現代人類的智識特質,例如懷疑論、反諷、理性個人主義。根據這個前提,他推斷文明正遭受野蠻新時代的威脅:「生命和思想慢慢屈服於狂熱分子和殭屍挑起的,可怕又輕慢的衝突。」(注47)芬基爾克羅直覺判斷法國文化領域有某種根本的元素被打破了,這想法獲得其他人支持,最主要是反現代的作家及評論家菲利普‧穆瑞,還有讓‧弗朗索瓦‧馬太的《內在的野蠻》(La Barbarie intérieure, 1999)一書,從哲學層面痛陳大眾文化敗壞了文明。(注48)
隨著衰敗這個主題進入文化領域,法國文學不可避免地成為受到檢視的對象。一九九五年《精神》的前編輯尚‧瑪利‧多梅納(Jean-Marie Domenach)以駭人聽聞的說法形容當代法國文學,他批評真正的文學評論傳統已經消失,就像英國、美國一樣,由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紐約書評之類把持;他也抨擊多數法國小說走入「邪門歪道」,欠缺有效的人物塑造,脫離社會現實,喜愛異常的格式與省略。(注49)《快訊》週刊也刊出標題為「小說之死」的長文呼應多梅納的慘淡觀點,透過沮喪論調指出新流行的寫作形式看似內斂、表達主觀,實則「歇斯底里、急躁、悲慘、自大狂,極端清教徒卻又極端情色」。(注50)十多年後,小說家派崔克‧貝森(Patrick Besson)對法國當代文學概況的看法一樣消極,標題挑釁地定為「法國文學死了嗎?」(注51)而英語世界也有類似觀察,覺得當代法國文學已經迷失方向,變得過於內向也過於痴迷在抽象概念上,不再繼承過去優秀的說故事能力。
然而,在這個層面上法國人又出現矛盾:他們有兩千多個關於書籍的獎項,包括久負盛名的龔古爾、勒諾多、費米娜和美第奇,每年的文學季(rentrée littéraire)也越來越盛大,怎麼看都覺得法國文學活力十分充沛。事實上,這個問題必須從國際舞臺來分析,雖然福樓拜、大仲馬、普魯斯特和卡繆已然是全球文學遺產的一部分,繼承他們路線的暢銷(或獲獎)作家如凱特琳‧彭歌(Katherine Pancol)、紀優‧穆索(Guillaume Musso)、安娜‧戈華達(Anna Gavalda)、艾曼紐‧卡黑爾(Emmanuel Carrère)、阿梅麗‧諾冬(Amélie Nothomb)、瑪麗‧達里厄斯克(Marie Darrieussecq)、克里斯多夫‧歐諾迪比奧(Christophe Ono-dit-Biot),很難在英語世界吸引到足夠讀者。即便諾貝爾獎得主勒克萊齊奧和派崔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也一樣,在英語世界中幾乎沒有知名度。雖然翻譯法國小說並出版以美國為最多,但數量相對而言依舊少(二〇一二年有六十二部,二〇一三年有七十七部),(注52)且多半是小量發行,也只有極少數能夠進入美國的暢銷排行榜。
觀察能夠打進美國市場的作品,會發現內容符合對於法國人的刻板印象:過分發達的腦力,代表人物是妙莉葉‧芭貝里(Muriel Barbery)《刺蝟的優雅》(The Elegance of Hedgehog)裡極有教養的女門房荷妮;縱使在最可怕的情境中依舊性格輕浮輕率,洛朗‧比奈(Laurent Binet)的《HHhH》是作者想像力融入納粹安全部長海德里希被暗殺的故事;經久不衰的反猶太思想,像是依蕾娜‧內米洛夫斯基(Irène Némirovsky)的《法蘭西組曲》(Suite français)在她死後才發表,內容是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作者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內;當然還有性變態,好比米歇爾‧維勒貝克的所有作品。
二十一世紀初法國經濟每況愈下,成為衰敗論者的新戰場,主要論述來自尼可拉‧巴斐雷(Nicolas Baverez)《失速下墜的法國》(La France qui tombe, 2003),這本小冊發揮很大影響力,用意是更加聚焦於佩雷菲特的診斷,基底則是雷蒙‧阿隆的保守自由主義。巴斐雷的主要論點是法國之所以倒退,原因在於社會精英從十九世紀後期刻意推行相關政策,「法國模式」產生了巨大的公部門,政府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尤其是醫療和福利方面),也更傾向內部社會和諧而排斥劇烈變革;呼應史丹利‧奧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經典說法:「社會僵局。」(注53)據巴斐雷分析,法國面對後冷戰的世界變遷只有固定套路:其他國家進行的經濟現代化是減少公部門規模、促進創新和競爭力,但歷屆法國政府不分左右只會重申傳統的「法國模式」,從而使國家債務攀升,外來投資卻急劇下跌。因此,法國國內生產總值三分之一以上用於福利和公部門人事,只有百分之二點五進入投資。(注54)他估計這種「政治自閉症」(又是病理學詞彙)是「政治、經濟和社會,以至於智力和道德層次的癱瘓」。他斷言後果必然是「法國失速下墜」。(注55)
還有更細緻的版本出現在已故的雅克‧馬賽(Jacques Marseille)的《內戰在法國的妙用》(Du bon usage de 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這本書在二〇〇五年歐盟公投後問世,借鑑一系列歷史案例試圖說明法國衰敗並非必然,政治危機有可能化為變革動力,戴高樂一九五八年回歸就是鐵證。二十一世紀初很難有這麼樂觀的想法,法國社會產生了新的隔閡──就業者與失業者、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獲得政府保護的領域和曝露在全球化風險下的領域。他的結論是,法國精英最可能採取的行動路線就是「脆弱地躲回殼裡」。(注56)
經濟停滯的預言在二〇一二年的總統選舉中得到克里斯逖安‧聖德田(Christian Saint-Etienne)的《語無倫次的法文》(L’Incohérence française)一書呼應。書中將持續不斷的經濟困境歸咎於法國精英的「智力怯懦」。(注57)菲利普‧馬尼爾(Philippe Manière)的《生活最苦的國家》(Le Pays où la vie est plus dure)也是同一主題的演繹。但比起西蒙娜‧瓦普勒(Simone Wapler)的《為何法國會破產》(Pourquoi la France va faire faillite),(注58)已經少了很多末日氛圍的災難性終結。巴斐雷在二〇一二發行的另一本小冊中,簡直像是在傷口上撒鹽,哀怨表示就連具有相同意識形態的人也沒聽見自己的訴求:儘管薩科吉承諾改革法國制度,卻進一步擴大公共支出和國家借貸,從而加劇國家衰落的速度。他認為除非統治者願意放棄中央經濟統制論和反自由經濟的偏見,否則狀況不會好轉。(注59)
將衰敗等同於政府失靈的這個主題催生了大量文獻,許多人盡力分析各部門遭遇的危機,並提供(偶爾算是)睿智的建言。(注60)問題是用於診斷問題的語言往往過度膨脹,針對教育體系的討論尤其如是。校長馬克‧勒布利斯(Marc Le Bris)認為法國公眾(公立)學校可謂「文化浩劫」,基本的識字、算術、一般紀律都不行,教師失去權威,經典文化被摒棄。(注61)他示警說,原本共和派理念之一就是傳承國家文化,如今看來並沒有達成。(注62)另一本小冊的態度同樣激烈,教師尚‧保羅‧布里格利(Jean-Paul Brighelli)譴責「製造白癡」的教程,主張根本問題出在在一九六八以後的教育哲學從傳統模式轉向於學生無益的「能力」,以及個別自律。(注63)這種新平均主義表面光鮮亮麗,不稱學生為學生(élèves),套上了「學習者」的頭銜(apprenants)。(注64)布里格利指出這種系統的一大惡果,是資產階級的社會精英和遭受「去思考化」的底層(注65)之間的文化差距越來越大。一九八〇年代早期開始實行另項一計畫,試圖為「偏鄉」設置「優先教育區」(ZEPS),結果也徹底失敗。(注66)就教育而言,共和派的最終理念應當是促進機會平等,但這樣的雙軌制根本背道而馳。(注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