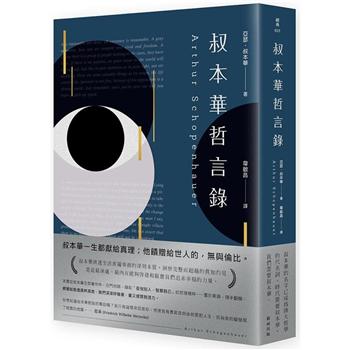同情
真正的道德原動力就是同情。
對眾生懷著無限的同情,是做出合乎道德的良好行為的一個最牢固和最可靠的保證。
不幸是同情的條件,同情是仁愛的源泉。
要消除我們對他人的仇恨心態,沒有什麼方法比採用某種會引起自己同情他人的審視角度,更加容易達到目的。
唯一適合抑制我們的憎恨或鄙視情緒的是憐憫,而不是我們口口聲聲尋求的「尊嚴」和「價值」。
每個人都帶有嫉妒和同情這兩種彼此對立的相反特質,因為這兩種特質產生於一個人不可避免地對自己狀況與他人狀況做出的比較。
嫉妒就是在人、我之間築起一堵厚牆,但對於懷有同情心的人來說,這堵牆壁是脆弱和透明的。事實上,這堵牆有時候會被同情心完全推倒。
公正
正是為實踐公正所付出的犧牲,公正這一美德受人敬重,因為如果這一美德只涉及無關痛癢的小犧牲,那便得不到別人的敬重。
公正這一美德的實質,就在於公正的人並不會把與生活須臾不離的負擔和痛苦,通過玩弄狡猾或強力轉嫁到別人身上,就像那些不義者所做的那樣;而是自己扛起命運給予自己的那一份負擔和痛苦。
公正之人得不打折扣地承擔起人生所應有的全部禍害和磨難。
仁愛
基督教把仁愛視為所有美德中的最偉大者,甚至把仁愛也施予我們的敵人。這是基督教做出的最大貢獻。
在亞洲,比基督教還早一千多年,人們就把對鄰人的無邊仁愛,不僅作為真理和準則,也是實踐的內容。
心懷仁愛的人,在其他每一個人的身上重又認出了自己的本質。這樣,心懷仁愛的人就把自己的命運與人的總體命運等同了起來。
由於仁愛這一美德,我們甚至把本來落在別人肩上的苦難也接了過來,使自己得到了比在正常情形下,自己個人所要承受的更多份額。
勇氣
勇氣之所以是美德,就在於我們心甘情願地直面此時此刻對我們構成威脅的惡行,並有所作為,目的就是以行動防止將來發生更大的罪惡。
勇氣具有堅忍的特性——堅忍意味著我們清楚意識到除了此刻威脅著我們的惡行以外,還有更大的惡行;而我們此刻的倉惶退卻或躲避,將招致更加可怕的惡行。
勇氣使我們能夠承受各種犧牲和實現自我征服;勇氣因而起碼與美德有了一定的關聯。
一個全然形而下,因而是純粹依據經驗的解釋並不足以解釋勇氣何以成為美德,因為這樣一種解釋只能立足於勇氣的有利和用處方面。
懦弱
懦弱似乎與高貴的性格並不相稱,因為懦弱暴露出了人過度關注自身。
吝嗇
金錢作為這一世上所有好處的抽象代表,現在就成了吝嗇之人那已經遲鈍、呆滯的胃口咬住不放的枯槁根塊——這已成了他們抽象中的自我。
這種金錢慾望就像其對象物一樣具有某種象徵性,並且也是無法消除的。這是對世俗樂趣執著的眷戀,它頑固、偏執,就好像要延續至此身之後;它是經昇華以後換上了精神形式的肉慾;它是匯聚所有無法饜足的慾望的抽象焦點。
慳吝之人捨棄了快感享受,目的就是更能穩妥地躲避苦痛。據此,「堅忍和捨棄」就成為了吝嗇之人的座右銘。
既然慳吝之人知道發生不幸的可能性難以窮盡,通往危險的道路又數不勝數,那他們就動用一切手段,盡可能地在自己的周圍內外三重築起堅固的城堡,以抵御不測與不幸。誰又能說防備的功夫做得太過?
只有懂得命運如何出爾反爾捉弄我們的人,最終才會達成自己的目的。哪怕防備功夫做得太過,這一差錯也只給自己本人帶來害處,不會讓別人受累。
揮霍
雖然像人們所說的那樣,不少吝嗇之人歸根到底只是直接嗜愛金錢本身,那不少揮霍成性的人也的確同樣只是為了揮霍而胡亂大肆揮霍。
奢侈、揮霍源自一種動物性的認識侷限——對於只侷限於認識現時此刻的人來說,那只在頭腦中存在的將來概念是不會產生任何效果的——並且,奢侈、揮霍是建立在人的這一錯覺之上:感官樂趣真有其肯定和實在的價值。
為了那些空洞、匆匆即逝並且經常只是想像出來的快樂,揮霍之人付出了將來入不敷出、囊空如洗的淒涼代價。
奢侈揮霍不但導致貧困,而且還由貧困導致犯罪。
財富
(雖然)人的自身比起財產和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具有壓倒性的優勢,由此可知,注重保持身體健康和發揮個人自身才能比全力投入獲得財富更為明智。但我們不應該把這一說法錯誤地理解為:我們應該忽略獲得我們的生活必需品。
真正稱為財富的,亦即過分的豐裕盈餘對我們的幸福卻說明不大。
財富除了能滿足人真正、自然的需求以外,對於我們的真正幸福沒有多大影響。
對於我們認為可能得到的東西,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視線範圍。我們的要求不會超出這一視線範圍。
在我們心目範圍之內的具體之物一旦出現,而我們又確信能夠得到它,那我們就會感到幸福。但是如果得到這具體之物有重重困難,根本就沒有得到它的希望和可能,那他就會感覺不幸和痛苦。所有在他視線以外的東西,都不會對他產生任何影響。
窮人不會因為得不到巨大的財富而焦慮不安,但富人在計畫失算落空的時候,不會考慮到自己已經擁有相當可觀的財物,並以此安慰自己。
財富猶如海水,一個人喝得越多,他就越感到口渴。
我們在失去了財富或者安逸的處境以後,當我們挺住了最初的陣痛,我們慣常的心境與當初相比較,並沒有發生很大的改變。
當命運減少了我們的財富以後,我們自己也就相應降低了我們的要求。
我們之所以感到不滿,原因就在於我們不斷試圖提高我們的要求,同時,其他妨礙我們成功的條件因素卻保持不變。
我們應把現有的財富視為能夠抵禦眾多可能發生的不幸和災禍的城牆,而不是一紙任由我們尋歡作樂的許可證。
金錢是人的抽象中的幸福,那些再也沒有能力享受具體幸福的人,只有一門心思撲在金錢上面了。
真正的道德原動力就是同情。
對眾生懷著無限的同情,是做出合乎道德的良好行為的一個最牢固和最可靠的保證。
不幸是同情的條件,同情是仁愛的源泉。
要消除我們對他人的仇恨心態,沒有什麼方法比採用某種會引起自己同情他人的審視角度,更加容易達到目的。
唯一適合抑制我們的憎恨或鄙視情緒的是憐憫,而不是我們口口聲聲尋求的「尊嚴」和「價值」。
每個人都帶有嫉妒和同情這兩種彼此對立的相反特質,因為這兩種特質產生於一個人不可避免地對自己狀況與他人狀況做出的比較。
嫉妒就是在人、我之間築起一堵厚牆,但對於懷有同情心的人來說,這堵牆壁是脆弱和透明的。事實上,這堵牆有時候會被同情心完全推倒。
公正
正是為實踐公正所付出的犧牲,公正這一美德受人敬重,因為如果這一美德只涉及無關痛癢的小犧牲,那便得不到別人的敬重。
公正這一美德的實質,就在於公正的人並不會把與生活須臾不離的負擔和痛苦,通過玩弄狡猾或強力轉嫁到別人身上,就像那些不義者所做的那樣;而是自己扛起命運給予自己的那一份負擔和痛苦。
公正之人得不打折扣地承擔起人生所應有的全部禍害和磨難。
仁愛
基督教把仁愛視為所有美德中的最偉大者,甚至把仁愛也施予我們的敵人。這是基督教做出的最大貢獻。
在亞洲,比基督教還早一千多年,人們就把對鄰人的無邊仁愛,不僅作為真理和準則,也是實踐的內容。
心懷仁愛的人,在其他每一個人的身上重又認出了自己的本質。這樣,心懷仁愛的人就把自己的命運與人的總體命運等同了起來。
由於仁愛這一美德,我們甚至把本來落在別人肩上的苦難也接了過來,使自己得到了比在正常情形下,自己個人所要承受的更多份額。
勇氣
勇氣之所以是美德,就在於我們心甘情願地直面此時此刻對我們構成威脅的惡行,並有所作為,目的就是以行動防止將來發生更大的罪惡。
勇氣具有堅忍的特性——堅忍意味著我們清楚意識到除了此刻威脅著我們的惡行以外,還有更大的惡行;而我們此刻的倉惶退卻或躲避,將招致更加可怕的惡行。
勇氣使我們能夠承受各種犧牲和實現自我征服;勇氣因而起碼與美德有了一定的關聯。
一個全然形而下,因而是純粹依據經驗的解釋並不足以解釋勇氣何以成為美德,因為這樣一種解釋只能立足於勇氣的有利和用處方面。
懦弱
懦弱似乎與高貴的性格並不相稱,因為懦弱暴露出了人過度關注自身。
吝嗇
金錢作為這一世上所有好處的抽象代表,現在就成了吝嗇之人那已經遲鈍、呆滯的胃口咬住不放的枯槁根塊——這已成了他們抽象中的自我。
這種金錢慾望就像其對象物一樣具有某種象徵性,並且也是無法消除的。這是對世俗樂趣執著的眷戀,它頑固、偏執,就好像要延續至此身之後;它是經昇華以後換上了精神形式的肉慾;它是匯聚所有無法饜足的慾望的抽象焦點。
慳吝之人捨棄了快感享受,目的就是更能穩妥地躲避苦痛。據此,「堅忍和捨棄」就成為了吝嗇之人的座右銘。
既然慳吝之人知道發生不幸的可能性難以窮盡,通往危險的道路又數不勝數,那他們就動用一切手段,盡可能地在自己的周圍內外三重築起堅固的城堡,以抵御不測與不幸。誰又能說防備的功夫做得太過?
只有懂得命運如何出爾反爾捉弄我們的人,最終才會達成自己的目的。哪怕防備功夫做得太過,這一差錯也只給自己本人帶來害處,不會讓別人受累。
揮霍
雖然像人們所說的那樣,不少吝嗇之人歸根到底只是直接嗜愛金錢本身,那不少揮霍成性的人也的確同樣只是為了揮霍而胡亂大肆揮霍。
奢侈、揮霍源自一種動物性的認識侷限——對於只侷限於認識現時此刻的人來說,那只在頭腦中存在的將來概念是不會產生任何效果的——並且,奢侈、揮霍是建立在人的這一錯覺之上:感官樂趣真有其肯定和實在的價值。
為了那些空洞、匆匆即逝並且經常只是想像出來的快樂,揮霍之人付出了將來入不敷出、囊空如洗的淒涼代價。
奢侈揮霍不但導致貧困,而且還由貧困導致犯罪。
財富
(雖然)人的自身比起財產和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具有壓倒性的優勢,由此可知,注重保持身體健康和發揮個人自身才能比全力投入獲得財富更為明智。但我們不應該把這一說法錯誤地理解為:我們應該忽略獲得我們的生活必需品。
真正稱為財富的,亦即過分的豐裕盈餘對我們的幸福卻說明不大。
財富除了能滿足人真正、自然的需求以外,對於我們的真正幸福沒有多大影響。
對於我們認為可能得到的東西,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視線範圍。我們的要求不會超出這一視線範圍。
在我們心目範圍之內的具體之物一旦出現,而我們又確信能夠得到它,那我們就會感到幸福。但是如果得到這具體之物有重重困難,根本就沒有得到它的希望和可能,那他就會感覺不幸和痛苦。所有在他視線以外的東西,都不會對他產生任何影響。
窮人不會因為得不到巨大的財富而焦慮不安,但富人在計畫失算落空的時候,不會考慮到自己已經擁有相當可觀的財物,並以此安慰自己。
財富猶如海水,一個人喝得越多,他就越感到口渴。
我們在失去了財富或者安逸的處境以後,當我們挺住了最初的陣痛,我們慣常的心境與當初相比較,並沒有發生很大的改變。
當命運減少了我們的財富以後,我們自己也就相應降低了我們的要求。
我們之所以感到不滿,原因就在於我們不斷試圖提高我們的要求,同時,其他妨礙我們成功的條件因素卻保持不變。
我們應把現有的財富視為能夠抵禦眾多可能發生的不幸和災禍的城牆,而不是一紙任由我們尋歡作樂的許可證。
金錢是人的抽象中的幸福,那些再也沒有能力享受具體幸福的人,只有一門心思撲在金錢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