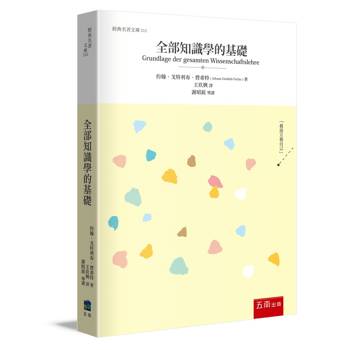前言
這部書本來不是寫來公開發表的,假如不是在它甚至尚未完成時就很不鄭重地已和一部分民眾見了面,我是不會在本書開頭有什麼話要和讀者大眾說的。事情的原委我先就只說這麼一句!—我一直相信,而且現在仍然相信,我已發現了哲學上升為一門明白無誤的科學所必經的道路。我曾謹慎地宣布過這一點,說明我是如何按照這個想法工作過,如何在情況改變了之後仍不得不按此想法工作並將計畫付諸實行的。我當時那樣做是很自然的。但別的專家,別的認識問題研究者對我的想法進行分析、審查和評判,不管是出於內在原因還是什麼外在原因,他們不願走我為科學知識指引的道路,試圖反駁我,這同樣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對我所提出的東西,不經任何審查就直截了當地加以反對,至多吧,煞費苦心地加以歪曲,製造一切機會來瘋狂地進行誹謗和詆毀,這究竟有什麼好處我卻看不出來。究竟是什麼東西使那些裁判官們變得如此完全失去理性的呢?我是從來不重視人云亦云的膚淺之見的,難道偏要我鄭重其事地來談論這些嗎?我為什麼非這樣做不可呢?—特別是我有的是事情要做;只要這些笨蛋們不逼著我揭發他們的拙劣手法來進行自衛,他們是完全可以在我面前大搖大擺地走他們的路的。
也許, 他們的敵意態度還有另一種原因?—對於正直的人,我有下面的話要說,當然只對這類人我的話才有意義。—不論我的學說是真正的哲學還是胡說八道,只要我是老老實實進行研究的,那它就一點也不涉及我的個人品德。我認為,我有幸而發現了真正的哲學,這並不抬高我的個人價值,正如我不幸在歷代的錯誤上面添加新的錯誤,並不降低我的個人價值一樣。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考慮我個人,但對於真理我懷有一顆火熱的心,凡我認為是真理的東西,我將永遠竭盡所能,堅定而大力地宣講。
在這本書裡,包括〈從理論能力略論知識學的特徵〉那篇東西裡,我相信我已把我的體系作了充分闡述,以致任何一位專家不論對於體系的根據與規模也好,還是對於進一步發展這個體系必須採取的方式也好,都完全可以一目了然。我的處境不允許我做出確切的承諾,說我一定會在什麼時候和怎麼樣進一步發展我這個體系。
我自己聲明,我對體系的闡述是不完善和有缺點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它本是為我講課需要不得已分頁印發給我的聽課學生用的,對於學生,我可以透過口頭講解來加以補充;另一方面是因為我要盡可能地避免使用一套固定的名詞術語,這些東西是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們用來使任何體系喪失精神變為僵屍的最方便手段。這條準則,在將來闡明我的體系時我也還要信守不渝,直到我對體系做出最終的完滿表述為止。現在,我還完全不想擴建它,只盼望能鼓舞讀者們起來和我一起從事未來的建築。在人們嚴格規定每一個個別命題之前,必須首先對整體有一個鳥瞰,從關聯中加以說明。這樣一種方法,當然以願意讓體系得到公正對待的善意為前提,而不以專門從中尋找錯誤的敵意為前提。
我聽到了很多抱怨,說這本書現已為外界知道了的部分和《論知識學的概念》那本著作都晦澀難懂。如果對後一著作的抱怨是專對該書的第八節講的,那可能確實是我的不對,因為我提出了我從整個體系規定下來的一些原理而沒把該體系講出來;並且我曾期望讀者和評論家們有耐心,讓一切都像我所闡述的那樣不要確定下來。如果指責是對整個著作而發的,那我預先就承認,在思辨的專業領域裡我將永遠寫不出能使那些不能理解它的人們能夠理解的東西。如果那部著作是他們的理解力的極限,那麼它也就是我的可理解性的極限;我們彼此的精神由這個界限區分開來,我請求他們不要為閱讀我的著作而糟蹋時間。—假如這種不理解有任何一種什麼原因的話,那麼知識學之所以總是不能為某些讀者所理解的原因就存在於知識學自身之內,也就是說,知識學以有自由內觀的能力為前提。—然後,任何哲學著作的作者都有權要求讀者緊緊抓住推論的線索不放,不要在讀到後面的時候已把前面的忘記掉。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說我這些著作中還有不能被理解和肯定得不到正確理解的東西,那麼它們是什麼,我至少是不知道;而且我堅決認為,一本書的作者自己在這個問題的回答上是有發言權的。完全思考清楚了的東西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知道,一切都是完全思考清楚的,因而我是願意把每一個主張都提到盡可能清晰的高度的,如果我當時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
特別我認為需要提醒的是,我並不是把一切都說了出來,而是想留一些給我的讀者去思索。有些我預料一定會出現的誤解,只要我多說幾句話就一定可以避免。這幾句話我之所以沒說,是因為我想鼓勵獨立思考。知識學根本不應該把自己強加於人,它應該像它對於它的創立者那樣成為一種需要。
我請求本書未來的評論家們先消化整體,然後從整體的觀點去考察每個個別的思想。哈勒的書刊檢查官發表了他的高見,猜測我只是想開開玩笑;《論知識學的概念》一書的另外一些評論家顯然也同樣抱有這個看法;他們對待事情這樣輕率,他們的高見這麼滑稽,彷彿他們一定要用開玩笑來回敬開玩笑。
* 這個前言發表於《全部知識學的基礎》第二批稿件,即其第三篇初次出版的時候,第三篇付印較遲,約與《略論知識學的特徵》同時交稿。—譯者注
這部書本來不是寫來公開發表的,假如不是在它甚至尚未完成時就很不鄭重地已和一部分民眾見了面,我是不會在本書開頭有什麼話要和讀者大眾說的。事情的原委我先就只說這麼一句!—我一直相信,而且現在仍然相信,我已發現了哲學上升為一門明白無誤的科學所必經的道路。我曾謹慎地宣布過這一點,說明我是如何按照這個想法工作過,如何在情況改變了之後仍不得不按此想法工作並將計畫付諸實行的。我當時那樣做是很自然的。但別的專家,別的認識問題研究者對我的想法進行分析、審查和評判,不管是出於內在原因還是什麼外在原因,他們不願走我為科學知識指引的道路,試圖反駁我,這同樣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對我所提出的東西,不經任何審查就直截了當地加以反對,至多吧,煞費苦心地加以歪曲,製造一切機會來瘋狂地進行誹謗和詆毀,這究竟有什麼好處我卻看不出來。究竟是什麼東西使那些裁判官們變得如此完全失去理性的呢?我是從來不重視人云亦云的膚淺之見的,難道偏要我鄭重其事地來談論這些嗎?我為什麼非這樣做不可呢?—特別是我有的是事情要做;只要這些笨蛋們不逼著我揭發他們的拙劣手法來進行自衛,他們是完全可以在我面前大搖大擺地走他們的路的。
也許, 他們的敵意態度還有另一種原因?—對於正直的人,我有下面的話要說,當然只對這類人我的話才有意義。—不論我的學說是真正的哲學還是胡說八道,只要我是老老實實進行研究的,那它就一點也不涉及我的個人品德。我認為,我有幸而發現了真正的哲學,這並不抬高我的個人價值,正如我不幸在歷代的錯誤上面添加新的錯誤,並不降低我的個人價值一樣。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考慮我個人,但對於真理我懷有一顆火熱的心,凡我認為是真理的東西,我將永遠竭盡所能,堅定而大力地宣講。
在這本書裡,包括〈從理論能力略論知識學的特徵〉那篇東西裡,我相信我已把我的體系作了充分闡述,以致任何一位專家不論對於體系的根據與規模也好,還是對於進一步發展這個體系必須採取的方式也好,都完全可以一目了然。我的處境不允許我做出確切的承諾,說我一定會在什麼時候和怎麼樣進一步發展我這個體系。
我自己聲明,我對體系的闡述是不完善和有缺點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它本是為我講課需要不得已分頁印發給我的聽課學生用的,對於學生,我可以透過口頭講解來加以補充;另一方面是因為我要盡可能地避免使用一套固定的名詞術語,這些東西是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們用來使任何體系喪失精神變為僵屍的最方便手段。這條準則,在將來闡明我的體系時我也還要信守不渝,直到我對體系做出最終的完滿表述為止。現在,我還完全不想擴建它,只盼望能鼓舞讀者們起來和我一起從事未來的建築。在人們嚴格規定每一個個別命題之前,必須首先對整體有一個鳥瞰,從關聯中加以說明。這樣一種方法,當然以願意讓體系得到公正對待的善意為前提,而不以專門從中尋找錯誤的敵意為前提。
我聽到了很多抱怨,說這本書現已為外界知道了的部分和《論知識學的概念》那本著作都晦澀難懂。如果對後一著作的抱怨是專對該書的第八節講的,那可能確實是我的不對,因為我提出了我從整個體系規定下來的一些原理而沒把該體系講出來;並且我曾期望讀者和評論家們有耐心,讓一切都像我所闡述的那樣不要確定下來。如果指責是對整個著作而發的,那我預先就承認,在思辨的專業領域裡我將永遠寫不出能使那些不能理解它的人們能夠理解的東西。如果那部著作是他們的理解力的極限,那麼它也就是我的可理解性的極限;我們彼此的精神由這個界限區分開來,我請求他們不要為閱讀我的著作而糟蹋時間。—假如這種不理解有任何一種什麼原因的話,那麼知識學之所以總是不能為某些讀者所理解的原因就存在於知識學自身之內,也就是說,知識學以有自由內觀的能力為前提。—然後,任何哲學著作的作者都有權要求讀者緊緊抓住推論的線索不放,不要在讀到後面的時候已把前面的忘記掉。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說我這些著作中還有不能被理解和肯定得不到正確理解的東西,那麼它們是什麼,我至少是不知道;而且我堅決認為,一本書的作者自己在這個問題的回答上是有發言權的。完全思考清楚了的東西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知道,一切都是完全思考清楚的,因而我是願意把每一個主張都提到盡可能清晰的高度的,如果我當時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
特別我認為需要提醒的是,我並不是把一切都說了出來,而是想留一些給我的讀者去思索。有些我預料一定會出現的誤解,只要我多說幾句話就一定可以避免。這幾句話我之所以沒說,是因為我想鼓勵獨立思考。知識學根本不應該把自己強加於人,它應該像它對於它的創立者那樣成為一種需要。
我請求本書未來的評論家們先消化整體,然後從整體的觀點去考察每個個別的思想。哈勒的書刊檢查官發表了他的高見,猜測我只是想開開玩笑;《論知識學的概念》一書的另外一些評論家顯然也同樣抱有這個看法;他們對待事情這樣輕率,他們的高見這麼滑稽,彷彿他們一定要用開玩笑來回敬開玩笑。
* 這個前言發表於《全部知識學的基礎》第二批稿件,即其第三篇初次出版的時候,第三篇付印較遲,約與《略論知識學的特徵》同時交稿。—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