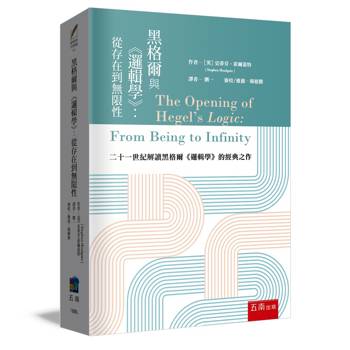第二章 無預設的思維
以純存在開端每一位現代黑格爾評論家都絕不承認,黑格爾真的認為他的哲學是無預設的。然而,從黑格爾文本的幾處段落以及從他最早的批評者們的證言中卻能很明顯地看出,黑格爾確實曾經這麼認為,例如:在《百科全書邏輯學》中,他寫道:
同樣地,在踏入科學的時候,所有的⋯⋯預設或先見都必須要放棄,它們可能取自表象,也可能取自思維;因為科學就在於,所有這類規定都應當在它之內得到探究,而這些規定及其對立之所謂,也應當在它之內得到認識⋯⋯對一切的懷疑,也就是在一切上的完全的無預設性(die gänzliche Voraussetzungslosigkeit)應當先行於科學。(EL 124/167-8 [§78])1
在《邏輯學》中,同樣的觀點被表述為:
開端必須是絕對的開端,或者是相同的意思,抽象的開端;它因此無需預設任何東西,不必透過任何東西被中介,也沒有根據;不如說,它本身倒應當是整個科學的根據。(SL 70/1: 68-9 [175])
這一觀念對於黑格爾的巨大重要性也可以透過19世紀黑格爾最重要的批評者們而得到驗證,例如:謝林在1830年代評論說:「黑格爾哲學自誇是一種什麼也不預設,完全無預設的哲學」;特蘭德倫堡(Trendelenburg)在1843年提到黑格爾的「關於無預設的純粹思維的傲慢學說」;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在他的《非科學的最後附言》(Cond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1846)中這樣引入他對黑格爾的討論:「以直接的東西開端,因而沒有任何預設的體系。」這些人中沒有人相信黑格爾的哲學真的是無預設的(或者相信無預設性值得欲求),但他們全都認真對待黑格爾說他要避免預設任何東西的宣稱。事實上,這也恰恰是為什麼他們如此渴望要反駁這個宣稱的原因。2
可是,「不帶前提地」進行哲學思考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正如我們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這意味著我們在哲學的一開始不預設任何對思想的特殊理解及其範疇,也不(和康德一起)假定概念是「某個可能的判斷的述詞」(CPR 205/109 [B 94])。然而,這也就意味著,我們並不假定思想應當受到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法則支配,或者假定不矛盾律行之有效,或者假定思想畢竟受到無論什麼原理或法則的約束。簡單來說,這意味著我們要放棄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萊布尼茲或康德(或20世紀的符號邏輯)那裡所學到的關於思想的一切東西—意味著我們要「從一切東西中抽離出來」(EL 124/168 [§78])。這並不是說,我們假定亞里斯多德的(或者後弗雷格的)形式邏輯原理純粹是錯誤的(黑格爾也主張三段論推理的規則最終將在《邏輯學》中表明自己是有效的—儘管只適用於哲學以外思想的一個限定的領域)。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在一開始就假定這些原則是明顯正確的並預先確定什麼東西才算作合理的。因此,我們不應當指望形式邏輯提供一個標準,藉以來確立黑格爾在《邏輯學》中的論證是否合理(或者說,更有可能是藉以來斷定這些論證是詭辯的)。正如繆爾(G. R. G. Mure)所評論的:「使某個原則免於批判,並把它預設為一種標準,藉以譴責某個邏輯的方法,這是一種明目張膽的迴避問題」;而如果說有一件事是真正批判的哲學家所不能做的,那麼在黑格爾看來,這件事就是「迴避問題」。3
因此,無前提地進行哲學思考並不是要預先拒絕一切傳統上算作「思想」、「概念」或者「理性」的東西。它只是要將我們所熟悉的關於思想的假設懸置起來,並且在邏輯科學的進程中去尋求發現這些假設是否會證明自己是正確的。一門邏輯科學必須在開始就將我們所熟悉的關於思想的假設置於一旁,因為它就是要成為這樣一種訓練:確定思想究竟意味著什麼,以及(如果有的話)哪些範疇和法則是思想所固有的。從叔本華到波普,黑格爾的批評者們也許會譴責他故意破壞不矛盾律(並在這個過程中攪亂青年人的頭腦),但黑格爾的本意卻並不是要故意拒絕任何傳統的思想法則。事實上,對於在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這類浪漫主義者的工作中,他視為是「粗暴地拒絕一切方法」的東西(SL 53/1: 49),他本人是極為批判的。他的觀點僅僅是:「邏輯學⋯⋯不能預設反思的這些形式或者思維的規則與法則,因為它們構成邏輯學內容本身的一部分,必須首先在邏輯學之內得到證實」(SL 43/1: 35,我的強調)。所以,真正來說,黑格爾不得不在《邏輯學》的一開始就對這種可能性保持開放:傳統的思想法則也許支配、也許不支配思想。因此,如果說黑格爾的《邏輯學》確實破壞了不矛盾律—我在這裡並不是認為它真的破壞了—那也會是由於思想證明自己完全不受該法則支配的緣故,而不是因為黑格爾簡單地決定要拋棄它。
此時此刻,我們需要考慮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如果我們要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考察思想,也就是不預設它有任何特殊的結構,使用任何特殊的概念來運作,或者受任何特殊的規則支配的話,那麼我們要把思想理解成什麼呢?我們考察的對象應該是什麼樣的呢?思想在最低程度上是怎樣的呢?黑格爾在《百科全書邏輯學》§78中的論述表明了他的回答:思想在最低程度上就是「從一切東西中抽離出來,緊握它的純粹的抽象,緊握思維的單純性」的自由(EL 124/168)。在黑格爾看來,將它關於自己的預設都懸置起來的這種自由的、自我批判的思想,除了它自身,除了它自己的簡單的存在(being)之外,不會留下什麼可供思考的東西。換一種(由古佐尼〔Ute Guzzoni〕敏銳的評論所建議的)方式來說就是:當思想將一切關於它是什麼的假設都給棄置一旁之後,它不會留下什麼可供思考的東西,除了「它存在」這樣一個簡單的思想。4 因此,黑格爾的無預設的邏輯科學是以對簡單地存在著—不是作為任何特殊的東西的存在,而是就單純地存在起來(be-ing)本身—的思想本身的思想為開端的。所以,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所考察的第一個範疇,就是關於純然無規定的最簡單存在(being tout court)的範疇。黑格爾在一開始就說,當前現有的
只是⋯⋯決心,那就是:人們願意考察思想本身(das Denken als solches)。因此,開端⋯⋯不可以任何東西為前提⋯⋯它因而必須完全是一種直接的東西,或就是僅僅直接的東西本身⋯⋯因此,開端就是純粹的存在(das reine Sein)。(SL 70/1: 68-9 [175])
那條通向黑格爾的邏輯學科學的「普遍懷疑」之路,很明顯非常類似於笛卡兒所走的路。然而,黑格爾的結論卻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思想故存在」。5 黑格爾相信,思想的必要的範疇必須從思想的這個純存在中被演繹出來。
黑格爾擁有方法嗎?
我們稍後將在本研究中更細緻地考察黑格爾《邏輯學》的開端。我現在希望引起注意的,是另外一個重要的—並且是潛在地相當令人不安的—結論,這個結論是黑格爾基進的無預設的承諾的結果。我們不僅必須透過將思想本身設想為完全無規定的存在來開始,我們也必須以不假定思想應當採取任何特殊的方式或遵從任何特定的程序規則來實施我們對思想的檢驗。正如理查.溫菲爾德(Richard Winfield)所指出的,我們對思想的檢驗「不能由任何命題演算、推理法則、發現的邏輯、語義分析或有關意向性的理論來指導或背書」,因為這些東西都不能在一開始就被假定為擁有任何有效性。6 這並不是說,黑格爾在他的《邏輯學》中不應該採用任何方法。而是他的方法僅限於考量無規定的存在本身,並陳述關於這種存在的思想所涉及的東西。這就是說,在黑格爾「抽離」一切之後,他的方法必須僅僅在於「接受當前現有的東西」並冷靜地「觀察」(Zusehen)它。7 不管怎樣,黑格爾也許並沒有假定我們要按照任何指定的規則去越過對無規定的存在所進行的原初考量,甚至根本就沒有假定我們要越過關於無規定的存在的那種思想,因為那麼做將會預設太多的東西。
1 亦參見Hegel, LHP 137-8/92。
2 參見F. W. J. von Schelling,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trans. A. Bow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8; F. A. Trendelenburg, The Logical Question in Hegel’s System, in G. W. F. Hegel: Critical Assessments, ed. R. Stern, 4 vols. (London: Routledge, 1993), 1: 205; S. Kierkegaard,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rans. D. F. Swenson and W. Lowr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01。
3 參見G. R. G. Mure, A Study of Hegel’s Logic (1950)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4), p. 33。亦參見J. Burbidge, On Hegel’s Logic: Fragments of a Commentary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1981), p. 4:「用形式邏輯的慣用標準來評估黑格爾的邏輯學是在迴避問題。因為黑格爾所探詢的是一切邏輯有效性的根據。」
4 U. Guzzoni, Werden zu sich. Eine Untersuchung zu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Freiburg/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1963), p. 35.
5 參見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trans. J. Cottingham, R. Stoothoff, D. Murdoch,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91), 1: 196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1: 10)。
6 R. Winfield, Reason and Justice (Albany: SUNY Press, 1988), p. 142.
7 Hegel, SL 69/1: 68 (175);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Logik und Metaphysik. Heidelberg 1817, ed. K. Gloy, Ausgewählte Nach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 vol. 11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2), p. 21. 接下來對《邏輯學和形上學講演錄》的引用將採用下面的形式:VLM 21。對於黑格爾來說,現象學也要求我們在意識內在地發展著自己的時候「袖手旁觀」(zusehen);參見PhS 85/77。
以純存在開端每一位現代黑格爾評論家都絕不承認,黑格爾真的認為他的哲學是無預設的。然而,從黑格爾文本的幾處段落以及從他最早的批評者們的證言中卻能很明顯地看出,黑格爾確實曾經這麼認為,例如:在《百科全書邏輯學》中,他寫道:
同樣地,在踏入科學的時候,所有的⋯⋯預設或先見都必須要放棄,它們可能取自表象,也可能取自思維;因為科學就在於,所有這類規定都應當在它之內得到探究,而這些規定及其對立之所謂,也應當在它之內得到認識⋯⋯對一切的懷疑,也就是在一切上的完全的無預設性(die gänzliche Voraussetzungslosigkeit)應當先行於科學。(EL 124/167-8 [§78])1
在《邏輯學》中,同樣的觀點被表述為:
開端必須是絕對的開端,或者是相同的意思,抽象的開端;它因此無需預設任何東西,不必透過任何東西被中介,也沒有根據;不如說,它本身倒應當是整個科學的根據。(SL 70/1: 68-9 [175])
這一觀念對於黑格爾的巨大重要性也可以透過19世紀黑格爾最重要的批評者們而得到驗證,例如:謝林在1830年代評論說:「黑格爾哲學自誇是一種什麼也不預設,完全無預設的哲學」;特蘭德倫堡(Trendelenburg)在1843年提到黑格爾的「關於無預設的純粹思維的傲慢學說」;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在他的《非科學的最後附言》(Cond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1846)中這樣引入他對黑格爾的討論:「以直接的東西開端,因而沒有任何預設的體系。」這些人中沒有人相信黑格爾的哲學真的是無預設的(或者相信無預設性值得欲求),但他們全都認真對待黑格爾說他要避免預設任何東西的宣稱。事實上,這也恰恰是為什麼他們如此渴望要反駁這個宣稱的原因。2
可是,「不帶前提地」進行哲學思考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正如我們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這意味著我們在哲學的一開始不預設任何對思想的特殊理解及其範疇,也不(和康德一起)假定概念是「某個可能的判斷的述詞」(CPR 205/109 [B 94])。然而,這也就意味著,我們並不假定思想應當受到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法則支配,或者假定不矛盾律行之有效,或者假定思想畢竟受到無論什麼原理或法則的約束。簡單來說,這意味著我們要放棄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萊布尼茲或康德(或20世紀的符號邏輯)那裡所學到的關於思想的一切東西—意味著我們要「從一切東西中抽離出來」(EL 124/168 [§78])。這並不是說,我們假定亞里斯多德的(或者後弗雷格的)形式邏輯原理純粹是錯誤的(黑格爾也主張三段論推理的規則最終將在《邏輯學》中表明自己是有效的—儘管只適用於哲學以外思想的一個限定的領域)。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在一開始就假定這些原則是明顯正確的並預先確定什麼東西才算作合理的。因此,我們不應當指望形式邏輯提供一個標準,藉以來確立黑格爾在《邏輯學》中的論證是否合理(或者說,更有可能是藉以來斷定這些論證是詭辯的)。正如繆爾(G. R. G. Mure)所評論的:「使某個原則免於批判,並把它預設為一種標準,藉以譴責某個邏輯的方法,這是一種明目張膽的迴避問題」;而如果說有一件事是真正批判的哲學家所不能做的,那麼在黑格爾看來,這件事就是「迴避問題」。3
因此,無前提地進行哲學思考並不是要預先拒絕一切傳統上算作「思想」、「概念」或者「理性」的東西。它只是要將我們所熟悉的關於思想的假設懸置起來,並且在邏輯科學的進程中去尋求發現這些假設是否會證明自己是正確的。一門邏輯科學必須在開始就將我們所熟悉的關於思想的假設置於一旁,因為它就是要成為這樣一種訓練:確定思想究竟意味著什麼,以及(如果有的話)哪些範疇和法則是思想所固有的。從叔本華到波普,黑格爾的批評者們也許會譴責他故意破壞不矛盾律(並在這個過程中攪亂青年人的頭腦),但黑格爾的本意卻並不是要故意拒絕任何傳統的思想法則。事實上,對於在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這類浪漫主義者的工作中,他視為是「粗暴地拒絕一切方法」的東西(SL 53/1: 49),他本人是極為批判的。他的觀點僅僅是:「邏輯學⋯⋯不能預設反思的這些形式或者思維的規則與法則,因為它們構成邏輯學內容本身的一部分,必須首先在邏輯學之內得到證實」(SL 43/1: 35,我的強調)。所以,真正來說,黑格爾不得不在《邏輯學》的一開始就對這種可能性保持開放:傳統的思想法則也許支配、也許不支配思想。因此,如果說黑格爾的《邏輯學》確實破壞了不矛盾律—我在這裡並不是認為它真的破壞了—那也會是由於思想證明自己完全不受該法則支配的緣故,而不是因為黑格爾簡單地決定要拋棄它。
此時此刻,我們需要考慮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如果我們要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考察思想,也就是不預設它有任何特殊的結構,使用任何特殊的概念來運作,或者受任何特殊的規則支配的話,那麼我們要把思想理解成什麼呢?我們考察的對象應該是什麼樣的呢?思想在最低程度上是怎樣的呢?黑格爾在《百科全書邏輯學》§78中的論述表明了他的回答:思想在最低程度上就是「從一切東西中抽離出來,緊握它的純粹的抽象,緊握思維的單純性」的自由(EL 124/168)。在黑格爾看來,將它關於自己的預設都懸置起來的這種自由的、自我批判的思想,除了它自身,除了它自己的簡單的存在(being)之外,不會留下什麼可供思考的東西。換一種(由古佐尼〔Ute Guzzoni〕敏銳的評論所建議的)方式來說就是:當思想將一切關於它是什麼的假設都給棄置一旁之後,它不會留下什麼可供思考的東西,除了「它存在」這樣一個簡單的思想。4 因此,黑格爾的無預設的邏輯科學是以對簡單地存在著—不是作為任何特殊的東西的存在,而是就單純地存在起來(be-ing)本身—的思想本身的思想為開端的。所以,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所考察的第一個範疇,就是關於純然無規定的最簡單存在(being tout court)的範疇。黑格爾在一開始就說,當前現有的
只是⋯⋯決心,那就是:人們願意考察思想本身(das Denken als solches)。因此,開端⋯⋯不可以任何東西為前提⋯⋯它因而必須完全是一種直接的東西,或就是僅僅直接的東西本身⋯⋯因此,開端就是純粹的存在(das reine Sein)。(SL 70/1: 68-9 [175])
那條通向黑格爾的邏輯學科學的「普遍懷疑」之路,很明顯非常類似於笛卡兒所走的路。然而,黑格爾的結論卻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思想故存在」。5 黑格爾相信,思想的必要的範疇必須從思想的這個純存在中被演繹出來。
黑格爾擁有方法嗎?
我們稍後將在本研究中更細緻地考察黑格爾《邏輯學》的開端。我現在希望引起注意的,是另外一個重要的—並且是潛在地相當令人不安的—結論,這個結論是黑格爾基進的無預設的承諾的結果。我們不僅必須透過將思想本身設想為完全無規定的存在來開始,我們也必須以不假定思想應當採取任何特殊的方式或遵從任何特定的程序規則來實施我們對思想的檢驗。正如理查.溫菲爾德(Richard Winfield)所指出的,我們對思想的檢驗「不能由任何命題演算、推理法則、發現的邏輯、語義分析或有關意向性的理論來指導或背書」,因為這些東西都不能在一開始就被假定為擁有任何有效性。6 這並不是說,黑格爾在他的《邏輯學》中不應該採用任何方法。而是他的方法僅限於考量無規定的存在本身,並陳述關於這種存在的思想所涉及的東西。這就是說,在黑格爾「抽離」一切之後,他的方法必須僅僅在於「接受當前現有的東西」並冷靜地「觀察」(Zusehen)它。7 不管怎樣,黑格爾也許並沒有假定我們要按照任何指定的規則去越過對無規定的存在所進行的原初考量,甚至根本就沒有假定我們要越過關於無規定的存在的那種思想,因為那麼做將會預設太多的東西。
1 亦參見Hegel, LHP 137-8/92。
2 參見F. W. J. von Schelling,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trans. A. Bow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8; F. A. Trendelenburg, The Logical Question in Hegel’s System, in G. W. F. Hegel: Critical Assessments, ed. R. Stern, 4 vols. (London: Routledge, 1993), 1: 205; S. Kierkegaard,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rans. D. F. Swenson and W. Lowr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01。
3 參見G. R. G. Mure, A Study of Hegel’s Logic (1950)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4), p. 33。亦參見J. Burbidge, On Hegel’s Logic: Fragments of a Commentary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1981), p. 4:「用形式邏輯的慣用標準來評估黑格爾的邏輯學是在迴避問題。因為黑格爾所探詢的是一切邏輯有效性的根據。」
4 U. Guzzoni, Werden zu sich. Eine Untersuchung zu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Freiburg/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1963), p. 35.
5 參見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trans. J. Cottingham, R. Stoothoff, D. Murdoch,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91), 1: 196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1: 10)。
6 R. Winfield, Reason and Justice (Albany: SUNY Press, 1988), p. 142.
7 Hegel, SL 69/1: 68 (175);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Logik und Metaphysik. Heidelberg 1817, ed. K. Gloy, Ausgewählte Nach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 vol. 11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2), p. 21. 接下來對《邏輯學和形上學講演錄》的引用將採用下面的形式:VLM 21。對於黑格爾來說,現象學也要求我們在意識內在地發展著自己的時候「袖手旁觀」(zusehen);參見PhS 8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