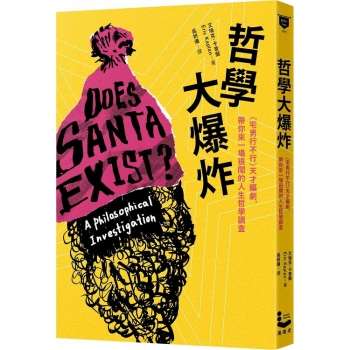導論
我兒子,他朋友的媽媽,還有兩種解釋
直到我兒子阿里上小學為止,聖誕老人的本體論原本跟我的生活無關。阿里並不相信聖誕老人。他本來該在十二月初跟他的朋友史蓋樂一起去動物園,而史蓋樂的媽媽譚米打電話給我,說她不想讓她兒子去,因為動物園裡有馴鹿,而她覺得馴鹿會導致關於聖誕老人的討論。譚米的兒子史蓋樂真心相信有聖誕老人。他仍然百分之百是個很甜美的孩子,還沒進入酸溜溜的青少年叛逆期,而她希望他能保持這個狀態,至少再一陣子。所以譚米想要取消這個出遊行程,以便確保阿里不會跟她兒子說:「沒有聖誕老人啦——他只是你爸媽裝的,」然後動搖了他的信念。
我覺得這種反應讓人困擾,因為我想譚米正在犧牲她兒子跟阿里(他是真人)的友誼,以便維持他跟聖誕老人(他不是真人)的關係。
為什麼我這麼確定聖誕老人不存在?這不是因為我從來沒見過他——我從來沒見過以色列超模芭兒・拉菲麗,但她存在,或者至少在我走筆至此時還在。這也不是因為我如果去了北極,不會見到他跟他的小精靈們——只會看到很多雪、很多冰等等——因為有的是辦法解釋我為何看不到。聖誕老人有可能從他的鬍子放射出一種能量場,讓人看不到他,小精靈們可能有台導致光線折射的機器,或者我可能遇到他了,卻被聖誕老婆婆說服,動了某種抹消記憶的腦部手術。不,我確定真正的理由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他存在,而且對於聖誕老人的信念,跟很多我知道為真的其他事情兜不攏——例如說,馴鹿不會飛,玩具是從玩具店來的,諸如此類。
我把這件事告訴我女兒,她說:「我相信有聖誕老人。」我也問她是不是相信有復活節兔,她則說:「對。我是小孩,所以我什麼都相信。」
我把這件事告訴我太太,她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羅馬尼亞長大的心理學家,而她的論調大致上是這個路線:「美國父母在這種蠢事上面對他們的小孩撒謊,然後小孩長大了發現他們的父母對他們撒謊。難怪美國小孩心理狀態都亂糟糟的。」譚米的行為仍然讓我很困惑。我可以兩道兩種可能的解答:
「騙子」解釋
基於某種理由,過去美國兒童被教導要相信有聖誕老人——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覺得這是個好辦法,可以把他們嚇到變乖。孩子們長大了、不再相信聖誕老人了,卻又認定騙自己的孩子去相信聖誕老人是好主意。所以社會上基本上分成兩群人——騙子跟被騙的人。騙子們的動機從善意(當爸媽的大概是這樣)到自私自利(聖誕商品賣家、希望有個全國神話來團結這個移民之國的美國政客)都有。咱們就直白地說這是「騙子」故事吧。
我有觀察到「騙子」故事屬實的證據。我在好萊塢工作,此地把大量影像與故事灌進全球的意識之中。當我們在替某個叫做《宅男行不行》的影集寫某一集劇本的時候,謝爾頓在「龍與地下城」遊戲裡殺了聖誕老人,其中一名編劇想要確定我們的故事對於聖誕老人存在與否保持開放性結論,因為他的孩子會看這個節目,而且他們相信有聖誕老人。當然啦,因為他是替一部靠廣告吃飯的美國情境喜劇當編劇,他說謊的善意動機跟我們的廣告主沒那麼善意的動機一拍即合。
「瘋子」解釋
這個難題的另一個解答是,譚米心中有些東西是分裂或解離的。所以根據這個理論,有可能譚米心中有一部分仍然相信聖誕老人。她跟其他大人說話的時候絕口不提,但跟她的孩子獨處時,她是相信的。這一部分相信聖誕老人的譚米,可能甚至不是能夠控制她嘴巴的那一部分。所以她可能永遠不會說「我相信聖誕老人」,但她很容易有跟這位紅衣阿伯有關的夢境、幻想與感受。因此,她對於讓她兒子失去對聖誕老人的信心感到很不安,因為她腦袋裡的某個系統也相信這件事。一個人怎麼可能既相信又不相信聖誕老人呢?如果你是陰謀論故事的強烈支持者,你可能不會相信事情就是這樣——你可能會認為,如果她當真自白說她相信聖誕老人,她只是在撒謊。畢竟她在店裡買了玩具——她怎麼可能誠心主張這些玩具是從煙囪裡掉下來的呢?
但人會在不同的時候與不同的脈絡下,相信不同的事。咱們來想像一下譚米回家去上床睡覺。當她漂入夢鄉時,聽到她腦中有個聲音,那聲音聽起來很像她自己的。那聲音說:「聖誕老人真的存在。我記得等著他來的時候。我怎麼知道他沒來?對,有一部分的我認為他沒來,而且永遠不會來,但為什麼我應該聽那一部分的話呢?」
譚米體內有兩個不同的譚米。其中一個譚米一度相信聖誕老人,但現在從店裡買玩具,還有另一個譚米還是相信聖誕老人。這個譚米在想到聖誕老人的時候感覺很愉快,想到艾瑞克不信聖誕老人就火大。這個譚米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回應聖誕老人的影像、聖誕老人電視節目、還有跟聖誕老人相關的歌曲。
譚米的自我可以在同一時間分裂成幾個;她可以在同一時刻是超過一個以上的譚米——也就是說,她腦袋裡可以有個聲音說:「當然啦,聖誕老人不存在。」還有另一個聲音說:「我希望他送我某樣好東西!」或者她的自我可以在不同時間裡分裂成幾個。也就是說,她可以整年都拿聖誕老人開玩笑,直到聖誕季來臨為止,然後在聖誕期間講得像是真心相信那位快活的老聖徒。
既然這番說法訴諸於腦袋裡的聲音,咱們就很壞心腸地稱之為「瘋子」解釋吧。
「騙子」與「瘋子」解釋從深層來說是相似的,因為「騙子」訴諸於人際層級的分裂,「瘋子」則訴諸於個人層級上的分裂。靠陰謀運作、建立於謊言之上的的社會是精神分裂的;瘋狂的人則對自己撒謊。
在「瘋子」解釋中,譚米內在有某種不統一——有一部分的她相信,另一部分的她不相信。在「騙子」解釋中,美國有種不統一——有一部分的美國相信,另一部分的美國不相信。而在兩種狀況下,不同部分之間的關係,都有某種搞砸的地方。你甚至可以把這兩種解釋對調。你可以說譚米是在對自己說謊,或者美國在聖誕老人這個主題上有點瘋瘋的。
「騙子」跟「瘋子」解釋哪個正確?
我兒子,他朋友的媽媽,還有兩種解釋
直到我兒子阿里上小學為止,聖誕老人的本體論原本跟我的生活無關。阿里並不相信聖誕老人。他本來該在十二月初跟他的朋友史蓋樂一起去動物園,而史蓋樂的媽媽譚米打電話給我,說她不想讓她兒子去,因為動物園裡有馴鹿,而她覺得馴鹿會導致關於聖誕老人的討論。譚米的兒子史蓋樂真心相信有聖誕老人。他仍然百分之百是個很甜美的孩子,還沒進入酸溜溜的青少年叛逆期,而她希望他能保持這個狀態,至少再一陣子。所以譚米想要取消這個出遊行程,以便確保阿里不會跟她兒子說:「沒有聖誕老人啦——他只是你爸媽裝的,」然後動搖了他的信念。
我覺得這種反應讓人困擾,因為我想譚米正在犧牲她兒子跟阿里(他是真人)的友誼,以便維持他跟聖誕老人(他不是真人)的關係。
為什麼我這麼確定聖誕老人不存在?這不是因為我從來沒見過他——我從來沒見過以色列超模芭兒・拉菲麗,但她存在,或者至少在我走筆至此時還在。這也不是因為我如果去了北極,不會見到他跟他的小精靈們——只會看到很多雪、很多冰等等——因為有的是辦法解釋我為何看不到。聖誕老人有可能從他的鬍子放射出一種能量場,讓人看不到他,小精靈們可能有台導致光線折射的機器,或者我可能遇到他了,卻被聖誕老婆婆說服,動了某種抹消記憶的腦部手術。不,我確定真正的理由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他存在,而且對於聖誕老人的信念,跟很多我知道為真的其他事情兜不攏——例如說,馴鹿不會飛,玩具是從玩具店來的,諸如此類。
我把這件事告訴我女兒,她說:「我相信有聖誕老人。」我也問她是不是相信有復活節兔,她則說:「對。我是小孩,所以我什麼都相信。」
我把這件事告訴我太太,她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羅馬尼亞長大的心理學家,而她的論調大致上是這個路線:「美國父母在這種蠢事上面對他們的小孩撒謊,然後小孩長大了發現他們的父母對他們撒謊。難怪美國小孩心理狀態都亂糟糟的。」譚米的行為仍然讓我很困惑。我可以兩道兩種可能的解答:
「騙子」解釋
基於某種理由,過去美國兒童被教導要相信有聖誕老人——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覺得這是個好辦法,可以把他們嚇到變乖。孩子們長大了、不再相信聖誕老人了,卻又認定騙自己的孩子去相信聖誕老人是好主意。所以社會上基本上分成兩群人——騙子跟被騙的人。騙子們的動機從善意(當爸媽的大概是這樣)到自私自利(聖誕商品賣家、希望有個全國神話來團結這個移民之國的美國政客)都有。咱們就直白地說這是「騙子」故事吧。
我有觀察到「騙子」故事屬實的證據。我在好萊塢工作,此地把大量影像與故事灌進全球的意識之中。當我們在替某個叫做《宅男行不行》的影集寫某一集劇本的時候,謝爾頓在「龍與地下城」遊戲裡殺了聖誕老人,其中一名編劇想要確定我們的故事對於聖誕老人存在與否保持開放性結論,因為他的孩子會看這個節目,而且他們相信有聖誕老人。當然啦,因為他是替一部靠廣告吃飯的美國情境喜劇當編劇,他說謊的善意動機跟我們的廣告主沒那麼善意的動機一拍即合。
「瘋子」解釋
這個難題的另一個解答是,譚米心中有些東西是分裂或解離的。所以根據這個理論,有可能譚米心中有一部分仍然相信聖誕老人。她跟其他大人說話的時候絕口不提,但跟她的孩子獨處時,她是相信的。這一部分相信聖誕老人的譚米,可能甚至不是能夠控制她嘴巴的那一部分。所以她可能永遠不會說「我相信聖誕老人」,但她很容易有跟這位紅衣阿伯有關的夢境、幻想與感受。因此,她對於讓她兒子失去對聖誕老人的信心感到很不安,因為她腦袋裡的某個系統也相信這件事。一個人怎麼可能既相信又不相信聖誕老人呢?如果你是陰謀論故事的強烈支持者,你可能不會相信事情就是這樣——你可能會認為,如果她當真自白說她相信聖誕老人,她只是在撒謊。畢竟她在店裡買了玩具——她怎麼可能誠心主張這些玩具是從煙囪裡掉下來的呢?
但人會在不同的時候與不同的脈絡下,相信不同的事。咱們來想像一下譚米回家去上床睡覺。當她漂入夢鄉時,聽到她腦中有個聲音,那聲音聽起來很像她自己的。那聲音說:「聖誕老人真的存在。我記得等著他來的時候。我怎麼知道他沒來?對,有一部分的我認為他沒來,而且永遠不會來,但為什麼我應該聽那一部分的話呢?」
譚米體內有兩個不同的譚米。其中一個譚米一度相信聖誕老人,但現在從店裡買玩具,還有另一個譚米還是相信聖誕老人。這個譚米在想到聖誕老人的時候感覺很愉快,想到艾瑞克不信聖誕老人就火大。這個譚米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回應聖誕老人的影像、聖誕老人電視節目、還有跟聖誕老人相關的歌曲。
譚米的自我可以在同一時間分裂成幾個;她可以在同一時刻是超過一個以上的譚米——也就是說,她腦袋裡可以有個聲音說:「當然啦,聖誕老人不存在。」還有另一個聲音說:「我希望他送我某樣好東西!」或者她的自我可以在不同時間裡分裂成幾個。也就是說,她可以整年都拿聖誕老人開玩笑,直到聖誕季來臨為止,然後在聖誕期間講得像是真心相信那位快活的老聖徒。
既然這番說法訴諸於腦袋裡的聲音,咱們就很壞心腸地稱之為「瘋子」解釋吧。
「騙子」與「瘋子」解釋從深層來說是相似的,因為「騙子」訴諸於人際層級的分裂,「瘋子」則訴諸於個人層級上的分裂。靠陰謀運作、建立於謊言之上的的社會是精神分裂的;瘋狂的人則對自己撒謊。
在「瘋子」解釋中,譚米內在有某種不統一——有一部分的她相信,另一部分的她不相信。在「騙子」解釋中,美國有種不統一——有一部分的美國相信,另一部分的美國不相信。而在兩種狀況下,不同部分之間的關係,都有某種搞砸的地方。你甚至可以把這兩種解釋對調。你可以說譚米是在對自己說謊,或者美國在聖誕老人這個主題上有點瘋瘋的。
「騙子」跟「瘋子」解釋哪個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