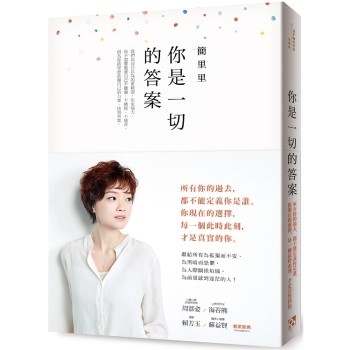一直正確,是最大的錯誤
人的成長大概是個理想不斷破滅的過程,聽起來令人難過。比如,你慢慢知道,王子和公主歷經艱難,最後其實並未過上童話裡的生活,不過是柴米油鹽,生兒育女,還要為了買多大的房子、孩子怎麼教育,以及生老病死的各種問題困倦爭吵。
這世上,所謂「美好」,大抵是很少存在的。
前段時間我很煩躁的時候,我媽給我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故事說伊甸園裡的亞當和夏娃在蛇的誘惑下,偷食了禁果,於是人有了羞恥心和好壞之分。於是上帝罰男人永生勞動,女人要忍受十月懷胎之苦,而蛇只能用腹部行走。「所以啊,你來到這世上,本來就是來贖罪的」。
這是你來的本來目的。其實《聖經》早就告訴了人這個道理。
剛開始做心理諮詢的時候,我還是個小丫頭。像每個渴望成為好諮詢師的人一樣,我認真、負責任,睜大眼睛去看來訪者的所謂「症狀」。像插花一樣,渴望將枝條修剪整齊,將顏色搭配好看。我認真地和來訪者說每一句話,渴望把事情做得完美。比如……你看,你可以這樣,你可以那樣,你這麼做,其實會傷害自己,你換個方式。大抵是因為夏娃也咬了那蘋果,在我心裡面,「對錯」、「好壞」是如此清晰。我對我自己同樣苛刻,不要說錯話,不要用錯力,不要做超越範疇的事情,以至於捆綁了手腳。後來我去見督導。督導說,身為一個諮詢師,當你一直用力不犯錯誤,所謂的「一直正確」,正是最大的「錯誤」。
精神分析的治療裡面,治療師有一個原則,叫先跟隨來訪者,同時跳出來觀察,再用它來工作。所謂跟隨來訪者,是治療師允許自己跟隨自己(的感受)來做反應(來訪者的客體能夠在諮詢關係中投射出來,而諮詢師的放鬆,也能夠讓自己被來訪者啟動的那一部分展現在諮詢室內);而治療師要保留一隻眼睛,來觀察這期間的動力和移情5,利用此中有意義的部分,和來訪者工作。
而當諮詢師自己緊張兮兮絕不犯錯,來訪者無法放鬆下來,所謂的「客體」無法登場,治療師自己的阻抗使得自己無法在治療關係中發生作用,治療便無法進行下去。用力過猛,治療便變成雞湯式的「創可貼」了。好在,督導每次總說,你這樣也滿好,我年輕的時候也這樣,沒事兒。好像跑題了。
其實,我原本是打算說,這世上其實並無「好壞」之分,人和人說穿了不過一樣,各有各的掙扎苦痛,各有各的幸福甜蜜。
做諮詢久了,我慢慢不再想要改變來訪者。因為即便是「症狀」,也往往都有其存在的意義。所謂「依賴」也好,「苛責自己」也罷,抑或是抑鬱症、強迫症,其實都不那麼緊要。因為這世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症狀」,無非有人「症狀」消失得更快一些,有人「症狀」消失得更慢一些,而幾乎每個人,直到走進墳墓,也都有著這樣那樣的症狀。可是大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生活,也都過了「差不多」的人生。
所以,諮詢師提的一些具體建議,比如,你換一個思維方式;或者你在網上看到諮詢師寫了你要積極向上,你要學會無條件地去愛等等諸如此類(遍地都是)的話語,這些不過是理想狀態。就像童話故事裡,王子和公主舉行了盛大的婚禮,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樣。
事實上,如果你就是還做不到所謂「積極思維」,就是還沒學會「無條件接納」,沒關係,因為你必然有不能積極思維的原因,必然有不能無條件接納的動機。更何況糾結並非壞事,混沌也非所謂「不好」。這世界上的人,過得「糟糕」是常態,過得「還行」就很少了,如果能夠過得「很好」,那千真萬確是偶然的事情。
別要求自己不難過、不糟糕,混沌、糟糕也是種狀態。而狀態的本質是:它總會變化的。別急。
*****
你總是比想像的更強大一些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我特別抑鬱,因為生活裡面臨的各種衝突,還因為我內心充滿了改變和成長的願望。有天中午我和幾個諮詢師一起吃飯,席間我吐槽不斷,然後有個年長一些的諮詢師跟我說,恭喜你哦,一個人沒有經歷過抑鬱,是無法成為一個好的諮詢師的。
這句話當然是句玩笑話,可是我覺得是真的。一個好的諮詢師,一定要走長長長長的道路,去發現和面對真實的自己。這是個鮮血淋漓的過程。一個人真正去撥開自己的外殼,面對自己的內心,這是非常需要勇氣,並且帶著撕裂一般疼痛的事情。你不得不去面對你生命中那些有意無意的、你想要隔離開但潛意識偷偷幫你收拾起來的、藏匿不見的創傷;你不得不面對自己的軟弱無助、羞愧、憤怒和悲傷。尤其是當一個人學了些皮毛知識,一瓶子不滿半瓶子響叮噹的時候,對自己的行為、情緒異常敏感並將其放大,經常亂貼標籤,看自己哪兒都是問題。簡直不能活命。
因此我很感激我生活中的朋友。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無法用正常的語言來描述一件雞毛蒜皮的事情。比如我燒壞了一口鍋,我會坐下來,嘟嘟囔囔,從我三歲以前跟我媽的互動關係、我媽和她媽媽的互動關係,還有我和我爸的互動關係、我爸和他爸爸的互動關係,再加上我爸和我媽之間的互動關係,一直講到它是如何影響我深層次的人格形成、影響我今天的行為,我的潛意識如何發生阻抗,以至於把鍋燒壞的。
我的朋友是多麼善良的一群人啊!他們出於各種原因,沒有直接將我從座位上面踢下去。多數時候,他們非常、非常憂慮地看著我,說,真的,Jane,你想多了。
可是在瞭解自己的途中,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至少是我經歷的一個過程。努力地去探尋,需要支援,也需要幫助。人們常常說,你是一個心理諮詢師,你一定更知道怎樣快速地調節情緒。那,其實我並不知道如何能讓自己馬上開心起來,可是我想,在這條長長的、自我探索的道路上,「瞭解自己」本身給了我很多勇氣和力量,讓我在困難的情形下,更容易接納自己的脆弱、無能、恐懼和憤怒,諸如此類,哪怕在別人看來有些神經兮兮。
其實,當人們能夠理解自己,理解自己行為背後的動力、能量,被自己接納、理解、支持,而不被自己苛責、不近人情地要求的時候,人是有無窮無盡的力量和智慧,來面對生活裡面的七七八八左左右右的。
心理諮詢師希望能夠盡一切的力量,幫助人們更安全、更勇敢地走過這條長長的、黑暗的道路。然後有一天,當你千真萬確放下對自己的束縛,和自己站在一起的時候,你總是比你想像的更強大一些。
*****
要照顧別人,先照顧好自己
前段時間我在單向街講抑鬱症,講到什麼是好的陪伴、好的共情,講到陪老爺爺哭的小男孩兒的故事。大意是說當朋友抑鬱的時候,我們應該陪他哭,而不急於將他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講座結束之後,有人提問說,自己就是這樣陪伴自己的朋友,可是時間一久,自己也難堪重負,心生逃離的念頭。又覺得自己怎能這樣可惡,在朋友需要的時候,不做個「合格」的朋友?怎麼能在朋友需要自己的時候,不陪著他哭,反而想逃離呢?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還是讓我先來講講心理諮詢吧。
心理諮詢師的入門課,便是要讓諮詢師看清楚這樣一個事實:你自己的力量幫不到任何一個人。一個人之所以能夠改變他的生活態度,之所以「好」起來,仰仗的是他自己內在的力量。
諮詢師倘若相信自己的「武功蓋世」,便是自戀地剝奪了來訪者本來的生長。這一方面使得諮詢師變得像小學老師一樣高大偉岸又面目可憎,一方面使來訪者不斷體驗挫敗── 諮詢師比我更強大,我總是依靠別人的力量才能感到好一點兒。
Stephen King(史蒂芬.金)31談寫作的時候說,故事就像是埋在地下的一個化石,作家的任務是不斷地往下挖掘,直到將整個化石完整地挖出來。他說,不要試圖去構造故事,它們在你到達之前已經在那兒了。
我想心理諮詢是一樣的。心理諮詢師沒有能力去賦予任何來訪者能力、信心、勇氣或是其他任何一樣東西。這些能力、信心、勇氣、力量,在你遇見來訪者之前,已經在他的身體裡面居住很久了。而諮詢師的任務,不過是像作家、考古學家一樣,將它們從重重灰塵迷霧之中,還原出來。
所以,諮訪關係(治療師和來訪者的關係)的本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和另一個普通人的關係。一個人但凡存在,就必然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軟弱。來訪者是這樣,諮詢師也是。諮詢師在相信來訪者有力量的同時,也要承受來自來訪者的壓力、阻抗、攻擊和種種測試,難免受到「傷害」,想逃離。
於是督導老師常常說:在諮訪關係中,治療師的首要任務是先讓自己在這段關係裡面生存下來,然後來訪者才能有信心,和你一起走下去。
你看,連靠此吃飯的治療師,都要先在諮訪關係中保全自己,然後才能繼續工作啊!
所以回到我們討論的問題上:你是如此努力地想做完美的朋友或家人,但當你不堪重負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我今天整理郵件,然後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回答類似這樣的詢問我幾乎可以做一個範本出來,下面這些話,我用不同的方式,或長或短,寫了無數遍:你好,謝謝來信。
你在他身邊,這樣用心地陪他,已經做得足夠好了。
你作為一個朋友,並不能夠承擔更多的事情,比如說負責他的情緒、保護他的安全。如果你要全權為他負責,這超越了朋友或家人(甚至人和人之間)的界限。
作為朋友,給予適當的陪伴(而非超越你個人能力的陪伴)即可,同時,他也需要你真實的回饋(如:傾訴你的壓力,給予建議,甚至表達你自己的不滿等等)。專業的諮詢或治療請交給他的諮詢師去做。如果一定要打破界限(長期的、二十四小時的關注),你可以求助他的家人(更多其他家人)或相關的社會機構。你做得已經很多、很好了。
要照顧好別人,先照顧好自己。這樣照顧才是可持續的。
祝好。
簡里里
*****
黑暗中見到光芒
最近常有人來問我能不能分享些跟心理相關的話題。我每次都高興應允,說那我來分享一下抑鬱這個主題吧,主辦方都面露難色,問:能不能講點兒積極的、正能量的?
我覺得很尷尬,因為其實我私下覺得在諸多和心理相關的主題裡面,所謂的「抑鬱」和「不高興」是最有「正能量」和光芒的。所以我總是想來給「抑鬱」正一正名,剝繭抽絲,窺見它的價值。
我上大學的時候大家還流行手寫信,每次寫信都和朋友相互問候最近開心嗎、過得好嗎。出國之前,我從來不知道「不開心」是什麼意思,雖然每次都寫這個問候語作為開頭,但權作禮貌。直到我出國以後有了抑鬱的「症狀」感受,「開心」和「不開心」才真的進入我的意識裡面。
我為自己「不高興」這件事情糾結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直到看到這麼一句話:「一切在哲學、詩歌、藝術、政治領域成績卓著的人,即使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也不例外,都是憂鬱的常客。」我才釋然了。
嘿,原來我有做天才的潛質。
玩笑歸玩笑。回顧我的每一次「抑鬱」發作,都會帶來無與倫比的價值。所以我們不講臨床診斷的「抑鬱症」,我們來講一講「不高興」的價值。
有一個精神分析的前輩,叫梅蘭妮.克萊因,她是客體關係理論的創始人。她提出了人在心理上有兩個特殊的位置:PS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即偏執分裂樣位置;另一個是D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就是抑鬱位置。這個理論背後有很複雜的東西,不細贅了。但我想借用她的PS位置和D位置講一講抑鬱的價值。
先讓我講一個自己的故事。我上大學的時候不好好學習,每次都差一點點拿不到獎學金。我每次去見老師的時候,都跟她說,我只花了一個晚上看書,所以沒考好,如果我花一個星期看書的話就一定沒問題。
直到有一天,我的老師跟我說,Jane 你知道嗎,你每次都跟我說你是準備的時間不足,但我覺得,你根本就是在害怕失敗,你害怕你複習一週也考不到前面去,所以給自己找了這麼個藉口。
老師的這句話如當頭一棒。因為她說的是對的,我不敢面對的是我對失敗的恐懼。
所以她說完這番話之後,我不得不面對我自己的恐懼和懦弱。你可以想像,我在奮起之前,陷入了漫長的思考和不高興。
我從自己的PS位置,走向了D位置。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聽我的督導這麼講,他說你可以把PS位理解為 Photoshop(美化圖片軟體),就是說在這個位置上,你會把「痛苦的真相」PS(美化)成你可以接受的樣子。比如,我不願意去面對「我恐懼失敗」這個痛苦的真相,於是我就把它美化成為「我沒時間複習,如果我有時間複習,我才不比別人差」。
這個故事你聽起來一定會覺得熟悉。
我做諮詢師這麼多年來,來訪者每次都會帶來一個PS過的問題進入諮詢室,他會說,如果我的孩子聽話就沒事了,如果我老公回心轉意就沒事了,如果我考試過了就沒事了,如果我跟領導的關係處好了就沒事了,如果我找到女朋友就沒事了……
剛做諮詢師的時候,你會陷入來訪者的圈套,你真的幫他處理這些實際的問題。然後你發現,這個問題好了,下一個問題又來了。當你不去面對PS樣貌背後真實的問題的時候,生活總像是和你藏貓兒的小朋友,沒完沒了。
你必須陪伴來訪者,一起在適當的時候,離開美化過的PS位置,起身向D位置行走。
在D位置上,你開始面對「真相」。D位置標準的翻譯是抑鬱位,也譯作「黑暗」。你開始思考你的行為、你的動機,你還要去面對你的脆弱、孤獨、懦弱、恐懼等等。你開始不斷地思考,幾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抑鬱」。
所以我說,一個人能陷入「抑鬱位」是非常勇敢的。待在PS位置上可能很煩躁,但是並不令人恐懼和悲傷;而如果一個人真正開始思考,面對自己的「黑暗」,那是非常勇敢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夠這麼做。35但是一個人並非一定要永遠待在D位置上。你既可以隨時回到PS位置上去喘口粗氣,也可以再憋口氣,完成整個「哀悼」(哀悼你的喪失,比如你再也無法獲得的時間、童年、愛情或是工作)的過程,超越D位置。
讓我來講個超越D位置的故事。
克萊因在她的一本書裡面講了一個A小姐的故事。A小姐的兒子在事故中喪生了,她非常難過,前後做了兩個夢。在第一個夢裡,她進入兒子的房間,為兒子收拾床鋪和書桌,就好像兒子還活著一樣;在第二個夢裡,她走到一個湖邊,她的兒子在湖中央,大聲地喊她:「媽媽,媽媽救我!」她在湖邊站了一會兒,扭頭離開了。
在第一個夢裡,她在一個被美化過的位置。痛苦太大了,而「哀悼」還尚未完成,所以她需要美化這個痛苦:兒子還活著,他還會回來。在第二個夢裡,她走過了D位置,完成了「哀悼」的過程,她用行動表達:你已經不在了,而我還活著,我要繼續活下去。
這個情節大家應該也不陌生。《全面啟動》裡面也講了這麼一個故事:主人公一直不肯面對妻子已故這件事情,直到最後,他坐電梯離開底下那個世界。妻子求他不要離開,他說妳已經死了,而我要繼續生活了。在故事結尾,他終於離開了沉迷的幻象。
所以扯個題外話。去接受心理諮詢不是個特別美妙的過程,是個挺辛苦的,需要耐心和勇氣的過程,因為你要去面對你的抑鬱和黑暗。我年輕一些的時候有些理想主義,會把諮詢描述成一個溫暖美妙的過程。實際上我年紀越大,越覺得不是的,這是個很辛苦的過程。因為你必須要允許你的諮詢師陪你一起沉下去,面對那些黑暗的位置。
幾年前我的督導說,在D位置這個黑暗處有大光芒。我特別不能理解,我說,在這個抑鬱、黑暗的位置為什麼有大光芒呢?督導覺得沒法回答我,就說,你做一做就知道了。
後來我慢慢理解了這個過程,可還是沒辦法用語言描述出來。最接近的語言大概是,你能在黑暗處看見自己和他人最深的力量和勇氣。這給你真的、踏實的信心和希望,讓你能夠帶著對未知的期待和恐懼,唱著歌上路。
讓我來講個自己的故事作為結尾。我在一個督導小組上和督導講了我自己的一個來訪者。那個來訪者每次向我敘述她的困境時,我坐在她對面,都像在聽自己的困境。她的孤獨、哀傷、無望,她描述的每一天的生活,時鐘滴答滴答,就像是另一個我自己生活在另一個空間裡。
在討論的過程中,小組裡面另一個諮詢師問我:「她看起來這麼好,為什麼會絕望呢?」我啞然,想,他們真不了解她呢。督導轉向他說:「你看 Jane,你看她那麼優雅體面,但也許她內心悲傷,甚至絕望。她看起來好不好,和她內心的感受這兩者之間沒有關係,沒有任何關係。」
這是每個人都要做的功課。
人都要最終面對自己的黑暗,哪怕你是所有人的醫治者。你總認為你需要依賴他人的力量,但最終你還是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從黑暗中尋找光芒。
達爾文說,有時候,正視悲傷就像動物趨利避害的本能一樣,引導著我們去做出最有利的行動。黑暗是另外一種光明。
最後,祝願你勇敢,並總能超越你的D位置,在黑暗中見到光芒。
人的成長大概是個理想不斷破滅的過程,聽起來令人難過。比如,你慢慢知道,王子和公主歷經艱難,最後其實並未過上童話裡的生活,不過是柴米油鹽,生兒育女,還要為了買多大的房子、孩子怎麼教育,以及生老病死的各種問題困倦爭吵。
這世上,所謂「美好」,大抵是很少存在的。
前段時間我很煩躁的時候,我媽給我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故事說伊甸園裡的亞當和夏娃在蛇的誘惑下,偷食了禁果,於是人有了羞恥心和好壞之分。於是上帝罰男人永生勞動,女人要忍受十月懷胎之苦,而蛇只能用腹部行走。「所以啊,你來到這世上,本來就是來贖罪的」。
這是你來的本來目的。其實《聖經》早就告訴了人這個道理。
剛開始做心理諮詢的時候,我還是個小丫頭。像每個渴望成為好諮詢師的人一樣,我認真、負責任,睜大眼睛去看來訪者的所謂「症狀」。像插花一樣,渴望將枝條修剪整齊,將顏色搭配好看。我認真地和來訪者說每一句話,渴望把事情做得完美。比如……你看,你可以這樣,你可以那樣,你這麼做,其實會傷害自己,你換個方式。大抵是因為夏娃也咬了那蘋果,在我心裡面,「對錯」、「好壞」是如此清晰。我對我自己同樣苛刻,不要說錯話,不要用錯力,不要做超越範疇的事情,以至於捆綁了手腳。後來我去見督導。督導說,身為一個諮詢師,當你一直用力不犯錯誤,所謂的「一直正確」,正是最大的「錯誤」。
精神分析的治療裡面,治療師有一個原則,叫先跟隨來訪者,同時跳出來觀察,再用它來工作。所謂跟隨來訪者,是治療師允許自己跟隨自己(的感受)來做反應(來訪者的客體能夠在諮詢關係中投射出來,而諮詢師的放鬆,也能夠讓自己被來訪者啟動的那一部分展現在諮詢室內);而治療師要保留一隻眼睛,來觀察這期間的動力和移情5,利用此中有意義的部分,和來訪者工作。
而當諮詢師自己緊張兮兮絕不犯錯,來訪者無法放鬆下來,所謂的「客體」無法登場,治療師自己的阻抗使得自己無法在治療關係中發生作用,治療便無法進行下去。用力過猛,治療便變成雞湯式的「創可貼」了。好在,督導每次總說,你這樣也滿好,我年輕的時候也這樣,沒事兒。好像跑題了。
其實,我原本是打算說,這世上其實並無「好壞」之分,人和人說穿了不過一樣,各有各的掙扎苦痛,各有各的幸福甜蜜。
做諮詢久了,我慢慢不再想要改變來訪者。因為即便是「症狀」,也往往都有其存在的意義。所謂「依賴」也好,「苛責自己」也罷,抑或是抑鬱症、強迫症,其實都不那麼緊要。因為這世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症狀」,無非有人「症狀」消失得更快一些,有人「症狀」消失得更慢一些,而幾乎每個人,直到走進墳墓,也都有著這樣那樣的症狀。可是大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生活,也都過了「差不多」的人生。
所以,諮詢師提的一些具體建議,比如,你換一個思維方式;或者你在網上看到諮詢師寫了你要積極向上,你要學會無條件地去愛等等諸如此類(遍地都是)的話語,這些不過是理想狀態。就像童話故事裡,王子和公主舉行了盛大的婚禮,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樣。
事實上,如果你就是還做不到所謂「積極思維」,就是還沒學會「無條件接納」,沒關係,因為你必然有不能積極思維的原因,必然有不能無條件接納的動機。更何況糾結並非壞事,混沌也非所謂「不好」。這世界上的人,過得「糟糕」是常態,過得「還行」就很少了,如果能夠過得「很好」,那千真萬確是偶然的事情。
別要求自己不難過、不糟糕,混沌、糟糕也是種狀態。而狀態的本質是:它總會變化的。別急。
*****
你總是比想像的更強大一些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我特別抑鬱,因為生活裡面臨的各種衝突,還因為我內心充滿了改變和成長的願望。有天中午我和幾個諮詢師一起吃飯,席間我吐槽不斷,然後有個年長一些的諮詢師跟我說,恭喜你哦,一個人沒有經歷過抑鬱,是無法成為一個好的諮詢師的。
這句話當然是句玩笑話,可是我覺得是真的。一個好的諮詢師,一定要走長長長長的道路,去發現和面對真實的自己。這是個鮮血淋漓的過程。一個人真正去撥開自己的外殼,面對自己的內心,這是非常需要勇氣,並且帶著撕裂一般疼痛的事情。你不得不去面對你生命中那些有意無意的、你想要隔離開但潛意識偷偷幫你收拾起來的、藏匿不見的創傷;你不得不面對自己的軟弱無助、羞愧、憤怒和悲傷。尤其是當一個人學了些皮毛知識,一瓶子不滿半瓶子響叮噹的時候,對自己的行為、情緒異常敏感並將其放大,經常亂貼標籤,看自己哪兒都是問題。簡直不能活命。
因此我很感激我生活中的朋友。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無法用正常的語言來描述一件雞毛蒜皮的事情。比如我燒壞了一口鍋,我會坐下來,嘟嘟囔囔,從我三歲以前跟我媽的互動關係、我媽和她媽媽的互動關係,還有我和我爸的互動關係、我爸和他爸爸的互動關係,再加上我爸和我媽之間的互動關係,一直講到它是如何影響我深層次的人格形成、影響我今天的行為,我的潛意識如何發生阻抗,以至於把鍋燒壞的。
我的朋友是多麼善良的一群人啊!他們出於各種原因,沒有直接將我從座位上面踢下去。多數時候,他們非常、非常憂慮地看著我,說,真的,Jane,你想多了。
可是在瞭解自己的途中,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至少是我經歷的一個過程。努力地去探尋,需要支援,也需要幫助。人們常常說,你是一個心理諮詢師,你一定更知道怎樣快速地調節情緒。那,其實我並不知道如何能讓自己馬上開心起來,可是我想,在這條長長的、自我探索的道路上,「瞭解自己」本身給了我很多勇氣和力量,讓我在困難的情形下,更容易接納自己的脆弱、無能、恐懼和憤怒,諸如此類,哪怕在別人看來有些神經兮兮。
其實,當人們能夠理解自己,理解自己行為背後的動力、能量,被自己接納、理解、支持,而不被自己苛責、不近人情地要求的時候,人是有無窮無盡的力量和智慧,來面對生活裡面的七七八八左左右右的。
心理諮詢師希望能夠盡一切的力量,幫助人們更安全、更勇敢地走過這條長長的、黑暗的道路。然後有一天,當你千真萬確放下對自己的束縛,和自己站在一起的時候,你總是比你想像的更強大一些。
*****
要照顧別人,先照顧好自己
前段時間我在單向街講抑鬱症,講到什麼是好的陪伴、好的共情,講到陪老爺爺哭的小男孩兒的故事。大意是說當朋友抑鬱的時候,我們應該陪他哭,而不急於將他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講座結束之後,有人提問說,自己就是這樣陪伴自己的朋友,可是時間一久,自己也難堪重負,心生逃離的念頭。又覺得自己怎能這樣可惡,在朋友需要的時候,不做個「合格」的朋友?怎麼能在朋友需要自己的時候,不陪著他哭,反而想逃離呢?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還是讓我先來講講心理諮詢吧。
心理諮詢師的入門課,便是要讓諮詢師看清楚這樣一個事實:你自己的力量幫不到任何一個人。一個人之所以能夠改變他的生活態度,之所以「好」起來,仰仗的是他自己內在的力量。
諮詢師倘若相信自己的「武功蓋世」,便是自戀地剝奪了來訪者本來的生長。這一方面使得諮詢師變得像小學老師一樣高大偉岸又面目可憎,一方面使來訪者不斷體驗挫敗── 諮詢師比我更強大,我總是依靠別人的力量才能感到好一點兒。
Stephen King(史蒂芬.金)31談寫作的時候說,故事就像是埋在地下的一個化石,作家的任務是不斷地往下挖掘,直到將整個化石完整地挖出來。他說,不要試圖去構造故事,它們在你到達之前已經在那兒了。
我想心理諮詢是一樣的。心理諮詢師沒有能力去賦予任何來訪者能力、信心、勇氣或是其他任何一樣東西。這些能力、信心、勇氣、力量,在你遇見來訪者之前,已經在他的身體裡面居住很久了。而諮詢師的任務,不過是像作家、考古學家一樣,將它們從重重灰塵迷霧之中,還原出來。
所以,諮訪關係(治療師和來訪者的關係)的本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和另一個普通人的關係。一個人但凡存在,就必然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軟弱。來訪者是這樣,諮詢師也是。諮詢師在相信來訪者有力量的同時,也要承受來自來訪者的壓力、阻抗、攻擊和種種測試,難免受到「傷害」,想逃離。
於是督導老師常常說:在諮訪關係中,治療師的首要任務是先讓自己在這段關係裡面生存下來,然後來訪者才能有信心,和你一起走下去。
你看,連靠此吃飯的治療師,都要先在諮訪關係中保全自己,然後才能繼續工作啊!
所以回到我們討論的問題上:你是如此努力地想做完美的朋友或家人,但當你不堪重負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我今天整理郵件,然後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回答類似這樣的詢問我幾乎可以做一個範本出來,下面這些話,我用不同的方式,或長或短,寫了無數遍:你好,謝謝來信。
你在他身邊,這樣用心地陪他,已經做得足夠好了。
你作為一個朋友,並不能夠承擔更多的事情,比如說負責他的情緒、保護他的安全。如果你要全權為他負責,這超越了朋友或家人(甚至人和人之間)的界限。
作為朋友,給予適當的陪伴(而非超越你個人能力的陪伴)即可,同時,他也需要你真實的回饋(如:傾訴你的壓力,給予建議,甚至表達你自己的不滿等等)。專業的諮詢或治療請交給他的諮詢師去做。如果一定要打破界限(長期的、二十四小時的關注),你可以求助他的家人(更多其他家人)或相關的社會機構。你做得已經很多、很好了。
要照顧好別人,先照顧好自己。這樣照顧才是可持續的。
祝好。
簡里里
*****
黑暗中見到光芒
最近常有人來問我能不能分享些跟心理相關的話題。我每次都高興應允,說那我來分享一下抑鬱這個主題吧,主辦方都面露難色,問:能不能講點兒積極的、正能量的?
我覺得很尷尬,因為其實我私下覺得在諸多和心理相關的主題裡面,所謂的「抑鬱」和「不高興」是最有「正能量」和光芒的。所以我總是想來給「抑鬱」正一正名,剝繭抽絲,窺見它的價值。
我上大學的時候大家還流行手寫信,每次寫信都和朋友相互問候最近開心嗎、過得好嗎。出國之前,我從來不知道「不開心」是什麼意思,雖然每次都寫這個問候語作為開頭,但權作禮貌。直到我出國以後有了抑鬱的「症狀」感受,「開心」和「不開心」才真的進入我的意識裡面。
我為自己「不高興」這件事情糾結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直到看到這麼一句話:「一切在哲學、詩歌、藝術、政治領域成績卓著的人,即使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也不例外,都是憂鬱的常客。」我才釋然了。
嘿,原來我有做天才的潛質。
玩笑歸玩笑。回顧我的每一次「抑鬱」發作,都會帶來無與倫比的價值。所以我們不講臨床診斷的「抑鬱症」,我們來講一講「不高興」的價值。
有一個精神分析的前輩,叫梅蘭妮.克萊因,她是客體關係理論的創始人。她提出了人在心理上有兩個特殊的位置:PS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即偏執分裂樣位置;另一個是D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就是抑鬱位置。這個理論背後有很複雜的東西,不細贅了。但我想借用她的PS位置和D位置講一講抑鬱的價值。
先讓我講一個自己的故事。我上大學的時候不好好學習,每次都差一點點拿不到獎學金。我每次去見老師的時候,都跟她說,我只花了一個晚上看書,所以沒考好,如果我花一個星期看書的話就一定沒問題。
直到有一天,我的老師跟我說,Jane 你知道嗎,你每次都跟我說你是準備的時間不足,但我覺得,你根本就是在害怕失敗,你害怕你複習一週也考不到前面去,所以給自己找了這麼個藉口。
老師的這句話如當頭一棒。因為她說的是對的,我不敢面對的是我對失敗的恐懼。
所以她說完這番話之後,我不得不面對我自己的恐懼和懦弱。你可以想像,我在奮起之前,陷入了漫長的思考和不高興。
我從自己的PS位置,走向了D位置。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聽我的督導這麼講,他說你可以把PS位理解為 Photoshop(美化圖片軟體),就是說在這個位置上,你會把「痛苦的真相」PS(美化)成你可以接受的樣子。比如,我不願意去面對「我恐懼失敗」這個痛苦的真相,於是我就把它美化成為「我沒時間複習,如果我有時間複習,我才不比別人差」。
這個故事你聽起來一定會覺得熟悉。
我做諮詢師這麼多年來,來訪者每次都會帶來一個PS過的問題進入諮詢室,他會說,如果我的孩子聽話就沒事了,如果我老公回心轉意就沒事了,如果我考試過了就沒事了,如果我跟領導的關係處好了就沒事了,如果我找到女朋友就沒事了……
剛做諮詢師的時候,你會陷入來訪者的圈套,你真的幫他處理這些實際的問題。然後你發現,這個問題好了,下一個問題又來了。當你不去面對PS樣貌背後真實的問題的時候,生活總像是和你藏貓兒的小朋友,沒完沒了。
你必須陪伴來訪者,一起在適當的時候,離開美化過的PS位置,起身向D位置行走。
在D位置上,你開始面對「真相」。D位置標準的翻譯是抑鬱位,也譯作「黑暗」。你開始思考你的行為、你的動機,你還要去面對你的脆弱、孤獨、懦弱、恐懼等等。你開始不斷地思考,幾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抑鬱」。
所以我說,一個人能陷入「抑鬱位」是非常勇敢的。待在PS位置上可能很煩躁,但是並不令人恐懼和悲傷;而如果一個人真正開始思考,面對自己的「黑暗」,那是非常勇敢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夠這麼做。35但是一個人並非一定要永遠待在D位置上。你既可以隨時回到PS位置上去喘口粗氣,也可以再憋口氣,完成整個「哀悼」(哀悼你的喪失,比如你再也無法獲得的時間、童年、愛情或是工作)的過程,超越D位置。
讓我來講個超越D位置的故事。
克萊因在她的一本書裡面講了一個A小姐的故事。A小姐的兒子在事故中喪生了,她非常難過,前後做了兩個夢。在第一個夢裡,她進入兒子的房間,為兒子收拾床鋪和書桌,就好像兒子還活著一樣;在第二個夢裡,她走到一個湖邊,她的兒子在湖中央,大聲地喊她:「媽媽,媽媽救我!」她在湖邊站了一會兒,扭頭離開了。
在第一個夢裡,她在一個被美化過的位置。痛苦太大了,而「哀悼」還尚未完成,所以她需要美化這個痛苦:兒子還活著,他還會回來。在第二個夢裡,她走過了D位置,完成了「哀悼」的過程,她用行動表達:你已經不在了,而我還活著,我要繼續活下去。
這個情節大家應該也不陌生。《全面啟動》裡面也講了這麼一個故事:主人公一直不肯面對妻子已故這件事情,直到最後,他坐電梯離開底下那個世界。妻子求他不要離開,他說妳已經死了,而我要繼續生活了。在故事結尾,他終於離開了沉迷的幻象。
所以扯個題外話。去接受心理諮詢不是個特別美妙的過程,是個挺辛苦的,需要耐心和勇氣的過程,因為你要去面對你的抑鬱和黑暗。我年輕一些的時候有些理想主義,會把諮詢描述成一個溫暖美妙的過程。實際上我年紀越大,越覺得不是的,這是個很辛苦的過程。因為你必須要允許你的諮詢師陪你一起沉下去,面對那些黑暗的位置。
幾年前我的督導說,在D位置這個黑暗處有大光芒。我特別不能理解,我說,在這個抑鬱、黑暗的位置為什麼有大光芒呢?督導覺得沒法回答我,就說,你做一做就知道了。
後來我慢慢理解了這個過程,可還是沒辦法用語言描述出來。最接近的語言大概是,你能在黑暗處看見自己和他人最深的力量和勇氣。這給你真的、踏實的信心和希望,讓你能夠帶著對未知的期待和恐懼,唱著歌上路。
讓我來講個自己的故事作為結尾。我在一個督導小組上和督導講了我自己的一個來訪者。那個來訪者每次向我敘述她的困境時,我坐在她對面,都像在聽自己的困境。她的孤獨、哀傷、無望,她描述的每一天的生活,時鐘滴答滴答,就像是另一個我自己生活在另一個空間裡。
在討論的過程中,小組裡面另一個諮詢師問我:「她看起來這麼好,為什麼會絕望呢?」我啞然,想,他們真不了解她呢。督導轉向他說:「你看 Jane,你看她那麼優雅體面,但也許她內心悲傷,甚至絕望。她看起來好不好,和她內心的感受這兩者之間沒有關係,沒有任何關係。」
這是每個人都要做的功課。
人都要最終面對自己的黑暗,哪怕你是所有人的醫治者。你總認為你需要依賴他人的力量,但最終你還是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從黑暗中尋找光芒。
達爾文說,有時候,正視悲傷就像動物趨利避害的本能一樣,引導著我們去做出最有利的行動。黑暗是另外一種光明。
最後,祝願你勇敢,並總能超越你的D位置,在黑暗中見到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