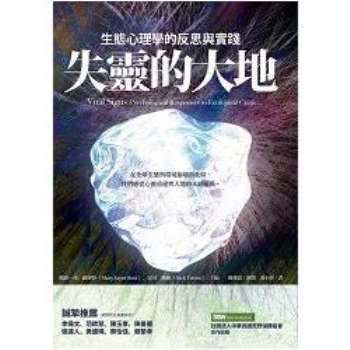引言
真正的前景非常黑暗,所以任何嚴肅的思考都應該從這個事實出發。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我們不知道也無法得知:我們來此是要擔任這世界的臨終看護者,還是地球生命新篇章的接生婆。
──喬安娜‧梅西(Joanna Macy)
心理實務工作者反映出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樣貌──包括它的各種分支。在我們的能力發揮到極致時,我們也對社會產生反思,發現它的種種問題,並提供各種向前邁進的可能性;甚至反省我們與它的關係。所有這些運作過程都可見於本文集,因為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呈現整個心理世界──包括諮商、心理治療、榮格分析、精神分析和其他較鮮為人知的心理學──對於我們的社會正在面臨的眾多生態危機,所做出的廣泛與多樣回應。已在英國進行的相關工作是本書的重心,但也納入幾篇美國及歐洲作者的文章,因為這些作者提供了重要的觀點。某些篇章的學術風格濃厚,某些則迥然相異,多數文章是介於兩者之間。
當然,「生命徵象」(Vital Signs)是醫護人員用來評估病人情況的嚴重性時,所使用的基本生理機能測量值。這本文集的主要焦點不是在物質世界中、當許多地球系統受到嚴重壓迫並開始崩潰時,人們所面臨的困境;這類資訊在其他許多地方都可以取得(Lovelock,2010)。反之,我們關心的是人們在心理上所面臨的困境,隨著生態情勢的新聞逐漸穿透我們的防線,每個人和社會整體都使勁地想要找到一個適當的回應。我們所謂的「生命徵象」,指的就是這樣的回應已經開始成形:希望的跡象、療癒的跡象。
西方世界普遍都花了幾十年,才開始認真地面對各種環環相扣的危機,回想起來這些問題至少在一九五○年代就已明顯可見,而心理實務界的人士也一樣。英國最早的倡議行動或許是在一九八○年代中期,當保羅‧芬克(Paul Fink)和其他人受到喬安娜‧梅西的「絕望與賦權」(Joanna Macy,1983)工作的啟發,創立了一個英國的互助網絡(Interhelp Network,Senders,1994);當時主要的焦點是在核子彈上,但環境議題始終是主題的一部分。還有其他人,諸如保羅‧馬特尼(Paul Maiteny)、葛拉漢‧甘姆(Graham Game)及珍妮‧古魯特(Jenny Grut),也在這段時間開始,將生態學與心理學連結在一起。稍後,部分受到美國發展的啟發,希拉蕊‧普林特斯(Hilary Prentice)和塔妮亞‧都利(Tania Dolley)於一九九五年成立了一個生態心理學團體,也是是新成立的組織「心理治療師及諮商師之社會責任」(PCSR)的一部分;瑪麗─簡恩‧若斯特(Mary-Jayne Rust)也成為該團體的一員。兩年後,希拉蕊和塔妮亞創立了英國生態心理學網絡(UK Ecopsychology Network),它的後裔就是現今的生態心理學英國線上網絡(Ecopsychology UK Online Network),擁有超過六百位成員。尼可‧托頓(Nick Totton)受到伙伴海倫‧弗雀爾(Hélène Fletcher)的影響,在二○○三年主動與生態心理學連結;尼可、海倫、瑪莉─簡恩以及希拉蕊,於二○○四年在鄧弗里斯(Dumfries)附近的羅里斯敦霍爾(Laurieston Hall)共同組織了一個生態心理學聚會。這些不過是正在逐漸加速發展與連結過程中的片段而已。
然而,環境議題進入主流心理治療的速度相當遲緩,一如它進入主流文化的速度也相當遲緩。撰寫本書之際,英國的心理治療師與心理治療組織,似乎正在組成一個跨模式的聯盟,目標是要將心理治療界中,嘗試面對目前情境的不同團體與個人聚集在一起。PCSR在其中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過去幾年,已有許多以生態心理學為主題的研討會及活動登場。經過這一切活動,卡爾那克出版社(Karnac Books)的奧勒弗‧拉斯朋(Oliver Rathbone)邀請我們製作這本文集,並且承諾要快速出版。
奧勒弗賦予我們對文集的自由決定權。我們思考過各種可能性,例如歐洲地區的、專注於臨床應用的、來自世界各地特別令人激賞的文章等,然而收集這些文章的程序看起來非常複雜,或者能夠提供的資料不是過多就是太少。由於這個領域的許多文章源自美國,我們最後決定為英國的作者集結文集,但並不嚴格自限;我們的目的是要呈現出現有的廣泛多樣的作品,而不是只選擇同好的作品。書中有多位作者並無出版品,或者出版經驗較少,不過他們在生態心理學的領域都相當活躍。我們認為,英國的生態心理學具有特殊的觀點和獨特的貢獻。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領域中促進討論與對話,以期能引發更多發展完整的理論與實作。要將生態心理學建構成一門學科、清楚表達出各種作法之間的相容性或不相容性的關係,這一切都還在早期發展階段。這個領域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發展成熟,在術語用詞上達成協議(或在使用不同術語上達成協議),並且發展出有組織的形態。這是任何新觀點都要經歷的常見過程。
雖然認知到這段成熟過程的緩慢,我們當然也同樣清楚外在環境所面臨的緊急狀態,這是生態心理學家要實現的使命之一。在理論方面,縱使沒有環境崩潰的議題需要面對,生態心理學仍然非常重要,這個領域探索著人類與人類以外的一切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兩者共存時所產生的治療價值;在現實方面,災難帶來的失落、生命複雜性遭到不可逆轉的破壞、以及維持地球生命的系統即將面臨的威脅等,則完全引導著生態心理學的發展。
從這個角度看來,生態心理學也是為氣候變遷及其他正在發生的生態危機(污染、資源的過度消耗、棲地的破壞等)發展覺察力的更大運動的一部分。然而除了聚焦於心理學之外,生態心理學與這場大運動中其他參與者不同的幾個觀點,在於廣泛地知覺人類只是全球生態系統的元素之一;並且在道德上與實務上形成共識,認為人性無法把其他物種拋出救生船而拯救自己。生態系統的成敗將由人類、人類之外(other-than human)、超越人類(more-than human)的一切,共同承擔;無法認清這一點,是我們的文化從廣大整體中解離出來的症狀,也是導致我們陷入目前情況的肇因之一。
在這個領域努力了許久的人士之間,流傳著越來越令人憂心的問題:萬一我們失敗了怎麼辦?萬一人類社會無法過渡到無碳經濟模式(carbon-free economy)──其他需要同時發生的文化與實務上的轉變,也無法發生怎麼辦?在每個可能的模式中,剩下的時間都非常緊迫;全球生態系統的重大破壞已經確鑿無疑,科學家預測「引爆點」效應(“tipping point” effect)即將失控。儘管人們對這個危機的覺察度已經比十年前高,但大眾的態度並沒有重大的改變跡象。確實,在英國和其他地區,人們對於生態議題的關注被近來的經濟危機所遮掩,似乎一點也沒有察覺到生態、社會和經濟危機是完全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我們既無法肯定地預測未來,也沒有多少值得樂觀的具體基礎。接下來又該怎麼辦?
或許生態心理學在未來的角色,是幫助人們面對伴隨「世界末日」而來的痛苦與絕望,並且保存某種希望。就我們所能預見的,世界並不會就此結束;但現今的人類社會、我們成長於其中的世界,將不復存在:數萬億的人類及非人類生物將會死亡,正在發生中的物種大滅絕即將加速,地球的很大一部分將無法住人。不過,在任何情況下都將有某種倖存者,極小部分的人類很可能是那「某種倖存者」的一部分,必須取得所需的一切協助,才能心智健全地活下去,帶著健全的文化種子前進、建立生態意識。生態心理學目前存在的形態,或許是這種未來所需的理論或實務的起始點。
不過,儘管世界其他地區正因為我們富裕的生活風格而成為受害者,承受著苦難,我們也尚未走到末日的田地,而生態心理學也還無法承接那樣的重責大任。這本文集所提供的,是關於生態心理學當前發展的樣本,以及它可能發展的方向。我們希望這些文章能讓以下社群產生興趣,並為之所用:已經涉入生態心理學領域,且想要發展與精煉想法的人;開始有所覺察,想要了解更多現況及該從何處加入的人;關心人類與其所屬生態系統的關係、想尋找能夠探索這些關係的方法,及是什麼使這段關係產生問題的任何人。
我們將本書分為六部,一如往常,這種分類總是有些武斷,因為許多章節可以被合理地分類到不只一部之中,且許多章節的材料包含了不只一部的主題。特別是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每一章都談及在當前的嚴重情況下可以做些什麼。不過,感覺上有分類的幫助更大,以下是我們所選擇的分類。
第一部〈脈絡〉包含了四章,聚焦於為我們所處的現況提供各種觀點,即生態危機及其心理影響和肇因。在開場的第一章,薇奧拉‧山普森(Viola Sampson)為氣候變遷帶來了具體的而非智性上的探索,試圖將理性的回應深植於情感的土壤之中,在大環境中找到地區性的地位,並且使物質世界與愛連結,因為這是唯一有效的行動基礎。蘇姍‧巴德納爾(Susan Bodnar)為我們的各種理論提供了不同的紮根方式,利用一份可被稱為精神分析式之微觀人類學(psychoanalytical micro-anthropology)的研究中,詳細記載某些紐約居民對於氣候變遷的反應。彼得‧查特洛斯(Peter Chatalos)在本文集中最早問世的文章裡,以愛滋病來比喻地球對我們的「文化自閉症」(cultural autism)所產生的全球免疫反應。保羅‧馬特尼以非常有效的方式,跨越多數早期文獻的紋理,思考人類在地球上的角色有何獨特之處,這獨特之處可以如何有創意地運用,而不是破壞。
接續薇奧拉的文章,第二部專注於〈非人類及超越人類〉,越來越多人使用這個片語來描述地球上的其他物種及現象,使它們與人類至少有平等的立足之地。瑪格麗特‧柯爾(Margaret Kerr)及大衛‧基(David Key)寫到與地方的關係,及在野外獨處如何能開啟我們的無意識及超個人經驗。凱文‧霍爾(Kevin Hall)及布萊德蕭(G. A. Bradshaw)兩人以截然不同的風格提出假設,認為人類鑲嵌於與其他物種關係中的優越感,對於我們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多麼具有破壞性,而如果這些關係能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又將帶來多少益處。在第二部最後一章,英格爾‧柏克蘭(Inger Birkeland)及亞斯翠‧阿森(Astri Aasen)精采地描述了挪威一群孩子,以孩子有機會時就能發揮的本能,與當地一片超越人類的小地方所建立的一段充滿想像力的關係。這四個篇章及其他書籍中要描述的強烈訊息是在這場危機中,人類必須在超越自身物種利害關係以外的地方尋找解決之道。相較之下,以〈後現代主義觀點〉為主題的第三部是以智性而非感性的方式來表達作者對生態的看法,對他們所見到的單純而浪漫的「自然」紀錄提出評論(我們這篇引言中努力避開使用「自然」一詞,但有很好的理由)。馬丁‧喬丹(Martin Jordan)及約瑟夫‧塔茲(Joseph Dodds)運用多種評論理論,主要是德勒茲(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理論,分別探索了生態心理學的可能性,嚴厲地質疑生態心理學的假設及特權概念。這個取向在風格和內容上都與我們熟悉的方法大有逕庭,但我們認為它為這個領域添加了重要的自我質疑元素。
最後三部從各種面向探索了關鍵的問題:我們能做什麼?首先是〈如何是好:可能的未來〉,其中包括了四篇文獻回顧,主題在於如何使人類文化深入到心的改變中,也就是喬安娜‧梅西所謂「大轉變」(The Great Turning)的變化版。瑪麗-珍‧羅斯特的焦點在於重新找回與非人類及超越人類領域的親密關係,及喪失這段親密關係所造成的傷痛。米克‧柯林斯(Mick Collins)及共同作者運用了史丹‧葛羅夫(Stan Grof)「靈性浮現」(spiritual emergence)的概念為中心意象,表現出以下的改變:根據葛羅夫和其他人的理念,許多個別情感危機,及傳統上被稱為「崩潰」(breakdowns)的情緒,也是一種「突破/崩越」(break-throughs),是創造轉變的機會,作者並且認為這種情況也以全球性的規模發生中。希拉蕊‧普林特斯提供的是目前英國在生態學與心理學關係上的部分歷史,並且透過英國第一個轉型城鎮托特尼斯(Transition Town Totnes)的「心與靈團體」(Heart and Soul Group),記錄了這段歷史近期的繁華發展,她也分享了她對「生態與心理」的反思。傑洛米‧伯恩斯坦(Jerome Bernstein)的文章溫暖而親和地總結了他對於邊界意識(Borderland consciouness)的概念,「為自我(ego)之外的力量所形塑,打開自己以接受所有生命系統彼此相連且互相依賴的事實」,他透過不同的文字,描寫出與柯林斯等人所描述的靈性浮現現象一致的景象。xxi
〈如何是好:影響態度〉提出四篇根據心理學的取向,如何改變與環境議題相關的人類行為。湯姆‧克朗普頓(Tom Crompton)運用他參與環境運動的廣泛經驗以及諸多研究發現,主張「個人越是認同自我內在的目標及自我超越的價值,也就越能對非人類的自然表現出正面的態度及行為」,因此若僅只倡議改變人們的作為,這種運動本身的價值就很有限。珊德拉‧懷特(Sandra White)提供了一種對於何以人們具有環境意識卻未能進一步行動的理解方式,她將焦點放在否認(denial),以及犧牲的意義上。這一部的最後兩篇文章分別探討了特定的倡議行動實務。蘿絲瑪麗‧藍黛爾(Rosemary Randall)敘述了劍橋的「碳會談」(Carbon Conversations)計畫,與小團體共同促進低消費的生活風格。大衛‧基和瑪格麗特‧柯爾於本書的第二篇文章描述了他們「自然改變計畫」(Natural Change Project)的故事,這個由世界自然基金會蘇格蘭分會(WWF Scotland)所成立的計畫,試圖在荒野地區將生態心理學運用於實務工作,參與者是由受邀的個人所組成的小團體,這些人在各種領域中有其影響力,但過去不曾主動參與環境議題。
本書大多數(而非全部)作者是心理治療師、諮商師或分析師;有趣的是,目前為止所提到的篇章中,對於治療本身的討論極少。這是本書最後一部的主題,〈如何是好;臨床實務〉。尼可‧托頓的文章探討了生態思維與情感或許真的能改變心理治療的實務,而不只是被用來當作「補強」工具。克里斯‧羅伯斯頓(Chris Roberston)以優美的文字,來回穿梭於臨床小品文和普通生態理論之間,說明兩者可以如何啟發彼此,以及個案的「病症和弱點本身」如何「成為原料,在他與超越人類的存在之間,幫忙建構連結感及隨之而來的受呵護感。」
在如此豐富和多樣的文集中,最突出的主題為何呢?基於資料來源,我們可以想像本書收集的文章,會強調在基於情況所需做出實務上的改變之前,必須先在心理上有深層的改變。如稍早提及的,情況的緊急程度與為此必須付出的情緒轉變程度之間,存在著緊繃的張力。我們希望很多事情能更早發生,但卻沒有,因此也無疑地不可能達成了。如同在科技領域,目前在心理學領域至關緊要的,也是以一種可行的速度、穩定地努力下去,而非因為恐慌而喪失了我們的精熟技能。
此外,文集中所有作者除了對情況的嚴重性意見一致,其餘幾乎完全沒有共識。最明顯的主題,其實是彼此之間的差異:每位作者都表達了與其他多數人不同的觀點,也對情勢的某些面向提出了自己的診斷及(或)補救辦法。我們甚至很難看出大家投入的是相同的任務,或屬於同一領域的一份子。讀者甚至會想問:到底一個可識別的「生態心理學」領域是否真的存在?然而,這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個健康的跡象,一個生命徵象!而不是缺陷。在心理層次及實務層次上,我們正目睹各種創造性的想法和局部的解決之道開花結果,目前為止,沒有人知道哪個或哪些作法最有效。(不過我們很肯定的是,在本書中不斷出現的主題,即化解人類與其他物種間的隔閡、個人與世界的隔閡及「內在」與「外在」的隔閡,對情勢的發展十分重要。)
如薇奧拉‧山普森在她的文章中,引用了某些常見的環境保護主題所說的,或許我們只是像在鐵達尼號上把躺椅搬來搬去一樣,在面對龐大到無法理解、遑論能對它發揮影響力的事件時,做著無謂的事情好讓我們的頭腦保持忙碌。就某種程度上,情況確實如此。然而,社會運動的基本原則,是沒有人能夠隻手改變世界;這永遠是一項過度龐大的任務,而我們只能盡量以自己的方式,做到自己能力所及的事。如我們在前面提出的理由,對我們而言,目前的任務面向之一,也是一個在許多層次上都具有價值的面向,就是去思索生態危機中的心理面向;而本書所收集的文章對這項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真正的前景非常黑暗,所以任何嚴肅的思考都應該從這個事實出發。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我們不知道也無法得知:我們來此是要擔任這世界的臨終看護者,還是地球生命新篇章的接生婆。
──喬安娜‧梅西(Joanna Macy)
心理實務工作者反映出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樣貌──包括它的各種分支。在我們的能力發揮到極致時,我們也對社會產生反思,發現它的種種問題,並提供各種向前邁進的可能性;甚至反省我們與它的關係。所有這些運作過程都可見於本文集,因為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呈現整個心理世界──包括諮商、心理治療、榮格分析、精神分析和其他較鮮為人知的心理學──對於我們的社會正在面臨的眾多生態危機,所做出的廣泛與多樣回應。已在英國進行的相關工作是本書的重心,但也納入幾篇美國及歐洲作者的文章,因為這些作者提供了重要的觀點。某些篇章的學術風格濃厚,某些則迥然相異,多數文章是介於兩者之間。
當然,「生命徵象」(Vital Signs)是醫護人員用來評估病人情況的嚴重性時,所使用的基本生理機能測量值。這本文集的主要焦點不是在物質世界中、當許多地球系統受到嚴重壓迫並開始崩潰時,人們所面臨的困境;這類資訊在其他許多地方都可以取得(Lovelock,2010)。反之,我們關心的是人們在心理上所面臨的困境,隨著生態情勢的新聞逐漸穿透我們的防線,每個人和社會整體都使勁地想要找到一個適當的回應。我們所謂的「生命徵象」,指的就是這樣的回應已經開始成形:希望的跡象、療癒的跡象。
西方世界普遍都花了幾十年,才開始認真地面對各種環環相扣的危機,回想起來這些問題至少在一九五○年代就已明顯可見,而心理實務界的人士也一樣。英國最早的倡議行動或許是在一九八○年代中期,當保羅‧芬克(Paul Fink)和其他人受到喬安娜‧梅西的「絕望與賦權」(Joanna Macy,1983)工作的啟發,創立了一個英國的互助網絡(Interhelp Network,Senders,1994);當時主要的焦點是在核子彈上,但環境議題始終是主題的一部分。還有其他人,諸如保羅‧馬特尼(Paul Maiteny)、葛拉漢‧甘姆(Graham Game)及珍妮‧古魯特(Jenny Grut),也在這段時間開始,將生態學與心理學連結在一起。稍後,部分受到美國發展的啟發,希拉蕊‧普林特斯(Hilary Prentice)和塔妮亞‧都利(Tania Dolley)於一九九五年成立了一個生態心理學團體,也是是新成立的組織「心理治療師及諮商師之社會責任」(PCSR)的一部分;瑪麗─簡恩‧若斯特(Mary-Jayne Rust)也成為該團體的一員。兩年後,希拉蕊和塔妮亞創立了英國生態心理學網絡(UK Ecopsychology Network),它的後裔就是現今的生態心理學英國線上網絡(Ecopsychology UK Online Network),擁有超過六百位成員。尼可‧托頓(Nick Totton)受到伙伴海倫‧弗雀爾(Hélène Fletcher)的影響,在二○○三年主動與生態心理學連結;尼可、海倫、瑪莉─簡恩以及希拉蕊,於二○○四年在鄧弗里斯(Dumfries)附近的羅里斯敦霍爾(Laurieston Hall)共同組織了一個生態心理學聚會。這些不過是正在逐漸加速發展與連結過程中的片段而已。
然而,環境議題進入主流心理治療的速度相當遲緩,一如它進入主流文化的速度也相當遲緩。撰寫本書之際,英國的心理治療師與心理治療組織,似乎正在組成一個跨模式的聯盟,目標是要將心理治療界中,嘗試面對目前情境的不同團體與個人聚集在一起。PCSR在其中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過去幾年,已有許多以生態心理學為主題的研討會及活動登場。經過這一切活動,卡爾那克出版社(Karnac Books)的奧勒弗‧拉斯朋(Oliver Rathbone)邀請我們製作這本文集,並且承諾要快速出版。
奧勒弗賦予我們對文集的自由決定權。我們思考過各種可能性,例如歐洲地區的、專注於臨床應用的、來自世界各地特別令人激賞的文章等,然而收集這些文章的程序看起來非常複雜,或者能夠提供的資料不是過多就是太少。由於這個領域的許多文章源自美國,我們最後決定為英國的作者集結文集,但並不嚴格自限;我們的目的是要呈現出現有的廣泛多樣的作品,而不是只選擇同好的作品。書中有多位作者並無出版品,或者出版經驗較少,不過他們在生態心理學的領域都相當活躍。我們認為,英國的生態心理學具有特殊的觀點和獨特的貢獻。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領域中促進討論與對話,以期能引發更多發展完整的理論與實作。要將生態心理學建構成一門學科、清楚表達出各種作法之間的相容性或不相容性的關係,這一切都還在早期發展階段。這個領域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發展成熟,在術語用詞上達成協議(或在使用不同術語上達成協議),並且發展出有組織的形態。這是任何新觀點都要經歷的常見過程。
雖然認知到這段成熟過程的緩慢,我們當然也同樣清楚外在環境所面臨的緊急狀態,這是生態心理學家要實現的使命之一。在理論方面,縱使沒有環境崩潰的議題需要面對,生態心理學仍然非常重要,這個領域探索著人類與人類以外的一切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兩者共存時所產生的治療價值;在現實方面,災難帶來的失落、生命複雜性遭到不可逆轉的破壞、以及維持地球生命的系統即將面臨的威脅等,則完全引導著生態心理學的發展。
從這個角度看來,生態心理學也是為氣候變遷及其他正在發生的生態危機(污染、資源的過度消耗、棲地的破壞等)發展覺察力的更大運動的一部分。然而除了聚焦於心理學之外,生態心理學與這場大運動中其他參與者不同的幾個觀點,在於廣泛地知覺人類只是全球生態系統的元素之一;並且在道德上與實務上形成共識,認為人性無法把其他物種拋出救生船而拯救自己。生態系統的成敗將由人類、人類之外(other-than human)、超越人類(more-than human)的一切,共同承擔;無法認清這一點,是我們的文化從廣大整體中解離出來的症狀,也是導致我們陷入目前情況的肇因之一。
在這個領域努力了許久的人士之間,流傳著越來越令人憂心的問題:萬一我們失敗了怎麼辦?萬一人類社會無法過渡到無碳經濟模式(carbon-free economy)──其他需要同時發生的文化與實務上的轉變,也無法發生怎麼辦?在每個可能的模式中,剩下的時間都非常緊迫;全球生態系統的重大破壞已經確鑿無疑,科學家預測「引爆點」效應(“tipping point” effect)即將失控。儘管人們對這個危機的覺察度已經比十年前高,但大眾的態度並沒有重大的改變跡象。確實,在英國和其他地區,人們對於生態議題的關注被近來的經濟危機所遮掩,似乎一點也沒有察覺到生態、社會和經濟危機是完全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我們既無法肯定地預測未來,也沒有多少值得樂觀的具體基礎。接下來又該怎麼辦?
或許生態心理學在未來的角色,是幫助人們面對伴隨「世界末日」而來的痛苦與絕望,並且保存某種希望。就我們所能預見的,世界並不會就此結束;但現今的人類社會、我們成長於其中的世界,將不復存在:數萬億的人類及非人類生物將會死亡,正在發生中的物種大滅絕即將加速,地球的很大一部分將無法住人。不過,在任何情況下都將有某種倖存者,極小部分的人類很可能是那「某種倖存者」的一部分,必須取得所需的一切協助,才能心智健全地活下去,帶著健全的文化種子前進、建立生態意識。生態心理學目前存在的形態,或許是這種未來所需的理論或實務的起始點。
不過,儘管世界其他地區正因為我們富裕的生活風格而成為受害者,承受著苦難,我們也尚未走到末日的田地,而生態心理學也還無法承接那樣的重責大任。這本文集所提供的,是關於生態心理學當前發展的樣本,以及它可能發展的方向。我們希望這些文章能讓以下社群產生興趣,並為之所用:已經涉入生態心理學領域,且想要發展與精煉想法的人;開始有所覺察,想要了解更多現況及該從何處加入的人;關心人類與其所屬生態系統的關係、想尋找能夠探索這些關係的方法,及是什麼使這段關係產生問題的任何人。
我們將本書分為六部,一如往常,這種分類總是有些武斷,因為許多章節可以被合理地分類到不只一部之中,且許多章節的材料包含了不只一部的主題。特別是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每一章都談及在當前的嚴重情況下可以做些什麼。不過,感覺上有分類的幫助更大,以下是我們所選擇的分類。
第一部〈脈絡〉包含了四章,聚焦於為我們所處的現況提供各種觀點,即生態危機及其心理影響和肇因。在開場的第一章,薇奧拉‧山普森(Viola Sampson)為氣候變遷帶來了具體的而非智性上的探索,試圖將理性的回應深植於情感的土壤之中,在大環境中找到地區性的地位,並且使物質世界與愛連結,因為這是唯一有效的行動基礎。蘇姍‧巴德納爾(Susan Bodnar)為我們的各種理論提供了不同的紮根方式,利用一份可被稱為精神分析式之微觀人類學(psychoanalytical micro-anthropology)的研究中,詳細記載某些紐約居民對於氣候變遷的反應。彼得‧查特洛斯(Peter Chatalos)在本文集中最早問世的文章裡,以愛滋病來比喻地球對我們的「文化自閉症」(cultural autism)所產生的全球免疫反應。保羅‧馬特尼以非常有效的方式,跨越多數早期文獻的紋理,思考人類在地球上的角色有何獨特之處,這獨特之處可以如何有創意地運用,而不是破壞。
接續薇奧拉的文章,第二部專注於〈非人類及超越人類〉,越來越多人使用這個片語來描述地球上的其他物種及現象,使它們與人類至少有平等的立足之地。瑪格麗特‧柯爾(Margaret Kerr)及大衛‧基(David Key)寫到與地方的關係,及在野外獨處如何能開啟我們的無意識及超個人經驗。凱文‧霍爾(Kevin Hall)及布萊德蕭(G. A. Bradshaw)兩人以截然不同的風格提出假設,認為人類鑲嵌於與其他物種關係中的優越感,對於我們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多麼具有破壞性,而如果這些關係能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又將帶來多少益處。在第二部最後一章,英格爾‧柏克蘭(Inger Birkeland)及亞斯翠‧阿森(Astri Aasen)精采地描述了挪威一群孩子,以孩子有機會時就能發揮的本能,與當地一片超越人類的小地方所建立的一段充滿想像力的關係。這四個篇章及其他書籍中要描述的強烈訊息是在這場危機中,人類必須在超越自身物種利害關係以外的地方尋找解決之道。相較之下,以〈後現代主義觀點〉為主題的第三部是以智性而非感性的方式來表達作者對生態的看法,對他們所見到的單純而浪漫的「自然」紀錄提出評論(我們這篇引言中努力避開使用「自然」一詞,但有很好的理由)。馬丁‧喬丹(Martin Jordan)及約瑟夫‧塔茲(Joseph Dodds)運用多種評論理論,主要是德勒茲(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理論,分別探索了生態心理學的可能性,嚴厲地質疑生態心理學的假設及特權概念。這個取向在風格和內容上都與我們熟悉的方法大有逕庭,但我們認為它為這個領域添加了重要的自我質疑元素。
最後三部從各種面向探索了關鍵的問題:我們能做什麼?首先是〈如何是好:可能的未來〉,其中包括了四篇文獻回顧,主題在於如何使人類文化深入到心的改變中,也就是喬安娜‧梅西所謂「大轉變」(The Great Turning)的變化版。瑪麗-珍‧羅斯特的焦點在於重新找回與非人類及超越人類領域的親密關係,及喪失這段親密關係所造成的傷痛。米克‧柯林斯(Mick Collins)及共同作者運用了史丹‧葛羅夫(Stan Grof)「靈性浮現」(spiritual emergence)的概念為中心意象,表現出以下的改變:根據葛羅夫和其他人的理念,許多個別情感危機,及傳統上被稱為「崩潰」(breakdowns)的情緒,也是一種「突破/崩越」(break-throughs),是創造轉變的機會,作者並且認為這種情況也以全球性的規模發生中。希拉蕊‧普林特斯提供的是目前英國在生態學與心理學關係上的部分歷史,並且透過英國第一個轉型城鎮托特尼斯(Transition Town Totnes)的「心與靈團體」(Heart and Soul Group),記錄了這段歷史近期的繁華發展,她也分享了她對「生態與心理」的反思。傑洛米‧伯恩斯坦(Jerome Bernstein)的文章溫暖而親和地總結了他對於邊界意識(Borderland consciouness)的概念,「為自我(ego)之外的力量所形塑,打開自己以接受所有生命系統彼此相連且互相依賴的事實」,他透過不同的文字,描寫出與柯林斯等人所描述的靈性浮現現象一致的景象。xxi
〈如何是好:影響態度〉提出四篇根據心理學的取向,如何改變與環境議題相關的人類行為。湯姆‧克朗普頓(Tom Crompton)運用他參與環境運動的廣泛經驗以及諸多研究發現,主張「個人越是認同自我內在的目標及自我超越的價值,也就越能對非人類的自然表現出正面的態度及行為」,因此若僅只倡議改變人們的作為,這種運動本身的價值就很有限。珊德拉‧懷特(Sandra White)提供了一種對於何以人們具有環境意識卻未能進一步行動的理解方式,她將焦點放在否認(denial),以及犧牲的意義上。這一部的最後兩篇文章分別探討了特定的倡議行動實務。蘿絲瑪麗‧藍黛爾(Rosemary Randall)敘述了劍橋的「碳會談」(Carbon Conversations)計畫,與小團體共同促進低消費的生活風格。大衛‧基和瑪格麗特‧柯爾於本書的第二篇文章描述了他們「自然改變計畫」(Natural Change Project)的故事,這個由世界自然基金會蘇格蘭分會(WWF Scotland)所成立的計畫,試圖在荒野地區將生態心理學運用於實務工作,參與者是由受邀的個人所組成的小團體,這些人在各種領域中有其影響力,但過去不曾主動參與環境議題。
本書大多數(而非全部)作者是心理治療師、諮商師或分析師;有趣的是,目前為止所提到的篇章中,對於治療本身的討論極少。這是本書最後一部的主題,〈如何是好;臨床實務〉。尼可‧托頓的文章探討了生態思維與情感或許真的能改變心理治療的實務,而不只是被用來當作「補強」工具。克里斯‧羅伯斯頓(Chris Roberston)以優美的文字,來回穿梭於臨床小品文和普通生態理論之間,說明兩者可以如何啟發彼此,以及個案的「病症和弱點本身」如何「成為原料,在他與超越人類的存在之間,幫忙建構連結感及隨之而來的受呵護感。」
在如此豐富和多樣的文集中,最突出的主題為何呢?基於資料來源,我們可以想像本書收集的文章,會強調在基於情況所需做出實務上的改變之前,必須先在心理上有深層的改變。如稍早提及的,情況的緊急程度與為此必須付出的情緒轉變程度之間,存在著緊繃的張力。我們希望很多事情能更早發生,但卻沒有,因此也無疑地不可能達成了。如同在科技領域,目前在心理學領域至關緊要的,也是以一種可行的速度、穩定地努力下去,而非因為恐慌而喪失了我們的精熟技能。
此外,文集中所有作者除了對情況的嚴重性意見一致,其餘幾乎完全沒有共識。最明顯的主題,其實是彼此之間的差異:每位作者都表達了與其他多數人不同的觀點,也對情勢的某些面向提出了自己的診斷及(或)補救辦法。我們甚至很難看出大家投入的是相同的任務,或屬於同一領域的一份子。讀者甚至會想問:到底一個可識別的「生態心理學」領域是否真的存在?然而,這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個健康的跡象,一個生命徵象!而不是缺陷。在心理層次及實務層次上,我們正目睹各種創造性的想法和局部的解決之道開花結果,目前為止,沒有人知道哪個或哪些作法最有效。(不過我們很肯定的是,在本書中不斷出現的主題,即化解人類與其他物種間的隔閡、個人與世界的隔閡及「內在」與「外在」的隔閡,對情勢的發展十分重要。)
如薇奧拉‧山普森在她的文章中,引用了某些常見的環境保護主題所說的,或許我們只是像在鐵達尼號上把躺椅搬來搬去一樣,在面對龐大到無法理解、遑論能對它發揮影響力的事件時,做著無謂的事情好讓我們的頭腦保持忙碌。就某種程度上,情況確實如此。然而,社會運動的基本原則,是沒有人能夠隻手改變世界;這永遠是一項過度龐大的任務,而我們只能盡量以自己的方式,做到自己能力所及的事。如我們在前面提出的理由,對我們而言,目前的任務面向之一,也是一個在許多層次上都具有價值的面向,就是去思索生態危機中的心理面向;而本書所收集的文章對這項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