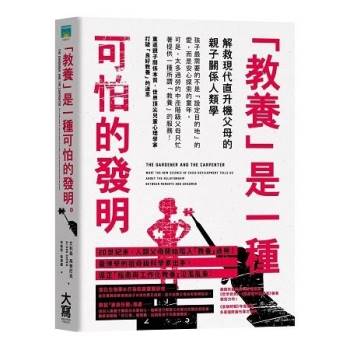6.玩耍行為
在狄更斯的《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裡,當已經瘋掉的郝薇仙(Miss Havisham)小姐坐在傾倒頹廢的宅邸裡,命令貧苦孤兒英雄皮普(Pip)去玩耍,這場景既滑稽、又令人不寒而慄。
「我煩悶極了。」郝薇仙小姐說道,「要消遣解悶。我已經和男男女女們玩夠了,所以想找個孩子來玩。玩吧。」
我想,哪怕是最喜歡爭辯的讀者也會承認,她要一個可憐的孩子在如此情況下玩耍,恐怕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困難的事了。
「得了,得了。」她用右手手指做了個不耐煩的動作,「現在玩吧,玩吧,玩吧。」
郝薇仙小姐可能是個極端例子,但狄更斯這令人不寒而慄的喜劇反映了某些關於玩耍的深度奧秘。
孩童愛玩耍,孩童和玩耍一向搭配在一起。大多數的父母親和老師對於這想法僅有模糊的概念:玩耍是件好事。甚至我們可能認為鼓勵玩耍是項好的教養技術。
但是你仔細想想,把玩耍當作教養的目標有些矛盾。畢竟,玩耍的定義就是當你沒打算做任何事的時候而做的事。這個活動的目標就是不要有目標。如果依大人所想的來決定玩耍的形式,那麼玩耍還算是玩耍嗎?即使你不是郝薇仙小姐,你能叫孩童去玩耍嗎?
科學也指出玩耍矛盾的部分。玩耍對於學習有益,這概念有著近乎直覺的吸引力。但是如果玩耍真能讓你變更聰明、更加專注,或是更能理解他人,為什麼不直接進行變更聰明、變得更專注,或是更直接進行強調的動作呢?為什麼要經由複雜的玩耍繞路而行?
直到現在,這樣的矛盾也在實際科學證據上有同樣的回應。直到最近,非常意外的是,很少有研究證明我們的直覺想法:玩耍能幫助孩童學習。
有部分的問題來自於玩耍和學習實在有太多不同的方式。我們談的是探索遊戲?還是打鬧遊戲?假裝遊戲或是電玩遊戲?我們談的學習是語言學習、發展運動技巧、理解其他人的想法、促進執行功能,或是改善日常生活的理論?每種玩耍可能和某種不同的學習相關,因此沒理由相信所有種類的玩耍都和所有的學習相關。
我將在這個章節裡概述某些不同種類的玩耍,以及我們所知道的這些玩耍,如何幫助孩童學習。首先,我們必須思考一個演化問題:動物為什麼要玩耍?
年幼的人類會玩耍,幼狼、海豚、老鼠和烏鴉也會玩耍。連章魚看起來也會玩弄塑膠瓶。幼狼玩打獵遊戲、小烏鴉玩棍子、幼鼠和兄弟們玩耍打鬧、小貓玩線球。
玩耍普遍見於有較長幼年時期、大量親代投資( p a r e n t a l investment)和腦容量較大的社會動物身上—像我們人類的動物。幾乎任何擁有較長幼年時期的動物,大部分的幼年時光都花在玩耍上。
然而,我們指的玩耍到底是什麼?玩演戲、玩打架、玩曲棍球和玩扮家家酒等遊戲,有什麼共同處?老鼠和牠的兄弟、烏鴉和牠的挖掘棍子,以及貓咪和牠的線球,三者之間有什麼底層連結?
試圖定義玩耍的生物學家指出,所有的玩耍都有五項特徵。首先,玩耍不是工作。玩耍可能看起來像在打架、打獵、挖洞或掃地,但實際上卻沒有達成任何目的。小貓沒有真的將線球吃下去,小烏鴉並沒有真的把昆蟲挖出來,打鬥的幼鼠並沒有真的傷害牠的兄弟,而玩扮家家酒並沒有將真的食物放進冰箱,房間也沒有變的比較乾淨些—實則相反。
玩耍並不只是沒有成效的行為,而它的特點讓你能將它和真實工作做區別。當老鼠玩打架遊戲時,彼此只是輕觸對方的脖子;真的打架時,牠們會痛咬對方腹部側邊。當孩童假裝倒茶時,誇張的大動作通常會使茶水濺出杯外,而非真的有利於倒茶動作。非常年幼的動物假裝打獵或假裝性交,並不會真的將戰利品帶回家或生出幼獸。
玩耍很好玩。你跟9個月大的幼兒玩躲貓貓遊戲,他們會開心地發出咯咯笑聲。動物世界裡,玩耍也帶來歡樂、開心,以及同等量的微笑和笑聲。舉例來說,老鼠打鬧時,牠們會發出超聲頻的吱喳笑聲,因為笑聲音頻太高的關係,人類無法聽到。
蒙郝薇仙小姐的恩准,但玩耍是自願性的動作。這是動物為了自己的緣故而進行,不是因為收到命令或是為了獎賞而去玩耍。事實上,幼鼠會為了能夠玩耍而先工作—牠們學會按下柵欄,因為柵欄打開,牠們就能玩耍。如果剝奪幼鼠玩耍的時間,想玩耍的渴望像慾望一樣逐漸累積,一旦有機會玩耍,牠們會立刻玩起來。孩童也是—想一想學校孩童終於等到下課休息時,開心、歡樂的叫聲。然而,玩耍跟其他基本的慾望,像是對於食物、水和保溫的需求,並不相同。當其他的基本需求都滿足的前提之下,動物才會進行玩耍。當動物面臨飢餓或壓力時,玩耍的頻率則會下降。跟一般童年時期一樣,玩耍需要的是安全感。
跳舞機器人
打鬧遊戲似乎幫助動物和孩童與其他動物和人互動。探索遊戲幫助動物和孩童學習事物運作的方式。而假想遊戲幫助孩童思考可能性,以及理解其他人的心智。
可是我們仍然得找出問題的答案:玩耍為什麼能夠提供幫助?然而,工程學可能為此提供一個答案,而非心理學。如同狂熱者創造新物種,大自然也可能有時候也使用同樣的技術。
假設你現在要製造一個機器人,你也許不想要那種只會一再重複同樣動作的工業機器人,你想要的機器人是能夠適應千變萬化世界的,就跟人和動物一樣。那你應該做什麼?
設計只會做一件事情的機器人相對簡單,而要設計一台機器人,能夠處理不斷改變的情況,就困難的多。你能設計一台可以走路的機器人,但當你把它側翻,或是它自己撞到牆,或是膝蓋扭到,或是甚至失去一隻手或腳,會發生什麼事?生物能很快地適應這類的改變。請想一下一名受傷的士兵能大幅調整普通走路的步伐,並學會用義肢走路,甚至是跑步。然而,就另一方面來說,機器人面對改變時,通常是無能為力的。
電腦科學家哈得.立普森(Hod Lipson)已發現一個策略,就是讓機器人去發展機器身體運作方式的內部圖像。然後,當機器內部改變或是外在世界改變,機器人就能預測會發生什麼事情。這與下列狀況十分雷同:貝葉斯孩童努力找出如果積木是Zando會發生什麼事。達成以上目標最好的方式結果,是給機器人有機會玩耍—隨機測試不同的動作與得到結果。
立普森的機器人一開始用很蠢又隨機的方式到處舞動—就像在婚禮上喝醉酒的表現—在它試圖做出任何有用的動作之前。但之後,當遇到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時,它就能運用玩耍跳舞階段收集到的資料,來決定如何行動。當工程師把其中的一個機器肢體拿掉,機器人仍舊能行走。一開始看起來無用的跳舞,之後卻能讓機器人更強壯。
機器人的例子也許能給我們線索,關於玩耍對於孩童的益處。玩耍讓孩童有機會能隨意改變、嘗試各種不同的動作和想法,然後得到結果。就像是立普森的機器人測試機器身體的各個動作,幼鼠嘗試不同的攻擊和防衛模式,而年幼烏鴉則是試著將棍子顛倒放,然後將其右端向上,或是像孩童擺弄著平衡木。或是在假想遊戲裡,實驗可能較具內在性。孩童或成人小說讀者正思考著,如果世界變得不同,會發生什麼事,然後得到結果。如果是猴子的生日會怎樣?或是娜塔莎的第一球會是怎樣?或是皮耶的第一次戰鬥會怎樣?
玩耍的愚蠢和其隨機的異常性,都是使玩耍變得如此有效的原因。立普森本來能嘗試預測設計的機器人後代在每種狀況下應該做的事,就像我們試圖在孩子身上做的。但那僅能夠提供給他們,發生預料之中的事情時所需的資訊。然而,玩耍帶來的禮物是,它教導我們在預料之外的事情發生時,該如何處理。
這也解釋了另一個關於玩耍令人費解的事實。為什麼玩耍很有趣?為什麼我們特別喜愛有趣動作?目標導向的行動值得做,這是很容易理解的──畢竟,我們達到目標,然後得到獎勵。但是,你怎能夠確定動物或孩童,能處理演化也未預期到的情況?我們永遠在面對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不論是粉碎的膝蓋,新的摔跤(或是調情)動作,或是任何人類同伴施加於我們的心理學驚喜。工程成果建議的解決方法:讓機器人、動物或是孩童有機會玩耍──有機會能廣泛地探索、隨意地行動、做蠢事和不為任何理由而做事。
然而,要那樣做你必須使探索過程本身是有樂趣的,不受任何特定結果的支配。這跟性交一樣。從內部的觀點看來,我們追求性是為了尋求歡愉,而嬰兒只是副產品。但從演化的觀點來看剛好相反—生育是最終的目的,而我們在性交中得到的歡愉只是用來激勵我們進行該活動。
因此, 我們玩耍不是因為它最終帶來給我們強大的認知功能—雖然那可能是進行玩耍的演化動機。我們玩耍是因為它非常有趣。
超越郝薇仙小姐
雖然還需要進行很多實驗,但是玩耍和學習相輔相成,這對於老鼠和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的讀者來說都是同樣重要的。讓孩童玩耍顯然是重要的。對於照顧者的角色,還有要再多加敘述的嗎?是否父母親能夠幫助孩童玩得更好呢?
一項令人沮喪近似郝薇仙小姐風格的發現指出,成人實際上會妨礙孩童玩耍。伊莉莎白.波納維茲(Elizabeth Bonawitz)和同事運用學校教育裡的直接指導在串珠實驗裡,用以對比有趣、探索式的學習方式。他們給學齡前孩童有著許多塑膠管的玩具,每根塑膠管能啟動不同的作用。如果你按其中一根管子,裝置會發出嗶嗶聲;按另一根管子,則會出現一面原本藏起來的鏡子;再按另一根管子,則燈會亮起來,還有按了會播放音樂的管子。
接受實驗的孩童裡,有一半的孩童見到實驗者帶來玩具並說:「哦,請看這個好玩玩具!哎喲!」然後她「意外地」撞到其中一根管子,然後裝置響起嗶嗶聲。而另一半的孩童則見到像是學校老師的實驗人員。她說:「哦,請看我帶來的好玩玩具!讓我展示給你看它是如何運作。」她故意按會讓裝置發出嗶嗶聲的管子,然後就將玩具單獨留給這兩組孩童玩耍。
兩組孩童都立刻讓裝置發出嗶嗶聲—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如何讓裝置發出嗶嗶聲。問題在於他們是否也能得知其他的功能。當實驗者意外啟動玩具之後,孩童對它非常感興趣,然後自己也試著玩。他們隨意嘗試不同的動作,結果他們發掘玩具所有的功能。然而,當實驗者扮演像老師一樣的角色,該組的孩童會按管子讓裝置嗶嗶叫,然後一再按管子,讓玩具喋喋不休地發出嗶嗶聲,而不會嘗試新的功能。
實驗者意外讓裝置發出嗶嗶聲,而不是試圖刻意教導孩童玩具的操作方式,該組孩童比起另外一組孩童,玩玩具的時間比較長,也會嘗試更多不同的動作,然後發掘更多「隱藏」的功能。
因此教導是把雙面刃。孩童對於被教導一事非常敏感,如同我們在前幾章節內容裡提到的。但是,教導似乎阻止孩童更進一步發掘所有玩具能提供的可能性。孩童變得更積極於模仿老師的動作,而不是自己發掘事物。(跟我一樣的大學教師能辨認出這樣的症狀到成年時期依舊持續存在。)
記得前面我提到模仿章節裡三個動作實驗嗎?在該項實驗裡,4歲的孩童看見一名成人對著玩具進行一連串複雜的動作,像是左右搖晃玩具、按壓它,然後拉起玩具上的圓環,或是輕敲它、按按鈕,然後翻轉它。有時候,這玩具撥放音樂,有時候沒反應。事件的模式指出可能有更簡單的方式能讓機器啟動。例如,你需要做的只是拉起玩具的圓環。
當成人說她一點都不知道玩具的運作方式,孩童就能發掘更聰明的策略。但是當成人的舉動像老師,並說她正展示的玩具的運作方式,孩童則只會模仿老師的動作。
老師和大人總是搞砸事情嗎?其實不盡然。自發玩耍的天性是未受指導的、多變的。但當你像在學校一樣,想要教導孩童某件特定的事情時,該怎麼辦?
實驗人員在一項研究裡,試著教導學齡前孩童一項深具挑戰性的幾何學的形狀概念。學齡前孩童並不知道幾何學上重要的形狀基本原則。他們一開始也不知道三角形有三個邊,不論邊長是多少,內角是銳角或是鈍角。
研究人員給4歲孩童一套有著不同種形狀圖案的卡片──有典型的形狀,像是等邊三角形和正方形,也有較不常見的形狀,像平行四邊形。
其中一組孩童只能玩形狀卡。對於第二組孩童,實驗人員也參與遊戲。他們穿戴偵探帽,並解釋他們將發掘形狀的秘密。然後,他們點出一組幾何學定義上的三角形和五角形,再請孩童找出其中共同的祕密。當孩童們回應時,成人將孩童的回答詳加說明,然後再問他們問題,以上都是遊戲的一部分。我也將奧古斯都的老虎和精靈用同樣的方式加以詳細描述—他自己可能不會想出蒂妲妮亞和艾莉兒這樣的名字。
對於第三組孩童,實驗人員則扮演老師的角色。他們說的話和實驗人員對第二組孩童說的話一模一樣。但是,跟第二組相反的是,他們不鼓勵孩童自己找出秘密,而是由實驗人員直接告訴他們各種形狀和定義。
一週之後,研究人員要求孩童將一組新的形狀卡片分成「真實」形狀(符合幾何學規則的形狀),和「假」形狀(不符合幾何學規則的形狀)。第二組「引導遊戲」裡的孩童,表現比其他兩組都要來得好。他們對於形狀的特性學習地比較深刻,也更全面性地瞭解形狀的原則。
這類的引導遊戲能夠提供給老師和教育家當作範本。科學家使用「支架」(scaffolding)這個詞彙,形容這類的互動。成人並沒有替孩童建構知識,相反地,成人建構支架,而支架幫助孩童自己建構知識。引導遊戲的方法與早先我提過關於孩童的學習和聆聽方法相近。
照顧者其實有許多方法能夠促成玩耍,而不用告知孩童進行玩耍或是試圖控制玩耍的方式。首先,我們從動物研究裡得到一項重要經驗。玩耍是人類童年時期裡的基礎部分,即使在很糟的情況下,玩耍仍會出現。恐怖的納粹集中營裡的孩童也會玩耍,但是在穩定、安全的環境裡,玩耍活動明顯蓬勃發展。與其他人相比,照顧者在尋找資源,創造適合玩耍的環境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這顯然不是件簡單或是特別有趣的事,而且沒有人能做得完美,但是讓孩子玩耍是件極為容易的事。
第二種方法,照顧者能促進孩童世界的豐富性。不同文化的孩童裡玩耍的方式都不同,因為圍繞孩童身旁,用來玩耍的東西都不同,從棍子、石頭和玉米穗軸,到蘋果平板電腦,而成人能夠提供這些玩具。成人提供給孩童掌握自身文化裡特定工具的機會,就像讓幼鳥玩棍子和葉子的成年烏鴉。
《WIRED》雜誌曾經舉辦評比,將棍子列為歷史上最好玩的玩具。除了棍子之外,還有罐子、平底鍋、灑水壺、金魚和毛毛蟲,甚至是蘋果手機和平板電腦都是好玩的玩具。
成人有時候也可以一起玩耍。當孩童探索他人的心智時,最佳玩具當然是實際真人的心智。「引導遊戲」就是個好例子。成人讓孩童主導遊戲方向,但他們也在身旁建議或詳加說明(或是戴著很蠢的偵探帽)。
跟孩子一起玩還有個更重要的理由。玩耍對大人來說也是很有樂趣的。以收集足夠資源給孩子玩而言,並不是很有趣的工作,但玩耍可以是一種補償。我跟奧古斯都一樣喜愛花園裡的精靈,但坦白說,如果不是奧古斯都的關係,我應該不會參與如此裝模作樣的遊戲,我也不會在地毯上玩著玩具車閃電麥坤的競速遊戲,也不會將罐子裝滿積木,假裝它是碗湯,或是跟那些惡名昭彰,總是惹上麻煩的小猴子一樣,在床上跳來跳去。和喬吉安娜(Georgiana)妹妹玩躲貓貓和小蜘蛛時也很有趣,特別加上她具感染力的咯咯聲。
諷刺的是,當代來自中產階級的父母親可能會允許自己玩耍,但前提是他們相信這是養育工作的一部分。美國有著相當著名的清教徒特點,就是我們擅於將別國視為是簡單愉悅的事情,從食物、散步到性愛,變成耗費心力的工作案子。我們遵守地中海式飲食,卻不吃義大利麵和番茄,我們做有氧健行,卻不在飯後散步走走,我們奉行《性愛的愉悅》的內容,而不是性愛本身的愉悅。以上的種種原因都讓我們認為讓孩童自己自發地、任意地玩耍有助於學習,但演化故事的另一部分則告訴我們,玩耍本身就是令人感到滿足的好事──是愉悅、歡笑、父母親與孩童樂趣的來源。即使沒有其他原因,光是玩耍帶來的歡樂就足夠是正當理由。
在狄更斯的《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裡,當已經瘋掉的郝薇仙(Miss Havisham)小姐坐在傾倒頹廢的宅邸裡,命令貧苦孤兒英雄皮普(Pip)去玩耍,這場景既滑稽、又令人不寒而慄。
「我煩悶極了。」郝薇仙小姐說道,「要消遣解悶。我已經和男男女女們玩夠了,所以想找個孩子來玩。玩吧。」
我想,哪怕是最喜歡爭辯的讀者也會承認,她要一個可憐的孩子在如此情況下玩耍,恐怕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困難的事了。
「得了,得了。」她用右手手指做了個不耐煩的動作,「現在玩吧,玩吧,玩吧。」
郝薇仙小姐可能是個極端例子,但狄更斯這令人不寒而慄的喜劇反映了某些關於玩耍的深度奧秘。
孩童愛玩耍,孩童和玩耍一向搭配在一起。大多數的父母親和老師對於這想法僅有模糊的概念:玩耍是件好事。甚至我們可能認為鼓勵玩耍是項好的教養技術。
但是你仔細想想,把玩耍當作教養的目標有些矛盾。畢竟,玩耍的定義就是當你沒打算做任何事的時候而做的事。這個活動的目標就是不要有目標。如果依大人所想的來決定玩耍的形式,那麼玩耍還算是玩耍嗎?即使你不是郝薇仙小姐,你能叫孩童去玩耍嗎?
科學也指出玩耍矛盾的部分。玩耍對於學習有益,這概念有著近乎直覺的吸引力。但是如果玩耍真能讓你變更聰明、更加專注,或是更能理解他人,為什麼不直接進行變更聰明、變得更專注,或是更直接進行強調的動作呢?為什麼要經由複雜的玩耍繞路而行?
直到現在,這樣的矛盾也在實際科學證據上有同樣的回應。直到最近,非常意外的是,很少有研究證明我們的直覺想法:玩耍能幫助孩童學習。
有部分的問題來自於玩耍和學習實在有太多不同的方式。我們談的是探索遊戲?還是打鬧遊戲?假裝遊戲或是電玩遊戲?我們談的學習是語言學習、發展運動技巧、理解其他人的想法、促進執行功能,或是改善日常生活的理論?每種玩耍可能和某種不同的學習相關,因此沒理由相信所有種類的玩耍都和所有的學習相關。
我將在這個章節裡概述某些不同種類的玩耍,以及我們所知道的這些玩耍,如何幫助孩童學習。首先,我們必須思考一個演化問題:動物為什麼要玩耍?
年幼的人類會玩耍,幼狼、海豚、老鼠和烏鴉也會玩耍。連章魚看起來也會玩弄塑膠瓶。幼狼玩打獵遊戲、小烏鴉玩棍子、幼鼠和兄弟們玩耍打鬧、小貓玩線球。
玩耍普遍見於有較長幼年時期、大量親代投資( p a r e n t a l investment)和腦容量較大的社會動物身上—像我們人類的動物。幾乎任何擁有較長幼年時期的動物,大部分的幼年時光都花在玩耍上。
然而,我們指的玩耍到底是什麼?玩演戲、玩打架、玩曲棍球和玩扮家家酒等遊戲,有什麼共同處?老鼠和牠的兄弟、烏鴉和牠的挖掘棍子,以及貓咪和牠的線球,三者之間有什麼底層連結?
試圖定義玩耍的生物學家指出,所有的玩耍都有五項特徵。首先,玩耍不是工作。玩耍可能看起來像在打架、打獵、挖洞或掃地,但實際上卻沒有達成任何目的。小貓沒有真的將線球吃下去,小烏鴉並沒有真的把昆蟲挖出來,打鬥的幼鼠並沒有真的傷害牠的兄弟,而玩扮家家酒並沒有將真的食物放進冰箱,房間也沒有變的比較乾淨些—實則相反。
玩耍並不只是沒有成效的行為,而它的特點讓你能將它和真實工作做區別。當老鼠玩打架遊戲時,彼此只是輕觸對方的脖子;真的打架時,牠們會痛咬對方腹部側邊。當孩童假裝倒茶時,誇張的大動作通常會使茶水濺出杯外,而非真的有利於倒茶動作。非常年幼的動物假裝打獵或假裝性交,並不會真的將戰利品帶回家或生出幼獸。
玩耍很好玩。你跟9個月大的幼兒玩躲貓貓遊戲,他們會開心地發出咯咯笑聲。動物世界裡,玩耍也帶來歡樂、開心,以及同等量的微笑和笑聲。舉例來說,老鼠打鬧時,牠們會發出超聲頻的吱喳笑聲,因為笑聲音頻太高的關係,人類無法聽到。
蒙郝薇仙小姐的恩准,但玩耍是自願性的動作。這是動物為了自己的緣故而進行,不是因為收到命令或是為了獎賞而去玩耍。事實上,幼鼠會為了能夠玩耍而先工作—牠們學會按下柵欄,因為柵欄打開,牠們就能玩耍。如果剝奪幼鼠玩耍的時間,想玩耍的渴望像慾望一樣逐漸累積,一旦有機會玩耍,牠們會立刻玩起來。孩童也是—想一想學校孩童終於等到下課休息時,開心、歡樂的叫聲。然而,玩耍跟其他基本的慾望,像是對於食物、水和保溫的需求,並不相同。當其他的基本需求都滿足的前提之下,動物才會進行玩耍。當動物面臨飢餓或壓力時,玩耍的頻率則會下降。跟一般童年時期一樣,玩耍需要的是安全感。
跳舞機器人
打鬧遊戲似乎幫助動物和孩童與其他動物和人互動。探索遊戲幫助動物和孩童學習事物運作的方式。而假想遊戲幫助孩童思考可能性,以及理解其他人的心智。
可是我們仍然得找出問題的答案:玩耍為什麼能夠提供幫助?然而,工程學可能為此提供一個答案,而非心理學。如同狂熱者創造新物種,大自然也可能有時候也使用同樣的技術。
假設你現在要製造一個機器人,你也許不想要那種只會一再重複同樣動作的工業機器人,你想要的機器人是能夠適應千變萬化世界的,就跟人和動物一樣。那你應該做什麼?
設計只會做一件事情的機器人相對簡單,而要設計一台機器人,能夠處理不斷改變的情況,就困難的多。你能設計一台可以走路的機器人,但當你把它側翻,或是它自己撞到牆,或是膝蓋扭到,或是甚至失去一隻手或腳,會發生什麼事?生物能很快地適應這類的改變。請想一下一名受傷的士兵能大幅調整普通走路的步伐,並學會用義肢走路,甚至是跑步。然而,就另一方面來說,機器人面對改變時,通常是無能為力的。
電腦科學家哈得.立普森(Hod Lipson)已發現一個策略,就是讓機器人去發展機器身體運作方式的內部圖像。然後,當機器內部改變或是外在世界改變,機器人就能預測會發生什麼事情。這與下列狀況十分雷同:貝葉斯孩童努力找出如果積木是Zando會發生什麼事。達成以上目標最好的方式結果,是給機器人有機會玩耍—隨機測試不同的動作與得到結果。
立普森的機器人一開始用很蠢又隨機的方式到處舞動—就像在婚禮上喝醉酒的表現—在它試圖做出任何有用的動作之前。但之後,當遇到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時,它就能運用玩耍跳舞階段收集到的資料,來決定如何行動。當工程師把其中的一個機器肢體拿掉,機器人仍舊能行走。一開始看起來無用的跳舞,之後卻能讓機器人更強壯。
機器人的例子也許能給我們線索,關於玩耍對於孩童的益處。玩耍讓孩童有機會能隨意改變、嘗試各種不同的動作和想法,然後得到結果。就像是立普森的機器人測試機器身體的各個動作,幼鼠嘗試不同的攻擊和防衛模式,而年幼烏鴉則是試著將棍子顛倒放,然後將其右端向上,或是像孩童擺弄著平衡木。或是在假想遊戲裡,實驗可能較具內在性。孩童或成人小說讀者正思考著,如果世界變得不同,會發生什麼事,然後得到結果。如果是猴子的生日會怎樣?或是娜塔莎的第一球會是怎樣?或是皮耶的第一次戰鬥會怎樣?
玩耍的愚蠢和其隨機的異常性,都是使玩耍變得如此有效的原因。立普森本來能嘗試預測設計的機器人後代在每種狀況下應該做的事,就像我們試圖在孩子身上做的。但那僅能夠提供給他們,發生預料之中的事情時所需的資訊。然而,玩耍帶來的禮物是,它教導我們在預料之外的事情發生時,該如何處理。
這也解釋了另一個關於玩耍令人費解的事實。為什麼玩耍很有趣?為什麼我們特別喜愛有趣動作?目標導向的行動值得做,這是很容易理解的──畢竟,我們達到目標,然後得到獎勵。但是,你怎能夠確定動物或孩童,能處理演化也未預期到的情況?我們永遠在面對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不論是粉碎的膝蓋,新的摔跤(或是調情)動作,或是任何人類同伴施加於我們的心理學驚喜。工程成果建議的解決方法:讓機器人、動物或是孩童有機會玩耍──有機會能廣泛地探索、隨意地行動、做蠢事和不為任何理由而做事。
然而,要那樣做你必須使探索過程本身是有樂趣的,不受任何特定結果的支配。這跟性交一樣。從內部的觀點看來,我們追求性是為了尋求歡愉,而嬰兒只是副產品。但從演化的觀點來看剛好相反—生育是最終的目的,而我們在性交中得到的歡愉只是用來激勵我們進行該活動。
因此, 我們玩耍不是因為它最終帶來給我們強大的認知功能—雖然那可能是進行玩耍的演化動機。我們玩耍是因為它非常有趣。
超越郝薇仙小姐
雖然還需要進行很多實驗,但是玩耍和學習相輔相成,這對於老鼠和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的讀者來說都是同樣重要的。讓孩童玩耍顯然是重要的。對於照顧者的角色,還有要再多加敘述的嗎?是否父母親能夠幫助孩童玩得更好呢?
一項令人沮喪近似郝薇仙小姐風格的發現指出,成人實際上會妨礙孩童玩耍。伊莉莎白.波納維茲(Elizabeth Bonawitz)和同事運用學校教育裡的直接指導在串珠實驗裡,用以對比有趣、探索式的學習方式。他們給學齡前孩童有著許多塑膠管的玩具,每根塑膠管能啟動不同的作用。如果你按其中一根管子,裝置會發出嗶嗶聲;按另一根管子,則會出現一面原本藏起來的鏡子;再按另一根管子,則燈會亮起來,還有按了會播放音樂的管子。
接受實驗的孩童裡,有一半的孩童見到實驗者帶來玩具並說:「哦,請看這個好玩玩具!哎喲!」然後她「意外地」撞到其中一根管子,然後裝置響起嗶嗶聲。而另一半的孩童則見到像是學校老師的實驗人員。她說:「哦,請看我帶來的好玩玩具!讓我展示給你看它是如何運作。」她故意按會讓裝置發出嗶嗶聲的管子,然後就將玩具單獨留給這兩組孩童玩耍。
兩組孩童都立刻讓裝置發出嗶嗶聲—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如何讓裝置發出嗶嗶聲。問題在於他們是否也能得知其他的功能。當實驗者意外啟動玩具之後,孩童對它非常感興趣,然後自己也試著玩。他們隨意嘗試不同的動作,結果他們發掘玩具所有的功能。然而,當實驗者扮演像老師一樣的角色,該組的孩童會按管子讓裝置嗶嗶叫,然後一再按管子,讓玩具喋喋不休地發出嗶嗶聲,而不會嘗試新的功能。
實驗者意外讓裝置發出嗶嗶聲,而不是試圖刻意教導孩童玩具的操作方式,該組孩童比起另外一組孩童,玩玩具的時間比較長,也會嘗試更多不同的動作,然後發掘更多「隱藏」的功能。
因此教導是把雙面刃。孩童對於被教導一事非常敏感,如同我們在前幾章節內容裡提到的。但是,教導似乎阻止孩童更進一步發掘所有玩具能提供的可能性。孩童變得更積極於模仿老師的動作,而不是自己發掘事物。(跟我一樣的大學教師能辨認出這樣的症狀到成年時期依舊持續存在。)
記得前面我提到模仿章節裡三個動作實驗嗎?在該項實驗裡,4歲的孩童看見一名成人對著玩具進行一連串複雜的動作,像是左右搖晃玩具、按壓它,然後拉起玩具上的圓環,或是輕敲它、按按鈕,然後翻轉它。有時候,這玩具撥放音樂,有時候沒反應。事件的模式指出可能有更簡單的方式能讓機器啟動。例如,你需要做的只是拉起玩具的圓環。
當成人說她一點都不知道玩具的運作方式,孩童就能發掘更聰明的策略。但是當成人的舉動像老師,並說她正展示的玩具的運作方式,孩童則只會模仿老師的動作。
老師和大人總是搞砸事情嗎?其實不盡然。自發玩耍的天性是未受指導的、多變的。但當你像在學校一樣,想要教導孩童某件特定的事情時,該怎麼辦?
實驗人員在一項研究裡,試著教導學齡前孩童一項深具挑戰性的幾何學的形狀概念。學齡前孩童並不知道幾何學上重要的形狀基本原則。他們一開始也不知道三角形有三個邊,不論邊長是多少,內角是銳角或是鈍角。
研究人員給4歲孩童一套有著不同種形狀圖案的卡片──有典型的形狀,像是等邊三角形和正方形,也有較不常見的形狀,像平行四邊形。
其中一組孩童只能玩形狀卡。對於第二組孩童,實驗人員也參與遊戲。他們穿戴偵探帽,並解釋他們將發掘形狀的秘密。然後,他們點出一組幾何學定義上的三角形和五角形,再請孩童找出其中共同的祕密。當孩童們回應時,成人將孩童的回答詳加說明,然後再問他們問題,以上都是遊戲的一部分。我也將奧古斯都的老虎和精靈用同樣的方式加以詳細描述—他自己可能不會想出蒂妲妮亞和艾莉兒這樣的名字。
對於第三組孩童,實驗人員則扮演老師的角色。他們說的話和實驗人員對第二組孩童說的話一模一樣。但是,跟第二組相反的是,他們不鼓勵孩童自己找出秘密,而是由實驗人員直接告訴他們各種形狀和定義。
一週之後,研究人員要求孩童將一組新的形狀卡片分成「真實」形狀(符合幾何學規則的形狀),和「假」形狀(不符合幾何學規則的形狀)。第二組「引導遊戲」裡的孩童,表現比其他兩組都要來得好。他們對於形狀的特性學習地比較深刻,也更全面性地瞭解形狀的原則。
這類的引導遊戲能夠提供給老師和教育家當作範本。科學家使用「支架」(scaffolding)這個詞彙,形容這類的互動。成人並沒有替孩童建構知識,相反地,成人建構支架,而支架幫助孩童自己建構知識。引導遊戲的方法與早先我提過關於孩童的學習和聆聽方法相近。
照顧者其實有許多方法能夠促成玩耍,而不用告知孩童進行玩耍或是試圖控制玩耍的方式。首先,我們從動物研究裡得到一項重要經驗。玩耍是人類童年時期裡的基礎部分,即使在很糟的情況下,玩耍仍會出現。恐怖的納粹集中營裡的孩童也會玩耍,但是在穩定、安全的環境裡,玩耍活動明顯蓬勃發展。與其他人相比,照顧者在尋找資源,創造適合玩耍的環境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這顯然不是件簡單或是特別有趣的事,而且沒有人能做得完美,但是讓孩子玩耍是件極為容易的事。
第二種方法,照顧者能促進孩童世界的豐富性。不同文化的孩童裡玩耍的方式都不同,因為圍繞孩童身旁,用來玩耍的東西都不同,從棍子、石頭和玉米穗軸,到蘋果平板電腦,而成人能夠提供這些玩具。成人提供給孩童掌握自身文化裡特定工具的機會,就像讓幼鳥玩棍子和葉子的成年烏鴉。
《WIRED》雜誌曾經舉辦評比,將棍子列為歷史上最好玩的玩具。除了棍子之外,還有罐子、平底鍋、灑水壺、金魚和毛毛蟲,甚至是蘋果手機和平板電腦都是好玩的玩具。
成人有時候也可以一起玩耍。當孩童探索他人的心智時,最佳玩具當然是實際真人的心智。「引導遊戲」就是個好例子。成人讓孩童主導遊戲方向,但他們也在身旁建議或詳加說明(或是戴著很蠢的偵探帽)。
跟孩子一起玩還有個更重要的理由。玩耍對大人來說也是很有樂趣的。以收集足夠資源給孩子玩而言,並不是很有趣的工作,但玩耍可以是一種補償。我跟奧古斯都一樣喜愛花園裡的精靈,但坦白說,如果不是奧古斯都的關係,我應該不會參與如此裝模作樣的遊戲,我也不會在地毯上玩著玩具車閃電麥坤的競速遊戲,也不會將罐子裝滿積木,假裝它是碗湯,或是跟那些惡名昭彰,總是惹上麻煩的小猴子一樣,在床上跳來跳去。和喬吉安娜(Georgiana)妹妹玩躲貓貓和小蜘蛛時也很有趣,特別加上她具感染力的咯咯聲。
諷刺的是,當代來自中產階級的父母親可能會允許自己玩耍,但前提是他們相信這是養育工作的一部分。美國有著相當著名的清教徒特點,就是我們擅於將別國視為是簡單愉悅的事情,從食物、散步到性愛,變成耗費心力的工作案子。我們遵守地中海式飲食,卻不吃義大利麵和番茄,我們做有氧健行,卻不在飯後散步走走,我們奉行《性愛的愉悅》的內容,而不是性愛本身的愉悅。以上的種種原因都讓我們認為讓孩童自己自發地、任意地玩耍有助於學習,但演化故事的另一部分則告訴我們,玩耍本身就是令人感到滿足的好事──是愉悅、歡笑、父母親與孩童樂趣的來源。即使沒有其他原因,光是玩耍帶來的歡樂就足夠是正當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