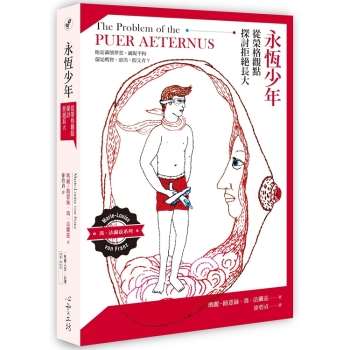1-5 被蛇吞掉的象
我們不能忘記在聖修伯里的成長過程中,當時的環境氛圍是相當具有幻滅感及憤世嫉俗的,他時常周旋的所謂重要生活無非就是與人談論橋牌及錢財之類的事物。因此,某方面來說他有充分的理由反抗這一切,並抓緊他內在藝術及整體的人生觀。同時,也對於這樣的成人生活感到厭倦、憎恨,並帶著革命使命與之作對。我們可以相當清楚的看見,他以隱微但又中肯的方式嘲笑成人的生活。
但是在此同時,他並不知道如何將自己拉出童年世界,又不至落入對成人生活唯一價值的幻滅。如果你將這一點與圖畫的象徵意義相結合,就顯得更糟糕,因為大蟒蛇顯然是吞噬性母性的意象,更深入的解讀則是無意識的吞噬面向,這讓生命有份窒息感,也抑止了人類的發展。當個體被無意識所擊敗時,將個體緊緊抓住的正是那帶有侵吞或是退行本質的無意識面向,也就是那種回頭看的傾向。你甚至可以說,大蟒蛇表現出朝向死亡的一種拉力。
被吞掉的動物是大象,因此我們需要先看一看牠的象徵意涵。直到古典時代晚期之前,歐洲國家對大象都不甚知悉,在那之前並沒有太多的神話素材是關於大象的。然而,在古典時代晚期之後,大象開始展現極大的重要性。當亞歷山大大帝前往印度時,他首次看見大象,在那之後大象被帶入歐洲。羅馬人在那之後將大象當作現代戰場上的坦克一般來使用。如果我們閱讀一些對於大象的著述,可以發現有極大量的神話幻想是繞著大象而轉。據說:「牠們是非常貞節的,一生只交配一次,同時有著非常神祕的交配方式以生產年輕一代,因此」根據中古世紀的報導顯示:「牠們帶有婚姻貞節的寓意。就如同獨角獸,大象也喜愛處子,同時也只能由處子及處女所馴服,這一點指出了基督化身的母題。」據說大象代表著不能被征服的堅忍力,同時也是基督的意象。古代認為大象極具雄心,如果牠們沒有得到應得的尊榮,會因為失望而死,因為牠們的榮譽感極高。蛇喜愛啜飲大象的冷血;牠們會偷偷鑽入大象腳底並噬飲大象的鮮血,而突然間大象就會倒地不起,這就是為什麼舉凡大象看見蛇,牠都會猛然上前一腳踩下。在中世紀時代,大象代表慷慨之人,但是也帶有不穩定及情緒化的特徵,因為據說大象是慷慨的、聰明的,因此牠是沉默寡言的,但是一旦牠落入盛怒情緒,感官娛樂沒能將之安撫下來,唯有音樂能讓牠心滿意足。
前面這段話是我從一本有趣的書中所摘錄的,書名是《象徵性的博學多聞者》(Polyhistor Symbolicus),由耶穌會的神父尼古拉斯.柯西紐斯(Nikolaus Caussinus)所作,書裡提供了關於大象的有趣故事,他一方面總結古代的俚語所言,同時還加上一些中世紀幻想。「大象時常沐浴,」他持續說到:「同時用花朵來為自己增添香氛,因此牠們代表淨化、貞潔及對上帝的虔敬崇拜。」這一點顯示歐洲人所經歷的是等同於當非洲人第一次遇見大象時的情況:他們將英雄的原型(archetype)投射在大象身上。在非洲,當人得到獅子的封號時,會被認為是極具尊榮的一件事,但是個人所能得到的最高尊榮卻是大象的封號,這被認為是遠遠超過獅子的封號,獅子所代表的是酋長類型的勇者意象,而大象則是巫師的原型,牠同樣帶有勇氣,但是除此之外還帶有智慧及祕密的知識。因此,在非洲社群的階層中,大象代表著得到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人格。
而奇特的是,歐洲人也主動在大象身上投射出相同的特質,同時將之視為神聖英雄的意象,也就是基督的意象,牠有著傑出的品德,除了情緒化及傾向於暴怒兩點之外。這是讓人感到訝異的,但是那兩點正是聖修伯里的兩項顯著特質,因此可以說完全就是他個人特質的圖像。他本身是隱微、貞潔的—某種程度上是對感覺的敏銳性——相當具有雄心壯志,同時也敏感於一切會影響到個人榮譽的事物。他持續的找尋心中所想的信仰——他並不敬拜上帝,因為他並沒有找到上帝——但是他總是在追尋中。他是慷慨、聰明以及沉默寡言的,但也是易怒的,而且有落入恐怖暴怒情緒的傾向。因此,在那張大象的圖像中,就帶有讓人感到訝異的自我描繪,而我們也可以從中看見,原型的模式透過單純個人的方式而得到說明,兩者沒有太大的差異。大象是成人英雄的典範幻想,而這個典範幻想——亦即他靈魂中自己想要變成的樣貌的意象——被吞噬母親(devouring mother)所吞回,這第一張圖顯示了整個悲劇。我們常會見到兒時的夢境預示出二十或三十年之後的內在命運。第一張圖畫顯示出聖修伯里有著英雄的面向,相當鮮活且被激發,但這個面向從來都沒有真的被經歷,卻是被無意識的退行傾向所吞回。正如同我們所知道的後續發展,他是被死亡所吞回。
吞噬母親的神話自然也應該連結上他真實的母親,但是因為她仍在人世,顯然的,我不太願意對她做太多的評論。我最近在一份報紙上看見她的照片,顯示出無論她帶有怎樣的特質,她都是個相當強而有力的角色。她是個高大壯碩的女人,報紙上的文章提到她是個精力充沛的人,對於各式活動都感興趣,親身嘗試素描、繪畫及寫作,是個生動且充滿活力的人,儘管如今年歲已大,仍然是相當強健。顯而易見的,要一個敏感的男孩從這樣的母親影響中抽身,必然是相當困難的。據說她總是預期兒子的死亡,有許多回她以為兒子已經死了,還很戲劇化的穿戴著大片的黑紗,就像是法國女人成為寡婦時會喜歡穿著的樣子,但是後來相當失望的必須再一次將黑紗脫下,因為兒子根本還沒死。因此,我們所謂的死亡母親的原型模式就在她的心靈中鮮活上演。在我們的社會層級中,死亡母親的原型並不被公開承認,但是當我遇到下述的經驗當下,我感到震驚不已。
我當時需要去某地見某人,我去拜訪的屋主有個永恆少年兒子,這兒子幾乎都被母親所吞掉了。屋主是單純的一家人,他們經營麵包店,兒子則完全都不工作,成天只是穿上騎馬裝到處閒晃,是個典型的風流公子哥唐璜一族,相當貴氣同時每四、五天就換一個新女人,不過這些都只是我從閒話八卦中聽到的。這個年輕人有次帶著女友前去蘇黎世湖玩水,經典的劇碼出現——如同歌德會用的描述方式——他邊將她抓住的同時,自己就邊沉入水中,最後倆倆都沉入水裡。女孩子最後被救起,但是當他被救出水面時早已斷氣。這是我在報紙上看到的消息,但是當我再度回到這個屋子時,正好遇到那個母親,她當時是個寡婦,我對她至上哀悼之意,對她說當我聽到這個可怕的意外時,是何等的難過。她邀請我進入屋內,並帶我到起居室內坐下,起居室裡擺放著她兒子死時的巨幅照片,四周都是花朵,擺設的就像是英雄的墳墓。對此她表示:「看看他!他死亡當時的面容是何等的俊美。」我對此表示同意,接著她微笑說:「是這樣的,我寧願像這樣擁有他,也不願意將他送給另一個女人。」
3-4 「總有一天」與無聊感
在我的第一場演講中,我談到精神官能症所帶來的暫時性人生問題,也就是人們活在有一天(尚未,但是有一天)能夠的期待中,這常被連上救世主的情結。瑞士分析師瑞尼.瑪拉末(René Malamud)曾經給我一份人本主義哲學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的論文,他在文章中詳細談到這個問題。僅擷取一小部分內容如下,他說:
如果某人相信時間,那麼此人就沒有突然改變的可能性,他會持續不斷的期待當「時候到了」一切就會沒事了。假設某人沒能解決衝突,就會期待「時候到了」衝突就會自己解決,完全不需要做出決定。你常會看見那樣的狀況,特別是從個人的自我成就這一點來相信時間。人們會自我安慰,不僅僅是因為沒有真的做些什麼,也是因為沒有為必須做的事情做準備,因為有太多的時間,因此就沒必要匆促進行。我們可以從一個非常有天賦的作家的案例中得到這個機制的說明:這個作家想要寫一本書,認為那會成為世界文學界最重要的一本書,但是他除了對於想寫的內容有些想法,以及幻想這本書會帶來的影響,和告訴朋友們自己還沒有完全完成這本書之外,就什麼也沒再多做。實際的情況是,他連一個句子都還沒有寫出,連一個字都還沒寫下;但是,據他所言,他已經在這件事上投入了七年之久。當這類的人們越是年長後,越會緊抓住有一天他們會完成的幻想。當某些人到達一定的年紀,通常是在四十歲出頭,會乍然清醒,開始使用自身的力量,或者會出現像是精神官能症的崩潰,出於「假若沒有那個讓人感到安慰的時間假象時,就無法活著」這個事實。
這段話鮮明的描寫出我試圖要表達的內容。很久以前,英國的分析心理學家貝恩斯在他關於暫時性人生的論文中就寫過這一點,正如我先前所提到的。
《小王子》書中接下來的部分,我會詳細的閱讀。
喔!小王子!我就這麼一點一滴地開始了解你那悲傷的私密小生活……長久以來,你從觀看日落的安靜愉悅中找到唯一的娛樂。
我在第四天的早晨得知這些新的細節,當時你這麼告訴我:
「我很喜歡日落。我們一起去看日落吧。」
「不過我們還要等等,」我說。
「等等?等什麼?」
「等日落。我們必須要等到時候到了。」
起初,你似乎顯得非常驚訝。而接著你自己笑了笑。你對我說:
「我總以為自己還在家!」
是的。每個人都知道在美國的中午時分,太陽就在法國落下。
如果你可以在一分鐘之內飛到法國,你就能看到日落,直接從中午時分進入日落。可惜,法國太遠了。但是,在你的小小星球上,我的小王子,你只要將椅子挪個幾步,就可以隨你喜愛的看白晝或是暮色落下……
「有一天,」你對我這麼說:「我看了四十四次的日落!」
在那之後,你又說:
「你知道的⋯⋯當一個人很悲傷很悲傷的時候,就會喜愛日落……」
「所以你當時很悲傷嗎?」我問:「在四十四次日落那天?」
但是小王子沒有回答。
馮‧法蘭茲:你會如何解讀這部分?
學員:那是否是對於他自身早年死亡的預演?
馮‧法蘭茲:是的,可以這麼說——以那象徵性的四十四天。那是對他自身死亡的預感,此外,還有什麼?那是個不時想到死亡的浪漫方式,這在早期少年階段是常見的。但是這一點會如何連上其餘的問題?
學員:欠缺實際性。事物持續向後退;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看日落。
馮‧法蘭茲:是的,那是自我中心主義(egotism)的形式,是自戀主義(narcissism)的形式,而那也是當人們的生命不再流動以及當時間不被填滿時,自然會落入的心境,因為當你投入內在或外在的冒險時,你沒有時間看日落。然而,日落可能是忙碌的一天之後,所得到的一個寧靜美好片刻。假若日落讓你感到悲傷,那是因為在日落之前並沒有足夠的冒險。同樣的,我認為那和少年悲劇是有關的。人們,特別是當他們還年輕時,相當可能會受到無聊折磨。我記得自己在十四到十八歲那幾年常常感到無聊,在那之後就從來沒有這種感覺。表面上,那是因為個體必須要在學校裡待很長的時間而不能做喜歡的事。一旦我能夠做我喜歡做的事情,無聊的感覺就消失了。但是,相較於那樣的狀況,此處的無聊感顯得更加深刻。我曾經看過那樣的狀況,那是在年輕人間常見的精神官能症,但奇怪的是,這在他們年紀增長之後就會漸漸減輕。這與他們無法去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反倒總要去做不想做的事有關。因此,他們不覺得自己是在過生活,無聊感不過就是當個體不能活在生活中的主觀感受。事實上,並沒有真的無聊感。在大學裡,我仍然需要遵循無聊的課程,但是那時的我學會苦中作樂。如果你夠有創意,知道如何將自己置於現實中,你就能避開無聊感。我們將自身的自發幻想放入現實中,那麼無聊感就永遠消失了。接下來的人生就可以是愉快的或是不愉快的,充滿刺激的或是相反的,但是絕對不會是無聊的。因此,無聊感就是生命被阻擋的症狀,是個體不知道該如何將個人的內在投入現實中。如果我們知道要如何玩耍,無聊感就消失了。但是,有些孩子及成人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同時也不知道該如何帶出內在資源。在年少期,這不會是太過負面的症狀,因為某方面而言那是此時期的一部分,因為他們仍然無法實現自我。
一般年輕人所受的苦,部分主要來自於,就內在而言,他們已經是相當具有效能及理解力的成年人,但是從外在而言,他們並沒有得到使用這些能力的機會。他們被社會所抑制,造成的結果就是感到無聊。我曾經在學校裡教書,主要對象是十四歲到十八歲之間的學生。常見的許多問題來自於其實他們不僅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斷,而且內在也是豐富而具有理解力的,但是在外在的情境中,無論是在家中或是學校,他們都被以孩童的方式對待,得不到任何的機會。自然而然的,接下來就是生命受到阻滯,造成了想要與一切作對的無聊抗拒,一種帶著壞心情的貧乏作為。一般來說,如果我們能夠給予他們更多的理解、任務以及更多的責任,讓他們成功提升到更高的層次,那麼一切就會重回正軌。他們是被人為的困在低於他們所屬的層次,以致浮現出沉悶無聊感。
因此我們說:「正因為你感到無聊,也正因為你是懶惰的,你必須做兩倍的工作,但這些都是好差事。」那會終結無聊感!我們都知道,在十六到二十歲之間,自殺是相當常見的,但是在那之後就比較少見了。那個年紀的人常會有種奇怪的憂愁傷感,他們會感覺自己像是老人一樣。他們的臉上會出現彷彿自己知悉人生的表情,同時也覺得自己非常非常老,既然如此,與他人嬉戲玩樂或與女孩、男孩的玩樂有什麼樂趣可言,他們退縮到爺爺奶奶們的人生態度。這不過只是個症狀,意謂著他們還沒找到生命泉源的線索,因此以這樣的方式載浮載沉。而在這樣的年紀,對於那些與眾不同的少年來說,要找出他們人生的可能性會是更加困難的,於是生命就受到阻滯。顯然的,書中這個悲傷且不時看日出的孩子也有著相同的處境。
我們不能忘記在聖修伯里的成長過程中,當時的環境氛圍是相當具有幻滅感及憤世嫉俗的,他時常周旋的所謂重要生活無非就是與人談論橋牌及錢財之類的事物。因此,某方面來說他有充分的理由反抗這一切,並抓緊他內在藝術及整體的人生觀。同時,也對於這樣的成人生活感到厭倦、憎恨,並帶著革命使命與之作對。我們可以相當清楚的看見,他以隱微但又中肯的方式嘲笑成人的生活。
但是在此同時,他並不知道如何將自己拉出童年世界,又不至落入對成人生活唯一價值的幻滅。如果你將這一點與圖畫的象徵意義相結合,就顯得更糟糕,因為大蟒蛇顯然是吞噬性母性的意象,更深入的解讀則是無意識的吞噬面向,這讓生命有份窒息感,也抑止了人類的發展。當個體被無意識所擊敗時,將個體緊緊抓住的正是那帶有侵吞或是退行本質的無意識面向,也就是那種回頭看的傾向。你甚至可以說,大蟒蛇表現出朝向死亡的一種拉力。
被吞掉的動物是大象,因此我們需要先看一看牠的象徵意涵。直到古典時代晚期之前,歐洲國家對大象都不甚知悉,在那之前並沒有太多的神話素材是關於大象的。然而,在古典時代晚期之後,大象開始展現極大的重要性。當亞歷山大大帝前往印度時,他首次看見大象,在那之後大象被帶入歐洲。羅馬人在那之後將大象當作現代戰場上的坦克一般來使用。如果我們閱讀一些對於大象的著述,可以發現有極大量的神話幻想是繞著大象而轉。據說:「牠們是非常貞節的,一生只交配一次,同時有著非常神祕的交配方式以生產年輕一代,因此」根據中古世紀的報導顯示:「牠們帶有婚姻貞節的寓意。就如同獨角獸,大象也喜愛處子,同時也只能由處子及處女所馴服,這一點指出了基督化身的母題。」據說大象代表著不能被征服的堅忍力,同時也是基督的意象。古代認為大象極具雄心,如果牠們沒有得到應得的尊榮,會因為失望而死,因為牠們的榮譽感極高。蛇喜愛啜飲大象的冷血;牠們會偷偷鑽入大象腳底並噬飲大象的鮮血,而突然間大象就會倒地不起,這就是為什麼舉凡大象看見蛇,牠都會猛然上前一腳踩下。在中世紀時代,大象代表慷慨之人,但是也帶有不穩定及情緒化的特徵,因為據說大象是慷慨的、聰明的,因此牠是沉默寡言的,但是一旦牠落入盛怒情緒,感官娛樂沒能將之安撫下來,唯有音樂能讓牠心滿意足。
前面這段話是我從一本有趣的書中所摘錄的,書名是《象徵性的博學多聞者》(Polyhistor Symbolicus),由耶穌會的神父尼古拉斯.柯西紐斯(Nikolaus Caussinus)所作,書裡提供了關於大象的有趣故事,他一方面總結古代的俚語所言,同時還加上一些中世紀幻想。「大象時常沐浴,」他持續說到:「同時用花朵來為自己增添香氛,因此牠們代表淨化、貞潔及對上帝的虔敬崇拜。」這一點顯示歐洲人所經歷的是等同於當非洲人第一次遇見大象時的情況:他們將英雄的原型(archetype)投射在大象身上。在非洲,當人得到獅子的封號時,會被認為是極具尊榮的一件事,但是個人所能得到的最高尊榮卻是大象的封號,這被認為是遠遠超過獅子的封號,獅子所代表的是酋長類型的勇者意象,而大象則是巫師的原型,牠同樣帶有勇氣,但是除此之外還帶有智慧及祕密的知識。因此,在非洲社群的階層中,大象代表著得到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人格。
而奇特的是,歐洲人也主動在大象身上投射出相同的特質,同時將之視為神聖英雄的意象,也就是基督的意象,牠有著傑出的品德,除了情緒化及傾向於暴怒兩點之外。這是讓人感到訝異的,但是那兩點正是聖修伯里的兩項顯著特質,因此可以說完全就是他個人特質的圖像。他本身是隱微、貞潔的—某種程度上是對感覺的敏銳性——相當具有雄心壯志,同時也敏感於一切會影響到個人榮譽的事物。他持續的找尋心中所想的信仰——他並不敬拜上帝,因為他並沒有找到上帝——但是他總是在追尋中。他是慷慨、聰明以及沉默寡言的,但也是易怒的,而且有落入恐怖暴怒情緒的傾向。因此,在那張大象的圖像中,就帶有讓人感到訝異的自我描繪,而我們也可以從中看見,原型的模式透過單純個人的方式而得到說明,兩者沒有太大的差異。大象是成人英雄的典範幻想,而這個典範幻想——亦即他靈魂中自己想要變成的樣貌的意象——被吞噬母親(devouring mother)所吞回,這第一張圖顯示了整個悲劇。我們常會見到兒時的夢境預示出二十或三十年之後的內在命運。第一張圖畫顯示出聖修伯里有著英雄的面向,相當鮮活且被激發,但這個面向從來都沒有真的被經歷,卻是被無意識的退行傾向所吞回。正如同我們所知道的後續發展,他是被死亡所吞回。
吞噬母親的神話自然也應該連結上他真實的母親,但是因為她仍在人世,顯然的,我不太願意對她做太多的評論。我最近在一份報紙上看見她的照片,顯示出無論她帶有怎樣的特質,她都是個相當強而有力的角色。她是個高大壯碩的女人,報紙上的文章提到她是個精力充沛的人,對於各式活動都感興趣,親身嘗試素描、繪畫及寫作,是個生動且充滿活力的人,儘管如今年歲已大,仍然是相當強健。顯而易見的,要一個敏感的男孩從這樣的母親影響中抽身,必然是相當困難的。據說她總是預期兒子的死亡,有許多回她以為兒子已經死了,還很戲劇化的穿戴著大片的黑紗,就像是法國女人成為寡婦時會喜歡穿著的樣子,但是後來相當失望的必須再一次將黑紗脫下,因為兒子根本還沒死。因此,我們所謂的死亡母親的原型模式就在她的心靈中鮮活上演。在我們的社會層級中,死亡母親的原型並不被公開承認,但是當我遇到下述的經驗當下,我感到震驚不已。
我當時需要去某地見某人,我去拜訪的屋主有個永恆少年兒子,這兒子幾乎都被母親所吞掉了。屋主是單純的一家人,他們經營麵包店,兒子則完全都不工作,成天只是穿上騎馬裝到處閒晃,是個典型的風流公子哥唐璜一族,相當貴氣同時每四、五天就換一個新女人,不過這些都只是我從閒話八卦中聽到的。這個年輕人有次帶著女友前去蘇黎世湖玩水,經典的劇碼出現——如同歌德會用的描述方式——他邊將她抓住的同時,自己就邊沉入水中,最後倆倆都沉入水裡。女孩子最後被救起,但是當他被救出水面時早已斷氣。這是我在報紙上看到的消息,但是當我再度回到這個屋子時,正好遇到那個母親,她當時是個寡婦,我對她至上哀悼之意,對她說當我聽到這個可怕的意外時,是何等的難過。她邀請我進入屋內,並帶我到起居室內坐下,起居室裡擺放著她兒子死時的巨幅照片,四周都是花朵,擺設的就像是英雄的墳墓。對此她表示:「看看他!他死亡當時的面容是何等的俊美。」我對此表示同意,接著她微笑說:「是這樣的,我寧願像這樣擁有他,也不願意將他送給另一個女人。」
3-4 「總有一天」與無聊感
在我的第一場演講中,我談到精神官能症所帶來的暫時性人生問題,也就是人們活在有一天(尚未,但是有一天)能夠的期待中,這常被連上救世主的情結。瑞士分析師瑞尼.瑪拉末(René Malamud)曾經給我一份人本主義哲學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的論文,他在文章中詳細談到這個問題。僅擷取一小部分內容如下,他說:
如果某人相信時間,那麼此人就沒有突然改變的可能性,他會持續不斷的期待當「時候到了」一切就會沒事了。假設某人沒能解決衝突,就會期待「時候到了」衝突就會自己解決,完全不需要做出決定。你常會看見那樣的狀況,特別是從個人的自我成就這一點來相信時間。人們會自我安慰,不僅僅是因為沒有真的做些什麼,也是因為沒有為必須做的事情做準備,因為有太多的時間,因此就沒必要匆促進行。我們可以從一個非常有天賦的作家的案例中得到這個機制的說明:這個作家想要寫一本書,認為那會成為世界文學界最重要的一本書,但是他除了對於想寫的內容有些想法,以及幻想這本書會帶來的影響,和告訴朋友們自己還沒有完全完成這本書之外,就什麼也沒再多做。實際的情況是,他連一個句子都還沒有寫出,連一個字都還沒寫下;但是,據他所言,他已經在這件事上投入了七年之久。當這類的人們越是年長後,越會緊抓住有一天他們會完成的幻想。當某些人到達一定的年紀,通常是在四十歲出頭,會乍然清醒,開始使用自身的力量,或者會出現像是精神官能症的崩潰,出於「假若沒有那個讓人感到安慰的時間假象時,就無法活著」這個事實。
這段話鮮明的描寫出我試圖要表達的內容。很久以前,英國的分析心理學家貝恩斯在他關於暫時性人生的論文中就寫過這一點,正如我先前所提到的。
《小王子》書中接下來的部分,我會詳細的閱讀。
喔!小王子!我就這麼一點一滴地開始了解你那悲傷的私密小生活……長久以來,你從觀看日落的安靜愉悅中找到唯一的娛樂。
我在第四天的早晨得知這些新的細節,當時你這麼告訴我:
「我很喜歡日落。我們一起去看日落吧。」
「不過我們還要等等,」我說。
「等等?等什麼?」
「等日落。我們必須要等到時候到了。」
起初,你似乎顯得非常驚訝。而接著你自己笑了笑。你對我說:
「我總以為自己還在家!」
是的。每個人都知道在美國的中午時分,太陽就在法國落下。
如果你可以在一分鐘之內飛到法國,你就能看到日落,直接從中午時分進入日落。可惜,法國太遠了。但是,在你的小小星球上,我的小王子,你只要將椅子挪個幾步,就可以隨你喜愛的看白晝或是暮色落下……
「有一天,」你對我這麼說:「我看了四十四次的日落!」
在那之後,你又說:
「你知道的⋯⋯當一個人很悲傷很悲傷的時候,就會喜愛日落……」
「所以你當時很悲傷嗎?」我問:「在四十四次日落那天?」
但是小王子沒有回答。
馮‧法蘭茲:你會如何解讀這部分?
學員:那是否是對於他自身早年死亡的預演?
馮‧法蘭茲:是的,可以這麼說——以那象徵性的四十四天。那是對他自身死亡的預感,此外,還有什麼?那是個不時想到死亡的浪漫方式,這在早期少年階段是常見的。但是這一點會如何連上其餘的問題?
學員:欠缺實際性。事物持續向後退;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看日落。
馮‧法蘭茲:是的,那是自我中心主義(egotism)的形式,是自戀主義(narcissism)的形式,而那也是當人們的生命不再流動以及當時間不被填滿時,自然會落入的心境,因為當你投入內在或外在的冒險時,你沒有時間看日落。然而,日落可能是忙碌的一天之後,所得到的一個寧靜美好片刻。假若日落讓你感到悲傷,那是因為在日落之前並沒有足夠的冒險。同樣的,我認為那和少年悲劇是有關的。人們,特別是當他們還年輕時,相當可能會受到無聊折磨。我記得自己在十四到十八歲那幾年常常感到無聊,在那之後就從來沒有這種感覺。表面上,那是因為個體必須要在學校裡待很長的時間而不能做喜歡的事。一旦我能夠做我喜歡做的事情,無聊的感覺就消失了。但是,相較於那樣的狀況,此處的無聊感顯得更加深刻。我曾經看過那樣的狀況,那是在年輕人間常見的精神官能症,但奇怪的是,這在他們年紀增長之後就會漸漸減輕。這與他們無法去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反倒總要去做不想做的事有關。因此,他們不覺得自己是在過生活,無聊感不過就是當個體不能活在生活中的主觀感受。事實上,並沒有真的無聊感。在大學裡,我仍然需要遵循無聊的課程,但是那時的我學會苦中作樂。如果你夠有創意,知道如何將自己置於現實中,你就能避開無聊感。我們將自身的自發幻想放入現實中,那麼無聊感就永遠消失了。接下來的人生就可以是愉快的或是不愉快的,充滿刺激的或是相反的,但是絕對不會是無聊的。因此,無聊感就是生命被阻擋的症狀,是個體不知道該如何將個人的內在投入現實中。如果我們知道要如何玩耍,無聊感就消失了。但是,有些孩子及成人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同時也不知道該如何帶出內在資源。在年少期,這不會是太過負面的症狀,因為某方面而言那是此時期的一部分,因為他們仍然無法實現自我。
一般年輕人所受的苦,部分主要來自於,就內在而言,他們已經是相當具有效能及理解力的成年人,但是從外在而言,他們並沒有得到使用這些能力的機會。他們被社會所抑制,造成的結果就是感到無聊。我曾經在學校裡教書,主要對象是十四歲到十八歲之間的學生。常見的許多問題來自於其實他們不僅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斷,而且內在也是豐富而具有理解力的,但是在外在的情境中,無論是在家中或是學校,他們都被以孩童的方式對待,得不到任何的機會。自然而然的,接下來就是生命受到阻滯,造成了想要與一切作對的無聊抗拒,一種帶著壞心情的貧乏作為。一般來說,如果我們能夠給予他們更多的理解、任務以及更多的責任,讓他們成功提升到更高的層次,那麼一切就會重回正軌。他們是被人為的困在低於他們所屬的層次,以致浮現出沉悶無聊感。
因此我們說:「正因為你感到無聊,也正因為你是懶惰的,你必須做兩倍的工作,但這些都是好差事。」那會終結無聊感!我們都知道,在十六到二十歲之間,自殺是相當常見的,但是在那之後就比較少見了。那個年紀的人常會有種奇怪的憂愁傷感,他們會感覺自己像是老人一樣。他們的臉上會出現彷彿自己知悉人生的表情,同時也覺得自己非常非常老,既然如此,與他人嬉戲玩樂或與女孩、男孩的玩樂有什麼樂趣可言,他們退縮到爺爺奶奶們的人生態度。這不過只是個症狀,意謂著他們還沒找到生命泉源的線索,因此以這樣的方式載浮載沉。而在這樣的年紀,對於那些與眾不同的少年來說,要找出他們人生的可能性會是更加困難的,於是生命就受到阻滯。顯然的,書中這個悲傷且不時看日出的孩子也有著相同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