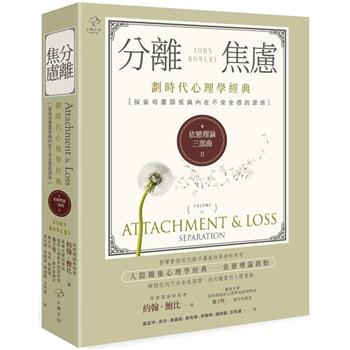【摘文1】
幼兒與母親分離後的反應
自博靈漢(Dorothy Burlingham)和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開始記錄寄宿幼兒園裡照料嬰兒和幼兒的經驗起,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世代的遠去。在這兩本出版於二戰期間的小冊子中,她們描繪照顧那些失去母親照料的幼兒所出現的嚴重問題。她們特別強調:在幼兒園的環境下,我們不可能為幼兒提供親生母親般的替代性照顧。漢普斯特德幼兒園曾經做過一些調整,以便每一位護士可以有足夠能力照顧幾個孩子,一般是幾個幼兒組成一個小組、由特定護士照顧。她們講述這些孩子對護士有非常強烈的占有欲,而且無論何時,只要特定護士關注別的孩子,他們會表現出非常強烈的嫉妒。
「托尼(3歲半)⋯⋯不允許瑪莉護士用『專屬他的』手去觸摸其他小朋友。吉姆(2∼3歲)無論何時,只要他『自己的』護士離開房間,就會大哭起來。雪莉(4歲)會在『她的』護士瑪莉恩有事離開時出現強烈不安。」
人們也許會問,為什麼?難道這些孩子本來就該這樣?他們本來就該對他們的護士有如此強烈的占有欲?在護士離開時,就該如此深受困擾?難道是因為給了他們太多關注、太過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所以寵壞他們了?或許,一些傳統主義者支持這個觀點。抑或是與此相反,孩子離開家後就面臨過多母親角色改變,或者是在幼兒園裡,可選擇什麼樣的人臨時替代母親角色本身就有太多限制?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轉向育兒的實踐。
這些在幼兒園的孩子不但對他們「自己的」護士有強烈占有欲和嫉妒心,而且也會對她有著異常敵對傾向,或者會拒絕她,甚至退縮到情感隔絕的狀態。下面的一些紀錄,可以闡明這一點:
「吉姆在17個月大時與非常漂亮而多情的母親分離,在我們的幼兒園也有良好的發展。待在園裡的期間,他對兩位年輕護士發展出了強烈依附,這兩個護士先後照顧過他。儘管吉姆適應環境、活躍,並且善於交際,但是一旦有什麼事情是與依附相關時,他的行為就會變得令人無法忍受。他會一直黏著護士,表現出過度的占有欲,完全不願意被留下、並且不斷索求,卻無法用任何方式表示他想要的是什麼。沒有特殊的跡象時,會看到吉姆躺在地板上啜泣,表現得很絕望。直到他最喜歡的護士離開了,有時只是一下子,他的這些反應才終止。他會變得安靜、沒有情緒反應。」
「雷吉剛來到我們這裡時只有5個月大,他在1歲8個月大時回家、回到母親身邊,兩個月後又回到幼兒園,從那一刻開始,他就一直與我們待在一起。與我們在一起時,他與兩個年輕護士發展出緊密的關係,這兩個護士曾在不同時間裡照顧過他。在他兩歲8個月大時,『他的』護士結婚了、第二段依附就突然破裂了。在她離開之後,雷吉覺得被遺棄了,並且變得絕望。兩週後護士回來看望雷吉,雷吉拒絕了。當護士對他講話時,雷吉把頭轉向另一邊;但是在她離開房間之後,雷吉盯著她走後關上的門。夜幕降臨時,雷吉呆呆的坐在床上,嘴裡唸著:『瑪莉是我的,但是我並不喜歡她。』」
這些觀察結果產生於戰爭時期的壓力下,它們被當作軼事一樣記錄下來,卻大多缺少細節。但是這些紀錄仍然在許多形式的心理病理學障礙上,擲入了一些光芒,讓人們重新審視它們的本質。那些發生在成年期的焦慮和憂鬱狀態,以及心理病理性狀況,往往可以與博靈漢和安娜.佛洛伊德所描述的焦慮、絕望和分離狀態,以一種系統型式聯繫起來。爾後的一些研究者也表示,年幼孩子無論何時與母親角色長時間分離,都很容易產生這種情況,無論他是不是對這種分離有所預期,或者就失去了母親角色。然而,在往後的生活中,我們通常很難確定一個人紊亂的情緒狀態是如何與他的經歷聯繫起來,也很難確定這個狀態是因為他當前經歷,還是因為過去經歷所產生的影響。在個體出生後早期的幾年人生,情緒狀態與人生經歷的關係,通常清晰明瞭。早期生活中的不安,可以看作是之後生活中出現病理性狀態的原型。
【摘文2】
是「過度依賴」還是「焦慮型依附」
在本書第一章,我們看到一些2∼4歲居住在漢普斯特德托兒所的兒童對某個或某幾個護士表現出強烈占有行為(引自博靈漢和安娜.佛洛伊德的研究)。舉個例子,從17個月大開始就住在這裡的吉姆,先對一個年輕護士產生了強烈依附,後來又依附了之後照顧他的護士。他對於每一個所依附的護士,都表現得非常黏人且占有欲很強,而且幾乎一刻也不願意讓護士離開。其他觀察者,包括我的同事羅伯遜和海尼克都發現,在托兒所裡,只要孩子有機會和工作人員建立依附關係,都會表現出如上所述的行為。而且,這些孩子回家之後,也會和母親如此相處。
我們在每一個年齡層都可以觀察到有形或是無形的依附行為,從童年期、青少年時期一直到成年時期。許多詞語可以描述這種依附行為,用來形容他們的詞有「嫉妒」、「占有欲」、「貪婪」、「不成熟」、「過度依賴」以及「很強的」或「強烈的」依附。從科學和臨床目的來說,這些用詞都有問題,因為它們源於逐漸被人放棄的理論,或是這些詞都使用模糊的描述,但是最重要的是這些詞都帶有「負面價值判斷」(adverse value judgement),並不恰當且沒有幫助。
儘管「嫉妒」和「占有欲」兩個詞描述精確,但是帶有一點輕蔑的意味。同樣的詞還有「貪婪」,這個詞常常意味著使用者的思維受到認為「源自被餵養的依附關係」這種假設影響。
「很強的」依附和「強烈的」依附,意思也是模糊的。這兩個詞,尤其是前一個詞甚至暗示這令人滿意的關係。
「不成熟」這個詞源於退化理論,這個理論在前一章最後已經有所提及,但是該理論與現有證據相悖。
在《依戀理論三部曲1:依附》的第12章中,我們已經提過「依賴」和「過度依賴」這兩個詞的模糊之處和錯誤的價值取向。我們將持續關注用詞的缺陷並且提出替代術語。
在臨床文獻中,或許沒有其他術語比「依賴」和「過度依賴」所使用得更加頻繁。黏人的孩子、不願意離開家的青少年、結婚後還和母親保持密切關係的妻子或者丈夫、需要他人陪伴的病人,以上這些或許遲早會被描述為「依賴」或者「過度依賴」。但是在使用這兩個詞時,隱含著不贊同、輕蔑的語氣。接下來,讓我們更仔細的考量使用這些詞時的個體行為,以及我們如何評價個體。
以本文的視角來看,大部分被治療師描述為依賴或者過度依賴的人是如此──他們所展示出的依附行為,在頻繁程度和緊迫性上超過治療師認為是正常的範疇。因此,觀察者使用這些詞語時包含了自己的價值和標準。這樣就造成了許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規範和價值不僅在個體和個體之間具有巨大差異,在文化和文化、次文化和次文化之間也存有巨大差異。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一些東方國家,有些行為不會獲得人們關注,甚至是其文化所提倡的;但是這些行為在西方文化下卻會受到懲罰,被認為是幼稚的依賴行為。另一個問題在於,即使是在同一個文化之下,在沒有了解其狀況、有機體功能和環境時,也不能有效評價其行為。如果不考慮兒童的年齡、他是否正在生病、是否最近經歷過度驚嚇,觀察者的判斷會有很大的誤差。那些容易被錯誤判斷為過度依賴的孩子,都是那些看起來比實際年紀大、處於疲勞或者生病狀態,最近有弟妹出生或者最近家裡有成年人去世的孩子。另一個典型例子是懷孕中或是正在照顧孩子的年輕女子。在以上所有例子中,依附行為的表現都比其他情況下更頻繁、更強烈。換句話說,在某些特定環境中,這些行為也在正常範圍之內,並不能說明個體的人格發展具有什麼樣的問題。
但是,所有年齡層都有人表現出不尋常、頻繁而急迫的依附行為,在所有年齡層中也會有人在無法解釋的情況下持續做出這些行為。當這種傾向超過一定的程度,個體就會被認為其出現了精神官能症的特徵。
當我們開始了解這些人時會發現──這個人很明顯在他有需要的時候對自己的依附對象可得性與反應沒有信心,因此他會不斷採取和依附對象保持接近的策略,以保證能夠隨時接觸到依附對象。但是將他們描述為「過度依賴」反而模糊了實際上的問題。甚至連「分離焦慮」(separation anxiety)這個術語也不是十分恰當。更好的方法是使用「焦慮型依附」(anxious attachment)或者「不安全依附」(insecure attachment)來形容這樣的情況。這樣的描述指出了行為核心,那就是「擔心依附對象不可及或者不對自己做出反應」。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加上這個詞可以幫助我們同理,我們通常會使用「焦慮型依附」這個術語。這個術語尊重一個人與依附對象保持親密關係的自然需求,並且暗示被描述的個體很害怕這段關係終結。
目前的研究理論是──儘管其他因果因素會對焦慮型依附發展產生一些影響,但是目前最明顯的影響是關於個人在依附對象可得性的經驗,這些經驗動搖了個體能不能在需要的時候是可以得到依附對象的信心。在下一章,我們將會仔細思考其他長久以來根深柢固於人們心中的替代性理論。
接下來的資料來自兩位工人階層的母親,她們分別描述了自己的孩子「過度依賴」時的情況,這些描述揭示了過度依賴的真實狀態。這些描述來自紐森夫婦的研究,該研究調查了七百名來自英國諾丁漢的4歲兒童。
一位礦工的妻子被詢問女兒是否有時候想要被母親摟抱時,她這麼回答:
「自從我在她兩歲時候因為住院離開她兩次(每次17天)之後,她就再也不信任我了。我完全不能去任何地方,即使去鄰居家串門子或是去購物,都要帶她一起去。她也從不離開我。今天,她從學校回來的時候像瘋了一樣跑進家裡,說:『哦,媽媽,我以為妳走了!』她無法忘記我之前曾經離開她,並無時無刻都要跟在我身邊。」
詢問一位卡車司機妻子同樣的問題時(她3個月前被丈夫拋棄過),她的回答如下:
「是的,最近開始,所有時間裡──自從丈夫離開之後。(研究者詢問:『那麼妳做了什麼呢?』)如果不忙的話,我會坐下來安撫女兒,因為,你知道的,她一直黏著我,不斷問:『妳愛我嗎? 妳不會離開我的,對吧?媽媽。』因此我會停下來試圖和她談談這個話題。但是我的意思是,在她這個年齡(大約4歲),有些事情確實沒辦法解釋清楚。她以前可以自己穿衣服,但是自從丈夫走了之後,她就開始依賴我了,我得幫她做所有瑣碎的事情。現在,我大多讓她去做自己愛做的事情。我覺得她在某些方面已經很不安了,我也不想讓她更不安。我確實在丈夫走了之後把她丟進了托兒所,我覺得這樣做能轉移她的注意力、讓她不再去想這件事,但是保母勸我無論如何都要把孩子帶回家,她說孩子整天都坐著哭。孩子肯定以為我也要拋棄她,因為父親離開了,而我又把她放進托兒所一整天。因此她只在托兒所待了兩週我就把她帶回家了。但是她現在很害怕被單獨留下來,如果我去廁所也要帶著她,她甚至不敢一個人待在房間裡。她很害怕被拋棄。」
總結這些表現出過度依賴和分離恐懼的孩子的表現之後,紐森夫婦寫道:「大部分孩子對於分離的恐懼是有現實基礎的,孩子或者他們的媽媽曾經住過院或者他們身上發生過其他分離事件。」然而,還有一些具有相同經歷的孩子並沒有明顯表現出分離焦慮,也有一些孩子並沒有類似的經歷卻恐懼分離。儘管個人經歷在產生分離焦慮中十分重要,但是顯然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
影響最大的有以下幾種因素:第一種是父母威脅要遺棄孩子,這經常被父母用來當作訓練或懲罰孩子的手段;第二種是孩子認為父母吵架會產生風險,導致父母分開。就目前的證據來看,如同薩蒂和費爾本很早以前的猜測──父母威脅要遺棄孩子,很可能是最有影響力的因素。我們也必須牢記,這種威脅之所以能對孩子有如此巨大的傷害在於「對孩子來說,分離是令人痛苦且令人恐懼的經歷」。
正因為如此,我們再一次回到我們的主題「分離」討論和母親分開對孩子來說有什麼樣的影響。【摘文3】
了解決定一個人的發展路徑的重要因素
根據瓦丁頓的理論,我們認為人格最根本特點是其「時間擴展性」(time-extended properties),可以被想像為「一系列可供選擇的發展路徑」。個體在最初從對每一位開放的眾多路徑中選擇哪一個路徑,取決於近乎無窮多的變項。但是在這些變項中有一些更容易被識別,因為這些變項的影響非常深遠。而研究者認為,沒有一種變項比孩子在家庭中的經歷對其人格發展有更為深遠的影響:因為,從生命的第一個月他與母親的關係到兒童期和青少年期他與雙親的關係,在這段過程中,他建立起關於各式各樣情境中依附對象會如何對待自己的運作模式,而在剩下的生命裡都會將自己的預期建立在這些運作模式上。
我們可以看到,與依附對象分離的體驗(無論持續多長時間),以及失去的經歷,或是被威脅要被拋棄的經歷──這些經歷都將個體處於最佳範圍內的某條路徑上的發展,轉向另一條在該範圍之外的路徑上。以鐵路作為比喻,這些經歷就像鐵路交叉處的道岔,讓火車從主要路線偏離到支線。比較幸運的是,通常這種偏離程度並不會很大,因而個體還可以輕易的回到主要路線上。相反的,其他時候,當某次偏離的程度過大且持續時間更久,或者又再次發生偏離,那麼此時如果要回到最初的路線就變得更困難,甚至不可能做到。
不過,我們千萬不要假定──分離、分離的威脅,以及失去是可以讓個體從發展最佳路徑上偏離出來,轉向次級路徑的僅存因素。如果現在呈現在此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家庭養育過程中,很多其他限制和缺點可能導致相同的結果。此外,這種偏離可能發生在任何一種被個體知覺為壓力或危機的生活事件之後,特別是當這個事件發生在不成熟的個體或是已經在次級發展路徑上的個體身上時。因此,有很多事件能夠將個體從原本的發展路徑轉向另一條發展路徑,而分離和失落的經歷以及被拋棄的威脅,只會是這些事件中的一小部分,這些大量的事件會被描述為生命中的重大變化。在這個定義的範疇中,還包括在一定情形中可能會幫助個體更良好發展的事件。
為什麼研究者將注意力集中於個體的分離和失落經歷,以及被拋棄的威脅,而不是其他事件呢?其原因相當多:首先,這些都是很容易被定義的事件,在短期內對個體有可被觀察到的影響。並且,如果個體繼續在嚴重偏離的路徑中發展,其長期影響也很容易被觀察到。因此,這些事件為研究者試圖闡明人格發展以及影響人格發展的因素等極為複雜的目標提供了有價值的切入點。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由於這些事件的影響並不限於人類,也能在其他物種中發現這些事件的影響,這提供了機會讓研究者重新完善人格發展理論。並且,也可以藉此機會改善理論在精神分析傳統、動物行為學和發展生物學中所內化的一些偏差觀念。
最後,這些事件在兒童、青少年以及成人生活中十分普遍,在我們所知的主要壓力來源占大部分,因而更清楚了解這些事件的影響,對於以理解、治療甚至在情況允許時,能夠及時幫助以預防精神障礙為己任的臨床心理學家。
不過,雖然或許我們證明了這項工作是有用的,但是這僅僅是個開始。人類的人格可能是地球上現存、複雜系統中最為複雜的一種。要描述人格建構的主要成分、要理解和預測人格工作的方式,以及最重要的,繪製出一個人千絲萬縷錯綜複雜的發展路徑,是我們全體未來的任務。
幼兒與母親分離後的反應
自博靈漢(Dorothy Burlingham)和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開始記錄寄宿幼兒園裡照料嬰兒和幼兒的經驗起,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世代的遠去。在這兩本出版於二戰期間的小冊子中,她們描繪照顧那些失去母親照料的幼兒所出現的嚴重問題。她們特別強調:在幼兒園的環境下,我們不可能為幼兒提供親生母親般的替代性照顧。漢普斯特德幼兒園曾經做過一些調整,以便每一位護士可以有足夠能力照顧幾個孩子,一般是幾個幼兒組成一個小組、由特定護士照顧。她們講述這些孩子對護士有非常強烈的占有欲,而且無論何時,只要特定護士關注別的孩子,他們會表現出非常強烈的嫉妒。
「托尼(3歲半)⋯⋯不允許瑪莉護士用『專屬他的』手去觸摸其他小朋友。吉姆(2∼3歲)無論何時,只要他『自己的』護士離開房間,就會大哭起來。雪莉(4歲)會在『她的』護士瑪莉恩有事離開時出現強烈不安。」
人們也許會問,為什麼?難道這些孩子本來就該這樣?他們本來就該對他們的護士有如此強烈的占有欲?在護士離開時,就該如此深受困擾?難道是因為給了他們太多關注、太過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所以寵壞他們了?或許,一些傳統主義者支持這個觀點。抑或是與此相反,孩子離開家後就面臨過多母親角色改變,或者是在幼兒園裡,可選擇什麼樣的人臨時替代母親角色本身就有太多限制?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轉向育兒的實踐。
這些在幼兒園的孩子不但對他們「自己的」護士有強烈占有欲和嫉妒心,而且也會對她有著異常敵對傾向,或者會拒絕她,甚至退縮到情感隔絕的狀態。下面的一些紀錄,可以闡明這一點:
「吉姆在17個月大時與非常漂亮而多情的母親分離,在我們的幼兒園也有良好的發展。待在園裡的期間,他對兩位年輕護士發展出了強烈依附,這兩個護士先後照顧過他。儘管吉姆適應環境、活躍,並且善於交際,但是一旦有什麼事情是與依附相關時,他的行為就會變得令人無法忍受。他會一直黏著護士,表現出過度的占有欲,完全不願意被留下、並且不斷索求,卻無法用任何方式表示他想要的是什麼。沒有特殊的跡象時,會看到吉姆躺在地板上啜泣,表現得很絕望。直到他最喜歡的護士離開了,有時只是一下子,他的這些反應才終止。他會變得安靜、沒有情緒反應。」
「雷吉剛來到我們這裡時只有5個月大,他在1歲8個月大時回家、回到母親身邊,兩個月後又回到幼兒園,從那一刻開始,他就一直與我們待在一起。與我們在一起時,他與兩個年輕護士發展出緊密的關係,這兩個護士曾在不同時間裡照顧過他。在他兩歲8個月大時,『他的』護士結婚了、第二段依附就突然破裂了。在她離開之後,雷吉覺得被遺棄了,並且變得絕望。兩週後護士回來看望雷吉,雷吉拒絕了。當護士對他講話時,雷吉把頭轉向另一邊;但是在她離開房間之後,雷吉盯著她走後關上的門。夜幕降臨時,雷吉呆呆的坐在床上,嘴裡唸著:『瑪莉是我的,但是我並不喜歡她。』」
這些觀察結果產生於戰爭時期的壓力下,它們被當作軼事一樣記錄下來,卻大多缺少細節。但是這些紀錄仍然在許多形式的心理病理學障礙上,擲入了一些光芒,讓人們重新審視它們的本質。那些發生在成年期的焦慮和憂鬱狀態,以及心理病理性狀況,往往可以與博靈漢和安娜.佛洛伊德所描述的焦慮、絕望和分離狀態,以一種系統型式聯繫起來。爾後的一些研究者也表示,年幼孩子無論何時與母親角色長時間分離,都很容易產生這種情況,無論他是不是對這種分離有所預期,或者就失去了母親角色。然而,在往後的生活中,我們通常很難確定一個人紊亂的情緒狀態是如何與他的經歷聯繫起來,也很難確定這個狀態是因為他當前經歷,還是因為過去經歷所產生的影響。在個體出生後早期的幾年人生,情緒狀態與人生經歷的關係,通常清晰明瞭。早期生活中的不安,可以看作是之後生活中出現病理性狀態的原型。
【摘文2】
是「過度依賴」還是「焦慮型依附」
在本書第一章,我們看到一些2∼4歲居住在漢普斯特德托兒所的兒童對某個或某幾個護士表現出強烈占有行為(引自博靈漢和安娜.佛洛伊德的研究)。舉個例子,從17個月大開始就住在這裡的吉姆,先對一個年輕護士產生了強烈依附,後來又依附了之後照顧他的護士。他對於每一個所依附的護士,都表現得非常黏人且占有欲很強,而且幾乎一刻也不願意讓護士離開。其他觀察者,包括我的同事羅伯遜和海尼克都發現,在托兒所裡,只要孩子有機會和工作人員建立依附關係,都會表現出如上所述的行為。而且,這些孩子回家之後,也會和母親如此相處。
我們在每一個年齡層都可以觀察到有形或是無形的依附行為,從童年期、青少年時期一直到成年時期。許多詞語可以描述這種依附行為,用來形容他們的詞有「嫉妒」、「占有欲」、「貪婪」、「不成熟」、「過度依賴」以及「很強的」或「強烈的」依附。從科學和臨床目的來說,這些用詞都有問題,因為它們源於逐漸被人放棄的理論,或是這些詞都使用模糊的描述,但是最重要的是這些詞都帶有「負面價值判斷」(adverse value judgement),並不恰當且沒有幫助。
儘管「嫉妒」和「占有欲」兩個詞描述精確,但是帶有一點輕蔑的意味。同樣的詞還有「貪婪」,這個詞常常意味著使用者的思維受到認為「源自被餵養的依附關係」這種假設影響。
「很強的」依附和「強烈的」依附,意思也是模糊的。這兩個詞,尤其是前一個詞甚至暗示這令人滿意的關係。
「不成熟」這個詞源於退化理論,這個理論在前一章最後已經有所提及,但是該理論與現有證據相悖。
在《依戀理論三部曲1:依附》的第12章中,我們已經提過「依賴」和「過度依賴」這兩個詞的模糊之處和錯誤的價值取向。我們將持續關注用詞的缺陷並且提出替代術語。
在臨床文獻中,或許沒有其他術語比「依賴」和「過度依賴」所使用得更加頻繁。黏人的孩子、不願意離開家的青少年、結婚後還和母親保持密切關係的妻子或者丈夫、需要他人陪伴的病人,以上這些或許遲早會被描述為「依賴」或者「過度依賴」。但是在使用這兩個詞時,隱含著不贊同、輕蔑的語氣。接下來,讓我們更仔細的考量使用這些詞時的個體行為,以及我們如何評價個體。
以本文的視角來看,大部分被治療師描述為依賴或者過度依賴的人是如此──他們所展示出的依附行為,在頻繁程度和緊迫性上超過治療師認為是正常的範疇。因此,觀察者使用這些詞語時包含了自己的價值和標準。這樣就造成了許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規範和價值不僅在個體和個體之間具有巨大差異,在文化和文化、次文化和次文化之間也存有巨大差異。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一些東方國家,有些行為不會獲得人們關注,甚至是其文化所提倡的;但是這些行為在西方文化下卻會受到懲罰,被認為是幼稚的依賴行為。另一個問題在於,即使是在同一個文化之下,在沒有了解其狀況、有機體功能和環境時,也不能有效評價其行為。如果不考慮兒童的年齡、他是否正在生病、是否最近經歷過度驚嚇,觀察者的判斷會有很大的誤差。那些容易被錯誤判斷為過度依賴的孩子,都是那些看起來比實際年紀大、處於疲勞或者生病狀態,最近有弟妹出生或者最近家裡有成年人去世的孩子。另一個典型例子是懷孕中或是正在照顧孩子的年輕女子。在以上所有例子中,依附行為的表現都比其他情況下更頻繁、更強烈。換句話說,在某些特定環境中,這些行為也在正常範圍之內,並不能說明個體的人格發展具有什麼樣的問題。
但是,所有年齡層都有人表現出不尋常、頻繁而急迫的依附行為,在所有年齡層中也會有人在無法解釋的情況下持續做出這些行為。當這種傾向超過一定的程度,個體就會被認為其出現了精神官能症的特徵。
當我們開始了解這些人時會發現──這個人很明顯在他有需要的時候對自己的依附對象可得性與反應沒有信心,因此他會不斷採取和依附對象保持接近的策略,以保證能夠隨時接觸到依附對象。但是將他們描述為「過度依賴」反而模糊了實際上的問題。甚至連「分離焦慮」(separation anxiety)這個術語也不是十分恰當。更好的方法是使用「焦慮型依附」(anxious attachment)或者「不安全依附」(insecure attachment)來形容這樣的情況。這樣的描述指出了行為核心,那就是「擔心依附對象不可及或者不對自己做出反應」。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加上這個詞可以幫助我們同理,我們通常會使用「焦慮型依附」這個術語。這個術語尊重一個人與依附對象保持親密關係的自然需求,並且暗示被描述的個體很害怕這段關係終結。
目前的研究理論是──儘管其他因果因素會對焦慮型依附發展產生一些影響,但是目前最明顯的影響是關於個人在依附對象可得性的經驗,這些經驗動搖了個體能不能在需要的時候是可以得到依附對象的信心。在下一章,我們將會仔細思考其他長久以來根深柢固於人們心中的替代性理論。
接下來的資料來自兩位工人階層的母親,她們分別描述了自己的孩子「過度依賴」時的情況,這些描述揭示了過度依賴的真實狀態。這些描述來自紐森夫婦的研究,該研究調查了七百名來自英國諾丁漢的4歲兒童。
一位礦工的妻子被詢問女兒是否有時候想要被母親摟抱時,她這麼回答:
「自從我在她兩歲時候因為住院離開她兩次(每次17天)之後,她就再也不信任我了。我完全不能去任何地方,即使去鄰居家串門子或是去購物,都要帶她一起去。她也從不離開我。今天,她從學校回來的時候像瘋了一樣跑進家裡,說:『哦,媽媽,我以為妳走了!』她無法忘記我之前曾經離開她,並無時無刻都要跟在我身邊。」
詢問一位卡車司機妻子同樣的問題時(她3個月前被丈夫拋棄過),她的回答如下:
「是的,最近開始,所有時間裡──自從丈夫離開之後。(研究者詢問:『那麼妳做了什麼呢?』)如果不忙的話,我會坐下來安撫女兒,因為,你知道的,她一直黏著我,不斷問:『妳愛我嗎? 妳不會離開我的,對吧?媽媽。』因此我會停下來試圖和她談談這個話題。但是我的意思是,在她這個年齡(大約4歲),有些事情確實沒辦法解釋清楚。她以前可以自己穿衣服,但是自從丈夫走了之後,她就開始依賴我了,我得幫她做所有瑣碎的事情。現在,我大多讓她去做自己愛做的事情。我覺得她在某些方面已經很不安了,我也不想讓她更不安。我確實在丈夫走了之後把她丟進了托兒所,我覺得這樣做能轉移她的注意力、讓她不再去想這件事,但是保母勸我無論如何都要把孩子帶回家,她說孩子整天都坐著哭。孩子肯定以為我也要拋棄她,因為父親離開了,而我又把她放進托兒所一整天。因此她只在托兒所待了兩週我就把她帶回家了。但是她現在很害怕被單獨留下來,如果我去廁所也要帶著她,她甚至不敢一個人待在房間裡。她很害怕被拋棄。」
總結這些表現出過度依賴和分離恐懼的孩子的表現之後,紐森夫婦寫道:「大部分孩子對於分離的恐懼是有現實基礎的,孩子或者他們的媽媽曾經住過院或者他們身上發生過其他分離事件。」然而,還有一些具有相同經歷的孩子並沒有明顯表現出分離焦慮,也有一些孩子並沒有類似的經歷卻恐懼分離。儘管個人經歷在產生分離焦慮中十分重要,但是顯然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
影響最大的有以下幾種因素:第一種是父母威脅要遺棄孩子,這經常被父母用來當作訓練或懲罰孩子的手段;第二種是孩子認為父母吵架會產生風險,導致父母分開。就目前的證據來看,如同薩蒂和費爾本很早以前的猜測──父母威脅要遺棄孩子,很可能是最有影響力的因素。我們也必須牢記,這種威脅之所以能對孩子有如此巨大的傷害在於「對孩子來說,分離是令人痛苦且令人恐懼的經歷」。
正因為如此,我們再一次回到我們的主題「分離」討論和母親分開對孩子來說有什麼樣的影響。【摘文3】
了解決定一個人的發展路徑的重要因素
根據瓦丁頓的理論,我們認為人格最根本特點是其「時間擴展性」(time-extended properties),可以被想像為「一系列可供選擇的發展路徑」。個體在最初從對每一位開放的眾多路徑中選擇哪一個路徑,取決於近乎無窮多的變項。但是在這些變項中有一些更容易被識別,因為這些變項的影響非常深遠。而研究者認為,沒有一種變項比孩子在家庭中的經歷對其人格發展有更為深遠的影響:因為,從生命的第一個月他與母親的關係到兒童期和青少年期他與雙親的關係,在這段過程中,他建立起關於各式各樣情境中依附對象會如何對待自己的運作模式,而在剩下的生命裡都會將自己的預期建立在這些運作模式上。
我們可以看到,與依附對象分離的體驗(無論持續多長時間),以及失去的經歷,或是被威脅要被拋棄的經歷──這些經歷都將個體處於最佳範圍內的某條路徑上的發展,轉向另一條在該範圍之外的路徑上。以鐵路作為比喻,這些經歷就像鐵路交叉處的道岔,讓火車從主要路線偏離到支線。比較幸運的是,通常這種偏離程度並不會很大,因而個體還可以輕易的回到主要路線上。相反的,其他時候,當某次偏離的程度過大且持續時間更久,或者又再次發生偏離,那麼此時如果要回到最初的路線就變得更困難,甚至不可能做到。
不過,我們千萬不要假定──分離、分離的威脅,以及失去是可以讓個體從發展最佳路徑上偏離出來,轉向次級路徑的僅存因素。如果現在呈現在此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家庭養育過程中,很多其他限制和缺點可能導致相同的結果。此外,這種偏離可能發生在任何一種被個體知覺為壓力或危機的生活事件之後,特別是當這個事件發生在不成熟的個體或是已經在次級發展路徑上的個體身上時。因此,有很多事件能夠將個體從原本的發展路徑轉向另一條發展路徑,而分離和失落的經歷以及被拋棄的威脅,只會是這些事件中的一小部分,這些大量的事件會被描述為生命中的重大變化。在這個定義的範疇中,還包括在一定情形中可能會幫助個體更良好發展的事件。
為什麼研究者將注意力集中於個體的分離和失落經歷,以及被拋棄的威脅,而不是其他事件呢?其原因相當多:首先,這些都是很容易被定義的事件,在短期內對個體有可被觀察到的影響。並且,如果個體繼續在嚴重偏離的路徑中發展,其長期影響也很容易被觀察到。因此,這些事件為研究者試圖闡明人格發展以及影響人格發展的因素等極為複雜的目標提供了有價值的切入點。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由於這些事件的影響並不限於人類,也能在其他物種中發現這些事件的影響,這提供了機會讓研究者重新完善人格發展理論。並且,也可以藉此機會改善理論在精神分析傳統、動物行為學和發展生物學中所內化的一些偏差觀念。
最後,這些事件在兒童、青少年以及成人生活中十分普遍,在我們所知的主要壓力來源占大部分,因而更清楚了解這些事件的影響,對於以理解、治療甚至在情況允許時,能夠及時幫助以預防精神障礙為己任的臨床心理學家。
不過,雖然或許我們證明了這項工作是有用的,但是這僅僅是個開始。人類的人格可能是地球上現存、複雜系統中最為複雜的一種。要描述人格建構的主要成分、要理解和預測人格工作的方式,以及最重要的,繪製出一個人千絲萬縷錯綜複雜的發展路徑,是我們全體未來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