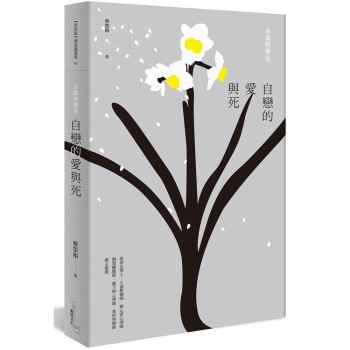【內文試閱】
[ 談自戀A版本 ]精神分析是種修行嗎?
這個子題是有些奇怪,是的,就先以奇怪的命題出發。尤其是要談「自戀」這個困難的主題,到底它和日常生活裡常聽到的要「做自己」有何同或異呢?不過,做為臨床家的特權是有機會,透過診療室裡,個案重複再重複要「做自己」的課題,來觀察到底這是什麼意思,以及這跟我們要談的「自戀」之間的關係。這個線索只是起點,仍需要先回到精神分析後設心理學的脈絡。
其實,這個標題是未來式的命題,它跟「自戀」主題的關係,要以後才會更明白。此刻我只是先標示出來,不過重點不在修行,而是在精神分析會是什麼?此刻,我只能先談眼前正在發生的事,但總是對未來有些想法掛在心中吧,不說出來,也就不會知道。雖然我知道,今天的主題是「自戀」。
先大膽提問,人世間果真有「自戀」這種東西嗎?或者純粹只是藉著語言和行動,所圍事出來的事情?不過,佛洛伊德還是談了「原初自戀」這種想法,這是什麼呢?我們真的能夠了解它嗎?它以什麼樣貌存在?有百分百純度的它,可以讓我們感受嗎?或者唯有比昂(Bion)提及的,自戀和「社會戀」(social-ism)是同時存在的,我倒想再推論,不只同時存在,在人世間的實情上,是兩者依著不同比例的混合,而自戀和社會戀各自百分百純金般的存在,只是烏托邦嗎?
或者如溫尼科特(Winnicott)所說的,沒有嬰兒這件事,有的是母親和嬰兒。如果我進一步解讀,一如「是否沒有自戀這件事,有的是社會戀和自戀」?那麼我這些話能夠指涉什麼,讓我們觀察、欣賞和想像嗎?
我會在不同時空和想法裡來來回回,需要來來回回,只是為了這個困難的主題,什麼是「自戀」?先回到我在其它文章曾說過的:
「以narcissism為例,佛洛伊德在1914年以《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引進這語詞,以前是Narcissus以美男子的名義活在希臘神話裡。他甚至拒絕美麗的回音女神Echo的親近,而一直看著水面裡自己的倒影,後來掉下水中,變成一朵水仙花的故事。這是美麗的故事,讀者不太會苛責Narcissus的舉動,何況他淹死後還是成為美麗的水仙。但是當佛洛伊德以水仙花的故事,來說明人性裡有這個領域,是人要讓自己永遠傳承下去的力量。
佛洛伊德以神話故事來描述,人們有這種只愛著自己影子的可能性,但是佛洛伊德把這字眼拓展成,具有原始的性學和精神病的特質傾向,也把愛情裡加進了有narcissism的風味。雖然神話裡,回音仙子和Narcissus的愛情是失敗的結果,卻蛻變出水仙花,佛洛伊德在這篇文章並不強調,那些死亡的傾向也頗有生的蛻變味道,但他在希臘神話所描繪的神話意義裡,加進了個人臨床觀察的推演。
以這些事例來看,我相信在未來,仍會有其它的情況會出現,或者會把narcissism推向更狹窄的定義,以容易捕捉這個語詞想傳遞的內容。但是如果這樣的話,也從以上的說明裡可以看出,一個詞的被運用,是某種程度的回到歷史的牽連,但又被增添了其它微妙的內涵。
也讓1968年起,美國的精神醫學診斷條例(DSM)藉由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語詞,把Narcissus帶進精神醫學的診斷裡,不過已不再與美麗有關了,而是強調只愛自己,會掉進水中淹死的比喻情節,也不會死後長出美麗令人懷念的水仙花了。也就是,從神話到心理學,這語詞的某些部分被棄置一旁,例如Narcissus的美貌。這是一個語詞的演變,當我們把它譯為『自戀』,雖然這語詞的翻譯並沒有引發我們的爭議,當我們使用『自戀』這詞語來談論心理世界時,雖然我們常說『戀愛』是愛的過程裡的某個階段,但何以不是被以『自愛』的翻譯呢?或者我們會覺得『自愛』是愛嗎?這是從我們的語詞『愛』的定義而問出的疑惑。」(引自本書:〈關於翻譯:以『精神分析』來了解psycho-analysis是可能的嗎?〉)
一如精神分析取向實作的過程,當我們知道了伊底帕斯情結或自戀的理論後,雖然仍只能先從目前此時此地談起,但是我們仍然無時無刻盼望著,哪一天能夠走到「伊底帕斯情結」啊。這可不是開玩笑,也不是只以比昂的「沒有欲望與沒有記憶」來搪塞,依我的解讀,比昂會提出來這個立場,並不是大家都做到了,而是大家都做不到,因此需要立這個文字碑,讓來來往往者能夠看到它。
那麼我是如何理解「破壞本能」和「破壞的自戀」?它們到底是什麼呢?破壞是針對什麼而說的?一般說法裡有大破大立,但有某種破壞一直被當作是問題時,是因為缺乏後續的大立?是從誰的角度來說的呢?是誰在破壞誰呢?
這和臨床工作有什麼關聯呢?它是我們需要的概念嗎?「破壞」和「破壞的自戀」,在臨床現象上的差異是什麼?何種情況會讓我們覺得「破壞的自戀」在展現呢?我們是依著哪些跡象做成這種判斷?我們如何區分跟自戀無關的破壞?或自戀是無所不在的,如同佛洛伊德所說的「原初自戀」,那麼當自戀遍及生活的所有細節,我們談論「自戀」這語詞還有什麼意義嗎?
我引用的這三篇參考文章(見後記),首先是臨床的負向反應和自戀有關,不過佛洛伊德原本是以這種反應是死亡本能,但是當說那是自戀時,就有了自戀和死亡本能的關連。這種自戀的現象是有破壞力,因此被當作是「破壞的自戀」,也就是,什麼情況下我們會說某種破壞是破壞本能在運作,而不是一般的破壞?是指重複性高,影響生活層面大,而且總是讓人覺得多說也無用的感受?「我也沒辦法」的強烈感受,是佛洛伊德說的負面治療效應裡的死亡本能?
不過,還是得回到一個很基本的實作課題,什麼情況會讓我們需要把「本能」這個如此難以捉摸,甚至不可能被五官察覺的語詞,做為我們要談論某些臨床現象的說詞呢?當我們搬出本能的語詞時是慎重的嗎?或者更像是展現我們做為治療師,是多麼無能為力的感覺?
因此「本能」,尤其是破壞的本能被搬出來,上演一場注定的悲劇?或者只是跑跑龍套,做為我們趨近更深沈挫折的串場?我們就是需要這個術語做為平台,不然我們根本就只能無言的嘆息,嘆著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的氣?或者所謂破壞本能的平台上,就是圍繞著各路來的嘆息聲,路過者也可以輕易就感受到的無奈,一如我們常是在和個案會談不久,就會想著,這個人怎麼這麼自戀?
或者覺得這個人怎麼充滿著死亡的氣息?只有不斷地破壞,無止盡的破壞,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被問,何以他們仍能活到此時,自己走進診療室裡?無論他們是想要什麼,或者不知想要什麼,但就是覺得想來說話,想來知道有另一個會聽他說話的人,就算他多麼強烈地想要把對方搞壞掉,但是能來診療室並且維持著這種相信,「可以把對方搞壞」,這種相信是什麼力量呢?
如果有人笑說,難道精神分析就只是搞性,搞自戀,搞本能,再加上伊底帕斯情結,然後就搞定一切了?也許我們會如佛洛伊德自嘆著,精神分析總是惹毛了人們,只因為他的論點是第三種對於人類自戀的衝擊,然後這樣就解釋了精神分析的命運了嗎?我們做為精神分析取向者的志氣是什麼呢?畢竟,佛洛伊德所描述的,人類有史以來對於人的自戀的三大衝擊案件,除了他的論點是第三案之外,前兩案件是天文學家伽利略和演化學家達爾文的挑釁。
當伽利略說太陽才是中心,地球只是圍著太陽打轉的星球,這可是嚴重的冒犯了地球是中心的主流論點。這差點讓伽利略被架上絞台。至於達爾文對於人的自戀的冒犯,是在漫長的人類史裡,人不是一直是人,而是可能由其它物種演化而來。伽俐略的假說後來發展成天文學,達爾文的演化論至今仍佔據著物種變化的主流論述。
也就是,現代人覺得伽利略和達爾文說對了重要現象呢。那麼,佛洛伊德的論點會走向伽利略和達爾文的命運嗎?那是誰的責任呢?佛洛伊德舉了這三個重大案件,難道只為了說明自己也有很偉大的發明和發現,或也有意圖覺得自己論點的命運,至少也能步上俐伽略和達爾文的後塵?
畢竟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三個案件後,人並沒有被這三大案件所摧毀,人還是活著,活下來,繼續生存著是證明了什麼呢?就算是有對於自戀衝擊的大案件,仍是不足以完全摧毀人類,人們還是活著和活下來,繼續展現人原本有的自戀,是否對於人類整體來說,這些重大案件的揭示,並不足以毀滅人類,但是就個體來說,這種對於自戀的衝擊,是否會有不同的故事呢?
這涉及了精神分析只談個體嗎?群體呢?佛洛伊德曾談群體心理學,以及比昂的自戀和社會(群體)戀,雖然目前流行的說法「做自己」,幾乎是不能任意被撼動和質疑的說法,但做自己是什麼意思呢?和我們談論的自戀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兩者間的地圖是同一國度,或是海中的兩個孤島?如果以大海來比喻,無論是多麼遙遠的孤島,兩者之間總是有相連的所在,這個所在是群體嗎?一如相同社會,同一個家庭裡,個人也是如此模式?
那麼,精神分析的個體主義,需要談論多少深層海底相連的海床呢?畢竟除了南北極浮冰,沒有孤島是如浮冰般漂浮的。
就算有了前述三大案例衝擊人的自戀,但是結果並沒有將自戀沖走,因此這三大案件不是洪水需要讓人另再造方舟來求生,而是在人生的茫茫大海依然自戀來求生。讓自戀就地成為一艘方舟?如果是這樣子,在洪水消退後,回頭來說自戀是眾多人生問題來源,這是恩將仇報嗎?這種比喻有重大的漏洞嗎?這對於我們了解自戀是幫忙,還是幫倒忙?
「自戀」會肯束手就擒嗎?或者說,自戀的力量就足以造就了一個孤島,社會群體裡的人際孤島,不只是漂浮的方舟,而是如海中孤島,自然有了自己的生態環境的發展。
因此還是勞煩了精神分析者,如克萊因(M. Klein)、寇哈特(Kohut)、葛林(A. Green)、溫尼科特等出面,想來相救,他們是搭著各自打造的方舟,活著自己的故事和命運?或者他們是各自的孤島,我們是搭著方舟的人,在孤島間流浪採集地方誌裡感人的故事和理念,再以我們自己的方言,來翻譯這些故事和理念?也許這些故事和理念,如同比昂描述臨床實作過程裡,浮現的「被選擇的事實」(selected facts)所打造成的島嶼?他們是各自圍繞著自戀的人性島嶼,在相同屬性的島嶼上,描述著自戀的周遭景緻?或他們描繪的風格和周邊風景不同的島嶼,只是湊巧取個相同的王國名稱?
而我們只能以自已的方言,翻譯採集到的故事和理念,甚至這不是大家想像中的,社會裡共通主流語言的翻譯。這是免不了的過程,至於實質在心中發揮功能的是,每個人以自身習得並累積的方言來了解這些情況。這種說法也許更貼切,更真實,也就是說,我們除了以被中譯出來的文字,來了解和想像外,還有其它我們自身特有的母語和興趣,以及風格所累積起來的複雜方言體系。
這不是一般說的,發出聲音的台語、客語和原住民語等而已,而是在人生過程裡,以這些為基礎再捲進來攪在一起的每個人自己的方言,是最後決定著我們所採集到孤島上的故事和理念的意義。故事也很重要,是每個人不同經驗帶來的情感因子隱藏的所在。例如,接受不同國度的訓練、不同督導等因子的影響,這些影響比能夠想得到的還要更深刻,因為那些涉及情感的交流。
如果這樣子,那怎麼辦呢?不同的特性和強調,卻有著相同的「自戀」的國名,這會發生什麼事呢?是否如同我的經驗裡,例如,我的布農族朋友和他的阿公及阿爸有相同的名字,但是朋友的媽媽叫著三個不同人的名字時,回應的人並不會答錯,是她每次都叫對人名,或是三個人都聽得出那聲音是呼喚他,這隱含著口氣情感和場合,或者是隱含著不同比重的尊敬和愛意?
好吧,我們在臨床實作的過程裡,浮現要稱呼某些場景是「自戀」時,我們是叫著公公、先生或兒子呢?或根本就是相互陌生的三個人,只是硬被我們湊合在一起?它們之間合得來嗎?它們說著相同的方言嗎?是否湊巧地,只有「自戀」這兩個字的發音是相同的,但是各有自己的家族史,不同的命運在等待著它們,有些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有」關係。
另外,是否溫尼科特描繪「假我」時,就意味著他是書寫著「自戀」的哀亡史?這可能是接續佛洛伊德所列舉的,對於人的自戀的三種打擊之外的第四種?「自戀」如何容忍為了活著和活下去,而需要有偽裝,這對自戀是最大的打擊?這種打擊猶如死亡才能忍受,是否這種死亡的結果,讓假我的發展史就是自戀的哀亡史?這也是造就了死亡本能的兄弟,或者這種死亡本能就是自戀的本尊,自戀只是它的化身?
從精神分析史的發展來看,當我們談「自戀」的好或壞,創造或破壞時,就像是自戀本身具有天使和惡魔的可能性。加上分裂機制的運轉,使得當「自戀」是天使時,就失去了惡魔;當「自戀」只偏重惡魔時,天使就消失了。是否這種原始的分裂機制(splitting)的作用,加上「自戀」的雙重特質,使得偏重一方時,就失去另一方。而這是最原始的失落、悲傷和抑鬱的起點,比佛洛伊德後來在《哀悼與憂鬱》裡,所提到的完整客體,例如父母親的死亡,所帶來的失落和憂鬱的論點還要更原始?
值得疑問的是,何以目前當某些讓人不愉快的態度和舉動,會讓我們命名那是「自戀」呢?這些都是如此活生生出現在互動過程裡,不過就臨床經驗來說,這常是當事者不自覺的現象,或者這裡所說的「不自覺」還不夠貼切和精準,而要說這些都是「自戀」在衰亡的過程裡,所遺留下來的梗或骨頭,硬梆梆的,如同刺那般,在人生的互動場域裡,我們說它是老梗,老是重複出現相同如刺般的硬梗,但它卻是最嬰兒的哭聲......
[ 談自戀A版本 ]精神分析是種修行嗎?
這個子題是有些奇怪,是的,就先以奇怪的命題出發。尤其是要談「自戀」這個困難的主題,到底它和日常生活裡常聽到的要「做自己」有何同或異呢?不過,做為臨床家的特權是有機會,透過診療室裡,個案重複再重複要「做自己」的課題,來觀察到底這是什麼意思,以及這跟我們要談的「自戀」之間的關係。這個線索只是起點,仍需要先回到精神分析後設心理學的脈絡。
其實,這個標題是未來式的命題,它跟「自戀」主題的關係,要以後才會更明白。此刻我只是先標示出來,不過重點不在修行,而是在精神分析會是什麼?此刻,我只能先談眼前正在發生的事,但總是對未來有些想法掛在心中吧,不說出來,也就不會知道。雖然我知道,今天的主題是「自戀」。
先大膽提問,人世間果真有「自戀」這種東西嗎?或者純粹只是藉著語言和行動,所圍事出來的事情?不過,佛洛伊德還是談了「原初自戀」這種想法,這是什麼呢?我們真的能夠了解它嗎?它以什麼樣貌存在?有百分百純度的它,可以讓我們感受嗎?或者唯有比昂(Bion)提及的,自戀和「社會戀」(social-ism)是同時存在的,我倒想再推論,不只同時存在,在人世間的實情上,是兩者依著不同比例的混合,而自戀和社會戀各自百分百純金般的存在,只是烏托邦嗎?
或者如溫尼科特(Winnicott)所說的,沒有嬰兒這件事,有的是母親和嬰兒。如果我進一步解讀,一如「是否沒有自戀這件事,有的是社會戀和自戀」?那麼我這些話能夠指涉什麼,讓我們觀察、欣賞和想像嗎?
我會在不同時空和想法裡來來回回,需要來來回回,只是為了這個困難的主題,什麼是「自戀」?先回到我在其它文章曾說過的:
「以narcissism為例,佛洛伊德在1914年以《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引進這語詞,以前是Narcissus以美男子的名義活在希臘神話裡。他甚至拒絕美麗的回音女神Echo的親近,而一直看著水面裡自己的倒影,後來掉下水中,變成一朵水仙花的故事。這是美麗的故事,讀者不太會苛責Narcissus的舉動,何況他淹死後還是成為美麗的水仙。但是當佛洛伊德以水仙花的故事,來說明人性裡有這個領域,是人要讓自己永遠傳承下去的力量。
佛洛伊德以神話故事來描述,人們有這種只愛著自己影子的可能性,但是佛洛伊德把這字眼拓展成,具有原始的性學和精神病的特質傾向,也把愛情裡加進了有narcissism的風味。雖然神話裡,回音仙子和Narcissus的愛情是失敗的結果,卻蛻變出水仙花,佛洛伊德在這篇文章並不強調,那些死亡的傾向也頗有生的蛻變味道,但他在希臘神話所描繪的神話意義裡,加進了個人臨床觀察的推演。
以這些事例來看,我相信在未來,仍會有其它的情況會出現,或者會把narcissism推向更狹窄的定義,以容易捕捉這個語詞想傳遞的內容。但是如果這樣的話,也從以上的說明裡可以看出,一個詞的被運用,是某種程度的回到歷史的牽連,但又被增添了其它微妙的內涵。
也讓1968年起,美國的精神醫學診斷條例(DSM)藉由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語詞,把Narcissus帶進精神醫學的診斷裡,不過已不再與美麗有關了,而是強調只愛自己,會掉進水中淹死的比喻情節,也不會死後長出美麗令人懷念的水仙花了。也就是,從神話到心理學,這語詞的某些部分被棄置一旁,例如Narcissus的美貌。這是一個語詞的演變,當我們把它譯為『自戀』,雖然這語詞的翻譯並沒有引發我們的爭議,當我們使用『自戀』這詞語來談論心理世界時,雖然我們常說『戀愛』是愛的過程裡的某個階段,但何以不是被以『自愛』的翻譯呢?或者我們會覺得『自愛』是愛嗎?這是從我們的語詞『愛』的定義而問出的疑惑。」(引自本書:〈關於翻譯:以『精神分析』來了解psycho-analysis是可能的嗎?〉)
一如精神分析取向實作的過程,當我們知道了伊底帕斯情結或自戀的理論後,雖然仍只能先從目前此時此地談起,但是我們仍然無時無刻盼望著,哪一天能夠走到「伊底帕斯情結」啊。這可不是開玩笑,也不是只以比昂的「沒有欲望與沒有記憶」來搪塞,依我的解讀,比昂會提出來這個立場,並不是大家都做到了,而是大家都做不到,因此需要立這個文字碑,讓來來往往者能夠看到它。
那麼我是如何理解「破壞本能」和「破壞的自戀」?它們到底是什麼呢?破壞是針對什麼而說的?一般說法裡有大破大立,但有某種破壞一直被當作是問題時,是因為缺乏後續的大立?是從誰的角度來說的呢?是誰在破壞誰呢?
這和臨床工作有什麼關聯呢?它是我們需要的概念嗎?「破壞」和「破壞的自戀」,在臨床現象上的差異是什麼?何種情況會讓我們覺得「破壞的自戀」在展現呢?我們是依著哪些跡象做成這種判斷?我們如何區分跟自戀無關的破壞?或自戀是無所不在的,如同佛洛伊德所說的「原初自戀」,那麼當自戀遍及生活的所有細節,我們談論「自戀」這語詞還有什麼意義嗎?
我引用的這三篇參考文章(見後記),首先是臨床的負向反應和自戀有關,不過佛洛伊德原本是以這種反應是死亡本能,但是當說那是自戀時,就有了自戀和死亡本能的關連。這種自戀的現象是有破壞力,因此被當作是「破壞的自戀」,也就是,什麼情況下我們會說某種破壞是破壞本能在運作,而不是一般的破壞?是指重複性高,影響生活層面大,而且總是讓人覺得多說也無用的感受?「我也沒辦法」的強烈感受,是佛洛伊德說的負面治療效應裡的死亡本能?
不過,還是得回到一個很基本的實作課題,什麼情況會讓我們需要把「本能」這個如此難以捉摸,甚至不可能被五官察覺的語詞,做為我們要談論某些臨床現象的說詞呢?當我們搬出本能的語詞時是慎重的嗎?或者更像是展現我們做為治療師,是多麼無能為力的感覺?
因此「本能」,尤其是破壞的本能被搬出來,上演一場注定的悲劇?或者只是跑跑龍套,做為我們趨近更深沈挫折的串場?我們就是需要這個術語做為平台,不然我們根本就只能無言的嘆息,嘆著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的氣?或者所謂破壞本能的平台上,就是圍繞著各路來的嘆息聲,路過者也可以輕易就感受到的無奈,一如我們常是在和個案會談不久,就會想著,這個人怎麼這麼自戀?
或者覺得這個人怎麼充滿著死亡的氣息?只有不斷地破壞,無止盡的破壞,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被問,何以他們仍能活到此時,自己走進診療室裡?無論他們是想要什麼,或者不知想要什麼,但就是覺得想來說話,想來知道有另一個會聽他說話的人,就算他多麼強烈地想要把對方搞壞掉,但是能來診療室並且維持著這種相信,「可以把對方搞壞」,這種相信是什麼力量呢?
如果有人笑說,難道精神分析就只是搞性,搞自戀,搞本能,再加上伊底帕斯情結,然後就搞定一切了?也許我們會如佛洛伊德自嘆著,精神分析總是惹毛了人們,只因為他的論點是第三種對於人類自戀的衝擊,然後這樣就解釋了精神分析的命運了嗎?我們做為精神分析取向者的志氣是什麼呢?畢竟,佛洛伊德所描述的,人類有史以來對於人的自戀的三大衝擊案件,除了他的論點是第三案之外,前兩案件是天文學家伽利略和演化學家達爾文的挑釁。
當伽利略說太陽才是中心,地球只是圍著太陽打轉的星球,這可是嚴重的冒犯了地球是中心的主流論點。這差點讓伽利略被架上絞台。至於達爾文對於人的自戀的冒犯,是在漫長的人類史裡,人不是一直是人,而是可能由其它物種演化而來。伽俐略的假說後來發展成天文學,達爾文的演化論至今仍佔據著物種變化的主流論述。
也就是,現代人覺得伽利略和達爾文說對了重要現象呢。那麼,佛洛伊德的論點會走向伽利略和達爾文的命運嗎?那是誰的責任呢?佛洛伊德舉了這三個重大案件,難道只為了說明自己也有很偉大的發明和發現,或也有意圖覺得自己論點的命運,至少也能步上俐伽略和達爾文的後塵?
畢竟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三個案件後,人並沒有被這三大案件所摧毀,人還是活著,活下來,繼續生存著是證明了什麼呢?就算是有對於自戀衝擊的大案件,仍是不足以完全摧毀人類,人們還是活著和活下來,繼續展現人原本有的自戀,是否對於人類整體來說,這些重大案件的揭示,並不足以毀滅人類,但是就個體來說,這種對於自戀的衝擊,是否會有不同的故事呢?
這涉及了精神分析只談個體嗎?群體呢?佛洛伊德曾談群體心理學,以及比昂的自戀和社會(群體)戀,雖然目前流行的說法「做自己」,幾乎是不能任意被撼動和質疑的說法,但做自己是什麼意思呢?和我們談論的自戀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兩者間的地圖是同一國度,或是海中的兩個孤島?如果以大海來比喻,無論是多麼遙遠的孤島,兩者之間總是有相連的所在,這個所在是群體嗎?一如相同社會,同一個家庭裡,個人也是如此模式?
那麼,精神分析的個體主義,需要談論多少深層海底相連的海床呢?畢竟除了南北極浮冰,沒有孤島是如浮冰般漂浮的。
就算有了前述三大案例衝擊人的自戀,但是結果並沒有將自戀沖走,因此這三大案件不是洪水需要讓人另再造方舟來求生,而是在人生的茫茫大海依然自戀來求生。讓自戀就地成為一艘方舟?如果是這樣子,在洪水消退後,回頭來說自戀是眾多人生問題來源,這是恩將仇報嗎?這種比喻有重大的漏洞嗎?這對於我們了解自戀是幫忙,還是幫倒忙?
「自戀」會肯束手就擒嗎?或者說,自戀的力量就足以造就了一個孤島,社會群體裡的人際孤島,不只是漂浮的方舟,而是如海中孤島,自然有了自己的生態環境的發展。
因此還是勞煩了精神分析者,如克萊因(M. Klein)、寇哈特(Kohut)、葛林(A. Green)、溫尼科特等出面,想來相救,他們是搭著各自打造的方舟,活著自己的故事和命運?或者他們是各自的孤島,我們是搭著方舟的人,在孤島間流浪採集地方誌裡感人的故事和理念,再以我們自己的方言,來翻譯這些故事和理念?也許這些故事和理念,如同比昂描述臨床實作過程裡,浮現的「被選擇的事實」(selected facts)所打造成的島嶼?他們是各自圍繞著自戀的人性島嶼,在相同屬性的島嶼上,描述著自戀的周遭景緻?或他們描繪的風格和周邊風景不同的島嶼,只是湊巧取個相同的王國名稱?
而我們只能以自已的方言,翻譯採集到的故事和理念,甚至這不是大家想像中的,社會裡共通主流語言的翻譯。這是免不了的過程,至於實質在心中發揮功能的是,每個人以自身習得並累積的方言來了解這些情況。這種說法也許更貼切,更真實,也就是說,我們除了以被中譯出來的文字,來了解和想像外,還有其它我們自身特有的母語和興趣,以及風格所累積起來的複雜方言體系。
這不是一般說的,發出聲音的台語、客語和原住民語等而已,而是在人生過程裡,以這些為基礎再捲進來攪在一起的每個人自己的方言,是最後決定著我們所採集到孤島上的故事和理念的意義。故事也很重要,是每個人不同經驗帶來的情感因子隱藏的所在。例如,接受不同國度的訓練、不同督導等因子的影響,這些影響比能夠想得到的還要更深刻,因為那些涉及情感的交流。
如果這樣子,那怎麼辦呢?不同的特性和強調,卻有著相同的「自戀」的國名,這會發生什麼事呢?是否如同我的經驗裡,例如,我的布農族朋友和他的阿公及阿爸有相同的名字,但是朋友的媽媽叫著三個不同人的名字時,回應的人並不會答錯,是她每次都叫對人名,或是三個人都聽得出那聲音是呼喚他,這隱含著口氣情感和場合,或者是隱含著不同比重的尊敬和愛意?
好吧,我們在臨床實作的過程裡,浮現要稱呼某些場景是「自戀」時,我們是叫著公公、先生或兒子呢?或根本就是相互陌生的三個人,只是硬被我們湊合在一起?它們之間合得來嗎?它們說著相同的方言嗎?是否湊巧地,只有「自戀」這兩個字的發音是相同的,但是各有自己的家族史,不同的命運在等待著它們,有些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有」關係。
另外,是否溫尼科特描繪「假我」時,就意味著他是書寫著「自戀」的哀亡史?這可能是接續佛洛伊德所列舉的,對於人的自戀的三種打擊之外的第四種?「自戀」如何容忍為了活著和活下去,而需要有偽裝,這對自戀是最大的打擊?這種打擊猶如死亡才能忍受,是否這種死亡的結果,讓假我的發展史就是自戀的哀亡史?這也是造就了死亡本能的兄弟,或者這種死亡本能就是自戀的本尊,自戀只是它的化身?
從精神分析史的發展來看,當我們談「自戀」的好或壞,創造或破壞時,就像是自戀本身具有天使和惡魔的可能性。加上分裂機制的運轉,使得當「自戀」是天使時,就失去了惡魔;當「自戀」只偏重惡魔時,天使就消失了。是否這種原始的分裂機制(splitting)的作用,加上「自戀」的雙重特質,使得偏重一方時,就失去另一方。而這是最原始的失落、悲傷和抑鬱的起點,比佛洛伊德後來在《哀悼與憂鬱》裡,所提到的完整客體,例如父母親的死亡,所帶來的失落和憂鬱的論點還要更原始?
值得疑問的是,何以目前當某些讓人不愉快的態度和舉動,會讓我們命名那是「自戀」呢?這些都是如此活生生出現在互動過程裡,不過就臨床經驗來說,這常是當事者不自覺的現象,或者這裡所說的「不自覺」還不夠貼切和精準,而要說這些都是「自戀」在衰亡的過程裡,所遺留下來的梗或骨頭,硬梆梆的,如同刺那般,在人生的互動場域裡,我們說它是老梗,老是重複出現相同如刺般的硬梗,但它卻是最嬰兒的哭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