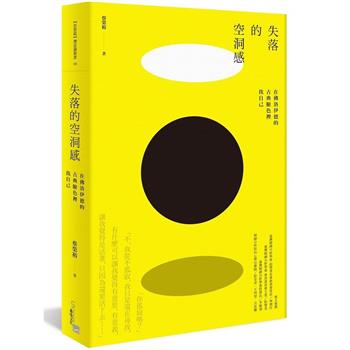【內文試閱一】
佛洛伊德的菜單說,預示了失落的空虛和空洞感
人是以焦慮和不安,來填滿空虛和空洞感嗎?這句話是否和臨床經驗貼近?具有代表性嗎?或只是某些案例的個別現象?從臨床經驗來看,潛在的脈絡裡,是隱含著自戀、邊緣型和帶有憤怒的抑鬱。
當佛洛伊德以拿菜單給肚子餓的人為例,來說明「詮釋」的侷限時,他所說的肚子餓的比喻,是空洞和空虛的延伸,也就是,佛洛伊德這個比喻裡,早就無意中說出自己的意向,是否他自覺想要表達的比喻裡,隱含著不自覺的未來方向?他花一生的功夫在說明,以精神官能症和詮釋為主的主要理論場域,那麼,從現在來看,他是否誤走了一生呢?
我倒不認為。他從臨床的實作出發,是得先如此,我們要走向生命更早期的經驗,總是得再穿過眼前的種種迷障。做為臨床家要穿越這些障礙或阻抗,自然得多方設想其中到底隱含著什麼內容?這些迷障,包括各式症狀如歇斯底里和焦慮等,可以說是「以焦慮和不安來填滿空虛和空洞感」,我覺得主張這句話很重要,這種說法不但不是忽略佛洛伊德的成就,而是我們得穿過佛洛伊德一輩子所描繪的場域,才有機會再往深處走。
精神分析取向的實作裡,必然可以觀察得到「退行反應」,所謂「退行」,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是指個案由於安全感的逐步建立,而更自然卻不自覺地呈現生命早年的某些經驗,包括創傷和修補的經驗總合。
如果只是看向空虛和空洞,而缺乏了解精神官能症狀群如何兼做戰士和使者,出來和當事者的人生糾纏,我們是很難往深處走。如果只是一心一意要避開這些症狀,就有些像是以催眠術避開阻抗的方式,以為這樣子就可以走到內心深處,但是就臨床經驗來說,以「建議」等技藝的施作,例如想以正向想法來取代負向想法,這些被避開的內容很快就會再包圍闖入者,讓正向想法變得孤掌難鳴。
這是佛洛伊德形容「移情」如戰場的緣由吧!對精神分析取向來說,不是避開它,也不是未經思索就直接迎戰,而是以我們的觀察、想像和猜測,顯微鏡般去描繪那些內容,和建構出它們是透過什麼機制發揮作用。
實作裡,無法如單方向直線般的因果關係,來處理臨床的複雜性,這是日常實務重複在告訴我們的經驗。不必然是治療師愈有經驗,就愈能帶著個案走得快,這是治療師的錯覺,畢竟,個案為了活著並活下去,所形成的種種防衛,就算被命名為「假我」,仍是很真實的存在,甚至在某些時候,如果現實上只能他一人獨自面對時,這些仍是很重要的活著和活下去的技能,而不能以過於理想化的壓迫,讓未準備好的戰士就上戰場。雖然什麼叫做「準備好」,仍有不同程度的看法,但不得不思索這個命題,否則會像溫尼科特所形容的,如同填鴨子般的強制,他的用詞是impingement。
回顧佛洛伊德一生的著作是相當深且廣,不過如果說他是偏重在本能、防衛機制、夢、性學理論和歇斯底里的焦點,不致於是太大的誤解。他在1914年提出《論自戀:引言》,是要打開另一扇眼界的窗了,這領域的探索和描繪,對佛洛伊德來說,可能受制於他原先提過的,精神病患者缺乏移情,因此無法被分析的影響,而沒有太深究。但是這篇文章對他來說,是要調整觀點的起步,不過,畢竟只是起步。
佛洛伊德要說明的自戀領域,並不是目前廣被使用的精神醫學DSM診斷條例的內容而已,而是要探索更廣大的原始心智的所在。可以廣義的說是「精神病」的領域,卻又不等於精神醫學診斷條例裡的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比昂後來表示,一般人格裡都有精神病和非精神病的部分,是在遠方遙遙呼應著佛洛伊德當年的想法。
另外,佛洛伊德對邊緣型的描繪也是相對的少,直到晚年,1938年《在防衛過程裡自我的分裂機制》,描述了目前常見的邊緣型個案常運用的心理機制,非黑即白,全好全壞等,令個案和其他人受苦的情感二分反應。邊緣型被預設是介於精神病和精神官能症之間的領域,不過就臨床現象來看,這種說法是過於明確的分野,因為就發展過程來說,這些生命早期的分裂機制作用,是出現在所有人的經驗裡。若以發展學的角度來說,是一直存在的,但診斷學上需要人為的橫切點來分類,也就是,邊緣型不必然是介於中間,而是穿透式的存在於人性或心智裡。這仍是待觀察和描繪的重要領域,克萊因學派有不少貢獻,不過仍是廣大待探索的地圖。至於臨床常見的,那些不屬於DSM診斷的重度憂鬱症,雖可以歸類在精神官能型憂鬱症的範疇,但從心理治療診療室的經驗來說,是可以在個案的身上發現,因為失落經驗而帶來不同程度的抑鬱,尤其從空洞式的空虛如浮塵的狀態,到充滿了憤怒的抑鬱,都是診療室裡常見的情況。雖然個案常是以焦慮、恐慌、不安、歇斯底里等精神官能症的型式來求診,但是只要開始心理治療,就會逐漸浮現,他們在虛空裡掙扎著,要活著和活下去。佛洛伊德曾在《哀悼與憂鬱》,以及另一篇以附錄的短文出現在《克制、症狀與焦慮》,談論失落所帶來人的空洞、空虛和失去了自己的感覺。
不過,他也說,這塊領域是他和精神分析還缺乏了解的地帶。
【內文試閱二】
失落的空洞感:在佛洛伊德的古典臉色裡找自己
《緣起十五想》
緣起一
當佛洛伊德表示,有時候分析師的詮釋,是如同給飢餓的人一份菜單時,他可能不自覺地呈現了,他在歇斯底里等精神官能症的豐富症狀和論述裡,有一份飢餓如失落、空洞的主題,這是他所忽視的,但是他使用的菜單比喻裡,卻洩露了他的認識。因為對他來說,處理歇斯底里和性倒錯等課題時,飢餓、失落和空洞並不是他當年深究的視野。但他卻如此精準地說出了菜單的比喻,好像洩露了天機,不自覺地預示了未來的焦點。在目前診療室裡常見的課題,「你孤寂嗎?」「不,我從不孤寂,我只是還在尋找,有什麼可以讓我覺得有意思、有意義,讓我覺得是活著,只因為還要活下去.......」
緣起二
有一片荒涼,人無言以對,以不可思議的模樣跑出來嚇人,既陌生又熟悉。
佛洛伊德在父親過世後,心情頗受影響,可以說因此開啟了佛洛伊德一段,被歷史學家稱為「自我分析」(self-analysis)的時期。這段時間,自我分析的成果之一是《夢的解析》的出版,書中大量使用自己的夢做為材料,開花成了世紀之書的風格。這是父親過世後的失落,所造就出來的成果,雖然佛洛伊德受自己身心症的影響,加上當代對於歇斯底里症、恐懼症和強迫症等的關注,讓佛洛伊德的焦點也在這些精神官能症上。不過相對的,在《哀悼與憂鬱》(1917),以及在《克制、症狀與焦慮》(1926)的第十一部分的附錄三裡,就明顯反映著佛洛伊德的其它心思,除了在精神官能症的處理和推論,對於失落以及相關的抑鬱是較少著墨,以及對於嚴重的憂鬱裡,潛在的自戀特質和分裂機制的影響,並未做出明顯意義的深究。
如何在現有知識的基礎上,再往前推想,以焦慮為基底的精神分析理論,站在它的肩膀上,望著客體失落所引發的憂鬱,而且是發生在伊底帕斯情結之前的失落。
緣起三
疑問:從佛洛伊德時代專注的歇斯底里、強迫症和恐懼等,隨著時間的演變,是否它們變少了?尤其是歇斯底里症,甚至「歇斯底里」這字眼變成某種負面觀點,被當作是責怪某些人的反應,這是怎麼回事呢?加上後來有人說,已經從歇斯底里的年代變成邊緣型的年代,這句話也許反映著某些臨床現實,但這是什麼意思?加上近來又變成憂鬱的年代,又是什麼意思呢?是症狀消失不見了,或只是相同問題卻以不同樣貌隨意出現呢?如果我們說,上述可能都是相同問題的起源,這是指什麼呢?或者從焦慮和歇斯底里,到邊緣型以及憂鬱成為話題,除了政治、經濟、社會學和藥物經濟的現象,以心理學來說這是什麼意思呢?精神分析的古典理論,對於這些外顯現象的變遷能夠有什麼觀點嗎?古典的理論就是過時了的想法嗎?尤其是2016年英國在政治體制裡設置「孤獨大臣」,這讓「憂鬱」的課題更聚焦在特定的孤獨上,精神分析如果從佛洛伊德的古典理論出發,能回應時代變遷裡的某些觀點嗎?或者精神分析的論點,已是亙古不變的真理了?畢竟,我們是先有個案,再有技術和理論,這是我以此刻最顯明被談論且臨床常見的現象做為出發的基礎。我的假設:外在現象上,反映著從歇斯底里走到目前被著重的憂鬱,不是這走向一定對,卻反映著一些心理動力的變遷,以及視野焦點的變化。古典理論是有豐富的資源,可以順手拈來回應這個命題,雖然不是馬上就有明確且完整的答案。畢竟,人性是多元和複雜的,因此本書除了介紹佛洛伊德的古典理論外,也希望讓讀者知道,這些古典理論仍是有能力來回應,症狀隨著時代變遷所隱含的各種意義。但有必要讓新意和古典相互流動,意味著古典理論不是只適合放在博物館裡供人參觀紀念而已,它們仍是觀看和解讀當代心理學現象的重要基礎和資源。也反應著精神分析視野的演變,歇斯底里、邊緣型或自戀型,以及當代的憂鬱(尤其孤寂更是焦點),不然英國不會設置「孤獨大臣」處理相關事務。我想的是,如何在現有的基礎,包括自體心理學的視野,思索精神分析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在理論和技術上,理解和回應這些外在變遷......
緣起四
「佛洛伊德發明精神分析的過程,同時也是探索、發現自己的歷程。一方面他緊密地與猶太家人聯繫,保持著規律的生活休閒:採菇、林間漫遊,甚至有著終身的牌友,另一方面則與當時的醫界名人共事,野心勃勃地要揚名立萬。同僚的冷漠、身心症的困擾、父親死亡的失落感等等,都將他禁錮在中年的存在危機、世紀末的維也納。精神分析的創立,可以說是救了自己。」這是楊明敏於2018吾境思塾,佛洛伊德系列課程II《佛洛伊德最困難的病人,從自己開始——性、夢與幻想》的文宣說帖。
我的想法:佛洛伊德在父親死亡後的失落感,是他自我分析的重要動力之一,也是《夢的解析》的重要起點。但是在他的理論裡,是著重外顯的身心症的潛在心理動機,相對地較少著墨於失落感。本課程是從佛洛伊德所缺乏的角度,來解讀佛洛伊德的文章......緣起五
知識與「分析的態度」,如果分析的態度是指三思,那麼要想什麼呢?我要以這些說明,做為我重讀古典理論的一個向度,但這只是回到佛洛伊德的一種方式。回到佛洛伊德前,先回到目前的診療室經驗,以焦慮和不安,以及它們和性學的關連是臨床可見的。在理論的視野下,焦慮是重要焦點,倒是目前臨床上個案的主述,有不少是以憂鬱為主,不是要忽略其中所隱含的焦慮,只是在精神分析的理論視野下,憂鬱相對是被忽略的現象。這種忽略是因為古典理論發展的時代因緣,相對的,憂鬱是在佛洛伊德的晚期才被著重。
憂鬱做為一種臨床症狀,只是後來才出現嗎?不必然吧,很大的可能性是憂鬱和焦慮都是共時存在的,而焦慮做為焦點,衍生出來的技藝主軸是對矛盾和移情加以詮釋。而憂鬱如同佛洛伊德於《哀悼與憂鬱》裡所形容的,重要客體失落後,在自我上遺留下來的陰影或空洞,幾乎大部分個案都會呈現的,只是量的強度有所不同。但這在臨床上也許不是由詮釋做為主導技術,畢竟這像是缺席、缺乏或空洞,是某種要被填飽或者被了解的技術。在蔡榮裕的書《不是拿走油燈就沒事了》裡,對於溫尼科特、葛林和冠哈特的討論裡曾嘗試觸及這個課題......
緣起六
從目前的診療室經驗來說,其實在佛洛伊德的案例報告裡,也可見由於失落而帶來的現象,抑鬱只是為了活著,而不斷的掙扎和不安,以及潛在的性學因子的作用,刺激著人如何活著的方式。因此我想進一步推論,焦慮和憂鬱是共同存在,各以不同的量在不同時候存在,甚至是相互依存的存在。如果佛洛伊德的原初場景和陽具欽羡,是有臨床的有效性,仍可以解釋我們所見的臨床現象時,它們不只是焦慮,而更是失落,而且是伊底帕斯情結之前「部分客體」的失落。
以下將會進一步闡述這些論點,我暫時提出的模式是,失落呈現的空洞是主要場域,而嬰孩在這種註定存在的空洞或陰影裡,做為舞台或家的感受,並在這個基礎上為了活著,而展開如麥克巴林(Michael Balint)所說的,原誤區和創造區般的自戀所發動的創造。這些創造能使用的材料就是自己的身體,這讓性學的發展如何被運用?是否性倒錯或戀物,有了活動展演人生的舞台?緣起七
在精神分析至今有限的焦點下,如果我們說嬰孩從母體出來、斷奶、原初場景、陽具欽羡和伊底帕斯情結種種挫折失落後,留下陰影和空洞,人要如何在這種處境裡,想辦法讓自己持續活著,仍能維持著對於未來的錯覺?這需要什麼必要的防衛機制呢?以及後來的人生裡,何以有著超高的理想,卻變成「殘酷的失敗者」,如同佛洛伊德所說的處於「潛意識的悲慘」?如何能在分析治療過程裡,走到「意識上的不快樂」呢?
文明趕走黑暗後,黑暗去了哪裡呢?這才是主要追蹤的焦點,如果以目前的知識來說,黑暗推演出焦慮、憂鬱、邊緣和自戀......
緣起八
回到歷史的脈絡,佛洛伊德的論述是從焦慮和失憶等精神官能症著手,並做為觀察的重點,進而建構出潛在的性學主題,雖然性學的說法至今仍帶來不少爭議。但是從診療室的治療經驗來說,他的性學、焦慮以及伊底帕斯情結的觀點,仍是臨床上有效的論點。所謂有效,並不是指告訴個案某些觀點,個案因此有了洞識,然後就跟著改善的意思,而是能夠以這些概念,做為了解和想像,個案在外顯的症狀和問題裡,仍有潛在的心理學值得思索。
不過,隨著佛洛伊德在診療室經驗的累積,他的視野和觀點也不斷地修改和增補,包括了重要的論點,例如《論自戀》,將對個案內在世界的視野,從精神官能症推向接近精神病層次的心理學假設,我認為,還有很重要的文章《哀悼和憂鬱》也有這個功能。
至於在《論自戀》和《哀悼與憂鬱》裡的客體觀點,本能層次的需要客體,和經由客體而獲得滿足是本能存在的目的,但是隨著年紀的變化,從客體獲得滿足的方式,也衍生了佛洛伊德所說的性倒錯的論點。如果將這裡所指出的,客體的選擇和運用,例如,如果後來選擇腳,做為性感刺激興奮的最重要客體,或者本能的滿足,不是用來滿足自戀的性活動,而最大的自戀可能是讓自己得以傳承下去,這些都是廣義的性倒錯的方式。從讓自己得以活著,並且活下去的角度來說,除了對過去的失落外,對於未來預期的失落,心理學的足跡可以走得多深呢?緣起九
「原初場景」的失落:這是人對於自己是怎麼來的想像之一,除了是送子鳥帶來的,還可能是來自嬰孩的「不知道」,不知道每天餵他的人,和另一個人在床上做出來的事是什麼意思?或者他們一直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是個人終生的性秘密?如果這是真的,就意味著每天餵他的人,不是完全屬於他,或者不是他的一部分,這是自己和他人分野的開始嗎?
「陽具欽羡」的失落:人一直在尋找某個「部分客體」,相對於在《哀悼與憂鬱》裡談論的,重要的完整客體,如父母的失去所帶來的,在自我上留下的陰影或空洞。臨床上可見某些個案一直在不同客體之間流轉,例如,初見面某人就覺得對方是自己要追尋的人,但是很快的就發現對方不是他們要的人。或者他們喜歡的對象,總是讓他們覺得無法依靠,是會很快再失去的人,因此他們反而選擇,自己不是那麼喜歡的人,做為在一起的對象。
佛洛伊德的菜單說,預示了失落的空虛和空洞感
人是以焦慮和不安,來填滿空虛和空洞感嗎?這句話是否和臨床經驗貼近?具有代表性嗎?或只是某些案例的個別現象?從臨床經驗來看,潛在的脈絡裡,是隱含著自戀、邊緣型和帶有憤怒的抑鬱。
當佛洛伊德以拿菜單給肚子餓的人為例,來說明「詮釋」的侷限時,他所說的肚子餓的比喻,是空洞和空虛的延伸,也就是,佛洛伊德這個比喻裡,早就無意中說出自己的意向,是否他自覺想要表達的比喻裡,隱含著不自覺的未來方向?他花一生的功夫在說明,以精神官能症和詮釋為主的主要理論場域,那麼,從現在來看,他是否誤走了一生呢?
我倒不認為。他從臨床的實作出發,是得先如此,我們要走向生命更早期的經驗,總是得再穿過眼前的種種迷障。做為臨床家要穿越這些障礙或阻抗,自然得多方設想其中到底隱含著什麼內容?這些迷障,包括各式症狀如歇斯底里和焦慮等,可以說是「以焦慮和不安來填滿空虛和空洞感」,我覺得主張這句話很重要,這種說法不但不是忽略佛洛伊德的成就,而是我們得穿過佛洛伊德一輩子所描繪的場域,才有機會再往深處走。
精神分析取向的實作裡,必然可以觀察得到「退行反應」,所謂「退行」,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是指個案由於安全感的逐步建立,而更自然卻不自覺地呈現生命早年的某些經驗,包括創傷和修補的經驗總合。
如果只是看向空虛和空洞,而缺乏了解精神官能症狀群如何兼做戰士和使者,出來和當事者的人生糾纏,我們是很難往深處走。如果只是一心一意要避開這些症狀,就有些像是以催眠術避開阻抗的方式,以為這樣子就可以走到內心深處,但是就臨床經驗來說,以「建議」等技藝的施作,例如想以正向想法來取代負向想法,這些被避開的內容很快就會再包圍闖入者,讓正向想法變得孤掌難鳴。
這是佛洛伊德形容「移情」如戰場的緣由吧!對精神分析取向來說,不是避開它,也不是未經思索就直接迎戰,而是以我們的觀察、想像和猜測,顯微鏡般去描繪那些內容,和建構出它們是透過什麼機制發揮作用。
實作裡,無法如單方向直線般的因果關係,來處理臨床的複雜性,這是日常實務重複在告訴我們的經驗。不必然是治療師愈有經驗,就愈能帶著個案走得快,這是治療師的錯覺,畢竟,個案為了活著並活下去,所形成的種種防衛,就算被命名為「假我」,仍是很真實的存在,甚至在某些時候,如果現實上只能他一人獨自面對時,這些仍是很重要的活著和活下去的技能,而不能以過於理想化的壓迫,讓未準備好的戰士就上戰場。雖然什麼叫做「準備好」,仍有不同程度的看法,但不得不思索這個命題,否則會像溫尼科特所形容的,如同填鴨子般的強制,他的用詞是impingement。
回顧佛洛伊德一生的著作是相當深且廣,不過如果說他是偏重在本能、防衛機制、夢、性學理論和歇斯底里的焦點,不致於是太大的誤解。他在1914年提出《論自戀:引言》,是要打開另一扇眼界的窗了,這領域的探索和描繪,對佛洛伊德來說,可能受制於他原先提過的,精神病患者缺乏移情,因此無法被分析的影響,而沒有太深究。但是這篇文章對他來說,是要調整觀點的起步,不過,畢竟只是起步。
佛洛伊德要說明的自戀領域,並不是目前廣被使用的精神醫學DSM診斷條例的內容而已,而是要探索更廣大的原始心智的所在。可以廣義的說是「精神病」的領域,卻又不等於精神醫學診斷條例裡的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比昂後來表示,一般人格裡都有精神病和非精神病的部分,是在遠方遙遙呼應著佛洛伊德當年的想法。
另外,佛洛伊德對邊緣型的描繪也是相對的少,直到晚年,1938年《在防衛過程裡自我的分裂機制》,描述了目前常見的邊緣型個案常運用的心理機制,非黑即白,全好全壞等,令個案和其他人受苦的情感二分反應。邊緣型被預設是介於精神病和精神官能症之間的領域,不過就臨床現象來看,這種說法是過於明確的分野,因為就發展過程來說,這些生命早期的分裂機制作用,是出現在所有人的經驗裡。若以發展學的角度來說,是一直存在的,但診斷學上需要人為的橫切點來分類,也就是,邊緣型不必然是介於中間,而是穿透式的存在於人性或心智裡。這仍是待觀察和描繪的重要領域,克萊因學派有不少貢獻,不過仍是廣大待探索的地圖。至於臨床常見的,那些不屬於DSM診斷的重度憂鬱症,雖可以歸類在精神官能型憂鬱症的範疇,但從心理治療診療室的經驗來說,是可以在個案的身上發現,因為失落經驗而帶來不同程度的抑鬱,尤其從空洞式的空虛如浮塵的狀態,到充滿了憤怒的抑鬱,都是診療室裡常見的情況。雖然個案常是以焦慮、恐慌、不安、歇斯底里等精神官能症的型式來求診,但是只要開始心理治療,就會逐漸浮現,他們在虛空裡掙扎著,要活著和活下去。佛洛伊德曾在《哀悼與憂鬱》,以及另一篇以附錄的短文出現在《克制、症狀與焦慮》,談論失落所帶來人的空洞、空虛和失去了自己的感覺。
不過,他也說,這塊領域是他和精神分析還缺乏了解的地帶。
【內文試閱二】
失落的空洞感:在佛洛伊德的古典臉色裡找自己
《緣起十五想》
緣起一
當佛洛伊德表示,有時候分析師的詮釋,是如同給飢餓的人一份菜單時,他可能不自覺地呈現了,他在歇斯底里等精神官能症的豐富症狀和論述裡,有一份飢餓如失落、空洞的主題,這是他所忽視的,但是他使用的菜單比喻裡,卻洩露了他的認識。因為對他來說,處理歇斯底里和性倒錯等課題時,飢餓、失落和空洞並不是他當年深究的視野。但他卻如此精準地說出了菜單的比喻,好像洩露了天機,不自覺地預示了未來的焦點。在目前診療室裡常見的課題,「你孤寂嗎?」「不,我從不孤寂,我只是還在尋找,有什麼可以讓我覺得有意思、有意義,讓我覺得是活著,只因為還要活下去.......」
緣起二
有一片荒涼,人無言以對,以不可思議的模樣跑出來嚇人,既陌生又熟悉。
佛洛伊德在父親過世後,心情頗受影響,可以說因此開啟了佛洛伊德一段,被歷史學家稱為「自我分析」(self-analysis)的時期。這段時間,自我分析的成果之一是《夢的解析》的出版,書中大量使用自己的夢做為材料,開花成了世紀之書的風格。這是父親過世後的失落,所造就出來的成果,雖然佛洛伊德受自己身心症的影響,加上當代對於歇斯底里症、恐懼症和強迫症等的關注,讓佛洛伊德的焦點也在這些精神官能症上。不過相對的,在《哀悼與憂鬱》(1917),以及在《克制、症狀與焦慮》(1926)的第十一部分的附錄三裡,就明顯反映著佛洛伊德的其它心思,除了在精神官能症的處理和推論,對於失落以及相關的抑鬱是較少著墨,以及對於嚴重的憂鬱裡,潛在的自戀特質和分裂機制的影響,並未做出明顯意義的深究。
如何在現有知識的基礎上,再往前推想,以焦慮為基底的精神分析理論,站在它的肩膀上,望著客體失落所引發的憂鬱,而且是發生在伊底帕斯情結之前的失落。
緣起三
疑問:從佛洛伊德時代專注的歇斯底里、強迫症和恐懼等,隨著時間的演變,是否它們變少了?尤其是歇斯底里症,甚至「歇斯底里」這字眼變成某種負面觀點,被當作是責怪某些人的反應,這是怎麼回事呢?加上後來有人說,已經從歇斯底里的年代變成邊緣型的年代,這句話也許反映著某些臨床現實,但這是什麼意思?加上近來又變成憂鬱的年代,又是什麼意思呢?是症狀消失不見了,或只是相同問題卻以不同樣貌隨意出現呢?如果我們說,上述可能都是相同問題的起源,這是指什麼呢?或者從焦慮和歇斯底里,到邊緣型以及憂鬱成為話題,除了政治、經濟、社會學和藥物經濟的現象,以心理學來說這是什麼意思呢?精神分析的古典理論,對於這些外顯現象的變遷能夠有什麼觀點嗎?古典的理論就是過時了的想法嗎?尤其是2016年英國在政治體制裡設置「孤獨大臣」,這讓「憂鬱」的課題更聚焦在特定的孤獨上,精神分析如果從佛洛伊德的古典理論出發,能回應時代變遷裡的某些觀點嗎?或者精神分析的論點,已是亙古不變的真理了?畢竟,我們是先有個案,再有技術和理論,這是我以此刻最顯明被談論且臨床常見的現象做為出發的基礎。我的假設:外在現象上,反映著從歇斯底里走到目前被著重的憂鬱,不是這走向一定對,卻反映著一些心理動力的變遷,以及視野焦點的變化。古典理論是有豐富的資源,可以順手拈來回應這個命題,雖然不是馬上就有明確且完整的答案。畢竟,人性是多元和複雜的,因此本書除了介紹佛洛伊德的古典理論外,也希望讓讀者知道,這些古典理論仍是有能力來回應,症狀隨著時代變遷所隱含的各種意義。但有必要讓新意和古典相互流動,意味著古典理論不是只適合放在博物館裡供人參觀紀念而已,它們仍是觀看和解讀當代心理學現象的重要基礎和資源。也反應著精神分析視野的演變,歇斯底里、邊緣型或自戀型,以及當代的憂鬱(尤其孤寂更是焦點),不然英國不會設置「孤獨大臣」處理相關事務。我想的是,如何在現有的基礎,包括自體心理學的視野,思索精神分析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在理論和技術上,理解和回應這些外在變遷......
緣起四
「佛洛伊德發明精神分析的過程,同時也是探索、發現自己的歷程。一方面他緊密地與猶太家人聯繫,保持著規律的生活休閒:採菇、林間漫遊,甚至有著終身的牌友,另一方面則與當時的醫界名人共事,野心勃勃地要揚名立萬。同僚的冷漠、身心症的困擾、父親死亡的失落感等等,都將他禁錮在中年的存在危機、世紀末的維也納。精神分析的創立,可以說是救了自己。」這是楊明敏於2018吾境思塾,佛洛伊德系列課程II《佛洛伊德最困難的病人,從自己開始——性、夢與幻想》的文宣說帖。
我的想法:佛洛伊德在父親死亡後的失落感,是他自我分析的重要動力之一,也是《夢的解析》的重要起點。但是在他的理論裡,是著重外顯的身心症的潛在心理動機,相對地較少著墨於失落感。本課程是從佛洛伊德所缺乏的角度,來解讀佛洛伊德的文章......緣起五
知識與「分析的態度」,如果分析的態度是指三思,那麼要想什麼呢?我要以這些說明,做為我重讀古典理論的一個向度,但這只是回到佛洛伊德的一種方式。回到佛洛伊德前,先回到目前的診療室經驗,以焦慮和不安,以及它們和性學的關連是臨床可見的。在理論的視野下,焦慮是重要焦點,倒是目前臨床上個案的主述,有不少是以憂鬱為主,不是要忽略其中所隱含的焦慮,只是在精神分析的理論視野下,憂鬱相對是被忽略的現象。這種忽略是因為古典理論發展的時代因緣,相對的,憂鬱是在佛洛伊德的晚期才被著重。
憂鬱做為一種臨床症狀,只是後來才出現嗎?不必然吧,很大的可能性是憂鬱和焦慮都是共時存在的,而焦慮做為焦點,衍生出來的技藝主軸是對矛盾和移情加以詮釋。而憂鬱如同佛洛伊德於《哀悼與憂鬱》裡所形容的,重要客體失落後,在自我上遺留下來的陰影或空洞,幾乎大部分個案都會呈現的,只是量的強度有所不同。但這在臨床上也許不是由詮釋做為主導技術,畢竟這像是缺席、缺乏或空洞,是某種要被填飽或者被了解的技術。在蔡榮裕的書《不是拿走油燈就沒事了》裡,對於溫尼科特、葛林和冠哈特的討論裡曾嘗試觸及這個課題......
緣起六
從目前的診療室經驗來說,其實在佛洛伊德的案例報告裡,也可見由於失落而帶來的現象,抑鬱只是為了活著,而不斷的掙扎和不安,以及潛在的性學因子的作用,刺激著人如何活著的方式。因此我想進一步推論,焦慮和憂鬱是共同存在,各以不同的量在不同時候存在,甚至是相互依存的存在。如果佛洛伊德的原初場景和陽具欽羡,是有臨床的有效性,仍可以解釋我們所見的臨床現象時,它們不只是焦慮,而更是失落,而且是伊底帕斯情結之前「部分客體」的失落。
以下將會進一步闡述這些論點,我暫時提出的模式是,失落呈現的空洞是主要場域,而嬰孩在這種註定存在的空洞或陰影裡,做為舞台或家的感受,並在這個基礎上為了活著,而展開如麥克巴林(Michael Balint)所說的,原誤區和創造區般的自戀所發動的創造。這些創造能使用的材料就是自己的身體,這讓性學的發展如何被運用?是否性倒錯或戀物,有了活動展演人生的舞台?緣起七
在精神分析至今有限的焦點下,如果我們說嬰孩從母體出來、斷奶、原初場景、陽具欽羡和伊底帕斯情結種種挫折失落後,留下陰影和空洞,人要如何在這種處境裡,想辦法讓自己持續活著,仍能維持著對於未來的錯覺?這需要什麼必要的防衛機制呢?以及後來的人生裡,何以有著超高的理想,卻變成「殘酷的失敗者」,如同佛洛伊德所說的處於「潛意識的悲慘」?如何能在分析治療過程裡,走到「意識上的不快樂」呢?
文明趕走黑暗後,黑暗去了哪裡呢?這才是主要追蹤的焦點,如果以目前的知識來說,黑暗推演出焦慮、憂鬱、邊緣和自戀......
緣起八
回到歷史的脈絡,佛洛伊德的論述是從焦慮和失憶等精神官能症著手,並做為觀察的重點,進而建構出潛在的性學主題,雖然性學的說法至今仍帶來不少爭議。但是從診療室的治療經驗來說,他的性學、焦慮以及伊底帕斯情結的觀點,仍是臨床上有效的論點。所謂有效,並不是指告訴個案某些觀點,個案因此有了洞識,然後就跟著改善的意思,而是能夠以這些概念,做為了解和想像,個案在外顯的症狀和問題裡,仍有潛在的心理學值得思索。
不過,隨著佛洛伊德在診療室經驗的累積,他的視野和觀點也不斷地修改和增補,包括了重要的論點,例如《論自戀》,將對個案內在世界的視野,從精神官能症推向接近精神病層次的心理學假設,我認為,還有很重要的文章《哀悼和憂鬱》也有這個功能。
至於在《論自戀》和《哀悼與憂鬱》裡的客體觀點,本能層次的需要客體,和經由客體而獲得滿足是本能存在的目的,但是隨著年紀的變化,從客體獲得滿足的方式,也衍生了佛洛伊德所說的性倒錯的論點。如果將這裡所指出的,客體的選擇和運用,例如,如果後來選擇腳,做為性感刺激興奮的最重要客體,或者本能的滿足,不是用來滿足自戀的性活動,而最大的自戀可能是讓自己得以傳承下去,這些都是廣義的性倒錯的方式。從讓自己得以活著,並且活下去的角度來說,除了對過去的失落外,對於未來預期的失落,心理學的足跡可以走得多深呢?緣起九
「原初場景」的失落:這是人對於自己是怎麼來的想像之一,除了是送子鳥帶來的,還可能是來自嬰孩的「不知道」,不知道每天餵他的人,和另一個人在床上做出來的事是什麼意思?或者他們一直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是個人終生的性秘密?如果這是真的,就意味著每天餵他的人,不是完全屬於他,或者不是他的一部分,這是自己和他人分野的開始嗎?
「陽具欽羡」的失落:人一直在尋找某個「部分客體」,相對於在《哀悼與憂鬱》裡談論的,重要的完整客體,如父母的失去所帶來的,在自我上留下的陰影或空洞。臨床上可見某些個案一直在不同客體之間流轉,例如,初見面某人就覺得對方是自己要追尋的人,但是很快的就發現對方不是他們要的人。或者他們喜歡的對象,總是讓他們覺得無法依靠,是會很快再失去的人,因此他們反而選擇,自己不是那麼喜歡的人,做為在一起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