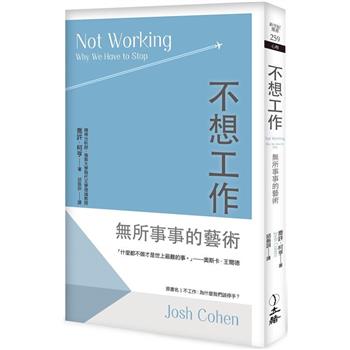第1章 過勞的人
「人們每分每秒都在工作」:安迪.沃荷
安迪.沃荷(Andy Warhol)最令人坐立難安的一幅畫作,我們這輩子都沒機會見到了。一九四九年,這個初出茅廬的商業藝術家才剛抵達曼哈頓,在畫布上畫了一系列大型畫作,但後來全都丟棄或銷毀了。其中一幅以原本刊載在《生活》(Life)週刊雜誌上的〈血腥星期六〉(Bloody Saturday)這張駭人相片為底本的畫作,畫的是一九三七年日軍轟炸上海時,一個小嬰孩孤伶伶地坐在上海南站殘垣斷壁間的模樣。
那個小嬰兒上身打直坐在月台邊緣,皮膚焦黑,衣衫破爛,雙眼盯著殘破的景象,張開嘴巴發出絕望的哭嚎。照沃荷傳記作者維克多.波克利斯(Victor Bockris)所說:「這幅畫非常恐怖,卻又出奇美觀。」這幅畫是以沃荷後來著稱的「墨跡畫法和粉彩」繪製而成。
這幅畫預示了他一九六二到六四年間知名的「死亡與災難」系列作,但是仍有一處驚人的差異:在「死亡與災難」系列作的畫面中可以看到電椅和各種交通事故,但是畫面中的人不是詭異地消失,就是散成融入背景殘骸的難辨屍塊,而這幅《上海小孩》卻是直接在我們眼前呈現出了鮮明而難解的痛苦創傷。
我有一名諮商多年的年輕男性個案,他童年時逃離了殘酷無比的內戰,後來輾轉來到倫敦。有一天,他帶著輕傷前來諮商,因為前一天下午騎單車時出了場差點送命的意外:他被一輛急駛的白色廂型車撞飛,但更嚇人的是他整個人趴在路上時,身旁的車子仍然一輛輛飛馳而過。「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個赤裸裸的嬰兒坐在馬路中間尖聲大哭。」他這樣說。
波克利斯給了我們一個提示,說不定當安迪.沃荷在察覺到一幅畫無意中竟成了他的自畫像,揭露出他內心最陰暗、最脆弱的角落時,就會毀了那幅畫。他當時的商業作品開鑿出了戰後消費文化中的深層感性,猶如一首滿是鮮花、小天使與蝴蝶的田園詩,映照出內心嚮往的童年。而那幅用色「出奇美觀」的《上海小孩》說不定就是小天使的對立面,是柔和的理想表面揮之不去卻又不明所以的黑暗創傷。
我們生命中的每個階段都會受到生命初期完全依賴大人生活的經驗制約,那些大人的看重或忽視、喜愛或厭惡,我們都只能照單全收。套句弗洛依德的術語,我們生來就受無助制約。
這份原初的無助經驗會深深烙印在我們心靈和肉體生活中,但是會對心靈和肉體有多大影響,還得看我們後來的人生經驗以及我們如何處理這份原初經驗的方式。身心所受到的各種創傷——戰爭、貧窮、忽視、意外、疾病等——都可能重新激發這層深埋的弱點與傾向。
那名摔車的個案在四歲的某個半夜醒來,結果發現媽媽不在家裡,只剩下孤單無力的自己去抵抗外頭的危險——不管那是真的還是想像出來的危險。他回想當時,或者也可能是想像當時他在一片漆黑中,一邊摸著牆,一邊放聲大哭,感覺自己就好像只用指尖吊掛在深淵邊上。他想,他比較害怕有什麼莫名的怪物跑出來,還是更害怕連一頭怪物也沒出現?(我不禁自問,還是更怕這兩種情況其實是同一回事呢?)那幅畫裡赤身露體、尖聲大哭的無助嬰兒就活生生顯現在這名棄兒的恐慌中,後來當這名年輕人倒臥在馬路上,看著車子一輛輛開過身邊那道陰影就又捲土重來了。
安迪.沃荷從小體弱多病,命運多舛,少有機會能夠擺脫嬰孩時期的無助恐懼。他兩歲時眼睛腫起來,母親拿了硼酸液幫他清洗;四歲時一隻手臂骨折卻沒發現,從此始終彎曲著;六歲時得了猩紅熱;到了八歲,則是(他每兩年一次劫難中最麻煩的)聖特維斯舞蹈症開始間斷發作。
舞蹈症這種病是由於中樞神經系統失調,導致患者無法控制肢體,會斷斷續續不斷瘋狂擺動四肢。這種不受控的感覺會讓小孩嚇到,以為自己發瘋了。安迪.沃荷的甩動症狀引起學校裡惡霸的注意,害他對上學充滿恐懼,連日常生活的肢體協調都不知如何是好,成天以淚洗面。他的童年生活因而成了他身體與情感疆界上一段永難癒合的傷口。
醫生囑咐要躺床一個月,持續觀察,所以安迪的母親茱莉亞就將安迪的床從臥室搬到了餐廳,就在廚房旁邊,好讓她能每小時檢查他的狀況,說不定就是這時開啟了他成年後不論搬幾次家還是與母親同住(當然愈來愈不用就近照看)的緊密關係。
這名小病人在床上有母親為他拿來的無數紙娃娃、漫畫書和雜誌可看可玩,他會剪下其中各種樣式重新拼貼。安迪.沃荷在他的《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 From A to B and Back Again)中描述場景時,不知是有意或無意地形塑出一種氛圍,就像他的迷你「工廠」:「我在夏天裡會成天聽著收音機,和我的查理麥卡錫娃娃躺在床上,整張床和枕頭下到處都是還沒剪下來的紙娃娃。」「工廠」就是安迪那間頗負盛名的工作室,他在那個收音機成天放著音樂的工作室裡創作出無數夾雜了性、毒品和狂熱情緒的瘋狂作品,而這張小時候的病床和他後來的「工廠」都帶著同一個核心矛盾:這張孩童病床和成年後的「工廠」都既是瘋狂創作的地點,也是無力退縮的床褥,既是恆動不歇的洪爐,也是停手止步的囚牢。
過了三年,安迪家多了另一張病床,躺著的是安迪沉默可靠的父親安德烈。若說茱莉亞象徵了撫慰和幽閉恐懼之間有多麼密切,那安德烈就代表了肉體上和情感上疏離的源頭。一九三九年,他離開了西維吉尼亞州惠靈市的礦區回到家裡,這是他最後一次離家打零工。他和其他一群礦工都喝了受污染的飲水,只能送回家,渾身黃疸地躺在床上。
這名彪形大漢就這樣在家裡待了三年,病情卻是日趨沉重。一九四二年,他終於撒手人寰,而且依照傳統,停靈在家三天。這個停屍家中的儀式對安迪而言顯然太過震撼,他跑回去躲在自己床下,怎樣都不肯看父親遺體一眼。後來他只能住在阿姨家中,直到父親移靈下葬才回去。
那場喪禮大概也是安迪參加過的唯一一場——就連三十年後他母親的喪禮,他也沒出席,還是同樣深怕面對死亡。波克利斯寫道:「他對死亡的恐懼大概使他堅決避免任何與死亡有關的事。」
安迪一方面面對的是茱莉亞的過度親密,戳穿了他身體與情感隱私的防護膜,另一方面則是與安德烈之間永難靠近的距離——通常是空間上彼此相隔,情感上也始終不親,最後則是天人永別。安迪.沃荷後來的人生與他的作品就一直受他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遊走懸宕所制約。無論是身體上或情感上的接觸,永遠都是太過或不足,不是過多就是太少。說不定,困擾了他一輩子的疑病症——這是布萊恩.迪倫(Brian Dillon)在《徹寒香梅》(Tormented Hope)書中的診斷——可以理解為他覺得身體受侵犯和遭到拋棄的肉體創傷;他其實就是那個滿身是傷的赤裸嬰兒。
※
在安迪.沃荷「死亡與災難」系列中的那些電椅、車禍、自殺、種族暴動等從報紙上裁下來的照片,都有一種漠不關心的氣息,彷彿全是某一架無名相機所拍攝的一樣。沃荷將這些傷亡照片浸泡在工業用黃色、綠色、紅色、橘色顏料裡,漬洗出一種冷淡漠然。
這些圖片每每都讓我覺得一陣羞愧不安,就好像我被人當場抓到一副看熱鬧的人那種呆樣的感覺。當你開車經過車禍現場時,前頭車輛的速度,還有你的車速都會不自覺放慢下來。就在那幾秒鐘裡,扭曲的擋泥板、滿地的碎玻璃,甚至是整灘整片的血跡,全都沒了人的氣息,就好像你的眼睛變成了一具冷酷的記錄器一樣。
我在看「死亡與災難」系列作之前就有過這種知覺分離的經驗了。車禍現場看起來既是猛力衝撞、毀滅與痛苦的可怕殘跡,卻也是一堆可替代物件零碎四散的隨意分布。我同時會覺得自己既太沒人性但又太有人性,離那片恐怖太遠卻又太近。
沃荷雖然「堅決避免任何與死亡有關的事」,卻免不了對死亡有一種執迷。迪倫說,當沃荷疑病症發作,覺得自己的皮膚和內臟都一直遭受病菌侵襲時,他就會幻想躲進一個乾淨的身體裡,完全沒有這些過敏反應:「他害怕生病卻也同樣害怕藥物,所以會想像所謂健康的身體就是永遠都不會生病也不用吃藥,而且還認為健康的身體就是一副完全統一自足,純屬自身的肉體。」
就是這份均衡自足的幻想為尖叫的上海小孩塗上了柔和的粉彩,替那幅景象裹上了一層商業外皮的諷刺味道。空蕩蕩的電椅象徵了強力激烈的電擊以及隨後永陷寧靜的死亡。人工色彩的漬洗刷掉了這種過與不及的雙重恐怖。許多藝評家都說這系列作帶有政治意涵,但沃荷在電台上與克雷斯.歐登伯格(Claes Oldenburg)和羅伊.里希騰斯坦(Roy Lichtenstein)對談時卻始終堅稱他這些畫作都只是「冷漠的一種表現」。
過了十多年之後,沃荷在《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中對繪畫大發妙論,而那些顏色的整平效果則為此更加添了一股詭祕曲折的氣息:「要知道,我覺得每一幅畫都應該同樣尺寸、同樣顏色,這樣就可以彼此互換,而且不會有人覺得自己拿到了比較好或比較差的畫。」換個方式說,他對繪畫的理想是同時要消除畫作內容和觀眾的反應——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引發,只有藝術家與觀眾之間完全純粹的不溝通。
中性、冷漠、放空——這就是沃荷在抵抗內心不斷紛擾,求取平衡的辦法。他的人生和作品始終都在尋求一種平靜柔和的狀態,但一方面卻不停受到痛苦與震驚的脅迫,而另一方面則是來自空寂與死亡的威嚇。他的性生活一直在長期禁慾和猛烈爆發而且往往貪求無厭的激情之間來回擺盪,就像他後來與「工廠」的「超級巨星」也一再重複著從如膠似漆到相敬如「冰」的關係一樣。
沃荷的人生和作品看起來也有點像是不斷重複排演著我們最基本的人生困境:我們希望愛人,也希望被愛。這是一份會令人興起需求、刺激、渴望和好奇的願望。如果愛能帶來滿足、關懷和保護,那也同樣永遠能使我們面臨冷漠、忽視與殘酷的風險。沃荷顯然覺得這雙重羈絆苦不堪言,才會在肉慾歡愛和禁慾冷感之間擺盪不休。
沃荷最傑出的作品就是他個性中那份後天養成的空虛,也是他對這股拉力的解決之道。他一九六三年到過好萊塢,後來在一九八○年《普普主義》(POPism)這本六○年代回憶錄中寫道他夢想著他的人生要像好萊塢那樣純然空洞:「空空洞洞的好萊塢,就是我最想要的人生樣貌。滿滿的塑膠。白上加白。」
想要過白上加白的生活,就是要永遠消除情緒的波動,清除點綴生命的各種色彩。按照沃荷的好友兼傳記作家大衛.波登(David Bourdon)所述,沃荷一九六四年時最愛的電影是《機器人誕生》(The Creation of the Humanoids);片中講的是在末日浩劫後人力短缺的世界裡,靠著創造人形機器人來補足勞動力。而電影的「美好結局」就在於「男女主角發現原來他們自己也是機器人」。從人化成為機器就是安迪.沃荷想要追求的美好人生結局。格林尼的《過勞案例》裡那種「無欲無求」的麻木冷漠在沃荷身上反而愈來愈成了他的靈感來源。
但是要維持這種無欲無求的狀態對沃荷來說實在太難,就連修佛的鴨長明也發現自己深深執著在不執著這個願念上。沃荷一直想讓自己變得像機器人那樣中性冷淡,到頭來卻只發現自己的人欲異樣迸發,落得個徒勞無功。
沃荷的外顯人格就是想將「無欲之欲」化為自身本質的一種嘗試。因此冷漠就鑽進了他的目光、他的聲音、他的習性——成了他每天的模樣。弔詭的是,這人格卻也得靠他身邊各種過度的創意、情感、藥物、性愛刺激來滋養。一大群藝術家、變裝人、追星族和超級巨星在一九六○年代都住在「工廠」裡頭,而待在這不停冒著沸騰的愛恨糾葛、嫉妒渴望的一大鍋釜中央的,卻是那個無動於衷的機器人。
※
安迪.沃荷一九四○年代中葉在匹茲堡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學商業藝術,那裡的老師派瑞.戴維斯(Perry Davis)說青春期的安迪給人一種「十足無性生活的印象」。終其一生,他身邊的親朋好友都說過這樣的話。他的藝術家朋友露絲.克里曼(Ruth Kligman)說她記得沃荷曾經警告過她:「性佔去了太多時間。」!而「工廠」裡另一位舉足輕重的共同創辦人傑拉德.瑪蘭加(Gerard Malanga)也說:「他幾乎完全沒有性生活可言。」
沃荷的文章更加強了這種他對性事避之唯恐不及的印象。他在《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寫道:「在螢幕上與書頁間的性愛怎麼樣都比床上的刺激多了。」一將性事外化出來,變成悅目的藝術品而非感覺享受的樂事,那就變美了。性愛只屬於螢幕或書頁,這樣才能夠普遍化,而且散布給觀眾和讀者。性愛一變成「私事」,那就只是浪費時間;沃荷寫道:「專屬於個人的愛和性都糟透了。」愛一變成個人的事,就玷污了無名機器那種白上加白的理想。
這份看似對性愛的抗拒顯然並沒排除對他人性生活的無盡好奇——反而還增強了這份好奇心。瑪蘭加說,擁抱獨身主義「讓他能恣意操弄自己找來的那些豔麗出眾的俊男美女於股掌之上。」
沃荷雖然退出了性愛的交易場,卻一手掌握了自己和其他人的情愛生活。「你可以忠於某個地點或某個東西,就像你忠於某個人一樣。」他在《普普人生》裡這麼說。保持距離和物化因此不再僅是代表拒絕而已,反而成了一種連結的形式。
沃荷的物化傾向從他成年初期就相當明顯。科技產品——電話、錄音機、電視螢幕、照相機,還有筆和筆刷——提供了透過媒介而親近的方式,即使是在最親密的關係裡,也維持著一段冷酷的距離。大約在一九五一年左右,他獨自住在曼哈頓那時起,就養成了一輩子重度依賴電話的習慣。喬治.克勞勃(George Klauber)是沃荷在卡內基理工學院時的朋友,他也搬到了紐約,而且還帶沃荷進入了紐約的地下同志文化圈;他還記得沃荷有一次半夜兩點從自己床上打給他,要克勞勃把自己和新情人怎麼共度良宵給一五一十地說個清楚。
波克利斯說得好:「安迪害怕獨自入睡,卻又沒辦法跟任何人共枕同眠。」&抱著硬殼電話而非柔軟情人上床顯然是對症下藥。電話還只是性愛替代品的第一步——沃荷的窺淫癖形塑了他的性生活和藝術創作,他的性趣不是因情人撩動,是因別人的性生活而勃發。
照沃荷在《普普人生》中的說法,從一九五○年代末起,電視就開始取代了親密關係。但是直到一九六四年沃荷買了錄音機(他稱之為「我老婆」)之後,他才真正宣告拋棄一切感情生活。「買到錄音機之後,就真的結束了我可能會有的感情生活,但是我也樂見如此。再也不會有什麼麻煩了,因為麻煩的意思其實就是好錄音帶,一旦麻煩本身變成了好錄音帶,那就不再是麻煩了。」「麻煩」是屬於個別個人的;一將麻煩外化、重製,就成了非個人的事物,是能不帶情感來檢視的東西,而不是待人感受的體驗。
沃荷與他的錄音機之間的「婚姻」所產下最耀眼的成果就是他的「小說」《a》,這是在「工廠」裡來來去去的演員之間,連續好幾個小時漫無止盡而且常常不知所云的對話記錄,靠沃荷的「老婆」錄下來後轉抄成書。我們習於認為親密與冷漠這兩者彼此對反,但是讀過《a》就會覺得並非如此;能夠竊聽對話者之間不講形式、沒有目的的私人對話實在是太過詭異了。多到炸的細節、缺乏頭緒或敘述形式,還有對原汁原味、不加一丁點兒組織安排的堅持,這全都令讀者困惑不已、難以消受。因為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無生命的科技產品,那一大堆的字串話語教人摸不著頭腦;我們在這本書裡閱聽了不少東西,但幾乎沒有什麼能夠讓人理解和記住的。
沃荷的下一個記錄器材是一架寶萊克斯(Bolex)攝影機,而他對這機器也有同樣反應;他會把攝影機放在睡覺的人身前,或是一幢大樓前方,甚至是一個正在口交的男體上身(這是我們推測的)前面,屢屢讓人更在意「觀看」這個行為本身,而不去細想觀看的內容。隨便挑其中任何一支影片看個十幾分鐘之後,那份無聊的感覺就會將我從螢幕上的影像推到我腦袋裡那一堆接連不斷的聯想裡頭。正因沒什麼內容可看,使得我的注意力移轉到了「觀看」這件事上頭。
「把一切都攤平在同一個層次上看,」(這是沃荷在《普普人生》中的建議,而他大多數的藝術創作也隱約都強迫我們必須採取這種立場觀看。這讓我們能夠窺見一個將我們內心生活與外在世界的內容擺在同一平面,平等看待一切的世界會是什麼模樣。
但是說要待在這樣一個世界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他人生各個時刻中,慾望、暴怒、痛苦時不時總會從他那份故作中性的外貌下穿透出來,玷染了那份努力維持白上加白的表面。
(全文未完)
「人們每分每秒都在工作」:安迪.沃荷
安迪.沃荷(Andy Warhol)最令人坐立難安的一幅畫作,我們這輩子都沒機會見到了。一九四九年,這個初出茅廬的商業藝術家才剛抵達曼哈頓,在畫布上畫了一系列大型畫作,但後來全都丟棄或銷毀了。其中一幅以原本刊載在《生活》(Life)週刊雜誌上的〈血腥星期六〉(Bloody Saturday)這張駭人相片為底本的畫作,畫的是一九三七年日軍轟炸上海時,一個小嬰孩孤伶伶地坐在上海南站殘垣斷壁間的模樣。
那個小嬰兒上身打直坐在月台邊緣,皮膚焦黑,衣衫破爛,雙眼盯著殘破的景象,張開嘴巴發出絕望的哭嚎。照沃荷傳記作者維克多.波克利斯(Victor Bockris)所說:「這幅畫非常恐怖,卻又出奇美觀。」這幅畫是以沃荷後來著稱的「墨跡畫法和粉彩」繪製而成。
這幅畫預示了他一九六二到六四年間知名的「死亡與災難」系列作,但是仍有一處驚人的差異:在「死亡與災難」系列作的畫面中可以看到電椅和各種交通事故,但是畫面中的人不是詭異地消失,就是散成融入背景殘骸的難辨屍塊,而這幅《上海小孩》卻是直接在我們眼前呈現出了鮮明而難解的痛苦創傷。
我有一名諮商多年的年輕男性個案,他童年時逃離了殘酷無比的內戰,後來輾轉來到倫敦。有一天,他帶著輕傷前來諮商,因為前一天下午騎單車時出了場差點送命的意外:他被一輛急駛的白色廂型車撞飛,但更嚇人的是他整個人趴在路上時,身旁的車子仍然一輛輛飛馳而過。「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個赤裸裸的嬰兒坐在馬路中間尖聲大哭。」他這樣說。
波克利斯給了我們一個提示,說不定當安迪.沃荷在察覺到一幅畫無意中竟成了他的自畫像,揭露出他內心最陰暗、最脆弱的角落時,就會毀了那幅畫。他當時的商業作品開鑿出了戰後消費文化中的深層感性,猶如一首滿是鮮花、小天使與蝴蝶的田園詩,映照出內心嚮往的童年。而那幅用色「出奇美觀」的《上海小孩》說不定就是小天使的對立面,是柔和的理想表面揮之不去卻又不明所以的黑暗創傷。
我們生命中的每個階段都會受到生命初期完全依賴大人生活的經驗制約,那些大人的看重或忽視、喜愛或厭惡,我們都只能照單全收。套句弗洛依德的術語,我們生來就受無助制約。
這份原初的無助經驗會深深烙印在我們心靈和肉體生活中,但是會對心靈和肉體有多大影響,還得看我們後來的人生經驗以及我們如何處理這份原初經驗的方式。身心所受到的各種創傷——戰爭、貧窮、忽視、意外、疾病等——都可能重新激發這層深埋的弱點與傾向。
那名摔車的個案在四歲的某個半夜醒來,結果發現媽媽不在家裡,只剩下孤單無力的自己去抵抗外頭的危險——不管那是真的還是想像出來的危險。他回想當時,或者也可能是想像當時他在一片漆黑中,一邊摸著牆,一邊放聲大哭,感覺自己就好像只用指尖吊掛在深淵邊上。他想,他比較害怕有什麼莫名的怪物跑出來,還是更害怕連一頭怪物也沒出現?(我不禁自問,還是更怕這兩種情況其實是同一回事呢?)那幅畫裡赤身露體、尖聲大哭的無助嬰兒就活生生顯現在這名棄兒的恐慌中,後來當這名年輕人倒臥在馬路上,看著車子一輛輛開過身邊那道陰影就又捲土重來了。
安迪.沃荷從小體弱多病,命運多舛,少有機會能夠擺脫嬰孩時期的無助恐懼。他兩歲時眼睛腫起來,母親拿了硼酸液幫他清洗;四歲時一隻手臂骨折卻沒發現,從此始終彎曲著;六歲時得了猩紅熱;到了八歲,則是(他每兩年一次劫難中最麻煩的)聖特維斯舞蹈症開始間斷發作。
舞蹈症這種病是由於中樞神經系統失調,導致患者無法控制肢體,會斷斷續續不斷瘋狂擺動四肢。這種不受控的感覺會讓小孩嚇到,以為自己發瘋了。安迪.沃荷的甩動症狀引起學校裡惡霸的注意,害他對上學充滿恐懼,連日常生活的肢體協調都不知如何是好,成天以淚洗面。他的童年生活因而成了他身體與情感疆界上一段永難癒合的傷口。
醫生囑咐要躺床一個月,持續觀察,所以安迪的母親茱莉亞就將安迪的床從臥室搬到了餐廳,就在廚房旁邊,好讓她能每小時檢查他的狀況,說不定就是這時開啟了他成年後不論搬幾次家還是與母親同住(當然愈來愈不用就近照看)的緊密關係。
這名小病人在床上有母親為他拿來的無數紙娃娃、漫畫書和雜誌可看可玩,他會剪下其中各種樣式重新拼貼。安迪.沃荷在他的《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 From A to B and Back Again)中描述場景時,不知是有意或無意地形塑出一種氛圍,就像他的迷你「工廠」:「我在夏天裡會成天聽著收音機,和我的查理麥卡錫娃娃躺在床上,整張床和枕頭下到處都是還沒剪下來的紙娃娃。」「工廠」就是安迪那間頗負盛名的工作室,他在那個收音機成天放著音樂的工作室裡創作出無數夾雜了性、毒品和狂熱情緒的瘋狂作品,而這張小時候的病床和他後來的「工廠」都帶著同一個核心矛盾:這張孩童病床和成年後的「工廠」都既是瘋狂創作的地點,也是無力退縮的床褥,既是恆動不歇的洪爐,也是停手止步的囚牢。
過了三年,安迪家多了另一張病床,躺著的是安迪沉默可靠的父親安德烈。若說茱莉亞象徵了撫慰和幽閉恐懼之間有多麼密切,那安德烈就代表了肉體上和情感上疏離的源頭。一九三九年,他離開了西維吉尼亞州惠靈市的礦區回到家裡,這是他最後一次離家打零工。他和其他一群礦工都喝了受污染的飲水,只能送回家,渾身黃疸地躺在床上。
這名彪形大漢就這樣在家裡待了三年,病情卻是日趨沉重。一九四二年,他終於撒手人寰,而且依照傳統,停靈在家三天。這個停屍家中的儀式對安迪而言顯然太過震撼,他跑回去躲在自己床下,怎樣都不肯看父親遺體一眼。後來他只能住在阿姨家中,直到父親移靈下葬才回去。
那場喪禮大概也是安迪參加過的唯一一場——就連三十年後他母親的喪禮,他也沒出席,還是同樣深怕面對死亡。波克利斯寫道:「他對死亡的恐懼大概使他堅決避免任何與死亡有關的事。」
安迪一方面面對的是茱莉亞的過度親密,戳穿了他身體與情感隱私的防護膜,另一方面則是與安德烈之間永難靠近的距離——通常是空間上彼此相隔,情感上也始終不親,最後則是天人永別。安迪.沃荷後來的人生與他的作品就一直受他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遊走懸宕所制約。無論是身體上或情感上的接觸,永遠都是太過或不足,不是過多就是太少。說不定,困擾了他一輩子的疑病症——這是布萊恩.迪倫(Brian Dillon)在《徹寒香梅》(Tormented Hope)書中的診斷——可以理解為他覺得身體受侵犯和遭到拋棄的肉體創傷;他其實就是那個滿身是傷的赤裸嬰兒。
※
在安迪.沃荷「死亡與災難」系列中的那些電椅、車禍、自殺、種族暴動等從報紙上裁下來的照片,都有一種漠不關心的氣息,彷彿全是某一架無名相機所拍攝的一樣。沃荷將這些傷亡照片浸泡在工業用黃色、綠色、紅色、橘色顏料裡,漬洗出一種冷淡漠然。
這些圖片每每都讓我覺得一陣羞愧不安,就好像我被人當場抓到一副看熱鬧的人那種呆樣的感覺。當你開車經過車禍現場時,前頭車輛的速度,還有你的車速都會不自覺放慢下來。就在那幾秒鐘裡,扭曲的擋泥板、滿地的碎玻璃,甚至是整灘整片的血跡,全都沒了人的氣息,就好像你的眼睛變成了一具冷酷的記錄器一樣。
我在看「死亡與災難」系列作之前就有過這種知覺分離的經驗了。車禍現場看起來既是猛力衝撞、毀滅與痛苦的可怕殘跡,卻也是一堆可替代物件零碎四散的隨意分布。我同時會覺得自己既太沒人性但又太有人性,離那片恐怖太遠卻又太近。
沃荷雖然「堅決避免任何與死亡有關的事」,卻免不了對死亡有一種執迷。迪倫說,當沃荷疑病症發作,覺得自己的皮膚和內臟都一直遭受病菌侵襲時,他就會幻想躲進一個乾淨的身體裡,完全沒有這些過敏反應:「他害怕生病卻也同樣害怕藥物,所以會想像所謂健康的身體就是永遠都不會生病也不用吃藥,而且還認為健康的身體就是一副完全統一自足,純屬自身的肉體。」
就是這份均衡自足的幻想為尖叫的上海小孩塗上了柔和的粉彩,替那幅景象裹上了一層商業外皮的諷刺味道。空蕩蕩的電椅象徵了強力激烈的電擊以及隨後永陷寧靜的死亡。人工色彩的漬洗刷掉了這種過與不及的雙重恐怖。許多藝評家都說這系列作帶有政治意涵,但沃荷在電台上與克雷斯.歐登伯格(Claes Oldenburg)和羅伊.里希騰斯坦(Roy Lichtenstein)對談時卻始終堅稱他這些畫作都只是「冷漠的一種表現」。
過了十多年之後,沃荷在《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中對繪畫大發妙論,而那些顏色的整平效果則為此更加添了一股詭祕曲折的氣息:「要知道,我覺得每一幅畫都應該同樣尺寸、同樣顏色,這樣就可以彼此互換,而且不會有人覺得自己拿到了比較好或比較差的畫。」換個方式說,他對繪畫的理想是同時要消除畫作內容和觀眾的反應——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引發,只有藝術家與觀眾之間完全純粹的不溝通。
中性、冷漠、放空——這就是沃荷在抵抗內心不斷紛擾,求取平衡的辦法。他的人生和作品始終都在尋求一種平靜柔和的狀態,但一方面卻不停受到痛苦與震驚的脅迫,而另一方面則是來自空寂與死亡的威嚇。他的性生活一直在長期禁慾和猛烈爆發而且往往貪求無厭的激情之間來回擺盪,就像他後來與「工廠」的「超級巨星」也一再重複著從如膠似漆到相敬如「冰」的關係一樣。
沃荷的人生和作品看起來也有點像是不斷重複排演著我們最基本的人生困境:我們希望愛人,也希望被愛。這是一份會令人興起需求、刺激、渴望和好奇的願望。如果愛能帶來滿足、關懷和保護,那也同樣永遠能使我們面臨冷漠、忽視與殘酷的風險。沃荷顯然覺得這雙重羈絆苦不堪言,才會在肉慾歡愛和禁慾冷感之間擺盪不休。
沃荷最傑出的作品就是他個性中那份後天養成的空虛,也是他對這股拉力的解決之道。他一九六三年到過好萊塢,後來在一九八○年《普普主義》(POPism)這本六○年代回憶錄中寫道他夢想著他的人生要像好萊塢那樣純然空洞:「空空洞洞的好萊塢,就是我最想要的人生樣貌。滿滿的塑膠。白上加白。」
想要過白上加白的生活,就是要永遠消除情緒的波動,清除點綴生命的各種色彩。按照沃荷的好友兼傳記作家大衛.波登(David Bourdon)所述,沃荷一九六四年時最愛的電影是《機器人誕生》(The Creation of the Humanoids);片中講的是在末日浩劫後人力短缺的世界裡,靠著創造人形機器人來補足勞動力。而電影的「美好結局」就在於「男女主角發現原來他們自己也是機器人」。從人化成為機器就是安迪.沃荷想要追求的美好人生結局。格林尼的《過勞案例》裡那種「無欲無求」的麻木冷漠在沃荷身上反而愈來愈成了他的靈感來源。
但是要維持這種無欲無求的狀態對沃荷來說實在太難,就連修佛的鴨長明也發現自己深深執著在不執著這個願念上。沃荷一直想讓自己變得像機器人那樣中性冷淡,到頭來卻只發現自己的人欲異樣迸發,落得個徒勞無功。
沃荷的外顯人格就是想將「無欲之欲」化為自身本質的一種嘗試。因此冷漠就鑽進了他的目光、他的聲音、他的習性——成了他每天的模樣。弔詭的是,這人格卻也得靠他身邊各種過度的創意、情感、藥物、性愛刺激來滋養。一大群藝術家、變裝人、追星族和超級巨星在一九六○年代都住在「工廠」裡頭,而待在這不停冒著沸騰的愛恨糾葛、嫉妒渴望的一大鍋釜中央的,卻是那個無動於衷的機器人。
※
安迪.沃荷一九四○年代中葉在匹茲堡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學商業藝術,那裡的老師派瑞.戴維斯(Perry Davis)說青春期的安迪給人一種「十足無性生活的印象」。終其一生,他身邊的親朋好友都說過這樣的話。他的藝術家朋友露絲.克里曼(Ruth Kligman)說她記得沃荷曾經警告過她:「性佔去了太多時間。」!而「工廠」裡另一位舉足輕重的共同創辦人傑拉德.瑪蘭加(Gerard Malanga)也說:「他幾乎完全沒有性生活可言。」
沃荷的文章更加強了這種他對性事避之唯恐不及的印象。他在《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寫道:「在螢幕上與書頁間的性愛怎麼樣都比床上的刺激多了。」一將性事外化出來,變成悅目的藝術品而非感覺享受的樂事,那就變美了。性愛只屬於螢幕或書頁,這樣才能夠普遍化,而且散布給觀眾和讀者。性愛一變成「私事」,那就只是浪費時間;沃荷寫道:「專屬於個人的愛和性都糟透了。」愛一變成個人的事,就玷污了無名機器那種白上加白的理想。
這份看似對性愛的抗拒顯然並沒排除對他人性生活的無盡好奇——反而還增強了這份好奇心。瑪蘭加說,擁抱獨身主義「讓他能恣意操弄自己找來的那些豔麗出眾的俊男美女於股掌之上。」
沃荷雖然退出了性愛的交易場,卻一手掌握了自己和其他人的情愛生活。「你可以忠於某個地點或某個東西,就像你忠於某個人一樣。」他在《普普人生》裡這麼說。保持距離和物化因此不再僅是代表拒絕而已,反而成了一種連結的形式。
沃荷的物化傾向從他成年初期就相當明顯。科技產品——電話、錄音機、電視螢幕、照相機,還有筆和筆刷——提供了透過媒介而親近的方式,即使是在最親密的關係裡,也維持著一段冷酷的距離。大約在一九五一年左右,他獨自住在曼哈頓那時起,就養成了一輩子重度依賴電話的習慣。喬治.克勞勃(George Klauber)是沃荷在卡內基理工學院時的朋友,他也搬到了紐約,而且還帶沃荷進入了紐約的地下同志文化圈;他還記得沃荷有一次半夜兩點從自己床上打給他,要克勞勃把自己和新情人怎麼共度良宵給一五一十地說個清楚。
波克利斯說得好:「安迪害怕獨自入睡,卻又沒辦法跟任何人共枕同眠。」&抱著硬殼電話而非柔軟情人上床顯然是對症下藥。電話還只是性愛替代品的第一步——沃荷的窺淫癖形塑了他的性生活和藝術創作,他的性趣不是因情人撩動,是因別人的性生活而勃發。
照沃荷在《普普人生》中的說法,從一九五○年代末起,電視就開始取代了親密關係。但是直到一九六四年沃荷買了錄音機(他稱之為「我老婆」)之後,他才真正宣告拋棄一切感情生活。「買到錄音機之後,就真的結束了我可能會有的感情生活,但是我也樂見如此。再也不會有什麼麻煩了,因為麻煩的意思其實就是好錄音帶,一旦麻煩本身變成了好錄音帶,那就不再是麻煩了。」「麻煩」是屬於個別個人的;一將麻煩外化、重製,就成了非個人的事物,是能不帶情感來檢視的東西,而不是待人感受的體驗。
沃荷與他的錄音機之間的「婚姻」所產下最耀眼的成果就是他的「小說」《a》,這是在「工廠」裡來來去去的演員之間,連續好幾個小時漫無止盡而且常常不知所云的對話記錄,靠沃荷的「老婆」錄下來後轉抄成書。我們習於認為親密與冷漠這兩者彼此對反,但是讀過《a》就會覺得並非如此;能夠竊聽對話者之間不講形式、沒有目的的私人對話實在是太過詭異了。多到炸的細節、缺乏頭緒或敘述形式,還有對原汁原味、不加一丁點兒組織安排的堅持,這全都令讀者困惑不已、難以消受。因為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無生命的科技產品,那一大堆的字串話語教人摸不著頭腦;我們在這本書裡閱聽了不少東西,但幾乎沒有什麼能夠讓人理解和記住的。
沃荷的下一個記錄器材是一架寶萊克斯(Bolex)攝影機,而他對這機器也有同樣反應;他會把攝影機放在睡覺的人身前,或是一幢大樓前方,甚至是一個正在口交的男體上身(這是我們推測的)前面,屢屢讓人更在意「觀看」這個行為本身,而不去細想觀看的內容。隨便挑其中任何一支影片看個十幾分鐘之後,那份無聊的感覺就會將我從螢幕上的影像推到我腦袋裡那一堆接連不斷的聯想裡頭。正因沒什麼內容可看,使得我的注意力移轉到了「觀看」這件事上頭。
「把一切都攤平在同一個層次上看,」(這是沃荷在《普普人生》中的建議,而他大多數的藝術創作也隱約都強迫我們必須採取這種立場觀看。這讓我們能夠窺見一個將我們內心生活與外在世界的內容擺在同一平面,平等看待一切的世界會是什麼模樣。
但是說要待在這樣一個世界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他人生各個時刻中,慾望、暴怒、痛苦時不時總會從他那份故作中性的外貌下穿透出來,玷染了那份努力維持白上加白的表面。
(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