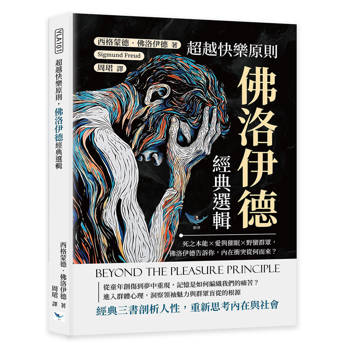第五章 死之本能
大腦皮層能感應刺激,卻不具備面向內部的抵禦興奮保護層,如此情況必定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傳送這些來自內部的興奮刺激,獲得越來越多的實質意義,而且這類傳送還經常會導致某些類似於創傷性精神官能症的實際障礙。這種內部的興奮,最主要的來源就是有機體的「本能」──產生於身體內部,並且被傳遞到心理結構的所有力量的代表。本能的問題同時也是心理學研究中最重要、最模糊不清的內容。
本能所產生的衝動,不屬於聚集性的神經過程,而屬於力爭得到釋放的自由活動神經過程。將來可能會發現,這個假設並不過於輕率。所有關於這些過程的知識中,最齊全的那一部分來自對夢境的研究。在研究夢時發現,無意識系統的運作過程,完全不同於前意識系統(或意識系統)的運作過程。在無意識系統中,貫注力可以很容易地被全部轉移、置換和濃縮。但如果把它用於前意識,則勢必不會收到任何有用的效果。白天的前意識記憶殘留已根據無意識系統的法則而被重新處理,這一點也是我們所熟悉的顯夢特徵展現。我把在無意識系統中發現的那類過程稱作「原發性」心理過程,以區別在正常清醒狀態下所獲得的「繼發性」過程。既然所有的本能衝動都把無意識系統作為衝擊的目標,那麼說它們都遵循原發性過程,就不算什麼新奇的想法了。
而且,人們很容易把原發性心理過程和布洛伊爾的自由活動貫注力畫上等號,把繼發性心理過程和在其聚集性或收緊性的貫注力中所發生的變化畫上等號。如果可以這樣畫等號的話,那麼把那些到達原發過程的本能興奮聚集起來,就將成為心理結構高層次的任務。一旦這種聚集失敗,就會產生類似於創傷性精神官能症的障礙;而且,只有成功完成這種聚集之後,快樂原則(及其衍生的現實原則)才有可能毫無阻礙地占據主導地位。在此之前,心理結構的另一任務,即控制或約束興奮程度,將作為它的首要大事。其實這個任務並未與快樂原則對立,但也不受快樂原則支配,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它。
前面已經指出,在幼兒早期的心智活動以及精神分析的治療過程中,表現出的各種強迫性重複,於相當程度上顯示出一種本能的特徵,並且當它們的活動與快樂原則對立時,就好像有種「魔幻的力量」在發揮作用。在研究兒童遊戲時發現,兒童之所以會重複那些不快樂的經歷,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處在主動地位,比起被動地體驗強烈感受,這使他們更能徹底地掌握它,好像每重複一遍都能掌握得更加扎實一樣。兒童並不能使快樂體驗經常性重複,他們竭盡所能固執地要求一模一樣的重複體驗。這種情況也會隨著時間消失,就好比一個笑話第二次被人聽到,它就幾乎不會再引人發笑了;一個劇本被第二次搬上舞臺,便不能帶給觀眾如同第一次上演時同樣強烈的感受。同理,我們絕對不可能說服剛剛津津有味地讀完一本書的成年人,立即將這本書重讀一遍,因為新奇往往是快樂的必要條件。但是,小孩子們卻會不厭其煩地纏著大人重複他曾教過他們或和他們一起玩過的遊戲,直到把大人逼得厭倦不堪才肯罷休。同樣地,如果向孩子講了一則有趣的故事,他就會一遍又一遍地聽這個故事,而不願去聽另一則新的故事。並且他還會嚴格要求講述者必須把故事講得一模一樣,甚至還會糾正講述過程中的任何變動──成人做這些改變實際上是想要讓小孩獲得新鮮感。所有這些都沒有與快樂原則相互矛盾。顯然,重新體驗相同事物本身,就是快樂的泉源。相反地,強迫正在接受精神分析的病人,在移情過程中重複自己童年經歷的事情,顯然一點都沒有顧及快樂原則。這個患者的行為舉止完全像個小孩,也就表明,他身上並沒有被壓抑之幼年經歷的記憶印記表現為聚集形式,而是──換一種形式來說──根本無法遵循那個繼發過程。並且,正是由於沒有聚集,這些被壓抑之幼年經歷的記憶印記,具有在夢中形成幻想的能力。當分析工作接近尾聲,試圖引導病患和醫生完全脫離時,同樣的強迫性重複現象也成為經常遇到的治療障礙。還可以這樣設想:當不熟悉精神分析的人們莫名地感到恐懼──害怕喚醒某種他們覺得最好是留在夢中的東西──他們害怕出現這種彷彿受某種「魔幻的力量」驅使的強迫性現象。
大腦皮層能感應刺激,卻不具備面向內部的抵禦興奮保護層,如此情況必定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傳送這些來自內部的興奮刺激,獲得越來越多的實質意義,而且這類傳送還經常會導致某些類似於創傷性精神官能症的實際障礙。這種內部的興奮,最主要的來源就是有機體的「本能」──產生於身體內部,並且被傳遞到心理結構的所有力量的代表。本能的問題同時也是心理學研究中最重要、最模糊不清的內容。
本能所產生的衝動,不屬於聚集性的神經過程,而屬於力爭得到釋放的自由活動神經過程。將來可能會發現,這個假設並不過於輕率。所有關於這些過程的知識中,最齊全的那一部分來自對夢境的研究。在研究夢時發現,無意識系統的運作過程,完全不同於前意識系統(或意識系統)的運作過程。在無意識系統中,貫注力可以很容易地被全部轉移、置換和濃縮。但如果把它用於前意識,則勢必不會收到任何有用的效果。白天的前意識記憶殘留已根據無意識系統的法則而被重新處理,這一點也是我們所熟悉的顯夢特徵展現。我把在無意識系統中發現的那類過程稱作「原發性」心理過程,以區別在正常清醒狀態下所獲得的「繼發性」過程。既然所有的本能衝動都把無意識系統作為衝擊的目標,那麼說它們都遵循原發性過程,就不算什麼新奇的想法了。
而且,人們很容易把原發性心理過程和布洛伊爾的自由活動貫注力畫上等號,把繼發性心理過程和在其聚集性或收緊性的貫注力中所發生的變化畫上等號。如果可以這樣畫等號的話,那麼把那些到達原發過程的本能興奮聚集起來,就將成為心理結構高層次的任務。一旦這種聚集失敗,就會產生類似於創傷性精神官能症的障礙;而且,只有成功完成這種聚集之後,快樂原則(及其衍生的現實原則)才有可能毫無阻礙地占據主導地位。在此之前,心理結構的另一任務,即控制或約束興奮程度,將作為它的首要大事。其實這個任務並未與快樂原則對立,但也不受快樂原則支配,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它。
前面已經指出,在幼兒早期的心智活動以及精神分析的治療過程中,表現出的各種強迫性重複,於相當程度上顯示出一種本能的特徵,並且當它們的活動與快樂原則對立時,就好像有種「魔幻的力量」在發揮作用。在研究兒童遊戲時發現,兒童之所以會重複那些不快樂的經歷,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處在主動地位,比起被動地體驗強烈感受,這使他們更能徹底地掌握它,好像每重複一遍都能掌握得更加扎實一樣。兒童並不能使快樂體驗經常性重複,他們竭盡所能固執地要求一模一樣的重複體驗。這種情況也會隨著時間消失,就好比一個笑話第二次被人聽到,它就幾乎不會再引人發笑了;一個劇本被第二次搬上舞臺,便不能帶給觀眾如同第一次上演時同樣強烈的感受。同理,我們絕對不可能說服剛剛津津有味地讀完一本書的成年人,立即將這本書重讀一遍,因為新奇往往是快樂的必要條件。但是,小孩子們卻會不厭其煩地纏著大人重複他曾教過他們或和他們一起玩過的遊戲,直到把大人逼得厭倦不堪才肯罷休。同樣地,如果向孩子講了一則有趣的故事,他就會一遍又一遍地聽這個故事,而不願去聽另一則新的故事。並且他還會嚴格要求講述者必須把故事講得一模一樣,甚至還會糾正講述過程中的任何變動──成人做這些改變實際上是想要讓小孩獲得新鮮感。所有這些都沒有與快樂原則相互矛盾。顯然,重新體驗相同事物本身,就是快樂的泉源。相反地,強迫正在接受精神分析的病人,在移情過程中重複自己童年經歷的事情,顯然一點都沒有顧及快樂原則。這個患者的行為舉止完全像個小孩,也就表明,他身上並沒有被壓抑之幼年經歷的記憶印記表現為聚集形式,而是──換一種形式來說──根本無法遵循那個繼發過程。並且,正是由於沒有聚集,這些被壓抑之幼年經歷的記憶印記,具有在夢中形成幻想的能力。當分析工作接近尾聲,試圖引導病患和醫生完全脫離時,同樣的強迫性重複現象也成為經常遇到的治療障礙。還可以這樣設想:當不熟悉精神分析的人們莫名地感到恐懼──害怕喚醒某種他們覺得最好是留在夢中的東西──他們害怕出現這種彷彿受某種「魔幻的力量」驅使的強迫性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