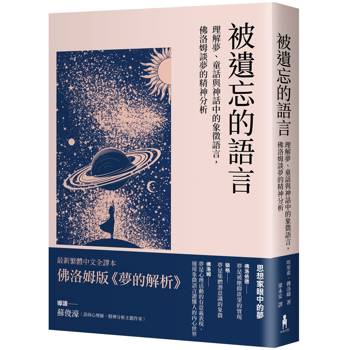第一章 導論
如果感到困惑的能力真的是智慧的開端,那麼這個事實對現代人的智慧來說,是一種悲哀的評價。無論我們的文學素養和普及教育有多少優點,我們都已失去了能感到困惑的天賦。如今,一切事物都被認為應該有人知道——即使我們自己不知道,也總有某位專家知道,因為「知道那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正是他的職責所在。事實上,感到困惑反而讓人尷尬,被視為智力不足的象徵。如今,即使是孩子也很少會感到驚訝,至少他們會盡量避免表現出來。隨著年齡增長,我們逐漸喪失感到驚訝的能力。掌握正確的答案似乎至關重要;相較之下,能否提出正確的問題則被認為微不足道。
這種態度或許正是為何生活中最令人困惑的現象之一:夢境,很少引發我們感到驚奇與提問的原因。我們每個人都會做夢,但我們並不了解自己的夢,卻表現得彷彿睡夢中的心智活動毫無異常。其實,這些活動與我們清醒時邏輯清楚、目標明確的思考相比,顯得相當奇特。
當我們清醒時,我們是主動、理性的存在,努力追求我們想要的事物,並準備好保護自己免受攻擊。我們一邊行動,一邊觀察。我們觀看外在的事物,雖然可能不是看到它們本來的樣子,但至少是以一種我們能加以使用和操縱的方式來觀看它們。但是,我們也相當缺乏想像力,除非是在孩提時期或是身為詩人,否則我們的想像力很少能超越那些來自實際經驗的故事和情節。我們很有效率,但有些乏味。我們將白天觀察到的領域稱為「現實」,並以我們的「現實主義」和操縱現實的聰明才智感到自豪。
當我們睡著時,我們會以另一種存在形式醒來。我們會做夢。我們編造出從未發生的故事,有時甚至會編造出現實中沒有任何先例的故事。我們有時是英雄,有時是惡棍;我們有時看到最美的風景並感到快樂;我們常常會被拋入極度恐怖的情景。但無論我們在夢中扮演什麼角色,我們都是創作者。做的是屬於我們的夢,由我們編造情節。
大多數的夢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它們不遵循那些在我們清醒時支配我們思考的邏輯法則。夢境中忽略了空間和時間的概念。我們會看見死去的人還活著,會身處現在卻目睹發生在許多年前的事。我們可以夢見兩件不可能同時發生的事同時發生。我們同樣不理會空間的法則。在夢中,可以瞬間移動到遙遠的地方,也可以輕而易舉地同時身處兩地、讓兩個人融合為一個人,或是讓一個人突然變成另一個人。事實上,我們是夢中世界的創造者,在這個世界裡,原本限制我們身體所有活動的時間和空間毫無力量可言。
我們的夢還有另一個奇怪之處:我們會夢見多年未曾想起的人與事,我們醒著的時候絕對不會想起他們。他們突然出現在夢裡,就像我們曾經多次想起的熟人一樣。在睡眠中,我們似乎能夠挖掘那龐大的經驗和記憶寶庫,但在白天清醒時,我們根本沒意識到自己擁有這些經驗與記憶。
然而,儘管有這些奇特的特質,當我們做夢時,夢境對我們來說卻是真實的,其真實程度不亞於我們醒著時所經歷的一切。夢中沒有「彷彿」這回事。夢是真實、當下的經驗,甚至會引發兩個問題:什麼是真實?我們如何知道夢境是不真實的,而醒著時經歷的一切才是真實的?一位中國詩人曾恰如其分地表達出這種感受:「我昨晚夢見自己變成一隻蝴蝶,如今我不知,我究竟是夢見變成蝴蝶的人,還是一隻夢見自己是人的蝴蝶。」
當我們醒來時,這一切令人興奮的生動體驗不僅會消失,還很難記得住。我們一回頭就將夢忘得一乾二凈,根本不記得曾經生活在另一個世界。有些夢在我們醒來的那一刻還依稀記得,但下一秒鐘就想不起來。我們有時會記得一些夢境,而這些正是當我們說「我做了一個夢」時所指的內容。就像有些友善或不友善的幽靈曾經來訪,到了破曉時分突然消失蹤影。我們幾乎記不起他們曾經來過,以及我們曾經全神貫注地與它們相處。
也許,比剛才說的那些都還要讓人困惑的,是我們在睡眠中創造的夢境,與人類最古老的創作——也就是「神話」——非常相似。
事實上,我們對神話並不太感到困惑。如果神話作為宗教的一部分而受到尊敬,我們就會給它們約定俗成的、膚淺的認可,將其視為令人尊崇之傳統的一部分。如果神話不具有這種傳統的權威,就會被視為在科學啟蒙之前,人類幼稚的思想表現。總之,無論被忽視、鄙視或尊重,神話都被認為屬於一個與我們自身思維完全不同的世界。然而,事實是,我們的許多夢境在風格和內容上都與神話相似。我們醒著時覺得這些神話奇特而疏離,卻有能力在睡著時創造出這些神話般的產物。
神話中,同樣會發生在受時空法則支配的世界裡不可能發生的戲劇性事件:英雄為拯救世界而離鄉背井,或者他因逃避自己的使命而落入大魚的腹中;英雄死而復生;神話中的鳥浴火重生後,變得更加美麗。當然,就像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夢一樣,不同的民族也創造出不同的神話。儘管有這些差異,所有神話和所有夢境都有一個共通之處:它們是以同一個語言「寫成」,而這個語言就是象徵語言(symbolic language)。
巴比倫人、印度人、埃及人、希伯來人、希臘人的神話,與阿散蒂人(Ashantis)或楚克人(Trukese)的神話,是用相同的語言書寫的。今天住在紐約或巴黎的人做的夢,與幾千年前生活在雅典或耶路撒冷的人所紀錄的夢,基本上是相同的。古代人與現代人描述夢境時所使用的語言,與人類文明肇始之時,那些創造神話的人所使用的語言相同。
象徵語言是一種以感官體驗與外在世界的事件,來表達內在體驗、感受和思想的語言。這種語言的邏輯不同於我們日常所使用的約定俗成的語言,其運作原則不是以時間與空間為主,而是以情感強度與意象聯想為核心。它是人類至今所發展出的,唯一一種共同語言,適用於所有化,並貫串古今。它擁有自己的語法和句法,一個人若想理解神話、童話和夢的意義,就必須理解象徵語言。
然而,現代人已經遺忘象徵語言——不是在睡著的時候,而是在清醒的時候。我們在清醒狀態中是否也應該理解象徵語言?對於生活在古代東、西方偉大文明的人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無庸置疑。對他們而言,神話和夢境是心靈最重要的表達方式之一,不懂得解讀它們則形同文盲。直到近幾百年的西方文化中,這種態度才發生改變。如今,神話被認為充其量只是科學興起之前人類心靈的天真虛構,是在人類尚未發現自然奧祕、尚未學會如何掌控自然力量之前所創造出來的產物。
在現代啟蒙運動的評價中,夢的地位更為不堪。夢被認為毫無意義,不值得成年人關注。成年人忙於製造機器之類的重要事務,自視為「現實主義者」,眼中只有可以被他們征服和操縱的事物。這些「現實主義者」對每種型號的汽車各有特殊的稱呼,但卻只知道用「愛」一個字來涵蓋各式各樣的情感體驗。
此外,如果我們所有的夢都是令人愉快的幻象,可以滿足我們內心的願望,那麼我們可能會對它們較為友善。然而,很多夢境只會帶給我們焦慮的心緒。它們通常是噩夢,會讓我們醒來時慶幸自己只是在做夢。其他的夢雖然不是噩夢,但可能由於其他原因而令人不安。它們與我們白天認定的自我形象格格不入。我們有時會夢見自己憎恨原以為喜歡的人,夢見我們喜愛原以為自己不感興趣的人。儘管我們相信自己一向謙遜。卻夢見自己懷有野心;當我們為自己的獨立而感到自豪時,卻夢見自己處於屈服和屈辱的境地。但比這一切事實更糟的是,我們不理解自己的夢,而醒著時的我們本來確信,只要用心思考便能理解一切。為了逃避這種證明「我們的理解力有局限性」的壓倒性證據,我們選擇指責夢境毫無意義。
在過去幾十年間,人對神話和夢的態度有深刻的轉變。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佛洛伊德研究的推動。他最初只是想幫助精神官能症患者了解他們患病的原因,但後來開始將夢視為一種普遍的人類現象進行研究,因為無論生病或是健康的人都一樣會做夢。他認為夢在本質上跟神話和童話沒有什麼不同,理解其中一種,就會理解其他兩種。人類學家的研究使人們重新關注神話。他們收集並研究神話,這個領域的先驅,例如巴霍芬(J. J. Bachofen),成功地為人類的史前史提供新的見解。
但神話和夢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並受到許多限制。其中之一是教條主義和僵化。這源於各個精神分析學派的主張,每一派都堅稱只有自己的詮釋才是對象徵語言的唯一正確理解。結果,我們忽視了象徵語言的多面性,並試圖將它強行塞入只有一種意義的框架之中。
另一個限制是,釋夢至今仍被認為,只有當精神科醫師用它來治療精神官能症患者時,才具正當性。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相信象徵語言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學習的一種外語。理解象徵語言能讓我們觸及神話這個最重要的智慧泉源,而且它也讓我們觸及自身人格的更深層次。事實上,它有助於我們理解一種人類特有的經驗層次,因為這個層次在內容與形式上都是全人類共通的。
《塔木德》說:「未經理解的夢就像一封未打開的信件。」確實,夢和神話都是我們與自己之間的重要溝通。如果我們不理解它們所使用的語言,就會錯過在我們沒有忙著操控外部世界的時候,自己所知道、也對自己說過的許多事情。
如果感到困惑的能力真的是智慧的開端,那麼這個事實對現代人的智慧來說,是一種悲哀的評價。無論我們的文學素養和普及教育有多少優點,我們都已失去了能感到困惑的天賦。如今,一切事物都被認為應該有人知道——即使我們自己不知道,也總有某位專家知道,因為「知道那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正是他的職責所在。事實上,感到困惑反而讓人尷尬,被視為智力不足的象徵。如今,即使是孩子也很少會感到驚訝,至少他們會盡量避免表現出來。隨著年齡增長,我們逐漸喪失感到驚訝的能力。掌握正確的答案似乎至關重要;相較之下,能否提出正確的問題則被認為微不足道。
這種態度或許正是為何生活中最令人困惑的現象之一:夢境,很少引發我們感到驚奇與提問的原因。我們每個人都會做夢,但我們並不了解自己的夢,卻表現得彷彿睡夢中的心智活動毫無異常。其實,這些活動與我們清醒時邏輯清楚、目標明確的思考相比,顯得相當奇特。
當我們清醒時,我們是主動、理性的存在,努力追求我們想要的事物,並準備好保護自己免受攻擊。我們一邊行動,一邊觀察。我們觀看外在的事物,雖然可能不是看到它們本來的樣子,但至少是以一種我們能加以使用和操縱的方式來觀看它們。但是,我們也相當缺乏想像力,除非是在孩提時期或是身為詩人,否則我們的想像力很少能超越那些來自實際經驗的故事和情節。我們很有效率,但有些乏味。我們將白天觀察到的領域稱為「現實」,並以我們的「現實主義」和操縱現實的聰明才智感到自豪。
當我們睡著時,我們會以另一種存在形式醒來。我們會做夢。我們編造出從未發生的故事,有時甚至會編造出現實中沒有任何先例的故事。我們有時是英雄,有時是惡棍;我們有時看到最美的風景並感到快樂;我們常常會被拋入極度恐怖的情景。但無論我們在夢中扮演什麼角色,我們都是創作者。做的是屬於我們的夢,由我們編造情節。
大多數的夢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它們不遵循那些在我們清醒時支配我們思考的邏輯法則。夢境中忽略了空間和時間的概念。我們會看見死去的人還活著,會身處現在卻目睹發生在許多年前的事。我們可以夢見兩件不可能同時發生的事同時發生。我們同樣不理會空間的法則。在夢中,可以瞬間移動到遙遠的地方,也可以輕而易舉地同時身處兩地、讓兩個人融合為一個人,或是讓一個人突然變成另一個人。事實上,我們是夢中世界的創造者,在這個世界裡,原本限制我們身體所有活動的時間和空間毫無力量可言。
我們的夢還有另一個奇怪之處:我們會夢見多年未曾想起的人與事,我們醒著的時候絕對不會想起他們。他們突然出現在夢裡,就像我們曾經多次想起的熟人一樣。在睡眠中,我們似乎能夠挖掘那龐大的經驗和記憶寶庫,但在白天清醒時,我們根本沒意識到自己擁有這些經驗與記憶。
然而,儘管有這些奇特的特質,當我們做夢時,夢境對我們來說卻是真實的,其真實程度不亞於我們醒著時所經歷的一切。夢中沒有「彷彿」這回事。夢是真實、當下的經驗,甚至會引發兩個問題:什麼是真實?我們如何知道夢境是不真實的,而醒著時經歷的一切才是真實的?一位中國詩人曾恰如其分地表達出這種感受:「我昨晚夢見自己變成一隻蝴蝶,如今我不知,我究竟是夢見變成蝴蝶的人,還是一隻夢見自己是人的蝴蝶。」
當我們醒來時,這一切令人興奮的生動體驗不僅會消失,還很難記得住。我們一回頭就將夢忘得一乾二凈,根本不記得曾經生活在另一個世界。有些夢在我們醒來的那一刻還依稀記得,但下一秒鐘就想不起來。我們有時會記得一些夢境,而這些正是當我們說「我做了一個夢」時所指的內容。就像有些友善或不友善的幽靈曾經來訪,到了破曉時分突然消失蹤影。我們幾乎記不起他們曾經來過,以及我們曾經全神貫注地與它們相處。
也許,比剛才說的那些都還要讓人困惑的,是我們在睡眠中創造的夢境,與人類最古老的創作——也就是「神話」——非常相似。
事實上,我們對神話並不太感到困惑。如果神話作為宗教的一部分而受到尊敬,我們就會給它們約定俗成的、膚淺的認可,將其視為令人尊崇之傳統的一部分。如果神話不具有這種傳統的權威,就會被視為在科學啟蒙之前,人類幼稚的思想表現。總之,無論被忽視、鄙視或尊重,神話都被認為屬於一個與我們自身思維完全不同的世界。然而,事實是,我們的許多夢境在風格和內容上都與神話相似。我們醒著時覺得這些神話奇特而疏離,卻有能力在睡著時創造出這些神話般的產物。
神話中,同樣會發生在受時空法則支配的世界裡不可能發生的戲劇性事件:英雄為拯救世界而離鄉背井,或者他因逃避自己的使命而落入大魚的腹中;英雄死而復生;神話中的鳥浴火重生後,變得更加美麗。當然,就像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夢一樣,不同的民族也創造出不同的神話。儘管有這些差異,所有神話和所有夢境都有一個共通之處:它們是以同一個語言「寫成」,而這個語言就是象徵語言(symbolic language)。
巴比倫人、印度人、埃及人、希伯來人、希臘人的神話,與阿散蒂人(Ashantis)或楚克人(Trukese)的神話,是用相同的語言書寫的。今天住在紐約或巴黎的人做的夢,與幾千年前生活在雅典或耶路撒冷的人所紀錄的夢,基本上是相同的。古代人與現代人描述夢境時所使用的語言,與人類文明肇始之時,那些創造神話的人所使用的語言相同。
象徵語言是一種以感官體驗與外在世界的事件,來表達內在體驗、感受和思想的語言。這種語言的邏輯不同於我們日常所使用的約定俗成的語言,其運作原則不是以時間與空間為主,而是以情感強度與意象聯想為核心。它是人類至今所發展出的,唯一一種共同語言,適用於所有化,並貫串古今。它擁有自己的語法和句法,一個人若想理解神話、童話和夢的意義,就必須理解象徵語言。
然而,現代人已經遺忘象徵語言——不是在睡著的時候,而是在清醒的時候。我們在清醒狀態中是否也應該理解象徵語言?對於生活在古代東、西方偉大文明的人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無庸置疑。對他們而言,神話和夢境是心靈最重要的表達方式之一,不懂得解讀它們則形同文盲。直到近幾百年的西方文化中,這種態度才發生改變。如今,神話被認為充其量只是科學興起之前人類心靈的天真虛構,是在人類尚未發現自然奧祕、尚未學會如何掌控自然力量之前所創造出來的產物。
在現代啟蒙運動的評價中,夢的地位更為不堪。夢被認為毫無意義,不值得成年人關注。成年人忙於製造機器之類的重要事務,自視為「現實主義者」,眼中只有可以被他們征服和操縱的事物。這些「現實主義者」對每種型號的汽車各有特殊的稱呼,但卻只知道用「愛」一個字來涵蓋各式各樣的情感體驗。
此外,如果我們所有的夢都是令人愉快的幻象,可以滿足我們內心的願望,那麼我們可能會對它們較為友善。然而,很多夢境只會帶給我們焦慮的心緒。它們通常是噩夢,會讓我們醒來時慶幸自己只是在做夢。其他的夢雖然不是噩夢,但可能由於其他原因而令人不安。它們與我們白天認定的自我形象格格不入。我們有時會夢見自己憎恨原以為喜歡的人,夢見我們喜愛原以為自己不感興趣的人。儘管我們相信自己一向謙遜。卻夢見自己懷有野心;當我們為自己的獨立而感到自豪時,卻夢見自己處於屈服和屈辱的境地。但比這一切事實更糟的是,我們不理解自己的夢,而醒著時的我們本來確信,只要用心思考便能理解一切。為了逃避這種證明「我們的理解力有局限性」的壓倒性證據,我們選擇指責夢境毫無意義。
在過去幾十年間,人對神話和夢的態度有深刻的轉變。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佛洛伊德研究的推動。他最初只是想幫助精神官能症患者了解他們患病的原因,但後來開始將夢視為一種普遍的人類現象進行研究,因為無論生病或是健康的人都一樣會做夢。他認為夢在本質上跟神話和童話沒有什麼不同,理解其中一種,就會理解其他兩種。人類學家的研究使人們重新關注神話。他們收集並研究神話,這個領域的先驅,例如巴霍芬(J. J. Bachofen),成功地為人類的史前史提供新的見解。
但神話和夢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並受到許多限制。其中之一是教條主義和僵化。這源於各個精神分析學派的主張,每一派都堅稱只有自己的詮釋才是對象徵語言的唯一正確理解。結果,我們忽視了象徵語言的多面性,並試圖將它強行塞入只有一種意義的框架之中。
另一個限制是,釋夢至今仍被認為,只有當精神科醫師用它來治療精神官能症患者時,才具正當性。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相信象徵語言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學習的一種外語。理解象徵語言能讓我們觸及神話這個最重要的智慧泉源,而且它也讓我們觸及自身人格的更深層次。事實上,它有助於我們理解一種人類特有的經驗層次,因為這個層次在內容與形式上都是全人類共通的。
《塔木德》說:「未經理解的夢就像一封未打開的信件。」確實,夢和神話都是我們與自己之間的重要溝通。如果我們不理解它們所使用的語言,就會錯過在我們沒有忙著操控外部世界的時候,自己所知道、也對自己說過的許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