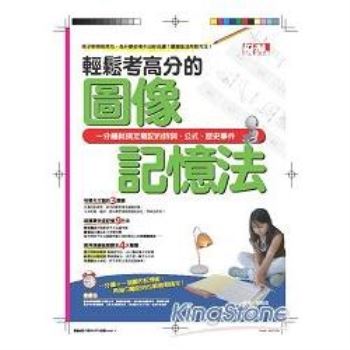1-1到底記憶是什麼?
簡單的說,記憶就是記住+回憶。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在記住想記的內容後,在特定的時間內將它源源本本地回憶出來。
為什麼一定要在特定的時間內呢?
考試時看到題目覺得答案好像呼之欲出,但是又想不起來到底要選B還是C,即使努力得都快想破頭了,還是想不起來哪一個才是正確答案,下課鈴響後只好不甘心的將考卷交給老師。走出教室的那一剎那才猛然想起,「啊!剛剛那一題的答案是B。」請問,這時候跑去跟老師要分數,老師會給我們嗎?
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在街上遇到一個多年不見的老友,老友看起來只是變胖、變老了一點,其他都沒什麼變,於是你很快的認出他來,他也剛好認出你了,但是兩人怎樣就是都想不起對方的名字,於是只好對他說聲「嗨!好久不見!最近好嗎?」他也很熱情的回應,同時我們在腦中快速地搜索可能的資料,但是打過招呼之後,還是想不起對方的名字,只好草草結束這段偶遇。萬一被發現自己完全忘了對方的名字,那不是糗大了!兩天之後在吃飯時,突然一個名字閃過腦中,「對啦!就是陳淑芬。哎呀!怎麼現在才想起來,我的記憶真差!」
這不是從小到大常常發生在我們周遭的情況嗎?
從這個現象我們也可以發現,記憶其實是完美的,一旦我們記住了,就不可能忘掉了,只是我們無法在特定的時間內將它回憶出來,於是我們認為自己的記憶力不好。
請問動物園裡的一種動物,牠有四隻腳、長眼睫毛、個子很高、同時背上長著兩座山,牠是哪一種動物?沒錯,就是駱駝。請問你現在就身處在動物園中嗎?不然,為何你知道答案是駱駝呢?因為過去我們曾經去過動物園也看過駱駝,所以當問題一出來時,我們腦中就開始進行圖像搜索,尋找有哪種動物的特徵符合上面的描述。因此,即使駱駝並不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也能正確回答出「駱駝」這個答案,同時「駱駝的圖像」也會出現在腦海中。
當我說到「駱駝」時,請問你的腦中出現的是「駱駝」這兩個字,還是「駱駝的樣子」?相信大家出現的都是「駱駝的樣子」。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回憶」靠的是圖像而不是文字。所以記憶要好,必須要靠圖像。
那麼,請你現在不要想「駱駝的樣子」!
是不是發現大腦反而更會出現「駱駝的樣子」呢?是不是發現自己的大腦好像變得不聽話了。文字與圖像在大腦中進行競爭的結果,就是大腦對於「圖像」的吸收強度遠遠超過「文字」。
若問你昨天晚餐吃什麼,當你在回答問題的同時,你的大腦正在搜索回憶的路徑,你會想到昨天晚上在哪裡或與什麼人一起吃晚餐的畫面,緊接著會有晚餐的菜色、情境、感覺以及空間位置等,大腦所回憶的盡是圖像,皆屬於圖像的功能,而絕非不符合大腦記憶方式的文字與數字名稱。因此,了解左右腦的功能,對我們的學習非常重要。
3-3關鍵三:具體圖解比抽象文字好記
如果時空大錯亂,我們跟過去的北京人、山頂洞人生存在同一時代、空間中,請問我們跟他們的差異性在哪裡?我們一樣會因為肚子餓而去覓食,只是現在的我們用錢去買食物,而北京人自己狩獵食物。我們會因為天氣冷而用錢購買衣服,而北京人則用手邊的樹葉與皮革,編製成足以遮蔽身體的衣物。
假設北京人跟我們一樣都會用錢買東西,也不需要為了三餐溫飽而花費許多的時間,請問我們跟北京人的行為有什麼不一樣?據考古學家和科學家研究,五十萬年前北京人的大腦居然跟我們現在沒有太大差異,為什麼我們的行為會出現如此大的不同呢?原因就出現在「教育」這兩個字上。北京人必須投注大量的時間與心力去滿足身體的基本需求,而我們不用,因此我們就多出了很多時間去思考、傳承、尋找、創造讓自己更便利、更美好的生活。人類的生活必須衣食無虞了,才有餘力去實施教育這件事。
早期的教育傳承是透過神話故事說明大自然的現象,再運用人類的想像力賦予合理化的解釋,隨之代代流傳下來。天空為什麼會打雷、閃電、下雨?中國創造出了雷公電母;北歐創造了富饒之神索爾,一揮斧頭就會產生雷電,一動槌子就會下雨(索爾的故事來自《蘇菲的世界》上集)。從中我們發現,在文字尚未出現之前,教育的傳承都是運用視覺上的圖像與大腦的思考,透過聽覺上的故事性將之結合起來,然後再經由生動的描述,讓聽者「印象」深刻,因此神話故事就能八九不離十的代代傳承。
文字出現後一切起了巨大的變化,生動活潑的「印象」傳承不再是焦點,而是事實的描述。大量抽象的描述不斷產生,文字也愈來愈豐富了,慢慢的我們的學習變得好像愈來愈難以「想像」的複雜。這個難以「想像」指的是我們已經缺少實體的物件可以幫助認識,於是「學習」變得愈來愈困難,這不是學習者的問題,而是學習方法的問題。
舉例來說,小時候媽媽敎我們學習1、2、3、4時,她是不是在上下樓梯時一邊踏著步伐,一邊唸著一步、兩步、三步?或是拿著蘋果時一邊指,一邊數?還是媽媽一開始就在白紙上畫著「1」、「2」、「3」?相信全天下的媽媽都一樣,都是先用蘋果或是手指頭敎我們數數,才敎我們數字怎麼寫。發現了嗎?當我們在學習數字這樣的抽象概念時,第一步是用具體的物件來幫助認識。
(1)學習的第一步─連結物件和聲音
臺灣常常有各式大大小小的選舉,當我的外甥女兩歲多時,每次她只要看到國旗,自然而然就會大聲喊出「凍蒜」。 她不認識國旗所代表的意義,她認識的是國旗這個具體物件,和當此物件出現時大人們所喊出的聲音,於是她將這樣的物件和聲音連結起來,這就是我們學習的第一步。
(2)學習的第二步─運用視覺圖像記住抽象符號
當我們會數數字了,媽媽就開始敎我們怎樣寫出抽象的數字符號:「1」的形狀像一隻筆或是棍子,「2」的形狀像一隻鴨子,「3」的形狀像人的耳朵,「4」的形狀像帆船或是三角旗,「6」的形狀像一個孕婦的側面,「7」的形狀像老爺爺拿的柺杖,「8」的形狀像眼鏡的鏡框,「9」的形狀像氣球,「0」的形狀像甜甜圈或是雞蛋,於是我們懂得怎樣「畫」出這些抽象的數字符號。我會說它是「畫出」來的,是因為我們去看國小小朋友寫字,常常形狀對了,筆劃順序卻不對。形狀是視覺的圖像,視覺圖像容易記得,而筆劃順序對剛學寫字的小孩而言,就不是這麼直接可以記住的。學習過程的第二步就是運用視覺的圖像來幫助我們記住抽象的符號,不論是文字符號或數字符號。
每一個抽象的符號都學會了,才能進入抽象概念的建立階段。簡單的說就是我們一定先學會認識「1」、「2」、「3」、「4」的符號,才能認識進階的加減乘除運算。有了加減乘除的抽象概念,才能進入機率組合的學習,或是建立微分、積分的觀念。
因此大腦學習的步驟可以簡化成:具體物件符號建立抽象觀念。符號的建立必須依賴具體的圖像,抽象觀念的建立必須奠基於符號的意義之上。所以,學習是一步步向上登的。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剛學過的東西馬上又忘了,如果我們連「1」、「2」、「3」、「4」的符號與其代表意義都記不住,怎麼可能學得好加減乘除呢?學習力與記憶力互為因果關係,學習能力好的人記憶力也好。
簡單的說,記憶就是記住+回憶。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在記住想記的內容後,在特定的時間內將它源源本本地回憶出來。
為什麼一定要在特定的時間內呢?
考試時看到題目覺得答案好像呼之欲出,但是又想不起來到底要選B還是C,即使努力得都快想破頭了,還是想不起來哪一個才是正確答案,下課鈴響後只好不甘心的將考卷交給老師。走出教室的那一剎那才猛然想起,「啊!剛剛那一題的答案是B。」請問,這時候跑去跟老師要分數,老師會給我們嗎?
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在街上遇到一個多年不見的老友,老友看起來只是變胖、變老了一點,其他都沒什麼變,於是你很快的認出他來,他也剛好認出你了,但是兩人怎樣就是都想不起對方的名字,於是只好對他說聲「嗨!好久不見!最近好嗎?」他也很熱情的回應,同時我們在腦中快速地搜索可能的資料,但是打過招呼之後,還是想不起對方的名字,只好草草結束這段偶遇。萬一被發現自己完全忘了對方的名字,那不是糗大了!兩天之後在吃飯時,突然一個名字閃過腦中,「對啦!就是陳淑芬。哎呀!怎麼現在才想起來,我的記憶真差!」
這不是從小到大常常發生在我們周遭的情況嗎?
從這個現象我們也可以發現,記憶其實是完美的,一旦我們記住了,就不可能忘掉了,只是我們無法在特定的時間內將它回憶出來,於是我們認為自己的記憶力不好。
請問動物園裡的一種動物,牠有四隻腳、長眼睫毛、個子很高、同時背上長著兩座山,牠是哪一種動物?沒錯,就是駱駝。請問你現在就身處在動物園中嗎?不然,為何你知道答案是駱駝呢?因為過去我們曾經去過動物園也看過駱駝,所以當問題一出來時,我們腦中就開始進行圖像搜索,尋找有哪種動物的特徵符合上面的描述。因此,即使駱駝並不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也能正確回答出「駱駝」這個答案,同時「駱駝的圖像」也會出現在腦海中。
當我說到「駱駝」時,請問你的腦中出現的是「駱駝」這兩個字,還是「駱駝的樣子」?相信大家出現的都是「駱駝的樣子」。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回憶」靠的是圖像而不是文字。所以記憶要好,必須要靠圖像。
那麼,請你現在不要想「駱駝的樣子」!
是不是發現大腦反而更會出現「駱駝的樣子」呢?是不是發現自己的大腦好像變得不聽話了。文字與圖像在大腦中進行競爭的結果,就是大腦對於「圖像」的吸收強度遠遠超過「文字」。
若問你昨天晚餐吃什麼,當你在回答問題的同時,你的大腦正在搜索回憶的路徑,你會想到昨天晚上在哪裡或與什麼人一起吃晚餐的畫面,緊接著會有晚餐的菜色、情境、感覺以及空間位置等,大腦所回憶的盡是圖像,皆屬於圖像的功能,而絕非不符合大腦記憶方式的文字與數字名稱。因此,了解左右腦的功能,對我們的學習非常重要。
3-3關鍵三:具體圖解比抽象文字好記
如果時空大錯亂,我們跟過去的北京人、山頂洞人生存在同一時代、空間中,請問我們跟他們的差異性在哪裡?我們一樣會因為肚子餓而去覓食,只是現在的我們用錢去買食物,而北京人自己狩獵食物。我們會因為天氣冷而用錢購買衣服,而北京人則用手邊的樹葉與皮革,編製成足以遮蔽身體的衣物。
假設北京人跟我們一樣都會用錢買東西,也不需要為了三餐溫飽而花費許多的時間,請問我們跟北京人的行為有什麼不一樣?據考古學家和科學家研究,五十萬年前北京人的大腦居然跟我們現在沒有太大差異,為什麼我們的行為會出現如此大的不同呢?原因就出現在「教育」這兩個字上。北京人必須投注大量的時間與心力去滿足身體的基本需求,而我們不用,因此我們就多出了很多時間去思考、傳承、尋找、創造讓自己更便利、更美好的生活。人類的生活必須衣食無虞了,才有餘力去實施教育這件事。
早期的教育傳承是透過神話故事說明大自然的現象,再運用人類的想像力賦予合理化的解釋,隨之代代流傳下來。天空為什麼會打雷、閃電、下雨?中國創造出了雷公電母;北歐創造了富饒之神索爾,一揮斧頭就會產生雷電,一動槌子就會下雨(索爾的故事來自《蘇菲的世界》上集)。從中我們發現,在文字尚未出現之前,教育的傳承都是運用視覺上的圖像與大腦的思考,透過聽覺上的故事性將之結合起來,然後再經由生動的描述,讓聽者「印象」深刻,因此神話故事就能八九不離十的代代傳承。
文字出現後一切起了巨大的變化,生動活潑的「印象」傳承不再是焦點,而是事實的描述。大量抽象的描述不斷產生,文字也愈來愈豐富了,慢慢的我們的學習變得好像愈來愈難以「想像」的複雜。這個難以「想像」指的是我們已經缺少實體的物件可以幫助認識,於是「學習」變得愈來愈困難,這不是學習者的問題,而是學習方法的問題。
舉例來說,小時候媽媽敎我們學習1、2、3、4時,她是不是在上下樓梯時一邊踏著步伐,一邊唸著一步、兩步、三步?或是拿著蘋果時一邊指,一邊數?還是媽媽一開始就在白紙上畫著「1」、「2」、「3」?相信全天下的媽媽都一樣,都是先用蘋果或是手指頭敎我們數數,才敎我們數字怎麼寫。發現了嗎?當我們在學習數字這樣的抽象概念時,第一步是用具體的物件來幫助認識。
(1)學習的第一步─連結物件和聲音
臺灣常常有各式大大小小的選舉,當我的外甥女兩歲多時,每次她只要看到國旗,自然而然就會大聲喊出「凍蒜」。 她不認識國旗所代表的意義,她認識的是國旗這個具體物件,和當此物件出現時大人們所喊出的聲音,於是她將這樣的物件和聲音連結起來,這就是我們學習的第一步。
(2)學習的第二步─運用視覺圖像記住抽象符號
當我們會數數字了,媽媽就開始敎我們怎樣寫出抽象的數字符號:「1」的形狀像一隻筆或是棍子,「2」的形狀像一隻鴨子,「3」的形狀像人的耳朵,「4」的形狀像帆船或是三角旗,「6」的形狀像一個孕婦的側面,「7」的形狀像老爺爺拿的柺杖,「8」的形狀像眼鏡的鏡框,「9」的形狀像氣球,「0」的形狀像甜甜圈或是雞蛋,於是我們懂得怎樣「畫」出這些抽象的數字符號。我會說它是「畫出」來的,是因為我們去看國小小朋友寫字,常常形狀對了,筆劃順序卻不對。形狀是視覺的圖像,視覺圖像容易記得,而筆劃順序對剛學寫字的小孩而言,就不是這麼直接可以記住的。學習過程的第二步就是運用視覺的圖像來幫助我們記住抽象的符號,不論是文字符號或數字符號。
每一個抽象的符號都學會了,才能進入抽象概念的建立階段。簡單的說就是我們一定先學會認識「1」、「2」、「3」、「4」的符號,才能認識進階的加減乘除運算。有了加減乘除的抽象概念,才能進入機率組合的學習,或是建立微分、積分的觀念。
因此大腦學習的步驟可以簡化成:具體物件符號建立抽象觀念。符號的建立必須依賴具體的圖像,抽象觀念的建立必須奠基於符號的意義之上。所以,學習是一步步向上登的。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剛學過的東西馬上又忘了,如果我們連「1」、「2」、「3」、「4」的符號與其代表意義都記不住,怎麼可能學得好加減乘除呢?學習力與記憶力互為因果關係,學習能力好的人記憶力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