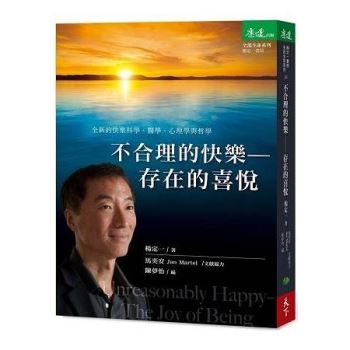書摘1
導論
在我們人生的快步調之下,快樂已經不再是一種選擇。不快樂,是現代人面對的最大危機。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的訊息指出,二○二○年全世界有三大疾病需要重視,憂鬱症正是其中之一。
憂鬱症在現代社會不斷地蔓延。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比例是男性的兩倍。憂鬱以及憂鬱帶來的慢性失調已經成為女性最普遍的健康問題,也是男性除了心血管疾病之外的大問題。四分之一以上的美國人一生會遭遇至少一次嚴重的憂鬱症,台灣的憂鬱人口則逾百萬,中國大陸超過一六%的大學生出現中度以上的情緒問題。
美國有兩位科學家針對全球各地四十三個國家超過六千名年輕學生,調查他們的快樂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華人學生的快樂程度最低,如果得分最低是一分,最快樂是七分,那麼華人學生的得分只有三‧三,而荷蘭學生最高是五‧四。如果被詢問到理論上一個人可以多快樂,華人學生的得分四‧五一樣是最低的,而巴西學生的得分六‧二最高。或許可以這麼說,我們的年輕孩子非但不快樂,甚至不敢奢望快樂。
年輕人不快樂的情況,愈來愈普遍。我相信每一個人身邊都遇過憂鬱、甚至有自殺念頭的年輕人。長期照護的疲憊、擔心憂鬱家人自殺的不安與無力感,還可能進一步引發身邊親近的人一併產生憂鬱。不快樂,帶來的社會成本,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高得多,甚至可以影響到一個社會是否能夠永續生存。
不快樂,不光造成健康的衰退,而且是人生幸福和滿足感最大的殺手。懂得快樂,自然深化生命的意義,也自然找回生命的健康和潛能。一個快樂的人,不光是學習、工作更有效率,也自然對自己和身邊的人更友善,更有利他的行為。
這本書的中心理念──要得到快樂,其實比任何人想的都更簡單。我們天生本來就是快樂,而且腦和生理架構就是支持快樂。可惜,透過人生和環境帶來的經驗,我們變得不快樂。
這本書會分成幾個層面來探討這個主題──用現代的心理學、社會學、醫學和生物學,來重新定義──何謂快樂。目前有沒有足夠的根據,可以得出一套通往快樂的實證公式?我會盡量將這些各自獨立的事實貫通,帶領讀者回到一個整體觀,這是這本書前半所要觸及的。我相信你很快就會發現,快樂,其實有一個「不合理」的層面。快樂,不是純粹理性的產物,它離不開感受,也就是英語裡的 “gut feeling”(直接翻譯過來是「腸道的感覺」,指的就是靈感或直覺)。你會發現,人生的快樂是身心綜合的產物,既離不開大腦的快樂,也離不開身體的快樂。
而且,和大家想的不一樣,是透過身體的快樂,我們才會找到身心均衡的快樂。現代人長期的失衡,過度偏重頭腦,而帶來不快樂。讓注意力落回身體,自然讓念頭降下來。身心均衡,自然快樂,我們也才能超越身心,找回真正的快樂。
這種觀點,對頭腦而言,是不理性、不合理的。但我相信,只要深入探討下去,你一定也會同意,而且符合你對快樂、對生命最直觀的體會。
懂了這些,就已經推翻了我們自己過去對快樂的種種看法和限定,所得到的公式也會截然不同。
這一不合理的層面,還不僅於此。我們可能不會想到,快樂和人生追求的目標及成果不見得直接相關。怎麼活這一生,比這一生活成什麼樣子,有時候是更重要的。
快樂,不需要理由。這一句話,和流行的觀點完全不同。就我目前為止所看到的心理學和科學,都還在合理的層面不斷強調──快樂是可以學來的,也可以追求到的。然而,所有「合理」的快樂非但短暫,身心很快就會適應,甚至對快樂的追求,反而成了不快樂的來源。
我在這本書的後半,想帶給你一個全然不同的理解──快樂,其實是「存在」,也就是「在」的觀念。假如真有永恆的快樂存在,其實是一種存在的成就,它是「在的喜悅」(joy of being),而不是「追求的快樂」(joy of doing)。
我相信,徹底懂了這些觀念,而可以隨時帶回生活中,會讓你這一生截然不同。但願這本小書能成為我們一起快樂的同伴。
書摘2
追求和期待
人間最期待的快樂,大概就是期待本身了。
巴夫洛夫(Ivan Pavlov)是一百多年前的俄國科學家,在聖彼得堡大學附設醫院進行研究。有一天,他注意到實驗室的狗只要看到他穿著實驗衣走進來,就開始流口水,而且產生快樂的反應。他很快聯想到,狗在期待接下來的餵食。他後來發現,除了白色的實驗衣,他還可以用別的方式引起同樣的反應。他餵狗吃肉,同時敲鈴。這樣的組合重複了幾次,到後來,只要敲鈴,狗就會流口水,效果和他的實驗衣一樣。就這樣,巴夫洛夫就發現了制約反射,而且認為這是學習的基礎。無論動物或人,把一個刺激和自己的反應建立連結,這就是學習。
這個發現,使他得到一九○四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巴夫洛夫不光證實了制約反射的存在,也同時驗證了一個非常古老的道理──熟能生巧 (Practice makes perfect.)。希臘七賢之一佩里安德(Periander, 627 - 587 BC) 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練習,即是一切」(Practice is everything.)。也就是說,任何學習,包括身心的快樂,都必須要重複再重複。
以前的人認為,快樂是可以學得來的。只要抑制負面的情緒,包括貪婪、嫉妒、恐懼,快樂自然就能浮出來。無論各個文化也都有禁欲、苦修、控制自己的感受 (askesis)的傳統。透過練習,透過一再的重複,化為生命的習慣,等於是為頭腦做了重新的制約,也就是學習。當然,用現代的語言,包括我所稱的新的神經迴路,談的也是「練習」這個古老的學問。
多巴胺和期待系統
從巴夫洛夫的制約學習,演變出一套獎懲的理論。我們會發現,對獎勵(也就是好的結果)的期待,自然引領著我們去做某件事。舉例來說,每個人都體驗過愛情的威力,光是想起那一個人,心頭小鹿亂跳,腳步也不由自主地輕快起來,時間過得特別長或特別短。為了約會或等電話,可以特別早起或晚睡。
戀愛中的大腦發生了什麼?研究人員找來十名女性和七名男性,戀愛時間從一個月到十七個月,請他們輪流看愛人和一位熟人的照片,中間還安排一些讓他們分心的事情,以免兩張照片的效果相互干擾。同時,用fMRI拍下他們的大腦影像。發現大腦中分泌多巴胺(dopamine)的位置都活化起來了。
談到在腦內帶來快樂的小分子,大概沒有一個比多巴胺更重要。
多巴胺的結構比起前面提到的腦內啡和喜悅酼胺都簡單,早在一九一○年就已經在實驗室用含有九個碳原子的左旋多巴(L-dopa)透過一個簡單的反應,得到由八個碳原子所組成的多巴胺。然而一直要到一九五七年,科學家才知道多巴胺也存在於腦部,再隔一年,才知道多巴胺不只是其他神經傳導分子的前身,它本身就有神經傳導的功能,在神經細胞受到刺激時,分泌出來傳遞訊息。這項發現,後來得到二○○○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如果你看過電影《無語問蒼天》(Awakenings,也譯做《睡人》),大概還記得原本像蠟像一樣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的患者,在用藥之後「解凍」了。這個藥物就是左旋多巴,能通過血腦屏障,在腦中轉化成多巴胺。
相信你看到多巴胺的結構,會覺得相當不可思議。這麼簡單的構造,就是一個胺基(-NH2)再多連上幾個碳氫的結構,就可以讓我們的人生動起來,帶來積極進取的快樂。
不只是動起來,多巴胺還帶來期待的心情,讓人願意為了美好感覺的獎勵,而去嘗試新的經驗、認識新的人、學習新的事物。就連剛到一個新的工作環境,都可能帶來很多生理和心理的興奮反應。就好像腦部有一套期待系統(anticipation system,又稱獎勵系統 rewarding system)帶領著我們去投入,而多巴胺就是其中的主角。
期待和獎勵所帶來的快樂其實不太一樣。在追求的時候,主導著我們積極進取的,是一種興奮感。我們都看過小孩子為了一根還沒到手的棒棒糖,多麼開心地跳上跳下,或心甘情願地去等待。對獎勵的期待,本身就帶來快樂的心情。等拿到棒棒糖時,拆開糖果紙,放到嘴裡,期待已久的獎勵終於實現了,化成甜蜜的心情和滿足。有意思的是,獎勵本身帶來的快樂,不像期待那麼持久和激動,好像獎勵到手那一瞬間,也就到底了。
科學家用期待和獎勵這兩個詞來描述同一個系統,也正表達了這種快樂的兩個層面──期待引領我們去追求,而追求到的時候,帶來快樂的獎勵,而這樣的學習也就構成了正向的制約。
期待系統完全受到多巴胺的作用,不光是帶來正向的念頭,還會促使我們去規劃、執行。說到這裡,希望你忍耐一下科學家凡事都要說明白的習慣。這個期待或獎勵系統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在腦部有一個明確的腦區,和前幾章提到的邊緣系統,也就是「情緒腦」的位置很接近。
期待系統包括了前腦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中腦的腹側被蓋區(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和中腦的黑質(substantia nigra)。這些位置,含有許多生成多巴胺的神經細胞。我們也可以從下圖看到這些區域與腦部其他位置的連線,包括與負責認知、規劃的前額葉之間的連線。這也代表了,期待系統對整個腦的運作影響重大。書摘3
快樂,也會消退
可惜的是,對於身心的快樂,腦部有一個「適應」的機制,也就是前頭提到的享樂適應。舉例來說,人會期待好事發生,像加薪、升職、獎勵,一旦得到了,就好像沒有原本還在期待時那麼快樂。透過刺激帶來的快樂,「劑量」好像要愈加愈多,而增加的邊際效應愈來愈少。
任何活動,比如看電視,使用電腦、電話、網路、飲食所帶來的滿足感,都會很快地飽和,沒多久就乏味了。人要逃避無聊的感覺,自然會追求變化。包括外遇,或換一個伴侶,也有一部份是出於逃避一再重複的感覺,想得到快樂。
為什麼會如此,從神經細胞運作的角度來看,一點也沒有什麼好驚訝的。
不同的神經細胞掌管不同的訊息,有些專管外界的刺激,如聲、光、壓力的變化,有些專門接收其他細胞的訊號,包括神經細胞。一個神經細胞接收到某種訊息,也許是電,也許是神經傳導分子的刺激,內外的離子濃度發生變化,造成電位的改變,進而去改變下一個神經細胞的狀態。這個促成改變其他神經細胞狀態的電位,就叫做「動作電位」。
只要刺激的量達到一定的門檻,神經細胞就會放電。然而,每次放電的大小都一樣。也就是面對任何刺激,只有「放電」、「不放電」兩種可能。放電後,短時間內不會再產生動作電位。膜上的鈉離子通道變得不敏感,必須要更大的刺激,才能達到再度放電的門檻。然而,反覆刺激同一個神經細胞,這些刺激對樹突的作用也會降低。
由於神經系統的傳遞速度相當快,科學家設計了一種「單一細胞電生理」的特殊方法,幫助我們立即觀察神經細胞受到刺激之後的變化。我以前也用這樣的方法,帶領年輕的學生探討神經的運作。我請來自加拿大的馬奕安博士(Jan Martel Ph.D.)重新繪製下圖,一方面說明「單一細胞電生理」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讓「重複刺激,會讓細胞敏感性降低」的概念更為清晰。
圖下方的箭頭,就是神經細胞受到刺激的時間點。除了透過物理、電,也可以用化學物質(例如尼古丁或本來就會出現在腦部的神經傳導分子)來刺激神經細胞。從這張圖,我們會看到,只要刺激神經細胞,就會產生電壓的變化。這種電壓的變化,也就是所謂的「動作電位」,經過軸突的傳遞,可以活化或抑制下一個細胞。然而,神經細胞很快就會恢復原狀,讓電壓回到原本的水平。我們可以看到,反覆地給予同一個刺激,所觀察到的動作電位逐漸變小。甚至到最後,即使繼續刺激,也不會再產生動作電位。
腦部的運作,是透過神經傳導分子和神經元之間的作用,而這些分子常常釋放,自然會達成飽和,造成對刺激的適應。從心理的層面來說,前面提到的享樂適應也就是這麼一回事。如果我們一再重複某個刺激,那麼同一刺激帶來的快樂強度也會慢慢消退。也難怪人天性會追求變化。變化可以重新設定腦部的神經迴路,讓它回復原本的反應門檻值。
前頭提過舒茲做的猴子和蘋果的實驗,相信你還記得,一開始給猴子蘋果時,牠們腦中分泌多巴胺的位置(黑質)都活躍起來了。只是,多重複幾次,再怎麼給蘋果,引發的效益愈來愈低,幾乎和沒給過蘋果之前差不多。
然而,這時候如果把蘋果改成葡萄乾,這個意外的驚喜會使腦部大量釋放多巴胺,你也會看到猴子露出驚喜的表情,甚至感染到牠的快樂。不過,一樣地,如果葡萄乾再來幾次,這個效應也會淡化。再怎麼好吃,猴子也習慣了。
人也是一樣的,習慣了美食之後,再怎麼精心烹調,吸引力也會減少。
最有意思的是,吃過葡萄乾的猴子,如果再回到蘋果餐,會發現多巴胺的釋放量甚至比還沒有吃蘋果時更低。和葡萄乾相較,蘋果太令人失望了,多巴胺的量才釋放得那麼低,就像中國人說的「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不過,假如蘋果餐繼續持續下去,那麼腦部還是會繼續分泌多巴胺,就好像沒發生過葡萄乾這回事一樣。
透過經驗的轉換,所自然造出的對比,等於是重新設定快樂的路徑。一般心理學家建議要輪替帶來快樂的經驗,以避免「對快樂的疲乏」。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即使疲乏了,腦內自然有某種生理機制幫助我們適應這一疲乏,再度回到快樂的固定值。只是人和動物不同在於,透過前額葉造出發達的認知和記憶,對於過去經驗過的總是念念不忘,對於未來還沒得到的更是充滿期待。於是,總是需要更多,永遠不會滿足。有了更多,會想要更多。再怎麼變化,永遠會想要更新鮮的變化。
說真的,再怎麼去追求新鮮感,人還是有飽和的一天,早晚要落回不快樂的窠臼。無論多巴胺帶來多少的刺激,或血清素為我們踩多少次不快樂的剎車,最後我們還是會習慣的。一再重複愉快的經驗,愉快的感受也會逐漸降下來,可以說,我們都適應了。
這種「溜溜球效應」相信我們都經驗過,也只是證明腦必須不斷地要新的,要好的刺激。不光要多,還要有妥當的變化。然而,再怎麼變化,也總有疲乏的一天。我才說,要想透過外在的刺激,來達到永恆的快樂,是靠不住的。而透過種種方式去逃避無聊,逃避對快樂的疲乏,也只是白費力氣。
導論
在我們人生的快步調之下,快樂已經不再是一種選擇。不快樂,是現代人面對的最大危機。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的訊息指出,二○二○年全世界有三大疾病需要重視,憂鬱症正是其中之一。
憂鬱症在現代社會不斷地蔓延。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比例是男性的兩倍。憂鬱以及憂鬱帶來的慢性失調已經成為女性最普遍的健康問題,也是男性除了心血管疾病之外的大問題。四分之一以上的美國人一生會遭遇至少一次嚴重的憂鬱症,台灣的憂鬱人口則逾百萬,中國大陸超過一六%的大學生出現中度以上的情緒問題。
美國有兩位科學家針對全球各地四十三個國家超過六千名年輕學生,調查他們的快樂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華人學生的快樂程度最低,如果得分最低是一分,最快樂是七分,那麼華人學生的得分只有三‧三,而荷蘭學生最高是五‧四。如果被詢問到理論上一個人可以多快樂,華人學生的得分四‧五一樣是最低的,而巴西學生的得分六‧二最高。或許可以這麼說,我們的年輕孩子非但不快樂,甚至不敢奢望快樂。
年輕人不快樂的情況,愈來愈普遍。我相信每一個人身邊都遇過憂鬱、甚至有自殺念頭的年輕人。長期照護的疲憊、擔心憂鬱家人自殺的不安與無力感,還可能進一步引發身邊親近的人一併產生憂鬱。不快樂,帶來的社會成本,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高得多,甚至可以影響到一個社會是否能夠永續生存。
不快樂,不光造成健康的衰退,而且是人生幸福和滿足感最大的殺手。懂得快樂,自然深化生命的意義,也自然找回生命的健康和潛能。一個快樂的人,不光是學習、工作更有效率,也自然對自己和身邊的人更友善,更有利他的行為。
這本書的中心理念──要得到快樂,其實比任何人想的都更簡單。我們天生本來就是快樂,而且腦和生理架構就是支持快樂。可惜,透過人生和環境帶來的經驗,我們變得不快樂。
這本書會分成幾個層面來探討這個主題──用現代的心理學、社會學、醫學和生物學,來重新定義──何謂快樂。目前有沒有足夠的根據,可以得出一套通往快樂的實證公式?我會盡量將這些各自獨立的事實貫通,帶領讀者回到一個整體觀,這是這本書前半所要觸及的。我相信你很快就會發現,快樂,其實有一個「不合理」的層面。快樂,不是純粹理性的產物,它離不開感受,也就是英語裡的 “gut feeling”(直接翻譯過來是「腸道的感覺」,指的就是靈感或直覺)。你會發現,人生的快樂是身心綜合的產物,既離不開大腦的快樂,也離不開身體的快樂。
而且,和大家想的不一樣,是透過身體的快樂,我們才會找到身心均衡的快樂。現代人長期的失衡,過度偏重頭腦,而帶來不快樂。讓注意力落回身體,自然讓念頭降下來。身心均衡,自然快樂,我們也才能超越身心,找回真正的快樂。
這種觀點,對頭腦而言,是不理性、不合理的。但我相信,只要深入探討下去,你一定也會同意,而且符合你對快樂、對生命最直觀的體會。
懂了這些,就已經推翻了我們自己過去對快樂的種種看法和限定,所得到的公式也會截然不同。
這一不合理的層面,還不僅於此。我們可能不會想到,快樂和人生追求的目標及成果不見得直接相關。怎麼活這一生,比這一生活成什麼樣子,有時候是更重要的。
快樂,不需要理由。這一句話,和流行的觀點完全不同。就我目前為止所看到的心理學和科學,都還在合理的層面不斷強調──快樂是可以學來的,也可以追求到的。然而,所有「合理」的快樂非但短暫,身心很快就會適應,甚至對快樂的追求,反而成了不快樂的來源。
我在這本書的後半,想帶給你一個全然不同的理解──快樂,其實是「存在」,也就是「在」的觀念。假如真有永恆的快樂存在,其實是一種存在的成就,它是「在的喜悅」(joy of being),而不是「追求的快樂」(joy of doing)。
我相信,徹底懂了這些觀念,而可以隨時帶回生活中,會讓你這一生截然不同。但願這本小書能成為我們一起快樂的同伴。
書摘2
追求和期待
人間最期待的快樂,大概就是期待本身了。
巴夫洛夫(Ivan Pavlov)是一百多年前的俄國科學家,在聖彼得堡大學附設醫院進行研究。有一天,他注意到實驗室的狗只要看到他穿著實驗衣走進來,就開始流口水,而且產生快樂的反應。他很快聯想到,狗在期待接下來的餵食。他後來發現,除了白色的實驗衣,他還可以用別的方式引起同樣的反應。他餵狗吃肉,同時敲鈴。這樣的組合重複了幾次,到後來,只要敲鈴,狗就會流口水,效果和他的實驗衣一樣。就這樣,巴夫洛夫就發現了制約反射,而且認為這是學習的基礎。無論動物或人,把一個刺激和自己的反應建立連結,這就是學習。
這個發現,使他得到一九○四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巴夫洛夫不光證實了制約反射的存在,也同時驗證了一個非常古老的道理──熟能生巧 (Practice makes perfect.)。希臘七賢之一佩里安德(Periander, 627 - 587 BC) 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練習,即是一切」(Practice is everything.)。也就是說,任何學習,包括身心的快樂,都必須要重複再重複。
以前的人認為,快樂是可以學得來的。只要抑制負面的情緒,包括貪婪、嫉妒、恐懼,快樂自然就能浮出來。無論各個文化也都有禁欲、苦修、控制自己的感受 (askesis)的傳統。透過練習,透過一再的重複,化為生命的習慣,等於是為頭腦做了重新的制約,也就是學習。當然,用現代的語言,包括我所稱的新的神經迴路,談的也是「練習」這個古老的學問。
多巴胺和期待系統
從巴夫洛夫的制約學習,演變出一套獎懲的理論。我們會發現,對獎勵(也就是好的結果)的期待,自然引領著我們去做某件事。舉例來說,每個人都體驗過愛情的威力,光是想起那一個人,心頭小鹿亂跳,腳步也不由自主地輕快起來,時間過得特別長或特別短。為了約會或等電話,可以特別早起或晚睡。
戀愛中的大腦發生了什麼?研究人員找來十名女性和七名男性,戀愛時間從一個月到十七個月,請他們輪流看愛人和一位熟人的照片,中間還安排一些讓他們分心的事情,以免兩張照片的效果相互干擾。同時,用fMRI拍下他們的大腦影像。發現大腦中分泌多巴胺(dopamine)的位置都活化起來了。
談到在腦內帶來快樂的小分子,大概沒有一個比多巴胺更重要。
多巴胺的結構比起前面提到的腦內啡和喜悅酼胺都簡單,早在一九一○年就已經在實驗室用含有九個碳原子的左旋多巴(L-dopa)透過一個簡單的反應,得到由八個碳原子所組成的多巴胺。然而一直要到一九五七年,科學家才知道多巴胺也存在於腦部,再隔一年,才知道多巴胺不只是其他神經傳導分子的前身,它本身就有神經傳導的功能,在神經細胞受到刺激時,分泌出來傳遞訊息。這項發現,後來得到二○○○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如果你看過電影《無語問蒼天》(Awakenings,也譯做《睡人》),大概還記得原本像蠟像一樣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的患者,在用藥之後「解凍」了。這個藥物就是左旋多巴,能通過血腦屏障,在腦中轉化成多巴胺。
相信你看到多巴胺的結構,會覺得相當不可思議。這麼簡單的構造,就是一個胺基(-NH2)再多連上幾個碳氫的結構,就可以讓我們的人生動起來,帶來積極進取的快樂。
不只是動起來,多巴胺還帶來期待的心情,讓人願意為了美好感覺的獎勵,而去嘗試新的經驗、認識新的人、學習新的事物。就連剛到一個新的工作環境,都可能帶來很多生理和心理的興奮反應。就好像腦部有一套期待系統(anticipation system,又稱獎勵系統 rewarding system)帶領著我們去投入,而多巴胺就是其中的主角。
期待和獎勵所帶來的快樂其實不太一樣。在追求的時候,主導著我們積極進取的,是一種興奮感。我們都看過小孩子為了一根還沒到手的棒棒糖,多麼開心地跳上跳下,或心甘情願地去等待。對獎勵的期待,本身就帶來快樂的心情。等拿到棒棒糖時,拆開糖果紙,放到嘴裡,期待已久的獎勵終於實現了,化成甜蜜的心情和滿足。有意思的是,獎勵本身帶來的快樂,不像期待那麼持久和激動,好像獎勵到手那一瞬間,也就到底了。
科學家用期待和獎勵這兩個詞來描述同一個系統,也正表達了這種快樂的兩個層面──期待引領我們去追求,而追求到的時候,帶來快樂的獎勵,而這樣的學習也就構成了正向的制約。
期待系統完全受到多巴胺的作用,不光是帶來正向的念頭,還會促使我們去規劃、執行。說到這裡,希望你忍耐一下科學家凡事都要說明白的習慣。這個期待或獎勵系統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在腦部有一個明確的腦區,和前幾章提到的邊緣系統,也就是「情緒腦」的位置很接近。
期待系統包括了前腦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中腦的腹側被蓋區(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和中腦的黑質(substantia nigra)。這些位置,含有許多生成多巴胺的神經細胞。我們也可以從下圖看到這些區域與腦部其他位置的連線,包括與負責認知、規劃的前額葉之間的連線。這也代表了,期待系統對整個腦的運作影響重大。書摘3
快樂,也會消退
可惜的是,對於身心的快樂,腦部有一個「適應」的機制,也就是前頭提到的享樂適應。舉例來說,人會期待好事發生,像加薪、升職、獎勵,一旦得到了,就好像沒有原本還在期待時那麼快樂。透過刺激帶來的快樂,「劑量」好像要愈加愈多,而增加的邊際效應愈來愈少。
任何活動,比如看電視,使用電腦、電話、網路、飲食所帶來的滿足感,都會很快地飽和,沒多久就乏味了。人要逃避無聊的感覺,自然會追求變化。包括外遇,或換一個伴侶,也有一部份是出於逃避一再重複的感覺,想得到快樂。
為什麼會如此,從神經細胞運作的角度來看,一點也沒有什麼好驚訝的。
不同的神經細胞掌管不同的訊息,有些專管外界的刺激,如聲、光、壓力的變化,有些專門接收其他細胞的訊號,包括神經細胞。一個神經細胞接收到某種訊息,也許是電,也許是神經傳導分子的刺激,內外的離子濃度發生變化,造成電位的改變,進而去改變下一個神經細胞的狀態。這個促成改變其他神經細胞狀態的電位,就叫做「動作電位」。
只要刺激的量達到一定的門檻,神經細胞就會放電。然而,每次放電的大小都一樣。也就是面對任何刺激,只有「放電」、「不放電」兩種可能。放電後,短時間內不會再產生動作電位。膜上的鈉離子通道變得不敏感,必須要更大的刺激,才能達到再度放電的門檻。然而,反覆刺激同一個神經細胞,這些刺激對樹突的作用也會降低。
由於神經系統的傳遞速度相當快,科學家設計了一種「單一細胞電生理」的特殊方法,幫助我們立即觀察神經細胞受到刺激之後的變化。我以前也用這樣的方法,帶領年輕的學生探討神經的運作。我請來自加拿大的馬奕安博士(Jan Martel Ph.D.)重新繪製下圖,一方面說明「單一細胞電生理」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讓「重複刺激,會讓細胞敏感性降低」的概念更為清晰。
圖下方的箭頭,就是神經細胞受到刺激的時間點。除了透過物理、電,也可以用化學物質(例如尼古丁或本來就會出現在腦部的神經傳導分子)來刺激神經細胞。從這張圖,我們會看到,只要刺激神經細胞,就會產生電壓的變化。這種電壓的變化,也就是所謂的「動作電位」,經過軸突的傳遞,可以活化或抑制下一個細胞。然而,神經細胞很快就會恢復原狀,讓電壓回到原本的水平。我們可以看到,反覆地給予同一個刺激,所觀察到的動作電位逐漸變小。甚至到最後,即使繼續刺激,也不會再產生動作電位。
腦部的運作,是透過神經傳導分子和神經元之間的作用,而這些分子常常釋放,自然會達成飽和,造成對刺激的適應。從心理的層面來說,前面提到的享樂適應也就是這麼一回事。如果我們一再重複某個刺激,那麼同一刺激帶來的快樂強度也會慢慢消退。也難怪人天性會追求變化。變化可以重新設定腦部的神經迴路,讓它回復原本的反應門檻值。
前頭提過舒茲做的猴子和蘋果的實驗,相信你還記得,一開始給猴子蘋果時,牠們腦中分泌多巴胺的位置(黑質)都活躍起來了。只是,多重複幾次,再怎麼給蘋果,引發的效益愈來愈低,幾乎和沒給過蘋果之前差不多。
然而,這時候如果把蘋果改成葡萄乾,這個意外的驚喜會使腦部大量釋放多巴胺,你也會看到猴子露出驚喜的表情,甚至感染到牠的快樂。不過,一樣地,如果葡萄乾再來幾次,這個效應也會淡化。再怎麼好吃,猴子也習慣了。
人也是一樣的,習慣了美食之後,再怎麼精心烹調,吸引力也會減少。
最有意思的是,吃過葡萄乾的猴子,如果再回到蘋果餐,會發現多巴胺的釋放量甚至比還沒有吃蘋果時更低。和葡萄乾相較,蘋果太令人失望了,多巴胺的量才釋放得那麼低,就像中國人說的「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不過,假如蘋果餐繼續持續下去,那麼腦部還是會繼續分泌多巴胺,就好像沒發生過葡萄乾這回事一樣。
透過經驗的轉換,所自然造出的對比,等於是重新設定快樂的路徑。一般心理學家建議要輪替帶來快樂的經驗,以避免「對快樂的疲乏」。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即使疲乏了,腦內自然有某種生理機制幫助我們適應這一疲乏,再度回到快樂的固定值。只是人和動物不同在於,透過前額葉造出發達的認知和記憶,對於過去經驗過的總是念念不忘,對於未來還沒得到的更是充滿期待。於是,總是需要更多,永遠不會滿足。有了更多,會想要更多。再怎麼變化,永遠會想要更新鮮的變化。
說真的,再怎麼去追求新鮮感,人還是有飽和的一天,早晚要落回不快樂的窠臼。無論多巴胺帶來多少的刺激,或血清素為我們踩多少次不快樂的剎車,最後我們還是會習慣的。一再重複愉快的經驗,愉快的感受也會逐漸降下來,可以說,我們都適應了。
這種「溜溜球效應」相信我們都經驗過,也只是證明腦必須不斷地要新的,要好的刺激。不光要多,還要有妥當的變化。然而,再怎麼變化,也總有疲乏的一天。我才說,要想透過外在的刺激,來達到永恆的快樂,是靠不住的。而透過種種方式去逃避無聊,逃避對快樂的疲乏,也只是白費力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