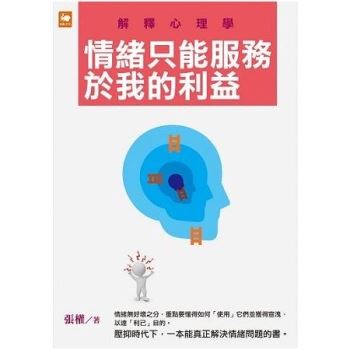前言
本書不是寫給「有識」之士看的,亦不作什麼學術研究。「解釋心理學」這個書名可能會令人出現混淆,因它用了「心理學」這個極專業名稱,但本書並非要去「解釋」傳統的心理學,只是想打破既定的學術框架,用純個人的經驗去「解釋」自己情緒之由來,是一個平凡人據其個人之生活體驗、每天有血有肉與人的短兵相接,所記錄下來的一些人生看法;用一種閒話家常的語言、盡量淺白的道理,藉以讓每個人了解自己「內在」的運作;因為我們身處一個極其壓抑的時代,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點心理問題、情緒困擾。
就心理學範疇而言,我討厭象牙塔式的學術探索,並非我害怕艱澀的學習過程,而是這種所謂的科研、對於真正的「用家」有什麼幫助?尤其心理學這麼個人化,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的一門學說,就如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指紋,絕對沒有一個人是相同的;道理相同,將心理學仿照科學方法論證的弊端在於――怎可用一個預設的學術框架去概括所有人的心路歷程、演變經過。
而更嚴重的是,各門各派的心理學專家、每天埋頭苦幹在研究的結果,其最終的成果都與中國宋朝儒家一脈相承者的朱熹一樣――格物致知。但「格物致知」對於現世的生活又有何益?因為,作為一個每天忙於生活的普通現代人,他最迫切追求的是另一個更實在的層次――格物致用。
美國二十世紀一位有名的心理學大師,被譽為「人本主義心理學精神之父」――亞伯拉罕‧哈羅德‧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走向生命的巔峰:馬斯洛的人本心理學》一書說,馬斯洛對其母親,他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憎恨和根深蒂固的敵意。這種感情不僅存在於他的孩提時代,即便其母先他幾年辭世時也依然未減。他甚至拒絕參加母親葬禮。由於其母篤信宗教,在他年幼時經常以上帝的懲罰來威脅他,故而他後來逐漸形成了對宗教的不信任,甚至憎惡。他一度為對其母親的感情問題專門接受過心理治療,結果都無濟於事。
「能醫不自醫」的馬斯洛那股根深蒂固之憎恨,直到他母親離世也沒有消弭,直到1969年他自己謝世的前一年,馬斯洛曾這樣描述對自己母親的感情:我所有討厭、憎恨、拒絕的不僅是她的外表,而且還包括她的價值觀、世界觀,她的吝嗇、自私,以及對世界上任何其他人包括她丈夫和孩子都缺乏感情……她認為世上任何與她有分歧的人都是壞的,對她的孫子她也漠不關心,沒有朋友、大大咧咧、骯髒,與父母關係疏離,對她的兄妹亦沒有一點手足之情……我不知道我的烏托邦精神、道德感、人道主義、仁慈、愛、友誼及其他所有健康的感情來自何處,我僅能肯定這是母愛缺乏所帶來的後果。我的生活哲學研究、理論建構的動力,均源於對母親的憎恨、對其所支持的一切事物的拒絕。
坦白而言,馬斯洛的學說我並沒涉獵過多,但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其內心的一股憎恨,竟然在對方死後依然難以釋懷;甚至乎在自己行將就木之際,馬斯洛對母親的仇恨仍然縈繞心中揮之不去;我恕難苟同,也不認為這種深藏憎恨的人生有什麼「巔峰」可言。
我並非有意貶低他人的成就,亦無能力質疑心理學家們的論證,我只是個普通人,但我內心有種理念:一個哲學家不該怕死,一個心理學家不應受到情緒困擾,就如一個神父不能死於梅毒。好死不死,作為一個神父可以有千百種死法,但就是不能死於梅毒,因為這與你的身分不配嘛!換句話說,你的理論不可以違背你的實踐,連在自己身上也做不到,更遑論能有效地施展在其他人身上。
另一個有相同「陰影」、在心理學界更赫赫有名的――佛洛依德(Sigismund Schlomo Freud 1856-1939)。佛洛依德的「戀母情結」,從某角度觀之,也是另類走不出童年陰影的心理障礙。孩童時對自己母親的胴體有個「無意識」的生理遐想,不單是佛洛依德,就算是我、我更相信有很多少男都有過同樣的「回溯」,但這種無意識的「欲求」只是一閃而過,不曾在心中激起過任何波瀾,踏進青春期後更自動煙消雲散,可能有些人連一點記憶都沒了,因為這時個體會很正常地投入真實的異性欲求當中,而完全蓋過了那曾經有過的幼稚「幻想」。但那股對自己母親曾經有過之「欲求」,在佛洛依德長大後的很多年仍然令他思潮起伏,他說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情結。不錯,佛洛依德無法擺脫這種情結,所以當他看到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的故事時,立即獲得醍醐灌頂般的覺悟,並斷言:「在所有後來變為精神病患的兒童的精神生活中,他們的父母起了主要作用。」及後,佛洛依德並將這個故事設為框架,作為自己「戀母情結」學說的奠基,更成為他個人學派的獨創旗幟。
佛洛依德的「泛性」學說,強調童年時的第一次性衝動對個體一生有著多嚴重的影響,認為性壓抑是很多精神官能症的元兇,我們很多精神問題都因這些「欲念」未曾獲得滿足才會衍生;佛氏這種言論,處於當時已受到不少微言,在今天看來更是乏善可陳。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正常的現代男人不可能沒有「性壓抑」,就算生活在蠻荒時代或古代,除了極少數的部落領袖與一些帝王之外,也不是每個男人發現有「心儀」的女人都能與之交配,隨時都可獲得性滿足。更何況,我們的「內在」又是極其複雜的構造,怎可用一種「泛性」理論,認為性欲一旦獲得滿足,個體便能萬事俱休?因為大家都明白,人除了性,「內在」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欲求,做愛和吃飯絕對不是人生的最終意義,反而當吃飯與做愛過後,人生的意義才真正開始。
一個人若不自覺心理有點問題,很少會去翻閱有關心理學的書籍;更有些人因想瞭解自己的心理問題,才一頭栽進心理學這個範疇,最後因利乘便,成為了一代的心理學宗師;但這些大師很多都終生沉淪在自己的痛苦精神當中,美國的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患有嚴重抑鬱症和身心疾病,經常靠閱讀《聖經》來維持意志力;在1875年,當詹姆士成為哈佛大學心理學講師後,他的憂鬱症依然困擾著他,他經常這樣來勉勵自己:
「我要找一個能令自己再想存活多四小時的理由」
找一個令自己願意活下去的理由,詹姆士最終找到了,據說他在1878年精神狀況漸趨好轉,應該走出了憂鬱的陰霾;但詹姆士的學說、詹姆士所找到的「理由」,只是在他自己身上「驗證」過,並不一定適合你,就如,不是每個人都能靠閱讀《聖經》來維持意志力。心理學書籍有很多人閱讀,因為每個人對自己的「內在」都會有興趣,但有多少人能學以致用,為什麼不能將學到的理論實踐在日常生活中?我並非指責心理學家們寫的書籍、提出的論證都是耍嘴皮的紙上談兵,只是他們太過注重學術方法上的研究,而忽略了真正「用家」是有血有肉與人每天短兵相接的人。所以,馬斯洛也好,詹姆士也好,佛洛依德也好,一眾心理學宗師也罷,他們只是埋頭苦幹在做「學術研究」;但一涉及研究就會走向科學性的系統論證,導致與「實際心理」情況愈走愈遠,因此,這些所謂研究最終也只能停留於學院式的層面,難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當一個普通人自覺心理有點問題,於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去認識心理學,最後,讀懂了一大堆艱澀的專業名詞、明白了一大批深奧的學術理論,但回頭一望,原來這些東西對他的生活完全沒有幫助。為什麼會沒有幫助?因為這些學院式的研究,他們的重點是在於研究問題並非解決問題。
在幾十億年的地球歷史中,人類的出現最多只有六百萬年,進入文明最多也只是一萬年,為什麼只有等到人類的出現地球才開始被瞭解?究竟是神創造了世界,還是人創造了神?
這些惱人的哲學問題,你不去問就不會有問題。英國哲學家羅素曾經說過,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他不會浪費時間去讀哲學,因為哲學的最主要功能:不是讓平凡人變得聰明,而是讓聰明人知道,自己並非如想像般那麼優秀。所以問題的重點,你只是個平凡人,去問這些問題對你的人生有何獲益?換句話說,每個讀心理學書籍的普通讀者,最關心的只是自己一些心理上、情緒中的疑問,並沒興趣亦無能力作深奧的探討。
坊間大部分的心理學書籍,什麼「心理學原理」、「心理咨詢」、「情緒管理」的呀,都是某些心理學「大師」依憑個人之心理運作而立論,滿書都是學述性研究、艱澀的專業用詞;目的在於鞏固其論證、想用科學之手段歸納出一套權威的心理學派系,多於幫助有心理障礙的人解決問題。這些紙上談兵的書籍,一般人要讀懂都非常艱苦,更何況能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大千世界,色相紛亂繁雜,不是每種東西的「設置」,都是為了給人類的智慧去了解的;況且,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智慧」,硬塞一些對他來說並沒有「用處」的東西給他去了解,對其個人的意義何在?生命太短促了,而人又是欲望的組合,要在生命的瞬間去解釋、攫取自己的存在意義。所以這本書探討的主題,不是心理之原型、謝絕一切學院式的研究、摒棄任何艱澀的詞彙和所謂的學術理論;就像一把「奧卡姆剃刀」,將那些令人感到厭煩的爭論、一些既累贅又空洞無物之普遍性概念,引刀成一快地無情剃除。盡量用淺白的語言,或一些每個人都經歷過的生活例子,讓我們瞭解自己情緒之起源;更想讓大家注意的是,當它們出現時我們怎去「解釋」和「使用」這些情緒,使之配合這個複雜而幻變的世代。若每個人能「明瞭」、「應用」自己的情緒,做到情緒只能「服務」於我的利益,我們就不會再受到所謂負面情緒的困擾,因為那刻對你來說,情緒已沒有好壞之分,又何來痛苦之理?
所以《解釋心理學:情緒只能服務於我的利益》的關鍵概念,唯有你才能「解釋」自己的情緒、詮釋你自己的存在意義;重點在於,若無法改變外部的客觀事實,請立即更改內部的主觀解釋,因為這時你會明白,原來人生重要的不是命運,而是面對命運的態度。
本書不是寫給「有識」之士看的,亦不作什麼學術研究。「解釋心理學」這個書名可能會令人出現混淆,因它用了「心理學」這個極專業名稱,但本書並非要去「解釋」傳統的心理學,只是想打破既定的學術框架,用純個人的經驗去「解釋」自己情緒之由來,是一個平凡人據其個人之生活體驗、每天有血有肉與人的短兵相接,所記錄下來的一些人生看法;用一種閒話家常的語言、盡量淺白的道理,藉以讓每個人了解自己「內在」的運作;因為我們身處一個極其壓抑的時代,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點心理問題、情緒困擾。
就心理學範疇而言,我討厭象牙塔式的學術探索,並非我害怕艱澀的學習過程,而是這種所謂的科研、對於真正的「用家」有什麼幫助?尤其心理學這麼個人化,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的一門學說,就如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指紋,絕對沒有一個人是相同的;道理相同,將心理學仿照科學方法論證的弊端在於――怎可用一個預設的學術框架去概括所有人的心路歷程、演變經過。
而更嚴重的是,各門各派的心理學專家、每天埋頭苦幹在研究的結果,其最終的成果都與中國宋朝儒家一脈相承者的朱熹一樣――格物致知。但「格物致知」對於現世的生活又有何益?因為,作為一個每天忙於生活的普通現代人,他最迫切追求的是另一個更實在的層次――格物致用。
美國二十世紀一位有名的心理學大師,被譽為「人本主義心理學精神之父」――亞伯拉罕‧哈羅德‧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 1908-1970)。《走向生命的巔峰:馬斯洛的人本心理學》一書說,馬斯洛對其母親,他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憎恨和根深蒂固的敵意。這種感情不僅存在於他的孩提時代,即便其母先他幾年辭世時也依然未減。他甚至拒絕參加母親葬禮。由於其母篤信宗教,在他年幼時經常以上帝的懲罰來威脅他,故而他後來逐漸形成了對宗教的不信任,甚至憎惡。他一度為對其母親的感情問題專門接受過心理治療,結果都無濟於事。
「能醫不自醫」的馬斯洛那股根深蒂固之憎恨,直到他母親離世也沒有消弭,直到1969年他自己謝世的前一年,馬斯洛曾這樣描述對自己母親的感情:我所有討厭、憎恨、拒絕的不僅是她的外表,而且還包括她的價值觀、世界觀,她的吝嗇、自私,以及對世界上任何其他人包括她丈夫和孩子都缺乏感情……她認為世上任何與她有分歧的人都是壞的,對她的孫子她也漠不關心,沒有朋友、大大咧咧、骯髒,與父母關係疏離,對她的兄妹亦沒有一點手足之情……我不知道我的烏托邦精神、道德感、人道主義、仁慈、愛、友誼及其他所有健康的感情來自何處,我僅能肯定這是母愛缺乏所帶來的後果。我的生活哲學研究、理論建構的動力,均源於對母親的憎恨、對其所支持的一切事物的拒絕。
坦白而言,馬斯洛的學說我並沒涉獵過多,但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其內心的一股憎恨,竟然在對方死後依然難以釋懷;甚至乎在自己行將就木之際,馬斯洛對母親的仇恨仍然縈繞心中揮之不去;我恕難苟同,也不認為這種深藏憎恨的人生有什麼「巔峰」可言。
我並非有意貶低他人的成就,亦無能力質疑心理學家們的論證,我只是個普通人,但我內心有種理念:一個哲學家不該怕死,一個心理學家不應受到情緒困擾,就如一個神父不能死於梅毒。好死不死,作為一個神父可以有千百種死法,但就是不能死於梅毒,因為這與你的身分不配嘛!換句話說,你的理論不可以違背你的實踐,連在自己身上也做不到,更遑論能有效地施展在其他人身上。
另一個有相同「陰影」、在心理學界更赫赫有名的――佛洛依德(Sigismund Schlomo Freud 1856-1939)。佛洛依德的「戀母情結」,從某角度觀之,也是另類走不出童年陰影的心理障礙。孩童時對自己母親的胴體有個「無意識」的生理遐想,不單是佛洛依德,就算是我、我更相信有很多少男都有過同樣的「回溯」,但這種無意識的「欲求」只是一閃而過,不曾在心中激起過任何波瀾,踏進青春期後更自動煙消雲散,可能有些人連一點記憶都沒了,因為這時個體會很正常地投入真實的異性欲求當中,而完全蓋過了那曾經有過的幼稚「幻想」。但那股對自己母親曾經有過之「欲求」,在佛洛依德長大後的很多年仍然令他思潮起伏,他說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情結。不錯,佛洛依德無法擺脫這種情結,所以當他看到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的故事時,立即獲得醍醐灌頂般的覺悟,並斷言:「在所有後來變為精神病患的兒童的精神生活中,他們的父母起了主要作用。」及後,佛洛依德並將這個故事設為框架,作為自己「戀母情結」學說的奠基,更成為他個人學派的獨創旗幟。
佛洛依德的「泛性」學說,強調童年時的第一次性衝動對個體一生有著多嚴重的影響,認為性壓抑是很多精神官能症的元兇,我們很多精神問題都因這些「欲念」未曾獲得滿足才會衍生;佛氏這種言論,處於當時已受到不少微言,在今天看來更是乏善可陳。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正常的現代男人不可能沒有「性壓抑」,就算生活在蠻荒時代或古代,除了極少數的部落領袖與一些帝王之外,也不是每個男人發現有「心儀」的女人都能與之交配,隨時都可獲得性滿足。更何況,我們的「內在」又是極其複雜的構造,怎可用一種「泛性」理論,認為性欲一旦獲得滿足,個體便能萬事俱休?因為大家都明白,人除了性,「內在」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欲求,做愛和吃飯絕對不是人生的最終意義,反而當吃飯與做愛過後,人生的意義才真正開始。
一個人若不自覺心理有點問題,很少會去翻閱有關心理學的書籍;更有些人因想瞭解自己的心理問題,才一頭栽進心理學這個範疇,最後因利乘便,成為了一代的心理學宗師;但這些大師很多都終生沉淪在自己的痛苦精神當中,美國的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患有嚴重抑鬱症和身心疾病,經常靠閱讀《聖經》來維持意志力;在1875年,當詹姆士成為哈佛大學心理學講師後,他的憂鬱症依然困擾著他,他經常這樣來勉勵自己:
「我要找一個能令自己再想存活多四小時的理由」
找一個令自己願意活下去的理由,詹姆士最終找到了,據說他在1878年精神狀況漸趨好轉,應該走出了憂鬱的陰霾;但詹姆士的學說、詹姆士所找到的「理由」,只是在他自己身上「驗證」過,並不一定適合你,就如,不是每個人都能靠閱讀《聖經》來維持意志力。心理學書籍有很多人閱讀,因為每個人對自己的「內在」都會有興趣,但有多少人能學以致用,為什麼不能將學到的理論實踐在日常生活中?我並非指責心理學家們寫的書籍、提出的論證都是耍嘴皮的紙上談兵,只是他們太過注重學術方法上的研究,而忽略了真正「用家」是有血有肉與人每天短兵相接的人。所以,馬斯洛也好,詹姆士也好,佛洛依德也好,一眾心理學宗師也罷,他們只是埋頭苦幹在做「學術研究」;但一涉及研究就會走向科學性的系統論證,導致與「實際心理」情況愈走愈遠,因此,這些所謂研究最終也只能停留於學院式的層面,難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當一個普通人自覺心理有點問題,於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去認識心理學,最後,讀懂了一大堆艱澀的專業名詞、明白了一大批深奧的學術理論,但回頭一望,原來這些東西對他的生活完全沒有幫助。為什麼會沒有幫助?因為這些學院式的研究,他們的重點是在於研究問題並非解決問題。
在幾十億年的地球歷史中,人類的出現最多只有六百萬年,進入文明最多也只是一萬年,為什麼只有等到人類的出現地球才開始被瞭解?究竟是神創造了世界,還是人創造了神?
這些惱人的哲學問題,你不去問就不會有問題。英國哲學家羅素曾經說過,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他不會浪費時間去讀哲學,因為哲學的最主要功能:不是讓平凡人變得聰明,而是讓聰明人知道,自己並非如想像般那麼優秀。所以問題的重點,你只是個平凡人,去問這些問題對你的人生有何獲益?換句話說,每個讀心理學書籍的普通讀者,最關心的只是自己一些心理上、情緒中的疑問,並沒興趣亦無能力作深奧的探討。
坊間大部分的心理學書籍,什麼「心理學原理」、「心理咨詢」、「情緒管理」的呀,都是某些心理學「大師」依憑個人之心理運作而立論,滿書都是學述性研究、艱澀的專業用詞;目的在於鞏固其論證、想用科學之手段歸納出一套權威的心理學派系,多於幫助有心理障礙的人解決問題。這些紙上談兵的書籍,一般人要讀懂都非常艱苦,更何況能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大千世界,色相紛亂繁雜,不是每種東西的「設置」,都是為了給人類的智慧去了解的;況且,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智慧」,硬塞一些對他來說並沒有「用處」的東西給他去了解,對其個人的意義何在?生命太短促了,而人又是欲望的組合,要在生命的瞬間去解釋、攫取自己的存在意義。所以這本書探討的主題,不是心理之原型、謝絕一切學院式的研究、摒棄任何艱澀的詞彙和所謂的學術理論;就像一把「奧卡姆剃刀」,將那些令人感到厭煩的爭論、一些既累贅又空洞無物之普遍性概念,引刀成一快地無情剃除。盡量用淺白的語言,或一些每個人都經歷過的生活例子,讓我們瞭解自己情緒之起源;更想讓大家注意的是,當它們出現時我們怎去「解釋」和「使用」這些情緒,使之配合這個複雜而幻變的世代。若每個人能「明瞭」、「應用」自己的情緒,做到情緒只能「服務」於我的利益,我們就不會再受到所謂負面情緒的困擾,因為那刻對你來說,情緒已沒有好壞之分,又何來痛苦之理?
所以《解釋心理學:情緒只能服務於我的利益》的關鍵概念,唯有你才能「解釋」自己的情緒、詮釋你自己的存在意義;重點在於,若無法改變外部的客觀事實,請立即更改內部的主觀解釋,因為這時你會明白,原來人生重要的不是命運,而是面對命運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