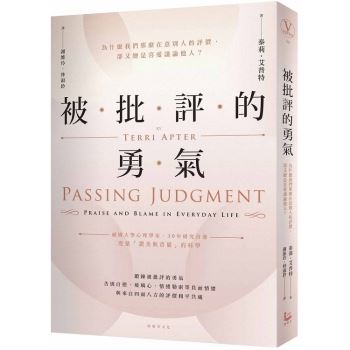●別用「專制型讚美」操控伴侶
讚美具有很多功能,可以用來發揮影響力、指派角色與篡代別人的評判量尺。當讚美關閉傾聽功能時、當讚美不再回應對方的欲望和需求時,它就會變成「專制型讚美」,變成儼然是施恩於人、操縱他人,有時甚至是對其恐嚇脅迫。
珍妮在吉爾出差之前,交給他剛從乾洗店取回來的西裝,吉爾就說:「你記性真好!我完全忘記這件事了。你總是這麼體貼,要是少了你,我就麻煩大了。」他正在表示讚賞,而且是針對小舉動表達溫暖、具同理心的感恩之情,這在夫妻間的讚美中至關重要。不過,吉爾的訊息同時也勾勒出他想要妻子扮演的角色:他特別提到珍妮體貼,是得力幫手,讓他免受自身忙亂所害。
這或許只是個人能力的正常分工,但當再三重申「你好體貼」時,它可能就有暗示作用,提醒吉爾指望和要求珍妮成為哪種人。在吉爾下次出差的前一天,珍妮告訴他:「你打包行李前,得先去拿回一堆乾洗衣物喔!」然後吉爾說:「超體貼的你可以去拿嗎?」 接下來他驚愕到說不出話,因為珍妮大發雷霆吼道:「我超討厭你這樣說!」在她看來,這種讚美已經成為壓力,而不是讚賞。
當艾莉克絲向葛拉漢提議為三歲兒子找個全職保母時,她提出經過縝密思考的論點。她推算過加長工作時數後,自己可以增加的收入;她特別強調,傍晚有個人幫忙能大幅減輕她晚上的緊繃與疲勞。葛拉漢邊聽邊看著那些數字,反覆思考之後說:「可是你是這麼棒的媽媽,我實在很難想像有誰能像你這麼好耶!你是照顧兒子的最佳人選啊!」
這是給予極度重要特質的高度評價。能成為照顧自己孩子的最佳人選,誰會不開心啊?但這個讚美也同時漠視了艾莉克絲的看法。就在葛拉漢的讚美喚起涉及孩子福祉的情感關聯,也召來完全圍繞於母親職責的強大文化勢力時,她準備好的成本收益分析全被摧毀。●家庭對情緒的評判
在某些家庭裡,除了快樂,其他情緒都是不可取的。珊曼參加我的中年人研究時,提到她母親:「每當我沮喪時,她的焦慮就會噴發。她不會看著我,而是藉由哼歌填補沉默。我會覺得生氣又羞愧。」聽到孩子以相當負面消極的方式陳述自己的生活(我覺得一無是處、我感覺好像快滅頂了、我不知道怎麼過下去),任何父母都會心煩意亂。孩子訴說的事有些是難得聽到,有的則是發出有麻煩的訊號,但父母拒絕傾聽孩子的感受,執意要求:「你真的不可以這樣想!」或「你怎麼可以說出這種話?」,就是傳達出責備的訊息。
然而在有些家庭裡,正面積極的情緒反而會受到責備。對無法感受喜悅的家族成員來說,興奮與欣喜之類的情緒會被當成是一種冒犯。著有《壞母親》的佩格.史翠普在書中提到,她家的評判系統是禁止喜悅開心的。史翠普的母親會因為女兒的快樂而惱怒與反感,她的論點是:「我如果沮喪失望,那其他人就不該覺得日子很快活。」遇到類似狀況的還有卡勒斯,他是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期待父母鮑伯和瑪莉亞能分享他獲頒獎學金的興奮之情,但瑪莉亞認為:「卡勒斯的一切都來得很容易,他以為能拿到獎學金全是憑他一己之力。他都沒感激我們的付出。」然後鮑伯就說:「他迫不及待想離開我們。」透過譴責卡勒斯的快樂,鮑伯和瑪莉亞抵消了彼此的焦慮和怨憤。鮑伯表示:「他還沒搞清楚狀況,不該就這麼興奮。」瑪莉亞的總結就是:「他向來不替人著想。他應該多考慮一下別人工作上的壓力,不該當面炫耀自己。」對鮑伯和瑪莉亞來說,卡勒斯的成功威脅到他們與兒子之間的連結,因此覺得卡勒斯的興奮隱含對他們的否決、批評和責備。
●蒐集情報、尋求盟友:職場的評判風向
個人的評判在職場中,擁有十分強大的職業影響力。管理者針對一位副理的領導能力徵詢回饋意見,聽到「她做簡報時,總會搞砸事情」的時候,原先對該名副理尚未形成的評判,便會轉變成絕對負面的評判;但若聽到「太有趣了!我好喜歡她脫稿行事的方式」時,對於該名副理在簡報中不太精練的部分,也會一掃疑慮。同樣的,競爭者或許也會在簡報上給予同事錯誤資訊,讓同事的預測失準,試圖藉此在專案上取得優勢。這種競爭者可以透過隨口警告別人的方式來灌輸懷疑:「別相信他的預測。他老是胸有成竹,但一直誤判。」運用巧妙的手腕,職場八卦就是快速、有效率與具殺傷力的傳達讚美與責備的媒介。
這種挾帶權威光環、再三複述的評判,會變成猶如事實般深植人心,之後要再提出異議就難上加難。被人講成「一直誤判」的同事或許會抗議:「我的預測通常是正確的,沒有一個預測者的推斷每次都能準確無誤啊!」但萬一他不明白別人背地裡對他的意見、不知道別人已經準備要提防他的錯誤,那他就無力為自己辯護了。
我們或許未能耳聞負面八卦,但可以感覺到。有時候,它對我們的工作有正向效應:知道自己是同事的八卦話題,會提高我們想協力合作的動機。但我們常常在談話時,捕捉到同事的微表情,以及他們之間迅速互瞥的眼神,這時職場就成了危險的地方,它包圍在背後議論與不定形的指控藩籬中。神經科學家理查.戴維森發現:「例如,要是你沒掌握懷怨競爭者之間互傳的無聲訊息,就無法與同事互動,那你極可能無法在未分心的最佳狀態中,正常工作。」起初無稽的八卦,最終演變成事實:我們無法專心,也喪失信心,執行能力深受其害,然後我們就這樣證實了負面評判所言不假。
●網路的惡意留言,反更引人關注
在社群媒體上,負面否定的留言與正面肯定的留言有相同的特性。它們都一樣含糊不清、令人費解,我們會反覆思考一些無法辯駁的問題,例如:為什麼這些回應如此負面?為何大家這麼反對我?什麼事讓他們這麼生氣?伊旺一直查看自己的手機,想搞清楚自己貼文下的那些負面否定留言。他解釋道:「我想知道他們是看我哪裡不順眼。」社群媒體上的糟糕體驗,看來似乎會讓人斷了使用它的念頭,但其實不然。我們反而會上癮,這時我們的做法就像遇到帶有自己負面消息的八卦,或者有人侮辱自己一樣,深陷於追蹤別人如何談論我們。因為執迷於評判,我們就很難對負面否定評判置之不理,不去爭辯、糾正或報復。
●網路霸凌:當評判不被當成人際交往的行為
「你可以先自我了結嗎?」在美國社群問答網站Ask.fr上,有個使用者這樣要求十六歲的潔西卡‧藍尼。還有一名使用者稱她為「蕩婦」,另一名則稱她「去你的王八蛋」。當這些負面留言逐漸攀增,潔西卡的世界似乎被它們所填滿。她認定了斷生命都勝過忍受一連串的責備攻擊。
如今大家都知道這樁「網路霸凌」的悲劇後果,父母、老師和立法者對此高度關切。然而,這些做出抨擊行為的行凶者,動機令人費解。他們發動這個過程是要惹是生非嗎?或他們單純只想說出自己的心聲?他們發表的評判與他們的真實信念有何關聯?他們有病嗎?他們很惡毒嗎?他們是誰?
在社群媒體上抨擊別人的人,往往在其他環境中,會展現同理心、自制力,甚至包容力。他們的人際關係行為是敏銳、敏感的,沒有跡象顯示他們會在社群網站上變成霸凌者。這些人在社群媒體上會表露南轅北轍的性格,並非因為他們平常會隱藏真正黑暗的那一面,而是由於他們的評判量尺不再把他們的評論當作是人際關係行為。此時,他們就像是在電玩情境中做出回應,他們和自己對付的人不過就是電玩裡的人物。
●同溫層使你更自戀、觀點更僵化
雖然經常有人認為,社群媒體讓人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意見,但其實它比較可能吸引到的,是志趣相投的貼文。部分原因是我們對「誰值得信賴與誰不可信賴」的評判:我們都會傾向於認為,從朋友處得來的資訊和評判,會比源自不認識的人更可靠。當我們喜歡與讚賞的人表達的評判與自己不同時,我們可能會與對方交流看法,但也只會質疑:「為何你會這樣想?」與「你怎麼會被那個政客騙了?」但在社群媒體上,只會有個人檔案、只會有留言,所以沒有理由要去跟那些讓我們不安的人交流。
事實上,社群網站的使用者對於評判觀點與自己不契合的人,很可能就會取消追蹤(unfollow)或刪除好友(unfriend)。當我們不理會意見與自己不一致的留言,而且讀取愈多肯定自身觀點的貼文,也許就會有錯誤印象,以為所看的內容是證實自己的評判。再者,這些網站用來抓住使用者注意力的運算法則,是根據使用者早先已經觀看的內容去演算,進而提升使用者看到與自己同調的評判的機率。結果就產生了回音室(echo chamber,又稱「同溫層」):一個人表達一項意見的心聲,接著其他人以贊同回應,這就像身處密閉空間,人的回聲會傳回自己說過的每句話。這種回音室效應會降低提出懷疑與反思評判的動力。已有發現顯示,這會讓人對自身的觀點更僵化,甚至對不同的觀點更具敵意。人也因此變得不只是更帶偏見,而且對於厭惡效應肆虐所造成的傷害,更加冷血。●愚蠢的推文,讓人丟了飯碗
平時明智有理的人做出特別卑劣評判的類似例子,比比皆是。原本在美國紐約工作的賈絲汀‧薩柯休假去非洲旅行,途中發了推文提到:「奇怪的德國佬」和得愛滋病的非洲人。當時(二○一三年),賈絲汀是一家網路媒體公司很成功的公關部門資深主管。在工作上,她向來要快速評估一個措辭的聯想力、避免冒犯,並保護自己與雇主的尊嚴。然而,在數位裝置詭譎怪誕的隱蔽性時常引發的幼稚心態包圍下,賈絲汀的評論看來似乎(當下對她而言)是可愛、活潑,甚至慧黠。但在數小時內,她就遭到成千上萬的憤怒回應攻訐。一名Instagram使用者幸災樂禍地表示:「我們快看到這個……婊子捲鋪蓋走人了。」賈絲汀在公關領域的職涯宣告終結。
讚美具有很多功能,可以用來發揮影響力、指派角色與篡代別人的評判量尺。當讚美關閉傾聽功能時、當讚美不再回應對方的欲望和需求時,它就會變成「專制型讚美」,變成儼然是施恩於人、操縱他人,有時甚至是對其恐嚇脅迫。
珍妮在吉爾出差之前,交給他剛從乾洗店取回來的西裝,吉爾就說:「你記性真好!我完全忘記這件事了。你總是這麼體貼,要是少了你,我就麻煩大了。」他正在表示讚賞,而且是針對小舉動表達溫暖、具同理心的感恩之情,這在夫妻間的讚美中至關重要。不過,吉爾的訊息同時也勾勒出他想要妻子扮演的角色:他特別提到珍妮體貼,是得力幫手,讓他免受自身忙亂所害。
這或許只是個人能力的正常分工,但當再三重申「你好體貼」時,它可能就有暗示作用,提醒吉爾指望和要求珍妮成為哪種人。在吉爾下次出差的前一天,珍妮告訴他:「你打包行李前,得先去拿回一堆乾洗衣物喔!」然後吉爾說:「超體貼的你可以去拿嗎?」 接下來他驚愕到說不出話,因為珍妮大發雷霆吼道:「我超討厭你這樣說!」在她看來,這種讚美已經成為壓力,而不是讚賞。
當艾莉克絲向葛拉漢提議為三歲兒子找個全職保母時,她提出經過縝密思考的論點。她推算過加長工作時數後,自己可以增加的收入;她特別強調,傍晚有個人幫忙能大幅減輕她晚上的緊繃與疲勞。葛拉漢邊聽邊看著那些數字,反覆思考之後說:「可是你是這麼棒的媽媽,我實在很難想像有誰能像你這麼好耶!你是照顧兒子的最佳人選啊!」
這是給予極度重要特質的高度評價。能成為照顧自己孩子的最佳人選,誰會不開心啊?但這個讚美也同時漠視了艾莉克絲的看法。就在葛拉漢的讚美喚起涉及孩子福祉的情感關聯,也召來完全圍繞於母親職責的強大文化勢力時,她準備好的成本收益分析全被摧毀。●家庭對情緒的評判
在某些家庭裡,除了快樂,其他情緒都是不可取的。珊曼參加我的中年人研究時,提到她母親:「每當我沮喪時,她的焦慮就會噴發。她不會看著我,而是藉由哼歌填補沉默。我會覺得生氣又羞愧。」聽到孩子以相當負面消極的方式陳述自己的生活(我覺得一無是處、我感覺好像快滅頂了、我不知道怎麼過下去),任何父母都會心煩意亂。孩子訴說的事有些是難得聽到,有的則是發出有麻煩的訊號,但父母拒絕傾聽孩子的感受,執意要求:「你真的不可以這樣想!」或「你怎麼可以說出這種話?」,就是傳達出責備的訊息。
然而在有些家庭裡,正面積極的情緒反而會受到責備。對無法感受喜悅的家族成員來說,興奮與欣喜之類的情緒會被當成是一種冒犯。著有《壞母親》的佩格.史翠普在書中提到,她家的評判系統是禁止喜悅開心的。史翠普的母親會因為女兒的快樂而惱怒與反感,她的論點是:「我如果沮喪失望,那其他人就不該覺得日子很快活。」遇到類似狀況的還有卡勒斯,他是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期待父母鮑伯和瑪莉亞能分享他獲頒獎學金的興奮之情,但瑪莉亞認為:「卡勒斯的一切都來得很容易,他以為能拿到獎學金全是憑他一己之力。他都沒感激我們的付出。」然後鮑伯就說:「他迫不及待想離開我們。」透過譴責卡勒斯的快樂,鮑伯和瑪莉亞抵消了彼此的焦慮和怨憤。鮑伯表示:「他還沒搞清楚狀況,不該就這麼興奮。」瑪莉亞的總結就是:「他向來不替人著想。他應該多考慮一下別人工作上的壓力,不該當面炫耀自己。」對鮑伯和瑪莉亞來說,卡勒斯的成功威脅到他們與兒子之間的連結,因此覺得卡勒斯的興奮隱含對他們的否決、批評和責備。
●蒐集情報、尋求盟友:職場的評判風向
個人的評判在職場中,擁有十分強大的職業影響力。管理者針對一位副理的領導能力徵詢回饋意見,聽到「她做簡報時,總會搞砸事情」的時候,原先對該名副理尚未形成的評判,便會轉變成絕對負面的評判;但若聽到「太有趣了!我好喜歡她脫稿行事的方式」時,對於該名副理在簡報中不太精練的部分,也會一掃疑慮。同樣的,競爭者或許也會在簡報上給予同事錯誤資訊,讓同事的預測失準,試圖藉此在專案上取得優勢。這種競爭者可以透過隨口警告別人的方式來灌輸懷疑:「別相信他的預測。他老是胸有成竹,但一直誤判。」運用巧妙的手腕,職場八卦就是快速、有效率與具殺傷力的傳達讚美與責備的媒介。
這種挾帶權威光環、再三複述的評判,會變成猶如事實般深植人心,之後要再提出異議就難上加難。被人講成「一直誤判」的同事或許會抗議:「我的預測通常是正確的,沒有一個預測者的推斷每次都能準確無誤啊!」但萬一他不明白別人背地裡對他的意見、不知道別人已經準備要提防他的錯誤,那他就無力為自己辯護了。
我們或許未能耳聞負面八卦,但可以感覺到。有時候,它對我們的工作有正向效應:知道自己是同事的八卦話題,會提高我們想協力合作的動機。但我們常常在談話時,捕捉到同事的微表情,以及他們之間迅速互瞥的眼神,這時職場就成了危險的地方,它包圍在背後議論與不定形的指控藩籬中。神經科學家理查.戴維森發現:「例如,要是你沒掌握懷怨競爭者之間互傳的無聲訊息,就無法與同事互動,那你極可能無法在未分心的最佳狀態中,正常工作。」起初無稽的八卦,最終演變成事實:我們無法專心,也喪失信心,執行能力深受其害,然後我們就這樣證實了負面評判所言不假。
●網路的惡意留言,反更引人關注
在社群媒體上,負面否定的留言與正面肯定的留言有相同的特性。它們都一樣含糊不清、令人費解,我們會反覆思考一些無法辯駁的問題,例如:為什麼這些回應如此負面?為何大家這麼反對我?什麼事讓他們這麼生氣?伊旺一直查看自己的手機,想搞清楚自己貼文下的那些負面否定留言。他解釋道:「我想知道他們是看我哪裡不順眼。」社群媒體上的糟糕體驗,看來似乎會讓人斷了使用它的念頭,但其實不然。我們反而會上癮,這時我們的做法就像遇到帶有自己負面消息的八卦,或者有人侮辱自己一樣,深陷於追蹤別人如何談論我們。因為執迷於評判,我們就很難對負面否定評判置之不理,不去爭辯、糾正或報復。
●網路霸凌:當評判不被當成人際交往的行為
「你可以先自我了結嗎?」在美國社群問答網站Ask.fr上,有個使用者這樣要求十六歲的潔西卡‧藍尼。還有一名使用者稱她為「蕩婦」,另一名則稱她「去你的王八蛋」。當這些負面留言逐漸攀增,潔西卡的世界似乎被它們所填滿。她認定了斷生命都勝過忍受一連串的責備攻擊。
如今大家都知道這樁「網路霸凌」的悲劇後果,父母、老師和立法者對此高度關切。然而,這些做出抨擊行為的行凶者,動機令人費解。他們發動這個過程是要惹是生非嗎?或他們單純只想說出自己的心聲?他們發表的評判與他們的真實信念有何關聯?他們有病嗎?他們很惡毒嗎?他們是誰?
在社群媒體上抨擊別人的人,往往在其他環境中,會展現同理心、自制力,甚至包容力。他們的人際關係行為是敏銳、敏感的,沒有跡象顯示他們會在社群網站上變成霸凌者。這些人在社群媒體上會表露南轅北轍的性格,並非因為他們平常會隱藏真正黑暗的那一面,而是由於他們的評判量尺不再把他們的評論當作是人際關係行為。此時,他們就像是在電玩情境中做出回應,他們和自己對付的人不過就是電玩裡的人物。
●同溫層使你更自戀、觀點更僵化
雖然經常有人認為,社群媒體讓人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意見,但其實它比較可能吸引到的,是志趣相投的貼文。部分原因是我們對「誰值得信賴與誰不可信賴」的評判:我們都會傾向於認為,從朋友處得來的資訊和評判,會比源自不認識的人更可靠。當我們喜歡與讚賞的人表達的評判與自己不同時,我們可能會與對方交流看法,但也只會質疑:「為何你會這樣想?」與「你怎麼會被那個政客騙了?」但在社群媒體上,只會有個人檔案、只會有留言,所以沒有理由要去跟那些讓我們不安的人交流。
事實上,社群網站的使用者對於評判觀點與自己不契合的人,很可能就會取消追蹤(unfollow)或刪除好友(unfriend)。當我們不理會意見與自己不一致的留言,而且讀取愈多肯定自身觀點的貼文,也許就會有錯誤印象,以為所看的內容是證實自己的評判。再者,這些網站用來抓住使用者注意力的運算法則,是根據使用者早先已經觀看的內容去演算,進而提升使用者看到與自己同調的評判的機率。結果就產生了回音室(echo chamber,又稱「同溫層」):一個人表達一項意見的心聲,接著其他人以贊同回應,這就像身處密閉空間,人的回聲會傳回自己說過的每句話。這種回音室效應會降低提出懷疑與反思評判的動力。已有發現顯示,這會讓人對自身的觀點更僵化,甚至對不同的觀點更具敵意。人也因此變得不只是更帶偏見,而且對於厭惡效應肆虐所造成的傷害,更加冷血。●愚蠢的推文,讓人丟了飯碗
平時明智有理的人做出特別卑劣評判的類似例子,比比皆是。原本在美國紐約工作的賈絲汀‧薩柯休假去非洲旅行,途中發了推文提到:「奇怪的德國佬」和得愛滋病的非洲人。當時(二○一三年),賈絲汀是一家網路媒體公司很成功的公關部門資深主管。在工作上,她向來要快速評估一個措辭的聯想力、避免冒犯,並保護自己與雇主的尊嚴。然而,在數位裝置詭譎怪誕的隱蔽性時常引發的幼稚心態包圍下,賈絲汀的評論看來似乎(當下對她而言)是可愛、活潑,甚至慧黠。但在數小時內,她就遭到成千上萬的憤怒回應攻訐。一名Instagram使用者幸災樂禍地表示:「我們快看到這個……婊子捲鋪蓋走人了。」賈絲汀在公關領域的職涯宣告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