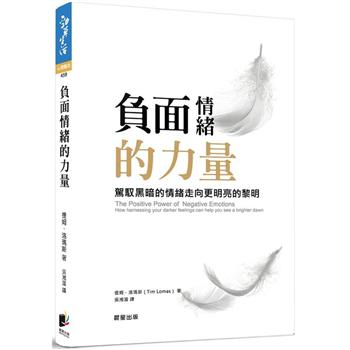第一章
悲傷
將悲傷做為我們踏上旅途的第一站,乍看似乎有點令人生畏。凝視著那個寂寞的深淵,我們已經手足發顫、全身籠罩在寒意裡。的確,當我開始思考寫作這一章時,我自己就覺得有點呼吸困難。如同許多人,我也時常感受到自己肩膀上的悲傷氣息,並且對深入那個黑暗,深覺惶恐。然而,用悲傷來開始我們的故事,也許更能讓我們領悟本書的關鍵訊息,那就是:所有的黑暗情緒,包括悲傷本身,不僅都是正常的,甚且是意想不到的意義與價值的源泉源。
聽起來或許有點令人吃驚。表面上看,悲傷顯然是一種完全無法彌補的感受——一種絕望、不容寬恕的狀況。當然,它也是快樂的反面論述,一種喜悅和快樂的絕對缺乏。沒錯,就某種意義而言,悲傷的確是一個黑暗、預示不幸的地方,一個很少人會主動選擇去拜訪的地方。因此,我無意當一個精明地站在路口、試圖向你推銷悲傷的陰暗人物。我的目的不是要將悲傷說得似乎很誘人或甚至很必要,彷彿我們非悲傷不可似的。這不是一本有關「應該怎麼做」的書。老天知道,我們已經承受太多負擔——包括那些我們應該如何感受及反應的壓力——卻沒有添增任何期望的砝碼。
但若悲傷降臨在我們身上——這是每個人偶爾都會有的遭遇——我們該怎麼辦呢?這是錯的嗎?我們應該感到羞愧、接受斥責、甚至以醫學方式處理嗎?或者,我們可以藉由承認它通常是一種完全自然且恰當的情緒,甚至矛盾地說是一種可以幫助我們成長的情緒,而跟它和平共處?
悲傷與憂鬱的區別
說到悲傷的潛在效能,我必須馬上強調,我現在要談的並非憂鬱——一種嚴重、深具破壞性、令人衰弱失能的疾病。沒錯,世界衛生組織早已做出令人憂心的預測:到2020年時,憂鬱將成為全球排名第二的失能負擔。當然,當我們企圖區別悲傷和憂鬱的不同時,那一灘水馬上就變得混濁了,因為這兩者間有許多複雜的重疊處。在經常使用的悲傷光譜上,我們看到悲傷會逐漸地變成憂鬱。然而,至關重要的是,那個光譜所呈現的並不是一個危險的滑坡,而在其上悲傷會處於最終將無情地滑入憂鬱的長期危險中。反之,悲傷光譜這個理念所代表的是:悲傷是正常的、自然的,是人類情況的一個固有(雖然不幸)的層面。話說回來,悲傷若變得足夠強烈,且(或)持續的時間不斷延長,那麼,它就可能會越過兩者之間的界線,成為憂鬱。當悲傷「出了問題」,悲傷變成憂鬱的時刻就會出現。至於那條界線可能在哪裡,我推薦大家參考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所制定的指標。最重要的是,假如你擔心自己可能有憂鬱的傾向,或者,如果你覺得自己真的有了任何一種精神疾病的問題,我的建議是,請儘快就醫,你的醫生將會提供你適當的輔導和協助。
然而,在提及一個人越過線變成憂鬱之前,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我們不能將正常的悲傷視作一種疾病。它是我們人性的一部份;用十四世紀教士湯瑪斯•金碧士的話說就是:它是「人類靈魂恰當的哀愁」之一。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們總是想用醫學的方式處理本書所討論的那些負面情緒,將它們視作需要用藥物治療的疾病。例如,在安東尼•霍威茲和傑若姆•威克菲爾德和著的書《悲傷的遺失》裡,他們就強調說:悲傷的寧靜尊嚴已經逐漸被侵蝕和遺忘了,已經被納入了憂鬱的醫學觀念裡。隨著這個侵蝕——受到如精神病學這類影響的驅使——悲傷很可能簡單地被視為一種輕微的憂鬱:比較不嚴重,當然,但仍然是錯誤,且令人不快的。近年來,在面對這個悲傷的隱伏侵蝕時,霍威茲和威克菲爾德已經開始引領了某種反向運動。這個運動企圖重建正常的悲傷,將之與臨床上的憂鬱區別開來,並承認它在一般人類情感的表單中,有其正當性的位置。
當悲傷以這樣的方式正常化時,它令人遺憾的普遍性和共通性,顯然就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沒有人對命運的無常、對震撼生命的失落或喪親之痛,無動於衷。在這些情況下,悲傷是全然恰當的反應。這類悲劇如此普遍,因此來自於它的溫馨提示,或許正能夠幫助我們培養某種程度的接受——既接受損失本身,也接受悲傷是一種正確的反應這個觀念。佛陀在2500多年前就採取了類似的立場;從那時候起,這個方式就一直在給予數以千萬計的人們安慰,無論是佛教徒還是非佛教徒。一個悲痛的母親,迦沙•喬達彌,陷入了失去孩子的極度痛苦中。悲痛之下,她向佛陀討取能夠使她的孩子神奇復活的靈藥。大慈大悲的佛陀說,祂可以幫這個忙,只要她能找來一把芥末子,並規定說,那一把芥末子必須從一個從未失去所愛之人的家庭裡取得。迦沙挨家挨戶可憐巴巴地去問,希望能找到一個從未承受過這種喪親之痛的人家。不用說,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悲傷的故事;他們與迦沙分享自己的悲傷,並在彼此共有的悲傷中建立起連結。雖然這並不能減緩迦沙的悲傷,但她與那些跟她承受類似喪親之痛的人們之間的交流卻讓她明白,悲傷是人性的一部份。最終,她學會了接受自己的失落,同時瞭解到,死亡是人類存在固有的一環。
在以這樣的方式培養「接受」時,佛陀提到了「兩支箭」。當我們失去某個人時,我們會被強烈的悲痛刺穿。這樣的痛,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痛,就是第一支箭,一支本身便足以重創我們的箭。但我們也總是對那個最早的反應產生反作用,於是開始對覺得悲傷感到悲傷(或者,譬如說,在另外一種狀況下,開始對覺得憤怒感到憤怒)。這種第二級反應——在心理學裡被稱之為「後設情緒」,也就是關於某種情緒的情緒)——就是那第二支箭。它所造成的創痛不亞於第一支,有時甚至更痛、更具破害性。要拔除第一支箭以減緩我們在經歷如喪親這樣的失去或受傷的感受,也許不可能;然而,假如我們願意努力接受自己的感受——或許可以將之視為我們在生命中某些時刻必須承載的負擔——那麼至少我們可以與它們和平共處,並藉此移除第二支箭所造成的痛苦。
我們不需成為佛教徒才能領悟「兩支箭」的觀念。誠然,佛教中的這個「接受」觀幾乎在每個宗教傳統及更廣泛的精神與療癒的論述裡,也都曾一再被強調過。例如,來自各行各業及各種宗教數不盡的人們都曾從美國神學家雷因霍爾德•尼布爾的名著《寧靜祈禱》一書裡獲得安慰和指引。那本書對接受觀有非常美麗的闡述:
上主,請賜給我接受我無法改變的事情的寧靜,
請賜給我改變我能夠改變的事情的勇氣,
也請賜給我能夠體會它們之中的不同的智慧。
然而,即使我們能夠視悲傷為正常,並因此而能與之和平共處時,我們仍可能會把它當作一種討厭的、不想要的情緒。某件事是「自然且正常的」,這樣的事實並不能賦予它正當性或高貴的情操。畢竟,疾病也是「自然的」,但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希望遠離疾病。然而,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在觀念上更進一步,並在悲傷中努力辨識出一些價值來。這麼做很重要,因為那意味著我們不僅能夠接受生命中悲傷的存在,並且學會了在某種程度上感激它。我們能夠理解到,即使悲傷有著憂鬱的面貌,它卻能扮演一個有用的角色,幫助我們擁有一個圓滿、充實的人生。基本上,我們之所以會悲傷,主要是因為我們所在意的人、地方、甚至事物受到了威脅、傷害,或遺失了。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便能瞭解,悲傷原來是「愛與關懷」的一種表達。
為了闡述這個理念並梳理其中的細微差別,請先將自己的內在想像成一個充滿了優雅、天使般的人物的地方。如同我在序裡所解釋的,提到這樣的人物時,我並不是在暗指任何不尋常的東西,或將它們比喻做那些通常與「瘋狂」有關聯的現象,例如幻聽或多重人格等。這些人物都是隱喻性的,是在我們內心中悲傷做為一種「關懷的表達」在運作的一系列不同的方式。在這一章裡,我們將遇見七個這樣的人物。而第一個就是,戰場軍醫。
戰場軍醫
有時,悲傷會在我們不知不覺中,慢慢地滲進我們的意識裡;有時,悲傷會在剎那間湧至,像一支大鐵鎚般,猛烈地將我們劈倒。
如同許多人,我也曾承受過肯定被認為很尋常的一種傷害:被愛人拋棄。雖然我後來明白,那種難過的事情當然不是世界末日,但在當時,我卻實實在在有那般感受。我在青少年時期,曾著迷於我的第一個女朋友。當時的我很天真,辜負了朋友、家人、以及最後我自己;為了那個新奇又刺激的感情,我犧牲了一切。墮落終於到頭,事情發生了。十八歲的我,在她念大學時,追隨她到一個遙遠的城市去。但不到一星期,她就丟開我,加入了她的新夥伴。我急驟下降,直接摔入悲傷裡。所有曾經同樣被如此拋棄過的,就能體會我當時所感受的痛苦。而且那個悲傷也不短暫;它縈繞在我心靈整整好幾個月。
所幸,我開始逐步重建自己。那是一個緩慢、往上的掙扎,包括了許多自我反省、嘗試新戀情、逃避到中國(此事我會在下一章詳述)、以及自信心和力氣的慢慢累積。然而,在那之前,我身陷黑暗中,長達幾個月。那是一段難熬的日子。除了被拋棄的悲傷,我同時也承受了其他一些傷害:背叛、困惑(我迷失在混亂的「為什麼」中)、受傷的自尊心、以及無邊無際的寂寞。奇怪的是,我竟然在那個遙遠的大學城裡待了三個月,沒有結識新朋友,沉浸在一種懊悔的自我放逐裡,我下定決心要撐到聖誕節來臨。我在一家鞋店打工(令人痛恨的工作),也在一家旅館裡短暫當過失敗的吧檯服務生(才上幾天班,我就因打破一張大玻璃桌而很丟臉的被解雇)。除此,我很少走出暫居的公寓。換言之,在深深的悲傷和痛苦中,我逃離了這個世界。這就是我們在這裡要討論的第一個悲傷角色:自我保護。
有時候,生命就像一座戰場,我們不可避免地會受傷,尤其是感情所造成的傷。回到本章主題,我們之所以會受傷,那是因為我們關懷某個人,因為我們愛他們;而那個關懷、那個愛,是一件珍貴的事。但是,我們也需要關愛自己,而悲傷正可以幫助這一點。當我們脆弱時,我們會抽離、會撤退,會催促自己去尋求庇護之所,以便遠離那傷害。這讓我們想到戰場上的軍醫,他在戰區中忙碌地拯救失去行動力的士兵,以防他們受到更大的傷害。當我們受到傷害,我們也因悲傷想逃離這個世界時,那就如同我們內在出現了這樣的一個軍醫。他衝到我們身邊,對我們說:「我們必須將你從這團混亂中撤離」,然後鼓舞我們緊急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休養並恢復力氣。
在心理學裡,這個保護機制有時就被視為某種形式的精神痛苦,與肉體的痛苦並列。辨識肉體痛苦的價值很容易——我們的身體發出訊號,告訴我們某個特別的刺激具有傷害性,而且(或者)我們已經受到創傷,因此,需要保護及治療的動作。我們碰觸火焰時所感受到的肉體痛苦,是我們學習火的危險所能夠擁有的最純粹、最直接的教訓。同然,我們手指燒傷所承受的肉體痛苦,便是身體在告訴我們,我們的皮肉已經受損、需要療護的方式。最後,我們終於學會了小心。悲傷所帶來的錐心般的情感痛苦,有時便擁有這樣的功能。某種情況具有傷害性,而且我們必須撤退到一個安全的距離——這就是一個內在的跡象。它就是我們內在的戰場軍醫,為了自我保護,正要將我們從戰場撤離。而若沒有這個撤退的誘因,我們便可能會繼續沉浸在傷害中,且因為脆弱而受到更嚴重的創傷。
我的悲傷最後促使我放棄前女友,並停止想要贏回她的一切徒勞。當然,我也曾因為某種古怪的絕望而衝動地想要接觸她、哀求她再給我們彼此一次機會,就好像神智不清的士兵企圖要回到戰場那般。所幸那樣絕望的時刻並不多,且越來越少。基本上,我的悲傷讓我放棄無謂的作戰,並放下我明白已經挽不回的那段感情。這非常的重要。當時雖然感到很痛苦,但長遠來看,那正是我需要的。我必須受苦、對那段關係感到絕望,如此才能撤離自己,並在最終走上一條較好的道路。
然而,一旦撤退,我們就必須修復、復原。這時,我們下一個悲傷的化身就該出現了——照護的護士。
保護的護士
軍醫也許能夠護送我們退出戰場,免於進一步傷害,但接下來呢?雖然短暫退出這個世界有其助益,但是容許這樣的撤離持續下去,卻是危險的事。畢竟,大多數的感情並非作戰,生命也不是經常位於戰區。何況,一旦復原,我們的人生還有許多重要的的事情待做。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應該試圖忘記我們的損失。以喪親為例:喪親之痛可能一直存在我們心中,而且那個傷痛可能正是我們與已經失去的所愛之人的連結。但我們仍然需要重拾自己、打理自己、並繼續生命的旅程。我們不斷前進,因為那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除此,既然我們不知道應該有何期待,我們更要懷抱希望,因為翻過地平線也許就是陽光燦爛的山谷。另一方面,如果脫離的狀況成為常態,如果悲傷持續存在,那我們很可能就會陷入患上憂鬱症的危機。
我並不是想藉此宣稱患上憂鬱症的臨界點在哪裡。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評估標準,連續兩周情緒低落,再加上其他一些徵狀(如渾身乏力)等,就是憂鬱症確診的依據。然而,這樣刻版的描述不見得永遠正確。譬如說,在我與女友分手後的連續幾個月悲傷期間,從「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指標來看,我可能已經學理性地得了憂鬱症。但從另一方面而言,在聽了我的故事後,一位敏感的醫生或許不會下這樣的診斷,反而可能會將我的憂鬱視作一個年輕人在感覺痛苦和迷失時的一種反應而已。所以,「可接受」的悲傷期也許因人而定,更視情況而定。話說回來,任何時候我都鼓勵你們去看醫生,如果你擔心自己的悲傷已經變得過度強烈且(或)持續延長的話。
當然,我們希望在受到照護後,能夠恢復健康,並覺得有了能力重新加入生命的旋轉。而這正是悲傷的第二個功能:在我們恢復力氣時,保護我們的安全。在戰場軍醫帶我們遠離傷害、將我們從痛苦的情境撤離後,悲傷可以確保我們停留在庇護所裡,直到我們足夠強壯、恢復行動力。從這方面來看,悲傷就像一名保護的護士,照顧著受傷的士兵,直到他們足夠健康,能靠自己的雙腳站立。神經生物學家認為這是一種「冬眠」的形式。如同某些動物會從冬天的酷寒中撤退,找一個溫暖的窩睡覺那般,悲傷也可以被視作一個黝暗卻具有療癒能力的繭。當我們受傷時,我們縮在裡面,保持我們的能量並補充我們的力氣。悲傷也就是那個護士溫柔、安撫的聲音,哄我們入眠,叮嚀我們平安健康地躺著,直到陽光來臨。
於是,在我們最脆弱的時候,悲傷保護我們、守衛我們。它完成這個使命的一個強大方式,便是引出我們身邊的人對我們的關懷。請想像一名你不認識的孩童在痛哭流涕,他很明顯地在悲傷。你會如何反應?我們多數人都會立即去幫助:那孩子的憂傷激起了人們想要伸出援手、給予安慰與協助的渴望。因此,說起來,悲傷及與之相關的動作(包括哭泣),會被視為「訊號行為」的一種有力形式,是有道理的。「發出訊號」能讓他人看見我們內在的世界,對周遭的人散播我們的情感狀態,並向他們警示我們的痛苦。它會吸引我們的保護者、照顧者、和有愛心的人——也就是看守我們並照顧我們恢復健康的守護天使們。
但是,在這個保護及恢復的復原階段,悲傷的功能不僅是引出他人的協助而已。透過進入冬眠這個動作,我們也獲得了一個機會,讓我們能夠審視並重新評估最先令我們落入這個低潮的事件與選擇。悲傷給我們總是要採取行動和顯得忙碌的瘋狂傾向一個喘息,而這個喘息給重要的質疑過程創造了時間與空間。有時候,我們就是需要在人生路途中暫停,並問自己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我要去哪裡?對我來說,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嗎?我為什麼在往這條道路前進?在停駐、疲憊、與脆弱中,我們甚至有可能在樹叢下發現生命中常因匆匆路過而忽略的某些清新小徑。我們看見之前未曾注意到的東西;曾經無明的洞察與瞭解也被開啟了。而就在這些清晰明瞭的時刻,我們遇見了悲傷的第三個化身——真相的見證人。
悲傷
將悲傷做為我們踏上旅途的第一站,乍看似乎有點令人生畏。凝視著那個寂寞的深淵,我們已經手足發顫、全身籠罩在寒意裡。的確,當我開始思考寫作這一章時,我自己就覺得有點呼吸困難。如同許多人,我也時常感受到自己肩膀上的悲傷氣息,並且對深入那個黑暗,深覺惶恐。然而,用悲傷來開始我們的故事,也許更能讓我們領悟本書的關鍵訊息,那就是:所有的黑暗情緒,包括悲傷本身,不僅都是正常的,甚且是意想不到的意義與價值的源泉源。
聽起來或許有點令人吃驚。表面上看,悲傷顯然是一種完全無法彌補的感受——一種絕望、不容寬恕的狀況。當然,它也是快樂的反面論述,一種喜悅和快樂的絕對缺乏。沒錯,就某種意義而言,悲傷的確是一個黑暗、預示不幸的地方,一個很少人會主動選擇去拜訪的地方。因此,我無意當一個精明地站在路口、試圖向你推銷悲傷的陰暗人物。我的目的不是要將悲傷說得似乎很誘人或甚至很必要,彷彿我們非悲傷不可似的。這不是一本有關「應該怎麼做」的書。老天知道,我們已經承受太多負擔——包括那些我們應該如何感受及反應的壓力——卻沒有添增任何期望的砝碼。
但若悲傷降臨在我們身上——這是每個人偶爾都會有的遭遇——我們該怎麼辦呢?這是錯的嗎?我們應該感到羞愧、接受斥責、甚至以醫學方式處理嗎?或者,我們可以藉由承認它通常是一種完全自然且恰當的情緒,甚至矛盾地說是一種可以幫助我們成長的情緒,而跟它和平共處?
悲傷與憂鬱的區別
說到悲傷的潛在效能,我必須馬上強調,我現在要談的並非憂鬱——一種嚴重、深具破壞性、令人衰弱失能的疾病。沒錯,世界衛生組織早已做出令人憂心的預測:到2020年時,憂鬱將成為全球排名第二的失能負擔。當然,當我們企圖區別悲傷和憂鬱的不同時,那一灘水馬上就變得混濁了,因為這兩者間有許多複雜的重疊處。在經常使用的悲傷光譜上,我們看到悲傷會逐漸地變成憂鬱。然而,至關重要的是,那個光譜所呈現的並不是一個危險的滑坡,而在其上悲傷會處於最終將無情地滑入憂鬱的長期危險中。反之,悲傷光譜這個理念所代表的是:悲傷是正常的、自然的,是人類情況的一個固有(雖然不幸)的層面。話說回來,悲傷若變得足夠強烈,且(或)持續的時間不斷延長,那麼,它就可能會越過兩者之間的界線,成為憂鬱。當悲傷「出了問題」,悲傷變成憂鬱的時刻就會出現。至於那條界線可能在哪裡,我推薦大家參考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所制定的指標。最重要的是,假如你擔心自己可能有憂鬱的傾向,或者,如果你覺得自己真的有了任何一種精神疾病的問題,我的建議是,請儘快就醫,你的醫生將會提供你適當的輔導和協助。
然而,在提及一個人越過線變成憂鬱之前,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我們不能將正常的悲傷視作一種疾病。它是我們人性的一部份;用十四世紀教士湯瑪斯•金碧士的話說就是:它是「人類靈魂恰當的哀愁」之一。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們總是想用醫學的方式處理本書所討論的那些負面情緒,將它們視作需要用藥物治療的疾病。例如,在安東尼•霍威茲和傑若姆•威克菲爾德和著的書《悲傷的遺失》裡,他們就強調說:悲傷的寧靜尊嚴已經逐漸被侵蝕和遺忘了,已經被納入了憂鬱的醫學觀念裡。隨著這個侵蝕——受到如精神病學這類影響的驅使——悲傷很可能簡單地被視為一種輕微的憂鬱:比較不嚴重,當然,但仍然是錯誤,且令人不快的。近年來,在面對這個悲傷的隱伏侵蝕時,霍威茲和威克菲爾德已經開始引領了某種反向運動。這個運動企圖重建正常的悲傷,將之與臨床上的憂鬱區別開來,並承認它在一般人類情感的表單中,有其正當性的位置。
當悲傷以這樣的方式正常化時,它令人遺憾的普遍性和共通性,顯然就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沒有人對命運的無常、對震撼生命的失落或喪親之痛,無動於衷。在這些情況下,悲傷是全然恰當的反應。這類悲劇如此普遍,因此來自於它的溫馨提示,或許正能夠幫助我們培養某種程度的接受——既接受損失本身,也接受悲傷是一種正確的反應這個觀念。佛陀在2500多年前就採取了類似的立場;從那時候起,這個方式就一直在給予數以千萬計的人們安慰,無論是佛教徒還是非佛教徒。一個悲痛的母親,迦沙•喬達彌,陷入了失去孩子的極度痛苦中。悲痛之下,她向佛陀討取能夠使她的孩子神奇復活的靈藥。大慈大悲的佛陀說,祂可以幫這個忙,只要她能找來一把芥末子,並規定說,那一把芥末子必須從一個從未失去所愛之人的家庭裡取得。迦沙挨家挨戶可憐巴巴地去問,希望能找到一個從未承受過這種喪親之痛的人家。不用說,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悲傷的故事;他們與迦沙分享自己的悲傷,並在彼此共有的悲傷中建立起連結。雖然這並不能減緩迦沙的悲傷,但她與那些跟她承受類似喪親之痛的人們之間的交流卻讓她明白,悲傷是人性的一部份。最終,她學會了接受自己的失落,同時瞭解到,死亡是人類存在固有的一環。
在以這樣的方式培養「接受」時,佛陀提到了「兩支箭」。當我們失去某個人時,我們會被強烈的悲痛刺穿。這樣的痛,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痛,就是第一支箭,一支本身便足以重創我們的箭。但我們也總是對那個最早的反應產生反作用,於是開始對覺得悲傷感到悲傷(或者,譬如說,在另外一種狀況下,開始對覺得憤怒感到憤怒)。這種第二級反應——在心理學裡被稱之為「後設情緒」,也就是關於某種情緒的情緒)——就是那第二支箭。它所造成的創痛不亞於第一支,有時甚至更痛、更具破害性。要拔除第一支箭以減緩我們在經歷如喪親這樣的失去或受傷的感受,也許不可能;然而,假如我們願意努力接受自己的感受——或許可以將之視為我們在生命中某些時刻必須承載的負擔——那麼至少我們可以與它們和平共處,並藉此移除第二支箭所造成的痛苦。
我們不需成為佛教徒才能領悟「兩支箭」的觀念。誠然,佛教中的這個「接受」觀幾乎在每個宗教傳統及更廣泛的精神與療癒的論述裡,也都曾一再被強調過。例如,來自各行各業及各種宗教數不盡的人們都曾從美國神學家雷因霍爾德•尼布爾的名著《寧靜祈禱》一書裡獲得安慰和指引。那本書對接受觀有非常美麗的闡述:
上主,請賜給我接受我無法改變的事情的寧靜,
請賜給我改變我能夠改變的事情的勇氣,
也請賜給我能夠體會它們之中的不同的智慧。
然而,即使我們能夠視悲傷為正常,並因此而能與之和平共處時,我們仍可能會把它當作一種討厭的、不想要的情緒。某件事是「自然且正常的」,這樣的事實並不能賦予它正當性或高貴的情操。畢竟,疾病也是「自然的」,但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希望遠離疾病。然而,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在觀念上更進一步,並在悲傷中努力辨識出一些價值來。這麼做很重要,因為那意味著我們不僅能夠接受生命中悲傷的存在,並且學會了在某種程度上感激它。我們能夠理解到,即使悲傷有著憂鬱的面貌,它卻能扮演一個有用的角色,幫助我們擁有一個圓滿、充實的人生。基本上,我們之所以會悲傷,主要是因為我們所在意的人、地方、甚至事物受到了威脅、傷害,或遺失了。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便能瞭解,悲傷原來是「愛與關懷」的一種表達。
為了闡述這個理念並梳理其中的細微差別,請先將自己的內在想像成一個充滿了優雅、天使般的人物的地方。如同我在序裡所解釋的,提到這樣的人物時,我並不是在暗指任何不尋常的東西,或將它們比喻做那些通常與「瘋狂」有關聯的現象,例如幻聽或多重人格等。這些人物都是隱喻性的,是在我們內心中悲傷做為一種「關懷的表達」在運作的一系列不同的方式。在這一章裡,我們將遇見七個這樣的人物。而第一個就是,戰場軍醫。
戰場軍醫
有時,悲傷會在我們不知不覺中,慢慢地滲進我們的意識裡;有時,悲傷會在剎那間湧至,像一支大鐵鎚般,猛烈地將我們劈倒。
如同許多人,我也曾承受過肯定被認為很尋常的一種傷害:被愛人拋棄。雖然我後來明白,那種難過的事情當然不是世界末日,但在當時,我卻實實在在有那般感受。我在青少年時期,曾著迷於我的第一個女朋友。當時的我很天真,辜負了朋友、家人、以及最後我自己;為了那個新奇又刺激的感情,我犧牲了一切。墮落終於到頭,事情發生了。十八歲的我,在她念大學時,追隨她到一個遙遠的城市去。但不到一星期,她就丟開我,加入了她的新夥伴。我急驟下降,直接摔入悲傷裡。所有曾經同樣被如此拋棄過的,就能體會我當時所感受的痛苦。而且那個悲傷也不短暫;它縈繞在我心靈整整好幾個月。
所幸,我開始逐步重建自己。那是一個緩慢、往上的掙扎,包括了許多自我反省、嘗試新戀情、逃避到中國(此事我會在下一章詳述)、以及自信心和力氣的慢慢累積。然而,在那之前,我身陷黑暗中,長達幾個月。那是一段難熬的日子。除了被拋棄的悲傷,我同時也承受了其他一些傷害:背叛、困惑(我迷失在混亂的「為什麼」中)、受傷的自尊心、以及無邊無際的寂寞。奇怪的是,我竟然在那個遙遠的大學城裡待了三個月,沒有結識新朋友,沉浸在一種懊悔的自我放逐裡,我下定決心要撐到聖誕節來臨。我在一家鞋店打工(令人痛恨的工作),也在一家旅館裡短暫當過失敗的吧檯服務生(才上幾天班,我就因打破一張大玻璃桌而很丟臉的被解雇)。除此,我很少走出暫居的公寓。換言之,在深深的悲傷和痛苦中,我逃離了這個世界。這就是我們在這裡要討論的第一個悲傷角色:自我保護。
有時候,生命就像一座戰場,我們不可避免地會受傷,尤其是感情所造成的傷。回到本章主題,我們之所以會受傷,那是因為我們關懷某個人,因為我們愛他們;而那個關懷、那個愛,是一件珍貴的事。但是,我們也需要關愛自己,而悲傷正可以幫助這一點。當我們脆弱時,我們會抽離、會撤退,會催促自己去尋求庇護之所,以便遠離那傷害。這讓我們想到戰場上的軍醫,他在戰區中忙碌地拯救失去行動力的士兵,以防他們受到更大的傷害。當我們受到傷害,我們也因悲傷想逃離這個世界時,那就如同我們內在出現了這樣的一個軍醫。他衝到我們身邊,對我們說:「我們必須將你從這團混亂中撤離」,然後鼓舞我們緊急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休養並恢復力氣。
在心理學裡,這個保護機制有時就被視為某種形式的精神痛苦,與肉體的痛苦並列。辨識肉體痛苦的價值很容易——我們的身體發出訊號,告訴我們某個特別的刺激具有傷害性,而且(或者)我們已經受到創傷,因此,需要保護及治療的動作。我們碰觸火焰時所感受到的肉體痛苦,是我們學習火的危險所能夠擁有的最純粹、最直接的教訓。同然,我們手指燒傷所承受的肉體痛苦,便是身體在告訴我們,我們的皮肉已經受損、需要療護的方式。最後,我們終於學會了小心。悲傷所帶來的錐心般的情感痛苦,有時便擁有這樣的功能。某種情況具有傷害性,而且我們必須撤退到一個安全的距離——這就是一個內在的跡象。它就是我們內在的戰場軍醫,為了自我保護,正要將我們從戰場撤離。而若沒有這個撤退的誘因,我們便可能會繼續沉浸在傷害中,且因為脆弱而受到更嚴重的創傷。
我的悲傷最後促使我放棄前女友,並停止想要贏回她的一切徒勞。當然,我也曾因為某種古怪的絕望而衝動地想要接觸她、哀求她再給我們彼此一次機會,就好像神智不清的士兵企圖要回到戰場那般。所幸那樣絕望的時刻並不多,且越來越少。基本上,我的悲傷讓我放棄無謂的作戰,並放下我明白已經挽不回的那段感情。這非常的重要。當時雖然感到很痛苦,但長遠來看,那正是我需要的。我必須受苦、對那段關係感到絕望,如此才能撤離自己,並在最終走上一條較好的道路。
然而,一旦撤退,我們就必須修復、復原。這時,我們下一個悲傷的化身就該出現了——照護的護士。
保護的護士
軍醫也許能夠護送我們退出戰場,免於進一步傷害,但接下來呢?雖然短暫退出這個世界有其助益,但是容許這樣的撤離持續下去,卻是危險的事。畢竟,大多數的感情並非作戰,生命也不是經常位於戰區。何況,一旦復原,我們的人生還有許多重要的的事情待做。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應該試圖忘記我們的損失。以喪親為例:喪親之痛可能一直存在我們心中,而且那個傷痛可能正是我們與已經失去的所愛之人的連結。但我們仍然需要重拾自己、打理自己、並繼續生命的旅程。我們不斷前進,因為那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除此,既然我們不知道應該有何期待,我們更要懷抱希望,因為翻過地平線也許就是陽光燦爛的山谷。另一方面,如果脫離的狀況成為常態,如果悲傷持續存在,那我們很可能就會陷入患上憂鬱症的危機。
我並不是想藉此宣稱患上憂鬱症的臨界點在哪裡。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評估標準,連續兩周情緒低落,再加上其他一些徵狀(如渾身乏力)等,就是憂鬱症確診的依據。然而,這樣刻版的描述不見得永遠正確。譬如說,在我與女友分手後的連續幾個月悲傷期間,從「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指標來看,我可能已經學理性地得了憂鬱症。但從另一方面而言,在聽了我的故事後,一位敏感的醫生或許不會下這樣的診斷,反而可能會將我的憂鬱視作一個年輕人在感覺痛苦和迷失時的一種反應而已。所以,「可接受」的悲傷期也許因人而定,更視情況而定。話說回來,任何時候我都鼓勵你們去看醫生,如果你擔心自己的悲傷已經變得過度強烈且(或)持續延長的話。
當然,我們希望在受到照護後,能夠恢復健康,並覺得有了能力重新加入生命的旋轉。而這正是悲傷的第二個功能:在我們恢復力氣時,保護我們的安全。在戰場軍醫帶我們遠離傷害、將我們從痛苦的情境撤離後,悲傷可以確保我們停留在庇護所裡,直到我們足夠強壯、恢復行動力。從這方面來看,悲傷就像一名保護的護士,照顧著受傷的士兵,直到他們足夠健康,能靠自己的雙腳站立。神經生物學家認為這是一種「冬眠」的形式。如同某些動物會從冬天的酷寒中撤退,找一個溫暖的窩睡覺那般,悲傷也可以被視作一個黝暗卻具有療癒能力的繭。當我們受傷時,我們縮在裡面,保持我們的能量並補充我們的力氣。悲傷也就是那個護士溫柔、安撫的聲音,哄我們入眠,叮嚀我們平安健康地躺著,直到陽光來臨。
於是,在我們最脆弱的時候,悲傷保護我們、守衛我們。它完成這個使命的一個強大方式,便是引出我們身邊的人對我們的關懷。請想像一名你不認識的孩童在痛哭流涕,他很明顯地在悲傷。你會如何反應?我們多數人都會立即去幫助:那孩子的憂傷激起了人們想要伸出援手、給予安慰與協助的渴望。因此,說起來,悲傷及與之相關的動作(包括哭泣),會被視為「訊號行為」的一種有力形式,是有道理的。「發出訊號」能讓他人看見我們內在的世界,對周遭的人散播我們的情感狀態,並向他們警示我們的痛苦。它會吸引我們的保護者、照顧者、和有愛心的人——也就是看守我們並照顧我們恢復健康的守護天使們。
但是,在這個保護及恢復的復原階段,悲傷的功能不僅是引出他人的協助而已。透過進入冬眠這個動作,我們也獲得了一個機會,讓我們能夠審視並重新評估最先令我們落入這個低潮的事件與選擇。悲傷給我們總是要採取行動和顯得忙碌的瘋狂傾向一個喘息,而這個喘息給重要的質疑過程創造了時間與空間。有時候,我們就是需要在人生路途中暫停,並問自己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我要去哪裡?對我來說,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嗎?我為什麼在往這條道路前進?在停駐、疲憊、與脆弱中,我們甚至有可能在樹叢下發現生命中常因匆匆路過而忽略的某些清新小徑。我們看見之前未曾注意到的東西;曾經無明的洞察與瞭解也被開啟了。而就在這些清晰明瞭的時刻,我們遇見了悲傷的第三個化身——真相的見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