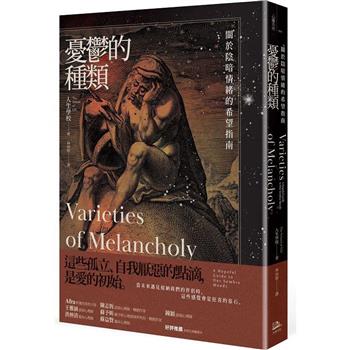【摘文1:內向與憂鬱】
憂鬱的人本質上也幾乎都是內向的人。現代世界標榜對待內向與外向者一視同仁,不過實際上,種種行動、獎賞和迷人特質都緊緊依附著外向陣營的天賦與感情。想要看起來正常或功成名就,個人就得使出渾身解數,對外向者來說,這是他們與生俱來的能力:使陌生人刮目相看、出席會議、發表演說、勝過對手、管理人們、以滿腔熱情參與活動、反映民意、社交、交遊廣闊、廣泛約會。
我們可能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會發現,儘管十分希望事實並不是如此,但無可否認的是,上述形象完全不是我們的本性。對我們來說,出席派對前不免擔心東、擔心西;發表演說前簡直緊張得要死;任何社交場合都是沉重的心理負擔;面對新聞和社群媒體常感心煩意亂;如果每天沒有幾個小時獨處、消化思緒,就渾身不自在;陌生的地方(尤其是臥房)令我們極度憂慮;不擅長在職場中對任何人負責;對於開懷玩樂極度謹慎,也對任何類型的集體狂熱退避三舍。我們並不討厭擁抱,但當有人衝上前擁抱我們,我們的身體會不自覺變得僵硬。
另一方面,我們喜愛待在家裡;我們很樂意一整個週末(甚至是好幾年)獨處,只要有幾本書和筆電的陪伴就行;整個世界上我們真正喜歡的人大概只有三個;我們喜歡探索自己心靈中的房間;知道如何坦白自己的弱點與焦慮的朋友令我們安心;我們希望再也不必出席派對;我們不會抱怨一切太過安靜;我們喜愛平和的風景與平淡無奇的日子。我們也很喜歡花。
不過這些特質卻使我們必須承擔現代世界的種種質疑:我們為何那麼羞怯?我們為何不能與其他人和樂共處?我們為什麼不願出門慶祝?我們的結論是自己很奇怪,可能病了,要到很久以後才會接受自己可能只是比較不一樣。
身為憂鬱的內向者,我們常緊抓著他人容易忽略的「小事」不放。派對或公司會議都可能令我們無比疲憊,因為我們要做的事不只有閒聊或發表意見,我們還會思索其他人對我們剛發表的言論有什麼看法;懷疑自己未能理解某個重要面向;角落某人古怪的敵意會令我們大吃一驚;擔心自己的臉做出某個不得體的愚蠢表情。被點名時,我們是人間喜劇的敏銳觀察者,但分分秒秒過去,過於在意別人的看法也令我們筋疲力盡。我們渴望人際聯繫,不過交往關係充滿地雷,尤其是剛開始的時候。對方對我們真正的想法是什麼?我們可以表達對他們的渴望嗎?他們會對我們感到反感嗎?難怪我們比較喜歡待在家裡讀書。
這聽起來不容易,不過內向的人生也可以非常豐富、充滿感激。我們很容易感到滿足,不需要喧囂與關注,不在乎哪裡舉辦大型派對。我們只想穿著自己平淡無趣的衣服四處閒逛,與少數我們能自在相處的人聊天,經常散散步或泡澡。只要細心觀察,不起眼的事物也可以很有趣。我們已經累積多少見識;踏上多少次旅途;讀過多少書;經歷過什麼樣的騷亂。我們真的不需要更多了。內向者已經做好充分準備,願意接納任何事件或人物的本質─任何令人生畏、強大、能引發共鳴、美麗或嚇人的成分。
小孩是天生的內向者。當陌生人進到房內時,他們會直覺地躲進照顧者的懷中。誰能怪他們呢?因為與孩子相比,陌生人那麼高大、聲音那麼奇怪、那麼自然而然地加入對話,而不是在旁謹慎地觀察一會兒(這才是自然的反應吧)。這些孩子也不需要太多外界刺激:紙箱蓋子怎麼都玩不膩;看著窗戶上的雨滴追逐彼此也饒富趣味;他們可以躺在臥房地板上,畫著一棵又一棵的樹,都沒發現已到了洗澡時間。此外,他們也很容易疲累,在熱鬧的生日派對上玩一個小時後就一定得回家小睡。
認識自己憂鬱而內向的一面不只是具詩意的自知,也對我們的心理健康有益,如果未能針對自己內向的個性做好妥善調適,我們很快就會不堪負荷並導致隨後的焦慮與猜疑。所謂的情緒崩潰通常單純是內向者迫切需要平靜、休息、自我同情與協調的表現。因此,經驗豐富的內向者知道自己必須抵抗外向世界的計謀。內向者的理智全賴他們有無能力堅守自己所需的保守日常作息。現在,我們至少能用「內向」來對他人解釋這種性格結構。下一步就是學習如何順從自己的個性,讓內向者過著他們性情所需的平靜生活。【摘文2:週日晚間與憂鬱】
憂鬱情緒通常約在下午五點至晚間七點半開始降臨,於六點達到高峰,此時天氣開始轉變,最後一道日光也將天空染成緋紅。
週日晚間的憂鬱感受常與工作有關,捨不得結束愉快的休息,不願返回辦公崗位。實際情況其實更為複雜,這個解釋無法完全說明。我們心情低迷的原因不只是明天有工作要做,而是因為那是不適合我們的工作,雖然我們也全然不知道適合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什麼。
我們內心都有一個所謂的「工作的自我」,這個自我擁有一套偏好和能力,渴望向現實原料施展影響力。我們想要在工作之中注入自己的重要元素,確保能在我們所提供的服務及產品中看見自己的樣子。這就是我們認知中的合適工作,我們需要合適工作就像我們需要愛一樣理所當然、一樣強烈。找不到職業歸屬就和尋不得親密伴侶一樣令人心碎。覺得自己入錯行、找不到真正的使命不是什麼小問題,反而可能是人生的核心危機。
週間我們通常可以不太去想這個問題,那時我們過於忙碌,受金錢的急迫需求所驅使。不過週日晚間,我們開始為這個問題煩擾。這個危機彷彿飄盪於兩個世界間的鬼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此只能猛敲意識的大門,要求一個答覆。我們感到傷心是因為,有一部分的自己意識到時間所剩不多,而我們現在的工作並不是餘生該做的事。週日晚間的痛苦來自意識的攪動,隱約叮嚀我們要在人生結束以前發揮更多潛力。週日晚間有其歷史。一直到最近以前,過去幾百年,能否透過工作表達真正自我只是少數人的問題。多數人工作是為了生存,能有最低收入就感激涕零。但現在我們的期望變高,由於看過夠多例子,我們知道真的有人這麼做,也就是是說,自己其實可以在商業引擎中運用自身真摯的天賦。我們知道自己不必在職場中悶悶不樂,也因此我們的無所作為只是徒增羞愧。
我們不應該這麼嚴苛對待自己。目前還沒有機制能把所有工作與有意義的天命配對在一起。因此雖然我們很確定現在這份工作不適合自己,卻也對真正的使命在何處茫然無知。
解決之道不外乎耐心與堅定的自我檢視。我們需要某些偵探技巧,或是學習考古學家拼湊破罐碎片的耐心。我們不該天真地用「週日憂鬱症」來解釋自己的煩憂,用喝酒和看影片來掩蓋這種情緒。我們應該將之視作一個核心問題,尋求埋藏在討好他人以及追逐地位與金錢等短期需求之下的真正自我。
換言之,我們不該只在週日晚間品嘗週日晚間的感受,而是應該把這些感受置於生活中心,用於敦促我們進行數月、甚至數年的持續探尋,鼓勵我們與自己、朋友、導師及專業人士對話討論。週日晚間的幾個小時中,悲傷與焦慮降臨是嚴重問題的徵兆。我們不只是因為兩天的休息即將告終而稍感困擾;我們難受的原因是:週日晚間提醒著我們,必須在為時已晚之前發掘真正的自我,還我們的天賦一個公道。
憂鬱的人本質上也幾乎都是內向的人。現代世界標榜對待內向與外向者一視同仁,不過實際上,種種行動、獎賞和迷人特質都緊緊依附著外向陣營的天賦與感情。想要看起來正常或功成名就,個人就得使出渾身解數,對外向者來說,這是他們與生俱來的能力:使陌生人刮目相看、出席會議、發表演說、勝過對手、管理人們、以滿腔熱情參與活動、反映民意、社交、交遊廣闊、廣泛約會。
我們可能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會發現,儘管十分希望事實並不是如此,但無可否認的是,上述形象完全不是我們的本性。對我們來說,出席派對前不免擔心東、擔心西;發表演說前簡直緊張得要死;任何社交場合都是沉重的心理負擔;面對新聞和社群媒體常感心煩意亂;如果每天沒有幾個小時獨處、消化思緒,就渾身不自在;陌生的地方(尤其是臥房)令我們極度憂慮;不擅長在職場中對任何人負責;對於開懷玩樂極度謹慎,也對任何類型的集體狂熱退避三舍。我們並不討厭擁抱,但當有人衝上前擁抱我們,我們的身體會不自覺變得僵硬。
另一方面,我們喜愛待在家裡;我們很樂意一整個週末(甚至是好幾年)獨處,只要有幾本書和筆電的陪伴就行;整個世界上我們真正喜歡的人大概只有三個;我們喜歡探索自己心靈中的房間;知道如何坦白自己的弱點與焦慮的朋友令我們安心;我們希望再也不必出席派對;我們不會抱怨一切太過安靜;我們喜愛平和的風景與平淡無奇的日子。我們也很喜歡花。
不過這些特質卻使我們必須承擔現代世界的種種質疑:我們為何那麼羞怯?我們為何不能與其他人和樂共處?我們為什麼不願出門慶祝?我們的結論是自己很奇怪,可能病了,要到很久以後才會接受自己可能只是比較不一樣。
身為憂鬱的內向者,我們常緊抓著他人容易忽略的「小事」不放。派對或公司會議都可能令我們無比疲憊,因為我們要做的事不只有閒聊或發表意見,我們還會思索其他人對我們剛發表的言論有什麼看法;懷疑自己未能理解某個重要面向;角落某人古怪的敵意會令我們大吃一驚;擔心自己的臉做出某個不得體的愚蠢表情。被點名時,我們是人間喜劇的敏銳觀察者,但分分秒秒過去,過於在意別人的看法也令我們筋疲力盡。我們渴望人際聯繫,不過交往關係充滿地雷,尤其是剛開始的時候。對方對我們真正的想法是什麼?我們可以表達對他們的渴望嗎?他們會對我們感到反感嗎?難怪我們比較喜歡待在家裡讀書。
這聽起來不容易,不過內向的人生也可以非常豐富、充滿感激。我們很容易感到滿足,不需要喧囂與關注,不在乎哪裡舉辦大型派對。我們只想穿著自己平淡無趣的衣服四處閒逛,與少數我們能自在相處的人聊天,經常散散步或泡澡。只要細心觀察,不起眼的事物也可以很有趣。我們已經累積多少見識;踏上多少次旅途;讀過多少書;經歷過什麼樣的騷亂。我們真的不需要更多了。內向者已經做好充分準備,願意接納任何事件或人物的本質─任何令人生畏、強大、能引發共鳴、美麗或嚇人的成分。
小孩是天生的內向者。當陌生人進到房內時,他們會直覺地躲進照顧者的懷中。誰能怪他們呢?因為與孩子相比,陌生人那麼高大、聲音那麼奇怪、那麼自然而然地加入對話,而不是在旁謹慎地觀察一會兒(這才是自然的反應吧)。這些孩子也不需要太多外界刺激:紙箱蓋子怎麼都玩不膩;看著窗戶上的雨滴追逐彼此也饒富趣味;他們可以躺在臥房地板上,畫著一棵又一棵的樹,都沒發現已到了洗澡時間。此外,他們也很容易疲累,在熱鬧的生日派對上玩一個小時後就一定得回家小睡。
認識自己憂鬱而內向的一面不只是具詩意的自知,也對我們的心理健康有益,如果未能針對自己內向的個性做好妥善調適,我們很快就會不堪負荷並導致隨後的焦慮與猜疑。所謂的情緒崩潰通常單純是內向者迫切需要平靜、休息、自我同情與協調的表現。因此,經驗豐富的內向者知道自己必須抵抗外向世界的計謀。內向者的理智全賴他們有無能力堅守自己所需的保守日常作息。現在,我們至少能用「內向」來對他人解釋這種性格結構。下一步就是學習如何順從自己的個性,讓內向者過著他們性情所需的平靜生活。【摘文2:週日晚間與憂鬱】
憂鬱情緒通常約在下午五點至晚間七點半開始降臨,於六點達到高峰,此時天氣開始轉變,最後一道日光也將天空染成緋紅。
週日晚間的憂鬱感受常與工作有關,捨不得結束愉快的休息,不願返回辦公崗位。實際情況其實更為複雜,這個解釋無法完全說明。我們心情低迷的原因不只是明天有工作要做,而是因為那是不適合我們的工作,雖然我們也全然不知道適合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什麼。
我們內心都有一個所謂的「工作的自我」,這個自我擁有一套偏好和能力,渴望向現實原料施展影響力。我們想要在工作之中注入自己的重要元素,確保能在我們所提供的服務及產品中看見自己的樣子。這就是我們認知中的合適工作,我們需要合適工作就像我們需要愛一樣理所當然、一樣強烈。找不到職業歸屬就和尋不得親密伴侶一樣令人心碎。覺得自己入錯行、找不到真正的使命不是什麼小問題,反而可能是人生的核心危機。
週間我們通常可以不太去想這個問題,那時我們過於忙碌,受金錢的急迫需求所驅使。不過週日晚間,我們開始為這個問題煩擾。這個危機彷彿飄盪於兩個世界間的鬼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此只能猛敲意識的大門,要求一個答覆。我們感到傷心是因為,有一部分的自己意識到時間所剩不多,而我們現在的工作並不是餘生該做的事。週日晚間的痛苦來自意識的攪動,隱約叮嚀我們要在人生結束以前發揮更多潛力。週日晚間有其歷史。一直到最近以前,過去幾百年,能否透過工作表達真正自我只是少數人的問題。多數人工作是為了生存,能有最低收入就感激涕零。但現在我們的期望變高,由於看過夠多例子,我們知道真的有人這麼做,也就是是說,自己其實可以在商業引擎中運用自身真摯的天賦。我們知道自己不必在職場中悶悶不樂,也因此我們的無所作為只是徒增羞愧。
我們不應該這麼嚴苛對待自己。目前還沒有機制能把所有工作與有意義的天命配對在一起。因此雖然我們很確定現在這份工作不適合自己,卻也對真正的使命在何處茫然無知。
解決之道不外乎耐心與堅定的自我檢視。我們需要某些偵探技巧,或是學習考古學家拼湊破罐碎片的耐心。我們不該天真地用「週日憂鬱症」來解釋自己的煩憂,用喝酒和看影片來掩蓋這種情緒。我們應該將之視作一個核心問題,尋求埋藏在討好他人以及追逐地位與金錢等短期需求之下的真正自我。
換言之,我們不該只在週日晚間品嘗週日晚間的感受,而是應該把這些感受置於生活中心,用於敦促我們進行數月、甚至數年的持續探尋,鼓勵我們與自己、朋友、導師及專業人士對話討論。週日晚間的幾個小時中,悲傷與焦慮降臨是嚴重問題的徵兆。我們不只是因為兩天的休息即將告終而稍感困擾;我們難受的原因是:週日晚間提醒著我們,必須在為時已晚之前發掘真正的自我,還我們的天賦一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