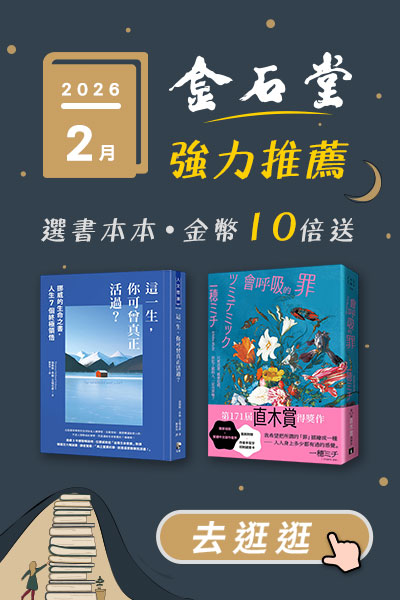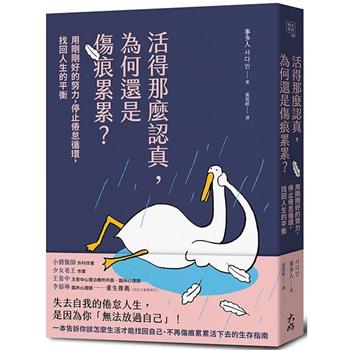讓我們更疲憊的虛偽自尊
被診斷出恐慌症與憂鬱症後,我開始心理諮商。過程中我回首過往十年,發現自己的自尊大幅低落,是源於我努力地想適應各種環境。從得到這兩種病症的結果來看,很明顯地,我過去的選擇是有問題的。
「好像不應該開心」的不安感
自從請了病假,我待在家裡的時間變長,卻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多出來的時間,只能不停地找事做。洗碗、打掃、洗衣服、整理抽屜、擦拭鞋櫃裡的所有鞋子、將用不到的東西放到網路拍賣、替大型盆栽換盆……直到沒事可做。
「醫生,我在家關不住。該怎麼說呢?我覺得自己很懶散。」
「你是不是覺得很不安?」
「好像是。我打掃、洗衣,能做的都做了,還是一直想找事來做。不停地胡思亂想,超過大腦的負荷……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你之前說想舒舒服服地待在家裡,現在可以盡情休息了,坐下來畫畫也不錯呀。」
「我倒是沒想過畫畫呢。」
突然擁有了大量的空白時間,卻不知該怎麼打發。做點小事確實能輕鬆獲得成就,但我不斷找事做的原因,與其說是為了成就感,不如說是因為不安感。我可以看想看的電影、畫畫或者讀詩,但總覺得做這些事好像沒什麼意義。
「做這些事,是不是毫無用處呀?」
我無法輕易放過自己,「現在是提升自我價值的好機會」、「玩樂沒用」這類想法依然在腦中盤旋,所以一直強迫自己找事做。
我覺得自己沒資格過得開心並享受人生樂趣,我的不安感源自「恐懼」和「愧疚」。我害怕過去努力累積的職涯中斷、害怕喪失實務工作的感覺、對自己把知識與能力埋沒在家中感到內疚、讓丈夫獨自養家活口充滿抱歉,同時也愧對接手的同事。
我的休息,讓這些情緒猛烈地反抗,不停地強迫我找事做,更不容許我抱持著「自己是因為生病才請假」的想法顧影自憐。
抹掉自我的社會面具
「這段時間的所有努力,會不會化為烏有?」
我害怕迄今為止用來支撐我的東西崩塌了。而我也逐漸明白,恐懼的背後隱藏著一個不堅定的真正自尊。不過我始終相信畢業的學校、就職的公司、職位、年薪、住所等等,這些拿得出手的背景是帶給我幸福的支柱。
只是這種幸福沒能持續多久。表面上我以為自己不再受華麗膚淺的事物左右,實際上沒有方向的生活,正在劇烈搖晃著我的人生。
於是我深信只要努力就能過上好生活,這成了支撐我、證明我自己的唯一信念。然而,這不過是另一個「虛假自尊」罷了,是另一個「面具」。
比起以「自己」的身分生活,許多人更習慣戴上面具後的身分。因為活在這世上,面具相當好用,它能幫助我們完美承擔起某人的子女、妻子、丈夫、父母或員工等多種角色的責任,有時也能自我保護。
很多時候,當我們適應了自己扮演的角色,我們會用「大家都是這樣生活的」為藉口來壓抑自己,不顧藏在面具後高喊著「不能這樣」的真實自我。
每個人都在適應這世界,即使我們扮演的角色不符合意願與天性。我們漸漸習慣戴著面具活出社會想要的樣子,也就慢慢遺忘了真正的自我。
然而,面具無法支撐我們度過無數考驗,必須懂得擁抱脫下面具後的真實自我。
我們需要一個不在意我是什麼模樣、在哪裡做些什麼,都會無條件愛著我們的人。那個人不會是父母,也不是配偶,而應該是你自己。
當你能成為「即使自己不努力奮發也會支持並守護自己」的人,就能脫下面具,用堅定的自尊過生活。
如果不能放棄想被他人愛、被他人肯定的渴望,那麼就算我們再富有、再寬裕,也永遠無法獲得自由。
此刻需要的是回到自我的勇氣
「你在家幹嘛?」
「我在看一本關於神經科學的書,不知道是否吃太多藥,我腦子好鈍,看不太懂。」
「什麼?夠了哦,你不要再看那些艱澀難懂的書了啦!去大玩特玩吧。」
朋友擔心我,特地打來關心卻聽見我這麼說而無言地回答。「玩?」好久沒聽到這個詞了。
「我很想,可是我不知道做什麼好。」
「做你覺得最沒用、最沒意義,但卻很有趣的事!」
我聽到這句「沒用的事」,整個回過神來。
「沒錯,我們小時候最愛做沒用的事,卻最幸福!」
「我之前不是辭掉研究所的實驗室工作嗎?那時我休息了兩個月,也沒有下一步的計畫,純粹因為太累了才辭職。所以我睡了兩個月的覺,每天追劇,看漫畫看到天亮,想幹嘛就幹嘛,這麼做才恢復了精力。」
我從朋友分享的親身經驗裡,重新思考「休息」的意義。
「休息,然後再往前走的勇氣。」
我們最終需要放下一切,回到自我的勇氣。通過這份勇氣,得以輕鬆地選擇能讓自己開心並享受樂趣與美麗的事物,且不會為此感到愧疚,這才是真正的「休息」。
我深切地意識到自己在僵化的面具裡掙扎太久,我在別的事上努力過了,現在應該努力與學習的方向是「休息」。這好像就是答案。
和朋友講完電話後,我決定盡情玩樂。我需要找回完整的自我,需要看似無意義,卻能讓心變得輕盈喜悅的某項事物。
無視身心信號的人們
晚上十點四十四分,辦公室另一頭燈暗了,隔壁部門好像都下班了。這時候,有個腳步聲停在我面前。
「哇,金科長你還沒下班?」
「是的,常務您要下班了嗎?」
「嗯,我有事。你留下來做什麼?趕快下班。」
「沒關係,我報告還沒寫完,您路上小心。」
「好吧,你忙到一個段落就回家吧。」
對痛苦遲鈍變成了日常
常務與我寒暄一陣後就下班了。這時,我的胸口傳來劇痛,胃痙攣也越來越強烈,但工作沒完成,我還不能下班。
我走進沒開燈的會議室,將幾把椅子併起來躺在上面,用腹式呼吸安撫長時工作而感到憤怒的身體。吐氣、吸氣、吐氣、吸氣……情況似乎好轉一些。
「好想回家,可是做完再走才能放心……算了,發完郵件就走吧。」
我躺在椅子上,用拳頭捶打一下腹部後起身。只不過躺了一會兒,時間已經過了十一點。
向來都是這樣:忍痛是理所當然的,工作處理不完則是豈有此理。無論何時,我把對工作的責任感看得比疼痛更重要,因為工作量和最終期限不是我能決定的,疼痛卻能由我控制。吞下從包包裡拿出來的止痛藥後,我催眠自己:
「再撐一下,再撐一下。」
後來,我才曉得那是對自己的一種殘害。某天,聽我聊起這件事的諮商心理師說:
「你在某些方面非常敏銳,但在某些方面卻很遲鈍。尤其是你沒發現自己需要休息這件事……沒感覺到自己很累,所以不斷地忍耐。」
聽了她的話,我仔細回想:
「我對疼痛很遲鈍嗎?」
我是個習慣疼痛的人,從小就經常感到肚子痛和偏頭痛,雖然身體沒什麼特殊毛病。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因為我天生神經系統比別人敏感,所以更容易感受到疼痛,我就是依蓮.艾倫博士說的「高敏感人士」。
有時,輕微的聲響、氣味與震動,就會帶給我巨大的壓力,並引發各種疼痛。不知不覺間,吃止痛藥和忍痛成了我的日常。
沒有平白無故的疼痛
除非是醫師,否則沒多少人能夠了解他人疼痛的原因和影響。人們普遍不喜歡生病的人,無論這個人是自己還是他人。因為,疼痛的本質就是「讓人想避開的痛苦」。
如果你經常不舒服而請病假,或許有同事會說:「管好自己的身體也是一種能力。」此時你若把治療身體優先於處理工作,可能就會被認為不負責任。
再者,很少人能理解「天生」敏感這回事。「拒絕敏感人士」這句話,已說明這世界吝於擁抱敏感。因此有時候對某些人來說,隱忍疼痛才是明智之舉。
舉例而言,在緊繃的職場上,我們很難「慢慢來」,總是會被問:「什麼時候能弄好這個給我?請盡快處理。」這種事天天上演。所以當身體有了小毛病,我們自然而然就會忽視它,不會說「我身體不舒服」,而是說「對不起,我馬上給您!」
當你習慣忍受疼痛後,你甚至會達到劇痛時也能控制表情的「境界」。當各種痛苦不時冒出,我們難以逐一處理時,就習慣了疼痛,而這是一件可怕的事。習慣忍痛的人會自動跳過「休息」的想法,如果再加上「一定得做到」的強迫與執著,那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我們習慣性地認為其他事比健康重要,那麼大腦就會發出更強烈的信號,造成疼痛加劇,甚至連帶其他地方一起痛起來。
「為什麼老是不聽我的話?這麼痛你也不聽嗎?還是要更痛呢?」
大腦拚命發出信號,傳送給無視直覺的我們。
不只傳遞信號給身體,當我們被言語傷害或遇到難以承受的事情時,大腦也會發出信號來保護我們的心。
與無視身體疼痛的人一樣,也有無視或對「心靈疼痛」反應遲鈍的人。這些人通常有三種特性:
第一,很會看別人臉色。比起檢視自己的傷口,更常忙著觀察周遭的人。
第二,堅持找出原因。比起尋找解決方案,更在乎因果關係。
第三,常常抱怨並指責別人。抱怨和指責是暫時緩解痛苦的手段,會因為想宣洩積累的情緒而反覆出現。這麼做雖能短暫安撫難受的情緒或轉移注意力,但這只是延遲痛苦,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所有疼痛都是有「原因」的。疼痛是身體想改正錯誤的信號,有時會反映在腸胃痙攣,有時則反映在難以忍受的悲傷或恐慌症。
心理治療師克勞斯.伯恩哈特(Klaus Bernhardt)在《零恐慌!》一書中,把人類的潛意識比喻成一臺超級電腦。
「潛意識像一臺超級電腦,通過直覺不斷分析、發送個體所處的環境資訊,告訴個體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它這麼做只有一個理由:保護個體。」
我們要保護自己,就得傾聽「直覺」。假如你選擇無視直覺、隱忍各種疼痛,平凡的人生也可能瞬間崩塌。有意識地努力覺察,跟隨直覺一點也不難。
「討厭!」是內心短暫而強烈的吶喊,請傾聽它吧,聰明的直覺會保護你。
為什麼倦怠會反覆發生?
據說,矽谷有許多高薪人士因職業倦怠而離職。谷歌、推特、Instagram與亞馬遜公司等大型科技企業的員工,平均就職不超過一年兩個月。縱使是看重橫向溝通與工作效率的歐美企業,旗下的員工似乎也逃不過倦怠的命運。
容易陷入倦怠循環的人格
人們出現倦怠症狀時,通常會暫時離職或請長假,替「電池」充電。只要充分休息一個月,狀態就能有所好轉。此後則會出現兩條岔路:一是為了避免再次倦怠而選擇善待自己,一是如同既往對公司奉獻一切。
不用多說也知道,會重複出現倦怠的人必屬後者。這類人就算狀況好轉也沒學到教訓,或無法意識到自己必須改變行為,抑或是索性將倦怠這回事拋到腦後。得不到教訓,就很容易回到過去。
我也曾是這樣的人。身心俱疲時,除了暫離公司休息一下,我沒想過其他解決方法。以為只要跳槽到加班情況少、員工福利好的公司,狀況就能改善。
在家休息兩個月後,我總算恢復一些做事的動力,面試了幾家公司,順利轉職。我抱著「這次應該會不一樣吧」的茫然期許,到新公司報到。
結果,情況和我想的不同。上班第三天就加班到晚上十一點,我的預感告訴我事情不對勁。預感應驗,如同戰爭般的日子一天天過去,為了確認當日工作,我每天比別人更早上班,卻也比別人更晚下班。
新公司沒有舊公司能互相幫助的組員,我一個人要處理的工作如潮水般湧來。在尚未適應新環境的狀態下,我必須耗費許多能量,才有辦法完成那些臨時交辦的業務。很多時候,我拖著沒電的身體回家後直接躺平。
到職四個多月時,我曾經很想拋下一切逃跑。這是一個信號,告訴我「事情不應該是這樣」。隨著專案正式開始,我度過了緊張的每一天,基於責任感,我想盡辦法拖著工作往前走,卻感到渾身不舒服,心底某處傳來信號:
「這樣不對吧,你要繼續在這裡工作嗎?」
信號十分強大,我卻決定更「理性」地思考:「不,如果現在辭職,求職時會更煩惱」、「剛開始會累很正常,大公司不好進,再撐一下吧。」
相信自己撐得住的自信,再次把我關進了「認分工作的監牢」。可是我越堅持,越覺得人生迷失在迷宮深處,內心相當混亂。
我那麼不想過這種生活,為什麼又走上了回頭路?是因為這份工作本來就這麼辛苦嗎?還是因為我不適合這份工作?是這行原本就很操嗎?還是因為上司追求完美主義,才讓我感到很疲憊?
好幾個月我反覆自問,卻始終無解。像個職場菜鳥那般的學習熱情也熄滅了,最後我終於承認,現在比過去活得更累。
重複相同選擇的理由
無論是工作還是人際關係,如果不斷出現我們不樂見的情況,那就應該深究其因。因為有很大的可能,問題是出在自己身上。
我們體內有個「世界」,是大腦以特定方式創造的,會受到生活周遭的影響而逐漸變化。當這個世界改變,我們就會改變,人生也會跟著變動。也就是說,我們的人生會隨著那個世界的改變而改變。但換個角度說,如果那個世界不變,人生也不會變。
所謂大腦創造的「世界」,指的是在大腦神經網路中創造的「心」。這是什麼意思呢?大家可能覺得「神經網路」和「心」不搭調,這是因為我們認為「心」是一種抽象模糊的概念,就像我們習慣說「下定決心」、「心痛」、「關心」。但令人驚訝的是,腦科學所說的「心」是有實體的,而且是一個具有「高度結構化且複雜」的集合體。
儘管我們認為,身為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人類,我們的行動都出自思想與情緒,但事實並非如此,人類的所有行為都由「神經系統」協調。
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表示,人類的思想與行為都出自「神經元(神經系統的單位)與神經元之間的相互作用」。神經元之間緊密相連,形成了數十億個複雜交錯的神經迴路,進而形成神經網路,也就是所謂的「心」。
在這個「心」中,錯綜複雜的資訊產生了認知(認識與知覺)、情緒(感情與心情)、動機(欲望與夢想)以及意志(選擇與決定)。
試著以一座樹木茂盛的森林來想像吧。每棵樹的樹枝蜿蜒交錯,朝不同方向生長,其中有幾棵樹幹特別粗壯的老樹,與這座森林一起走過風雨,克服了善變的氣候。
我們的大腦就和這座森林相似,裡頭的神經元就像延展的樹枝般,與其他神經元相連。當中某些相連的樹枝會因為連結而變粗,這是起因於我們不斷重複過往的相似經驗。
為什麼重複的經驗會加深神經元的連結?這無關我們的意志,純然是大腦認為重複的某些東西(思想、經驗等)是「重要」的。大腦的這個判斷,影響了我們在生活中所做出的許多選擇。也就是說,即使我們經過一番審慎的思考,最後還是很可能做出一個大腦所熟悉的「決定」。
大腦以我們的慣性行為與熟悉狀態作為基準點,一旦出現類似情況,就會拚命地採取相同的模式來應對。從飲食習慣、睡眠習慣、工作方式、說話方式、情感表達方式、無聊時做的行動、穿著打扮,以及在特定情況下的表情等,我們做出的許多選擇都遵照這個原則。我們認為某件事幸福或不幸福,或是某件事讓我們想起相關記憶也是如此。換言之,在我們身上不斷重複某些特定情況,其實是大腦做出熟悉選擇所造成的結果。
同理,從小形成的道德觀、價值觀、固有觀念與偏見也是如此。很久以前,這些思維模式就存在於大腦中,每當遇到特定情況,相同的思維模式就會無意識地啟動。
有些思維深植在大腦裡,很難偏離既定軌道。比如說,當一個人堅決認定「不能頂撞上司」,那麼這個人就很難和上司起衝突;原則主義者認為按原則做事是鐵律,也是一樣的情形。即使每次面對的是不同情況,大腦機制仍舊採用熟悉的思維模式,使我們做出相似的選擇。
想改變情況,就得改變思維模式
跳槽到新公司、繼續盲目「苦撐」,這終究是依循「心的習慣」所做出的選擇。此外,心急的決定、過度疲勞、勉強自己努力、渴望被認可、恐懼等等,也都是大腦根據既定模式做出的選擇。
倘若我從過去經驗出發,有意識地努力改變生活,說不定我的選擇就會有所不同。神經元會因為個體有意識地改變熟悉的思考與行動模式,而跟著改用不同的方式連結彼此,並且會受重新形塑後的「心」所影響。
然而當時我只是一再做出類似選擇,使大腦藉由這些選擇進一步強化了既定模式,最終產生了容易感到焦慮、恐懼和憂鬱的迴路。
如果你發現某些不希望的事不斷發生,很可能是你的思維模式自動做出了選擇。想改變生活,就得改變思維模式。這當然不容易,但如果你意識到渴望改變的決心,並且專注在自己想要的事物上,那麼就能輕鬆地改變既定模式。
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當我意識到生活需要改變,且專注在這件事時,就能對現在的一切放手,讓生活進入新的開始。渴望改變的決心,讓我擁有了回顧自我的時間。儘管需要費點工夫,但只要努力,每個人都能改變人生。請專注在自己想要的事物與生活上,往前進吧。儘管是第一次走的路,漸漸地也會越走越熟悉。別忘了,大腦喜歡「重複」。
被診斷出恐慌症與憂鬱症後,我開始心理諮商。過程中我回首過往十年,發現自己的自尊大幅低落,是源於我努力地想適應各種環境。從得到這兩種病症的結果來看,很明顯地,我過去的選擇是有問題的。
「好像不應該開心」的不安感
自從請了病假,我待在家裡的時間變長,卻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多出來的時間,只能不停地找事做。洗碗、打掃、洗衣服、整理抽屜、擦拭鞋櫃裡的所有鞋子、將用不到的東西放到網路拍賣、替大型盆栽換盆……直到沒事可做。
「醫生,我在家關不住。該怎麼說呢?我覺得自己很懶散。」
「你是不是覺得很不安?」
「好像是。我打掃、洗衣,能做的都做了,還是一直想找事來做。不停地胡思亂想,超過大腦的負荷……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你之前說想舒舒服服地待在家裡,現在可以盡情休息了,坐下來畫畫也不錯呀。」
「我倒是沒想過畫畫呢。」
突然擁有了大量的空白時間,卻不知該怎麼打發。做點小事確實能輕鬆獲得成就,但我不斷找事做的原因,與其說是為了成就感,不如說是因為不安感。我可以看想看的電影、畫畫或者讀詩,但總覺得做這些事好像沒什麼意義。
「做這些事,是不是毫無用處呀?」
我無法輕易放過自己,「現在是提升自我價值的好機會」、「玩樂沒用」這類想法依然在腦中盤旋,所以一直強迫自己找事做。
我覺得自己沒資格過得開心並享受人生樂趣,我的不安感源自「恐懼」和「愧疚」。我害怕過去努力累積的職涯中斷、害怕喪失實務工作的感覺、對自己把知識與能力埋沒在家中感到內疚、讓丈夫獨自養家活口充滿抱歉,同時也愧對接手的同事。
我的休息,讓這些情緒猛烈地反抗,不停地強迫我找事做,更不容許我抱持著「自己是因為生病才請假」的想法顧影自憐。
抹掉自我的社會面具
「這段時間的所有努力,會不會化為烏有?」
我害怕迄今為止用來支撐我的東西崩塌了。而我也逐漸明白,恐懼的背後隱藏著一個不堅定的真正自尊。不過我始終相信畢業的學校、就職的公司、職位、年薪、住所等等,這些拿得出手的背景是帶給我幸福的支柱。
只是這種幸福沒能持續多久。表面上我以為自己不再受華麗膚淺的事物左右,實際上沒有方向的生活,正在劇烈搖晃著我的人生。
於是我深信只要努力就能過上好生活,這成了支撐我、證明我自己的唯一信念。然而,這不過是另一個「虛假自尊」罷了,是另一個「面具」。
比起以「自己」的身分生活,許多人更習慣戴上面具後的身分。因為活在這世上,面具相當好用,它能幫助我們完美承擔起某人的子女、妻子、丈夫、父母或員工等多種角色的責任,有時也能自我保護。
很多時候,當我們適應了自己扮演的角色,我們會用「大家都是這樣生活的」為藉口來壓抑自己,不顧藏在面具後高喊著「不能這樣」的真實自我。
每個人都在適應這世界,即使我們扮演的角色不符合意願與天性。我們漸漸習慣戴著面具活出社會想要的樣子,也就慢慢遺忘了真正的自我。
然而,面具無法支撐我們度過無數考驗,必須懂得擁抱脫下面具後的真實自我。
我們需要一個不在意我是什麼模樣、在哪裡做些什麼,都會無條件愛著我們的人。那個人不會是父母,也不是配偶,而應該是你自己。
當你能成為「即使自己不努力奮發也會支持並守護自己」的人,就能脫下面具,用堅定的自尊過生活。
如果不能放棄想被他人愛、被他人肯定的渴望,那麼就算我們再富有、再寬裕,也永遠無法獲得自由。
此刻需要的是回到自我的勇氣
「你在家幹嘛?」
「我在看一本關於神經科學的書,不知道是否吃太多藥,我腦子好鈍,看不太懂。」
「什麼?夠了哦,你不要再看那些艱澀難懂的書了啦!去大玩特玩吧。」
朋友擔心我,特地打來關心卻聽見我這麼說而無言地回答。「玩?」好久沒聽到這個詞了。
「我很想,可是我不知道做什麼好。」
「做你覺得最沒用、最沒意義,但卻很有趣的事!」
我聽到這句「沒用的事」,整個回過神來。
「沒錯,我們小時候最愛做沒用的事,卻最幸福!」
「我之前不是辭掉研究所的實驗室工作嗎?那時我休息了兩個月,也沒有下一步的計畫,純粹因為太累了才辭職。所以我睡了兩個月的覺,每天追劇,看漫畫看到天亮,想幹嘛就幹嘛,這麼做才恢復了精力。」
我從朋友分享的親身經驗裡,重新思考「休息」的意義。
「休息,然後再往前走的勇氣。」
我們最終需要放下一切,回到自我的勇氣。通過這份勇氣,得以輕鬆地選擇能讓自己開心並享受樂趣與美麗的事物,且不會為此感到愧疚,這才是真正的「休息」。
我深切地意識到自己在僵化的面具裡掙扎太久,我在別的事上努力過了,現在應該努力與學習的方向是「休息」。這好像就是答案。
和朋友講完電話後,我決定盡情玩樂。我需要找回完整的自我,需要看似無意義,卻能讓心變得輕盈喜悅的某項事物。
無視身心信號的人們
晚上十點四十四分,辦公室另一頭燈暗了,隔壁部門好像都下班了。這時候,有個腳步聲停在我面前。
「哇,金科長你還沒下班?」
「是的,常務您要下班了嗎?」
「嗯,我有事。你留下來做什麼?趕快下班。」
「沒關係,我報告還沒寫完,您路上小心。」
「好吧,你忙到一個段落就回家吧。」
對痛苦遲鈍變成了日常
常務與我寒暄一陣後就下班了。這時,我的胸口傳來劇痛,胃痙攣也越來越強烈,但工作沒完成,我還不能下班。
我走進沒開燈的會議室,將幾把椅子併起來躺在上面,用腹式呼吸安撫長時工作而感到憤怒的身體。吐氣、吸氣、吐氣、吸氣……情況似乎好轉一些。
「好想回家,可是做完再走才能放心……算了,發完郵件就走吧。」
我躺在椅子上,用拳頭捶打一下腹部後起身。只不過躺了一會兒,時間已經過了十一點。
向來都是這樣:忍痛是理所當然的,工作處理不完則是豈有此理。無論何時,我把對工作的責任感看得比疼痛更重要,因為工作量和最終期限不是我能決定的,疼痛卻能由我控制。吞下從包包裡拿出來的止痛藥後,我催眠自己:
「再撐一下,再撐一下。」
後來,我才曉得那是對自己的一種殘害。某天,聽我聊起這件事的諮商心理師說:
「你在某些方面非常敏銳,但在某些方面卻很遲鈍。尤其是你沒發現自己需要休息這件事……沒感覺到自己很累,所以不斷地忍耐。」
聽了她的話,我仔細回想:
「我對疼痛很遲鈍嗎?」
我是個習慣疼痛的人,從小就經常感到肚子痛和偏頭痛,雖然身體沒什麼特殊毛病。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因為我天生神經系統比別人敏感,所以更容易感受到疼痛,我就是依蓮.艾倫博士說的「高敏感人士」。
有時,輕微的聲響、氣味與震動,就會帶給我巨大的壓力,並引發各種疼痛。不知不覺間,吃止痛藥和忍痛成了我的日常。
沒有平白無故的疼痛
除非是醫師,否則沒多少人能夠了解他人疼痛的原因和影響。人們普遍不喜歡生病的人,無論這個人是自己還是他人。因為,疼痛的本質就是「讓人想避開的痛苦」。
如果你經常不舒服而請病假,或許有同事會說:「管好自己的身體也是一種能力。」此時你若把治療身體優先於處理工作,可能就會被認為不負責任。
再者,很少人能理解「天生」敏感這回事。「拒絕敏感人士」這句話,已說明這世界吝於擁抱敏感。因此有時候對某些人來說,隱忍疼痛才是明智之舉。
舉例而言,在緊繃的職場上,我們很難「慢慢來」,總是會被問:「什麼時候能弄好這個給我?請盡快處理。」這種事天天上演。所以當身體有了小毛病,我們自然而然就會忽視它,不會說「我身體不舒服」,而是說「對不起,我馬上給您!」
當你習慣忍受疼痛後,你甚至會達到劇痛時也能控制表情的「境界」。當各種痛苦不時冒出,我們難以逐一處理時,就習慣了疼痛,而這是一件可怕的事。習慣忍痛的人會自動跳過「休息」的想法,如果再加上「一定得做到」的強迫與執著,那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我們習慣性地認為其他事比健康重要,那麼大腦就會發出更強烈的信號,造成疼痛加劇,甚至連帶其他地方一起痛起來。
「為什麼老是不聽我的話?這麼痛你也不聽嗎?還是要更痛呢?」
大腦拚命發出信號,傳送給無視直覺的我們。
不只傳遞信號給身體,當我們被言語傷害或遇到難以承受的事情時,大腦也會發出信號來保護我們的心。
與無視身體疼痛的人一樣,也有無視或對「心靈疼痛」反應遲鈍的人。這些人通常有三種特性:
第一,很會看別人臉色。比起檢視自己的傷口,更常忙著觀察周遭的人。
第二,堅持找出原因。比起尋找解決方案,更在乎因果關係。
第三,常常抱怨並指責別人。抱怨和指責是暫時緩解痛苦的手段,會因為想宣洩積累的情緒而反覆出現。這麼做雖能短暫安撫難受的情緒或轉移注意力,但這只是延遲痛苦,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所有疼痛都是有「原因」的。疼痛是身體想改正錯誤的信號,有時會反映在腸胃痙攣,有時則反映在難以忍受的悲傷或恐慌症。
心理治療師克勞斯.伯恩哈特(Klaus Bernhardt)在《零恐慌!》一書中,把人類的潛意識比喻成一臺超級電腦。
「潛意識像一臺超級電腦,通過直覺不斷分析、發送個體所處的環境資訊,告訴個體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它這麼做只有一個理由:保護個體。」
我們要保護自己,就得傾聽「直覺」。假如你選擇無視直覺、隱忍各種疼痛,平凡的人生也可能瞬間崩塌。有意識地努力覺察,跟隨直覺一點也不難。
「討厭!」是內心短暫而強烈的吶喊,請傾聽它吧,聰明的直覺會保護你。
為什麼倦怠會反覆發生?
據說,矽谷有許多高薪人士因職業倦怠而離職。谷歌、推特、Instagram與亞馬遜公司等大型科技企業的員工,平均就職不超過一年兩個月。縱使是看重橫向溝通與工作效率的歐美企業,旗下的員工似乎也逃不過倦怠的命運。
容易陷入倦怠循環的人格
人們出現倦怠症狀時,通常會暫時離職或請長假,替「電池」充電。只要充分休息一個月,狀態就能有所好轉。此後則會出現兩條岔路:一是為了避免再次倦怠而選擇善待自己,一是如同既往對公司奉獻一切。
不用多說也知道,會重複出現倦怠的人必屬後者。這類人就算狀況好轉也沒學到教訓,或無法意識到自己必須改變行為,抑或是索性將倦怠這回事拋到腦後。得不到教訓,就很容易回到過去。
我也曾是這樣的人。身心俱疲時,除了暫離公司休息一下,我沒想過其他解決方法。以為只要跳槽到加班情況少、員工福利好的公司,狀況就能改善。
在家休息兩個月後,我總算恢復一些做事的動力,面試了幾家公司,順利轉職。我抱著「這次應該會不一樣吧」的茫然期許,到新公司報到。
結果,情況和我想的不同。上班第三天就加班到晚上十一點,我的預感告訴我事情不對勁。預感應驗,如同戰爭般的日子一天天過去,為了確認當日工作,我每天比別人更早上班,卻也比別人更晚下班。
新公司沒有舊公司能互相幫助的組員,我一個人要處理的工作如潮水般湧來。在尚未適應新環境的狀態下,我必須耗費許多能量,才有辦法完成那些臨時交辦的業務。很多時候,我拖著沒電的身體回家後直接躺平。
到職四個多月時,我曾經很想拋下一切逃跑。這是一個信號,告訴我「事情不應該是這樣」。隨著專案正式開始,我度過了緊張的每一天,基於責任感,我想盡辦法拖著工作往前走,卻感到渾身不舒服,心底某處傳來信號:
「這樣不對吧,你要繼續在這裡工作嗎?」
信號十分強大,我卻決定更「理性」地思考:「不,如果現在辭職,求職時會更煩惱」、「剛開始會累很正常,大公司不好進,再撐一下吧。」
相信自己撐得住的自信,再次把我關進了「認分工作的監牢」。可是我越堅持,越覺得人生迷失在迷宮深處,內心相當混亂。
我那麼不想過這種生活,為什麼又走上了回頭路?是因為這份工作本來就這麼辛苦嗎?還是因為我不適合這份工作?是這行原本就很操嗎?還是因為上司追求完美主義,才讓我感到很疲憊?
好幾個月我反覆自問,卻始終無解。像個職場菜鳥那般的學習熱情也熄滅了,最後我終於承認,現在比過去活得更累。
重複相同選擇的理由
無論是工作還是人際關係,如果不斷出現我們不樂見的情況,那就應該深究其因。因為有很大的可能,問題是出在自己身上。
我們體內有個「世界」,是大腦以特定方式創造的,會受到生活周遭的影響而逐漸變化。當這個世界改變,我們就會改變,人生也會跟著變動。也就是說,我們的人生會隨著那個世界的改變而改變。但換個角度說,如果那個世界不變,人生也不會變。
所謂大腦創造的「世界」,指的是在大腦神經網路中創造的「心」。這是什麼意思呢?大家可能覺得「神經網路」和「心」不搭調,這是因為我們認為「心」是一種抽象模糊的概念,就像我們習慣說「下定決心」、「心痛」、「關心」。但令人驚訝的是,腦科學所說的「心」是有實體的,而且是一個具有「高度結構化且複雜」的集合體。
儘管我們認為,身為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人類,我們的行動都出自思想與情緒,但事實並非如此,人類的所有行為都由「神經系統」協調。
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表示,人類的思想與行為都出自「神經元(神經系統的單位)與神經元之間的相互作用」。神經元之間緊密相連,形成了數十億個複雜交錯的神經迴路,進而形成神經網路,也就是所謂的「心」。
在這個「心」中,錯綜複雜的資訊產生了認知(認識與知覺)、情緒(感情與心情)、動機(欲望與夢想)以及意志(選擇與決定)。
試著以一座樹木茂盛的森林來想像吧。每棵樹的樹枝蜿蜒交錯,朝不同方向生長,其中有幾棵樹幹特別粗壯的老樹,與這座森林一起走過風雨,克服了善變的氣候。
我們的大腦就和這座森林相似,裡頭的神經元就像延展的樹枝般,與其他神經元相連。當中某些相連的樹枝會因為連結而變粗,這是起因於我們不斷重複過往的相似經驗。
為什麼重複的經驗會加深神經元的連結?這無關我們的意志,純然是大腦認為重複的某些東西(思想、經驗等)是「重要」的。大腦的這個判斷,影響了我們在生活中所做出的許多選擇。也就是說,即使我們經過一番審慎的思考,最後還是很可能做出一個大腦所熟悉的「決定」。
大腦以我們的慣性行為與熟悉狀態作為基準點,一旦出現類似情況,就會拚命地採取相同的模式來應對。從飲食習慣、睡眠習慣、工作方式、說話方式、情感表達方式、無聊時做的行動、穿著打扮,以及在特定情況下的表情等,我們做出的許多選擇都遵照這個原則。我們認為某件事幸福或不幸福,或是某件事讓我們想起相關記憶也是如此。換言之,在我們身上不斷重複某些特定情況,其實是大腦做出熟悉選擇所造成的結果。
同理,從小形成的道德觀、價值觀、固有觀念與偏見也是如此。很久以前,這些思維模式就存在於大腦中,每當遇到特定情況,相同的思維模式就會無意識地啟動。
有些思維深植在大腦裡,很難偏離既定軌道。比如說,當一個人堅決認定「不能頂撞上司」,那麼這個人就很難和上司起衝突;原則主義者認為按原則做事是鐵律,也是一樣的情形。即使每次面對的是不同情況,大腦機制仍舊採用熟悉的思維模式,使我們做出相似的選擇。
想改變情況,就得改變思維模式
跳槽到新公司、繼續盲目「苦撐」,這終究是依循「心的習慣」所做出的選擇。此外,心急的決定、過度疲勞、勉強自己努力、渴望被認可、恐懼等等,也都是大腦根據既定模式做出的選擇。
倘若我從過去經驗出發,有意識地努力改變生活,說不定我的選擇就會有所不同。神經元會因為個體有意識地改變熟悉的思考與行動模式,而跟著改用不同的方式連結彼此,並且會受重新形塑後的「心」所影響。
然而當時我只是一再做出類似選擇,使大腦藉由這些選擇進一步強化了既定模式,最終產生了容易感到焦慮、恐懼和憂鬱的迴路。
如果你發現某些不希望的事不斷發生,很可能是你的思維模式自動做出了選擇。想改變生活,就得改變思維模式。這當然不容易,但如果你意識到渴望改變的決心,並且專注在自己想要的事物上,那麼就能輕鬆地改變既定模式。
我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當我意識到生活需要改變,且專注在這件事時,就能對現在的一切放手,讓生活進入新的開始。渴望改變的決心,讓我擁有了回顧自我的時間。儘管需要費點工夫,但只要努力,每個人都能改變人生。請專注在自己想要的事物與生活上,往前進吧。儘管是第一次走的路,漸漸地也會越走越熟悉。別忘了,大腦喜歡「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