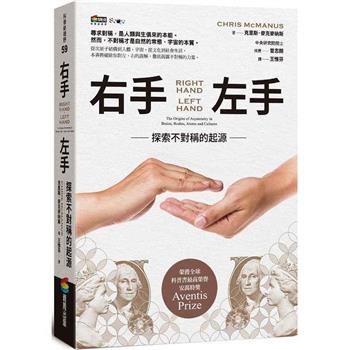早在威廉出世之前,達爾文就思索過孩童發育與演化之間的關聯,並在他的科學日誌中草草寫下「嬰孩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babies)這樣一個標題,還列出幾個需要回答的問題。威廉四歲半時,他還做了個實驗:
我靠近他的臉,發出很大的鼾聲,這讓他認真了起來,變得害怕,突然間就哭了。這很有趣,因為之前我曾對著他發出各種奇怪的聲音或是扮鬼臉,但他總是把它們當作是笑話。我又重複做了這實驗。
「我又重複做了這實驗。」這句話巧妙反映出達爾文集父親、自然學家與實驗科學家多重身分的心態。想必小嘟弟後來又被奶媽與母親的驚人之舉嚇哭過幾次。
就跟他的多數詳細筆記與想法一樣,達爾文直到多年之後才發表他的想法。1877年,達爾文在甫創刊的哲學與心理學期刊《心智》(Mind)上讀到泰尼(Hippolyte Adolphe Taine)描述孩童語言發展的文章後,他回頭去整理自己當年留下的筆記,最後寫出在他所有科學著作中最具個人色彩的作品,題為〈一個嬰兒的傳記式描寫〉(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an infant)。這時威廉都已經三十七歲,在南安普頓當銀行職員。此時孩童發展的研究還在起步階段,達爾文的紀錄是當時少數對一個嬰兒的系統性觀察,這對此領域的開展有相當幫助。威廉十一週大時,達爾文研究了他的偏手性,並在筆記上寫下:
現在十一週大,用右手拿奶瓶。餵奶時有時是以右手臂抱著,有時是左手臂。他沒有用左手拿奶瓶,即使當奶瓶放在左邊時也是。這孩子並沒有進行任何使用手臂的練習。
還不滿十二週的某一天,用右手握住凱薩琳的手指,並放到嘴巴裡。
剛滿十二週的那天與隔天,用左手握住奶瓶,就跟之前用右手做的一樣,這表示他的右手至少領先左手一週。之所以說「至少」,是因為我不十分確定自己所觀察到的,是否就是他第一次用右手的時候。
這些粗略的評論、想法與觀察最後被整理出來,成為一篇科學論文:
七十七天大時,他會以右手握住奶瓶(餵奶時也是),不論奶媽是用左手,還是右手抱他都是如此。儘管我試著讓他用左手握奶瓶,但要到一週後,他才做得到,可見右手的發育領先了左手一週。
根據這樣的觀察,達爾文認為他的兒子應該是個右利者。但事情並非如此,他在這篇文章後面提到:「然而,後來我發現這個嬰孩是個左利者,這無疑是遺傳自他的祖父、母親與某個舅舅。」達爾文在其他地方也一再表示,「眾所皆知,這是由遺傳造成的」。
達爾文之所以會在孩子這麼小的時候就關心起他的慣用手,當然是有原因的。他自己本身是右利者,但妻子愛瑪與威廉的祖父則是左利者,雖然我們不確定這裡所指的究竟是祖父還是外祖父,不過外公約書亞.魏居伍德二世的可能性比爺爺羅伯.達爾文要大些。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左利人口眾多的家族。在達爾文的所有孩子中,有八個都活到可以確定慣用手的年紀,而當中有兩個是左利者。這個比例就是雙親分別為左利與右利時,孩子出現左利的典型比例。
達爾文對偏手性的興趣,尤其是對自己孩子的偏手性,在今日看來也並非不尋常。我從 1970 年代開始從事偏手性的研究,父母最常問的問題之一便是,何時他們可以得知孩子是左利還是右利?不過,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也許是「左利有多普遍?」讓我們就從這一點開始討論,但請你先完成以下這份簡單的偏手性問卷調查:
雖然這不是最複雜或最精密的偏手性問卷調查,但已足夠達到這個目標,而且近來已被邁斯翠屋博物館(Vestry House Museum)的奈格爾.賽德勒(Nigel Sadler)拿來調查北倫敦沃聖森林(WalthamForest)近三千名學童的偏手性,那是一項規模相當龐大而且具有代表性的抽樣調查。
要計算這份問卷很簡單,算出你選擇左的次數,這數值應該是介於零(若你是一個高度的右利者)到十(若你是一個高度的左利者)之間。看看圖 7.2 就可以知道自己和他人之間的差別。先看主圖的 X 軸,代表使用左手的次數,數字從十排到零,Y 軸是每一項選左的人數比例,很明顯地,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不使用左手從事這些活動,被歸類成高度右利。由於他們所占的比例過高,所以很難看出其他部分的比例關係。為了要凸顯這些次要的部分,又在圖中做了一個小圖,放大了主圖中選用左手與中間值的部分。
結果這部分呈現一個 J 形曲線,右邊最高(高度右利),然後一直減少到中間時幾乎為零,接著又開始攀升到左邊(高度左利)。在高度左利與右利之間的是中間型,若是他們使用左手的次數在六到九之間,就稱為低度左利,若是介於一到四次,則為低度右利。至於得到五分,那些一半的活動用左手,一半用右手的 1%人口又是怎麼回事呢?難道他們兩隻手都一樣靈活嗎?恐怕不是。當追加進行另一份更精密、更仔細的問卷調查後,發現多數人還是會偏用某一隻手;換句話說,他們不是低度左利,就是低度右利。雖然的確有人宣稱自己是雙手都很靈活,但當他們在實驗室接受比較嚴格的測試時,還是會顯現出偏用左手或右手的傾向。除非有人認真苦練,也許是為了娛樂助興,不然幾乎沒有人可以雙手書寫得一樣好。如果你認為自己的雙手都很靈活,那試試圖 7.3 的練習。
先用鬧鐘或計時器設定三十秒,在這段時間內用細字筆在每一個圈圈中畫上一個點,越多越好,然後再換另一隻手。在這項測試中,幾乎沒有人的左右手會得到一樣的結果。那到底有多少人是左利者呢?按照慣例,那些以左手完成一半以上活動的人就算是左利者。沃聖森林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 11%的人是左利者,這份抽樣足以代表整個英國,甚至西方世界的概況;不過這個比例,稍後我們會提到,在老人族群或是世界的其他地方會更低。
圖 7.2 同時也顯示出其他訊息。在男性中,左利的比例是11.6%,但女性則只有 8.6%,也就是說男人中左利的情形比女人常見,這結果和其他研究相類似。整體而言,男性左利與女性左利的比例約為五比四。這並不是多大的差距,但卻是普遍存在的事實,而且也反映出左利的重要生物機制。達爾文家族就透露出這種性別差異的線索,在八名男性中有三名左利(38%),而在六名女性中有一名左利(17%)。
認為性與偏手性有關的概念可回溯到心理學。佛洛伊德在1897 年與 1898 年時曾與懷赫姆.弗立斯(Wilhelm Fliess)通信討論這個概念,雖然他們的討論主要著重在弗立斯提出的「雙B」(Bi-Bi)理論,即雙性戀(bisexuality)與雙側性(bilaterality)的關聯。弗立斯認為潛伏的左利傾向與潛伏的同性戀傾向有關。在現代,這個想法有過一段錯綜複雜的歷史。整體而言,左利的比例在男同性戀中較男異性戀稍高,不過要解釋這份資料並不容易,因為美國在 1920 年代到 1970 年代,「左利」成了稱呼「同性戀」的俚語。在經由外科手術變性的族群中,左利也比較多,同樣地,在性別認知混淆的美國孩童中,也是左利者比較多。現階段還不清楚這些現象的成因,尤其是還要考慮統計上左利男性比女性高的這部分因素,不過可以確定的一點是,這中間存有某種模式,等待我們去解釋。
圖 7.2 還顯示了另外一件事。仔細看看在零分、一分到四分的右利者,超過三分之二的右利是高度右利。但在左利這部分則沒有那麼極端,比較一下十分到六分的左利者,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高度左利,也就是說,右利者的偏手性較左利者強烈。這部分要歸因於左利者居住在一個「右利的世界」,所有的器物用品都是依據右利者的需要設計的,從微波爐、電腦鍵盤到鋼琴都是如此,自然而然,左利者學會適應右利的世界,常常使用到右手,雖然他們並非天生如此。這點也許可以解釋圖 7.2 的一部分,但並不是完整的解釋,因為在十項問題中只有一道(剪刀那題)提到的物品是專為右利者設計的。
一個全面的解答其實更有趣,反映出許多的左利者以及一些右利者,實際上沒有特定的慣用手,可能在從事某些活動時偏用某隻手,而其他技能活動則是另一隻手。我在十二歲參加夏令營時,就發現自己正是如此。有人教我如何使用手握型的短斧,由於我是右利,自然就用右手拿著。然後我再學如何用長斧,這時有人問我:「你是左撇子嗎?」因為在下砍之前,我都將斧頭放在我的左肩上。對我而言,這是最自然的方式。圖 7.2 中,得分介於一到九之間的許多右利者與左利者,都在慣用手上展現出類似的不一致性。
大約是從十五年前,研究人員才開始嚴肅看待這個議題,探討為何有許多人沒有特定的慣用手。引發這股研究風潮的,主要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圭爾夫大學(Uni. of Guelph)的麥克.彼得斯(Michael Peters)的研究。麥克發現在三分之一的左利者中,會偏好以左手寫字,但是以右手丟球,而且右手丟得比較準。後來又發現在右利者中,有 2%–3% 的人,會以右手寫字,但偏好以左手丟球。雖然這是研究上的新發現,但有人早已記錄過這樣的現象,比方先驅的性學家哈弗洛克.伊利斯(Havelock Ellis)在他的自傳中就說過:「除了丟石頭或丟球外,我做什麼事都是用右手。⋯⋯我從來沒用過右手丟球,而且⋯⋯我也沒有以左手寫過字。」
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是以「偏手性」這個詞來討論,但有些研究者認為使用「單邊性」(sidedeness)的概念可能更貼切,因為除了左右手之外,其他許多行為層面似乎也都展現出對於某一邊的偏好,從手臂、腿、眼、耳朵到腳都是如此,其中有些不對稱與偏手性有關,但並非每項都是。
偏腳性(footedness)與偏手性有相關,慣用右手的人多半也慣用右腳,而慣用左手的則偏用左腳。要測試偏腳性的方法很直接,只要請受試者在球門前踢顆足球就會知道,踢球的腳就是慣用腳。職業足球員的偏腳性則是以他們碰觸足球的次數來判斷,球員以慣用腳來踢球的比例高達 85%,而且幾乎沒有人是平均地使用左右腳。換句話說,就算是專業球員,也不是左右腳都可以靈活運用的。他們就跟其他普通人一樣,有 20% 的人慣用左腳,這比10% 的左利者要多,這表示許多右利者具有「跨側性」(crosslateral),用右手寫字,但以左腳踢球。
耳朵的慣用主要是從接聽電話時來判斷,約有六成的人偏用右耳,四成的人偏用左耳;右利者多用右耳,而左利者偏用左耳。雖然過去對慣用耳的研究甚少,但隨著行動電話日益普及,這個情況也將有所改觀。
相較於對慣用耳的忽略,用眼的差別倒是被徹底研究過。要知道你的慣用眼是右眼還是左眼,只要將你的手臂伸長,指向遠方的一個小物體,這時閉上一隻眼,如果你的手指還指著物體,那睜開的這隻眼就是你的慣用眼;如果你睜開的是非慣用眼,手指會偏離該物體。這是眼睛的「視覺優勢」,一隻眼睛看物體的視覺會優於另一隻。「偏眼性」(eyedness)還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問題來確認,只要問受試者是用哪一隻眼睛來看鑰匙孔或是顯微鏡便可以明白。大約有七成的人偏用右眼,三成的人偏用左眼。雖然左利者中用左眼的人較多,右利者中用右眼的較多,然而還是有許多人展現出跨側性,用身體這一側的手寫字,但用另一側的眼睛看世界,這種習慣會造成什麼影響,目前仍未有定論。在 1920 年代,山繆.歐頓(Samuel Orton)認為跨側性優勢(cross-dominance)會造成閱讀障礙,引起識字困難症(dyslexia),有不少人支持這個理論,但相關證據還很薄弱。
人還有許多其他的側性,像是多數人都會用右邊的牙齒來咀嚼,但許多這種偏用某一側的特性並不特別引起大家的興趣。不過我對其中的兩種著迷了好一陣子,因為這些行為是如此的瑣碎、平凡而且毫無意義:一個是合掌,另一個是交叉手臂。要看出合掌的不同,只要立刻雙手互握,讓手指相互交錯在一起即可。哪一隻手的拇指在上面,左手還是右手?現在試試看另一種合掌的方式,你會發現自己稍微遲疑了一下,而且覺得手指之間似乎不大能密合。第一次本能性的合掌比較容易,也較自然。合掌的行為似乎不是習得的,實際上若沒有特別提出來,多數人不會注意到自己的習慣,而且這個行為很小的時候就有,如圖 7.4 所示。這是我女兒法蘭西絲卡六週大的照片,她自發性地做出合掌的動作。在英國,約有六成的人合掌時,左手拇指會在上,不論是左利還是右利族群,都是這個比例。有趣的是,一路往東調查,從歐洲、亞洲到大洋洲,便會發現這個比例也漸次下滑,到了新幾內亞東邊的所羅門群島時,左手姆指在上的比例只剩下三成。更奇妙的是,合掌的行為似乎是家族性的,雖然並不是很明顯;但通常合掌時左手在上的夫妻比右手在上的夫妻更有機會生育出左手在上的下一代。
交叉手臂是另一項可以自己測試出的側性。迅速地將伸直的手臂在胸前交叉,看看是左手腕在右手腕上,還是右手腕在左手腕上方?現在試著顛倒過來。每當我在課堂上讓學生做練習時,總是會引發一陣哄堂大笑,因為有許多人直接在胸前旋轉手臂,轉了一圈又回到原來的樣子,還是同一隻手腕在上方。要將「錯」的那隻手腕放在上方會有點困難,需要思考一下,而且會覺得有點彆扭。在英國,約有六成的人是左手腕在上方,這個比例在右利與左利的族群中是一樣的,而且不論合掌時是左拇指在上還是右拇指在上,也都是這個比例。這表示慣用手、合掌與交叉雙臂之間對於左右的偏用並無關聯。不對稱的特徵不勝枚舉,比方說有五分之一的人會抖動自己的耳朵,而只會抖動其中一隻耳朵的人當中,會抖左耳的人數是會抖右耳的兩倍。這些現象真是相當不可思議,但為何會產生這樣的不對稱特徵,至今完全是個謎。
不過,偏手性的確需要解釋,多數科學家將研究重點放在行為上的不對稱性,這麼做是有許多緣由的。首先,和其他的不對稱特徵相比,這是當中最極端的,大幅偏離了「變動型不對稱性」隨機差異造成的性狀各半之混合比例。再者,要取得大量的可靠資料也很容易,只要藉由簡單的問卷調查或是觀看人群,不論是真實生活或是照片都可以做到。因此,可試著探究多數右利與少數左利的現象出現的時間點、形成機制與原因。
達爾文對威廉的偏手性極感興趣,然而即便在詳盡的觀察之後,還是下了錯誤的結論。那麼,究竟在何時才可能確定孩子的偏手性呢?小孩的偏手性不易研究,尤其是一、兩歲的時候。實際上,在成長的階段似乎有一段模糊的時期,對於手的偏好搖擺不定,今天是右手,明天又變成左手。模糊期結束的時間也有變異,通常要到十八個月大或是兩足歲時才能確定偏手性,而在那之後,一輩子都不會改變。
既然孩童的偏手性要到兩歲時才會明確,研究人員因此認為沒有必要去調查嬰孩在那之前的偏手性,但這樣的假設卻被貝爾法斯特(Belfast)的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的彼得.海波(Peter Hepper)所推翻了。他是一名胎兒行為專家。利用超音波掃描,他發現腹中的胎兒就像嬰孩一樣,會吸吮大拇指,而且他們在十二週大時就會這麼做了。海波檢查過上百個胎兒,發現其中有超過九成的胎兒會吸吮右手拇指。由於大腦皮質的不對稱特徵也大概是在這個時期出現,海波自然會把這兩點聯想在一起,假設大腦的不對稱是造成胎兒吸吮右手拇指的主因。等到後來他檢視了十週大的胎兒,發現這時候他們雖然不會吸吮拇指,卻會揮動手臂與腿。他觀察了胎兒左右手腳運動的情形,看看其中是否有差異。結果有85% 的胎兒移動的都是右手臂。這一點意味著他之前推測大腦的不對稱發育早於肢體的想法並不正確,因為在這時期,腦中的神經元尚未連接到脊椎神經,所以這些早期的不對稱行為似乎是由脊椎神經或是肢體本身所造成的,也就顯示出偏手性並不是由大腦皮質所控制,可能是由神經系統比較下游的層級所負責。不過,目前依舊不知道這個過程是如何進行的,也不確定到底是位在哪個部位。
我靠近他的臉,發出很大的鼾聲,這讓他認真了起來,變得害怕,突然間就哭了。這很有趣,因為之前我曾對著他發出各種奇怪的聲音或是扮鬼臉,但他總是把它們當作是笑話。我又重複做了這實驗。
「我又重複做了這實驗。」這句話巧妙反映出達爾文集父親、自然學家與實驗科學家多重身分的心態。想必小嘟弟後來又被奶媽與母親的驚人之舉嚇哭過幾次。
就跟他的多數詳細筆記與想法一樣,達爾文直到多年之後才發表他的想法。1877年,達爾文在甫創刊的哲學與心理學期刊《心智》(Mind)上讀到泰尼(Hippolyte Adolphe Taine)描述孩童語言發展的文章後,他回頭去整理自己當年留下的筆記,最後寫出在他所有科學著作中最具個人色彩的作品,題為〈一個嬰兒的傳記式描寫〉(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an infant)。這時威廉都已經三十七歲,在南安普頓當銀行職員。此時孩童發展的研究還在起步階段,達爾文的紀錄是當時少數對一個嬰兒的系統性觀察,這對此領域的開展有相當幫助。威廉十一週大時,達爾文研究了他的偏手性,並在筆記上寫下:
現在十一週大,用右手拿奶瓶。餵奶時有時是以右手臂抱著,有時是左手臂。他沒有用左手拿奶瓶,即使當奶瓶放在左邊時也是。這孩子並沒有進行任何使用手臂的練習。
還不滿十二週的某一天,用右手握住凱薩琳的手指,並放到嘴巴裡。
剛滿十二週的那天與隔天,用左手握住奶瓶,就跟之前用右手做的一樣,這表示他的右手至少領先左手一週。之所以說「至少」,是因為我不十分確定自己所觀察到的,是否就是他第一次用右手的時候。
這些粗略的評論、想法與觀察最後被整理出來,成為一篇科學論文:
七十七天大時,他會以右手握住奶瓶(餵奶時也是),不論奶媽是用左手,還是右手抱他都是如此。儘管我試著讓他用左手握奶瓶,但要到一週後,他才做得到,可見右手的發育領先了左手一週。
根據這樣的觀察,達爾文認為他的兒子應該是個右利者。但事情並非如此,他在這篇文章後面提到:「然而,後來我發現這個嬰孩是個左利者,這無疑是遺傳自他的祖父、母親與某個舅舅。」達爾文在其他地方也一再表示,「眾所皆知,這是由遺傳造成的」。
達爾文之所以會在孩子這麼小的時候就關心起他的慣用手,當然是有原因的。他自己本身是右利者,但妻子愛瑪與威廉的祖父則是左利者,雖然我們不確定這裡所指的究竟是祖父還是外祖父,不過外公約書亞.魏居伍德二世的可能性比爺爺羅伯.達爾文要大些。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左利人口眾多的家族。在達爾文的所有孩子中,有八個都活到可以確定慣用手的年紀,而當中有兩個是左利者。這個比例就是雙親分別為左利與右利時,孩子出現左利的典型比例。
達爾文對偏手性的興趣,尤其是對自己孩子的偏手性,在今日看來也並非不尋常。我從 1970 年代開始從事偏手性的研究,父母最常問的問題之一便是,何時他們可以得知孩子是左利還是右利?不過,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也許是「左利有多普遍?」讓我們就從這一點開始討論,但請你先完成以下這份簡單的偏手性問卷調查:
雖然這不是最複雜或最精密的偏手性問卷調查,但已足夠達到這個目標,而且近來已被邁斯翠屋博物館(Vestry House Museum)的奈格爾.賽德勒(Nigel Sadler)拿來調查北倫敦沃聖森林(WalthamForest)近三千名學童的偏手性,那是一項規模相當龐大而且具有代表性的抽樣調查。
要計算這份問卷很簡單,算出你選擇左的次數,這數值應該是介於零(若你是一個高度的右利者)到十(若你是一個高度的左利者)之間。看看圖 7.2 就可以知道自己和他人之間的差別。先看主圖的 X 軸,代表使用左手的次數,數字從十排到零,Y 軸是每一項選左的人數比例,很明顯地,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不使用左手從事這些活動,被歸類成高度右利。由於他們所占的比例過高,所以很難看出其他部分的比例關係。為了要凸顯這些次要的部分,又在圖中做了一個小圖,放大了主圖中選用左手與中間值的部分。
結果這部分呈現一個 J 形曲線,右邊最高(高度右利),然後一直減少到中間時幾乎為零,接著又開始攀升到左邊(高度左利)。在高度左利與右利之間的是中間型,若是他們使用左手的次數在六到九之間,就稱為低度左利,若是介於一到四次,則為低度右利。至於得到五分,那些一半的活動用左手,一半用右手的 1%人口又是怎麼回事呢?難道他們兩隻手都一樣靈活嗎?恐怕不是。當追加進行另一份更精密、更仔細的問卷調查後,發現多數人還是會偏用某一隻手;換句話說,他們不是低度左利,就是低度右利。雖然的確有人宣稱自己是雙手都很靈活,但當他們在實驗室接受比較嚴格的測試時,還是會顯現出偏用左手或右手的傾向。除非有人認真苦練,也許是為了娛樂助興,不然幾乎沒有人可以雙手書寫得一樣好。如果你認為自己的雙手都很靈活,那試試圖 7.3 的練習。
先用鬧鐘或計時器設定三十秒,在這段時間內用細字筆在每一個圈圈中畫上一個點,越多越好,然後再換另一隻手。在這項測試中,幾乎沒有人的左右手會得到一樣的結果。那到底有多少人是左利者呢?按照慣例,那些以左手完成一半以上活動的人就算是左利者。沃聖森林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 11%的人是左利者,這份抽樣足以代表整個英國,甚至西方世界的概況;不過這個比例,稍後我們會提到,在老人族群或是世界的其他地方會更低。
圖 7.2 同時也顯示出其他訊息。在男性中,左利的比例是11.6%,但女性則只有 8.6%,也就是說男人中左利的情形比女人常見,這結果和其他研究相類似。整體而言,男性左利與女性左利的比例約為五比四。這並不是多大的差距,但卻是普遍存在的事實,而且也反映出左利的重要生物機制。達爾文家族就透露出這種性別差異的線索,在八名男性中有三名左利(38%),而在六名女性中有一名左利(17%)。
認為性與偏手性有關的概念可回溯到心理學。佛洛伊德在1897 年與 1898 年時曾與懷赫姆.弗立斯(Wilhelm Fliess)通信討論這個概念,雖然他們的討論主要著重在弗立斯提出的「雙B」(Bi-Bi)理論,即雙性戀(bisexuality)與雙側性(bilaterality)的關聯。弗立斯認為潛伏的左利傾向與潛伏的同性戀傾向有關。在現代,這個想法有過一段錯綜複雜的歷史。整體而言,左利的比例在男同性戀中較男異性戀稍高,不過要解釋這份資料並不容易,因為美國在 1920 年代到 1970 年代,「左利」成了稱呼「同性戀」的俚語。在經由外科手術變性的族群中,左利也比較多,同樣地,在性別認知混淆的美國孩童中,也是左利者比較多。現階段還不清楚這些現象的成因,尤其是還要考慮統計上左利男性比女性高的這部分因素,不過可以確定的一點是,這中間存有某種模式,等待我們去解釋。
圖 7.2 還顯示了另外一件事。仔細看看在零分、一分到四分的右利者,超過三分之二的右利是高度右利。但在左利這部分則沒有那麼極端,比較一下十分到六分的左利者,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高度左利,也就是說,右利者的偏手性較左利者強烈。這部分要歸因於左利者居住在一個「右利的世界」,所有的器物用品都是依據右利者的需要設計的,從微波爐、電腦鍵盤到鋼琴都是如此,自然而然,左利者學會適應右利的世界,常常使用到右手,雖然他們並非天生如此。這點也許可以解釋圖 7.2 的一部分,但並不是完整的解釋,因為在十項問題中只有一道(剪刀那題)提到的物品是專為右利者設計的。
一個全面的解答其實更有趣,反映出許多的左利者以及一些右利者,實際上沒有特定的慣用手,可能在從事某些活動時偏用某隻手,而其他技能活動則是另一隻手。我在十二歲參加夏令營時,就發現自己正是如此。有人教我如何使用手握型的短斧,由於我是右利,自然就用右手拿著。然後我再學如何用長斧,這時有人問我:「你是左撇子嗎?」因為在下砍之前,我都將斧頭放在我的左肩上。對我而言,這是最自然的方式。圖 7.2 中,得分介於一到九之間的許多右利者與左利者,都在慣用手上展現出類似的不一致性。
大約是從十五年前,研究人員才開始嚴肅看待這個議題,探討為何有許多人沒有特定的慣用手。引發這股研究風潮的,主要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圭爾夫大學(Uni. of Guelph)的麥克.彼得斯(Michael Peters)的研究。麥克發現在三分之一的左利者中,會偏好以左手寫字,但是以右手丟球,而且右手丟得比較準。後來又發現在右利者中,有 2%–3% 的人,會以右手寫字,但偏好以左手丟球。雖然這是研究上的新發現,但有人早已記錄過這樣的現象,比方先驅的性學家哈弗洛克.伊利斯(Havelock Ellis)在他的自傳中就說過:「除了丟石頭或丟球外,我做什麼事都是用右手。⋯⋯我從來沒用過右手丟球,而且⋯⋯我也沒有以左手寫過字。」
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是以「偏手性」這個詞來討論,但有些研究者認為使用「單邊性」(sidedeness)的概念可能更貼切,因為除了左右手之外,其他許多行為層面似乎也都展現出對於某一邊的偏好,從手臂、腿、眼、耳朵到腳都是如此,其中有些不對稱與偏手性有關,但並非每項都是。
偏腳性(footedness)與偏手性有相關,慣用右手的人多半也慣用右腳,而慣用左手的則偏用左腳。要測試偏腳性的方法很直接,只要請受試者在球門前踢顆足球就會知道,踢球的腳就是慣用腳。職業足球員的偏腳性則是以他們碰觸足球的次數來判斷,球員以慣用腳來踢球的比例高達 85%,而且幾乎沒有人是平均地使用左右腳。換句話說,就算是專業球員,也不是左右腳都可以靈活運用的。他們就跟其他普通人一樣,有 20% 的人慣用左腳,這比10% 的左利者要多,這表示許多右利者具有「跨側性」(crosslateral),用右手寫字,但以左腳踢球。
耳朵的慣用主要是從接聽電話時來判斷,約有六成的人偏用右耳,四成的人偏用左耳;右利者多用右耳,而左利者偏用左耳。雖然過去對慣用耳的研究甚少,但隨著行動電話日益普及,這個情況也將有所改觀。
相較於對慣用耳的忽略,用眼的差別倒是被徹底研究過。要知道你的慣用眼是右眼還是左眼,只要將你的手臂伸長,指向遠方的一個小物體,這時閉上一隻眼,如果你的手指還指著物體,那睜開的這隻眼就是你的慣用眼;如果你睜開的是非慣用眼,手指會偏離該物體。這是眼睛的「視覺優勢」,一隻眼睛看物體的視覺會優於另一隻。「偏眼性」(eyedness)還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問題來確認,只要問受試者是用哪一隻眼睛來看鑰匙孔或是顯微鏡便可以明白。大約有七成的人偏用右眼,三成的人偏用左眼。雖然左利者中用左眼的人較多,右利者中用右眼的較多,然而還是有許多人展現出跨側性,用身體這一側的手寫字,但用另一側的眼睛看世界,這種習慣會造成什麼影響,目前仍未有定論。在 1920 年代,山繆.歐頓(Samuel Orton)認為跨側性優勢(cross-dominance)會造成閱讀障礙,引起識字困難症(dyslexia),有不少人支持這個理論,但相關證據還很薄弱。
人還有許多其他的側性,像是多數人都會用右邊的牙齒來咀嚼,但許多這種偏用某一側的特性並不特別引起大家的興趣。不過我對其中的兩種著迷了好一陣子,因為這些行為是如此的瑣碎、平凡而且毫無意義:一個是合掌,另一個是交叉手臂。要看出合掌的不同,只要立刻雙手互握,讓手指相互交錯在一起即可。哪一隻手的拇指在上面,左手還是右手?現在試試看另一種合掌的方式,你會發現自己稍微遲疑了一下,而且覺得手指之間似乎不大能密合。第一次本能性的合掌比較容易,也較自然。合掌的行為似乎不是習得的,實際上若沒有特別提出來,多數人不會注意到自己的習慣,而且這個行為很小的時候就有,如圖 7.4 所示。這是我女兒法蘭西絲卡六週大的照片,她自發性地做出合掌的動作。在英國,約有六成的人合掌時,左手拇指會在上,不論是左利還是右利族群,都是這個比例。有趣的是,一路往東調查,從歐洲、亞洲到大洋洲,便會發現這個比例也漸次下滑,到了新幾內亞東邊的所羅門群島時,左手姆指在上的比例只剩下三成。更奇妙的是,合掌的行為似乎是家族性的,雖然並不是很明顯;但通常合掌時左手在上的夫妻比右手在上的夫妻更有機會生育出左手在上的下一代。
交叉手臂是另一項可以自己測試出的側性。迅速地將伸直的手臂在胸前交叉,看看是左手腕在右手腕上,還是右手腕在左手腕上方?現在試著顛倒過來。每當我在課堂上讓學生做練習時,總是會引發一陣哄堂大笑,因為有許多人直接在胸前旋轉手臂,轉了一圈又回到原來的樣子,還是同一隻手腕在上方。要將「錯」的那隻手腕放在上方會有點困難,需要思考一下,而且會覺得有點彆扭。在英國,約有六成的人是左手腕在上方,這個比例在右利與左利的族群中是一樣的,而且不論合掌時是左拇指在上還是右拇指在上,也都是這個比例。這表示慣用手、合掌與交叉雙臂之間對於左右的偏用並無關聯。不對稱的特徵不勝枚舉,比方說有五分之一的人會抖動自己的耳朵,而只會抖動其中一隻耳朵的人當中,會抖左耳的人數是會抖右耳的兩倍。這些現象真是相當不可思議,但為何會產生這樣的不對稱特徵,至今完全是個謎。
不過,偏手性的確需要解釋,多數科學家將研究重點放在行為上的不對稱性,這麼做是有許多緣由的。首先,和其他的不對稱特徵相比,這是當中最極端的,大幅偏離了「變動型不對稱性」隨機差異造成的性狀各半之混合比例。再者,要取得大量的可靠資料也很容易,只要藉由簡單的問卷調查或是觀看人群,不論是真實生活或是照片都可以做到。因此,可試著探究多數右利與少數左利的現象出現的時間點、形成機制與原因。
達爾文對威廉的偏手性極感興趣,然而即便在詳盡的觀察之後,還是下了錯誤的結論。那麼,究竟在何時才可能確定孩子的偏手性呢?小孩的偏手性不易研究,尤其是一、兩歲的時候。實際上,在成長的階段似乎有一段模糊的時期,對於手的偏好搖擺不定,今天是右手,明天又變成左手。模糊期結束的時間也有變異,通常要到十八個月大或是兩足歲時才能確定偏手性,而在那之後,一輩子都不會改變。
既然孩童的偏手性要到兩歲時才會明確,研究人員因此認為沒有必要去調查嬰孩在那之前的偏手性,但這樣的假設卻被貝爾法斯特(Belfast)的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的彼得.海波(Peter Hepper)所推翻了。他是一名胎兒行為專家。利用超音波掃描,他發現腹中的胎兒就像嬰孩一樣,會吸吮大拇指,而且他們在十二週大時就會這麼做了。海波檢查過上百個胎兒,發現其中有超過九成的胎兒會吸吮右手拇指。由於大腦皮質的不對稱特徵也大概是在這個時期出現,海波自然會把這兩點聯想在一起,假設大腦的不對稱是造成胎兒吸吮右手拇指的主因。等到後來他檢視了十週大的胎兒,發現這時候他們雖然不會吸吮拇指,卻會揮動手臂與腿。他觀察了胎兒左右手腳運動的情形,看看其中是否有差異。結果有85% 的胎兒移動的都是右手臂。這一點意味著他之前推測大腦的不對稱發育早於肢體的想法並不正確,因為在這時期,腦中的神經元尚未連接到脊椎神經,所以這些早期的不對稱行為似乎是由脊椎神經或是肢體本身所造成的,也就顯示出偏手性並不是由大腦皮質所控制,可能是由神經系統比較下游的層級所負責。不過,目前依舊不知道這個過程是如何進行的,也不確定到底是位在哪個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