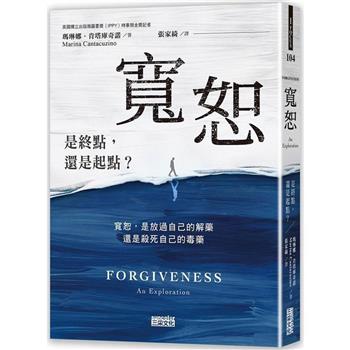第一章 雜亂無章的寬恕
「寬恕擁有廣大浩瀚的光譜……光譜一端是遊樂場上的小吵鬧,光譜另一端卻是種族大屠殺,偏偏無論哪種情境,都只能套用這兩個字。」
——作家茱莉.尼科爾森(Julie Nicholson)
***
關於寬恕的描述,我最喜歡的莫過於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名言,意思大概如下:「寬恕就像紫羅蘭,把它的香氣留在那踩扁它的腳踝上。」之所以喜歡這句話是因為它道出了寬恕的雜亂無章,雖然寬恕是傷害破壞的產物,卻也可能是療傷良藥。部分倡導寬恕的人看不見寬恕的繁複層次,一昧鼓吹寬恕是近乎萬無一失、單一簡化的療法,可以治癒個人與社會的傷口,可想而知這種定位可能讓人產生誤會。
寬恕的範圍富有彈性、可隨情況調整變化,不是一種人人適用的萬用款,也不是某次遭到輕忽冒犯後寬宏大量的單一舉動,而是人類持續修復自我破碎的進程。某些時候寬恕也許易如反掌,某些時候怎樣就是無法原諒。寬恕具有流動性,變化多端,跟所有嘗試描述寬恕的定義一樣。在我搜集網羅的故事當中,寬恕可以濃縮成一種能量,具有轉化力量卻令人心神不安、撫慰人心卻又沮喪。它具有減緩疼痛的力量,同時也可能讓人刺痛。寬恕可為憂傷帶來意義,也可能讓人困惑不解,既是矛盾對立,也清澈透明。
當我們相信自己是對的,表明自身立場、製造對立敘述,憤怒和辯解就會產生。但要是我們接受自己不是全盤皆知,我們的動機也不再是不計代價絕對要「贏」,那麼我們就能夠建立信任感。我看見寬恕與「不知」之間存在一種深遠連結,意思是我們願意擁抱矛盾和不確定。
「寬恕並不是原諒某種行為,而是原諒人類與生俱來的不完美。」我和薩曼莎.勞勒(Samantha Lawler)在明尼亞波里斯(Minneapolis)市政中心準備一場寬恕論壇活動時,她這麼說。這是我初次與薩曼莎見面,那天下午她向我敘述十八歲那年,父親在佛州羅德岱堡(Fort Lauderdale)自家勒斃母親的故事。
接踵而來的十三年,強烈交織的悲痛怨恨,讓她無聲沉默,她的人生變得一片朦朧。悲痛是因為她失去母親,憤怒是因為毀了這個家庭的人居然是父親,她下重誓這輩子再也不想見到他。「大家都告訴我哭出來比較好,」她告訴我。「所以有時我會整整一個下午都在痛哭,可是隨著一年年過去,我感受的悲痛無望卻毫無減輕。」直到薩曼莎加入地標論壇(Landmark Forum)為期三天的個人成長研討會,她才逐漸敞開心扉,這是她第一次與其他受害者產生強烈連結,課程結束後她決定和自己在人生路上失聯的人和解,於是聯絡父親的監獄安排會面。這一聯絡不得了,她聽到監獄說其實他們一直想方設法聯絡她,因為她父親正處於病危狀態,隨時可能逝世。
於是在二〇一二年十月,她從紐約出發前往佛州探視父親。她說:「我和父親只有十分鐘時間。當下我幾乎認不出他,他只剩下昔日輪廓的空殼,多次中風發作,肌肉萎縮,還患有愛滋病,需要插管呼吸,而且無法言語,還得以手銬固定在病床上。」然而那整整十分鐘,薩曼莎的父親卻目不轉睛地凝望著她,直到她情緒漸漸平息,內心卻激動萬分。她現在總算清楚看見審判日的模樣。「那一瞬間我發現他的人生正如我所期望——淒涼痛苦。但當時我卻深深明白,他承受的痛苦並不能減輕我的痛苦,我們兩人長期承受的痛苦非但枉然,也對我本來獲得療癒的可能性毫無助益。看見他慘不忍睹的模樣,令我深感震驚,過往恩怨瞬間一筆勾消。我不斷告訴他我有多愛他,我已經原諒他,並為了我這麼晚才來探望他、告訴他這些話道歉,後來我發現在那十分鐘,我們之間並不存在仇恨或罪惡感,沒有所謂對與錯,只存在一種不需要言語、不需要道歉的深沉連結。在那十分鐘內,我又找回我的爸爸,離開監獄時,我總算感覺沉重重量逐漸瓦解。」
「寬恕並不是原諒某種行為,而是原諒人類與生俱來的不完美。」我一直很欣賞薩曼莎對於寬恕的詮釋,寬恕不只是原諒既成傷害那麼簡單,也讓我們擔起人類犯錯的責任,畢竟我們不過只是脆弱的人類。她的觀點也讓我理解,為何有些人能夠原諒多數人覺得不可饒恕的事。我現在明白了,當人們原諒令人髮指的暴行與邪惡,他們原諒的其實不是罪行,而是人人皆會犯錯失敗的人性本質。他們之所以發揮同理心,不是因為他們能夠容忍自己遭遇的傷害,而是因為他們能對那些思想扭曲、殘酷無情的人,也就是莎士比亞形容的「大自然的受損品」產生同情心。他們可以站在對方殘敗不堪的立場,想像他們為何如此鐵石心腸,只能任憑變態衝動吞噬自我。
當你聽到最近某起罪不可赦的殘酷暴行,新聞標題挾帶「禽獸」、「惡魔」、「野獸」等字眼時,或許會覺得這些形容都再恰當不過,在這種令人產生強烈道德反感的時刻,要想像這種人值得原諒實在不容易,但確實有人罕見地選擇原諒這些社會稱為「野獸」的人,用意卻不是替他們辯解,只是為了釋放自我。另一個可能就是選擇原諒的一方能夠理解,罪犯犯下的惡行不過反映出一個人的童年創傷,他們可以理解在暴力和缺乏關愛的環境下長大,一個人可能會出現道德缺陷的情況,長大後就變成忿忿不平的大人,進而演變成社會問題。再不然選擇原諒的人可能只是把罪行當作一種遭到暴力影響或洗腦的後果,以致於無法產生正常的同理心,無法分辨是非對錯。同理心就像是肌肉,要是不鍛鍊,它就會失去功用,癱軟無力。
在《你認識的惡魔》(The Devil You Know)中,關.亞德歇(Gwen Adshead)分享她在英格蘭高度警戒的布羅德摩精神病院擔任精神科醫師的經驗談。她在序言中挑戰讀者踏進一個世界,而在這個世界裡「良善與邪惡、是非對錯、受害人與加害人,定義絕對不是黑白分明、不可翻轉,而是一種可能並存的共生關係」。在了解良善與邪惡之間的親密連結後,我總算明白為何有人可以原諒玷污人性本質、難以輕饒的惡行。作家兼大屠殺倖存者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談及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警衛時,也點出相同連結:「那裡沒有惡魔。我在集中營時一個惡魔都沒看見,只看見如同你我的人,而他們只是因為德國盛行法西斯主義和納粹勢力崛起,才會變成那樣。如果法西斯主義或納粹勢力又死灰復燃,諸如你我的人也會變成那樣,而且處處可見。」
《一九一八~一九五六年的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也反映出相同情懷,反政府立場的俄羅斯諾貝爾獎得主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精闢解釋,為何我們不想為人類的可憎惡行負責:「若單純只有惡人躲在陰暗角落犯罪,那很簡單,我們只需要將這些人繩之以法,摧毀他們就好。偏偏區分良善與邪惡的那條線亦刺穿每顆人類的心臟,而又有誰願意毀滅自己的心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