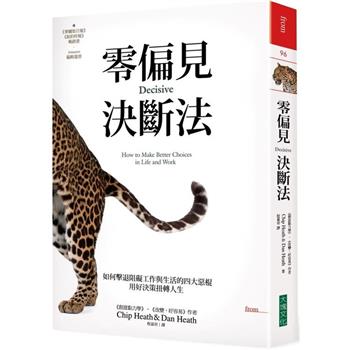-決策會遇到的四大惡棍-
1.
史迪夫•寇爾(Steve Cole)在非營利組織希望實驗室(HopeLab)擔任研發副總裁。實驗室成立的宗旨,是希望運用科技來提升青少年的身體健康。他說:「生活中,我們總會想:『我到底該做這件事或那件事?』要不要試著這樣問:『有沒有什麼方法,能讓我同時做這件事和那件事?』或許令人難以置信,但在多數情況下,人們是可以同時完成兩件工作的。」
寇爾帶領希望實驗室的團隊執行一項重要企畫,要尋找具專業設計能力的夥伴,一起完成某種行動裝置,以衡量青少年的運動量。舊金山灣區具備這種能力的公司至少有七、八家。依商業議約的常規,希望實驗室會請這幾家廠商各自提出建議書,之後從中挑出最好的一家簽約。
但寇爾這次沒這麼做,他用的是「賽馬模式」(horse race)。他縮減了工作範圍,使之僅涵蓋此企畫的第一階段,然後同時請五家廠商各自進行第一階段的工作(特別要澄清的是,寇爾並未把預算變成五倍──作為非營利組織,希望實驗室的資源有限。寇爾知道,他在第一回合學到的東西,會讓後續幾個回合更具效益)。
經過這樣的程序,寇爾掌握了行動裝置幾種不同的設計腹案。在接下來的設計工作中,或是選取他最喜歡的設計,或是擷取各家精華;他還可以把配合度不好或效率不佳的廠商先刷掉。
寇爾這種做法是在對付決策行為上會遇到的第一個惡棍──「偏狹的框架」(narrow framing)。也就是在界定選項時,經常過於狹窄,甚至掉入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有人會問:「到底要不要跟夥伴拆夥?」而不是問:「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搞好跟夥伴的關係?」有人會問:「該不該買部新車?」而不是問:「要讓我們一家人生活更優裕,錢該怎麼花才是最上算的?」
在引言中提到的例子,若是問:「香儂該不該請克里夫走路?」思維就卡在偏狹的框架裡了。也就是說,我們只聚焦在單一選項,而放棄了所有其他可能。
寇爾採取的賽馬模式,是跳出陷阱的一種方法。這種做法並不容易為人所理解,他必須在組織內部據理力爭。「起初,同仁都覺得我瘋了。因為初期要投入不少錢,也需要時間。不過,現在大家都這麼做了!(用這種方法)我們有機會見到更多人,瞭解這個產業更多的面向。你得以整合不同的議題,所以你清楚那都是正確的,並且也學會欣賞每家公司的獨到之處。這些都不是跟某人聊聊天就可以掌握的訊息。況且,五家廠商都知道還有其他四家競爭對手,必定會把最好的拿出來。」
看看這跟「正反意見表列法」有什麼不同。寇爾可以針對每家廠商分別列出優缺點,分析評估後就做出決定。然而,這會陷入偏狹的框架中。也就是說,下意識裡,我們會認為只有一家廠商獨具能力,可以提出完美的解決辦法,而且只要從廠商提出的建議文件就可以做出判斷。
2.
還有一個不容易覺察的面向是,當寇爾跟廠商分別接觸後,很難避免會有自己的偏好,總有比較合得來的廠商。理智上,他或許知道,個人偏愛的廠商未必能做出最好的產品,但是在表列正反意見時,頗有可能會偷偷給這家廠商加重計分。寇爾自己甚至未必能覺察這樣的情況。因為,不管正面、反面,全是自己腦袋的產物,我們極容易會有偏見。當我們自以為在做不偏不倚的比較時,腦袋卻是聽從本能直覺在運作。
生活中慣常的習性是這樣的:面對某種情境,迅速產生某種信念,之後再去尋找支撐這個信念的訊息。這種大有問題的習性稱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這是決策行為會遇到的第二個惡棍。
一九六○年代,與抽煙相關的研究很多。最經典的例子是:當時的醫學研究對抽煙產生的危害並不那麼清楚,當抽煙者面對「抽煙不會導致肺癌」與「抽煙將導致肺癌」兩份報告時,願意看前一篇的人總是多一點(如果要知道這種習性會如何導致品質不良的決策,可以設想一種情境:你的老闆盯著面前的兩份報告-「支持你的意見的佐證資料」與「反對你的意見的佐證資料」,看看在會議上,哪一本被提出來的機會比較大)。
研究人員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相同的結論,當人們有機會從這個世界蒐集資訊的時候,多會傾向選取可支撐他們既有態度、信念或行動的相關訊息。政黨人物會找支持他們的媒體作為發聲的管道,從來不會找另一方的見解來檢視自己的信念。急著買新車或電腦的人,會找到理由合理化自己的購買行為,卻不會同樣賣力地找出該延遲購買的理由。
「確認偏誤」的弔詭,在於它可以看起來很「科學」。我們不是一天到晚在蒐集資料嗎!引言裡提過的專事研究決策的洛瓦羅教授說:「『確認偏誤』或許是企業人士唯一最大的課題,即使是最具經驗的管理工作者也會算計錯誤。人們忙進忙出,到處搜羅資料,卻渾然不覺自己根本是在造假!」
在工作與生活中,我們經常假裝想要得到真相,骨子裡其實是在尋找自信。「這件牛仔褲讓我看起來很肥嗎?」「你覺得我這首詩寫得如何?」這類發問,是沒有辦法得到誠實的回答。
也見過連音階都抓不準的拙劣歌手參加電視歌唱比賽,當評審給出無情的評論時,卻是一臉錯愕,受到嚴重打擊的樣子。於是我們瞭解,這可能是他這輩子第一次聽到最誠實的意見。或許是急於尋求更進一步的肯定,這些人的聚光燈就只停留在親朋好友給予的鼓勵和支持上。不難理解的是,在這類的肯定聲中,他們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有機會成為新的人氣偶像。殊不知,這是從一堆極度扭曲的資料所推導出來的合理結論。
這是「確認偏誤」之所以可怕的地方:當我們希望某件事是真的,就會把聚光燈打在支持這件事的事證上,之後,就從燈下所見的事物,推導出想要的結論,然後恭喜自己做了非常合理的決定!真是傷腦筋!
3.
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在他的回憶錄《十倍速時代》(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中提到,一九八五年他擔任英特爾(Intel)總裁時,面對的重大決定是,要不要砍掉記憶晶片這條產品線。英特爾是從記憶晶片起家。早期,它是市場上唯一的供應來源。然而,一九七○年代末,有十多家競爭者相繼加入市場。
當時,英特爾已經發展出另一項產品-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一九八一年IBM的新產品「個人電腦」選定英特爾這款微處理器作為核心,更是一項重大突破。於是,英特爾匆忙建置了微處理器的生產線,因應可能的市場需求。
這時候,英特爾成了有兩種主力產品的公司:記憶晶片與微處理器。當時,記憶晶片是公司的主要營收來源。一九八○年代初期,日本廠商進入市場,威脅了英特爾原本具備的市場優勢。「從日本參訪回來的人所描述的狀況,令人心驚。」葛洛夫說。當時,有人說,某家日本公司同時進行數個世代的記憶晶片設計,十六K的設計小組在一個樓層,六十四K的設計團隊在樓上,二五六K則在更上面一個樓層。
英特爾的客戶這時開始吹捧日系廠商記憶晶片的品質優異。「事實上,日系廠商宣稱的品質水準,以我們的理解,是根本做不到的。」葛洛夫說:「我們直覺的反應就是否認。然而,這真是錯的離譜。就像多數人遇上類似狀況時那般,異口同聲猛烈抨擊,認為這些訊息不正確。直到自己人確認了客戶之前的說法大致可信後,才開始改善品質。於是,我們被遠遠地拋在後頭了。」
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這十年間,日系廠商的市占率從三○%成長到六○%。如何因應日本廠商這波攻勢,英特爾內部掀起了熱烈的討論。有人主張投資規模更大的記憶晶片新廠,在生產技術上躍進,超越日本人;有人主張繼續投入更先進的設計技術,讓日本人追不上;還有第三陣營則主張加倍投入公司進入特定領域市場的新策略。
爭論持續了一陣子,沒有結論。公司虧損愈益嚴重。雖然微處理器業務成長迅速,但記憶體業務的下滑,拖累了公司的獲利能力。葛洛夫回憶一九八四年時是這麼說的:「那是極度嚴酷和挫折的一年。我們努力工作,卻根本看不清楚要怎麼做才能翻轉公司的狀況。完全失去了方向。」
又經過了幾個月沒有結果的爭論,到了一九八五年中,葛洛夫與英特爾的董事長兼執行長戈登•摩爾(Gordon Moore),在辦公室討論這個陷入無所適從的記憶晶片業務。他們兩位已經被公司內部沒完沒了的爭論,搞得疲憊不堪。那時,葛洛夫突然有了靈感:
我望著窗外遠處大美洲主題樂園(Great America amusement park)裡旋轉中的摩天輪,一陣子後,轉身對戈登說:「如果我們被掃地出門,董事會找來新的執行長,你覺得他會怎麼處理這件事?」戈登毫不遲疑地回答道:「他會要我們退出記憶晶片業務。」
我面無表情地看著他,過了好一會,開口說:「那,要不要我們兩個走出這道門再走進來,自己解決這個問題?」
那真是個清醒的時刻。從沒有歷史包袱、遠離內部爭議的外人的視角來檢視,收掉記憶晶片事業是再清楚不過的選擇了。轉換視角──「如果是別人接手,會怎麼做?」──終於讓戈登和葛洛夫清楚地看到更廣闊的天地。
當然,要退出記憶晶片市場不是件容易的事。內部激烈反對的人不在少數。有人認為記憶體技術是英特爾的核心能力所在,放棄這項產品,終將導致相關技術領域的研發失去活水源頭。有人則堅信,英特爾的業務團隊如果沒有辦法同時提供全系列的記憶晶片與微處理器產品,就沒有辦法得到客戶的青睞。
在業務團隊咬牙切齒發了好一陣子牢騷之後,葛洛夫堅持要求他們向客戶明確表示,公司未來不會再銷售記憶晶片。多數客戶聽到這消息時的反應是打個大呵欠,有個客戶說:「你們這個決定可真是花了不少時間哪!」
一九八五年英特爾做了這個決策後,主宰了微處理器的市場。如果在葛洛夫靈光乍現那天,投資一千美元在英特爾,到二○一二年,市值則高達四萬七千美元(比標準普爾五百指數的七千六百美元高出很多)。可以很篤定地說,當時葛洛夫的確做了正確的決定。
✽
葛洛夫的這段敘述,點出了許多專家學者對決策的看法有著嚴重的缺陷。檢視與決策相關的諸多研究文獻,可以發現,許多所謂的決策模式,基本上都只是洋洋灑灑的一套試算表。如果你打算買棟房子,或許會把看過的八間標的物,依照價位、地點、坪數等幾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排序,之後再給這些因素不同的權重(例如:價位比坪數重要),然後開始計算,找出答案(嗯,還是搬回去跟父母住吧)。
這類分析少了一個關鍵因素-情緒。葛洛夫面對這項決定時,困難之處並不在於缺乏資訊,也並非不知道選項,而是他感受到很多矛盾,腦中充滿短期壓力、公司裡不同陣營各執己見的紛擾,凡此種種,讓他看不見必須退出記憶晶片市場的長期考量。
這是決策行為會遇到的第三個惡棍-「短期的情緒」(short-term emotion)。遇上困難的決定時,人們會思緒翻騰,腦袋重複著相同的論述,對於所處的情境焦慮不安,每天都有不同的想法冒出來。如果要做的決定真的是只用試算表就可以呈現,只要沒有新的訊息加入,基本上,試算表中的數字是不會變化的。然而,腦袋並不是這般運作的,我們的腦子不斷揚起大量的沙塵,使我們看不清前方的道路。這時候,最需要的是找到不同的視角。
富蘭克林很清楚這種短暫的情緒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他在「心智代數」裡給了很有智慧的建議:寫完正反意見之後,多放幾天,讓某個特定的想法可以隨著情緒起伏而有所增刪。畢竟,深度評估選項與放大視野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方式。毫無疑問的,葛洛夫在這幾年間,肯定曾列出該不該退出記憶晶片市場的所有正反意見。然而,分析到最後還是卡住了。所幸他能快速抽離,從接手的人會怎麼做的視角來思考,順利過了這關。
4.
(核子反應爐)發生爐心熔毀的機會,一萬年才會有一次。
──威達利•斯開亞洛夫(Vitali Sklyarov)
烏克蘭電力部部長,車諾比核電廠出事前兩個月
哪些傢伙會想聽演員講話?
──哈利•華納(Harry Warner)
華納製片公司,一九二七年
這家公司做出來的電子玩具能有什麼用處呢?
──威廉•歐通(William Orton)
西聯電報公司(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mpany)總裁
一八七六年他錯失良機,沒能買下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發明的電話專利權
談到決策行為會遇到的第四個惡棍之前,先把時間倒回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當時四個年輕人組成的搖滾樂團披頭四(Beatles),應英國主要音樂製作公司之一的德卡唱片(Decca Records)之邀,到倫敦試唱。「我們非常興奮,」約翰•藍儂(John Lennon)在回憶時說道:「是德卡耶!」在一個鐘頭的試唱裡,披頭四演唱了十五首曲子,多是知名曲目。唱完後,披頭四跟樂團經紀人布萊恩•艾普思坦(Brian Epstein)滿心期待地等著,希望能把合約簽下來。
最後等到的回覆是:德卡決定放棄。唱片公司傑出的星探迪克•羅威(Dick Rowe)寫了封信給艾普思坦:「我們不喜歡這些年輕人的樣子,我認為多人組成的樂團沒有前景,吉他四人組的樂團更是看不到未來!」
羅威不久後就會發現,他碰上了決策行為中的第四大惡棍-「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我們都自認知道的夠多,能掌握未來所有的事情。
回到前面的案例,葛洛夫的同事不是振振有詞的認為,如果英特爾不再生產記憶晶片,我們會失去技術研發的活水源頭;業務團隊也將因為產品線不完整而無法有所成就。事實證明這是錯的:英特爾的技術研發和業務一直非常健全。然而,很有意思的是,當時提出這些看法的人絲毫不覺得有什麼不確定性,也不會用模稜兩可的說法來表達看法,像是「有沒有可能會……」或「我有點擔心,總有一天會……」。他們就是很篤定自己的看法絕對正確。
有個研究發現,醫生們判定為絕對正確的診斷,有四○%是誤診。一群學生認為只有一%錯誤率的事,事後發現錯誤率高達二七%。
我們就是太相信自己對未來的看法。當我們對未來的事情表達意見時,會把聚光燈照在手邊可以掌握的訊息,並且只根據這些導出結論。想像一下,某家旅行社的負責人在一九九二年是這麼說的:我們是鳳凰城地區的市場領導者,客戶關係維繫得非常好。這地區的市場會快速成長,未來十年擴充一倍易如反掌。我們得跑在市場前面,新的分公司得趕緊設立。
問題是,我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是我們不知道的。哎呀!網際網路來了。關於這家旅行社就先談到這裡了。
未來總是有股神秘的力量讓我們震驚。對於不知道的事情,連聚光燈該怎麼打恐怕都束手無策。
✽
談到這裡,先做個整理。正常的決策程序通常包含以下四個步驟:
• 面臨抉擇。
• 分析選項。
• 做出選擇。
• 安於現狀。
從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見,每個階段都會遇上讓人頭痛的惡棍:
• 面臨抉擇。但「偏狹的框架」讓我們少了很多選項。
• 分析選項。但「確認偏誤」讓我們只蒐集支撐自己想法的訊息。
• 做出選擇。但「短期的情緒」常引誘我們做出錯誤的決定。
• 安於現狀。但「過度自信」讓我們誤以為可以掌握未來發生的所有事情。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很清楚我們真正面對的是什麼了吧!我們知道,決策會遇到四大惡棍,還知道「正反意見表列法」不足以對抗這四大惡棍,說白一點,連最起碼的應付都做不到。
瞭解了這些之後,我們來把注意力轉移到樂觀一點的想法上:要用什麼樣的程序,方能打敗這幾個惡棍,做出好一點的決定呢?
(未完)
1.
史迪夫•寇爾(Steve Cole)在非營利組織希望實驗室(HopeLab)擔任研發副總裁。實驗室成立的宗旨,是希望運用科技來提升青少年的身體健康。他說:「生活中,我們總會想:『我到底該做這件事或那件事?』要不要試著這樣問:『有沒有什麼方法,能讓我同時做這件事和那件事?』或許令人難以置信,但在多數情況下,人們是可以同時完成兩件工作的。」
寇爾帶領希望實驗室的團隊執行一項重要企畫,要尋找具專業設計能力的夥伴,一起完成某種行動裝置,以衡量青少年的運動量。舊金山灣區具備這種能力的公司至少有七、八家。依商業議約的常規,希望實驗室會請這幾家廠商各自提出建議書,之後從中挑出最好的一家簽約。
但寇爾這次沒這麼做,他用的是「賽馬模式」(horse race)。他縮減了工作範圍,使之僅涵蓋此企畫的第一階段,然後同時請五家廠商各自進行第一階段的工作(特別要澄清的是,寇爾並未把預算變成五倍──作為非營利組織,希望實驗室的資源有限。寇爾知道,他在第一回合學到的東西,會讓後續幾個回合更具效益)。
經過這樣的程序,寇爾掌握了行動裝置幾種不同的設計腹案。在接下來的設計工作中,或是選取他最喜歡的設計,或是擷取各家精華;他還可以把配合度不好或效率不佳的廠商先刷掉。
寇爾這種做法是在對付決策行為上會遇到的第一個惡棍──「偏狹的框架」(narrow framing)。也就是在界定選項時,經常過於狹窄,甚至掉入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有人會問:「到底要不要跟夥伴拆夥?」而不是問:「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搞好跟夥伴的關係?」有人會問:「該不該買部新車?」而不是問:「要讓我們一家人生活更優裕,錢該怎麼花才是最上算的?」
在引言中提到的例子,若是問:「香儂該不該請克里夫走路?」思維就卡在偏狹的框架裡了。也就是說,我們只聚焦在單一選項,而放棄了所有其他可能。
寇爾採取的賽馬模式,是跳出陷阱的一種方法。這種做法並不容易為人所理解,他必須在組織內部據理力爭。「起初,同仁都覺得我瘋了。因為初期要投入不少錢,也需要時間。不過,現在大家都這麼做了!(用這種方法)我們有機會見到更多人,瞭解這個產業更多的面向。你得以整合不同的議題,所以你清楚那都是正確的,並且也學會欣賞每家公司的獨到之處。這些都不是跟某人聊聊天就可以掌握的訊息。況且,五家廠商都知道還有其他四家競爭對手,必定會把最好的拿出來。」
看看這跟「正反意見表列法」有什麼不同。寇爾可以針對每家廠商分別列出優缺點,分析評估後就做出決定。然而,這會陷入偏狹的框架中。也就是說,下意識裡,我們會認為只有一家廠商獨具能力,可以提出完美的解決辦法,而且只要從廠商提出的建議文件就可以做出判斷。
2.
還有一個不容易覺察的面向是,當寇爾跟廠商分別接觸後,很難避免會有自己的偏好,總有比較合得來的廠商。理智上,他或許知道,個人偏愛的廠商未必能做出最好的產品,但是在表列正反意見時,頗有可能會偷偷給這家廠商加重計分。寇爾自己甚至未必能覺察這樣的情況。因為,不管正面、反面,全是自己腦袋的產物,我們極容易會有偏見。當我們自以為在做不偏不倚的比較時,腦袋卻是聽從本能直覺在運作。
生活中慣常的習性是這樣的:面對某種情境,迅速產生某種信念,之後再去尋找支撐這個信念的訊息。這種大有問題的習性稱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這是決策行為會遇到的第二個惡棍。
一九六○年代,與抽煙相關的研究很多。最經典的例子是:當時的醫學研究對抽煙產生的危害並不那麼清楚,當抽煙者面對「抽煙不會導致肺癌」與「抽煙將導致肺癌」兩份報告時,願意看前一篇的人總是多一點(如果要知道這種習性會如何導致品質不良的決策,可以設想一種情境:你的老闆盯著面前的兩份報告-「支持你的意見的佐證資料」與「反對你的意見的佐證資料」,看看在會議上,哪一本被提出來的機會比較大)。
研究人員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相同的結論,當人們有機會從這個世界蒐集資訊的時候,多會傾向選取可支撐他們既有態度、信念或行動的相關訊息。政黨人物會找支持他們的媒體作為發聲的管道,從來不會找另一方的見解來檢視自己的信念。急著買新車或電腦的人,會找到理由合理化自己的購買行為,卻不會同樣賣力地找出該延遲購買的理由。
「確認偏誤」的弔詭,在於它可以看起來很「科學」。我們不是一天到晚在蒐集資料嗎!引言裡提過的專事研究決策的洛瓦羅教授說:「『確認偏誤』或許是企業人士唯一最大的課題,即使是最具經驗的管理工作者也會算計錯誤。人們忙進忙出,到處搜羅資料,卻渾然不覺自己根本是在造假!」
在工作與生活中,我們經常假裝想要得到真相,骨子裡其實是在尋找自信。「這件牛仔褲讓我看起來很肥嗎?」「你覺得我這首詩寫得如何?」這類發問,是沒有辦法得到誠實的回答。
也見過連音階都抓不準的拙劣歌手參加電視歌唱比賽,當評審給出無情的評論時,卻是一臉錯愕,受到嚴重打擊的樣子。於是我們瞭解,這可能是他這輩子第一次聽到最誠實的意見。或許是急於尋求更進一步的肯定,這些人的聚光燈就只停留在親朋好友給予的鼓勵和支持上。不難理解的是,在這類的肯定聲中,他們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有機會成為新的人氣偶像。殊不知,這是從一堆極度扭曲的資料所推導出來的合理結論。
這是「確認偏誤」之所以可怕的地方:當我們希望某件事是真的,就會把聚光燈打在支持這件事的事證上,之後,就從燈下所見的事物,推導出想要的結論,然後恭喜自己做了非常合理的決定!真是傷腦筋!
3.
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在他的回憶錄《十倍速時代》(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中提到,一九八五年他擔任英特爾(Intel)總裁時,面對的重大決定是,要不要砍掉記憶晶片這條產品線。英特爾是從記憶晶片起家。早期,它是市場上唯一的供應來源。然而,一九七○年代末,有十多家競爭者相繼加入市場。
當時,英特爾已經發展出另一項產品-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一九八一年IBM的新產品「個人電腦」選定英特爾這款微處理器作為核心,更是一項重大突破。於是,英特爾匆忙建置了微處理器的生產線,因應可能的市場需求。
這時候,英特爾成了有兩種主力產品的公司:記憶晶片與微處理器。當時,記憶晶片是公司的主要營收來源。一九八○年代初期,日本廠商進入市場,威脅了英特爾原本具備的市場優勢。「從日本參訪回來的人所描述的狀況,令人心驚。」葛洛夫說。當時,有人說,某家日本公司同時進行數個世代的記憶晶片設計,十六K的設計小組在一個樓層,六十四K的設計團隊在樓上,二五六K則在更上面一個樓層。
英特爾的客戶這時開始吹捧日系廠商記憶晶片的品質優異。「事實上,日系廠商宣稱的品質水準,以我們的理解,是根本做不到的。」葛洛夫說:「我們直覺的反應就是否認。然而,這真是錯的離譜。就像多數人遇上類似狀況時那般,異口同聲猛烈抨擊,認為這些訊息不正確。直到自己人確認了客戶之前的說法大致可信後,才開始改善品質。於是,我們被遠遠地拋在後頭了。」
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這十年間,日系廠商的市占率從三○%成長到六○%。如何因應日本廠商這波攻勢,英特爾內部掀起了熱烈的討論。有人主張投資規模更大的記憶晶片新廠,在生產技術上躍進,超越日本人;有人主張繼續投入更先進的設計技術,讓日本人追不上;還有第三陣營則主張加倍投入公司進入特定領域市場的新策略。
爭論持續了一陣子,沒有結論。公司虧損愈益嚴重。雖然微處理器業務成長迅速,但記憶體業務的下滑,拖累了公司的獲利能力。葛洛夫回憶一九八四年時是這麼說的:「那是極度嚴酷和挫折的一年。我們努力工作,卻根本看不清楚要怎麼做才能翻轉公司的狀況。完全失去了方向。」
又經過了幾個月沒有結果的爭論,到了一九八五年中,葛洛夫與英特爾的董事長兼執行長戈登•摩爾(Gordon Moore),在辦公室討論這個陷入無所適從的記憶晶片業務。他們兩位已經被公司內部沒完沒了的爭論,搞得疲憊不堪。那時,葛洛夫突然有了靈感:
我望著窗外遠處大美洲主題樂園(Great America amusement park)裡旋轉中的摩天輪,一陣子後,轉身對戈登說:「如果我們被掃地出門,董事會找來新的執行長,你覺得他會怎麼處理這件事?」戈登毫不遲疑地回答道:「他會要我們退出記憶晶片業務。」
我面無表情地看著他,過了好一會,開口說:「那,要不要我們兩個走出這道門再走進來,自己解決這個問題?」
那真是個清醒的時刻。從沒有歷史包袱、遠離內部爭議的外人的視角來檢視,收掉記憶晶片事業是再清楚不過的選擇了。轉換視角──「如果是別人接手,會怎麼做?」──終於讓戈登和葛洛夫清楚地看到更廣闊的天地。
當然,要退出記憶晶片市場不是件容易的事。內部激烈反對的人不在少數。有人認為記憶體技術是英特爾的核心能力所在,放棄這項產品,終將導致相關技術領域的研發失去活水源頭。有人則堅信,英特爾的業務團隊如果沒有辦法同時提供全系列的記憶晶片與微處理器產品,就沒有辦法得到客戶的青睞。
在業務團隊咬牙切齒發了好一陣子牢騷之後,葛洛夫堅持要求他們向客戶明確表示,公司未來不會再銷售記憶晶片。多數客戶聽到這消息時的反應是打個大呵欠,有個客戶說:「你們這個決定可真是花了不少時間哪!」
一九八五年英特爾做了這個決策後,主宰了微處理器的市場。如果在葛洛夫靈光乍現那天,投資一千美元在英特爾,到二○一二年,市值則高達四萬七千美元(比標準普爾五百指數的七千六百美元高出很多)。可以很篤定地說,當時葛洛夫的確做了正確的決定。
✽
葛洛夫的這段敘述,點出了許多專家學者對決策的看法有著嚴重的缺陷。檢視與決策相關的諸多研究文獻,可以發現,許多所謂的決策模式,基本上都只是洋洋灑灑的一套試算表。如果你打算買棟房子,或許會把看過的八間標的物,依照價位、地點、坪數等幾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排序,之後再給這些因素不同的權重(例如:價位比坪數重要),然後開始計算,找出答案(嗯,還是搬回去跟父母住吧)。
這類分析少了一個關鍵因素-情緒。葛洛夫面對這項決定時,困難之處並不在於缺乏資訊,也並非不知道選項,而是他感受到很多矛盾,腦中充滿短期壓力、公司裡不同陣營各執己見的紛擾,凡此種種,讓他看不見必須退出記憶晶片市場的長期考量。
這是決策行為會遇到的第三個惡棍-「短期的情緒」(short-term emotion)。遇上困難的決定時,人們會思緒翻騰,腦袋重複著相同的論述,對於所處的情境焦慮不安,每天都有不同的想法冒出來。如果要做的決定真的是只用試算表就可以呈現,只要沒有新的訊息加入,基本上,試算表中的數字是不會變化的。然而,腦袋並不是這般運作的,我們的腦子不斷揚起大量的沙塵,使我們看不清前方的道路。這時候,最需要的是找到不同的視角。
富蘭克林很清楚這種短暫的情緒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他在「心智代數」裡給了很有智慧的建議:寫完正反意見之後,多放幾天,讓某個特定的想法可以隨著情緒起伏而有所增刪。畢竟,深度評估選項與放大視野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方式。毫無疑問的,葛洛夫在這幾年間,肯定曾列出該不該退出記憶晶片市場的所有正反意見。然而,分析到最後還是卡住了。所幸他能快速抽離,從接手的人會怎麼做的視角來思考,順利過了這關。
4.
(核子反應爐)發生爐心熔毀的機會,一萬年才會有一次。
──威達利•斯開亞洛夫(Vitali Sklyarov)
烏克蘭電力部部長,車諾比核電廠出事前兩個月
哪些傢伙會想聽演員講話?
──哈利•華納(Harry Warner)
華納製片公司,一九二七年
這家公司做出來的電子玩具能有什麼用處呢?
──威廉•歐通(William Orton)
西聯電報公司(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mpany)總裁
一八七六年他錯失良機,沒能買下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發明的電話專利權
談到決策行為會遇到的第四個惡棍之前,先把時間倒回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當時四個年輕人組成的搖滾樂團披頭四(Beatles),應英國主要音樂製作公司之一的德卡唱片(Decca Records)之邀,到倫敦試唱。「我們非常興奮,」約翰•藍儂(John Lennon)在回憶時說道:「是德卡耶!」在一個鐘頭的試唱裡,披頭四演唱了十五首曲子,多是知名曲目。唱完後,披頭四跟樂團經紀人布萊恩•艾普思坦(Brian Epstein)滿心期待地等著,希望能把合約簽下來。
最後等到的回覆是:德卡決定放棄。唱片公司傑出的星探迪克•羅威(Dick Rowe)寫了封信給艾普思坦:「我們不喜歡這些年輕人的樣子,我認為多人組成的樂團沒有前景,吉他四人組的樂團更是看不到未來!」
羅威不久後就會發現,他碰上了決策行為中的第四大惡棍-「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我們都自認知道的夠多,能掌握未來所有的事情。
回到前面的案例,葛洛夫的同事不是振振有詞的認為,如果英特爾不再生產記憶晶片,我們會失去技術研發的活水源頭;業務團隊也將因為產品線不完整而無法有所成就。事實證明這是錯的:英特爾的技術研發和業務一直非常健全。然而,很有意思的是,當時提出這些看法的人絲毫不覺得有什麼不確定性,也不會用模稜兩可的說法來表達看法,像是「有沒有可能會……」或「我有點擔心,總有一天會……」。他們就是很篤定自己的看法絕對正確。
有個研究發現,醫生們判定為絕對正確的診斷,有四○%是誤診。一群學生認為只有一%錯誤率的事,事後發現錯誤率高達二七%。
我們就是太相信自己對未來的看法。當我們對未來的事情表達意見時,會把聚光燈照在手邊可以掌握的訊息,並且只根據這些導出結論。想像一下,某家旅行社的負責人在一九九二年是這麼說的:我們是鳳凰城地區的市場領導者,客戶關係維繫得非常好。這地區的市場會快速成長,未來十年擴充一倍易如反掌。我們得跑在市場前面,新的分公司得趕緊設立。
問題是,我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是我們不知道的。哎呀!網際網路來了。關於這家旅行社就先談到這裡了。
未來總是有股神秘的力量讓我們震驚。對於不知道的事情,連聚光燈該怎麼打恐怕都束手無策。
✽
談到這裡,先做個整理。正常的決策程序通常包含以下四個步驟:
• 面臨抉擇。
• 分析選項。
• 做出選擇。
• 安於現狀。
從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見,每個階段都會遇上讓人頭痛的惡棍:
• 面臨抉擇。但「偏狹的框架」讓我們少了很多選項。
• 分析選項。但「確認偏誤」讓我們只蒐集支撐自己想法的訊息。
• 做出選擇。但「短期的情緒」常引誘我們做出錯誤的決定。
• 安於現狀。但「過度自信」讓我們誤以為可以掌握未來發生的所有事情。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很清楚我們真正面對的是什麼了吧!我們知道,決策會遇到四大惡棍,還知道「正反意見表列法」不足以對抗這四大惡棍,說白一點,連最起碼的應付都做不到。
瞭解了這些之後,我們來把注意力轉移到樂觀一點的想法上:要用什麼樣的程序,方能打敗這幾個惡棍,做出好一點的決定呢?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