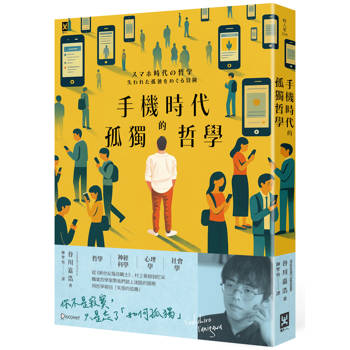〔試閱一〕
聚在一起高談闊論,卻無意聆聽別人的現代社會
尼采說:「你們的拚命工作只是一種自我逃避」。我們就從他批判的對象,也就是我們「自我逃避的模樣」開始說起吧。我們逃避自己的本領可不是蓋的。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這種狀態,不妨認識一下哲學家何塞.奧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奧特加是一位西班牙哲學家。哲學跟西班牙的組合很稀奇吧?但值得各位關注的,是他的著作《大眾的反叛》。奧特加分析了現代社會的特徵,並且從顯而易見的現象切入:城市的擁擠。
城市裡人滿為患,租屋供不應求,旅館一房難求,火車座無虛席,咖啡館裡萬頭攢動,公園裡散步者比肩繼踵,名醫的診療室裡病人大排長龍,劇院場場爆滿,海灘上也擠滿了戲水的人。尋找空間這件事,在過去根本稱不上是問題,如今卻幾乎成為日常的麻煩。
總之,人多得亂成一團。奧特加認為,一言以蔽之,城市的特徵無非就是人多。儘管城市裡聚集了擁有多元背景與屬性的人,但大家都一窩蜂地擠到相同的地方,彷彿這種多元性根本不存在。
也許有人會想:新冠疫情下遠距工作模式普及,或是移居外地的風潮,已經讓狀況有些改變。不過,只要大家能理解人對於「想要在場親身參與話題」的執念,那麼奧特加的論述至今依然適用。各位可以回想一下,我們是如何成群結隊地關注熱門新聞與內容,或是總覺得不能錯過,非得稍微瞄一眼群眾談論的八卦?無論在線上或是線下,這種「一窩蜂」的現象,正是我們社會的基本特徵。而奧特加依據這個觀察,進一步指出另一個重要的現象,這一點相當有趣,我們來看看他怎麼說:
相反地,現代人對這個世界已發生的,或即將發生的一切,都抱持極其明確的「想法」。如果自己已經具備了所有必要的東西,那麼還有什麼聆聽別人的必要?如今,聆聽的理由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判斷、發表意見,以及下結論。
人聚在一起,所為何事?奧特加說,他們為的不是傾聽別人,而是自信十足地談論自己的思想。在一片喧囂中,每個人只顧著高談闊論,無意聆聽別人。好似所有議題都與自己有關,對任何事都有「意見」,都要發表評論。遇到不怎麼在乎的社會問題,反倒當作不存在。在奧特加的眼中,我們所身處的社會就是如此。
只要想想社群媒體上的情景、咖啡館裡的對話,以及熱鬧街頭上的路人群像,就會發現事實或許真的如奧特加所說。人們只在乎自己,希望世界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運轉,一味關注自己的形象與發言,對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即使面對專家也大言不慚;相信偽科學的人,甚至根據神祕的理論嘲笑科學家是「資訊弱者」⋯⋯我們彷彿失去了對別人與世界的興趣。
接下來我們會發現,奧特加的論述有多麼無懈可擊。當我向別人介紹奧特加的言論時,無論是學生、上班族、自由工作者、大老闆、老年人,一定會出現「我懂,我懂」、「哦,那種人我遇過」這一類反應。目前還沒有人讓我失望過。
然而,讀到這裡,如果有人心想「沒錯,就是有這種人!臉皮未免也太厚了」,那麼,你並沒有發現,自己也正是奧特加所批判的現代人:認為奧特加所描述的與自己無關。這剛好符合他指出的現代人特徵,也就是凡事都依照自己心中的「標準答案」去判斷、發表意見、下結論。奧特加希望大眾警惕的,正是這種姿態。
〔試閱二〕
自我啟發的陷阱:過度正向思考,可能通向憂鬱
首先,回想一下帕斯卡所描繪的人類形象。他認為,人總是忙著投入各種活動與交流,不斷尋求消遣而無法平靜下來。這種姿態中,隱約可以看出人類似乎必須勉強提高興致,彷彿如果不透過自我肯定來振奮情緒的話,就無法應付日常生活。事實上,現代社會環境更加劇了這種傾向。
接著,我們把焦點從十七世紀的帕斯卡轉移到現代。社會學家鈴木謙介曾在一次談論現代年輕人求職活動的訪談中,說過下面這段很有意思的話:
比方說,在剛開始求職時,年輕人就被迫要尋找自己適合的職業。但照理來說,「適合的職業」是在經驗、成就與人際關係的累積下慢慢浮現的。所以,幾乎沒有就業經驗的學生,不可能知道自己適合什麼工作。他們不得不告訴自己「這就是我想做的工作」,勉強提高興致投入面試。然而,因為這本來就很勉強,所以亢奮的狀態無法持久;高漲的情緒一旦趨於低落,就得再強迫自己回到亢奮的狀態,如此循環。
雖然訪談中以求職活動當作例子,但這種心理狀態,其實在現代社會也很常見。我們似乎非得振奮情緒,才能認真生活,可是那股亢奮的情緒並不持久,而我們又無法忍受情緒低落的狀態,只好不斷勉強提高興致。這個狀態又稱作「亢奮式自我啟發」,它與「只要努力就會成功」的價值觀、「肯定找得到適合我的工作」的幻想、前景不明朗的社會、不穩定的就業市場以及對未來隱約的擔憂,全部糾纏在一起、逐漸變質,讓我們處於在焦躁與憂鬱之間反覆交替的心理模式中。
這種心理變化,可能已直接影響到現代人的心理健康。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料,全球憂鬱症患者中成人約占百分之五,也就是大約二.八億人。這個驚人的數字,一部分與一九八○年代《國際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標準(DSM)》改訂後,擴大了「憂鬱症(depression)」的診斷範圍有關;另一部分與八○年代末到九○年代新一代抗鬱劑問世,製藥業界所推行的全球市場行銷,使憂鬱症受到大眾廣泛認知有關。
隨著憂鬱症及其他精神疾病愈來愈常見,心理健康逐漸被視為「個人的問題」。這股「自己負責」的趨勢,導致「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心理疾病,必須藉由服藥來控制」的生活成為常態。
聚在一起高談闊論,卻無意聆聽別人的現代社會
尼采說:「你們的拚命工作只是一種自我逃避」。我們就從他批判的對象,也就是我們「自我逃避的模樣」開始說起吧。我們逃避自己的本領可不是蓋的。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這種狀態,不妨認識一下哲學家何塞.奧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奧特加是一位西班牙哲學家。哲學跟西班牙的組合很稀奇吧?但值得各位關注的,是他的著作《大眾的反叛》。奧特加分析了現代社會的特徵,並且從顯而易見的現象切入:城市的擁擠。
城市裡人滿為患,租屋供不應求,旅館一房難求,火車座無虛席,咖啡館裡萬頭攢動,公園裡散步者比肩繼踵,名醫的診療室裡病人大排長龍,劇院場場爆滿,海灘上也擠滿了戲水的人。尋找空間這件事,在過去根本稱不上是問題,如今卻幾乎成為日常的麻煩。
總之,人多得亂成一團。奧特加認為,一言以蔽之,城市的特徵無非就是人多。儘管城市裡聚集了擁有多元背景與屬性的人,但大家都一窩蜂地擠到相同的地方,彷彿這種多元性根本不存在。
也許有人會想:新冠疫情下遠距工作模式普及,或是移居外地的風潮,已經讓狀況有些改變。不過,只要大家能理解人對於「想要在場親身參與話題」的執念,那麼奧特加的論述至今依然適用。各位可以回想一下,我們是如何成群結隊地關注熱門新聞與內容,或是總覺得不能錯過,非得稍微瞄一眼群眾談論的八卦?無論在線上或是線下,這種「一窩蜂」的現象,正是我們社會的基本特徵。而奧特加依據這個觀察,進一步指出另一個重要的現象,這一點相當有趣,我們來看看他怎麼說:
相反地,現代人對這個世界已發生的,或即將發生的一切,都抱持極其明確的「想法」。如果自己已經具備了所有必要的東西,那麼還有什麼聆聽別人的必要?如今,聆聽的理由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判斷、發表意見,以及下結論。
人聚在一起,所為何事?奧特加說,他們為的不是傾聽別人,而是自信十足地談論自己的思想。在一片喧囂中,每個人只顧著高談闊論,無意聆聽別人。好似所有議題都與自己有關,對任何事都有「意見」,都要發表評論。遇到不怎麼在乎的社會問題,反倒當作不存在。在奧特加的眼中,我們所身處的社會就是如此。
只要想想社群媒體上的情景、咖啡館裡的對話,以及熱鬧街頭上的路人群像,就會發現事實或許真的如奧特加所說。人們只在乎自己,希望世界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運轉,一味關注自己的形象與發言,對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即使面對專家也大言不慚;相信偽科學的人,甚至根據神祕的理論嘲笑科學家是「資訊弱者」⋯⋯我們彷彿失去了對別人與世界的興趣。
接下來我們會發現,奧特加的論述有多麼無懈可擊。當我向別人介紹奧特加的言論時,無論是學生、上班族、自由工作者、大老闆、老年人,一定會出現「我懂,我懂」、「哦,那種人我遇過」這一類反應。目前還沒有人讓我失望過。
然而,讀到這裡,如果有人心想「沒錯,就是有這種人!臉皮未免也太厚了」,那麼,你並沒有發現,自己也正是奧特加所批判的現代人:認為奧特加所描述的與自己無關。這剛好符合他指出的現代人特徵,也就是凡事都依照自己心中的「標準答案」去判斷、發表意見、下結論。奧特加希望大眾警惕的,正是這種姿態。
〔試閱二〕
自我啟發的陷阱:過度正向思考,可能通向憂鬱
首先,回想一下帕斯卡所描繪的人類形象。他認為,人總是忙著投入各種活動與交流,不斷尋求消遣而無法平靜下來。這種姿態中,隱約可以看出人類似乎必須勉強提高興致,彷彿如果不透過自我肯定來振奮情緒的話,就無法應付日常生活。事實上,現代社會環境更加劇了這種傾向。
接著,我們把焦點從十七世紀的帕斯卡轉移到現代。社會學家鈴木謙介曾在一次談論現代年輕人求職活動的訪談中,說過下面這段很有意思的話:
比方說,在剛開始求職時,年輕人就被迫要尋找自己適合的職業。但照理來說,「適合的職業」是在經驗、成就與人際關係的累積下慢慢浮現的。所以,幾乎沒有就業經驗的學生,不可能知道自己適合什麼工作。他們不得不告訴自己「這就是我想做的工作」,勉強提高興致投入面試。然而,因為這本來就很勉強,所以亢奮的狀態無法持久;高漲的情緒一旦趨於低落,就得再強迫自己回到亢奮的狀態,如此循環。
雖然訪談中以求職活動當作例子,但這種心理狀態,其實在現代社會也很常見。我們似乎非得振奮情緒,才能認真生活,可是那股亢奮的情緒並不持久,而我們又無法忍受情緒低落的狀態,只好不斷勉強提高興致。這個狀態又稱作「亢奮式自我啟發」,它與「只要努力就會成功」的價值觀、「肯定找得到適合我的工作」的幻想、前景不明朗的社會、不穩定的就業市場以及對未來隱約的擔憂,全部糾纏在一起、逐漸變質,讓我們處於在焦躁與憂鬱之間反覆交替的心理模式中。
這種心理變化,可能已直接影響到現代人的心理健康。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料,全球憂鬱症患者中成人約占百分之五,也就是大約二.八億人。這個驚人的數字,一部分與一九八○年代《國際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標準(DSM)》改訂後,擴大了「憂鬱症(depression)」的診斷範圍有關;另一部分與八○年代末到九○年代新一代抗鬱劑問世,製藥業界所推行的全球市場行銷,使憂鬱症受到大眾廣泛認知有關。
隨著憂鬱症及其他精神疾病愈來愈常見,心理健康逐漸被視為「個人的問題」。這股「自己負責」的趨勢,導致「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心理疾病,必須藉由服藥來控制」的生活成為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