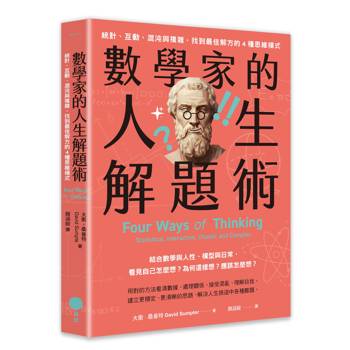四種思考途徑
人終其一生不斷在進行的一件事就是思考。
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刻,我們的思緒都在流動。有時候是下達指令,有時候是給予鼓勵,有時候則是鞭策我們分析過去所為、以為將來借鑑。就這樣,我們腦中的齒輪持續運轉,試圖更深入地理解這個世界。
然而,我們卻極少審視自己的思路。我們從未好好分析過,何種思維能導向正確答案,何種又會造成誤導。我們多半都沒去好好想過,怎樣才能形成最好的想法。
人們常會想著該怎麼好好照顧身體⋯⋯就算不太成功,至少也有那份心。我們會去健身房,或盡量飲食清淡;會檢討要怎樣讓自己更有動力、更持久地朝讓自己更健康努力;也會暫時放下工作,試圖為生活減壓。
但我們卻很少停下來,好好問自己:我思考生活的方式,真的是正確的嗎?
科學與數學,其實都是在追尋更好的思考方式。當我們看著那些講述宇宙起源、自然奧祕或人體構造的紀錄片時,常會以為科學只是在蒐集事實。但其實不然,至少不全然。對於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科學家來說,首要目標是鍛鍊與打磨我們的思維,好讓我們更接近真相。至於透過這樣的思維所揭示出的具體事實,反而是次要的成果。
本書要介紹四種思考方法,四種讓我們更接近真相的途徑。
這四種方法的源頭可追溯至1984年,一位二十四歲青年所寫的一篇論文,他是史提芬.沃夫朗(Stephen Wolfram),從小便是神童,日後成為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寫這篇論文時,正在研究一套深奧難懂的數學模型,名為格狀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透過在嶄新的Sun工作站上進行電腦模擬,沃夫朗成功歸類出這些自動機所產生的模式類型,從而假設無論生物或是物理、個人或社會、自然或人工的所有過程,都能歸屬於他在模擬中觀察到的四種行為之一:(I)穩定、(II)週期性、(III)混沌或(IV)複雜。我們肉眼所見或所做的一切,全都可以歸入這四大類中。
所謂的穩定系統,指的是一旦達到平衡狀態,就會維持在這個狀態。比如排骨牌遊戲,將骨牌一張接一張直立排好,當第一張被推倒後,其餘骨牌將依序倒下,最後靜靜地躺成一排,這就是穩定。其他例子還有:球滾下山坡後停在谷底不再移動;用杵臼將香料研磨成均勻的混合物;狗狗在長距離散步後安詳地睡著等。
週期性系統則有著重覆模式。例如走路、騎單車、或是騎馬,分別是雙腿、腳踏車輪和馬腿進行的週期性動作。它也體現在海浪有規律地一波波拍打沙灘時,那一道道間隔均勻的波浪線;或是廚師將菜切成等分大小時快速反覆落刀的動作。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是週期性的:吃早餐、上班、吃午餐、下班、 吃晚餐、看電視、上床睡覺,周而復始。
混沌就是無法預知明天是否會下雨的情形(至少在英國是這樣)。擲骰子、丟銅板,或是轉動俄羅斯輪盤,都屬於混沌。煮義大利麵時,水分子在沸騰的鍋中隨機振動、四處亂竄的樣子也是。還有那些偶遇,以及自動門開啟或關閉的隨機瞬間,都體現了混沌。
複雜則在社會中俯拾皆是。跨越全球的貨物和服務運送、文明的興衰、政府和大型跨國組織的結構,都充滿了複雜性。複雜也在日常生活中,在與親友的關係裡,我們可能同時感受到愛與挫折。複雜也存在於我們體內,是數十億個大腦神經元的發送,也是你的人生故事,訴說著你是如何走到今天。
有時候,我們的行為會讓我們在不同類型之間移動。以爭執與討論為例。我得承認,我是那種凡事都想追根究柢的人,對於追求「正確」答案相當執著。要是有我不了解的問題,或是有人提出我不同意的觀點,我往往會想要和他爭論,以找出真相。
但我愛和人爭論的個性有時也會帶來一些麻煩,特別是對與我同住或共事的人而言,他們不見得想花時間去細細討論每一件事。
因此,為了減少無謂的爭論,我套用沃夫朗理論,發現真正值得爭論的問題只有兩種:朝著穩定解決方案前進的第一類爭論;針對重要的新想法進行討論,但可能永遠也討論不出結果的第四類爭論。至於第二類爭論,只會在同一個爭議點上爭論不休;第三類爭論則是你一言、我一句,混亂無章,只是比誰大聲。這兩類都要避免。
有了這套分類後,就比較容易分辨自己當前所進行的爭論是哪一類。接著,我會思考該怎麼讓第二類爭論轉為第一類,或者從第三類轉為第四類。我也會思考該如何讓第一類爭論更快趨於穩定,就像某種超高效的杵臼,能夠快速研磨出實情。
你會發現,用這種方式去想事情,會讓你的視角不再只盯著眼前在做的事,而是以俯瞰的角度看清全貌。沃夫朗的分類,讓我們能去思考一個「總體」的應對方式,來處理那些表面上看起來非常不同的挑戰。
2002年,沃夫朗發表了畢生代表作《新式科學》(A New Kind of Science),提出一套以格狀自動機模型為核心的科學研究方法。這套理論涵蓋範圍極廣(全書重達5.6磅重、共1192頁),書中大膽宣稱透過研究格狀自動機,可以更深入理解生物界、物理界,乃至幾乎所有事物。不過,沃夫朗並未針對格狀自動機如何為我們所生活的複雜真實世界提供深入見解一事提出太多具體細節。
因未能提出實用的見解,沃夫朗的理論始終未被科學界認真看待,這些創見也未能獲得大眾關注。我在維基百科搜尋沃夫朗的研究時,只找到一個專門介紹格狀自動機數學特性的頁面。沃夫朗這套分類法始終停留在抽象層面,與現實脫節。
沃夫朗所欠缺的,是告訴我們如何用這四種分類來形塑並釐清我們看待世界的方法,而這正是我在這本書中要補足的。這四種思維類型其實一點也不抽象,而是日常情境中非常有用的工具。我在這本書中不把它們當成沃夫朗所謂的新式科學,而是將其視為實用工具,可以用來說服朋友和你一起去慢跑、與伴侶爭議時進行有效溝通、搞懂為何在派對上總是被冷落在一旁,甚至重新看待自己這個獨一無二、複雜多面的個體。
為了好好探討這種全新且更實際的思考方式,我將沃夫朗的四種類型拓展成本書的四個部分。
在我看來,第一類屬於「統計思維」。什麼時候該相信數字,什麼時候又該抱持懷疑?更重要的是,面對那些關於飲食、運動、幸福或成功的科學研究建議時,又該如何解讀?數據和統計雖然是了解社會整體的關鍵,但我會證明,這些數字對你個人的影響力,並沒有新聞標題所宣稱的那麼大。
那麼,我們該如何在生活中獲得更高的實現和滿足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借助第二類的「互動思維」:發現這個社會所組成的世界的祕密。我們要如何建立具有建設性的群體互動?又該如何改變溝通方式來化解分歧?我會說明要如何更了解自己對他人的影響力,在他人虧待我們時又要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改善與他人的關係遠比你想得要容易許多。
不過,這有個問題。我們越想掌控生活,生活就越難以預測。在一個不可能事事盡在掌握的世界裡,那些試圖讓生活回到正軌的努力,往往只會製造失序和紊亂。第三類「混沌思維」能幫助我們判斷何時該努力維持掌控、何時又該放手。
問題越複雜,解決起來就越困難。但怎樣才叫做複雜?我認為一個系統的複雜度,取決於你能用多簡短的方式去描述它。當我們學會用最精簡的方式去歸納自己的社交情況、煩惱和思緒,就能夠掌握到問題的核心。這類思維不像前三種是用來解決日常問題的,第四類「複雜思維」較著重於內省和自我反思,焦點在於找到讓我們更能了解自己和周遭人的敘事。
從第一類到第四類思維的演進,我們能看到過去一百年來科學思想的發展脈絡,以及形塑現代科學思維的英雄和反英雄人物。這個歷程帶領我們內省自身並向外觀照我們所共同創造的世界,從日常做家事這類平凡問題,到「人之所以為人」這種深奧的哲學探索。
現在,就讓我們跟著一位年輕的博士生踏上這趟發現之旅⋯⋯
人終其一生不斷在進行的一件事就是思考。
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刻,我們的思緒都在流動。有時候是下達指令,有時候是給予鼓勵,有時候則是鞭策我們分析過去所為、以為將來借鑑。就這樣,我們腦中的齒輪持續運轉,試圖更深入地理解這個世界。
然而,我們卻極少審視自己的思路。我們從未好好分析過,何種思維能導向正確答案,何種又會造成誤導。我們多半都沒去好好想過,怎樣才能形成最好的想法。
人們常會想著該怎麼好好照顧身體⋯⋯就算不太成功,至少也有那份心。我們會去健身房,或盡量飲食清淡;會檢討要怎樣讓自己更有動力、更持久地朝讓自己更健康努力;也會暫時放下工作,試圖為生活減壓。
但我們卻很少停下來,好好問自己:我思考生活的方式,真的是正確的嗎?
科學與數學,其實都是在追尋更好的思考方式。當我們看著那些講述宇宙起源、自然奧祕或人體構造的紀錄片時,常會以為科學只是在蒐集事實。但其實不然,至少不全然。對於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科學家來說,首要目標是鍛鍊與打磨我們的思維,好讓我們更接近真相。至於透過這樣的思維所揭示出的具體事實,反而是次要的成果。
本書要介紹四種思考方法,四種讓我們更接近真相的途徑。
這四種方法的源頭可追溯至1984年,一位二十四歲青年所寫的一篇論文,他是史提芬.沃夫朗(Stephen Wolfram),從小便是神童,日後成為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寫這篇論文時,正在研究一套深奧難懂的數學模型,名為格狀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透過在嶄新的Sun工作站上進行電腦模擬,沃夫朗成功歸類出這些自動機所產生的模式類型,從而假設無論生物或是物理、個人或社會、自然或人工的所有過程,都能歸屬於他在模擬中觀察到的四種行為之一:(I)穩定、(II)週期性、(III)混沌或(IV)複雜。我們肉眼所見或所做的一切,全都可以歸入這四大類中。
所謂的穩定系統,指的是一旦達到平衡狀態,就會維持在這個狀態。比如排骨牌遊戲,將骨牌一張接一張直立排好,當第一張被推倒後,其餘骨牌將依序倒下,最後靜靜地躺成一排,這就是穩定。其他例子還有:球滾下山坡後停在谷底不再移動;用杵臼將香料研磨成均勻的混合物;狗狗在長距離散步後安詳地睡著等。
週期性系統則有著重覆模式。例如走路、騎單車、或是騎馬,分別是雙腿、腳踏車輪和馬腿進行的週期性動作。它也體現在海浪有規律地一波波拍打沙灘時,那一道道間隔均勻的波浪線;或是廚師將菜切成等分大小時快速反覆落刀的動作。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是週期性的:吃早餐、上班、吃午餐、下班、 吃晚餐、看電視、上床睡覺,周而復始。
混沌就是無法預知明天是否會下雨的情形(至少在英國是這樣)。擲骰子、丟銅板,或是轉動俄羅斯輪盤,都屬於混沌。煮義大利麵時,水分子在沸騰的鍋中隨機振動、四處亂竄的樣子也是。還有那些偶遇,以及自動門開啟或關閉的隨機瞬間,都體現了混沌。
複雜則在社會中俯拾皆是。跨越全球的貨物和服務運送、文明的興衰、政府和大型跨國組織的結構,都充滿了複雜性。複雜也在日常生活中,在與親友的關係裡,我們可能同時感受到愛與挫折。複雜也存在於我們體內,是數十億個大腦神經元的發送,也是你的人生故事,訴說著你是如何走到今天。
有時候,我們的行為會讓我們在不同類型之間移動。以爭執與討論為例。我得承認,我是那種凡事都想追根究柢的人,對於追求「正確」答案相當執著。要是有我不了解的問題,或是有人提出我不同意的觀點,我往往會想要和他爭論,以找出真相。
但我愛和人爭論的個性有時也會帶來一些麻煩,特別是對與我同住或共事的人而言,他們不見得想花時間去細細討論每一件事。
因此,為了減少無謂的爭論,我套用沃夫朗理論,發現真正值得爭論的問題只有兩種:朝著穩定解決方案前進的第一類爭論;針對重要的新想法進行討論,但可能永遠也討論不出結果的第四類爭論。至於第二類爭論,只會在同一個爭議點上爭論不休;第三類爭論則是你一言、我一句,混亂無章,只是比誰大聲。這兩類都要避免。
有了這套分類後,就比較容易分辨自己當前所進行的爭論是哪一類。接著,我會思考該怎麼讓第二類爭論轉為第一類,或者從第三類轉為第四類。我也會思考該如何讓第一類爭論更快趨於穩定,就像某種超高效的杵臼,能夠快速研磨出實情。
你會發現,用這種方式去想事情,會讓你的視角不再只盯著眼前在做的事,而是以俯瞰的角度看清全貌。沃夫朗的分類,讓我們能去思考一個「總體」的應對方式,來處理那些表面上看起來非常不同的挑戰。
2002年,沃夫朗發表了畢生代表作《新式科學》(A New Kind of Science),提出一套以格狀自動機模型為核心的科學研究方法。這套理論涵蓋範圍極廣(全書重達5.6磅重、共1192頁),書中大膽宣稱透過研究格狀自動機,可以更深入理解生物界、物理界,乃至幾乎所有事物。不過,沃夫朗並未針對格狀自動機如何為我們所生活的複雜真實世界提供深入見解一事提出太多具體細節。
因未能提出實用的見解,沃夫朗的理論始終未被科學界認真看待,這些創見也未能獲得大眾關注。我在維基百科搜尋沃夫朗的研究時,只找到一個專門介紹格狀自動機數學特性的頁面。沃夫朗這套分類法始終停留在抽象層面,與現實脫節。
沃夫朗所欠缺的,是告訴我們如何用這四種分類來形塑並釐清我們看待世界的方法,而這正是我在這本書中要補足的。這四種思維類型其實一點也不抽象,而是日常情境中非常有用的工具。我在這本書中不把它們當成沃夫朗所謂的新式科學,而是將其視為實用工具,可以用來說服朋友和你一起去慢跑、與伴侶爭議時進行有效溝通、搞懂為何在派對上總是被冷落在一旁,甚至重新看待自己這個獨一無二、複雜多面的個體。
為了好好探討這種全新且更實際的思考方式,我將沃夫朗的四種類型拓展成本書的四個部分。
在我看來,第一類屬於「統計思維」。什麼時候該相信數字,什麼時候又該抱持懷疑?更重要的是,面對那些關於飲食、運動、幸福或成功的科學研究建議時,又該如何解讀?數據和統計雖然是了解社會整體的關鍵,但我會證明,這些數字對你個人的影響力,並沒有新聞標題所宣稱的那麼大。
那麼,我們該如何在生活中獲得更高的實現和滿足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借助第二類的「互動思維」:發現這個社會所組成的世界的祕密。我們要如何建立具有建設性的群體互動?又該如何改變溝通方式來化解分歧?我會說明要如何更了解自己對他人的影響力,在他人虧待我們時又要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改善與他人的關係遠比你想得要容易許多。
不過,這有個問題。我們越想掌控生活,生活就越難以預測。在一個不可能事事盡在掌握的世界裡,那些試圖讓生活回到正軌的努力,往往只會製造失序和紊亂。第三類「混沌思維」能幫助我們判斷何時該努力維持掌控、何時又該放手。
問題越複雜,解決起來就越困難。但怎樣才叫做複雜?我認為一個系統的複雜度,取決於你能用多簡短的方式去描述它。當我們學會用最精簡的方式去歸納自己的社交情況、煩惱和思緒,就能夠掌握到問題的核心。這類思維不像前三種是用來解決日常問題的,第四類「複雜思維」較著重於內省和自我反思,焦點在於找到讓我們更能了解自己和周遭人的敘事。
從第一類到第四類思維的演進,我們能看到過去一百年來科學思想的發展脈絡,以及形塑現代科學思維的英雄和反英雄人物。這個歷程帶領我們內省自身並向外觀照我們所共同創造的世界,從日常做家事這類平凡問題,到「人之所以為人」這種深奧的哲學探索。
現在,就讓我們跟著一位年輕的博士生踏上這趟發現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