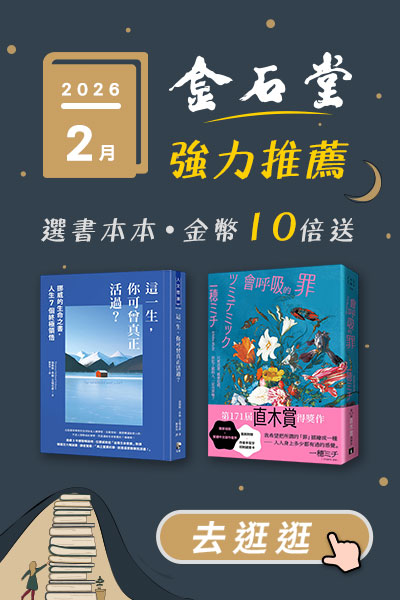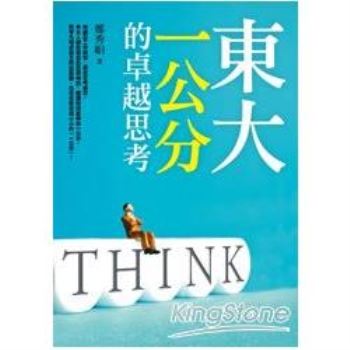◎破日文也能上東大
很多人只要聽到我是東大研究所畢業的,而且又在碩士班、博士班期間分別拿到兩次日本交流協會的獎學金,便會說:「哇,你一定很聰明!」、「你一定很會讀書!」
我聽了總是笑而不答,因為我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生來就天資聰穎、很會念書的人。
從小到大,我的學業成績始終維持中等,雖然小學一年級時拿過幾次第一名,但是後來考試的名次就越來越後退。國中時,以我在班上的成績來說,照理應該考不上前三志願,但我卻幸運地考上了第二志願師大附中。高三最後一次模擬考,我的成績在全校四百多位文組學生中排名三百多名(因為有近一百人沒有參加考試)。結果,大學聯考的成績公布,我在全校文組排名三十名以內,考上了第二志願的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進入大學後,成績一向普通的我,畢業時卻成為班上唯一拿到公費獎學金出國留學的學生,跌破了眾人眼鏡,因此,朋友都笑稱我是「職業黑馬」。
雖然,我在學習的過程中一路過關斬將、勇往直前,但我和其他人的資質差不多,其實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如果一定要說我跟別人有什麼不同的話,應該是「思考方式」和別人不太一樣吧!我從來不為自己設限,覺得自己沒有能力、時間或資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的信念是「不管現在的狀況如何,只要有心,一定可以達到自己想要做的事」只要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優秀的人,你就能夠成為優秀的人;換句話說,「只要不放棄自己,你永遠都有潛力可以打造屬於自己的未來」。
大三那年,為了實現去日本遊學的夢想,我開始四處尋找打工機會,努力地籌措遊學所需的經費。對於一個大學生而言,當家教自然是最有效率的賺錢方式。不過,考量到家教中心的登記手續,必須把時間浪費在等候通知上;倘若家教的地方離家比較遠,還要另外支付交通費,加上車程往返的時間,其實並不划算,因此,我仔細盤算過之後,決定在住家附近的小吃店張貼傳單。
為了開發「客源」,我常去那家小吃店吃麵,只要一見到有人盯著牆上傳單看,也絕不放過機會,立刻上前自我介紹。很快,我就遇到了兩位鄰居家長,願意雇用我擔任他們孩子的家教老師。
半年之後,我如願存到足以前往日本遊學一個月的日語學校學費、機票和住宿費用,且在東京度過了一個愉快又難忘的暑假。
升上大四後,有位日語老師告訴我,日本交流協會提供了優渥的獎學金給台灣留學生,包括日本公立研究所的兩年學雜費、來回機票,以及每個月將近二十萬日幣的生活補助。光是每月實領近二十萬日幣,就比一位日本大學畢業生能拿到的薪水還要高!如果能夠申請到這筆獎學金,既不用自己辛苦地打工存錢,也不用跟家裡伸手要錢,便可以實現日本留學的夢想。於是,我開始努力思考如何才能拿到這筆獎學金,並且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法。
首先,我查詢了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的考試科目,有日文、台灣歷史、地理和三民主義,共四個科目。為了準備筆試,在大四畢業前,我特別去K書中心租了兩個月的座位,讓自己回歸大學聯考那時的備戰狀態,以便全力衝刺。
在夜以繼日地埋首苦讀後,我順利通過了日本交流協會的筆試。之後,為了準備面試,除了把自己的研究計劃用日文背得滾瓜爛熟外,我還買了一本日本人所寫的面試大全,努力學習「日本式的面試之道」。
在面試當天,我厚臉皮地對主考官說:「學成之後,我想要成為日本和台灣的溝通橋樑。」不知道是否這句話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我很順利地通過面試,拿到了全額近兩百萬台幣的留日獎學金。
到了日本,第一次去拜訪我的指導教授吉見俊哉先生,他說的日文,其實我也只聽懂三成左右而已,他看我一臉茫然的模樣,只好改用英文跟我交談。
我還記得,新聞媒體政策的課堂上只有三位學生,老師的日文猶如催眠曲般讓人昏昏欲睡……一次,當我強忍著瞌睡、硬撐到下課,一位來自大陸的學姊跑來和我說,「我看妳上課時明明都快睡著了,還是努力地撐開眼皮,身體一直搖搖晃晃,我還非常擔心妳會從椅子上跌下來呢!」
「東大社會情報學研究所」的前身是創立於一九四九年的新聞研究所,它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一九二九年東京帝國大學時期的新聞研究室,系館內累積的圖書資源及研究論文數量十分豐富,是日本傳播研究的重鎮,每年招收研究所學生人數很少,一開始只有一至兩位學生,後來才逐漸增加招生人數,我那一屆只有七名學生。
不過,進入了人才濟濟的東大之後,我很快就發現一件事:
我沒有比別人聰明!
因此,「努力」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經過兩年的學習,準備碩士論文時,我花了整個暑假研究文獻,但是教授一看到我寫的論文,立刻毫不留情地批評「這樣的論文水準,不過是高中生的讀書心得而已」。
當下,我的心涼了半截,眼淚差點掉了下來,趕緊躲到廁所整理自己的情緒。看著鏡子中紅著眼眶的自己,我努力對自己說:「加油」、「不要哭」,眼淚卻還是不爭氣地滑下來……
回到研究室後,教授說有事必須離開,我不敢耽誤他的時間,又不願意放過能和教授單獨面談的機會,所以緊跟在他身後,一起搭上電車,窮追不捨地詢問他的意見,直到完全明白教授要求的論文標準為止。
事後,教授對其他同學稱讚我是個「一生懸命」(努力堅持到底)的人;或許是看到了我認真的學習態度,即使,平常他已經累到連搭電梯時都會闔上眼睛打瞌睡的程度,還是會繼續撥冗跟我討論修改論文的細節。
除此之外,他還會特別交代一些優秀的學長姊幫忙指導我,讓我在兩年內完成了長達二十萬字的論文,順利拿到碩士學位。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在教授研究室流下的「不甘心的眼淚」,正是支持我一路前進的動力。我不想要再一次因為自己的不甘心而哭泣,也不希望讓將來的自己後悔,因此,無論情況如何困難,我都告訴自己,一定要完成畢業論文,對於想要達成的目標,更該全力以赴!
◎幫助你登上高峰的「低氧腦」
進入東大當外國人研究生後,我的目標是考上東大社會情報學研究所,成為正式的東大學生。
為了順利考取東大研究所,我讓自己隨時處在「低氧腦」的狀態。「低氧腦」這個名詞是我自創的,意即「就算面對惡劣的環境,仍然專注地向前邁進。」。馬拉松選手在接受長跑訓練時,會特地挑選在氧氣稀少的高地進行跑步練習,讓自己的身體適應低氧狀態;接受過低氧訓練的馬拉松選手,經歷了惡劣環境的考驗,以後不管到任何地方比賽,都可以應付多變的天候和環境。
那段日子,我努力調適心情,讓心中的雜念和外界的誘惑徹底淨空。從確定要考東大的八月底開始,一直到隔年二月初考試為止,我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樣:念書、上課、吃飯、運動。早上八點到圖書館等開門,念書念到晚上九點圖書館關門才離開,除了圖書館休館日外,沒有一天間斷。
皇天不負苦心人,經過近半年的埋首苦讀,我終於通過了研究所入學筆試,接下來就是面試。
我記得,主考官之一就是我在第一堂課差點因為打瞌睡從椅子上跌下來的授課老師,他在問完所有專業問題後,抬頭看了一眼牆上的鐘,發現還有一些時間,於是又問了我一個基本問題:「我們上課時說的日文,你聽得懂幾成?」
我老實地說:「日常的會話大概是八成,但是上課的內容大概是七成吧。」
一般人可能認為,主動坦承自己日文程度不佳,大概很難考上以入學審核嚴格出名的東大研究所。但是,我不僅考上了,而且還成為「東大社會情報學研究所」創系以來第一位錄取的台灣學生。
這段期間鍛練出的「低氧腦」,讓我往後不管求學或工作,都能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完成目標,也成功地克服語言障礙的關卡,在東大的求學生活有如倒吃甘蔗,漸入佳境。此後,當我面對其他困難,或是覺得自己快要撐不下去時,就會回想起這段寶貴的經驗,讓它幫助自己勇敢地走下去。
我並不氣餒,再次致電過去,找到了那位總編輯。總編輯很高興我推薦這本書給她,但她對於我的英文能力似乎有些擔心。
「妳的英文很好嗎?」總編輯單刀直入地問。
「我的英文沒有很好……」
「……」電話那頭出現了片刻的沉默。
「可是,我看過這本書的日文版,而且我幫客戶上過課……」我不放棄地繼續說。
「好吧!妳先試譯兩頁,我們再決定要不要請妳翻譯整本書。」
結果,總編輯看了我的試譯之後還算滿意,決定放手一搏,讓我嘗試翻譯整本書。老實說,翻譯這本書的過程十分痛苦。自從高中畢業之後,我就沒有認真讀過英文,連一些簡單的英文單字也都忘光光了。每處理一段文字,往往就會遇到三、四個生字需要查字典,一天下來,約莫只能翻譯一頁的文章。
到了截稿前一個月,還有四分之一的內容沒有翻譯完,我本來想發包給別人,但一想到自己翻譯這本書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了重拾自己的英文能力,最後也還是咬緊牙關,如期完成了這項工作。
日文有一句話說「不戰敗」,意謂「不戰而敗」。例如,因為自己趕不上比賽時間,連比都沒比就輸了。對我來說,「畫地自限」就是典型的「不戰敗」。因為覺得自己「一定不行」、「能力不夠」或「失敗了太丟臉」,連試都沒有去試就直接放棄,真的是很可惜的事。
可惜,在面臨「做」與「不做」的重大抉擇時,人們往往會比較在意「損失所帶來的痛苦」,反而容易忽略了「獲利所帶來的快樂」;也就是先思考行動後的利益得失,再來決定是否要採取行動。
為什麼人們會傾向不去冒險呢?因為,停留在原來的「舒適區」,讓人感到安心。如果我們把人所處的狀況大致分成三個區塊,以熟悉程度來做區分,分別是「舒適區」、「學習區」、「恐慌區」。
在「舒適區」中,這裡有讓自己覺得舒服的衣服、舒服的朋友、舒服的食物,沒有新的挑戰或不熟悉的事情,所以不必花腦筋,不管在心理層面或是生理層面上都容易覺得自在舒服。
我們在家裡喜歡穿柔軟又舒適的舊衣服,因為舊衣服讓我們覺得放鬆;我們習慣和自己覺得安全的老朋友來往,逃避結交新朋友所需要面對的風險;我們平常吃的食物總是固定那幾樣,去吃的中餐店家也是那幾間,因為那是我們習慣或者熟悉的味道,這些衣服、朋友、食物讓我們覺得熟悉、自在。我們不必要多花精神和時間去重新適應。
「舒適區」之外,是「學習區」和「恐慌區」。後面這二個區塊裡是不熟悉或未知的人事地物。我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喜歡未知的、沒有嘗試過的東西,但是可以知道的是,要接觸這些新事物,我們或多或少必須花費時間、力氣去認識或者適應它。對於某些人來說,要離開溫暖又舒服的「舒適區」,就像是在寒冷的冬天早晨,離開溫暖的被窩一樣地困難。
離開自在的「舒適區」,且面對未知的情況時會感到害怕、緊張,是很正常的情緒反應。因為,在舒適區之外,有太多未知的、不可抗的因素,可能會影響到現有的生活節奏,甚至會危害到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些人的看法則完全不同,他們認為舒適區之外的世界充滿了未知,因而感到新鮮、剌激。
「恐慌區」指的是目前做不到,而且壓根不知道要怎麼開始去做,一想到就讓人頭皮發麻、陷入恐慌的事。例如,「在國家戲劇院用義大利文演出歌劇『塞維利亞理髮師』」、「不攜帶人工氧氣登上高達八千公尺的高山」,如果要我們現在立刻去做這些高難度的挑戰,失敗、出醜的機率很大。
在舒適的被窩(舒適區)和冷洌的高山(恐慌區)之間,存在很大的空間,也就是所謂的「學習區」(也稱為「伸展區」或「成長區」),在「學習區」裡,人們會遇見不熟悉或未知的事物,於是展開新的「挑戰」,有可能「失敗」,但也有可能「成功」,不管是哪一種後果,只要願意離開自己的「舒適區」,把腳趾頭伸進「學習區」,總是會有「新發現」、「新學習」;不僅發掘新的事物,也會發現自己對這個新事物的反應。人們在「挑戰」、「失敗」、「發現」、「學習」之間來來回回,會發現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讓沉睡的潛在能力得到更多發展、成長的空間。
很多人只要聽到我是東大研究所畢業的,而且又在碩士班、博士班期間分別拿到兩次日本交流協會的獎學金,便會說:「哇,你一定很聰明!」、「你一定很會讀書!」
我聽了總是笑而不答,因為我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生來就天資聰穎、很會念書的人。
從小到大,我的學業成績始終維持中等,雖然小學一年級時拿過幾次第一名,但是後來考試的名次就越來越後退。國中時,以我在班上的成績來說,照理應該考不上前三志願,但我卻幸運地考上了第二志願師大附中。高三最後一次模擬考,我的成績在全校四百多位文組學生中排名三百多名(因為有近一百人沒有參加考試)。結果,大學聯考的成績公布,我在全校文組排名三十名以內,考上了第二志願的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進入大學後,成績一向普通的我,畢業時卻成為班上唯一拿到公費獎學金出國留學的學生,跌破了眾人眼鏡,因此,朋友都笑稱我是「職業黑馬」。
雖然,我在學習的過程中一路過關斬將、勇往直前,但我和其他人的資質差不多,其實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如果一定要說我跟別人有什麼不同的話,應該是「思考方式」和別人不太一樣吧!我從來不為自己設限,覺得自己沒有能力、時間或資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的信念是「不管現在的狀況如何,只要有心,一定可以達到自己想要做的事」只要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優秀的人,你就能夠成為優秀的人;換句話說,「只要不放棄自己,你永遠都有潛力可以打造屬於自己的未來」。
大三那年,為了實現去日本遊學的夢想,我開始四處尋找打工機會,努力地籌措遊學所需的經費。對於一個大學生而言,當家教自然是最有效率的賺錢方式。不過,考量到家教中心的登記手續,必須把時間浪費在等候通知上;倘若家教的地方離家比較遠,還要另外支付交通費,加上車程往返的時間,其實並不划算,因此,我仔細盤算過之後,決定在住家附近的小吃店張貼傳單。
為了開發「客源」,我常去那家小吃店吃麵,只要一見到有人盯著牆上傳單看,也絕不放過機會,立刻上前自我介紹。很快,我就遇到了兩位鄰居家長,願意雇用我擔任他們孩子的家教老師。
半年之後,我如願存到足以前往日本遊學一個月的日語學校學費、機票和住宿費用,且在東京度過了一個愉快又難忘的暑假。
升上大四後,有位日語老師告訴我,日本交流協會提供了優渥的獎學金給台灣留學生,包括日本公立研究所的兩年學雜費、來回機票,以及每個月將近二十萬日幣的生活補助。光是每月實領近二十萬日幣,就比一位日本大學畢業生能拿到的薪水還要高!如果能夠申請到這筆獎學金,既不用自己辛苦地打工存錢,也不用跟家裡伸手要錢,便可以實現日本留學的夢想。於是,我開始努力思考如何才能拿到這筆獎學金,並且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法。
首先,我查詢了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的考試科目,有日文、台灣歷史、地理和三民主義,共四個科目。為了準備筆試,在大四畢業前,我特別去K書中心租了兩個月的座位,讓自己回歸大學聯考那時的備戰狀態,以便全力衝刺。
在夜以繼日地埋首苦讀後,我順利通過了日本交流協會的筆試。之後,為了準備面試,除了把自己的研究計劃用日文背得滾瓜爛熟外,我還買了一本日本人所寫的面試大全,努力學習「日本式的面試之道」。
在面試當天,我厚臉皮地對主考官說:「學成之後,我想要成為日本和台灣的溝通橋樑。」不知道是否這句話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我很順利地通過面試,拿到了全額近兩百萬台幣的留日獎學金。
到了日本,第一次去拜訪我的指導教授吉見俊哉先生,他說的日文,其實我也只聽懂三成左右而已,他看我一臉茫然的模樣,只好改用英文跟我交談。
我還記得,新聞媒體政策的課堂上只有三位學生,老師的日文猶如催眠曲般讓人昏昏欲睡……一次,當我強忍著瞌睡、硬撐到下課,一位來自大陸的學姊跑來和我說,「我看妳上課時明明都快睡著了,還是努力地撐開眼皮,身體一直搖搖晃晃,我還非常擔心妳會從椅子上跌下來呢!」
「東大社會情報學研究所」的前身是創立於一九四九年的新聞研究所,它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一九二九年東京帝國大學時期的新聞研究室,系館內累積的圖書資源及研究論文數量十分豐富,是日本傳播研究的重鎮,每年招收研究所學生人數很少,一開始只有一至兩位學生,後來才逐漸增加招生人數,我那一屆只有七名學生。
不過,進入了人才濟濟的東大之後,我很快就發現一件事:
我沒有比別人聰明!
因此,「努力」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經過兩年的學習,準備碩士論文時,我花了整個暑假研究文獻,但是教授一看到我寫的論文,立刻毫不留情地批評「這樣的論文水準,不過是高中生的讀書心得而已」。
當下,我的心涼了半截,眼淚差點掉了下來,趕緊躲到廁所整理自己的情緒。看著鏡子中紅著眼眶的自己,我努力對自己說:「加油」、「不要哭」,眼淚卻還是不爭氣地滑下來……
回到研究室後,教授說有事必須離開,我不敢耽誤他的時間,又不願意放過能和教授單獨面談的機會,所以緊跟在他身後,一起搭上電車,窮追不捨地詢問他的意見,直到完全明白教授要求的論文標準為止。
事後,教授對其他同學稱讚我是個「一生懸命」(努力堅持到底)的人;或許是看到了我認真的學習態度,即使,平常他已經累到連搭電梯時都會闔上眼睛打瞌睡的程度,還是會繼續撥冗跟我討論修改論文的細節。
除此之外,他還會特別交代一些優秀的學長姊幫忙指導我,讓我在兩年內完成了長達二十萬字的論文,順利拿到碩士學位。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在教授研究室流下的「不甘心的眼淚」,正是支持我一路前進的動力。我不想要再一次因為自己的不甘心而哭泣,也不希望讓將來的自己後悔,因此,無論情況如何困難,我都告訴自己,一定要完成畢業論文,對於想要達成的目標,更該全力以赴!
◎幫助你登上高峰的「低氧腦」
進入東大當外國人研究生後,我的目標是考上東大社會情報學研究所,成為正式的東大學生。
為了順利考取東大研究所,我讓自己隨時處在「低氧腦」的狀態。「低氧腦」這個名詞是我自創的,意即「就算面對惡劣的環境,仍然專注地向前邁進。」。馬拉松選手在接受長跑訓練時,會特地挑選在氧氣稀少的高地進行跑步練習,讓自己的身體適應低氧狀態;接受過低氧訓練的馬拉松選手,經歷了惡劣環境的考驗,以後不管到任何地方比賽,都可以應付多變的天候和環境。
那段日子,我努力調適心情,讓心中的雜念和外界的誘惑徹底淨空。從確定要考東大的八月底開始,一直到隔年二月初考試為止,我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樣:念書、上課、吃飯、運動。早上八點到圖書館等開門,念書念到晚上九點圖書館關門才離開,除了圖書館休館日外,沒有一天間斷。
皇天不負苦心人,經過近半年的埋首苦讀,我終於通過了研究所入學筆試,接下來就是面試。
我記得,主考官之一就是我在第一堂課差點因為打瞌睡從椅子上跌下來的授課老師,他在問完所有專業問題後,抬頭看了一眼牆上的鐘,發現還有一些時間,於是又問了我一個基本問題:「我們上課時說的日文,你聽得懂幾成?」
我老實地說:「日常的會話大概是八成,但是上課的內容大概是七成吧。」
一般人可能認為,主動坦承自己日文程度不佳,大概很難考上以入學審核嚴格出名的東大研究所。但是,我不僅考上了,而且還成為「東大社會情報學研究所」創系以來第一位錄取的台灣學生。
這段期間鍛練出的「低氧腦」,讓我往後不管求學或工作,都能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完成目標,也成功地克服語言障礙的關卡,在東大的求學生活有如倒吃甘蔗,漸入佳境。此後,當我面對其他困難,或是覺得自己快要撐不下去時,就會回想起這段寶貴的經驗,讓它幫助自己勇敢地走下去。
我並不氣餒,再次致電過去,找到了那位總編輯。總編輯很高興我推薦這本書給她,但她對於我的英文能力似乎有些擔心。
「妳的英文很好嗎?」總編輯單刀直入地問。
「我的英文沒有很好……」
「……」電話那頭出現了片刻的沉默。
「可是,我看過這本書的日文版,而且我幫客戶上過課……」我不放棄地繼續說。
「好吧!妳先試譯兩頁,我們再決定要不要請妳翻譯整本書。」
結果,總編輯看了我的試譯之後還算滿意,決定放手一搏,讓我嘗試翻譯整本書。老實說,翻譯這本書的過程十分痛苦。自從高中畢業之後,我就沒有認真讀過英文,連一些簡單的英文單字也都忘光光了。每處理一段文字,往往就會遇到三、四個生字需要查字典,一天下來,約莫只能翻譯一頁的文章。
到了截稿前一個月,還有四分之一的內容沒有翻譯完,我本來想發包給別人,但一想到自己翻譯這本書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了重拾自己的英文能力,最後也還是咬緊牙關,如期完成了這項工作。
日文有一句話說「不戰敗」,意謂「不戰而敗」。例如,因為自己趕不上比賽時間,連比都沒比就輸了。對我來說,「畫地自限」就是典型的「不戰敗」。因為覺得自己「一定不行」、「能力不夠」或「失敗了太丟臉」,連試都沒有去試就直接放棄,真的是很可惜的事。
可惜,在面臨「做」與「不做」的重大抉擇時,人們往往會比較在意「損失所帶來的痛苦」,反而容易忽略了「獲利所帶來的快樂」;也就是先思考行動後的利益得失,再來決定是否要採取行動。
為什麼人們會傾向不去冒險呢?因為,停留在原來的「舒適區」,讓人感到安心。如果我們把人所處的狀況大致分成三個區塊,以熟悉程度來做區分,分別是「舒適區」、「學習區」、「恐慌區」。
在「舒適區」中,這裡有讓自己覺得舒服的衣服、舒服的朋友、舒服的食物,沒有新的挑戰或不熟悉的事情,所以不必花腦筋,不管在心理層面或是生理層面上都容易覺得自在舒服。
我們在家裡喜歡穿柔軟又舒適的舊衣服,因為舊衣服讓我們覺得放鬆;我們習慣和自己覺得安全的老朋友來往,逃避結交新朋友所需要面對的風險;我們平常吃的食物總是固定那幾樣,去吃的中餐店家也是那幾間,因為那是我們習慣或者熟悉的味道,這些衣服、朋友、食物讓我們覺得熟悉、自在。我們不必要多花精神和時間去重新適應。
「舒適區」之外,是「學習區」和「恐慌區」。後面這二個區塊裡是不熟悉或未知的人事地物。我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喜歡未知的、沒有嘗試過的東西,但是可以知道的是,要接觸這些新事物,我們或多或少必須花費時間、力氣去認識或者適應它。對於某些人來說,要離開溫暖又舒服的「舒適區」,就像是在寒冷的冬天早晨,離開溫暖的被窩一樣地困難。
離開自在的「舒適區」,且面對未知的情況時會感到害怕、緊張,是很正常的情緒反應。因為,在舒適區之外,有太多未知的、不可抗的因素,可能會影響到現有的生活節奏,甚至會危害到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些人的看法則完全不同,他們認為舒適區之外的世界充滿了未知,因而感到新鮮、剌激。
「恐慌區」指的是目前做不到,而且壓根不知道要怎麼開始去做,一想到就讓人頭皮發麻、陷入恐慌的事。例如,「在國家戲劇院用義大利文演出歌劇『塞維利亞理髮師』」、「不攜帶人工氧氣登上高達八千公尺的高山」,如果要我們現在立刻去做這些高難度的挑戰,失敗、出醜的機率很大。
在舒適的被窩(舒適區)和冷洌的高山(恐慌區)之間,存在很大的空間,也就是所謂的「學習區」(也稱為「伸展區」或「成長區」),在「學習區」裡,人們會遇見不熟悉或未知的事物,於是展開新的「挑戰」,有可能「失敗」,但也有可能「成功」,不管是哪一種後果,只要願意離開自己的「舒適區」,把腳趾頭伸進「學習區」,總是會有「新發現」、「新學習」;不僅發掘新的事物,也會發現自己對這個新事物的反應。人們在「挑戰」、「失敗」、「發現」、「學習」之間來來回回,會發現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讓沉睡的潛在能力得到更多發展、成長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