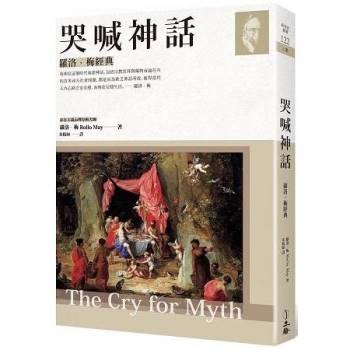神話是什麼
有效研究,神話...不是對科學興趣的圓滿解釋,而是關於原始事實的重新敍述,滿懷宗教願望和道德熱望。-布魯尼斯勞·馬林諾斯基《魔術,科學和宗教》
神話就是在無知的世界獲取意義的一種方式。神話是告知我們存在的重要性的方式。不論存在的意義是如薩特堅持的那樣要靠我們自己的堅毅在生活中體會到,還是象克科哥德堅持的需要我們去發現其中的意義,其結果都是一樣的:神話就是我們發現這種意義及其重要性的方式。神話就像是房間裏流淌的小溪:它們沒有暴露在外邊,而是構成了房間的結構,使得人們居住在裏面。
產生神話對於保持精神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而富有同情心的精神治療家將會發現這一點。事實上,當代精神療法的產生和發展恰是從我們的神話中分解得來的。
正是通過神話,一個健全的社會將她的成員們從患精神病的罪惡感和過度不安的狀態下緩解出來。例如,在遠古的希臘,神話的作用強大而且不可缺少,所以那個社會的人們能夠認識到存在的問題而不致陷入極度不安或罪惡感的狀態。由此我們發現那個時代的哲學家們熱衷於談論美麗、真理、善良和勇氣,並將此視為人類生命的美德。
但是,隨著古希臘神話的破滅,類似情況曾發生在西元二、三世紀時,盧克瑞提斯看到了「人們內心隱隱作痛,因懊悔而深感痛苦難忍,精神無法得到平靜,而不得不通過反抗、抱怨的方式發洩自己。」
我們生存的二十世紀是類似「心痛」和「反抗」的狀態。我們的神話已不再能使我們瞭解自身的存在,今天的人們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目標,從而陷入了不安和極度罪惡感的混亂狀態。於是大家紛紛湧向精神分析家或他們的代理人,或者是藥品、崇拜,來尋求幫助使大家團結在一起。精神分析家澤若姆·布諾娜這樣寫道:「當以前的神話不再適於人們各種各樣的困境時,首先在精神上出現了挫折,其次是在人們對內在身份的探求中。」
這種「對內在身份的探求」是一種廣泛的需求,它由此引起我們社會的精神分析學的發展以及其他多種形式的精神療法和多種萬靈丹和盲目崇拜的發展,且不管這些發展形式是積極的還是破壞性的。「我從來沒有承諾過你玫瑰園」
《我從來沒有承諾過你玫瑰園》這部自傳體小說,講述了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年輕女孩,德伯阿,在與一位精神病專家接觸治療的真實經歷,她的治療過程中發生的一些令人興奮的事讀來就象一部永恆的超越地球之外的電影。在她的治療過程中,我們不斷發現神話間的扣人心弦的相互作用。德伯阿(人們這樣稱呼她)同愛帝特、安特瑞伯、來克特們、克來特等那些生活在「外厄」王國的神話人物為伴。因為這個世界上再沒有別人能跟德伯阿進行交流,所以她非常需要這些神話形象。她這樣寫道:「外厄」的上帝已成為同伴-----秘密地,並且小心謹慎地分享她的孤獨」當她感到害怕或者在所謂的真實世界裏無法忍受孤獨時,她常常想逃向他們。
在去往休息地的路上,如德伯阿所說,她和她的父母在一家汽車旅館的相連的房間裏過夜。
在牆的另側,德伯阿伸展開身子睡覺。「外厄」王國有一種保持中立的地方叫第四位置。這裏只能靠偶然達到而不能靠慣例或有意識的行為。在第四位置,沒有什麼情感需要忍受,也沒有什麼過去和將來要我們消磨。
現在,已到達第四位置,躺在床上,將來與她沒有關係。隔壁的房間應該住著她的父母,很好。但是這是一個模糊正在消失的世界的一部分,而她現在正被拋向另一個新的毫不相關的世界,從舊世界轉移的過程,也便是她從外厄王國的複雜事物、從其他人物、從檢查官、從外厄的上帝轉移的過程。她翻了個身,睡了沉沉的、無夢的、寧靜的一夜。
次日清晨,她告訴我們,她感受到了神話帶給她的最大的安心和慰藉。
...當汽車駛出汽車旅館到陽光之下時,德伯阿意識到這次旅行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她所感覺到的平靜和自由可能為她從上帝和外厄王國得到一件新的禮物。
德伯阿設計的那些上帝不僅以其想像力的深度而著稱,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與30年後如《E·T·》,《傑帝的回歸》,《接觸第三類別》以及其他超世界電影中的描述極其相似,而這些電影在二十世紀末期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孩子和大人。德伯阿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是,如果有人想區別精神分裂症和完全有創造性的想像力,那他總會感到困惑。漢娜·喬治(她的筆名)這樣寫:她開始下落,同安特瑞伯一起穿過邊際有火光的黑暗到達外厄王國。下落的時間很長,有一段很長的黑暗,然後一陣灰暗,感覺成群接隊地穿過眼前。地點很熟悉,是「彼特」。在這裏,上帝們和克來特呻吟著,叫喊著,但叫的什麼卻令人費解。人的聲音也傳過來;並不帶有任何意思。世界被侵擾了,但這只是一個破滅的、不可辨認的世界。
在撒斯特那特羅斯為德伯阿治療的精神病專家,弗瑞德·弗羅姆·瑞斯曼,一開始就明白地告訴德伯阿不要違背意願地「趕走」那些上帝。弗瑞德博士,書中這麼稱呼她,把上帝用在治療中,有時她會建議德伯阿對上帝這麼這麼說,偶爾她也會問德伯阿上帝說了寫什麼。最重要的是弗羅姆·瑞斯曼博士尊重德伯阿對神話人物的需要,同時她也試圖幫助德伯阿明白,就是德伯阿自己創造了它們。
「我們說完了」,醫生優雅地說,「你告訴了我關於神秘世界的事實,你做得很好。我想讓你回去告訴那些上帝、克來特和監視員,就說我不怕他們,我們誰也不會因為他們的力量而停止工作。」
但是,當弗瑞德不得不到歐洲避暑時,德伯阿暫時派給一位充滿理性主義的年輕的精神病專家治療。這位年輕專家因無法理解德伯阿對神話的需要而一舉破壞了德伯阿的「幻想」。結果呢,德伯阿,她的上帝體系及其超越現實的王國陷入一片混亂,變了質。她退縮到了一個完全封閉的世界。她放火燒了休息地,嚴重燒傷了自己,而且她的行為舉止也象喪失人性一樣。這帶有文學色彩。而她的精神——被認為對她的意識起著最密切、最重要的作用——已經被掏空了,她沒有支柱了。
當弗瑞德博士從歐洲歸來後,德伯阿把這些告訴了她,德伯阿哭訴道,另外那個精神病專家,「只不過想證明他自己是多麼正確,多麼精明。」,她流著淚接著說,「那個專家可能也說過,恢復你的心智吧,停止愚蠢的行為,上帝詛咒我!」德伯阿呻吟道,「上帝詛咒我!」
我們可以將這位理性主義者的精神分析專家的行為視為對我們現在時代的諷喻。二十世紀裏,當我們熱衷於證明技術的正確時,我們一下子拋開了「愚蠢」的神話,以至我們剝奪了我們自己的精神,面臨著社會變質的威脅。德伯阿的神話一直持續到《我沒有承諾過你玫瑰園》一書的最後一頁。至此,她已經明白了她的神話也便是她自己豐富創造力的一部分。弗瑞德博士也曾幫助她理解了神話採取的形式——起初稱為精神分析法——其實在她自我能力之內。
儘管德伯阿對神話的產生起著一定的作用,但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她並沒有創造出對神話的需求。這種需求是我們人類命運的一部分,是我們的語言的一部分,是我們彼此交流的方式。在治療結束時,德伯阿的創造性以對她自己和社會有利的形式顯露出來;在徹斯特那特·羅治的治療徹底結束後,她寫作並發表了好幾部優秀的小說,其中至少兩部是關於嚴重患病者的。
本書的內容並非僅限於精神分裂症患者,而是關於我們大家對產生於我們人類特性的神話的需求。這些神話所採取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是,對神話的需求,事實上,神話的「哭喊」,將會存在於任何稱之為人類的人出現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都象德伯阿:儘管我們以各種獨特的、個人化的方式擁有自己的神話,但是這些神話卻成為連接我們的生物性和人性的不可或缺的橋樑。
神話是我們在與外面的世界接觸過程中對內在自我的一種解釋。通過它們的敍述,我們的社會成為整體。緣於中國、印度、西藏、日本及其它東方諸國的神話,出自不同的文化,所以我們只能部分地理解它們,但是它們已經呈現給了我們一座「花園」,最起碼我們可以在花園大門口賞花。約翰‧克波拜爾已經就世上不同國家的神話做過出色的調查,而我這本書,相比照,講述的是我們美國的神話,是那些在現實的世界裏、在精神治療中、在社會的和宗教的經歷中出現的神話。]在保持我們精神活躍的過程中,使我們在艱難的、常常毫無意義的世界裏獲得新的含義的過程中,神話起著基礎性的作用。一些永恆的東西如美麗、愛、理想會突然或不斷地用神話的語言出現。
由此而言,在精神治療中神話是很重要的。精神病專家允許患者認真對待他們自己的神話,不論這些神話來源於夢鄉、自由結合還是想像。崇拜和神話
已經過去的幾十年間,年輕人中自殺的統計數字驚人。70年代,年輕的白種人自殺者劇增。我們曾用諸如給精神壓抑者打電話等各種方式來阻止年輕人自殺。但是,只要我們還把掙錢作為最高目標,只要我們在家裏或在機關沒有教授一種道德的規範,只要這些年輕人沒有被激發形成一種人生哲學,只要電視裏仍充斥著暴力和性而沒有可信賴的顧問教我們如何去愛——只要這些還流行,那麼令人擔心的精神壓抑和自殺仍會在年輕人中繼續存在。
最近,在斯坦福大學的一次畢業講演中,一名學生代表這樣描述他的班級:不懂得「與過去和將來有何聯繫,對現實幾乎沒有感覺,缺乏支撐生命的信仰,世俗而迷信」,並且經常「沒有行為的目標和方法」。只要我們的世界或社會缺乏代表信仰和精神目標的神話,就會存在沮喪和自殺的現象。如下文所示,後面的章節我們會涉及到道德空虛的原因,這裏我們僅僅指出缺乏神話就好象缺少語言一樣,難以就某一主題進行溝通。
就在這樣的毫無目標的狀態下,我們忽然發現我們自己已接近二十世紀的尾聲了,許多狂亂的人們或湧向了新的盲目崇拜,或重新拾起舊的崇拜,一方面為他們的不安尋找答案,為他們的罪惡感或壓抑感尋找解脫,另一方面尋找什麼來填補生命的真空狀態,這一切看來似乎並不奇怪。而且他們也向占星家乞求指導。*[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這座城市的32000000人相信占星術。」它是「對生命意義的探求,」國際星術研究協會的主席堅持說。「知道你的星在哪里,就如同掌握了生命問題的天氣預報一樣。」特別是在非常時期,人們會尋找「生命的答案」。(紐約時代,1975年10月9日)
卡爾·賽根在他的電視影集中費了很大力氣攻擊占星術為偽科學。爭論出自他自己恰是占星術教授,而他看來沒有意識到占星術有著完全不同的基礎,占星術是一種神話,它也需要神話的語言。它亦有神話的缺點,也有其積極的影響。] 或者他們抓住緣自原始時期的迷信觀念,使人想起巫術的年代。*[這裏有許多類似的崇拜由瑞耐斯,傳帕,德·夫·約翰,羅德克裏斯琴,馬克唐那德,莫尼斯等引導。新的崇拜每年都出現。在這裏我並不想就這些派別的價值和不足作出評判;我提到它們,因為人們湧向它們是為了找到對待他們生命的方法,是為了找到處理他們的不安和獲取生命的意義和目標的方式。]理性主義出現,文明教育廣泛傳播,宗教信仰自我完善和清除所有迷信觀念,伴隨著這樣的時代,我們的二十世紀宣佈降臨了。事實上,啟蒙運動時的大部分不大能實現的目標現已經至少是部分實現了:我們一些人擁有大量財富,在西方社會大部分人將暴行中的自由視為目標,科學廣泛傳播。但是,發生了什麼?作為個人我們更加糊塗了,缺乏道德理想,害怕將來,不知道做些什麼來改變情況,也不知如何拯救我們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們原來是最好的盲從者,」阿奇伯德·邁克雷斯宣佈:
我們為事實所困,但是我們已失去或正在失去我們人類感知自己的能力…
...現在我們通過事實,通過幻想,運用頭腦已知道了。看來我們並不能像莎士比亞那樣獲得答案,莎士比亞知道是誰使得李爾王站在荒地上向失明的格魯塞斯特哭喊:… 「你看到世界如何運轉了,」 格魯塞斯特回答到:「我深情地看到了。」
語言只有在失去了人類的溫暖、顏色、親密的含義、存在的價值的情況下會放棄神話,而這些構成了每個人生命的意義。通過清楚他人語言的主題思想,通過嘗試對他人世界非常重要的詞語,我們彼此理解。失去了神話,我們就會象一群大腦損傷的人不能明白話語,不能聽到聲音。對於同時代文明的貧困和通常對神話解釋的虛假,我們更能證明後者。
從對麻醉劑的使用上可以看出對神話的渴求和因為沒有足夠的神話導致的缺乏勇氣。如果我們不能懂得生命的意義,我們只能借助古柯鹼、海洛因、猛擊或其他藥品,通過暫時地「飄飄欲仙」的感覺,暫時從日常煩惱中解脫出來,這也是我們在精神療法中常見的一種方式:當某人發現他的希望極渺茫時,他可能會考慮採取服用過量藥物或刺痛他自己的方法感受他的命運。如果我們註定要走向滅亡,那麼與其痛苦嗚咽倒不如猛撞離去。
今天,人們紛紛湧向崇拜,特別是年輕人和老年人,也暗示了對神話的迫切需要。任何組織只要它能許諾帶來福氣、愛,能指出通向上帝之路,它就會擁有觀眾,就會有人湧向它,不論它叫什麼。吉姆·約翰斯和圭亞那悲劇,因為聽從權威人士約翰斯980名追隨者集體自殺,這仍然是我們無法忘記的警鐘。盲目崇拜具有神話沒有的社會限制、約束、社會責任等力量。所以我們應該聽取神話的哭喊,因為除非我們獲得可信賴的神話,才能夠填補假神話和信仰巫術的真空。社會學家告訴我們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量投票表明人們對上帝的信仰正在下降,而對撒旦的信奉正在加強。有些人認為我們的社會正在分裂,需要某種方式予以解釋,而上述這種現象恰是此類人對神話強烈渴望的反映。
為了不被認為毫無目標和荒謬可笑,那些沒有能力的人便通過信仰撒旦來瞭解世界,來尋求因果關係,當受到不公正威脅時,來減少不和諧的產生,而這種不和諧是因他們對不可理解的不負責任的社會秩序的承諾而產生的。
有效研究,神話...不是對科學興趣的圓滿解釋,而是關於原始事實的重新敍述,滿懷宗教願望和道德熱望。-布魯尼斯勞·馬林諾斯基《魔術,科學和宗教》
神話就是在無知的世界獲取意義的一種方式。神話是告知我們存在的重要性的方式。不論存在的意義是如薩特堅持的那樣要靠我們自己的堅毅在生活中體會到,還是象克科哥德堅持的需要我們去發現其中的意義,其結果都是一樣的:神話就是我們發現這種意義及其重要性的方式。神話就像是房間裏流淌的小溪:它們沒有暴露在外邊,而是構成了房間的結構,使得人們居住在裏面。
產生神話對於保持精神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而富有同情心的精神治療家將會發現這一點。事實上,當代精神療法的產生和發展恰是從我們的神話中分解得來的。
正是通過神話,一個健全的社會將她的成員們從患精神病的罪惡感和過度不安的狀態下緩解出來。例如,在遠古的希臘,神話的作用強大而且不可缺少,所以那個社會的人們能夠認識到存在的問題而不致陷入極度不安或罪惡感的狀態。由此我們發現那個時代的哲學家們熱衷於談論美麗、真理、善良和勇氣,並將此視為人類生命的美德。
但是,隨著古希臘神話的破滅,類似情況曾發生在西元二、三世紀時,盧克瑞提斯看到了「人們內心隱隱作痛,因懊悔而深感痛苦難忍,精神無法得到平靜,而不得不通過反抗、抱怨的方式發洩自己。」
我們生存的二十世紀是類似「心痛」和「反抗」的狀態。我們的神話已不再能使我們瞭解自身的存在,今天的人們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目標,從而陷入了不安和極度罪惡感的混亂狀態。於是大家紛紛湧向精神分析家或他們的代理人,或者是藥品、崇拜,來尋求幫助使大家團結在一起。精神分析家澤若姆·布諾娜這樣寫道:「當以前的神話不再適於人們各種各樣的困境時,首先在精神上出現了挫折,其次是在人們對內在身份的探求中。」
這種「對內在身份的探求」是一種廣泛的需求,它由此引起我們社會的精神分析學的發展以及其他多種形式的精神療法和多種萬靈丹和盲目崇拜的發展,且不管這些發展形式是積極的還是破壞性的。「我從來沒有承諾過你玫瑰園」
《我從來沒有承諾過你玫瑰園》這部自傳體小說,講述了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年輕女孩,德伯阿,在與一位精神病專家接觸治療的真實經歷,她的治療過程中發生的一些令人興奮的事讀來就象一部永恆的超越地球之外的電影。在她的治療過程中,我們不斷發現神話間的扣人心弦的相互作用。德伯阿(人們這樣稱呼她)同愛帝特、安特瑞伯、來克特們、克來特等那些生活在「外厄」王國的神話人物為伴。因為這個世界上再沒有別人能跟德伯阿進行交流,所以她非常需要這些神話形象。她這樣寫道:「外厄」的上帝已成為同伴-----秘密地,並且小心謹慎地分享她的孤獨」當她感到害怕或者在所謂的真實世界裏無法忍受孤獨時,她常常想逃向他們。
在去往休息地的路上,如德伯阿所說,她和她的父母在一家汽車旅館的相連的房間裏過夜。
在牆的另側,德伯阿伸展開身子睡覺。「外厄」王國有一種保持中立的地方叫第四位置。這裏只能靠偶然達到而不能靠慣例或有意識的行為。在第四位置,沒有什麼情感需要忍受,也沒有什麼過去和將來要我們消磨。
現在,已到達第四位置,躺在床上,將來與她沒有關係。隔壁的房間應該住著她的父母,很好。但是這是一個模糊正在消失的世界的一部分,而她現在正被拋向另一個新的毫不相關的世界,從舊世界轉移的過程,也便是她從外厄王國的複雜事物、從其他人物、從檢查官、從外厄的上帝轉移的過程。她翻了個身,睡了沉沉的、無夢的、寧靜的一夜。
次日清晨,她告訴我們,她感受到了神話帶給她的最大的安心和慰藉。
...當汽車駛出汽車旅館到陽光之下時,德伯阿意識到這次旅行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她所感覺到的平靜和自由可能為她從上帝和外厄王國得到一件新的禮物。
德伯阿設計的那些上帝不僅以其想像力的深度而著稱,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與30年後如《E·T·》,《傑帝的回歸》,《接觸第三類別》以及其他超世界電影中的描述極其相似,而這些電影在二十世紀末期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孩子和大人。德伯阿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是,如果有人想區別精神分裂症和完全有創造性的想像力,那他總會感到困惑。漢娜·喬治(她的筆名)這樣寫:她開始下落,同安特瑞伯一起穿過邊際有火光的黑暗到達外厄王國。下落的時間很長,有一段很長的黑暗,然後一陣灰暗,感覺成群接隊地穿過眼前。地點很熟悉,是「彼特」。在這裏,上帝們和克來特呻吟著,叫喊著,但叫的什麼卻令人費解。人的聲音也傳過來;並不帶有任何意思。世界被侵擾了,但這只是一個破滅的、不可辨認的世界。
在撒斯特那特羅斯為德伯阿治療的精神病專家,弗瑞德·弗羅姆·瑞斯曼,一開始就明白地告訴德伯阿不要違背意願地「趕走」那些上帝。弗瑞德博士,書中這麼稱呼她,把上帝用在治療中,有時她會建議德伯阿對上帝這麼這麼說,偶爾她也會問德伯阿上帝說了寫什麼。最重要的是弗羅姆·瑞斯曼博士尊重德伯阿對神話人物的需要,同時她也試圖幫助德伯阿明白,就是德伯阿自己創造了它們。
「我們說完了」,醫生優雅地說,「你告訴了我關於神秘世界的事實,你做得很好。我想讓你回去告訴那些上帝、克來特和監視員,就說我不怕他們,我們誰也不會因為他們的力量而停止工作。」
但是,當弗瑞德不得不到歐洲避暑時,德伯阿暫時派給一位充滿理性主義的年輕的精神病專家治療。這位年輕專家因無法理解德伯阿對神話的需要而一舉破壞了德伯阿的「幻想」。結果呢,德伯阿,她的上帝體系及其超越現實的王國陷入一片混亂,變了質。她退縮到了一個完全封閉的世界。她放火燒了休息地,嚴重燒傷了自己,而且她的行為舉止也象喪失人性一樣。這帶有文學色彩。而她的精神——被認為對她的意識起著最密切、最重要的作用——已經被掏空了,她沒有支柱了。
當弗瑞德博士從歐洲歸來後,德伯阿把這些告訴了她,德伯阿哭訴道,另外那個精神病專家,「只不過想證明他自己是多麼正確,多麼精明。」,她流著淚接著說,「那個專家可能也說過,恢復你的心智吧,停止愚蠢的行為,上帝詛咒我!」德伯阿呻吟道,「上帝詛咒我!」
我們可以將這位理性主義者的精神分析專家的行為視為對我們現在時代的諷喻。二十世紀裏,當我們熱衷於證明技術的正確時,我們一下子拋開了「愚蠢」的神話,以至我們剝奪了我們自己的精神,面臨著社會變質的威脅。德伯阿的神話一直持續到《我沒有承諾過你玫瑰園》一書的最後一頁。至此,她已經明白了她的神話也便是她自己豐富創造力的一部分。弗瑞德博士也曾幫助她理解了神話採取的形式——起初稱為精神分析法——其實在她自我能力之內。
儘管德伯阿對神話的產生起著一定的作用,但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她並沒有創造出對神話的需求。這種需求是我們人類命運的一部分,是我們的語言的一部分,是我們彼此交流的方式。在治療結束時,德伯阿的創造性以對她自己和社會有利的形式顯露出來;在徹斯特那特·羅治的治療徹底結束後,她寫作並發表了好幾部優秀的小說,其中至少兩部是關於嚴重患病者的。
本書的內容並非僅限於精神分裂症患者,而是關於我們大家對產生於我們人類特性的神話的需求。這些神話所採取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是,對神話的需求,事實上,神話的「哭喊」,將會存在於任何稱之為人類的人出現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都象德伯阿:儘管我們以各種獨特的、個人化的方式擁有自己的神話,但是這些神話卻成為連接我們的生物性和人性的不可或缺的橋樑。
神話是我們在與外面的世界接觸過程中對內在自我的一種解釋。通過它們的敍述,我們的社會成為整體。緣於中國、印度、西藏、日本及其它東方諸國的神話,出自不同的文化,所以我們只能部分地理解它們,但是它們已經呈現給了我們一座「花園」,最起碼我們可以在花園大門口賞花。約翰‧克波拜爾已經就世上不同國家的神話做過出色的調查,而我這本書,相比照,講述的是我們美國的神話,是那些在現實的世界裏、在精神治療中、在社會的和宗教的經歷中出現的神話。]在保持我們精神活躍的過程中,使我們在艱難的、常常毫無意義的世界裏獲得新的含義的過程中,神話起著基礎性的作用。一些永恆的東西如美麗、愛、理想會突然或不斷地用神話的語言出現。
由此而言,在精神治療中神話是很重要的。精神病專家允許患者認真對待他們自己的神話,不論這些神話來源於夢鄉、自由結合還是想像。崇拜和神話
已經過去的幾十年間,年輕人中自殺的統計數字驚人。70年代,年輕的白種人自殺者劇增。我們曾用諸如給精神壓抑者打電話等各種方式來阻止年輕人自殺。但是,只要我們還把掙錢作為最高目標,只要我們在家裏或在機關沒有教授一種道德的規範,只要這些年輕人沒有被激發形成一種人生哲學,只要電視裏仍充斥著暴力和性而沒有可信賴的顧問教我們如何去愛——只要這些還流行,那麼令人擔心的精神壓抑和自殺仍會在年輕人中繼續存在。
最近,在斯坦福大學的一次畢業講演中,一名學生代表這樣描述他的班級:不懂得「與過去和將來有何聯繫,對現實幾乎沒有感覺,缺乏支撐生命的信仰,世俗而迷信」,並且經常「沒有行為的目標和方法」。只要我們的世界或社會缺乏代表信仰和精神目標的神話,就會存在沮喪和自殺的現象。如下文所示,後面的章節我們會涉及到道德空虛的原因,這裏我們僅僅指出缺乏神話就好象缺少語言一樣,難以就某一主題進行溝通。
就在這樣的毫無目標的狀態下,我們忽然發現我們自己已接近二十世紀的尾聲了,許多狂亂的人們或湧向了新的盲目崇拜,或重新拾起舊的崇拜,一方面為他們的不安尋找答案,為他們的罪惡感或壓抑感尋找解脫,另一方面尋找什麼來填補生命的真空狀態,這一切看來似乎並不奇怪。而且他們也向占星家乞求指導。*[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這座城市的32000000人相信占星術。」它是「對生命意義的探求,」國際星術研究協會的主席堅持說。「知道你的星在哪里,就如同掌握了生命問題的天氣預報一樣。」特別是在非常時期,人們會尋找「生命的答案」。(紐約時代,1975年10月9日)
卡爾·賽根在他的電視影集中費了很大力氣攻擊占星術為偽科學。爭論出自他自己恰是占星術教授,而他看來沒有意識到占星術有著完全不同的基礎,占星術是一種神話,它也需要神話的語言。它亦有神話的缺點,也有其積極的影響。] 或者他們抓住緣自原始時期的迷信觀念,使人想起巫術的年代。*[這裏有許多類似的崇拜由瑞耐斯,傳帕,德·夫·約翰,羅德克裏斯琴,馬克唐那德,莫尼斯等引導。新的崇拜每年都出現。在這裏我並不想就這些派別的價值和不足作出評判;我提到它們,因為人們湧向它們是為了找到對待他們生命的方法,是為了找到處理他們的不安和獲取生命的意義和目標的方式。]理性主義出現,文明教育廣泛傳播,宗教信仰自我完善和清除所有迷信觀念,伴隨著這樣的時代,我們的二十世紀宣佈降臨了。事實上,啟蒙運動時的大部分不大能實現的目標現已經至少是部分實現了:我們一些人擁有大量財富,在西方社會大部分人將暴行中的自由視為目標,科學廣泛傳播。但是,發生了什麼?作為個人我們更加糊塗了,缺乏道德理想,害怕將來,不知道做些什麼來改變情況,也不知如何拯救我們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們原來是最好的盲從者,」阿奇伯德·邁克雷斯宣佈:
我們為事實所困,但是我們已失去或正在失去我們人類感知自己的能力…
...現在我們通過事實,通過幻想,運用頭腦已知道了。看來我們並不能像莎士比亞那樣獲得答案,莎士比亞知道是誰使得李爾王站在荒地上向失明的格魯塞斯特哭喊:… 「你看到世界如何運轉了,」 格魯塞斯特回答到:「我深情地看到了。」
語言只有在失去了人類的溫暖、顏色、親密的含義、存在的價值的情況下會放棄神話,而這些構成了每個人生命的意義。通過清楚他人語言的主題思想,通過嘗試對他人世界非常重要的詞語,我們彼此理解。失去了神話,我們就會象一群大腦損傷的人不能明白話語,不能聽到聲音。對於同時代文明的貧困和通常對神話解釋的虛假,我們更能證明後者。
從對麻醉劑的使用上可以看出對神話的渴求和因為沒有足夠的神話導致的缺乏勇氣。如果我們不能懂得生命的意義,我們只能借助古柯鹼、海洛因、猛擊或其他藥品,通過暫時地「飄飄欲仙」的感覺,暫時從日常煩惱中解脫出來,這也是我們在精神療法中常見的一種方式:當某人發現他的希望極渺茫時,他可能會考慮採取服用過量藥物或刺痛他自己的方法感受他的命運。如果我們註定要走向滅亡,那麼與其痛苦嗚咽倒不如猛撞離去。
今天,人們紛紛湧向崇拜,特別是年輕人和老年人,也暗示了對神話的迫切需要。任何組織只要它能許諾帶來福氣、愛,能指出通向上帝之路,它就會擁有觀眾,就會有人湧向它,不論它叫什麼。吉姆·約翰斯和圭亞那悲劇,因為聽從權威人士約翰斯980名追隨者集體自殺,這仍然是我們無法忘記的警鐘。盲目崇拜具有神話沒有的社會限制、約束、社會責任等力量。所以我們應該聽取神話的哭喊,因為除非我們獲得可信賴的神話,才能夠填補假神話和信仰巫術的真空。社會學家告訴我們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量投票表明人們對上帝的信仰正在下降,而對撒旦的信奉正在加強。有些人認為我們的社會正在分裂,需要某種方式予以解釋,而上述這種現象恰是此類人對神話強烈渴望的反映。
為了不被認為毫無目標和荒謬可笑,那些沒有能力的人便通過信仰撒旦來瞭解世界,來尋求因果關係,當受到不公正威脅時,來減少不和諧的產生,而這種不和諧是因他們對不可理解的不負責任的社會秩序的承諾而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