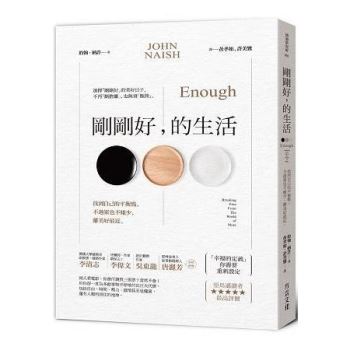資訊接收愈多,能理解的愈少
我們每天都被銷售訊息轟炸高達三千五百次,也就是在醒著的時候,每隔十五秒就遭受一次侵襲。二○○四年,世界各地的公司行號砸在廣告上的錢,總共超過二千億英鎊。過去十年來,英國的電視插撥廣告從三千支增加到八千支,電視頻道則從四個增加到一百二十三個。二○○六年,全球總共寄出了六兆封商務電子郵件,平均每天寄出一千萬封垃圾郵件。過去三十年內製造的新資訊,比之前五千年所製造的還多。除此之外,每個禮拜還能看到更多新的播客(podcast)、雜誌、增刊、有線頻道,以及廣播電台。另外還有網站、網頁內容、部落格,以及附有額外光碟的影片,裡面載有首輪看不到的一些內容。就連英國髮型連鎖店Toni & Guy,也開始在美容院裡裝設無線寬頻,好像即使是剪個頭髮,都不能沒有這些網路設施似的,美容院消費者會在網路上跟朋友說,「哈囉,親愛的,我正在髮型網路上上網。」
很多社會裡最聰明的人士,都受高薪的吸引而為廣告及行銷業助陣,設法把產品推銷給我們。在以前的年代,這些人本來可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或作家的,可是如今他們大量生產出來的複雜資訊,只會搞得我們頭昏腦脹而已。在媒體及預測公司恒利中心(Henley Centre)工作的專家,擔心我們會被銷售資訊弄得耳聾眼花。如今還有一些效果的傳統廣告活動,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資訊過多激起人類產生的本能反應,只會使今日的問題更加惡化:因為當我們被過多的資訊搞得困惑不堪時,就會覺得不得不搜尋更多資訊,以釐清自己的困惑。
恒利中心所做的一個調查顯示,我們正在變成一個囤積資訊的社會,新媒體等同在家裡囤積一大堆報紙的一種瘋狂生活方式。不滿這種調查結論的人之中,有七○%表示,「資訊對我來說永遠不嫌多。」可是也有一半的人說,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或精力去使用已擁有的資訊。想因應這種資訊超載感的一種方式,就是利用多工作業,設法在人腦中塞進更多資訊搜尋器。如今二十幾歲的人大都一面看著電視,一面上網。可是他們到底看進去了多少?電視廣告商擔心觀眾的注意力和記憶力就像降落傘一樣飄忽,也就是:資訊接收得愈多,理解得就愈少。我會到路易斯博士小屋去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大概是第一個強調此問題的人。一九九六年他就指出了一種新的社會病,並給了它一個很時髦的醫學名稱:「資訊疲乏症候群」(information fatigue syndrome)。路易斯曾經為路透社做過一個全球性研究,針對一千三百個在資訊壓力下工作的生意人作調查(這些人當時承受的資訊壓力,或許比現在的人少些)。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告訴他說,因資訊過多而產生的壓力,已經傷害了他們的親密關係,造成失眠,並使他們對自己的決策力產生懷疑。很多深受其苦的人的因應方式,是去搜尋更多資訊,以求了解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路易斯,一個六十幾歲的老頑童,直接把此病徵歸咎於資訊革命。當時他新杜撰的這個疾病,是如此契合我們的時代,以致很快就有了它自己的神話。英國《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很快就訪問了一個「資訊疲乏症候群患者」,談她痛苦的五年復原之路。翌年,艾德華・威爾許(Edward Welsh)甚至在《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裡報導說,這個病徵最初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的情報員身上檢查出來的。
當心資訊狂躁症上身
最近的研究支持路易斯早期的發現。倫敦大學研究者的報告說,通訊過度對人的影響可能比吸大麻還糟。他們聲稱,如果你吸一支大麻煙,你的智商可能暫時會減少四分。可是只要處於隨時可收發訊息和電子郵件的狀況,你的腦袋甚至可能完全關機,智商的整個十分都會喪失,有點像夜晚睡不著而導致頭昏腦脹的那種感覺。研究宣稱,這是因為你不斷覺得必須停下來檢查信箱,以致把專注力都耗竭了。這種持續處於分心狀況下的心理狀態,使得我們察覺不出原本應可提高生產力的那些訊息,結果減損了應有的生產力。同樣的,我們也因耽溺於網路訊息而不注意身邊的人,以致破壞了社交生活。報告中並對這種強迫性衝動創造了一個時髦的名稱:「資訊狂躁症」(infomania)。要見證這種強迫性衝動的影響有多深,只要坐在一個熱鬧的Pub裡,觀察人們對同伴禮貌性關注的文明禮儀,總是在一個人的手機響起時就中斷了便可得知。我們每個人都愈來愈有資訊癖,不斷強迫性地想抓住每個片段的資訊,希望有一天能發現奇妙的事情,以弄懂其他一切事物。這種弔詭的情況,象徵了我們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富裕年代裡所面對的許多問題。我們的求生策略,在其他原始人類死亡之際,伴隨著我們度過了幾千年充滿匱乏及威脅的歲月,如今卻正在破壞著我們享受富裕生活的機會。資訊狂躁症的根源,其實就深植在我們的進化心理學裡,它也是驅策我們追求更多食物、工作、財產、機會,以及幸福的潛在破壞性驅力。在我們祖先進化的熱帶大草原上,你必須提高警覺,就像這是生存所繫似的。沒錯,當時的確如此,你必須充分運用你所擁有的資訊。人類的新奇感,包括面對新臉孔、新形體、新概念等,很少會像現今時代這麼多,然而這會引發恐懼和好奇之間的心理衝突。這種新奇感會激起早期人類強烈的好奇心,讓他們克服絕種的恐懼,而去探索可能大有所獲的問題,像是:「如果我踢那隻蜥蜴一腳,會發生什麼事情?」可是走在時代前端探索未知的人,報酬和流血的機會都是最大的。許多世代之後,在原始人類大腦裡演化出來的報酬系統,會鼓勵人們去收集資訊,而且這在過去的演化大賽中,已證明是個致勝因素。
醫學測試顯示,這種機制在我們大腦中仍很活躍,每次我們學習某樣事物,身體就會給腦袋這種鴉片的快感。二○○六年,一位南加州大學腦神經科學家所做的研究報告指出,當我們掌握了一個新觀念時,理解力就會卡嚓一聲釋放出一股腦部化學物質,用海洛因似的鴉片類(opioid)天然物質來犒賞大腦。作此研究的歐文・彼德曼(Irving Biederman)說,在人類大腦要求新資訊的區域裡,有一簇鴉片類物質接收器。他認為,無論何時,只要我們從這世界學到了一些東西,或是想到了重要或聰明的想法,進化就會讓我們變得很興奮,因為這能讓我們搶先競爭者一步。「人類本來就被設計成要吸收資訊的,」他說,「如果你想了解某種艱深的理論,這並不是什麼有趣的事,可是一旦辦到了,你就會覺得很開心。」直到最近,大腦才完全關閉了這種用化學物質激勵我們索取新想法的機制。這種獎勵系統因為一而再的緊迫要求食物或安全,變得自動失效了。躺在今日舒適的沙發裡,已經沒有掠食者或饑荒來威脅我們的閒暇,所以資訊狂躁症甚至能在最懶惰和最憎惡冒險的人身上發作,結果產生了對恐怖新聞、陳腐消息、名人八卦及媒體垃圾的大量需求。只要能提供新奇感,我們就可從中獲得刺激。我們不斷尋找新資源,以求獲得小小的刺激,因為新奇經驗每重複一次,做為獎勵而分泌的鴉片類化學物質就會隨之減少。彼德曼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掃描自願接受實驗者的大腦,發現他們每重複看一次同樣的圖片,刺激就會減少。媒體業對這個發現所做的反應,就是向我們推銷能更迅速引爆反應的刺激,努力逼迫我們產生「哇,你看!」的反應,讓我們對新奇感上癮得更嚴重,並縮短我們注意力的持續期。
被垃圾資訊所淹沒
除了這種立即性的影響之外,我們被資訊淹沒的文化,也可能扼殺了我們關機自救的欲望,而使得人類無法繼續進化。這種危險就隱藏在虛擬世界裡愈來愈多的誘惑中,因為虛擬世界提供了許多捷徑,使我們大腦能經驗到生物學上令人興奮的暗示,像是擁有迷人又順從的伴侶,而這本來是必須走進外在真實世界才找得到的。我們追求刺激的大腦電路結構不再需要我們離開沙發,就能獲得滿足。我們的潛意識、本能化的大腦,並不在乎這種刺激只存在於不值錢的電腦世界,甚至不在乎明知這只是廉價的贗品,卻仍盡可能地沉浸其中。這就說明了何以愈來愈多人寧願看色情書刊,而不願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追求親密的性關係;寧願玩虛擬的電視球賽,也不願在真實世界做運動;寧願看交友節目,而不願花時間與朋友交往。「我們正在消滅自己的腦幹,」新墨西哥大學一位演化心理學家吉歐佛瑞・米勒(Geoffrey Miller)這麼說。他認為,人類龐大的發明才能,如今都用在創造虛擬經驗上,而不是用在製造真實事物的工業上,像是建立水力發電的水壩等。他甚至表示,這正是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與任何先進的外星文明搭上線之故,從理論上說,這些外星文明應該一直在圍繞我們銀河系一千億星球的某個行星上進化著。我們的知性生活從來未能跨越虛擬世界的科技階段,而能不沉迷其中:因為虛擬世界裡的外星人都寧願在外太空玩Martian版PlayStation的而絕種,也不願去做在銀河系建立殖民地的必要工作。不過,米勒倒是認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基因差異論,或許能產生另一種可能性,亦即另一群新人類可能從虛擬世界的文化中進化出來,他們拒斥廉價電腦刺激的誘惑,在現實世界中利用科技而活得更有建設性。「那些能堅持的人會進化得更有自制力,更有良心,也更實用主義。」米勒說。不過他擔心,能建構出這種嚴格社會的人,也許只有強硬的宗教狂熱份子,他們留著長鬍鬚,戴著頭飾,痛恨閒暇、娛樂和自由思想。我則希望進化出來的是另一種人,他們熱情、幽默,而且奉行知足主義。
不管未來會發生什麼情況,如今我們的生活的確已塞滿了垃圾資訊。我指的不只是非法垃圾郵件,還包括我們每天猛發給彼此的那些既佔時間又無營養的電子郵件、電話及網路資訊。我自己的記者工作,也像其他所有的通訊業一樣,被堵塞靈魂的污染所淹沒了(當然,也很罪惡地在製造污染)。如果你在奶油蛋糕工廠工作,一定會吃很多奶油蛋糕。如果你在巨額融資公司上班,一定會賺很多錢回家。我以往十五年都在各種媒體裡挖掘事實和意見,所以每天腦袋都會捲進資訊漩渦裡。
不成為方便的受害者
我不是唯一遇到這種情況的人。我每週兩次搭火車到倫敦,車廂的寧靜總是被乘客拒接手機的聲音打斷,搪塞的藉口包括:「我現在正在家裡/辦公室裡,沒辦法接聽電話。」也有人明顯地推諉責任:「我想那是彼得・巴克雷的住家,可是他去度假了。」有純粹的迂迴戰術:「我正要進隧道……」(按鍵關機);還有人公然說謊:「我的火車嚴重誤點。」結果,血壓升高了,對商業卻了無助益。對家人或社交來電,人們答機時經常帶點粗魯的惱怒:「可是我現在也沒辦法,我人在火車上。」不過,米勒倒是認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基因差異論,或許能產生另一種可能性,亦即另一群新人類可能從虛擬世界的文化中進化出來,他們拒斥廉價電腦刺激的誘惑,在現實世界中利用科技而活得更有建設性。「那些能堅持的人會進化得更有自制力,更有良心,也更實用主義。」米勒說。不過他擔心,能建構出這種嚴格社會的人,也許只有強硬的宗教狂熱份子,他們留著長鬍鬚,戴著頭飾,痛恨閒暇、娛樂和自由思想。我則希望進化出來的是另一種人,他們熱情、幽默,而且奉行知足主義。
不管未來會發生什麼情況,如今我們的生活的確已塞滿了垃圾資訊。我指的不只是非法垃圾郵件,還包括我們每天猛發給彼此的那些既佔時間又無營養的電子郵件、電話及網路資訊。我自己的記者工作,也像其他所有的通訊業一樣,被堵塞靈魂的污染所淹沒了(當然,也很罪惡地在製造污染)。如果你在奶油蛋糕工廠工作,一定會吃很多奶油蛋糕。如果你在巨額融資公司上班,一定會賺很多錢回家。我以往十五年都在各種媒體裡挖掘事實和意見,所以每天腦袋都會捲進資訊漩渦裡。
不成為方便的受害者
我不是唯一遇到這種情況的人。我每週兩次搭火車到倫敦,車廂的寧靜總是被乘客拒接手機的聲音打斷,搪塞的藉口包括:「我現在正在家裡/辦公室裡,沒辦法接聽電話。」也有人明顯地推諉責任:「我想那是彼得・巴克雷的住家,可是他去度假了。」有純粹的迂迴戰術:「我正要進隧道……」(按鍵關機);還有人公然說謊:「我的火車嚴重誤點。」結果,血壓升高了,對商業卻了無助益。對家人或社交來電,人們答機時經常帶點粗魯的惱怒:「可是我現在也沒辦法,我人在火車上。」根本問題是,電訊讓我們成了方便性的受害者。對我的編輯來說,如果按下快速撥號鍵,記者就能隨傳隨到,那麼他很容易就會要求記者馬上去寫田鼠。因為這麼做實在太容易了。然而,如果這些編輯不得不花點力氣才追蹤得到他的寫作記者,而這個追蹤過程的不便性,假設會讓他經歷到要求記者寫作所造成不便性的百分之三,那麼這些編輯在打電話之前,就會多考慮一下了。在此我應該指出的是,如果自由工作者有一種罪行比「沒空」還大(對編輯說沒空,就像不斷追問編輯問題一樣,會惹惱他們),那就是在編輯委託你寫報導時經常說「不,謝了」。如果經常那麼做,他們就會完全不再與你連絡了。我的最佳解決之道,是熱情地把e-mail地址給每個人。我愛e-mail。如果編輯真的想要什麼東西,他們就得寫幾句話來要,這會讓他們的時間預算透支很多。但他們一時的不便,卻是我護城河裡救命的水。如今若說寫e-mail稍微帶點悠閒的味道,那是因為人家希望我們回覆得比手機留言或傳簡訊稍慢一點。
濫用方便性,助長了我們與手機的愛憎關係。在我不使用手機的這幾年,朋友用盡各種詞彙對我一再侮辱,包括慢性子、失敗者、怪胎、好命人,以及最後問道:「天曉得你怎麼認為自己擺脫得了這個?」麻省理工學院「勒梅森發明指數」(Lemelson Invention Index)的調查就不斷指出,手機是我們最痛恨的現代工具。勒梅森調查說,人們不喜歡手機,是因為「他們覺得被手機綁住了,要不就是覺得別人使用手機不當而感到困擾」。不過,當然,對我們自己來說,無論何時,只要自己覺得方便,就能隨意打手機給別人,倒是沒什麼不好的。但是我對我太太這麼做的時候,卻覺得有點罪惡感。她成功地實施了手機門禁制度,也就是除非她想打給某人,或特別在等某通電話,其他時候她一律關機。她這麼做一直都很順利,只有當我突然覺得有事要跟她商量,卻發現她沒有開機時,我就會發一頓因手機引起的典型小脾氣,在留言裡面對她吼道,「如果你不開手機,那帶著這個鬼東西在身上幹嘛?」當然,我們會為此大吵一架。製造晶片的英特爾公司所做的研究中,發現了更多誤用手機的證據,認為手機大大減少了人們對社交的依賴。五分之一的受訪者承認他們會故意遲到,因為他們可以在最後一分鐘用手機改變約會時間,四分之三的人則說,擁有手機讓他們「與朋友碰面的時間更有彈性了」(換言之,他們會故意遲到,卻不承認)。甚至有人怪罪手機會引起精神疾病。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Granada University)對幾百個十八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做了研究,宣稱其中四○%可能對手機上癮,因為一旦他們沒接到電話,就會覺得「心情極壞又傷心」,而關機則會「造成焦慮、易怒、睡不好或失眠」,甚至「發抖或消化不良」。此外,勞工常會依賴私人數位幫手,譬如黑莓機,所以常被稱為「黑莓族」,這表示他們可能已經對使用黑莓機上了癮。不過這究竟是上癮,還是因為追求更多東西,而引發社會壓力的一種惡性循環現象?
設定品質的門檻
想實行資訊節食,不一定得捨棄電視,不過多數人都會基於不同的理由,很快就決定要這麼做。這是因為電視這種商品有很多的附帶性,也就是能把愈來愈多功能都集中在一台電視上,可以接收地面、衛星和電纜的訊號,也能接收影片和所有視頻的訊息,同時還可以上網、收發電子郵件、傳資料,甚至能協助家庭記帳,多重功能替代了原本的單一功能。從不休息的電視對知足主義者是個超級大挑戰。擔心自己消息不靈通或社交孤立的人,會想接收這種永不中斷的資訊輸出,這就是電視所帶來的誘惑。
在電視還限制在大約只有四台時,看電視可說是一種共同經驗。大家看電視的選擇有限,所以第二天可以在商店或辦公室裡跟人聊所看的節目,而不用擔心講的是廢話,或根本沒看過最近大家都在討論的熱門節目。後來,由於可選擇的娛樂方式愈來愈多,所以大家的娛樂經驗已經暴增到不可能有共同性的程度,除非你一直都在一無遺漏地收看所有的節目。我敢打賭很多人都想這麼做。因為我們被資訊弄壞了的腦袋,會盡可能蒐集資訊來解除困惑。我們在社交上習慣競爭的腦袋,會想要所有最好最新的訊息。然而除非每週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收看所有的頻道,否則總會擔心有些更有娛樂性的節目自己沒有看到。想堵住這麼多資訊管道的唯一明智之舉,就是創造自己的知足策略。其實很多人已經這麼做了,方法就是在資訊品質上設定門檻,也就是訂下「不看爛節目」的規定。可是品質是種很不確定的東西,而且就像地心引力一樣,總是往下墜。不管怎麼說,面對不時出現的垃圾,看看又何妨?而且我們大可用更樂觀的態度來看待資訊娛樂,只要欣賞它的本性,享受它的本色就行了。然而娛樂資訊雖能帶來歡樂,卻會日久成習,改變心智,並有可能使人沮喪,可說再也沒有比它更廉價而豐沛的東西了。這種描述聽起來滿熟悉的,因為這就像飲酒一樣。
享受資訊娛樂時,要採取審慎的享樂主義者的態度,就像我們對飲酒應採取的審慎態度一樣,就能在資訊的享樂上找到可承受的解決之道,因為至少我們對飲酒的作法已經有經驗了。在所有有關飲酒作樂的標題中,大多數人都努力想讓酒帶給人生歡樂,而不想讓酒徹底毀了自己的肝臟。所以我們常給自己制定一些做得到的規定,像是天黑之後才能喝酒,只有週末才喝,或喝酒必須佐餐等。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為了資訊節食策略而制定一些生活習慣,基本上是要檢視哪些資訊管道對我們最合適,至於每天應該何時開機,也要有相當的紀律。
我們必須提高警覺,與飲酒相比,資訊娛樂過量時的負面影響比較不那麼立即可見,我們不會有口齒不清的宿醉,所以很容易忽略資訊過量而長期潛伏的後遺症。這主要牽涉到它可能壟斷我們大部分時間,而這些時間本來可以花在更能讓人生幸福的活動上。這些滋養性的活動,包括運動、嗜好、走出戶外享受大自然、發揮創意、與家人伴侶和朋友作有意義的相處、積極參與社區活動、開發自己的內在資源及精神層面……或是就單純坐著,不做任何事情。儘管我們大腦的原始天性就是容易被溝通吸引,但臨床研究顯示,想讓大腦皮質有活躍的反應,沒有上述滋養性活動是辦不到的。缺少那些活動,我們就會陷入躺在沙發上吃巧克力的不幸狀態中。工時過長不是工作,而是苦役
很多創業者都可能嘲笑馬泰爾太天真,錯失了這個可飛黃騰達的良機。這是個發財的大好機會,他卻沒有善加利用而放手讓它溜走了,隨之溜走的還有刺激的人生,包括事業成長、早餐會報、行銷活動、銀行會議、躍躍欲試的投資人、稅務顧問、人力資源問題,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事情,可以讓他從牛群、乳酪和果園中脫身。很少有英國人能拒絕這種工作繁忙的人生景象,因為它承諾要給你一個富有又有成就的未來。英國人比歐盟其他所有國家的工時都更長,平均每週工作四十二小時。這包括無數不支薪的加班日在內,而且即使英國的假日津貼在歐盟中是最低的,英國人仍然放棄了價值百億英鎊的有薪休假。
這讓英國人步向死亡。每週工作超過四十一小時的人,若與工時較短者相比,罹患高血壓的可能性會提高很多。曾有一份提交給布魯塞爾歐盟議會的調查報告,該報告預測說,繁重的生活壓力意味著,六○%的中產階級成人到了二○二七年時,都會罹患高血壓。日本人把長期過度工作而導致心臟病死亡的現象,取名為「過勞死」。英文也有新名詞,形容強打精神也要硬撐著工作的人,叫做「勉強上班族」(presenteeism)。那些人在辦公桌前坐了好幾個鐘頭,卻什麼事也做不出來,因為他們太累、壓力太大、太缺乏激勵、太不專心,或太沮喪,以致生產力低落。這比不上班還糟糕,因為職場中產生的碳排放量,有五分之一來自通勤。所以如果我們沒有生產力,還不如待在家裡工作得好。
工時過長,聽起來像是不得不為人幹活的一種苦役,但如今即使社會上很多有錢人,也認為工作繁忙是件很帥的事情。根據社會經濟研究協會的一項報告指出:「如今忙碌才有面子,悠閒則反之。」所以一定要硬撐到底。一九七○年代中期,很多文化評論家忙著提出警告,認為西方生活方式將受到一種很特別的威脅。他們認為,聖經啟示錄的第五位騎士✽,就是無盡的休閒。我們即將進入一個十足的美好新世界,那裡有高功能電腦、工廠自動化設備,還能用人人買得起的省力家電來做所有的家事。可是專家也提出疑問:那麼在科技為我們省下的時間裡,我們能做什麼呢?如果大部分的日常時間都不拿來從事生產的話,我們對自己會有什麼看法?如果所有的基本需求都很容易獲得滿足,我們要怎麼建立生活目標呢?會有那麼多的娛樂來充實我們的生活,好讓我們不致陷入厭倦、沮喪和精神上的荒蕪嗎?記得童年時看普遍級電視節目,當時專家預測,未來社會會發生很多不幸的事件,也預測無紙辦公室的來臨。可是如今職場上仍忙著砍殺樹木,也傷害著我們自己。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怎麼工作才算聰明?
所有這些有關職場的社會怪現象,讓很多人陷入這種困境。你可以叫我怪胎,可是我真的很喜歡我的工作。我發現工作很有收穫,至少大半時候是如此。當工作有趣的時候,真的讓人很快樂。就算有時工作並不那麼順利,反正我們偶爾也都需要覺得自己是個可憐蟲。事業成就之所以能造成這麼奇怪的困境,是因為它能增強我們的自尊心,讓我們擁有目標感。至於我,我還在工作中找到了一些真正持久的友誼。此外就是金錢,錢是我下半生不可或缺的東西,這樣工作就不會破壞我下半生的個人身心平衡了。
這就是知足主義者的挑戰:我們要能合理地享受社會所創造的舒適和方便性;要能正當地工作,而仍擁有自我空間和時間去感受滿足;雖然常有煩惱,但不致失控,仍能實現理想,而不必退出江湖。在這個一直強調工作的世界裡,彷彿在說:「要不就長時間工作,要不就乾脆不要工作,」我們究竟該如何做到知足的理念呢?在企業界裡,有沒有可能只在職位上作左右移動,而不是向下移動,也就是只擁有很知足的野心,而不必從整個企業體系中被刷下來?也許荷蘭的例子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荷蘭員工的工時在北歐是最短的,每週幾乎比我們少工作四小時。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對於怎樣工作才算聰明的看法,與我們大相逕庭。一項對全歐洲的研究發現,英國管理者認為一個員工經常加班,表示你肯獻身工作,所以是個高效能者。然而荷蘭人卻認為,如果你不能在正常時間內完成工作,那麼一定是你或你的工作出了問題。如果我們都到荷蘭去,也許就能多體驗沒有工作的生活了。但對於一直被慫恿著在長時間工作中混日子的英國人來說,享受荷蘭人那種少工作的日子,簡直就是浪費時間、自我耽溺,甚至是自甘墮落。
大約十年前,我正在研究報紙有關賽車的專題報導,這是英國蓬勃發展的一個小產業,喬和珍公關公司(Joe and Jane Public)花錢請人在車賽中駕駛自己的跑車和機車。我問布蘭茲・哈奇(Brands Hatch)賽場的公關人員,究竟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來駕駛這些車。「噢,都是些滿有錢的人,」他回答,「就是會在工作日去打高爾夫球的那些人。他們有辦法彈性休假,而且因為在飆車的嗜好上已投下很多心力,所以也很願意為賽車騰出時間。」坐在無聊的編輯辦公室裡,我覺得心裡一陣嫉妒的刺痛。說真的,為什麼我不能效法他們的作風?
我們每天都被銷售訊息轟炸高達三千五百次,也就是在醒著的時候,每隔十五秒就遭受一次侵襲。二○○四年,世界各地的公司行號砸在廣告上的錢,總共超過二千億英鎊。過去十年來,英國的電視插撥廣告從三千支增加到八千支,電視頻道則從四個增加到一百二十三個。二○○六年,全球總共寄出了六兆封商務電子郵件,平均每天寄出一千萬封垃圾郵件。過去三十年內製造的新資訊,比之前五千年所製造的還多。除此之外,每個禮拜還能看到更多新的播客(podcast)、雜誌、增刊、有線頻道,以及廣播電台。另外還有網站、網頁內容、部落格,以及附有額外光碟的影片,裡面載有首輪看不到的一些內容。就連英國髮型連鎖店Toni & Guy,也開始在美容院裡裝設無線寬頻,好像即使是剪個頭髮,都不能沒有這些網路設施似的,美容院消費者會在網路上跟朋友說,「哈囉,親愛的,我正在髮型網路上上網。」
很多社會裡最聰明的人士,都受高薪的吸引而為廣告及行銷業助陣,設法把產品推銷給我們。在以前的年代,這些人本來可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或作家的,可是如今他們大量生產出來的複雜資訊,只會搞得我們頭昏腦脹而已。在媒體及預測公司恒利中心(Henley Centre)工作的專家,擔心我們會被銷售資訊弄得耳聾眼花。如今還有一些效果的傳統廣告活動,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資訊過多激起人類產生的本能反應,只會使今日的問題更加惡化:因為當我們被過多的資訊搞得困惑不堪時,就會覺得不得不搜尋更多資訊,以釐清自己的困惑。
恒利中心所做的一個調查顯示,我們正在變成一個囤積資訊的社會,新媒體等同在家裡囤積一大堆報紙的一種瘋狂生活方式。不滿這種調查結論的人之中,有七○%表示,「資訊對我來說永遠不嫌多。」可是也有一半的人說,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或精力去使用已擁有的資訊。想因應這種資訊超載感的一種方式,就是利用多工作業,設法在人腦中塞進更多資訊搜尋器。如今二十幾歲的人大都一面看著電視,一面上網。可是他們到底看進去了多少?電視廣告商擔心觀眾的注意力和記憶力就像降落傘一樣飄忽,也就是:資訊接收得愈多,理解得就愈少。我會到路易斯博士小屋去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大概是第一個強調此問題的人。一九九六年他就指出了一種新的社會病,並給了它一個很時髦的醫學名稱:「資訊疲乏症候群」(information fatigue syndrome)。路易斯曾經為路透社做過一個全球性研究,針對一千三百個在資訊壓力下工作的生意人作調查(這些人當時承受的資訊壓力,或許比現在的人少些)。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告訴他說,因資訊過多而產生的壓力,已經傷害了他們的親密關係,造成失眠,並使他們對自己的決策力產生懷疑。很多深受其苦的人的因應方式,是去搜尋更多資訊,以求了解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路易斯,一個六十幾歲的老頑童,直接把此病徵歸咎於資訊革命。當時他新杜撰的這個疾病,是如此契合我們的時代,以致很快就有了它自己的神話。英國《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很快就訪問了一個「資訊疲乏症候群患者」,談她痛苦的五年復原之路。翌年,艾德華・威爾許(Edward Welsh)甚至在《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裡報導說,這個病徵最初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的情報員身上檢查出來的。
當心資訊狂躁症上身
最近的研究支持路易斯早期的發現。倫敦大學研究者的報告說,通訊過度對人的影響可能比吸大麻還糟。他們聲稱,如果你吸一支大麻煙,你的智商可能暫時會減少四分。可是只要處於隨時可收發訊息和電子郵件的狀況,你的腦袋甚至可能完全關機,智商的整個十分都會喪失,有點像夜晚睡不著而導致頭昏腦脹的那種感覺。研究宣稱,這是因為你不斷覺得必須停下來檢查信箱,以致把專注力都耗竭了。這種持續處於分心狀況下的心理狀態,使得我們察覺不出原本應可提高生產力的那些訊息,結果減損了應有的生產力。同樣的,我們也因耽溺於網路訊息而不注意身邊的人,以致破壞了社交生活。報告中並對這種強迫性衝動創造了一個時髦的名稱:「資訊狂躁症」(infomania)。要見證這種強迫性衝動的影響有多深,只要坐在一個熱鬧的Pub裡,觀察人們對同伴禮貌性關注的文明禮儀,總是在一個人的手機響起時就中斷了便可得知。我們每個人都愈來愈有資訊癖,不斷強迫性地想抓住每個片段的資訊,希望有一天能發現奇妙的事情,以弄懂其他一切事物。這種弔詭的情況,象徵了我們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富裕年代裡所面對的許多問題。我們的求生策略,在其他原始人類死亡之際,伴隨著我們度過了幾千年充滿匱乏及威脅的歲月,如今卻正在破壞著我們享受富裕生活的機會。資訊狂躁症的根源,其實就深植在我們的進化心理學裡,它也是驅策我們追求更多食物、工作、財產、機會,以及幸福的潛在破壞性驅力。在我們祖先進化的熱帶大草原上,你必須提高警覺,就像這是生存所繫似的。沒錯,當時的確如此,你必須充分運用你所擁有的資訊。人類的新奇感,包括面對新臉孔、新形體、新概念等,很少會像現今時代這麼多,然而這會引發恐懼和好奇之間的心理衝突。這種新奇感會激起早期人類強烈的好奇心,讓他們克服絕種的恐懼,而去探索可能大有所獲的問題,像是:「如果我踢那隻蜥蜴一腳,會發生什麼事情?」可是走在時代前端探索未知的人,報酬和流血的機會都是最大的。許多世代之後,在原始人類大腦裡演化出來的報酬系統,會鼓勵人們去收集資訊,而且這在過去的演化大賽中,已證明是個致勝因素。
醫學測試顯示,這種機制在我們大腦中仍很活躍,每次我們學習某樣事物,身體就會給腦袋這種鴉片的快感。二○○六年,一位南加州大學腦神經科學家所做的研究報告指出,當我們掌握了一個新觀念時,理解力就會卡嚓一聲釋放出一股腦部化學物質,用海洛因似的鴉片類(opioid)天然物質來犒賞大腦。作此研究的歐文・彼德曼(Irving Biederman)說,在人類大腦要求新資訊的區域裡,有一簇鴉片類物質接收器。他認為,無論何時,只要我們從這世界學到了一些東西,或是想到了重要或聰明的想法,進化就會讓我們變得很興奮,因為這能讓我們搶先競爭者一步。「人類本來就被設計成要吸收資訊的,」他說,「如果你想了解某種艱深的理論,這並不是什麼有趣的事,可是一旦辦到了,你就會覺得很開心。」直到最近,大腦才完全關閉了這種用化學物質激勵我們索取新想法的機制。這種獎勵系統因為一而再的緊迫要求食物或安全,變得自動失效了。躺在今日舒適的沙發裡,已經沒有掠食者或饑荒來威脅我們的閒暇,所以資訊狂躁症甚至能在最懶惰和最憎惡冒險的人身上發作,結果產生了對恐怖新聞、陳腐消息、名人八卦及媒體垃圾的大量需求。只要能提供新奇感,我們就可從中獲得刺激。我們不斷尋找新資源,以求獲得小小的刺激,因為新奇經驗每重複一次,做為獎勵而分泌的鴉片類化學物質就會隨之減少。彼德曼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掃描自願接受實驗者的大腦,發現他們每重複看一次同樣的圖片,刺激就會減少。媒體業對這個發現所做的反應,就是向我們推銷能更迅速引爆反應的刺激,努力逼迫我們產生「哇,你看!」的反應,讓我們對新奇感上癮得更嚴重,並縮短我們注意力的持續期。
被垃圾資訊所淹沒
除了這種立即性的影響之外,我們被資訊淹沒的文化,也可能扼殺了我們關機自救的欲望,而使得人類無法繼續進化。這種危險就隱藏在虛擬世界裡愈來愈多的誘惑中,因為虛擬世界提供了許多捷徑,使我們大腦能經驗到生物學上令人興奮的暗示,像是擁有迷人又順從的伴侶,而這本來是必須走進外在真實世界才找得到的。我們追求刺激的大腦電路結構不再需要我們離開沙發,就能獲得滿足。我們的潛意識、本能化的大腦,並不在乎這種刺激只存在於不值錢的電腦世界,甚至不在乎明知這只是廉價的贗品,卻仍盡可能地沉浸其中。這就說明了何以愈來愈多人寧願看色情書刊,而不願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追求親密的性關係;寧願玩虛擬的電視球賽,也不願在真實世界做運動;寧願看交友節目,而不願花時間與朋友交往。「我們正在消滅自己的腦幹,」新墨西哥大學一位演化心理學家吉歐佛瑞・米勒(Geoffrey Miller)這麼說。他認為,人類龐大的發明才能,如今都用在創造虛擬經驗上,而不是用在製造真實事物的工業上,像是建立水力發電的水壩等。他甚至表示,這正是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與任何先進的外星文明搭上線之故,從理論上說,這些外星文明應該一直在圍繞我們銀河系一千億星球的某個行星上進化著。我們的知性生活從來未能跨越虛擬世界的科技階段,而能不沉迷其中:因為虛擬世界裡的外星人都寧願在外太空玩Martian版PlayStation的而絕種,也不願去做在銀河系建立殖民地的必要工作。不過,米勒倒是認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基因差異論,或許能產生另一種可能性,亦即另一群新人類可能從虛擬世界的文化中進化出來,他們拒斥廉價電腦刺激的誘惑,在現實世界中利用科技而活得更有建設性。「那些能堅持的人會進化得更有自制力,更有良心,也更實用主義。」米勒說。不過他擔心,能建構出這種嚴格社會的人,也許只有強硬的宗教狂熱份子,他們留著長鬍鬚,戴著頭飾,痛恨閒暇、娛樂和自由思想。我則希望進化出來的是另一種人,他們熱情、幽默,而且奉行知足主義。
不管未來會發生什麼情況,如今我們的生活的確已塞滿了垃圾資訊。我指的不只是非法垃圾郵件,還包括我們每天猛發給彼此的那些既佔時間又無營養的電子郵件、電話及網路資訊。我自己的記者工作,也像其他所有的通訊業一樣,被堵塞靈魂的污染所淹沒了(當然,也很罪惡地在製造污染)。如果你在奶油蛋糕工廠工作,一定會吃很多奶油蛋糕。如果你在巨額融資公司上班,一定會賺很多錢回家。我以往十五年都在各種媒體裡挖掘事實和意見,所以每天腦袋都會捲進資訊漩渦裡。
不成為方便的受害者
我不是唯一遇到這種情況的人。我每週兩次搭火車到倫敦,車廂的寧靜總是被乘客拒接手機的聲音打斷,搪塞的藉口包括:「我現在正在家裡/辦公室裡,沒辦法接聽電話。」也有人明顯地推諉責任:「我想那是彼得・巴克雷的住家,可是他去度假了。」有純粹的迂迴戰術:「我正要進隧道……」(按鍵關機);還有人公然說謊:「我的火車嚴重誤點。」結果,血壓升高了,對商業卻了無助益。對家人或社交來電,人們答機時經常帶點粗魯的惱怒:「可是我現在也沒辦法,我人在火車上。」不過,米勒倒是認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基因差異論,或許能產生另一種可能性,亦即另一群新人類可能從虛擬世界的文化中進化出來,他們拒斥廉價電腦刺激的誘惑,在現實世界中利用科技而活得更有建設性。「那些能堅持的人會進化得更有自制力,更有良心,也更實用主義。」米勒說。不過他擔心,能建構出這種嚴格社會的人,也許只有強硬的宗教狂熱份子,他們留著長鬍鬚,戴著頭飾,痛恨閒暇、娛樂和自由思想。我則希望進化出來的是另一種人,他們熱情、幽默,而且奉行知足主義。
不管未來會發生什麼情況,如今我們的生活的確已塞滿了垃圾資訊。我指的不只是非法垃圾郵件,還包括我們每天猛發給彼此的那些既佔時間又無營養的電子郵件、電話及網路資訊。我自己的記者工作,也像其他所有的通訊業一樣,被堵塞靈魂的污染所淹沒了(當然,也很罪惡地在製造污染)。如果你在奶油蛋糕工廠工作,一定會吃很多奶油蛋糕。如果你在巨額融資公司上班,一定會賺很多錢回家。我以往十五年都在各種媒體裡挖掘事實和意見,所以每天腦袋都會捲進資訊漩渦裡。
不成為方便的受害者
我不是唯一遇到這種情況的人。我每週兩次搭火車到倫敦,車廂的寧靜總是被乘客拒接手機的聲音打斷,搪塞的藉口包括:「我現在正在家裡/辦公室裡,沒辦法接聽電話。」也有人明顯地推諉責任:「我想那是彼得・巴克雷的住家,可是他去度假了。」有純粹的迂迴戰術:「我正要進隧道……」(按鍵關機);還有人公然說謊:「我的火車嚴重誤點。」結果,血壓升高了,對商業卻了無助益。對家人或社交來電,人們答機時經常帶點粗魯的惱怒:「可是我現在也沒辦法,我人在火車上。」根本問題是,電訊讓我們成了方便性的受害者。對我的編輯來說,如果按下快速撥號鍵,記者就能隨傳隨到,那麼他很容易就會要求記者馬上去寫田鼠。因為這麼做實在太容易了。然而,如果這些編輯不得不花點力氣才追蹤得到他的寫作記者,而這個追蹤過程的不便性,假設會讓他經歷到要求記者寫作所造成不便性的百分之三,那麼這些編輯在打電話之前,就會多考慮一下了。在此我應該指出的是,如果自由工作者有一種罪行比「沒空」還大(對編輯說沒空,就像不斷追問編輯問題一樣,會惹惱他們),那就是在編輯委託你寫報導時經常說「不,謝了」。如果經常那麼做,他們就會完全不再與你連絡了。我的最佳解決之道,是熱情地把e-mail地址給每個人。我愛e-mail。如果編輯真的想要什麼東西,他們就得寫幾句話來要,這會讓他們的時間預算透支很多。但他們一時的不便,卻是我護城河裡救命的水。如今若說寫e-mail稍微帶點悠閒的味道,那是因為人家希望我們回覆得比手機留言或傳簡訊稍慢一點。
濫用方便性,助長了我們與手機的愛憎關係。在我不使用手機的這幾年,朋友用盡各種詞彙對我一再侮辱,包括慢性子、失敗者、怪胎、好命人,以及最後問道:「天曉得你怎麼認為自己擺脫得了這個?」麻省理工學院「勒梅森發明指數」(Lemelson Invention Index)的調查就不斷指出,手機是我們最痛恨的現代工具。勒梅森調查說,人們不喜歡手機,是因為「他們覺得被手機綁住了,要不就是覺得別人使用手機不當而感到困擾」。不過,當然,對我們自己來說,無論何時,只要自己覺得方便,就能隨意打手機給別人,倒是沒什麼不好的。但是我對我太太這麼做的時候,卻覺得有點罪惡感。她成功地實施了手機門禁制度,也就是除非她想打給某人,或特別在等某通電話,其他時候她一律關機。她這麼做一直都很順利,只有當我突然覺得有事要跟她商量,卻發現她沒有開機時,我就會發一頓因手機引起的典型小脾氣,在留言裡面對她吼道,「如果你不開手機,那帶著這個鬼東西在身上幹嘛?」當然,我們會為此大吵一架。製造晶片的英特爾公司所做的研究中,發現了更多誤用手機的證據,認為手機大大減少了人們對社交的依賴。五分之一的受訪者承認他們會故意遲到,因為他們可以在最後一分鐘用手機改變約會時間,四分之三的人則說,擁有手機讓他們「與朋友碰面的時間更有彈性了」(換言之,他們會故意遲到,卻不承認)。甚至有人怪罪手機會引起精神疾病。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Granada University)對幾百個十八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做了研究,宣稱其中四○%可能對手機上癮,因為一旦他們沒接到電話,就會覺得「心情極壞又傷心」,而關機則會「造成焦慮、易怒、睡不好或失眠」,甚至「發抖或消化不良」。此外,勞工常會依賴私人數位幫手,譬如黑莓機,所以常被稱為「黑莓族」,這表示他們可能已經對使用黑莓機上了癮。不過這究竟是上癮,還是因為追求更多東西,而引發社會壓力的一種惡性循環現象?
設定品質的門檻
想實行資訊節食,不一定得捨棄電視,不過多數人都會基於不同的理由,很快就決定要這麼做。這是因為電視這種商品有很多的附帶性,也就是能把愈來愈多功能都集中在一台電視上,可以接收地面、衛星和電纜的訊號,也能接收影片和所有視頻的訊息,同時還可以上網、收發電子郵件、傳資料,甚至能協助家庭記帳,多重功能替代了原本的單一功能。從不休息的電視對知足主義者是個超級大挑戰。擔心自己消息不靈通或社交孤立的人,會想接收這種永不中斷的資訊輸出,這就是電視所帶來的誘惑。
在電視還限制在大約只有四台時,看電視可說是一種共同經驗。大家看電視的選擇有限,所以第二天可以在商店或辦公室裡跟人聊所看的節目,而不用擔心講的是廢話,或根本沒看過最近大家都在討論的熱門節目。後來,由於可選擇的娛樂方式愈來愈多,所以大家的娛樂經驗已經暴增到不可能有共同性的程度,除非你一直都在一無遺漏地收看所有的節目。我敢打賭很多人都想這麼做。因為我們被資訊弄壞了的腦袋,會盡可能蒐集資訊來解除困惑。我們在社交上習慣競爭的腦袋,會想要所有最好最新的訊息。然而除非每週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收看所有的頻道,否則總會擔心有些更有娛樂性的節目自己沒有看到。想堵住這麼多資訊管道的唯一明智之舉,就是創造自己的知足策略。其實很多人已經這麼做了,方法就是在資訊品質上設定門檻,也就是訂下「不看爛節目」的規定。可是品質是種很不確定的東西,而且就像地心引力一樣,總是往下墜。不管怎麼說,面對不時出現的垃圾,看看又何妨?而且我們大可用更樂觀的態度來看待資訊娛樂,只要欣賞它的本性,享受它的本色就行了。然而娛樂資訊雖能帶來歡樂,卻會日久成習,改變心智,並有可能使人沮喪,可說再也沒有比它更廉價而豐沛的東西了。這種描述聽起來滿熟悉的,因為這就像飲酒一樣。
享受資訊娛樂時,要採取審慎的享樂主義者的態度,就像我們對飲酒應採取的審慎態度一樣,就能在資訊的享樂上找到可承受的解決之道,因為至少我們對飲酒的作法已經有經驗了。在所有有關飲酒作樂的標題中,大多數人都努力想讓酒帶給人生歡樂,而不想讓酒徹底毀了自己的肝臟。所以我們常給自己制定一些做得到的規定,像是天黑之後才能喝酒,只有週末才喝,或喝酒必須佐餐等。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為了資訊節食策略而制定一些生活習慣,基本上是要檢視哪些資訊管道對我們最合適,至於每天應該何時開機,也要有相當的紀律。
我們必須提高警覺,與飲酒相比,資訊娛樂過量時的負面影響比較不那麼立即可見,我們不會有口齒不清的宿醉,所以很容易忽略資訊過量而長期潛伏的後遺症。這主要牽涉到它可能壟斷我們大部分時間,而這些時間本來可以花在更能讓人生幸福的活動上。這些滋養性的活動,包括運動、嗜好、走出戶外享受大自然、發揮創意、與家人伴侶和朋友作有意義的相處、積極參與社區活動、開發自己的內在資源及精神層面……或是就單純坐著,不做任何事情。儘管我們大腦的原始天性就是容易被溝通吸引,但臨床研究顯示,想讓大腦皮質有活躍的反應,沒有上述滋養性活動是辦不到的。缺少那些活動,我們就會陷入躺在沙發上吃巧克力的不幸狀態中。工時過長不是工作,而是苦役
很多創業者都可能嘲笑馬泰爾太天真,錯失了這個可飛黃騰達的良機。這是個發財的大好機會,他卻沒有善加利用而放手讓它溜走了,隨之溜走的還有刺激的人生,包括事業成長、早餐會報、行銷活動、銀行會議、躍躍欲試的投資人、稅務顧問、人力資源問題,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事情,可以讓他從牛群、乳酪和果園中脫身。很少有英國人能拒絕這種工作繁忙的人生景象,因為它承諾要給你一個富有又有成就的未來。英國人比歐盟其他所有國家的工時都更長,平均每週工作四十二小時。這包括無數不支薪的加班日在內,而且即使英國的假日津貼在歐盟中是最低的,英國人仍然放棄了價值百億英鎊的有薪休假。
這讓英國人步向死亡。每週工作超過四十一小時的人,若與工時較短者相比,罹患高血壓的可能性會提高很多。曾有一份提交給布魯塞爾歐盟議會的調查報告,該報告預測說,繁重的生活壓力意味著,六○%的中產階級成人到了二○二七年時,都會罹患高血壓。日本人把長期過度工作而導致心臟病死亡的現象,取名為「過勞死」。英文也有新名詞,形容強打精神也要硬撐著工作的人,叫做「勉強上班族」(presenteeism)。那些人在辦公桌前坐了好幾個鐘頭,卻什麼事也做不出來,因為他們太累、壓力太大、太缺乏激勵、太不專心,或太沮喪,以致生產力低落。這比不上班還糟糕,因為職場中產生的碳排放量,有五分之一來自通勤。所以如果我們沒有生產力,還不如待在家裡工作得好。
工時過長,聽起來像是不得不為人幹活的一種苦役,但如今即使社會上很多有錢人,也認為工作繁忙是件很帥的事情。根據社會經濟研究協會的一項報告指出:「如今忙碌才有面子,悠閒則反之。」所以一定要硬撐到底。一九七○年代中期,很多文化評論家忙著提出警告,認為西方生活方式將受到一種很特別的威脅。他們認為,聖經啟示錄的第五位騎士✽,就是無盡的休閒。我們即將進入一個十足的美好新世界,那裡有高功能電腦、工廠自動化設備,還能用人人買得起的省力家電來做所有的家事。可是專家也提出疑問:那麼在科技為我們省下的時間裡,我們能做什麼呢?如果大部分的日常時間都不拿來從事生產的話,我們對自己會有什麼看法?如果所有的基本需求都很容易獲得滿足,我們要怎麼建立生活目標呢?會有那麼多的娛樂來充實我們的生活,好讓我們不致陷入厭倦、沮喪和精神上的荒蕪嗎?記得童年時看普遍級電視節目,當時專家預測,未來社會會發生很多不幸的事件,也預測無紙辦公室的來臨。可是如今職場上仍忙著砍殺樹木,也傷害著我們自己。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怎麼工作才算聰明?
所有這些有關職場的社會怪現象,讓很多人陷入這種困境。你可以叫我怪胎,可是我真的很喜歡我的工作。我發現工作很有收穫,至少大半時候是如此。當工作有趣的時候,真的讓人很快樂。就算有時工作並不那麼順利,反正我們偶爾也都需要覺得自己是個可憐蟲。事業成就之所以能造成這麼奇怪的困境,是因為它能增強我們的自尊心,讓我們擁有目標感。至於我,我還在工作中找到了一些真正持久的友誼。此外就是金錢,錢是我下半生不可或缺的東西,這樣工作就不會破壞我下半生的個人身心平衡了。
這就是知足主義者的挑戰:我們要能合理地享受社會所創造的舒適和方便性;要能正當地工作,而仍擁有自我空間和時間去感受滿足;雖然常有煩惱,但不致失控,仍能實現理想,而不必退出江湖。在這個一直強調工作的世界裡,彷彿在說:「要不就長時間工作,要不就乾脆不要工作,」我們究竟該如何做到知足的理念呢?在企業界裡,有沒有可能只在職位上作左右移動,而不是向下移動,也就是只擁有很知足的野心,而不必從整個企業體系中被刷下來?也許荷蘭的例子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荷蘭員工的工時在北歐是最短的,每週幾乎比我們少工作四小時。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對於怎樣工作才算聰明的看法,與我們大相逕庭。一項對全歐洲的研究發現,英國管理者認為一個員工經常加班,表示你肯獻身工作,所以是個高效能者。然而荷蘭人卻認為,如果你不能在正常時間內完成工作,那麼一定是你或你的工作出了問題。如果我們都到荷蘭去,也許就能多體驗沒有工作的生活了。但對於一直被慫恿著在長時間工作中混日子的英國人來說,享受荷蘭人那種少工作的日子,簡直就是浪費時間、自我耽溺,甚至是自甘墮落。
大約十年前,我正在研究報紙有關賽車的專題報導,這是英國蓬勃發展的一個小產業,喬和珍公關公司(Joe and Jane Public)花錢請人在車賽中駕駛自己的跑車和機車。我問布蘭茲・哈奇(Brands Hatch)賽場的公關人員,究竟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來駕駛這些車。「噢,都是些滿有錢的人,」他回答,「就是會在工作日去打高爾夫球的那些人。他們有辦法彈性休假,而且因為在飆車的嗜好上已投下很多心力,所以也很願意為賽車騰出時間。」坐在無聊的編輯辦公室裡,我覺得心裡一陣嫉妒的刺痛。說真的,為什麼我不能效法他們的作風?